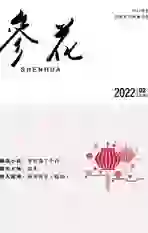“戏中戏”在电影中的叙事美学分析
2022-02-23甘世文
经典叙事原理“戏中戏”为文本叙事带来引人入胜的剧作效果。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进行剧作方法论研究,以日本电影《W的悲剧》为例,着重分析“戏中戏”结构蕴含的叙事美学。
一、何谓“戏中戏”
“戏中戏”作为一种剧作结构和表现手法,由来已久,古已有之。“中国现存最早的戏中戏作品是作于1435年的《神仙会》,晚于印度而约与西方同时。”[1]明朝至清朝中期,“戏中戏”手法在各类戏剧流派里得以大量运用。国外文艺作品中,“戏中戏”的成功运用在剧作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中文艺复兴时期,在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哈姆雷特》第三幕中上演的“贡扎果之死”当属经典。
在戏剧理论中,“‘戏中戏’是一种由上位系列的一组戏剧角色向另一组戏剧角色表演(下位系列)的戏剧。通过向文本中插入第二个虚构层面,剧作家在内层面上复制出外交际系统的表演情境。”总结而言,“戏中戏”是艺术创作中常见的一种套层结构,指在戏剧之中又套演主干故事之外的另一个故事。[2]
“戏中戏”既是戏曲戏剧惯用的叙事手法,也是电影叙事学中一种较为简单的套层结构。鉴于戏中之“戏”形式多样、界定不一,以及套层结构有多重分类。本文提到的“戏中戏”定义如下:在一部电影中,外部故事为电影主干,且承担主要叙述的功能;内部故事为套演的戏剧或电影片段。内部故事嵌入外部故事之间,形成套层结构,且代表一种套层性叙事手法。
“戏中戏”基于套层结构的多层次叙事原理,在本事叙事中辅之以他事,将主要文本与嵌入文本的多重时空叙事有机整合在同一作品中。随着影视艺术的发展,“戏中戏”在影视创作中也屡有实践。这一戏剧创作技巧沿用至今,发挥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二、结合《W的悲剧》分析“戏中戏”蕴含的叙事美学
《W的悲剧》采用了“戏中戏”的套层结构,全片围绕剧团排演《W的悲剧》这一叙事主线展开。主叙述层讲述了剧团年轻女演员三田静香的成名之路与爱情故事,嵌入文本即次叙述层则截取发生在和辻家的一场悬念迭生的谋杀案片段。现实与幻想两套叙事话语彼此独立又紧密交织,穿插展现、互文双关,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主题意蕴和情节内涵。
(一)隐喻之美
“戏中戏”作为一种剧情结构和表现手法由来已久,尤其在戏剧发展历程中,诸多经典剧目中均有“戏中戏”。电影借鉴戏剧的“戏中戏”手法,一定程度上可以唤起观众的审美移情。由戏剧积累而来的美学趣味,在电影中同样可以通过现实与虚幻之间的间离、交融,嵌入文本与主干故事之间的映照、渗透,带给观众多层次的美学体验。同时,“戏中戏”扩充了电影的艺术空间,丰富了剧作的表现手法,并成为表达创作意图、凸显电影美学的有效手段。
热奈特把叙述层次的功能分为三种,其中,第二种便是纯主题关系,“不要求元故事和故事之间存在任何时空的连续性:可形成对比或类比的关系。”[3]雷蒙·凯南论述次故事层叙述的故事对主敘述层所起的作用时,也谈到了“为主题服务的作用:次故事层和故事层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是类比的关系;即相似和对比。”[4]
《W的悲剧》中,舞台故事与现实生活这两条叙事线索交错,二者之间的主题类同、事件相似。舞台上的角色与现实中的人物情感有机交融,并隔空对话。于亦真亦假、亦虚亦实之间,通过主人公在“塑造戏中戏的角色中来表现和完成自己的性格”,[5]更巧妙地通过戏中戏的隐喻和类比,直观化映射主题,达到丰富题旨内涵之意。
例如,《W的悲剧》这部电影与戏中戏同名。“W”有两重含义:一是戏中的谋杀案发生地点为和辻家,其日文发音字头便为“W”。二是woman即女性。这意味这是和辻家的悲剧,更是电影里所有女性之爱的悲剧。
电影主题因“戏中戏”结构,更加突出了其深思性和哲理性。“悲剧中的悲剧,演员中的演员,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生活体验揉进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中。”[6]电影最后,真相大白,三田静香前途叵测。但她拒绝了森口昭夫的再一次挽留,在那寂寥的掌声中,坚定地朝着自己的女演员梦想走去,这份坚定更加加剧了三田静香的悲剧性色彩。
“戏中戏”通过主题的隐喻,使本不相关的两个文本得以紧密相连,隐喻不仅带来了风格观感上的朦胧含蓄之美,更使原本抽象的悲剧主题得以具体化,并在“戏中戏”片段不断的排演中被强化。从和辻家的悬疑案件到行业的明争暗斗,在统一主题的挈领下,借助隐喻的桥梁,观众将舞台与现实结合,既能由此及彼,延展丰富观影空间,联想个体生活经验,达到移情之效;反过来也有助于主题的突出和深化,使作品内涵更深刻与鲜明,而这也正是“戏中戏”带来的隐喻美学价值所在。
“戏中戏”带来的隐喻修辞增加了电影文本本身的审美价值,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创作者的初衷与情感,不同文本因隐喻而呈现出一种更具感染力的朦胧美。
(二)互文之美
作为电影套层叙事的经典结构,电影中的“戏中戏”在两重时空交错叙述,虚构文本与现实悲剧宛如房中之镜,镜中之房,为原本单一的叙述方式增添了多重意象,形成了互文表达。
互文一是指“上下文各有交错而又相互补足,交互见义并合而完整达意”,[7]指一种特殊修辞效应的汉语修辞手法,二是指与“Intertextuality(互文性)”译名相通的文本理论,即结构主义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最早提出的西方互文性理论。“汉语的修辞互文本质上是一种构成成分共享的互蕴结构互文,互为存在前提的互动结构互文,而西方的文本互文强调的也是其互涉互动的结构理念,关注的是多向度交互文本结构的生成。尽管没有严格意义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机构关系,但‘参互成文、合而见义’的结构理念于二者是完全互通的。”[8]“参互成文、合而见义”这一叙事策略在电影中经由“戏中戏”得到凸显,应用如下。
首先,内外文本层的互文呼应体现在叙事暗合上。“三田静香——摩子”这一复合形象是不同时空的同一人物,是同一主体的AB两面。三田静香与角色摩子在人物命运上不仅具有相似的悲剧性,在人物动作的选择上更是高度一致,都是出于某种目的而不得不选择替人“顶罪”,并在真相大白后付出情感或名誉上的惨痛代价。两个文本之间的互相指涉,形成动态共生的互文效果。
其次,不同文本之间相互参照带来的补充表达,也增强了电影的叙事张力。“戏中戏”里,摩子是和辻家谋杀案的中心人物,更是解开这起谜案的关键主角。而现实空间发生的种种争斗,也正是三田静香为了赢得同等的舞台身份所致。为了取代菊地香,三田静香从只有一句台词的女佣成为梦想的女主角摩子;为了效仿羽鸟翔,从籍籍无名的新人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三田静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两难抉择,她面临的困境在其化身为摩子时,融入了剧情并得以强化。三田静香在纯真自我和成名机会之间的迟疑茫然,摩子在自身名誉、性命和保全母亲、家庭之间的痛苦纠结,更是将人物困境推到了极致,使人物命运最终的发展轨迹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内层结构的核心段落中,淑枝得知真相,刺死道彦,随后自杀。摩子抱住淑枝哭诉,“谁叫我们是女人,是女人呢……妈妈,我不能讓你死呀……”摩子的台词也正是三田静香作为女演员的内心的所思所想。无论是戏剧中家境优渥、受到良好教育的和辻家的千金——摩子,还是现实里独自闯荡、生活不易的无名女演员——三田静香,都在电影中呈现了悲剧性。
因此,在嵌入文本与元文本的互文修辞中,电影《W的悲剧》的主题控诉与情感映射相互交织,产生了极为强大的互文效果。
(三)间离之美
电影中,现实与虚幻两条情节线并行发展,主干故事围绕排演戏剧《W的悲剧》展开。通过对内层文本建构过程的展现,强调了其潜在的虚拟性,带来间离式审视下的文本解构。
布莱希特提出非“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间离说”,强调对幻觉的打破,营造疏离关系,激发观众觉醒。这使观众、演员、角色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建构,并以此达到一种陌生惊讶的效果,促使观众理性地认识其中内涵。
以淑枝决定自首的段落为例,羽鸟翔饰演的淑枝在舞台上坦白真相时顿住了,“杀死伯父的是我,摩子她……”为其提词的三田静香和羽鸟翔一起说出台词,“是当了我的替罪羊。”羽鸟翔借着淑枝的角色坦白了现实中三田静香为自己顶包的事实真相。其心理处境被强化,传递出痛苦压抑的情感。这一“戏中戏”的运用使虚构文本中的矛盾得以延伸与激化,羽鸟翔脱离淑枝身份而存在,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间离的间离,由此呈现出一种陌生化审美的独特艺术魅力。
电影一开始便早已以间离的方式解构了选角、排练和巡演过程,从而构建了观众对于现实故事的认同。因此,当这一段落出现时,观众早已从淑枝的戏剧命运中跳脱出来,转而关注三田静香为羽鸟翔顶罪之后,二人的命运发展。观众自始至终处于一种清醒的评判态度,在观影时不被情节迷惑,反而对叙述背后的主题寓意产生了思考。
总而言之,“戏中戏”这一经典的剧作手法,以其独特韵味和艺术张力,在嵌入文本与主干故事的来回切换间,带给观众深层次的理解思考,扩充并拓深了电影的审美效果。
(四)嵌入之美
根据叙事学理论家普林斯的观点,嵌入叙事是指“叙事中的叙事”,与之相对的是框架叙事,即为嵌入叙事提供背景的叙事。[9]
在电影《W的悲剧》中,聚焦于初出茅庐的年轻女演员三田静香的明星梦,她为出演话剧《W的悲剧》付出爱情和成长的代价,最终登上舞台,形成了电影框架——嵌入式叙事结构,即本文论述的经典“戏中戏”结构。
结合电影《W的悲剧》分析,和辻家原本悠闲美好的新年度假,被一宗谋杀案的发生打破。这一“戏中之戏”作为嵌入叙事部分,以话剧形式嵌入在三田静香的成长线索这一框架叙事之中。嵌入故事与基本框架使电影呈现出丰富的形式面貌,提高了叙事的表现力。其中,最为显著的特性自然是“戏中戏”的套层叙事,形成了类型杂糅。
电影中,嵌入文本选取的是日本女作家夏树静子的代表作——同名推理小说《W的悲剧》。围绕“谁杀死了大外公”的谜团而展开,屋外大雪纷飞,屋内暗流涌动,凸显了“戏中戏”紧张刺激的氛围。而元文本则通过对都市图景的构造与对娱乐圈状貌势态的描摹,侧面展现出那个年代东京影剧行业中女性演员的众生相。
“戏中戏”的悬疑探案风格与外层文本的现实主义剧情风格通过套层结构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使不同类型之间的风格过渡自然,呈现出复合混杂的风格观感。且带来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融合,因为不论嵌入者或被嵌入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形态与特性,只是在新系统中达到相得益彰而已。它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我国古典美学所说的‘和而不同’,或者说异美相济。”[10]
在“戏中戏”结构中的类型过渡,相较于类型电影中的类型杂糅而言,更流畅贯通,舞台的存在成为类型转化的绝佳通道,观众的心理接受有章可循,而非毫无征兆的切换导致的突兀生硬。嵌入文本与元文本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差异与协调的平衡,而这正是“戏中戏”的嵌入带来的叙事效果。总而言之,电影中“戏中戏”的使用,带来了内外叙事文本的分层。作为重要的叙事策略,由此使风格各异的不同文本自然并置,嵌入叙事的形成带来了生机共存的兼容之感。
三、结语
“戏中戏”这一叙事策略在电影叙事中应用广泛,作为从戏曲戏剧演变而来的特殊叙事结构,“戏中戏”的套层叙事构建了真实与虚幻的两重意义空间,在电影本事中形成了两个彼此独立又互相影响的文本。嵌入文本在重构的叙事作品中,通过二者之间不断的互文叙述,强化了其内涵意蕴与美学意味。同时,次叙述层为主叙述层带来的补充叙述和主题审视,相较于单一叙事而言,增强了电影的表达效果。
本文结合《W的悲剧》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分析总结“戏中戏”的叙事美学效应。“戏中戏”这一经典叙事手法在叙事上功能多样、应用灵活,不仅丰富了电影本事的叙述手段,拓宽了艺术时空的表达空间,更以其蕴含的艺术魅力,为观众提供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李扬,齐晓晨.清中期以前“戏中戏”的发展[J].文化遗产,2010(02):75-81.
[2][德]曼弗雷德·普菲斯特.戏剧理论与戏剧分析[M].周靖波,李安定,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3][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
[4][以色列]雷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姚瑞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5]周远.巧妙的类比和对比——《卡门》和《W的悲剧》的结构艺术[J].电影评介,1987(02):29.
[6]徐冰.《W的悲剧》及其“套层结构”[J].电影评介,1987(01):22-23.
[7]舒新城,等.主编.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8]祝克懿.互文:语篇研究的新论域[J].当代修辞学,2010(05):1-12.
[9][法]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M].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0]黄鸣奋.嵌入美学与数码艺术[J].艺术百家,2013,29(04):59-67+13.
(作者简介:甘世文,女,硕士研究生,中央戏剧学院,研究方向:电影艺术)
(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