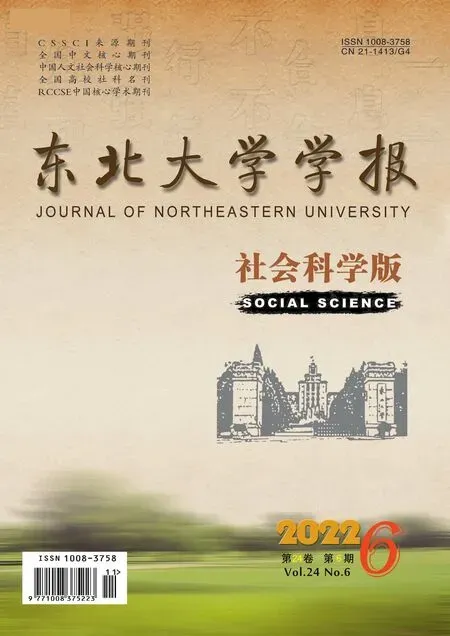唐娜·哈拉维伴生关系思想研究
2022-02-17李芳芳
李 芳 芳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自然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向来有两种对立的立场: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实在论虽有各种形式,但在自然的问题上他们的基本立场相似。实在论认为存在着一个自然世界,且能够独立于人的感知行为而存在,自然独立于心灵、文化、语言,是感知的实在;而我们关于自然的理论或陈述的真理性取决于自然世界本身,我们获得理论和陈述的实践本身不会影响到这个理论或陈述所表征的自然实在。简言之,自然是独立于人类的实在,自然实在决定着人类所建立的理论的真理性。社会建构论则与实在论相反:我们对自然的认识是基于社会文化的建构,特别是出于利益的建构;对自然认识的真理性取决于社会协商,真理是相对的,因此,社会建构论也常常与相对主义画上等号。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争论在自然问题上呈现出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站在实在论的立场,自然是本体论上的实在;而站在社会建构论的立场,社会或文化才是本体论上的存在,自然则是后天建构的。从实在论和建构论的两极看,我们关于自然的理论要么还原为自然实在,要么被解释为社会文化的建构。换言之,对于实在论而言,文化外在于自然,自然可以影响社会文化,但社会文化与自然无关;而对于社会建构论而言,社会文化单方面决定着自然。然而,无论是实在论还是社会建构论,都预先假设了自然与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两个世界,自然与文化是相分离的存在。
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提出伴生关系,重新梳理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为化解二元论找到一条新的路径。
一、自然/文化二分的根源:人类中心化与自然他者化
二元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根据差异将另一方边缘化,而将自身中心化,明确地说,二元论产生于人类的中心化与自然的他者化。以灵长类动物学为例,有人认为灵长类动物学是对猴子、猩猩等类人猿动物的揭示与发现。与“发现”的观点相反的是,哈拉维认为灵长类动物学是建构的产物,自然世界是人类工作的一项特殊成就。在考察了“二战”前后的灵长类动物学后,哈拉维指出,灵长类动物是什么,如何被描述,与彼时的社会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灵长类动物学是特定“秩序”(order)建构的产物。这种秩序是在对差异边界的划分协商中建立的,更为明确地说,灵长类动物学是在东方与西方、性与性别、自然与文化的差异基础之上所建立的二元论秩序下建构的产物。受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影响,哈拉维将灵长类动物学称之为“类人猿东方主义”[1]10。
我们对灵长类动物的理解观念是由特定的认知和描述实践所建立的,这些认知和描述实践总是浸润着人类特定的文化和象征意义。
首先,“类人猿东方主义”是指灵长类动物学将猴子、猩猩等类人猿的他者化。哈拉维指出,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种建构的核心是将自然建构为“他者”。
其次, “类人猿东方主义”揭示了他者化的最终结果是使类人猿彻底沦落为客体、 资源。 哈拉维反对这样一种自然观: 将自然客体化和资源化, 即把自然当作是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 可开采的对象。 在哈拉维看来, 自然不是一个有待人类涉猎的场所, 不是人类守卫或储藏的宝藏; 自然不是隐蔽的, 等待人类揭示或发现的存在; 自然也不是供人类阅读的, 以数学或生物医学编码的文本。 然而, 我们却发现, 在特定的文化特权下, 自然必然会沦为客体和资源,成为完全消极、 被动之物。
最后,当自然降格为客体,却可以反过来建构、巩固特定文化权威,成为特定文化权威的基础。例如,“二战”前的灵长类动物学将雄性铭写为一个群体的支配者,将雌性铭写为一个群体的从属者。雄性支配者及雌性从属者的确立是依照父权制文化而对自然铭写的结果,然而这一结果却被当成是自然本身,即被文化铭写的自然变成真正的自然,被铭写、被父权制文化建构的过程悄然隐退,自然反过来起到巩固和捍卫父权制文化的作用。雄性——支配者、雌性——从属者,这一被文化铭写建构的自然现象,演变为生物共同体的本质,成为了人类社会异性恋和父权制的自然起源和本质基础。“类人猿东方主义”就是指,灵长类动物学的建立是一个基于等级秩序的建构过程,既是一个他者的建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的建构过程。“类人猿东方主义,就是以他者为原材料,建构出自我的过程;是在对自然的挪用中,生产文化的过程;是从动物的泥潭中,生长出人类的过程;是从默默无闻的有色人种中,澄清白(人)的过程;是从女人的身体中,分离出男人的过程;是从性(sex)为原料精心制作出性别(gender)的过程;是通过激活身体,而凸显心灵的过程。”[1]11
当自然成为消极被动的资源时,自然与文化之间此消彼长的张力以及互相建构的关系却隐而不现了;在资本主义父权制、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文化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之后,被遮蔽不见的还有与其他文化形式相联系的自然,比如东方的自然、有色人种的自然、女性的自然等。我们所熟知的自然只是与单一文化特权彼此深刻建构的自然,虽然这个自然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性别(男性)中心主义等令人不满的烙印,但是,在历史长河中,这个自然又是我们离不开和无法摆脱的自然。
二、 自然与文化的伴生关系
哈拉维对于自然,持有建构论的立场,但她又不同于社会建构论,在她看来,自然与文化、自然与社会是同一个建构过程的结果。而社会建构论将社会或文化置于本体论的高度,将自然看成是社会或文化的建构,这是哈拉维所反对的。哈拉维认为自然是实践建构的产物,自然是在与社会或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彼此形成的,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能否建立一种与自然的非客体化的关系?
等级关系的建立,是基于自我的中心化,基于对自我的提升,从自我的视角观看他者,认识他者,他者成为了被观察者,成为了认识的消极对象。2003年,哈拉维出版了《伴生物种宣言:狗,人,及其重要的他者》一书,以“狗—人”关系为例,哈拉维描述了各种人与狗之间的故事,刻画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多种多样的互动形式,这些丰富的互动形式提供一种对待非人类的既非拟人化也非客体化的方式,这是一种将非人类还原为行动者(actor)的方式。在人和犬类结成的伴生关系中,人类与犬类是在共同栖息的基础上,共同进化、互为构造的,在人与宠物相处的日常中,陪伴和嬉戏的背后是深刻的、对物种间不可还原的差异的尊重,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交流和理解;对澳大利亚牧羊犬、比利牛斯犬等这些犬类的历史追溯,揭示了“纯种”狗只是一个浪漫传说,品种是建构的,是人类与犬类共同建构的产物,历史也是如此,重要的是“为了塑造更有活力的多物种未来,而学会如何继承艰难的历史往昔”[2]。2008年哈拉维出版了《与物种相遇》一书,深化了伴生关系的思想,人类与非人类、文化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伴随生成”(becoming with)的关系,“主体与客体在相遇之舞中塑造而成”[3]4。
伴生关系的核心在于:第一,关系是最小的分析单位。在主体与客体、人类与非人类的问题上,它将人是什么的问题,转变成了人在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中生成了什么、变成了谁。狗是人之为人的重要他者,并不是说理解人类的最好方法就是去考察人类与犬类之间的关系,哈拉维以毫不起眼的“人—狗”关系为例,想要说明“人是什么”是在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中浮现出来的。人与狗,只是无数伴生关系中的一种,所有的伴生关系都是真实而具体的存在。所有的他者都是重要的,因为离开了他者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离开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人类是什么便无从谈起。对于实在论或社会建构论来说,关于自然的知识,是人类对自然的表征或社会的建构,自然本身要么是独立的、与人类或主体相分离的存在,要么是被建构的毫无主动性的客体。对于实在论来说,关系是外在性的;对于社会建构论来说,关系是被动的或等级化的。
第二,伴生关系的双方存在着不可还原的差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对事物定义的一般形式就是“种+属差”。genus表示种,希腊文generic表示属,等同于英文的species,“物种”(species)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意义上就是事物的属,按照亚里士多德传统,种表示普遍的,而属表示的是差异,因此,物种是对事物差异的划分,隐含的是当我们提到伴生物种时,意味着互为伴生物种的双方不是同类,是不同的两个或多个物种。哈拉维强调理解伴生关系的前提,就是承认互为伴生关系的双方之间的不可还原的差异。物种是多样而具体的,可以包涵人工物、有机物、技术和人类等。哈拉维曾因《赛博格宣言》(ACyborgManifesto)名震一时,赛博格和“狗—人”,实际上是两种平行的人与他者的关系[4]。赛博格代表的是“人—技术”的关系,“狗—人”则指确确实实的狗与人的关系,赛博格和“狗—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文化。
三、伴生关系的哲学基础:怀特海过程哲学
拉图尔曾说“我们从未现代过”[5],而哈拉维则直指现代性的心脏,指出“我们从未成为人类”[3]4,在这里,哈拉维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更为基本的存在,主体和客体并非先验的存在,主体性和客体性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之中。在形成伴生关系的认识中,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哈拉维将伴生关系视为本体意义的存在,奠定了理论基础。
怀特海哲学始于对康德哲学的反思。众所周知,康德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哥白尼将“地心说”转变为“日心说”掀起了科学领域内的一场巨变,康德也发起了一场形而上学的整体革命。在康德之前,形而上学遭遇了合法性危机,其普遍性和必然性遭到了质疑,康德哲学的目标之一就是拯救形而上学的危机。为奠定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康德在“自在之物”与“现象”之间作出了严格区分,“自在之物”超越了人的认识能力,是不可知的,人只能认识纳入人先天直观形式的“现象”。如此一来,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就转变为我们能够经验到什么,而形而上学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也就转变为我们的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能否提供普遍必然性的基础。最终,通过一系列精妙的论证,康德将形而上学的普遍必然性植根于人主体自身的认知机制之中,“人为自然立法”就是他“哥白尼式的革命”所达到的一个重要结论。实际上,“人为自然立法”标志着一个从人的主体性进展到客体的过程,虽然康德自诩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当哥白尼的“日心说”戳破了人类是宇宙中心的幻想之后,康德又重新将人置于自然的中心。拉图尔曾批评以布鲁尔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是康德式的,社会建构论没有把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基础置于主体的认知机制之中,而是把知识的有效性置于社会之中,利益关系、社会结构成为了知识的基础,虽然其方法不是康德式的先验分析,而是形而下的经验描述,但是其解释知识的形式仍然是康德式的以主体进展到客体的过程。如同康德“人为自然立法”一样,社会建构论用主体的社会文化建构了自然,不仅以社会为自然立法,更进一步的是,康德的自在之物在社会建构论那里彻底消失了,自然只是被建构的消极被动客体。而怀特海过程哲学则是对康德哲学“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又一次翻转。
康德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主体的认知迈向客体的机制,怀特海则颠覆了这一机制,他将康德式的问题“我们如何规整世界”转变为了“世界如何规整自身”[6]。康德哲学的先验分析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怀特海哲学取向是本体论的,也就是说,康德要回答的问题是认知主体如何通达客体,而怀特海要回答的问题是事物的一般本体论结构是什么以及如何形成的。康德以及康德式的社会建构论,都恪守着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和客体、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界限,而怀特海则认为主体与客体、实体与属性的划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是有益的,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却是不恰当的。怀特海以一种非二元论的方式再一次重整了形而上学。
怀特海拒绝机械论世界观的实体观念,“实体”的观念在西方哲学中源远流长,经由笛卡尔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划分,逐渐成为机械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笛卡尔的观点,所谓实体就是“除了它自己,不需要任何东西便可存在”[7]10,换言之,实体是独立而永恒不变的。笛卡尔又将实体分为两类,精神的和物质的,既然实体是独立而永恒不变的,那么就意味着存在着独立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而整个形而上学的体系便是处理这独立且不变的实体问题,最终造成了难解的身/心二分等一系列二元论的难题,整个形而上学体系也变得裹足不前。在怀特海看来,除笛卡尔的实体之外,休谟的“印象”、康德的“综合”等都是如此,这些概念导致了形而上学局限在这些不可分析的终极之中,停滞不前。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怀特海以“实际实有”(actual entity)取代实体,“实际实有——亦称实际事态(actual occasion)——是构成世界的终极实在事物”[7]27。究竟何为“实际实有”呢?这里有两点需要澄清:首先,以“实际实有”为基础的形而上体系不同于康德式的以主体认知机制建构客体世界的方式,怀特海把“实际实有”规定为一个自我构成或自我决定的框架,因此,他的形而上学研究的是“世界如何规整自身”;其次,“实际实有”不同于笛卡尔式的实体,在笛卡尔那里,实体是预先给定,永恒不变的,而怀特海的“实际实有”并不是预定实体,也没有预定的结构。
“实际实有”能够取代实体成为形而上学的核心,根据在于怀特海将实在理解为“过程”(process),怀特海认为笛卡尔式的实体是不存在的,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过程是指“实际实有”生成的过程,而任何一个现实实有都是由与其他“实际实有”相互关联而成的,一个包含着另一个,整个世界就是由各种实际事态、各种“实际实有”相互关联、相互包涵而形成的有机系统。因此,怀特海的哲学也被称为过程哲学。哲学所要回答的“实际实有”“是什么”的问题就变成了“实际实有”是“如何生成(becoming)”的问题,“存在(being)是由它的生成构成的,这便是过程原理”[7]34。“实际实有”总是相互包裹,互相摄入(prehesion)的,“摄入,来表达一个实际实有借以造成它自身对他物凝聚的那种活动”[7]84。一个“实际实有”以它的主观形式、主观目标对前一个“实际实有”的摄入,就创造了新的“实际实有”,过程也就是创造性的、向未来开放的过程。因此,“实际实有”的生成是一种关联性的创新的生成。对“实际实有”的哲学追问也就变成对其生成的关联性的哲学追问。也就是说,实在的个体事实上虽然是具体的、特殊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对这个实在的具体性、特殊性进行哲学解释,哲学所能解释的是构成这个实在的“实际实有”、摄入和联系。实体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比如我们要了解或描述特定的实在——如金属或岩石,但这不是哲学形而上工作所要解答的。以“实际实有”代替实体作为其哲学的核心观念,所体现的是怀特海对“关联”(nexus)的推崇,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哲学,它所强调的是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事物生成的基础就是关系,事物的性质也是在关系中生成的,因此,与性质相较,关系具有优先性。
四、伴生关系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消解
对于哈拉维而言,怀特海的“实际实有”、摄入、关联,为她建立技科学的关系本体论,提供了哲学上的地基。
怀特海对实体的拒绝,不仅批评了以实体为核心的哲学传统,实际上也起到了对科学知识社会建构论的社会实体观念的质疑作用。社会建构论预设了社会实体的独立存在,并以此为其科学知识建构的解释基础,而怀特海则利用实在生成的过程说明了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实体,社会实体也是在关联中通过摄入而生成的。生成性也表明,“实际实有”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随着对其他“实际实有”的摄入而不断流变的,那么,社会实在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实际实有”表明,主体与客体都不是预构实体(preformedentities),它们都是生成而流变的。站在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基础上,哈拉维认为生物决定论或者社会建构论,都犯了怀特海所说的“误置具体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8]。所谓具体性误置指的是一种把抽象误认为是具体的错误。“实际实有”因摄入和关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是,人们常常忽视了动态的过程,抽象出某些范畴,然后就认为这些范畴就是具体的实在。因此,生物决定论或社会建构论的错误就在于:一来是把“自然”和“社会”这样的临时性、局部性的抽象范畴错当作具体而真实的世界;二来是误把后果视为是预先存在的原因或基础,所谓生物或社会都是生成的,生物和社会都是在相互关联中双向建构的。
哈拉维伴生关系的核心指向——“伴随生成”,受怀特海的影响颇深,正如怀特海过程哲学所表达的,存在不会先于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存在,实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过伴生关系,哈拉维揭示出主体和客体是在关系之中生成,预先并不存在,也没有单一的资源、统一的行动者或最终的结果。伴生关系,体现的是“跨越物种之间的、人类与非人类的本体论的编舞”[9]。
哈拉维通过伴生关系从根本上消解了主体与客体的划分。以主客二分为标志的二元论,成为了一个伪问题,二元论并没有本体论上的基础。
首先,他者、非人类不是客体与资源。他者或非人类是能够引发德里达所谓的“伦理中断”(ethical interruption)[10],以非客体化也非拟人化的面貌出场。德里达对动物的思考给予了哈拉维很大的启发。德里达在他的《动物故我在》(TheAnimalThatThereforIAm)一文中,从他与动物(猫)的相遇所引发的一系列情感体验出发,探讨了动物作为他者,以及人对动物所负有的伦理责任问题[10]。德里达认为与动物(猫)相遇时本能的“羞耻感”引发了伦理中断,即这只猫的出现使人陷入思考,中断了日常的活动,伦理中断被认为是决定一个存在是否是伦理上的他者的决定性因素。哈拉维指出,主客体的划分,是由等级关系所造成的错觉。以自我、人类为中心,从自我、人类的视角去观看和认识他者、非人类时,他者或非人类就被边缘化,被贬抑为被动消极的客体或资源,这种认识方式,是基于自我与他者、人类与非人类的等级关系,而等级关系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忽略了他者所引发的“伦理中断”,误将行动者认作是客体。
其次,哈拉维认为伴生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对不可还原的差异的尊重,而尊重体现在与非人类或他者的交流上,行动者之间的交流并不只依靠语言,更重要的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了解、认识他者,而不是“观看”他者。换言之,认识的产生是异质性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再次,主体与客体在伴生关系中生成。在伴生关系基础上的异质性实践不仅制造了知识,也制造了主体和客体,也就是说主体与客体是建构生成的,而非给定的。哈拉维将主体与客体看作是生成流变的存在,而非先验固定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变成了主体如何生成、变成了谁的问题;客体是什么的问题也变成了生成了什么物的问题。
最后,伴生关系强调了主客体生成的相关性。通过伴生关系,哈拉维强调了主客体的伴随生成的关系:主体如何生成以及变成了谁,是伴随着非人类行动者而言的,主体的生成流变是由客体影响的;同理,客体如何生成以及变成了什么,也与人类行动者密切相关。换言之,伴生关系强调的是主体与客体是双向建构的。主体与客体是生成的,也就意味着事实与价值都内化于知识客体之中。伴随生成的客体不再是一个中性的、独立于主体的客体,而是承载着价值与意义,深陷于多重意义网络中的客体。
通过对伴生物种和伴生关系的阐释,哈拉维提出了一种代替自我中心化、他者边缘化的处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新方式。在自我与他者、人类与非人类、文化与自然之间找到了一种既非相对主义,又非实在论的处理方式,为朝向一个去人类中心后的世界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既然人总是与他者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是时候该反思和重建与这些重要他者的伦理政治模式了。2016年,哈拉维出版了《与麻烦共在》一书,延续了她伴生关系的思想,在该书中哈拉维提出用神话小说中的“克苏鲁纪”(Chthulucene)代替人类世或资本世,来描述人类的处境,“克苏鲁纪由持续发生的多物种之间伴随生成的故事和实践构成……与人类世和资本世话语的主流叙事不同,在克苏鲁纪,人类不再是唯一重要的行动者,其他所有存在都会在这个世代作出相应的行动。秩序被重构:人类与大地共在,生物与非生物是大地的主流故事”[11]。
五、 结论与反思
通过对伴生关系的阐释,哈拉维指明了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人工物之间双向建构的关系,实现了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真正的对称性。
与其说哈拉维是一位后人类主义者,不如说哈拉维是一位反人类中心主义者。后人类主义思潮论域极为宽泛,物质女性主义(material feminism)、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超人类主义等都可囊括在“后人类”这一标签之下。后人类主义的兴起与当代以生命科学、信息科学为代表的高科技社会息息相关。确实,“人—技术”的关系是当代最具决定性力量的伴生关系,早在《赛博格宣言》中,哈拉维就宣告赛博格时代的来临。但是,她的赛博格并不是指向一个人被彻底技术化、机器化后的人类新形态。在一些后人类主义者眼中,赛博格甚至可以是离身性的(disembodiment),这种观点强调身体是生命的附加物,生命最终能够以信息的方式存在和延续。哈拉维坚决反对将她的赛博格与这种离身性的后人类主义划上等号。笔者认为,在伴生关系的意义上,才能更好地理解哈拉维赛博格的含义。按照她对伴生关系的理解,一方面,伴生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不可还原的差异”,差异的鸿沟永远存在于人和技术之间,技术不能完全同化人,人也无法完全同化技术,但彼此的影响可能会朝着越来越深入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哈拉维认为,人是具身性的存在,在讨论二元划分对女性身份政治的界定带来的影响时,她就强调了身体和性别对于建立女性主体的重要性。存在于伴生关系中的人类主体是一种肉身存在(flesh being)。也就是说,她将身体也放在伴生关系之中,这一观念打破了身体是一个纯粹物质实体的观念,将身体理解为物质性与符号性的身体,是关系性的身体。伴生关系、伴随生成有力地解构身体实体化的观念,身体成为了物质—符号关系的节点。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上,人不能离开具身性的实践活动去理解技术,也就是说,在人—技术的关系中,技术深刻地影响人、改变人,但永远不可能取代人,人的主体性受技术影响、在与技术的关系中生成流变,但技术永远不会取代人。
从《赛博格宣言》到《伴生物种宣言》再到“克苏鲁纪”,都延续了哈拉维对特权的拒绝和批判。与其说她描述了后人类的新世界,不如说她一直致力于批判一个由人类中心、男性中心、西方中心所造就的不平等的旧世界。哈拉维的对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反思、伴生关系本体的提出是对客体化自然、资源化自然的反思与批判。然而,伴随着资本与科技的结盟愈演愈烈,现实情况是自然越发被异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不断沦为人类的客体和资源,被视为服务于人类的奴仆,来自于他者的反抗更多地是依赖于人类行动者的支持,例如出现在科技公司实验室的致癌鼠,引发了人们的同情,激发了人们抵制基因修改技术运动。对非人类行动者的尊重与交流如何真正体现在当代的科技活动之中,而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汲取哈拉维这一学术资源,改变现有的对待他者的方式任重而道远。
除此之外,伴生物种的范围涵盖了机器、生物、人工制品等。伴生关系本体虽然为他者作为行动者的出场奠定了基础,但问题是,当哈拉维将物种的概念泛化之后,我们怎么理解诸如机器、工具等作为人类的他者呢?换言之,机器、工具、人工物等与人之间的伴生关系是否有着与生物、动物不同的展开形式呢?对于这一点,哈拉维并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她对伴生物种的定义太过宽泛,而在不同“物种”之间没有进一步进行区分,这一点也弱化了她的伴生关系本体论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