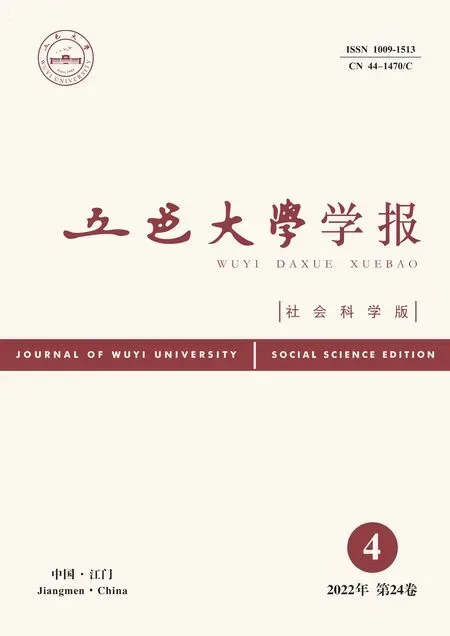岭南杂字文献俗讹字考释
2022-02-15周太空
周太空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杂字是明清以来社会下层流行的一种蒙学识字教材,这种杂字书以韵文形式连缀日常生活常见事物,汇集成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王建军《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收集了一百多种岭南杂字文献,这些杂字文献描写了岭南地区的日常生活,记载了岭南地区的风俗文化,对民俗学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同时,在语言文字学上也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但目前对于杂字的整理研究多从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角度出发,从语言文字角度研究较少。目前所见从语言文字角度研究岭南杂字的论文屈指可数,仅有徐国莉、王建军《西江流域疍家杂字方俗语词通释》,谢友中《〈清至民国岭南地区杂字文献集刊〉音韵述略》,李运富、宋丹丹《方言文献“”及相关字词考》等数篇①。岭南杂字记录了大量的方言俗语词、俗字、讹字,且版本较多。本文利用俗字知识及版本异文对岭南杂字中部分俗讹字进行考释整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俗字考释
杂字文献多为民间手抄,其间俗字夥多,一些俗字甚至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如:
或替换声旁作“䍇”。俗写“瓦” “缶”混用,声旁“扁”换为“乏”。广东江门《新抄幼学七言杂字》缸瓦类:“靛缸鼎锅,酒埕水䍇。”(11/317)可与上文广东广州《新增幼学信札》比勘。 “䍇”本有正字,音义与“甂”皆异。 《说文·缶部》:“䍇:下平缶也。从缶乏声,读若。”[6]104段注:“下当作不,字之误也。凡器无不下平者,以从乏之意求之。当是不平缶,反正为乏也。又以读若求之。”[7]227“䍇”用作“甂”俗写,与表示“不平缶”的“䍇”同形。
“厘”这一俗写在民间契约文书中也常见。储小旵(2021:84)认为是“厘”的简省符号。[8]今谓“厘”作“”实乃草书楷化的结果。“ 厘”草书作“(王羲之)”,楷化后作“”,“厂”头变为“丆”,“里”字草书笔画拉直似“”。
按“:恼眼”不词。“ 恼”当为“怒”字的音借,“恼眼”即“怒目”义。“”当为“突”字的增旁俗写,俗书“目” “日”相混。或作“努睛突眼”,杂剧《冯玉兰夜月泣江州》第二折:“( 正旦唱)倒惹他努睛突眼生嗔怒,一谜的将俺奔呼。”[15]
二、讹字考释
杂字书多为民间手写传抄,一些文字在传抄过程中极易发生讹变。一而再,再而三,使文字逐渐失去本真,令人费解。如:
2.哺嗻
光绪刻本《新编捷径杂字》鬼神章(新增):“府县城隍神主等,判官使者哺嗻们。”(1/303)
按:“哺嗻”费解。 “哺嗻”旁注音“布遮”。乾隆重刻本作“唓嗻”。作“唓嗻”是。《汉语大字典》:“唓:传说中守庙门的鬼。东边的叫唓,西边的叫嗻。”[22]作“唓嗻”与文意正合。盖“哺” “唓”形近相讹,抄写者又不知其义,认为“哺”即正字,遂以“布”为其注音。这是由于字形讹误,连带造成注音讹误。
3.鬼思
光绪刻本《新编捷径杂字》瓷器章:“诸般鬼思亦多情,笔架笔筒与净瓶。”(1/319)
按:“鬼思”一词令人费解。本章所列物品为瓷器类,则“鬼思”当为某一种瓷器物品。那么,“鬼思”到底为何物呢?检光绪黎明善抄本、全廷抡后裔藏本,皆作“鬼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乾隆重刻本,其刻本原作“鬼思”,而后又在“思”字上手书加上一个“山”旁,作“(崽)”,可能觉得加上“山”旁后,字形稍显拥挤,恐难以识读,又在天头上直接手书一个“”字。这种情况,杂字文献中常有。当文中的字体漫漶,以致难以识读的时候,抄写者通常会在该字所在列的天头上重新书写一个更为清晰的,以方便识读。据此,“鬼思”当为“鬼崽”的讹误。那么“鬼崽”又是何物呢?“鬼崽”在方言中一般可以用来指小孩,《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鬼崽仔】萍乡。称小孩儿(通常带欣赏、疼爱的意味。)”[21]2787“ 【鬼崽头】南宁平话。爱跟孩子们玩的年龄稍大的孩子。”[21]2787又柳州方言中有“灰面鬼崽”一词,《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灰面鬼崽】柳州。面人儿,用面粉和糯米粉,染成不同的颜色,捏成人物或动物的形象。”[21]1311据此,例句中的“鬼崽”可能也是“灰面鬼崽”一类的东西,因在“瓷器章”,所以这里的“鬼崽”当为瓷土烧制的人物或动物形象,即陶瓷娃娃之类的东西。 “诸般鬼思亦多情”指这些陶瓷娃娃表情丰富、生动可爱。
三、结 语
综上,杂字文献中的俗讹字可见一斑。近年来民间文献,如契约文书、档案、杂字文献逐渐成历史学、民俗学、文字学新的特色研究材料。而文献利用的第一步就是读懂文献,不对这些疑难俗字进行整理释读,必然影响后续研究。因此,对岭南杂字书中的疑难俗写进行考释,不仅可以丰富近代汉字的研究成果,还有助于历史学、民俗学等研究。
注释:
① 详参徐国莉、王建军:《西江流域疍家杂字方俗语词通释》,《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7年第4期,第45-50页;谢友中:《〈清至民国岭南地区杂字文献集刊〉音韵述略》,《梧州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69-75页;李运富、宋丹丹:《方言文献“”及相关字词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31-37页。
② 括号内数字表示例句在《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中的册数、页码。下同。
③ 文章所引《可洪音义》内容皆来源“CBETA电子佛典2104”,括号内数字和字母分别表示例句所在的册数、页码、栏数。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