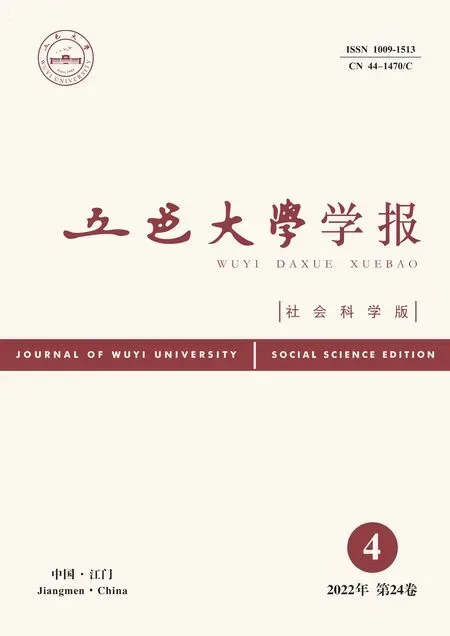《论语》英译本识解“偏离”之考辨
——以詹姆斯·理雅各、亚瑟·韦利译本为例
2022-02-15陆道夫李泳茹
陆道夫,李泳茹
(1.吉林外国语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2.广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孔子的《论语》一直被誉为万世之书、经典中的经典。自古以来,各路名家对它推崇备至。近代学者章太炎认为,读《三字经》不如读《百家姓》,读《百家姓》不如读诸子百家,读诸子百家不如读《论语》。梁启超更是把《论语》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崇高地步。国学大师钱穆,以及南怀瑾、林语堂等人都对《论语》推崇有加。在重视教育的日本,孩子们从3岁开始就必须学习《论语》。近年来,随着国家教育部对中小学教材的改编,国学内容所占的比重由过去的25%提高至35%,《论语》成为中小学生学习的要点,北京地区更是把《论语》纳入到了高考经典阅读的考察之中。这些说明,《论语》不仅仅是一部圣人语录,更是一盏从中可以洞悉人生、读懂社会的指路明灯。
中国知网显示,国内学界近年来关于英译本《论语》的研究,往往集中在翻译学理论、文化翻译、翻译技巧、译者主体、以及文化负载词等几个方面,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论语》英译本展开研究的成果相对偏少。有鉴于此,借助于认知语言学的识解理论,对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和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论语》英译本中出现的偏离现象进行归因研究,试图从中找到相应的翻译对策,以利于更准确、更有效地向西方读者推广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一、《论语》英译本的两种进路
《论语》几乎涉及当时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其问世以来,就受到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重视,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英译(外译)热潮。《论语》最早是由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16世纪译成拉丁文的,后来又被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籍的耶稣会教士和新教传教士不断地重译为拉丁文、法文、英文等西方语言。从1809年到1910年一个世纪里,英国新教传教士理雅各、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三位译者的译本水平最具代表性。
从《论语》300多年的英译历史来看,海外译者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学术型翻译,主要是面向专业读者。这类译文注重考证原文的义理辞章,尽量贴近原文的解释,注重译出中国哲学著作的内涵,以理雅各、刘殿爵、黄继忠、程石泉、安乐哲(Roger T. Ames)等为代表。另一种倾向则是大众通俗化的翻译,主要面向普通读者,以可读性和易接受性见长,以苏慧廉和亚瑟·韦利、刘殿爵等为代表。后来的林语堂(节译)、道森(Raymond Dawson)、华兹生(Burton Watson)、亨顿(David Hinton)、庞德(Ezra Pound)、魏鲁男(James Roland Ware)等译者继承了这种通俗易懂的译风,让英语读者读起来觉得亲切,并引起共鸣[1]。
理雅各和韦利两位译者谙熟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具有不同于西方汉学家的精深研究。理雅各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在他离开中国时,他的多卷本《中国经典》、《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就享誉西方汉学界。理雅各还是“儒莲翻译奖”的第一个获得者。
亚瑟·韦利的《论语》英译本出版于1938年。亚瑟·韦利终生从事汉学的研究。他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在英语语言表述和词语运用方面的优势[2],凝练且流畅,非常适合西方国家的英语读者,有利于目标语读者对《论语》充分的理解。韦利虽然对英语的运用驾轻就熟,但他一生从未到过中国,这就从客观上给他带来了理解中国文化的时空局限性,导致他对《论语》原文和儒家思想的理解有所偏离,使得他对《论语》的翻译产生文化信息的缺失和误差。
认知语言学学者Langacker R.W.曾专门解释过“识解”(Construal)这个概念。在他看来,“识解”是一种用交替的方式对同一场景进行构想和描述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详细程度、不同的心理扫描、指向性有利位置、图形-背景分离等加以实现的[3]。 “识解”是由辖域背景(scope)、视角(perspective)、突显(salience)、详略度(specificity)四个维度而构成,以解释为什么人们面对相同的事物,会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力[4]。所谓“辖域”,其实与出于理解一个表达而被激活的相关认知域有关。单就翻译角度而言,“辖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翻译活动的语境范围,亦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用于识解源语内容所激活的相关认知域和背景知识。而“识解”的“视角”层面,侧重点在于人们观察和描述事体所采取的角度,体现了观察者与情景之间的相对关系。以下以理雅各和韦利的《论语》英译本的偏离为例,从辖域和视角两个维度,对其翻译中的偏离误差加以分类,并找出偏离的成因,以达到管中窥豹、举一反三的研究效果。
二、《论语》英译本的偏离维度
按照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的说法,由于没有两种语言是相同的,无论是在赋予相应符号的意义上,还是这些符号在短语和句子中的排列方式上,语言之间不可能有绝对的对应[5]。由于译者自身的时代背景、成长经历、认知方式,以及对原文的理解方式不同,或者为了迎合读者的需要而采取归化、意译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就会导致译文产生偏离现象;如果偏离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误译。
两位译者《论语》英译本中的偏离现象大致分为四类:其一是语义理解错误;其二是不属于同一背景的事件合译;其三是句子主语的更改;其四是强调侧面的改变。根据识解理论,前两者属于辖域和背景的偏离,而后二者可视为视角的偏离。
(一)辖域的偏离
“辖域”(scope)层面的“识解”,对于源语的意旨理解有很大帮助。而对源语的正确理解,是克服译文偏离的前提。《论语》英译本中的语义理解错误,尤其是文化负载词的偏离识解错误,影响了译文的准确性和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
(1)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理译:Zengzi said, “A scholar must be both sturdy and steadfast, for his burden is heavy and his road is long.Benevolence is his burden; is that not heavy one? Only with death does his road end; is that not a long one?”①
韦译:Master Tseng said, the true Knight of the Way must perforce be both broad-shouldered and stout of heart; his burden is heavy and he has far to go. For Goodness is the burden he has taken upon himself; and must we not grant that it is a heavy one to bear? Only with death does his journey end; then must we not grant that he has far to go?②
熟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士”和“仁”这两个概念,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理雅各把“士”对应译成了“scholar”,明显限定了该词的语义范围;而且,在英语读者眼里,“scholar”特指受过系统专门的学术训练、知识渊博、有一定社会名望的精英阶层。韦利则把“士”直译为“Knight”。根据《柯林斯词典》对“Knight ”的解释,它指的是“In medieval times, a knight was a man of noble birth, who served his king or lord in battle”,其实是指欧洲中世纪时受过正式军事训练的骑士,服务于国王和贵族。《论语》中的“士”,其本意是指知识分子和读书人这一社会阶层而言,中国文化中传统中,并不存在“骑士”这种身份。理雅各和韦利分别把孔子心目中的“士”译成了西方的“学者”和“骑士”,显然是他们受其文化背景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
事实上,“仁、天、德、君子、小人”等这一类文化负载词,在英译《论语》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和难度。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仁”的概念在《论语》中总共出现了 109 次。《说文解字》对“仁”的解释是“亲也,从人从二”。 “仁”,也是孔子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其要旨在于“爱人”和“克己复礼”,是孔子其他道德观念(忠、信、恕等)的基础。因此,理雅各、韦利的译文都借用了古希腊哲学中的“善”(Goodness),意思是通过理性来自我实现的德性的卓越。但“Goodness”更多关乎于上帝的本性,主要是指“品德上的良善”。 “Goodness”一词的选用,不仅缺失了原文中“仁”在礼乐制度、学习品质等方面的确切含义,而且窄化了它的文化内涵。
为此,国内有学者干脆认为,用汉语拼音“Ren”加注释来翻译,倒不失为一种新尝试。也有学者认为,不妨先采用西方的概念去对应中国的特色文化负载词,然后在注释中进一步加以补充说明[6],这样不仅有助于扫除西方读者的理解障碍,还能消除了他们的文化陌生感,达到促进儒学传播、提升文化交流的主要目的。
《论语》英译本辖域层面的偏离现象,还体现在特定人或物的限定上。看看下面的例子:
(2)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理译:The Master (Confucius) said, “Is it not pleasant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be able to constantly apply it? Is not delightful to receive friends coming from afar, a man who feels no resentment at being coldshouldered by others, is he not a gentleman [man of perfect virtual]?”
韦译:The Master said, To learn and at due times to repeat what one has learnt, is that not after all a pleasure?That friends should come to one from afar, is this not after all delightful? To remain unsoured even though one’s merits are unrecognized by others, is that not after all what is expected of a gentleman?
由本例可知, 理雅各之所以选用了“constant”一词来翻译“时”,是因为他直接受到了朱熹注解的影响。朱熹将“时”解释为“时时”,这才有了理雅各的“constant(ly)”之类的翻译。理雅各、韦利两人在处理特定的人或物时,辖域的偏离也很明显。源语中的“朋友” “君子”分别被英语单词“friends” “ gentleman”直接对应,与孔子本人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核还有一定的距离。源语中的“朋”,究竟指的是哪一类“朋友”?究竟是“狐朋狗友”,还是“酒肉朋友”?“君子”又是指哪一类人?是谦谦君子,还是侠义君子?英译的表达,显然是窄化了概念内涵。相对而言,我国著名翻译家辜鸿铭先生的英译优势更突出。他将其中的“有朋……”一句译成“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7]。译文添补了一个“of congenial minds(志同道合)”,不仅限定了辖域,而且交代了背景,不会造成歧义。当然,如果套用或借用“Friends(of congenial minds) from afar bring delight”来英译此句,既押韵,又上口,可谓形意俱佳。至于“君子”的英译,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在理雅各和韦利的《论语》英译本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即便在文化负载词理解正确的基础上,如果把不属于同一辖域的不同事件进行合译,强行将不同话语并入同一语境,也会导致语义偏离,甚至造成误解。
(3)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理 译:The Master said, “While one's parents live,one should not stray far from them. If it is necessary to do so, one must be sure to inform them of where one is going.”
韦译:The Master said, While father and mother are alive, a good son does not wander far afield; or if he does so, goes only where he has said he was going.
两位译者采用折译的方法,把本来属于同一辖域的一个主体,拆解成了几个主语单位,从而造成了中心思想不突出,使得目标语读者容易产生不必要的歧义和困惑。尽管两位译者尽可能地避开汉语重意合(parataxis)的表达习惯,充分发挥了英语重形合(hypotaxis)的特点,译文使用了主从复合句的表达形式,但由于前后主语不一致,译文就产生了偏离。无论是译成“it”,还是译成“he”, 都会给目标语读者带来理解上的混乱。反之,如果在同一个辖域内,译文采取合译的方式,全句的主语和主旨思想就会变得更加明晰、准确。
(二)视角的偏离
由于中西方的文化预设、社会体制、宗教信仰、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差异,译者并不特别熟悉源语文本的文化语境、文化预设、文化内核等,只能按照译者自己的视角或方位(Perspective/Situatedness)去理解源语,因此,译文难免会带有译者自己的认知视角。当这种认知视角与源语有所偏离时,目标语读者就会产生理解上的误差,造成文化交流上的隔膜与障碍。因此,译者只有从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之深层维度去理解、认识和翻译,才有望在两种文本之间驾轻就熟地传达原旨,才能有效搭建两种文化的交流之桥。
理雅各的《论语》译本忠实原著,多直译,表达冗长,不仅可读性较弱,而且很难把源语的文化内核准确有效地传达给西方读者。韦利在翻译《论语》时多半采用散体翻译的现代语言表达,带有明显的异化倾向。他期望寻求中英文化的平等对话,但也容易导致译文的主体视角发生改变,从而产生译文的偏离。
(4)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
理译:The Master was wishing to go and live among the nine wild tribes of the east. Some one said, “They are rude. How can you do such a thing?” The Master said, “if a superior man dwelt among them, what rudeness would there be?”
韦译:The Master wanted to settle among the Nine Wild Tribes of the East. Someone said, I am afraid you would find it hard to put up with their lack of refinement.The Master said, Were a true gentleman to settle among them there would soon be no trouble about lack of refinement.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韦利译文的主体视角相对好些,与源语文本更加贴切。毕竟这段文字的主体重点是孔子,译文的主体不该发生太多的视角转变。韦利的译文读上去要比理雅各的译文稍微顺畅。
在“居九夷” “陋”字的翻译上,理雅各、韦利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理雅各把“居九夷”译成了普通名词“the nine wild tribes of the east”;韦利只是把每一个开头字母变成了大写字母,以示该词是专指特属。二人在认知的视角上存在着明显差异。然而,两位译者并没有完全理解孔子的理想追求。 “居九夷”并非特指“九个蛮夷部落”,而是泛指中原以外的边远地区。古代汉语中的“三、六、九”等数字往往都是虚指。此外,“陋”字在源语中的含义并非“粗鲁”之意,而是指“未开化、不高雅”。由此观之,理雅各的译文“rude”的选用是不恰当的,韦利的处理方式就稍胜一筹。源语中的“如之何”,理雅各的理解也是错误的,译成了“what rudeness would there be?”(怎么办),韦利用虚拟语气的形式较为准确地传达了孔子的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论语》英译本中过于看中某一侧面点的快速转变,也会导致译文偏离。再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5)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冶长篇第五》)
理译:The Master said,“My doctrines make no way. I will get upon a raft, and float about on the sea. He that will accompany me will be You, I dare to say.”Zilu hearing this was glad, upon which the Master said,“You is fond of daring than I am. He does not exercise his judgment upon matters.”
韦译:The Master said, The Way makes no progress.I shall get upon a raft and float out to sea. I am sure Yu would come with me. Tzu-lu on hearing of this was in high spirits. The Master said, That is Yu indeed! He sets far too much store by feats of physical daring. It seems as though I should never get hold of the right sort of people.
这段源语英译难点主要体现在译者对“无所取材”短语的三种不同理解。其一是把“材”解释为造桴的竹木材料。其二是把“材”解释成“裁”。朱子《论语集注》认为,材,与裁同,古字借用。其三是把“材”解释为“哉”。何晏《论语集解》认为,古字“材” “哉”同耳。理雅各和韦利的译文都采用了第二种解释,分别译成了“judgment upon matters”、 “get hold of the right sort of people”,符合孔子的言外之意。但是,两位译者却将视点转移到了孔子身上。事实上,译文的视点应该始终聚焦在“我”上,一旦视角发生了错位,就会带来理解上的困惑或歧义。
三、《论语》英译本偏离维度的归因分析与翻译对策
从上述挂一漏万的分析中不难发现,《论语》英译本之所以会出现翻译的“偏离”,不外乎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论语》本身的博大精深和理解难度;其次是译者的识解方式和思维习惯,译者每每会以不同的认知方式去解读源语文本,这种不同的认知方式,难免会导致译文的“偏离”误差。
如何解决译文的“偏离”误差?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指导,译者可以尽可能在完全识解原文的基础上,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创译源语,重构译文。如果目标语的读者越少误解、越少歧义,那就是较为理想的译本。
第一,异化与归化策略的灵活运用。两位译者的一部分译文由于受到识解方式的制约,更多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反而削弱了原文传递的文化内涵。异化与归化并非对立关系,应灵活运用。
第二,译者主体性的有效发挥。翻译是一种基于译者识解和重构原文意义的认知行为。译者首先是读者,因此,译者对源语的理解和阐释显得至关重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准确把握原语的知识背景与文化内涵,在翻译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之前,最好是先求证,再对源语的主题加以概括和补充,以准确再现源语内核,同时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需求。
第三,多元化的《论语》译本推介。《论语》一类的文化典籍倡导“知行合一“的君子品格,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为不同。所以,在英译典籍的过程中,也应发挥源语文本的应有功能,使《论语》通俗化、大众化、启蒙化的传播效果在英语世界里得到呈现。有国内学者通过对现已出版的30多种《论语》译本进行比对研究发现:较为成功的《论语》英译,应该通过口语化、语境化、本土化、故事化、时代化、多媒体化等多元共举的翻译策略[8],从语言形式、具体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多方位、多途径地将《论语》这类文化典籍推向西方社会大众,让文化典籍不再因为“曲高和寡”而被束之高阁或埋在故纸堆里。借助于翻译媒介,让文化经典“活”在每一代人的心里,应该而且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推广办法和传播途径[9]。
四、结 语
尽管理雅各和韦利的《论语》英译本因其忠于源语程度较高,在西方普遍流传,推动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解,但由于其本身翻译难度大以及译者主体识解的局限性,导致译本仍存在不足。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Why I Hate Arthur Waley? Translating Chinese in a Post-Victorian Era[10]一文中借汉学家和翻译家对韦利英译本的评价,引入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英译的看法。他认为,韦利的翻译给后辈译者带来一个巨大的难题——翻译究竟是“求同”,还是“存异”?这一难题,值得思考。
当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全人类文化交流和文化互鉴中,《论语》及其各种外译本仍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理论层面而言,识解理论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从实践层面来看,识解理论可以为中国大学校训、旅游景点标识语的对外英译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11]。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宣传推广过程中产生的识解偏离现象,将会随着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熟悉和理解而不断减少。
一个优秀的文化典籍英译本,应当在努力贴近外国读者阅读习惯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做到“传神达意” “得意忘形” “形神兼备” “灵韵有生”,尽量让译文读起来更亲切、更愉悦、更有趣[12]。唯如此,才能让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有更加全面、准确、深刻的理解,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注释:
① 本文所引理雅各翻译案例均引自其《英汉四书》,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本文所引亚瑟·韦利翻译案例均引自其《论语汉英对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