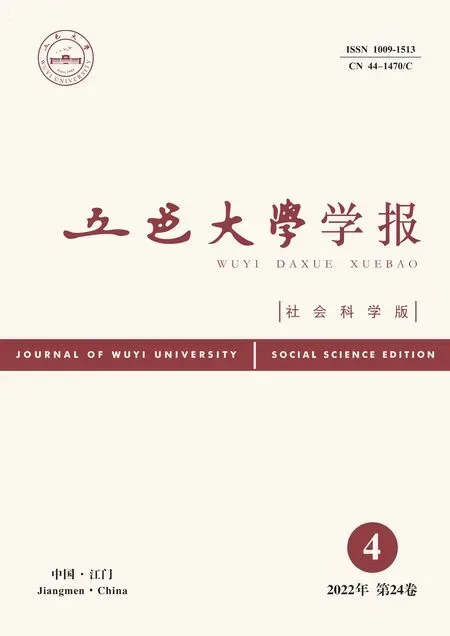论何梦瑶的诗歌艺术风格及影响
2022-02-15郭子凡
郭子凡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一、引 言
“惠门八子”是惠士奇赴广东任学政时,于当地组建的一个师门群体。同时也是继“岭南三大家”之后,在康乾时期广东诗坛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个文人群体。该群体虽以惠士奇为核心,但在惠氏离任之后,其所延续的意义已超越原师门的价值,而成为地域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地烙有“岭南” “粤东”的标识。此“八子”中,当属何梦瑶的诗学造诣最高,罗天尺次之。严迪昌认为:“康熙五十九年 (1720) 冬惠士奇任广东学政,三年间颇为扶持风雅,于是有‘惠门八子’出”,而其中“真有点影响的也只能算何梦瑶一人而已”[1]。
何梦瑶(1693—1764),字赞调,一字报之,号西池,晚年自号研农,广东南海人。曾受知于广东学政惠士奇,“惠门八子”之一。其所涉猎的学科广泛,工诗能医。著有若干医学著作,并撰有诗集《匊芳园诗钞》八卷。
何梦瑶对岭南医学所做出的贡献,已受到当代众多医学研究者的关注。然而研究者对他诗歌的关注度显然不够。何氏之诗虽属地域小众,但在清代的诗歌选集中却也占有一定的分量,受到同时代文人们的注目,如彭端淑的《雪夜诗谈》、黄培芳的《香石诗话》、王昶的《国朝词综》、张维屏的《国朝诗人征略》、钱林德《文献征存录》、谭莹的《乐志堂诗集》、张应昌的《国朝诗铎》、邱炜萲的《五百石洞天挥麈》、杨锺羲的《雪桥诗话三集》等都收载或评价了何梦瑶的诗歌。此外,何梦瑶更是当时诗学大家袁枚所青睐的对象。而在当代的研究中,何梦瑶的名字更多是夹杂在“惠门八子”中被提及,到了近十年来其诗歌才受到人们的重视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体。当前以何梦瑶的诗歌艺术为研究主体的论文有:游明的《<菊芳园诗钞〉校注》 《论何梦瑶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何梦瑶诗歌师承研究》及荀铁军的《何梦瑶的诗论及影响》,这些研究虽然关注到了何梦瑶的诗歌,但在认识上却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进一步在何梦瑶的诗歌中发掘他的个人特色,探索何诗在诗歌艺术上的因袭与创新,以及他作为“惠门八子”的诗人代表甚至是康乾时期广东诗坛的重要代表给粤东诗坛带来的影响。
二、“视域融合”:多形式地采借前人描写性的诗句
何梦瑶在诗歌创作上,也像诸多后学者一样善于对前人的诗句进行重复、模仿和借鉴。从他所学习、把玩的语句中看,他对前人诗歌中具描写性质的诗句尤其钟情,在其写景诗上尤甚。
写景诗是何氏诗集里数量居多的诗歌题材,其创作来源除了受到所见事物的激发,更是在前人的诗句中获得了灵感。像是借由他人之眼来观察事物,从中又包含着自己的体验,好比一种视域上的融合。如:
断桥流水无人处,更写梅花三两枝。(《红水河》其二)
断桥流水无人处,添种梅花三百树。(王冕《秋山图》)
首先,“断桥”与“梅花”是诗歌中经常成对出现的意象。但在以往的诗歌中,二者往往是作为已然配对存在的物象出现。何氏对前人诗歌的学习,除了前一句取其文字直接入诗外,后一句还效取其法,这也是两首诗歌异曲同工的妙处所在,即诗中的梅花并非是断桥边的可见之物,而是作者看到“断桥流水”后联想到的所要赋予的一个意象。其次,王冕的《秋山图》是一首题画诗,写的是画中之物,即虚中之实,而何氏的《红河水》正与此相反,是将造物者比为画师(“造物真成老画师”),而将实际存在的梅当作是作为画师的造物者笔下的图景,化实为虚。这种前后句内容指向或相似或相对的情形,更加印证了这两首诗的吻合是作者有意为之。再如:
秋水落霞乡梦远,昨宵归路月朦胧。(《咏茶》)
落霞秋水梦还乡(杨万里《以六一泉煮双井茶》)
昨宵归梦月千里(杨万里《送孙捡正德操龙图出知镇江二首其一》)
禅房花木妙难寻,自写松风万壑深。(《李橘园罗石湖见示诃林禅院听圆德上人弹琴诗次其韵》)
禅房花木深(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欲写万壑松风哀(李廌《崇福宫》)
这类诗歌的创作并不像何梦瑶其他诗歌那样只是简单引前人之句入诗,或是进行句内的词语更换,而是类似于惠洪在《冷斋夜话》中引用黄庭坚语所云的:“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2]里的“换骨”法。上例中,何梦瑶把“禅房花木深”的“深”字移置到整一联的尾字,这样就使得脱胎于前人诗句的上下两句有了一个更为密切的呼应关系;同时又用了“妙难寻”同义替换了原诗的“深”字,而在作者所创作的新景象中,“深”字的意思又不似原诗中表示的从里到外的距离,而是万壑之深,即一个从上到下的距离,使得诗歌内容形式富于变化。
除了诗歌之外,词作为一种可以承载着更多细腻描写的文体,也是何梦瑶青睐效仿的对象,而它反过来也影响了何梦瑶的诗歌创作,正如罗天尺所说,何梦瑶“因词以通诗”[3]26,如:
不断风前促织声,银河垂地夜三更。(《辛酉秋闱次主司胡吾山太史韵》)
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范仲淹《御街行·秋日怀旧》)
剩有闲亭棲野雀,不闻高柳咽残蝉。(《月夜过花下村与冯志言话旧》)
绿槐高柳咽新蝉。(苏轼《阮郎归·初夏》)
关于对前人描写性语句的化用,还有一点值得提的是何梦瑶对字面上具有描写性的典故的活用。原本用典是诗歌中常见的一种写作手法,但是何氏对前人典故的运用却不只是移事入诗,他还关注到这个包含着典事的词语本身的美感,巧用其意象,使之活现在自己的诗歌里。如《苏桥晚泊》“重檐凝露白,小袖障云蓝”。其中“云蓝小袖”一词出自苏轼《尺牍·与蔡景繁十四首》其六,原指苏轼的侍妾王朝云。至明清时期,该词才逐渐成为后人引用入诗的典故,且分化为苏轼侍妾、自家或他人之姬妾、歌舞妓暨青楼女子三个指向。按笔者所见,无论该词在后人的诗中指向何意,人们在运用该典故时,均以“云蓝小袖”四字原封不动地置于诗中,而何梦瑶在运用这个典故的时候,于词中插入了一个动词“障”,将之变成了一个以袖掩面的动态歌姬形象,这种写法颇具创新性。而这正是因为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来便是一个极具描写性的词语,从而使得何梦瑶于其间有了发挥的余地。
从上述内容可见,何梦瑶对前人诗歌的效法、对典故的采借,大都把关注点放在它们描写的可塑性上,将它们从“可读的文本”转化为“可写的文本”;且对所取的诗材用心雕琢,在吸收前人精华的同时善于将其进行调和,巧妙地运用字词的排比、形式的变化,不仅避免了生搬硬套,反而使其在情感表达、艺术表现上赋有更深一层的内涵。何梦瑶之诗虽兼取百家之长,但又倾向于以白居易、陆游、苏轼一派为代表的清雅诗风。罗天尺曾在《匊芳园诗钞》的序中对何梦瑶之诗评价到:“其品格类祖渭南,渭南诗意尽于句,拙生于巧。‘发无可白方言老,酒不能赊始知贫’,句法多同。报之炼不伤气,清不入佻,中藏变化,不一其体。”[3]25-26作为悉知何氏之诗的密友,罗天尺认为何梦瑶的诗品多似陆游,又胜于陆诗句法的单一,富于变化。檀萃亦在《楚庭稗珠录》中说到:“何西池梦瑶《匊芳园集》,出入白、苏间,略为生色。”[4]何梦瑶自己也曾写过:“廿年文酒无多日,盍早休官拟白苏。”[3]179从中可见,何梦瑶在学习对象选择上所表露出的风格倾向,正是他个人诗歌风格形成的基础。
三、“江山之助”:基于岭南特色的蝉联诗组创作
无论是袭用、改造前人诗句,活用前代典故,或是习法前人的创作习气,都是历代文学遗产对何梦瑶诗歌创作的助益,属于历时性的。此外,作为一个岭南诗人,何诗又无不浸淫在岭南文化当中,这种地域的、共时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何诗的题材上,更是影响到诗歌的形式。先来看《匊芳园诗钞》开篇所录的《珠江竹枝词》:
侬是珠江水上生,今年水比往年清。海珠寺右鱼珠左,无数人来看月明。
看月人谁得月多,湾船齐唱浪花歌。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见卖花人过河。
卖花声最断人肠,花落花开枉自伤。莫向百花坟上过,阿乔命薄似真孃。
不死人间是素馨,春风岁岁唤来生。昌华不少如花女,埋没何人唤姓名。
昌华苑接荔枝洲,影入珠江不肯流。试上五层楼上望,珊瑚千树水西头。
春日高楼大道旁,穿花盘缕试新妆。珠江旧是风流地,肯把斑骓送陆郎。
此组竹枝词是惠士奇督粤“观风”时何梦瑶应试所作。同时期的罗天尺也作了《珠江竹枝词》。罗氏之诗虽然受到惠士奇的手录传播,但是在后世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还是何梦瑶的《珠江竹枝词》流传更广。彭端淑在《雪夜诗谈》中说到:“(何梦瑶)粤东名宿。……读其竹枝词,清新雅隽,不减前人。”[5]何藻翔评之为“神韵独绝,得之风檐中犹难”[6]。杭世骏曾以《珠江竹枝词六首何监州》与之相和。钱林的《文献征存录》、袁枚的《随园诗话》、黄培芳的《香山诗话》和《番禺县志》,甚至光绪年间的上海《申报》,均刊有此作的全篇或截句,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广。该诗除了内容富有广东风味外,其所采用的蝉联式组诗形式更是一大亮点。在这组竹枝词中,每一联内容都带有珠江特色,可独立呈现,而要把握全诗的情感却必须将各联放置在一起,构成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来品读,否则将会因为断篇而发生情感态度的转移。如第二联所提到的“花田”,并非我们日常所理解的花海,而是指第四首所提到的素馨斜,即南汉葬宫人处。因此,整组词表面是记述了珠江的风物历史,实际上从第二首开始便已经奠定了一种悲的基调,如此一来,第三联起句“卖花声最断人肠”便不显得突兀,进而全组词的情感再随着后面的叙述一步步升华,最终在一句“珠江旧是风流地,肯把斑骓送陆郎”结束情感的回响。该组诗基于“悲情”的视角将珠江的风物、历史进行联想,并采用了联珠体的形式使上下联相互呼应,使得这种联想由点成线,有迹可循,让景与事更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对比《中华竹枝词全编》所收的42个诗人创作的《珠江竹枝词》,何梦瑶联珠体式的组诗创作在整个清代的珠江竹枝词组诗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他诗人的组诗创作,多是围绕着珠江这个地域的不同场景片段来进行描绘,无论是在内容或者形式上都没有像何氏所写的这样有如此紧密的互动和关联。这种联珠体的创作体式在他其他组诗中亦可见,如《珠池曲送芸墅张司马》:
南方有珠池,池珠胎应月。月色扬素辉,可玩不可掇。
珠崖亦有珠,珠江亦有珠。借问采珠人,明珠何处无。
采珠珠吐光,不采庸何伤。但愿采珠人,人人如孟尝。
忆从孟尝来,池珠散复聚。珠聚能几时,谁遣孟尝去。
梦尝不可留,池珠环池愁。孟尝留不可,珠池愁杀我。
莫唱珠池曲,愿作珠池珠。相随不相离,系君红罗襦。
组诗从珠池有珠开始,进而联系到采珠人,又通过东汉孟尝“合浦还珠”的典故,将池珠对孟尝的留恋转移到作者对张司马的惜别上。抛开题目的指引,我们很难从组诗的前几首中意会到作者的诗歌主题和情感,全组每一联看似都有其独立的意思,然而它们却又是通向主题情感必不可少的索引,而作者正是善于在每一联中进行步步为营的安排,从而构建起珠池曲和送别之间的桥梁。
何梦瑶这种联珠体式的创作模式大都是以岭南的风土人情为其主要内容。除此之外,岭南地区富有特色的竹枝词、民谣词曲也是影响何梦瑶创作的关键所在。像竹枝词、珠江曲这一类带有民间歌舞音乐性质的文学体裁,其音调的轻快、语言的通俗使之有别于一般诗词的庄严肃穆,使创作者更能够自由发挥,不受格律限制,从而创作出具有地域民俗特色的作品。何梦瑶蝉联诗组的创作正是得益于这种岭南地域的“江山之助”。
四、“唐诗之宋”:何梦瑶的师承与创作倾向
何梦瑶之诗善取前人之长,又强于推陈出新,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软宋诗”的风味。此处所讲的“软宋诗”,指的是江西派之前平易朴雅的宋诗风格,属于宋诗中的唐风,也称为“唐诗之宋”;相反,“硬宋诗”指的便是以江西派为代表的硬瘦生涩之风,也称为“宋诗之宋”[7]634。何梦瑶之诗之所以呈现出“软宋诗”的风貌,应与惠士奇在诗学上对惠门弟子的引导不无关系。
何梦瑶仅存的诗集《匊芳园诗钞》共分有八卷,其中卷一《煤尾集》所录之诗始于惠士奇督粤阶段,其后的卷集延续了该阶段的诗歌风格,总体上并没有显著的改变,因此可以判定,何梦瑶诗歌风格在其从学的阶段就已经形成了。之后经历不过是丰富了他诗歌的题材,对其诗歌风格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惠士奇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任广东学政,以“经学倡,三年之后通经者渐多,文体为之一变”[8]为其主要的文化功绩。而他对粤东诗歌所做出的推动,因为没有直接的成果呈现,或因被其经学功绩的光芒掩盖,往往容易被忽略。惠士奇在督学时期,常勉励士子要继承岭南诗家的风范,承担起传承岭南诗歌的使命,如苏珥在《春秋诗话》序中记到:“岭南旧为诗薮,代有名家,惠公尝勖及门接武。”[9]而在临别广东之际,惠氏还不忘寄言士子务必振兴“张曲江之风度”,可见他对岭南诗歌的传承与发展尤为挂心。
惠士奇历来以经学闻名,但他同时也注重词章之学,著有诗集《南中集》一卷、《采蓴集》一卷、《归耕集》一卷、《人海集》四卷、《咏史诗》一卷。其12岁能作“柳未成阴夕多照”之句,受到乡先辈的大力激赏。短短七字,质朴自然之风可见,与其父惠周惕之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又“特胜乃翁一筹”[10]。惠周惕康熙十年(1671)生惠士奇,此间一直居于吴中,约康熙二十年北上京师,到康熙三十年(1691)考上进士。而惠士奇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考上举人之前,未曾离乡,也不曾见载从游何人。因此,惠士奇少年时期的诗学启蒙很可能来自他的父亲惠周惕。而惠周惕年少从游徐枋,后入汪琬门下,又经汪琬介绍而师从王士禛,从其诗歌风格及风格形成的时间来看,后两者很可能是影响惠周惕诗风的两大师友。
如此一溯源,何梦瑶对“软宋诗”诗风的崇尚很可能远承汪琬和王士禛。首先来看汪琬,他是典型的宋诗派诗人,而在此之中他又是倾向于“软宋诗”一派的。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记载:“钝翁官部曹,后与王西樵昆弟诸人称诗都下,风格原近唐人,中年后以剑南、石湖为宗,后则颓然降格矣。”[11]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亦云:“其诗先规摹初唐,折而入宋。读宋人诗,亦是瓣香玉局,配以陆范,然轻率以出之。”[12]而汪琬自作的《读宋人诗》显然也透露出了他对范成大、苏轼、陆游、元好问的赞赏,侧面反映出了他的倾向所在。再来看王士禛,其最著名的“神韵说”提倡的是唐诗清淡悠远、典雅含蓄的风神韵致。但出于对学唐诗者肤廓空疏之弊的矫正,他又十分重视宋诗,因此他同样也是清代“硬宋诗”的倡导者。然而王士禛虽然推崇黄庭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的创作也走上了瘦硬生涩一路,毕竟他只是想借苏、黄之优长以矫学唐之空浮,因此总体上也是呈现出“软宋诗”的风范。
康熙八年(1669),惠周惕从学于王士禛。此前一二年,正是王士禛倡导的宋诗风受到侪辈效仿的初发期,惠周惕在此间追随王士禛,更是直接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至于他所汲取的是“唐诗之宋”还是“宋诗之宋”,从《砚谿先生遗稿》及其子惠士奇诗歌所承来看,显然是前者。
惠士奇所崇尚和表现于创作实践的诗风,对其所教授的学生或多或少会产生影响,罗天尺和何梦瑶便是最好的例子。黄培芳认为罗天尺之诗是粤诗由唐转而近宋的开风气者:“先田西畴师云,粤诗代守唐音,至石湖始别开面目近宋人矣。著有《瘿晕山房诗钞》……皆笔力崭然,不同凡近。”[13]而前文提到何梦瑶所采借的前人诗句显现出了以白、陆、苏为代表的清雅诗风的倾向,也正是向“唐诗之宋”转变的前期阶段。与此同时,何梦瑶在《读历朝诗》中也表明了自己崇尚“软宋诗”的倾向,他在论宋朝诗时说到:“海涵地负东坡老,玉质金相陆放翁。前辈风流谁继得,虞山应算后来雄。”[3]280其中的虞山即是将苏、陆并举的钱谦益,他所继承推举的便是宋诗中的唐风[7]633。何梦瑶选苏、陆为宋诗的代表,又言钱诗与之一脉相承,此中所表露的倾向不言而喻。在此基础上,何氏将这种审美贯彻到其创作实践中,从而其诗总体上也给人留下了“品格类祖渭南” “出入白、苏间”的印象。
除了对古人表示出崇拜,对今人的态度也可以反映出何梦瑶的诗学倾向。乾隆十七年(1752),杭世骏被聘为广东粤秀书院山长,于此期间开启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期,著有《岭南集》。何梦瑶于该集之序中自称为其后生,间接地表示出了对他诗风的认同。后来朱次琦进一步把何梦瑶看做杭世骏的门生,说到:“门下罗陈尽才俊,说诗更有何西池”[14],透露出二人诗歌之间的某种共通性的关联。比较杭、何二人的作品,其中唐宋兼采,平易朴雅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特别是杭世骏的《岭南集》,“写岭南山水风光的七言古诗风格逼近韩、苏,以雄奇胜,七绝小诗机杼近杨万里,以风调胜”,而其中也保留有其还乡家居期时“诗近白、苏,风格萧散”的余韵[15],与何梦瑶之诗颇为相似。
五、余 论
何梦瑶诗善“取他山之石为自身之玉”,又讲究运用的形式和技巧,富有创新性。此外,何梦瑶更是在惠士奇的直接影响下有意识地采宋诗之渊博典雅以纠后世学唐诗而呈现的疲软之病,以此来继承和振兴岭南诗风。综合诸多因素,何梦瑶的诗歌呈现出“炼不伤气,清不入佻,中藏变化,不一其体”的风格特征,这也为他知名度的提高和当时粤东诗坛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从何梦瑶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他这种带有“唐诗之宋”倾向的又不乏岭南地域风味的诗风颇得杭世骏的赏识。因为有着同样的文人逸趣,二人于岭南时期交游甚密,多聚于唱和雅集中。也正因为如此,何梦瑶被杭世骏纳于以其为中心的广东交往圈中,拓宽并大大超越了其原有惠门交往圈子,为何梦瑶等惠门弟子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交往平台,也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从对粤东诗坛的影响来看,作为康乾时期广东诗坛的重要代表[16],以何梦瑶、罗天尺为诗学领袖的“惠门八子”的诗歌风貌可以视作当时粤东诗风的一个缩影。他们的诗歌呈现出唐宋诗歌转型的某些特质,即大体上仍呈现出唐诗的风貌,但又融入了宋诗特有的平易纪实、渊博典雅的格调,从而避免了纯粹学唐所造成的空疏浮华。
广东历来多以唐诗为宗,且不随时代的风气转移。何梦瑶等人对宋诗的接受与借鉴,仍是从唐诗的美学标准出发,在唐诗的框架中汲取和运用宋诗的精华。然而,即便何、罗诗歌中的这种“近宋”的转变仍带有很强的唐诗色彩,但却也使得粤东诗歌的艺术手段更为丰富,题材更为日常而广泛,从而使粤诗在保有唐音传统的同时又不显得苍白和单调,具有接续和发展岭南诗学传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