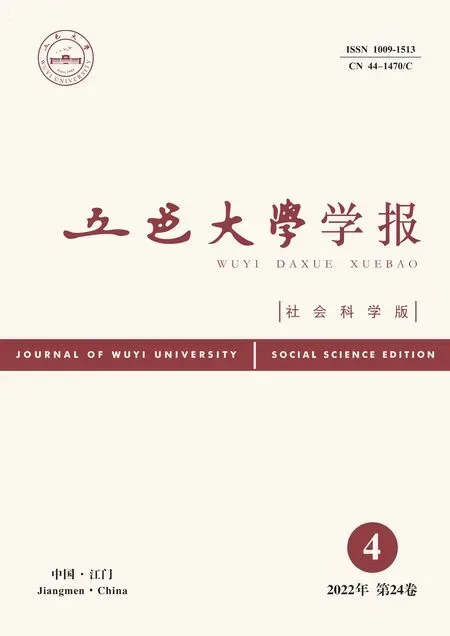从《快嘴李翠莲记》的饮食看“快嘴”的复杂性
2022-02-15杨崴
杨 崴
(香港都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院,香港 999077)
一、前 言
《快嘴李翠莲记》 (下称《翠莲记》)是宋朝人创作的小说话本①,原作者姓名无考,最早载于明朝洪楩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叙述了北宋东京女子李翠莲因能言善辩、口无遮拦,出嫁不久后即被公婆及丈夫以一纸休书遣返娘家,最终无奈出家的故事。就李翠莲的“快嘴”而言,目前学界对其态度呈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部分学者对翠莲的“快嘴”大力褒扬,如杨冰认为翠莲施展“快嘴”是为了反抗封建威权对女性的束缚;[1]肖燕怜点出这种“快嘴”是“张扬个性、主张自我”的行为;[2]罗志伟则强调了“快嘴”对古代父权意识、尊卑意识和繁琐婚俗的批判。[3]另有学者极力批判翠莲的“快嘴”,如王菊香、孙静文将研究视野回溯至北宋社会,称彼时的说书人和听众倾向以泼辣多嘴的翠莲为反面形象,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女子无论多么优秀只要 ‘多口舌’一定没有好下场”的共同价值观;[4]谢家顺则指出翠莲的“快嘴”不分场合、蛮横无理,其悲剧命运完全是咎由自取;[5]王诗丽亦以“违背了语言交际的得体原则和礼貌原则”来评判翠莲的“快嘴”。[6]由此可见,前人对“快嘴”的态度偏向赞扬和批判两个极端。但若细味翠莲的言论,可发现其对父母、公婆、丈夫、婚嫁随行人员等人显露的“快嘴”各有差异,尊贬与否完全是相机行事。那么,翠莲因人而异的“快嘴”是否应如前人一样以非褒即贬的态度来看待?是否完全符合赞扬者所言大胆反抗封建威权、争取个性解放,或否定者所称蛮横粗鲁、缺乏礼仪?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翠莲记》中的故事发生在饮食文化繁盛的宋代,彼时蓬勃的经济为饮食业奠定了丰盈的物质基础。宋代饮食品类繁多,烹饪技术亦愈加成熟,食物、饮品的“色、香、味、形”均较以往有所提升,坊市界限的打破又推进了饮食商业化的进程,更有多部饮食著作接踵涌现,可谓中国饮食史上承前启后的繁荣期。[7]而《翠莲记》中亦有多处饮食描写,涉及日常生活及婚嫁礼俗中的菜肴、面食、点心、果子、茶饮等各个品类,是北宋饮食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反映着个中人物的言行、性格、心理及其成因。故此,本文拟以《翠莲记》李翠莲“快嘴”言论中的饮食描写为切入点,以在上段末尾提出的两个问题为研究方向,再回溯北宋时期有关阶级、饮食、教育、婚嫁的政治制度及社会观念,探究李翠莲的“快嘴”如何因人而异、因何而生,以图客观地树立对李翠莲“快嘴”的评判态度。
二、对父母的“快嘴”:劝慰辩解
《翠莲记》在拉开故事帷幕之初,先介绍了张员外、李员外两家即将联姻的背景,接着呈现了李员外夫妇担心女儿李翠莲嫁到张家后,会因“口快如刀”[8]31惹得夫家人不快,便劝她“少则声”[8]31的情景。而翠莲当即开始展现她的“快嘴”,其中便提到了她烹煮饮食十分在行:“做得粗,整得细,三茶六饭一时备;推得磨,捣得碓,受得辛苦吃得累。烧卖匾食②有何难,三汤两割我也会。”[8]31-32口说无凭,翠莲在出嫁当日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烹饪能力:“爹拜禀,娘拜禀,蒸了馒头索了粉,果盒肴馔件件整。”[8]33翠莲花费如此多的唇舌和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烹饪技能,皆因烹煮饮食乃属传统女性言行准则“四德”之“妇功”,对古代女子来说可谓天经地义的要求,早在东汉便有班昭《女诫》称“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9],而在翠莲所处的北宋时期,司马光所著《家范》亦云“其女功,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10]。再联系翠莲所述“如此伏侍二公婆,他家有甚不欢喜?爹娘且请放心宽”[8]32,可知翠莲是想以“快嘴”劝慰父母,自己与其他良家妇女无甚差异,一样擅长厨头灶脑、蒸煎炒煮,劝二老不必多虑、不必担心她会惹夫家人生气,并没有为了责备、讽刺父母而施展“快嘴”的负面情绪。
同样在出嫁当日,当父母劝翠莲出嫁前要祭拜祖先时,翠莲立刻走到祖先牌位面前,一边祭拜一边喃喃许愿。观其所许之愿,除了许下在夫家能亲戚和睦、人丁兴旺的精神生活意愿外,还提到对夫家饮食生活的期盼:“金珠无数,米麦成仓。蚕桑茂胜,牛马捱眉。鸡鹅鸭鸟,满荡鱼鲜。”[8]33希望自己出嫁后能吃饱喝足,不会被夫家人亏待。但若深究其出嫁的缘由,如话本开头所述“话说本地有一王妈妈,与二边说合,门当户对,结为姻眷,选择吉日良时娶亲”[8]31,即无论是李员外夫妇还是媒人,都没有就张狼是否为合适的夫君来过问翠莲本人,加之翠莲本人祭祖时所说“今朝我嫁,未敢自专”[8]33、“男婚女嫁,理之自然”[8]33,可知翠莲嫁夫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仍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1]127,但翠莲也不敢当着父母的面反抗这种包办婚姻,甚至在祭拜祖先喃喃低语时,也不敢向祖先诉说自己受父母之命出嫁的无奈,只是希望自己能在夫家丰衣足食、子孙满堂而已。
完婚第三日时,婆婆向翠莲的母亲历数翠莲在夫家不受待见的“快嘴”和其他行为,母亲听后“羞惭无地”[8]37,径向翠莲道:“交你到人家,休要多言多语,全不听我。今朝方才三日光景,适间婆婆说你许多不是,使我惶恐千万,无言可答。”[8]37但直到此时,翠莲也完全没有责怪父母包办婚姻、未就婚事过问自己的意思,而是向母亲历数自己在夫家受到的冷遇,其中亦涉及饮食描写:“三日媳妇要上灶,说起之时被人笑。两碗稀粥把盐醮,吃饭无茶将水泡。”[8]37表明翠莲欲以自己的冷遇引起母亲的同情,更希望母亲能理解自己对夫家人的不敬。
由上述的饮食描写可知,翠莲对父母的“快嘴”以劝慰、辩解为主,并没有过多的负面情绪。甚至在父母包办翠莲的婚姻、责问翠莲为何在夫家仍然口若悬河之时,翠莲还是用 “快嘴”为自己开脱,不敢直接反抗父母的安排。论其因由,还需溯至翠莲的家庭环境和彼时的社会风气。首先,话本原文提到,翠莲年方十六岁,便“女红针指,书史百家,无所不通”[8]31,证明李员外夫妇极其重视培养翠莲的生活技能和文化素质。而且,翠莲每次辩解完,李员外夫妇几乎都会“大怒”③甚至“起身去打”[8]32,可知其家教极严。其次,宋代种种家训文本皆要求女子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毕恭毕敬、尽心尽力地侍奉父母,如未成年女子在鸡鸣时分(凌晨1点至3点)便要起床,并向父母问安、侍奉父母用餐,而已成年的未婚女子还须承担“为父母搔痒、出入扶持、盛洗脸水、拿擦脸毛巾以及做好饭菜等事情。”[12]50而就当时的社会婚嫁风俗而言,北宋女子在婚事上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据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若相媳妇,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钗子插冠中,谓之 ‘插钗子’;或不入意,即留一两端䌽段,与之压惊,则此亲不谐也”,被相中的女子只得接受结果,不得提出异议。[13]30囿于父母的严格管教,兼受女子必须尊奉父母和女子向无婚嫁选择权的传统观念影响,饶是肆言无忌如李翠莲,也不敢逾越底线,不敢在对父母的言行举止中透露出不满和反抗,惟有顺从父母意愿出嫁。
尤其值得论及的是,父母对翠莲“快嘴”的反应虽如前述多为“大怒”,但在出嫁当日,当翠莲又以“快嘴”论说自己已备齐食物和嫁妆、不须急于准备出嫁事务时,父母的反应却是“敢怒而不敢言”[8]33。 “敢怒而不敢言”典出唐朝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14],原文为“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15],意在批判秦朝极尽豪奢、目无人民的暴政,此后亦多用于形容在威权压迫之下、人们怒愤填膺却无法倾诉、憋闷难忍的心理状态。而《翠莲记》将此典用于形容父母代表的威权一方的心理状态,似与前文的“大怒”相悖,实则是反用典故的绝佳例证:“敢怒”与前文的多次“大怒”一脉相承,“不敢言”则是因为父母对翠莲的“快嘴”已感到厌烦和无奈,若再次大发雷霆惟恐引来翠莲更加频繁的“快嘴”。故此《翠莲记》中的“敢怒而不敢言”是将原典的威权者和被压迫者进行对调,因为其并非如原典一般形容憋闷难忍的感受,而是形容代表威权角色的父母对翠莲脱离掌控的“快嘴”深感无奈、宁可置之不理的心理状态。翠莲对父母的态度已是倾向于顺从、劝慰、辩解,但她“快嘴”的说话方式仍旧让父母感到厌烦和无奈,亦为下文翠莲对公婆、丈夫、婚嫁随行人员更为忤逆冒犯的“快嘴”作出了铺垫。
三、对公婆及丈夫的“快嘴”:触忤犯颜
翠莲嫁到夫家后的第二日,婆婆让她收拾家务,她便又开始施展“快嘴”:
菜自菜,姜自姜,各样果子各样妆;肉自肉,羊自羊,莫把鲜鱼搅白肠;酒自酒,汤自汤,醃鸡不要混腊獐。目下天色且是凉,便放五日也不妨。待我留些整齐的,三朝点茶请姨娘。总然亲戚吃不了,剩与公婆慢慢噇。[8]37
由此可知翠莲烹饪饮食、打理家务的能力甚好,但更应细味的是末句“总然亲戚吃不了,剩与公婆慢慢噇”[8]37,敢将剩饭剩菜交给公婆吃,无异于当面冒犯公婆,这是翠莲万万不敢对父母做出的举动,可见翠莲对公婆的态度与对父母的态度截然不同。
及至翠莲过门的第三日,公公唤她烧茶,她便立刻“刷洗锅儿,煎滚了茶,复到房中打点各样果子,泡了一盘茶,托至堂前,摆下椅子”[8]38,恭敬地请公婆和叔嫂喝茶。公婆叔嫂坐定后,她又说:“两个初煨黄栗子,半抄新炒白芝麻。江南橄榄连皮核,塞北胡桃去壳柤。二位大人慢慢吃,休得坏了你们牙!”[8]38-39翠莲所备栗子、芝麻、橄榄、胡桃四品,均为坚硬或涩苦的食物,而“橄榄”在宋代文学中更有特殊寓意。北宋王禹偁《橄榄》诗云:“皮肉苦且涩,厉口复弃遗。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饴。”[16]390诗中更直接点破“橄榄”乃喻指忠臣冒犯天威的直谏:“我今何所喻?喻彼忠臣辞。直道逆君耳,斥逐投天涯。”[16]390-391有宋一代的文学作品常用“橄榄”喻良臣忠言,即肇端于王诗④。故若从话本听众的角度考量,此处的饮食描写有两层意涵:若是目不知书的白丁听众,仅凭对这些食物的基本认识,也能晓其质之坚硬、明其味之苦涩,能理解翠莲借此讥讽公婆牙力不好、难以啃嚼苦硬食物;若是识文断字的文人听众,在通晓第一层意涵之余,仰赖对“橄榄”常喻指良臣忠言的了解,还能联想到话本中的翠莲欲将自己的言行与犯颜上谏的朝堂忠臣相类比,将在夫家的生活与昏君怠政相类比,意图为自己不受待见的“快嘴”正名,自认此举为反抗威权压迫的正当行为。
同为夫家人,相较公婆遭到的冒犯,丈夫张狼被翠莲“快嘴”冒犯的程度则更为严重。在新婚洞房之夜,翠莲开始质问丈夫给了多少聘礼,其中也涉及到了饮食方面的聘礼:“多少猪羊鸡鹅酒”[8]36,意在借此番故意质问,来拒绝张狼同床共枕的要求。此后,为达成不愿嫁给张狼、否认此次婚姻的目的,翠莲甚至以“揪住耳朵采头发,扯破了衣裳抓碎了脸,漏风的巴掌顺脸括”[8]36等暴力行为来吓唬张狼。可见翠莲对张狼“快嘴”的冒犯程度,远比之前对父母、公婆的更严重,几近威胁恐吓。
由此及彼,为何翠莲会产生不想出嫁的念头呢?这还需从当时的社会风气谈起。首先,在宋代社会,女子的活动相较此前的朝代更为自由,可登山踏青、外出聚会,还可参与蹴鞠、相扑等传统男性体育运动,甚或涌现出“有组织、有计划、有活动的交往社团”。[12]51-52李员外家作为处于社会上层的官员家庭,相信翠莲的类似活动只多不少。由此,在对女子管束较为宽松的社会风气中,翠莲萌生了不想接受父母包办、夫家指定的婚姻的念头,亦是理之常情。无奈囿于娘家的严格管教,她不敢在父母面前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当她嫁与夫家时,这种念头却愈加强烈,甚至敢于在明面上表现出反抗公婆及丈夫的言行,原因何如?且再看《东京梦华录》所载北宋东京男女婚配前的礼仪程序:夫家人和娘家人第一次见面是前述的“若相媳妇,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中”,若娘家的女儿被夫家人相中,此后双方或“望媒人传语”,或互赠钱财和礼品,却无法当面相见,直至“(迎娶)前一日女家先来(夫家)挂帐幔,铺设房卧”方为第二次见面,而第三次见面便是正式的“迎娶日”了。[13]30-31换言之,在迎亲之前,翠莲最多只见过夫家人三面,与丈夫和公婆极不熟悉。当翠莲嫁与夫家,便身处陌生环境,加之脱离了父母的管束、无所羁绊,自然就想在公婆和丈夫面前肆意地显露自己的不满情绪了。但如前文所述,翠莲对公婆和丈夫的态度也有些微差异,对丈夫的“快嘴”的冒犯程度远比对公婆的“快嘴”严重。这是因为翠莲虽有满腹怨气,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长幼有叙(序)”[11]111观念在她心中仍根深蒂固,故对作为长辈的公婆稍有收敛,对作为平辈的丈夫则更为肆无忌惮地冒犯。
四、对婚嫁随行人员的“快嘴”:恶言厉色
在娶亲当日登上出嫁车马之前,翠莲从母亲手中接过钱,赏赐给一众婚嫁随行人员。此时翠莲的“快嘴”又再施展开来,其中对媒婆的“快嘴”同样涉及到了饮食元素:“多得一贯文,与你这媒人婆买个烧饼,到家哄你呆老汉。”[8]34由此可知,翠莲对媒婆的态度鄙夷得几近施舍,与前述对父母、公婆、丈夫的态度均大相径庭。此后,当媒婆按礼俗让翠莲“开口接饭”[8]34时,翠莲却怒火中烧,开始运用诸多侮辱性词语来大骂媒婆,如“老泼狗”、“嚼舌嚼黄胡张口”、“白面老母狗”等等[8]34。在面对公婆和丈夫时,翠莲的“快嘴”就算再怎么冒犯和讽刺,也没有带着鄙夷的态度、使用如此之多的侮辱性词语。
当随行的阴阳先生劝翠莲对媒婆“出言不可太甚”[8]34时,翠莲则搬出自己富贵多财的娘家,辩称媒婆让其吞冷饭是委屈她了:
说我婆家多富贵,有财有宝有金银,杀牛宰马做茶饭……猪羊牛马赶成群……可耐伊家忒恁村,冷饭将来与我吞。若不看我公婆面,打得你眼里鬼火生![8]34
当中论及的“杀牛宰马”、“猪羊牛马赶成群”颇值得玩味。据《宋代物价研究》统计,北宋时期牛的单价是2贯余到10贯[17]299,马的单价是悬殊的8贯到100贯余[17]303-313,羊的单价是500文到5贯[17]314-316,猪的单价是1贯到1贯200文[17]316-317,鸡的单价是30文到1贯[17]318-319。从总体来看,牛作为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马作为主要的作战工具,两者单价均超过《翠莲记》提及的羊、猪、鸡等其他禽畜。而翠莲的娘家虽有“猪羊牛马赶成群”,却偏以价格高昂的牛马为日常饮食,不食价格低廉的猪羊,这对翠莲来说,真是再有力不过的标榜富贵家世的语言手段了。故此处的“快嘴”,表面上是翠莲因为含冷饭而感到委屈,实则是身具富贵家世的翠莲对媒婆和阴阳先生低贱出身的鄙夷。
综上可知,与父母、丈夫、公婆相较,翠莲的“快嘴”对以媒婆和阴阳先生为代表的婚嫁随行人员所持情绪最为负面,充斥着鄙夷和侮辱的意味。甚至在新婚洞房夜阴阳先生按婚俗“撒豆帐”⑤时,翠莲居然“跳起身来,摸着一根面杖,将先生夹腰两面杖……一顿直赶出房门去”[8]35,以暴力阻止阴阳先生的行为。而翠莲这种对媒婆和阴阳先生极尽鄙夷、侮辱、乃至打骂的态度,实应归因于中国古代的阶级差异。翠莲的父亲为东京李员外,在北宋,“员外”称谓本指“员外郎”官职,但民间多借此敬称无官职的富人和地主[18]。虽因文献无征,无法确定《翠莲记》中的李员外究竟是官员还是富有地主,但至少能将其身份锁定于京城官绅的范围内。翠莲出身于堂堂京城官绅家庭,当是“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士”阶层,即翠莲处于享尽富贵的社会顶端阶层。而媒婆和阴阳先生这些以说媒、算命等为生之人,在古代处于社会最底层,身居社会顶层的官员及读书人对其多持鄙夷态度,南宋袁采所著的《袁氏世范》便提到了“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脱漏妇女财物及引诱妇女为不美之事,皆此曹也。”[19]正因翠莲认识到她与媒婆等人所处阶层天壤悬隔,加之亟欲发泄被迫出嫁的不满情绪,当然就无所顾忌地对媒婆和阴阳先生投以鄙夷、侮辱的“快嘴”了。
五、结 语
总而言之,从《翠莲记》中各处饮食描写可知,李翠莲的“快嘴”具有复杂性,对父母、公婆、丈夫、婚嫁随行人员的“快嘴”各有差异。李翠莲对父母的“快嘴”,以劝慰、辩解为主,原因是父母对翠莲管教极严,加之北宋时期存有女子必须尊奉父母的要求和女子向无婚嫁选择权的传统观念,纵使翠莲心存对婚姻的不满,也不敢在父母面前表露。翠莲对公婆和丈夫的“快嘴”,则是直接冒犯及讽刺,这归因于翠莲身处脱离父母管束的陌生环境中,欲恣意表达自己对婚姻的不满。但翠莲对丈夫的“快嘴”却比对公婆的更狠毒,皆因翠莲仍然受着传统的长幼辈分观念影响,不敢对公婆太过放肆。而翠莲对以媒婆和阴阳先生为代表的婚嫁随行人员的“快嘴”和举动,则是极尽鄙夷和侮辱,甚至大打出手,实是翠莲所属的官绅阶级和婚嫁随行人员所属的社会底层阶级存在天壤之别所致。故《翠莲记》中的饮食描写真实再现了北宋日常生活及婚嫁礼俗中的饮食文化,同时亦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功能,多角度地反映着个中人物的言行、性格、心理及其深层成因。
因此,翠莲的“快嘴”的确是因人而异,不能简单地用前人的大胆反抗封建禁锢或缺乏言语礼仪等非褒即贬的态度来评判。翠莲虽然敢于在公婆、丈夫、媒婆及阴阳先生面前反抗婚姻禁锢,但仍然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敢在父母面前直言不满,故她的所谓“反抗”并不够大胆、不够彻底。而所谓翠莲的言论蛮横粗鲁、缺乏礼仪,实应归咎于封建社会并未赋予女性自由选择婚配对象的权利,却又残酷地钳制女性的个性解放思想,迫使翠莲以“快嘴”来宣泄不满情绪,最终酿成她日后被逐出夫家、无奈遁入空门的悲剧。
注释:
① 《快嘴李翠莲记》最早见于明代梓行的宋元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学界目前对其创作年代有宋、元两说,尤以宋话本说更为通行,故本文采纳宋话本说。详参:许建中:《《快嘴李翠莲记》散论》,《盐城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40页。
② “匾食”,即饺子,详参:徐海荣主编:《中国饮食史》,杭州出版社,2014年,第4卷,第152页。
③ 李员外夫妇在翠莲施展“快嘴”后的“大怒”有三次,分别为“员外与妈妈听翠莲说罢,大怒”、“翠莲道罢,爹妈大恼”、“员外、妈妈并哥嫂一齐起来,大怒”,分别参见:洪楩编印:《清平山堂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1、32、33页。
④ 孙华娟指出:“宋人以橄榄为诗料,不再仅以之作为异方风情的表征,主要集中于其果实回甘的特性,少数诗作咏其本物本味,大多或以之喻忠言,或喻人生。王禹偁有《橄榄》诗,着力描写了橄榄果实的形态与滋味,橄榄不但获得了被写真传神的资格,也首次被用来与忠臣谠言相比并。这一譬喻建立在本体与喻体皆苦尽方能甘来的相似特性之上,由于二者间明显的差异会引发读者强烈的阅读体验,因而显得如此妥帖和新妙,此后橄榄渐成为宋诗中不鲜见的诗语。”详参:孙华娟:《“霜柿” “橄榄”与宋诗》,上海《文汇报》2021年6月10日,12版。
⑤ 有关“撒豆帐”婚俗,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新娘乘坐出嫁车马,至夫家门口下车后,“有阴阳人执斗,内盛谷豆钱菓草节等呪祝,望门而撒,小儿辈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俗云厌青羊等杀神也”,再经过“坐虚帐”、“坐富贵”、“走送”、“高坐”、“利市缴门红”、“牵巾”之后,便是“男女各争先后对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䌽菓散掷,谓之‘撒帐’。”《翠莲记》中的“撒豆帐”应为“撒谷豆”及“撒帐”的结合。详参: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