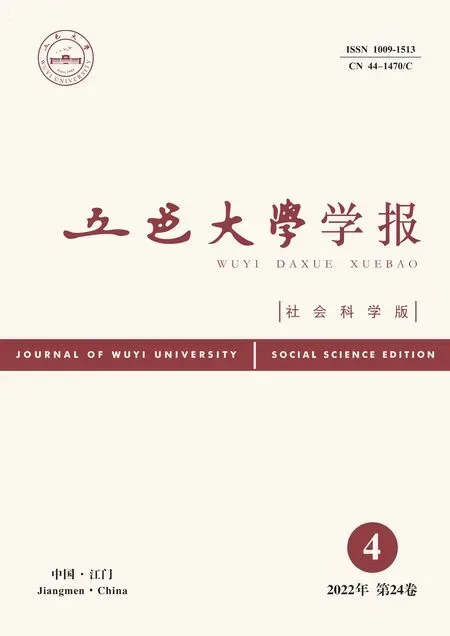陈献章境界论的基源与旨趣
2022-02-15杨抒漫
杨抒漫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陈献章,广东江门人,明代诗人、哲学家,其学问既有哲理指向,也有美学指向,二者的融汇在其境界论中有着生动体现。陈献章《与贺克恭黄门》以“自得之学”[1]133概括其学问,又以“自得之乐”[1]275归纳其在自得之学中获得的自由的精神境界。 “自得之学”和“自得之乐”是一体关系,能领悟此学,即能感知此乐,反之亦然,当代学界亦常用这两个词概括白沙心学及其境界与旨趣。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阐发了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当代人常以此说为划分古人境界论的理论模型,这在以往的白沙境界论研究中有所体现,例如,何静认为陈献章的自得是“与天地万物融通的境界”[2],这相当于《新原人》中的天地境界。用冯氏之说衡量白沙境界论,有得亦有失。其得在于冯氏为我们提供了精简凝练的境界论划分范式和术语;其失在于陈、冯二人的境界论有重大差异,不可混为一谈。冯氏境界论针对所有人而言,即“就大同方面看,人所可能有底境界”[3]45,不同人的境界有高低之分,低境界和高境界的区别恰如梦、觉之分,梦、觉不可一时俱在。与之不同,白沙境界论主要描述他本人的为学和处世之道,各境界恰如一山之顶峰与山腰,虽高低有别,但共成一体,并非如梦、觉一般泾渭分明。总之,在讨论白沙境界论时,可借力于但不可拘泥于冯友兰之说。陈献章境界论以诗歌为载体,以心学为内核,是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心学境界论的源流和特色。
一、陈献章的四种境界论概述
陈献章著作中的境界论主要有如下四种:
第一,宇宙境界。《湖山雅趣赋》云:“盼高山之漠漠,涉惊波之漫漫;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间。当其境与心融,时与意会,悠然而适,泰然而安。物我于是乎两忘,死生焉得而相干?”[1]275“境与心融”之“境”有两种含义:第一,指外境,即高山与烟波,其与心相融合,所塑造者为悠然安适的心境。白沙进一步向上通达“境”的第二种含义:境界,即“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间”和“物我于是乎两忘,死生焉得而相干”,这两组描写都指向具有超越性质的精神体验,反映了陈献章高邈超俗的胸襟。相较于心境,宇宙境界超出感官所能测知的范围。
第二,太和境界。《题冷庵》云:“是以冷自胜,于世非绝屏。假令务绝屏,过与近热等。我以道眼观,天下方首肯。寒暑两推移,正中太和境。”[1]719关于何谓太和境界,湛若水解释道:“以冷自胜,于世非有绝屏之心。若出于绝屏有意之私,与近热者过犹不及也。我以道眼观之,如寒暑之气得两平者,乃为中正太和耳。”[1]720根据这段解说,达到太和境界的人,其心中正平和,其出世并非刻意避世,因为刻意避世者反而未能从俗世的纷扰中解脱。
第三,本体境界。《藤蓑》云:“东风吹新蓑,浩荡沧溟黑。须臾月东上,万里天一碧。安得同心人,婆娑共今夕?”[1]729湛若水曰:“至于本体,复明其真境,可乐如此。安得同心之人,共此今夕之乐哉?盖勉人同进大道之意也。”[1]729可见,《藤蓑》并非纯粹的写景寄情之诗,而是含有对“本体”的追寻,具体到心学中,便是对心之本体的追寻。 “浩荡沧溟黑”喻指由于心学尚未得到普天之下学者的认同和践行,思想界尚处于迷茫状态,有待心学大家为其扫除迷雾。
第四,虚明境界。陈献章本人并未明确提出“虚明境界”的术语,这个概念出现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此书认为陈献章“空诸障翳,心境虚明,随处圆通”[4]。陈献章以虚明心境圆融地应对万事万物,由此,“虚明”不仅是刹那心境,更是贯穿于白沙学问和处世中的境界。
上述四种境界皆有其理论基源与深刻的思想旨趣,且与理学构成鲜明差异,对它们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陈献章的哲学思想与德行品质。
二、陈献章境界论的基源
(一)宇宙境界、本体境界与邵雍之学
宇宙境界和本体境界可以合而言之,因为作为二者之文本基础的《湖山雅趣赋》和《藤蓑》都描述了人对最高精神层次的寻获。
《湖山雅趣赋》中的宇宙境界未得到清晰界定,似只是一种虚廓宏大的心灵体验,但是,陈献章其他诗文对“宇宙”的描写足以帮助我们看清其思想中“宇宙”的真实含义。白沙笔下的“宇宙”除了指时间、空间中一切存在物的集合,还有特殊意义,其言曰:“千古在前,万古在后,上下四方,谁无宇宙。”[1]115宇宙在白沙笔下成了可为人所拥有的事物,人人皆有其特殊的宇宙。《与林郡博》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1]217白 沙 还 问 道:“宇 宙 无 穷,谁 当 负荷?”[1]139这里的宇宙不是存在物的集合体,而是吾人责任范围内的一部分,吾人应当负荷之、承载之。可见,白沙思想中带有哲学色彩的“宇宙”有如下两层含义:其一,宇宙是属我的存在;其二,我对宇宙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白沙说人对宇宙负有责任时,他并不是要求人力等于甚至大于宇宙之力,而是将宇宙作为属我之存在,从而解决渺小人类与无穷宇宙间的不对等性,使阔大的宇宙被收摄入吾心中,即心即宇宙,即渺小即无穷。能含摄宇宙的心是心之本体,即心体。《游江门记》对白沙之复见心体有所描述:“致虚者,所以养其心体,勿使邪动之欲得以干之,而常为万感万应之本也。”[1]945基于此,宇宙和本体终于以心为枢纽而结合了起来,宇宙境界和本体境界的交融亦成为不言自明的基本理论。宇宙、本体、心三者间的融合是心学内部的传统,在白沙之前,陆象山已有此意:“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5]白沙的“宇宙在我”之言“发明象山宇宙之旨”[1]916。在白沙之后,阳明亦倡此旨:“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6]在汇合宇宙和心体这一问题上,陆、陈、王一脉相承。
宇宙境界和本体境界都生发自心境,在《湖山雅趣赋》中,心境和境界间的源流关系十分清晰,在《藤蓑》中,白沙未明言其心境如何,但细味此诗对风景的描写,便可看出,白沙将幽寂隽逸的心境呈现于东风、沧溟、圆月、碧空之中,并使心境获得升华,变为光明本体展露无余的真境,即本体境界。
陈献章从心境中提炼境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袭自邵雍境界论。《明儒学案》以“学术类康节而受用太早”[7]5评价陈献章,邵、陈二人从心境中提炼宇宙境界的思路亦不谋而合。
关于邵雍从心境中开出境界的思路,其《尽心知性赞》云:“廓然心境大无伦,尽此规模有几人?我性即天天即我,莫于微处起经纶!”[8]可以看出,邵雍从广大光明的心境中获得了可与天地、宇宙、本体同列的阔远境界。邵雍从心境中开出宇宙境界的思路遭到众多学者的质疑,朱熹甚至认为此文非邵雍所作:“若是真实见得,必不恁地张皇。”且以其为“学佛者之论”[9]2552-2553。朱熹对《尽心知性赞》的不满在于两点:第一,此文的作者并非真有见于天理,故而言辞浮夸,果真成圣者反而平易敦朴;第二,此文带有佛学烙印,近似于释氏误以为宇宙万物都归属于我心,误以为若我心廓然澄澈,便是上达宇宙境界,此文无益于学者尽心知性,因为尽心知性者必先格物致知,“知性犹物格,尽心犹知至”[9]1422,若脱离格物穷理、直接从心上入手,所能得到的境界必然是伪境界或低下的境界。
有别于朱熹否定《尽心知性赞》从心境中开出境界的做法并将其与佛学相提并论,另一些学者承认此文确为邵雍所作并对之称赞有加。张九成曰:“学者欲识尽心之说,当于此求之。”[10]张九成被朱熹目为逃儒归释者,“凡张氏所论著皆阳儒阴释”[11]。当时确实有僧人甚为欣赏《尽心知性赞》,例如释惠彬认为其“确乎其不可拔”[12]。张九成、释惠彬的观点不占据主流地位,统治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朱子理学)坚持认为《尽心知性赞》从心境中开出宇宙境界的做法既夸大了心的能动作用,也携带着佛学基因。
陈献章的境界论也以心境为根基。白沙所说的心境不仅是由知、情、意等元素构成的主观精神体验,更是有利于道德动力和原则之实现的独特心灵状态;白沙所说的境界不是自我想象的产物,而是本心与万物的联通,由己心扩展至宇宙。简言之,由心境上升到境界的过程是以小见大的、简易直捷的。小者为心,大者为宇宙与本体。白沙自述其为学成德的过程为:其于静坐之中“见吾此心之体”,并将心体核验于万物之理和圣贤训导,发现自己的心得“各有头绪来历”[7]80-81,可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13]289。能达到宇宙和本体境界的人无论身处何方,皆可运用光明呈露之心体以应对周遭万事,其境界并非仅是想象和主观感受,而是能落实到日用常行中,借用《尽心知性赞》的话来说便是在廓然心境中感知并实现“心” “性” “天”之间的融通。
总之,陈献章宇宙境界和本体境界的基源皆为邵雍之学。也正因如此,人们对陈、邵二人境界论的批判往往相类,与朱熹认为《尽心知性赞》近佛相呼应,《明儒学案》用“似禅非禅”[7]5评价陈献章,这再次佐证了白沙与邵雍间的相似处。
(二)太和境界、虚明境界与道家思想
在明代,岭南人的情怀“与道家接近”[14]28。白沙的祖父“好读老氏书”[1]868,其父亦极崇尚自然,道家思想对陈献章的影响以家学为主要载体,这使得白沙诗文中时常出现老子遗风、南华余韵。
以《湖山雅趣赋》为例,其中的“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间”和“物我于是乎两忘,死生焉得而相干”带有鲜明的庄子思想色彩,具体言之:“形骸之外”出自《德充符》;“俯仰宇宙之间”化用自《让王》“立于宇宙之中”[15]966;物我两忘结合了《齐物论》的“吾丧我”[15]44和《大宗师》的“两忘而化其道”[15]242,对待生死的豁达态度更是庄子哲学基调之一。不仅《湖山雅趣赋》如此,《嘉会楼》亦然,其诗云:“残碣旧诗犹有迹,沧波烟艇已忘情。却怜扰扰浮生梦,欲向先生问八冥。”[1]959“忘情”本于《德充符》的“无情”之论,“浮生”本于《刻意》“其生若浮”[15]539,“梦”这一意象在《庄子》中十分常见,陈献章也常融梦于诗,“这与他所受的老庄家教密切相关”[14]30。理解陈献章的家学背景,有助于我们领悟其笔下的太和境界和虚明境界。
根据《题冷庵》,太和境界是“以道眼观”所得之境。何谓“道眼”?应结合白沙其他诗文中的“道眼”来理解此问题。《洗竹》云:“道眼看圆成。”[1]515《浮螺得月》云:“道眼大小同,乾坤一螺寄。东山月出时,我在观溟处。”[1]522据此,“道眼”是观物之眼,在道眼的审视下,万物呈现为圆融混成、大小齐同的状态,这指向《庄子·秋水》中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15]577。以道观物,所得为事物的齐同性,而道本身就是齐同性的象征,因其代表着万物的共同本质,所以,“道眼”所观的对象亦是道,这一推论合于湛甘泉对《浮螺得月》中“道眼”的定义:“道眼,见道之眼也。”[1]793《浮螺得月》与《藤蓑》异曲同工,二者都描述陈献章在月光之下面对沧溟,从而体悟本体,所不同者在于,《藤蓑》中的本体是作为白沙心学关键概念的心体,《浮螺得月》中的本体是与道家思想有深刻联系的道体,“见海之浩漫洪蒙而知道体之大无穷尽,即所谓道眼也”[1]793。总之,“以道眼观”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以道眼观物;其二,见道体之眼。
实际上,“道体”和“道眼”未出现在《庄子》中,反而常见于宋明理学著作。朱熹在注释“逝者如斯夫”时写道:“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13]113朱子还认为庄子“见得道体”[9]369。亦有众多宋明儒者将立足本体的观物之眼称为道眼。
那么,是否还能将道体、道眼视为陈献章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佐证呢?笔者的回答是:能。原因如下:陈献章笔下的道眼可以齐万物、见本质,道体是万物的本质而非仅限于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准则;而在朱熹等人笔下,道体虽指形而上的存在,但主要指人在人世伦常秩序的限制下、经历一系列修养工夫以后才能体悟者,具有属人性。朱熹认为,惟博文约礼、克己复礼可使人“见道体卓尔立在这里”[9]965,所见之道体亦在礼的格局中展开,而礼讲求差序与等级,是齐同性的反面。明代儒学家中,对道眼有所论述的人较多,兹举两例:刘宗周曰:“世人无日不在禽兽中生活,彼不自觉,不堪当道眼观。”[7]1542顾宪成曰:“以道眼观,通身皆道也。”[7]1393可见,与陈献章笔下的道眼不同,纯粹儒学语境中的道眼指发掘人性中道德规定性之眼光,道体为道德准则之根源,是剥落气质之性后才能呈露的天地之性,能否用道眼观物,取决于被观之物的状态,面对毁坏伦常之人,便不宜用道眼观之。所以,“道体” “道眼”虽非《庄子》术语,但白沙的道眼和道体思想显然更近于《庄子》而非儒学,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道体、道眼视为陈献章受到道家影响的佐证。当然,白沙以道眼观道体的思路并非弃绝道德准则,而是以审美的方式创新运用《秋水》中的“以道观之”,不脱离亦不局限于人世伦常,走进却不陷溺于万物齐同主义。
“以道眼观”落实为具体的观物方法,便是虚明以观物,将此方法发挥到极致,便可得虚明境界。虚者,空也,人清空内心的偏见,“空诸障翳”,站在具有超越性质的道的视角观照世界,超世离尘,由此可以获得对外物的明晰认识。《庄子·庚桑楚》云:“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15]810由正到静,由静到明,再到虚,反之亦然。成玄英在解读《庄子·大宗师》时也使用了“虚明”这一概念,认为真人“智照虚明”[15]231。或许正是这种对万物的虚明观照使得陈献章在进行严谨的哲学思辨和修身存养的同时亦能保留空灵洒落的诗人气质。在以虚观物、明见物性的基础上,主体遣荡了对特定外物的偏好,用《题冷庵》中的话来说,无论外物冷、热,皆不可动摇吾心,主体亦不刻意要求自身远离闹市、遁入山林,由此可得太和境界。杨起元以“太和”描述白沙的人生境界:“蔼然太和,形与性合,人与天侔。”[1]903白沙经历多次宦海浮沉,却仍能顺应自然、纵浪大化,可谓达至太和境界者。虚明境界和太和境界因“道眼”而连接,前者是道眼在观物方法中的形象化,后者是道眼在人生选择中的具体化,两者都是白沙生平事迹和心路历程的映现。
总之,陈献章虚明境界和太和境界的基源都是先秦道家思想。
上述四种境界间有着缜密的逻辑关系。参照本文前言处提出的山腰和顶峰之喻,太和境界和虚明境界为山腰,即较高的境界,在此境界中,白沙与外物为主客关系,虚明以观物、太和以应物,并且,这两者互相促进;本体境界和宇宙境界(近似于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为顶峰,即最高的境界,在此境界中,白沙与外物为一体关系,我心即宇宙。白沙从山腰攀缘而上,终抵顶峰,惟虚明太和者可体悟本体、融通宇宙,惟达至本体境界和宇宙境界者可真正以澄明宁静的心灵游于世间,不同层级的境界具有一体性。
三、陈献章境界论的旨趣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白沙使其境界论拥有了邵雍、老庄所未曾拥有的特殊旨趣——心学旨趣。
心学与理学颇有扞格,陈献章的境界论亦与一些理学家的观点相左。前文指出,陈献章从心境中提炼境界,其方法可谓以小见大、简易直捷,《明儒学案》却以“欲速见小之病”[7]5概括之。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13]145“欲速见小”者因贪图小利、一味求速而耽误大事。朱熹在译解《论语·雍也》澹台灭明行不由径时为该词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径,路之小而捷者。……不由径,则动必以正,而无见小欲速之意可知。”[13]88《眉州刊朱子语类序》云:“文公犹恐长学者欲速好径之心。”[9]9可见,见小欲速指希望修养有捷径可走。
以朱熹关于见小欲速的理论为先声,与陈献章同时代的理学家进一步割裂心、宇宙万物、天理三者间的联系。罗洪先云:“欲从其知之所发,以为心体;……畏难苟安者,取便于易从;见小欲速者,坚主于自信。”[7]413-414罗氏认为,畏难苟安者和见小欲速者都自信地将一己之心中善的萌芽作为圣贤所称述的最高准则,误以为见得本心之善端即是找到了通往天理的方便法门。亦有人将类似批评落实到对陈献章学问的评价中,例如,夏尚朴认为:圣人在求精一执中之道的同时致力于考古稽众,但白沙“直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谓诵习讲说为支离”[7]70,从而掀起了一股抛弃诵习、主张从心中直接获取精一执中之道的风气。与浩如烟海的典籍和外物相比,“心”是小的;与考古稽众相比,率循吾心以求良知是欲速不达的。所以,夏尚朴对白沙的批评可以“见小欲速”概括之。
部分理学家之所以将陈献章境界论中的以小见大、简易直捷误解为见小欲速,是因为他们认为“以小见大”包含着如下困境:复其本心、心体呈露、致良知等虽然于成己有益,但并不能使人直接与理合一,心的觉醒只是为学道路的起点,而非终点,若将其视为终点,便是欲速而不达,是希望在修身道路上走捷径,不仅无法成功,反而有危害自身德性的风险。换言之,理学家对心学家所说的“心”的作用抱有不信任态度,否认心境必能开出境界,即便持有某种心境的主体认为自己达到了最高境界,这一境界的真伪与善恶性质也饱受理学家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冯友兰的境界论也略具理学理论气质,达到道德境界者未必能开出天地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不是一体关系。此说的依据在于境界高低理论,“高低的分别,是以到某种境界所需要底人的觉解的多少为标准”[3]50。据此可推知,觉解愈多,境界愈高,若认为有少许觉解即可达到最高境界,那么便是见小欲速。这不适用于白沙境界论,因为,虽然虚明、太和境界低于本体、宇宙境界,但各境界背后的觉解并没有绝对的少、多之异,两类境界互为依托。
陈献章早已明白见小欲速之害,他回忆诚庵先生曾以“好高欲速,为戒自古”[1]109教导自己,这便是一证。面对理学家的批评,陈献章曾在谈及孔子“吾与点也”一语时为自己进行了间接辩护。据记载,白沙常以“吾与点也”一章教人,章枫山云:“朱子谓专理会‘与点’意思,恐入于禅。”白沙回应道:“朱子时,人多流于异学,故以此救之;今人溺于利禄之学深矣,必知此意,然后有进步处耳。”[7]75朱子认为专理会“与点”(只知道学习曾点春日浴沂时的洒脱恬淡之心境)恐怕将使人入于禅学,因其见小欲速,误将偶然呈现的洒脱恬淡心境等同于曾点的高级境界。白沙则认为,究竟采取何种方法来达至最高境界应以实际情况为转移,宋人受到佛教“顿悟”之说的影响,见小欲速,故需倡扬格物致知之旨以救正之;明人则为名利所束缚,景慕曾点并不会使人见小欲速,反而能促使人看淡名利,复得光明心境和境界,所以白沙尤其注重“吾与点也”在教化过程中的作用。不过,理学和心学之异如同朱陆之异,堪称“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16],因此,对于今人来讲,若要以白沙心学为出发点,完美驳斥理学家对心境与境界之关系的质疑,既非常困难,又无必要。与其陷入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的斗争漩涡中,不如单看陈献章如何在人生实践中落实其境界论,若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陈献章的生平事迹完全符合儒门圣学,那么,无论其事迹背后的哲学依据属于哪一学派、与其他学派存在怎样的抵牾,都可以认为白沙无愧于儒学的真精神,譬如登山,虽路径不同,“而造极登峰,其揆一也”[7]4。《明儒学案》载白沙及其门人“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7]79,这是对圣贤之道的忠实践行,所以,无论白沙境界论是否为哲学真理,其生平都告诉我们:白沙诗文中的四种境界的确是其生命历程和儒家人生哲学的真淳体现,具有超出心学、理学等学派纷争的独特价值。
四、结 语
陈献章思想中的宇宙境界、本体境界受到邵雍之学的影响,太和境界、虚明境界则是陈献章以老庄思想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学的体现。四种境界既为一体关系,也有层次之分。白沙从心境中开出境界的思路带有深厚的心学意蕴,具有注重心体、以小见大、简易直捷的特色,并与理学构成分歧。我们可从陈献章及其门人弟子的品质德行中看出:白沙确实将儒家思想落实到日用常行中,并以此作为接引后学的津梁,彰显在陈献章境界论中的独特的心学旨趣是难能可贵且无可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