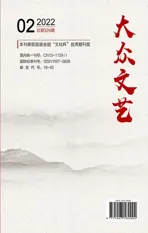从唐前期音乐编年看《破阵乐》的变迁
2022-02-15罗俊峰
罗俊峰
(湖南工业大学音乐学院,湖南株洲 412000)
音乐编年资料是本文立论的重要依据,通过编年的材料来梳理唐代音乐的走向及发展是一种较为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时段界定,由于本文采取纪年方式,其中以618—826年音乐活动记载较为频繁。笔者将所撰唐代音乐编年时间选取自公元618年至826年,即任半塘《唐戏弄》对唐代音乐文化的分期中初唐至中唐(618—826年)的这一时段,期望能从《破阵乐》具体年代的变化中,梳理出以编年形式研究唐代音乐活动、音乐事项前进历史轨迹的新内涵。
一、《破阵乐》变迁的历史过程
《破阵乐》是一部在唐代出现却又止于唐代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乐舞,在燕乐、雅乐表演中,九部伎、十部伎演出中,坐部伎、立部伎的节目中都有《破阵乐》的繁衍形式,而其发展更是贯穿着整个唐代。
作者进行梳理后发现,有确切记载年代的唐代音乐编年中对《破阵乐》进行论述的材料共有九条,分别出自旧唐书、唐会要、文献通考、唐六典、通资治通鉴六部典籍,时间依次为贞观元年(627)、贞观六年(632)、贞观七年(633)、永徽二年(651)、显庆元年(656)、麟德二年(665)、上元三年(676)、仪凤二年(677)、仪凤三年(678)。根据以上材料显示,《破阵乐》乐舞在宫廷的创设与改制主要集中在627年-678年共五十一年间,历经了唐太宗与唐高宗两朝。
具体记载《破阵乐》的事件,如文末表1所示:

表1
《破阵乐》乐舞在发展的过程中曾以多种形式出现,其形式包括纯乐曲、绘制乐舞、添入乐器伴奏,与宫弦合奏等;在《破阵乐》衍变过程中又出现了不同的名称,《秦王破阵乐》《破阵乐》《七德舞》《神功破阵乐》都是其鼎盛功德之形容。笔者以《破阵乐》出现的时间顺序作为主线,对《破阵乐》衍变形式加以论证,以期从材料本身爬梳《破阵乐》的发展过程。
二、以编年材料纵观《破阵乐》演变的内涵
能反映出《破阵乐》变迁的不仅只有其本身的历史记载,通过音乐编年材料扩大具体音乐事类的研究范围,更结合与之相关的其他记载才是能完整地展现《破阵乐》变迁之全貌。在对《破阵乐》改变的前后时间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出《破阵乐》每一次改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其历史线索基本如下:
1.太宗制乐,乐固江山
《破阵乐》于627年第一次登上宫廷舞台时也是唐太宗登基的第一年。太宗“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的感慨,体现出他清楚地知道《破阵乐》本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庄重的场合,但为何严谨不阿的太宗会允许出于民间的《破阵乐》登于雅乐这种有违礼法的事情发生呢?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他期望通过雅乐这种正式、庄严的乐舞类别被大家在政治上所肯定,向大家宣告他的独一无二,这是一种心理暗示的手段。
同时,这一时期太宗注重的是《破阵乐》的发扬蹈厉之声,它能提醒自己得江山之不易和守江山之难为,其后太宗在政治上一直保持着居安思危的谨慎态度,他期望借助乐舞表演提醒自己创业难,守业更难。故素来严谨治国的太宗允许“朕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的世间之乐演奏于雅乐场合的行为也就不难解释。
《破阵乐》在627年第一次演奏之后似乎销声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再无关于讨论《破阵乐》的只言片语。这不得不让人思考,《破阵乐》到底是演出了一次就不了了之,还是一直持续的表演而资料没有记载?直到632年记述创制《功成庆善乐》时提及的“冬至享宴,及国有大庆,与《七德》之舞皆奏于庭”之句,透露出了一系列的信息。《破阵乐》演出时间既有成定式的节庆演出,又有不固定的庆典场合,说明它的演奏并不是依据具体的物理时间,而是依据演出场合的需要。该时期注重的是《破阵乐》的表达功能而不是乐舞本身的娱情功能。
2.太宗改乐,乐兴舞成
(1)舞容
贞观七年(633年)也是将《破阵乐》脱离符号含义单纯作为音乐种类讨论的首次亮相,其中没有音乐描述只有对舞容舞姿的描写。“抑扬蹈厉”就是对《破阵乐》乐舞表演的概括,形容舞者按下与上举、时进时退的动作,或是声音的高低起伏,完全是模拟战争时的情形。
(2)普通观众眼中的《破阵乐》表演
不论从场面还是声音的模拟上,《破阵乐》乐舞都是十分精致而宏大的,足以感染在场的所有观众。而观众的反应又如何呢?在观看完《破阵乐》的表演后,在场的武臣将士不禁感叹:“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这是群臣对《破阵乐》乐舞的评价,也是对唐太宗的评价。
(3)有话语权者对《破阵乐》的态度
对于该条材料,很有趣的是谏臣魏徵的反应:“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者辄俛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
633年这条资料是太宗对《破阵乐》进行的最后讨论,之后再也没有关于太宗讨论《破阵乐》的记载。
3.高宗即位,悲痛禁乐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高宗即位之际便将乐悬及享群臣并停,其中必然包括《破阵乐》,此举可以理解为高宗的一片孝心和对太宗的追思之意。
高宗除了面对强势的父权而诱发的“阉割的焦虑”,另一方面还有来自朝臣的压力。就乐舞而言,“《破阵乐舞》者,情不忍观”证明乐舞自633年改制、制乐舞图的几十年间一直保持着“发扬蹈厉、百战百胜之形容”的原貌,可见乐工在表演《破阵乐》时倾注了较多的感情,一部乐舞能得如此实属不可多得。而在高宗“所司更不宜设”的诏令下“惨怆久之”是一种损失,进一步证明了《破阵乐》只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一时期大家所关注的《破阵乐》是政治的一种外化形式。
4.高宗论乐,再定宫悬
656年高宗改立太子,君权一步步集中证明高宗已经摆脱太宗的阴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对太宗的态度也有所变化,由656年对《破阵乐》的改制可见一斑。
高宗651年下令不设《破阵乐》以后没有提道乐舞演奏的任何信息,也没对乐舞有什么改动之处,但是656年独独修改了乐舞名称。其实高宗也并不需要乐舞本身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破阵乐》不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只是太宗权力的代表。
《破阵乐》以其“纪功旌德”功能歌颂太宗的功业,变为祭祀雅乐武舞的《神功破阵乐》此次改制后规模更加宏大,舞者形象虽然依然是“披甲执戟”,却增加了乐队“箫、笛、歌、鼓”等乐器编制,还与此前不同的是《破阵乐》“若舞即与宫悬合奏。其宴乐内二色舞者,仍依旧别设”,这种与宫悬合奏、合钟磬而歌舞的表演形式增添了《破阵乐》庄重的风格。
5.高宗论乐,乐不入雅
高宗积极创制属于自己的《上元舞》,而将《破阵乐》请入太庙暂废不用。其实并不是《神功破阵乐》不入雅乐,而是有了“更适合”的《上元舞》来替代《破阵乐》这一重要位置。
这个时期他不担心自己政治不稳定,也不担心臣民会否定他的功绩。他考虑的是上天会不会认同自己,他是否是“奉天承运”的绝对权威,以什么样的乐舞祀神可以通天,哪怕是再次运用已经废止的《破阵乐》也要把握住。观念、视角转变,接踵而来关注的方向就转变了。
6.乐成而奏,追思先祖盛德
仪凤三年七月八日(678)唐高宗在九成宫咸亨殿设宴,入座之宾包括韩王元嘉、霍王元轨及南北军将军等人。在音乐演奏过程中太常卿韦万石上奏,奏曰:“《破阵乐》是太宗即位宣扬‘宗祖盛烈’的乐舞而应当被后世继承,并传于后世,然而高宗即位后将该乐舞废停,故请奏《破阵乐》感念先祖”,此处笔者以为韦万石为代表的大臣应该是对高宗废止《破阵乐》有一定意见的,却不能以这种理由对高宗提出疑义。所以韦万石奏请高宗的理由并不是对高宗废止《破阵乐》有所不满,而是担心《破阵乐》废止而愧对其职,是担心礼制不妥,故应奏先祖之乐彰显祖宗的圣德与功绩,感念先祖、与天同乐。面对韦万石冠冕堂皇的理由高宗也不得不妥协,表示“上矍然改容,俯遂所请,有制令奏乐舞”。
细数高宗时期六次对《破阵乐》的讨论可分为四个时期:651年以“情不忍观,不宜设”为由久不演奏而“惨怆久之”为第一时期,唐高宗感于太宗强大的压力将《破阵乐》搁置,高宗即位之初关注的多为庙乐等;656年将《破阵乐》改为《神功破阵乐》,而665年增加《破阵乐》的乐队编制,此为第二阶段,伴随着对《破阵乐》名称、乐队编制的改变,高宗对《破阵乐》的注意力转移到乐舞本身;第三阶段高宗新造《上元舞》替代了《破阵乐》的地位,《破阵乐》虽成为高宗与大家热议的话题却并未付诸演奏,其内容有676年诏曰“《破阵乐》不入雅乐”而罢之;677年对《破阵乐》进行讨论,结果为“待修改讫”;第四阶段《破阵乐》重新搬上舞台,上下涕泗交流,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其舞容仍是让人念及太宗之盛烈。
三、依托于音乐编年的音乐研究
如若只是将材料按时间顺序罗列而进行平铺直叙地解读,便与一般音乐专题研究无异。音乐编年要求的是对每个时间点上的音乐事件和人物进行前后联系,给予全盘地考虑以突显同一音乐事项在不同时间节点内的不同表现,从相对外围的材料去关注被学者忽视的层面。笔者整理唐代音乐编年下的《破阵乐》犹是如此。
《破阵乐》与太宗之威名是分不开的,它由民间所奏的歌舞一跃登于雅乐,而在宫廷宴群臣的场合演奏,与唐以前的雅宴之乐泾渭分明形成天壤之别,除了说明当时音乐之风开明外,《破阵乐》在雅乐中的确立更代表太宗地位的确立。太宗在政权确立之初适时地运用乐舞这种形式和乐舞的内容来强化自己形象和统治,可见《破阵乐》脱离其音乐本身之外对臣民的教化性。
几年来《破阵乐》一直持续在冬至享宴和国有大庆时进行演奏,这正是太宗政治稳定、音乐之风开明的最好见证。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只有环境稳定时《破阵乐》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于是到了贞观七年,由太宗亲自制作乐舞图,然后由吕才紧锣密鼓的排练,最终以超高效率在宫廷演奏。此时《破阵乐》的记载与627年截然不同,此时的《破阵乐》几条材料无一例外地集中到《破阵乐》舞图所绘之队形、人数、衣物、道具等乐舞细节。这一时期《破阵乐》变迁是以乐舞本身形制发展为主的,注重的是其娱乐性,但《破阵乐》舞容乐风的发展同时也少不了皇帝对音乐的支持。
王权更迭到了高宗朝,高宗对《破阵乐》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将其下令废止。对高宗来说《破阵乐》就是代表太宗的政治符号,为了避免群臣观赏《破阵乐》时联系新旧政权进行比较。其后高宗接受《破阵乐》并为其改名、改乐队编制而开始关注到乐舞本身,关注《破阵乐》音乐性、娱乐性也是高宗政权稳定的产物,此时《破阵乐》的记载呈现出一片和谐的音乐讨论之风。
高宗朝制作的《上元舞》接替了《破阵乐》的地位,一跃成为执朝者的代名词。此时新制的乐舞、庙乐层出不穷,《上元舞》自然而然地接替《破阵乐》承担常奏于庭的工作。678年经太常少卿的奏请,《破阵乐》作为宣扬祖宗盛烈的前代乐舞不能束之高阁,对太宗哀思甚久的高宗在听完多年未竟的《破阵乐》后“欷歔感咽”。这一刻体现的都是《破阵乐》作为乐舞,追思往日、祭天、祀先祖的功能。
“教化性—娱乐性—功能性”,这体现的是一个循环过程,是乐舞伴随着政权更迭体现的不同内涵。在政权建立之初统治者更加关注的是乐舞所彰显的意义,如何教化民众。无论是太宗政权建立之初将歌颂自己功德的《破阵乐》作为雅乐演出,或是高宗在政权建立之初废止《破阵乐》演出,都是看到《破阵乐》所表现的具有确立统治或代表政权的意义,以礼乐体现政治意图。
随着统治稳定、文化开明、音乐之风盛行,乐舞的音乐性、社会性随即得到体现。太宗体现为制作《破阵乐》舞图并令吕才教乐工,高宗体现为改制《破阵乐》的乐器、演奏形式等。这一时期的音乐不再拘泥于政治讨论,不再局限于它所表达的意义,纯粹只是在乎其乐舞形制、舞容舞风的变化,与音乐本身更加贴近而具有艺术价值。
在不同时期着眼于乐舞意义、乐舞形制的侧重点后,到了政治统治成熟期开始关注乐舞的功能。古人以为音乐能通天感地,尤其具有祭天、祀先祖的功能。于是当政权稳定成熟便开始反观自己的政治得失,他们期望用音乐沟通天人,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
政权建立之初,以乐舞确立、稳固统治,教化民众;政治稳定,开始关注音乐本身,注重其音乐性和娱乐性;稳坐江山时开始观统治的天人得失,偏重音乐祭天地、祀先人的功能。如此循环往复,便是古代音乐伴随政权更迭、发展笼统之常态。古代音乐虽然一直伴随于礼,依附于政治,但也促成了一代代开明的音乐之风。
注释:
①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34页唐代分期及依据:“初唐,618-712年;盛唐,713-755年;中唐,756-826年;晚唐,827-906”。
②《新唐书•礼乐志》:“贞观初,更隋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凯安》,郊庙朝会同用之,舞者各六十四人”.《凯安》是唐代郊祀乐舞之一,665年武舞《凯安》变为《破阵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