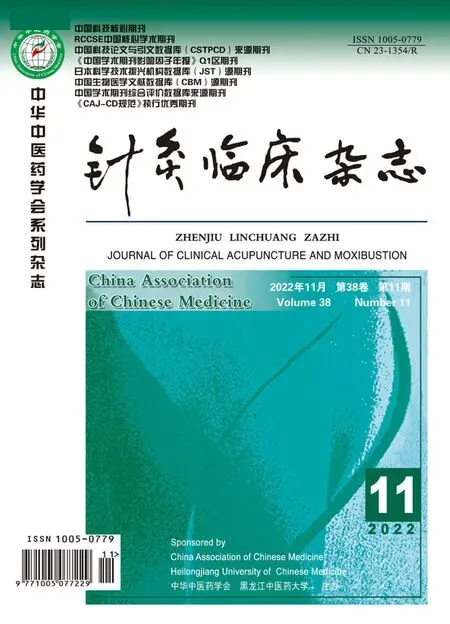基于“脑肠交互”探讨针灸治疗功能性胃肠病的效应机制
2022-02-14徐枝芳李亚男姚开芳陈志翰
张 悦,徐枝芳,2,3,李亚男,姚开芳,陈志翰,郭 义,2,3△
(1.天津中医药大学实验针灸学研究中心,天津 301617;2.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1617;3.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
功能性胃肠病(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FGIDs)是消化科常见的一类疾病,症状包括腹胀、腹泻、便秘与腹痛等,呈慢性、复发性和组合性的特点。根据最新的Roma Ⅳ指南[1],FGIDs可根据解剖位置、病理生理学和诊断学特点分为33类,较为常见的有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FD)、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大便失禁等,这些疾病在同一个患者身上也可能出现重叠。遗传、心理、饮食、环境与炎症等多因素交互作用导致了FGIDs。相关流行病学资料显示,该病在全球的发病率高达40%[2],女性患者多于男性,其中20%~25%的患者有严重的消化系统症状,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同时,FGIDs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给患者身心健康和社会生活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现今针对FGIDs的治疗方法仍主要采用对症治疗和抗抑郁治疗。因此,如何根治FGIDs及综合治疗其并发症仍是世界医学的难题。
脑肠轴是中枢神经系统与肠神经系统之间形成的双向通路,是“脑肠交互”的结构基础。通过脑肠轴,来自大脑的信号会影响胃肠感觉、运动与分泌方式以及肠道菌群;相反,胃肠神经、免疫、内分泌与肠道菌群信号也会影响大脑功能。FGIDs与脑肠轴功能紊乱关系密切。针灸是治疗FGIDs的绿色安全疗法,既往对其机制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对单一靶器官的调节作用,或从神经、内分泌与免疫单方面阐释针灸对脑肠轴紊乱的调节作用,不能完全阐明针灸治疗FGIDs其复杂症状的内在机制。因此,基于脑肠之间相互复杂作用探讨针灸治疗FGIDs的机制对针灸治疗该疾病的机制及临床研究至关重要。本研究拟从针灸治疗FGIDs的临床现状、与FGIDs病理相关的“脑肠交互”障碍和针灸基于“脑-肠”整体治疗功能性胃肠病的效应机制3方面阐释“针灸-脑肠交互-FGIDs”机理,以期为针灸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1 针灸治疗功能性胃肠病的临床研究现状
针灸被认为是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有效选择,并作为FGIDs的一种补充和替代疗法在全球广泛应用。1项1 075例的多中心、非劣效性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表明[3],在8周的治疗期间,电针双侧天枢、腹结和上巨虚穴能缓解慢性严重功能性便秘症状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与假针刺(非穴位浅刺)相比,取中脘、上脘、下脘、气海、天枢、足三里、内关、百会、神庭与印堂针刺治疗4周能明显缓解餐后窘迫综合征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且治疗效果可持续12周[4]。以上多中心、高质量的临床试验结果肯定了针灸治疗FGIDs的疗效及安全性。然而,根据GRADE评级,目前针灸治疗FGIDs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大多质量较低,主要原因有样本量不足、盲法缺失及针灸治疗方案具有异质性和缺乏长期随访等[5]。因此,未来应该进行更多的多中心、随机和双盲的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以期为针灸治疗FGIDs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提供更强有力的证据。
2 与功能性胃肠病病理相关的“脑肠交互”障碍
“脑肠交互”是脑-肠双向通信的动态交流过程,中枢神经系统通过神经投射和神经内分泌途径精细调控胃肠功能,胃肠神经、免疫、内分泌信号与肠道菌群信号反馈影响中枢对消化道信号的处理。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异常会引起与之关系密切的肠神经系统功能改变,反之亦然,这被称为“脑肠交互障碍”,现有证据表明FGIDs由“脑肠交互障碍”引起,其机制涉及中枢(心理应激)和外周(胃肠粘膜炎症、肠道菌群紊乱和内脏超敏反应)方面[1]。
根据FGIDs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心理社会因素被认为是FGIDs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脑肠轴为心理应激诱导胃肠功能紊乱提供了自主神经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两条中枢至消化道的下行传出通路,胃肠功能受自主神经支配,心理应激导致交感神经张力增加、迷走神经张力降低[6],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发FGIDs消化道症状,如吞咽困难、便秘和腹泻等;另一条关键通路是HPA轴,在心理应激状态下[7],中枢调节下丘脑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CRF),激活CRF信号通路引发局部炎症反应,增加肠上皮通透性。此外,“脑肠交互障碍”会导致血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VIP)、P物质(Substance P,SP)与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等神经肽过度分泌。肠道免疫系统包含多种免疫细胞,如肥大细胞能够表达多种受体响应来自中枢神经的激素、神经递质和神经肽的刺激,激活的肥大细胞脱颗粒会进一步释放大量炎性因子、5-HT、组胺与蛋白酶,加重炎症并激活肠神经元引起痛觉过敏[8]。肠道免疫微环境失衡可能更易于有害菌的定植,造成肠道菌群紊乱——表现为有益菌数量减少,有害菌数量增加。有害菌群的代谢产物可直接作用于肠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或肠免疫细胞加重炎症和疼痛信号传导[9]。此外,急性胃肠感染后部分患者肠黏膜仍存在的慢性炎症也是诱导FGIDs发病的因素之一,感染诱导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β与细菌内毒素会穿过血脑屏障,影响下丘脑CRF神经元并激活HPA轴[10],导致胃肠功能紊乱。
胃肠感觉神经元上的伤害性感受器被类胰蛋白酶、组胺、前列腺素、ATP、腺苷与炎性因子等炎症信号反复激活[11],导致其敏感度和反应性增加,引发FGIDs“外周痛觉敏化”。感觉神经元上的G蛋白偶联受体激活导致瞬时受体电位离子通道(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ion channel,TRP)的开放与敏化。TRPV1的激活引发局部CGRP、SP等神经肽释放,从而放大疼痛信号;TRPV4的激活诱导ATP胞吐并作用于黏膜下神经的ATP受体导致内脏感觉神经元持续激活[12]。此外,TRP通道还能够直接检测并对机械、温度及化学刺激做出反应,FGIDs常常表现为胃肠对机械扩张、温度、食物及环境(炎症、肠道菌群)刺激的敏感度增加,这与TRP通道的敏化相关。伤害性信号从肠道传入中枢,谷氨酸、γ-羟基丁酸与甘氨酸等神经递质介导了中枢敏化过程,首先敏化的部位是脊髓背角,脊髓背角汇聚内脏疼痛信号,此部位的敏化不仅会导致其对胃肠道的伤害性信号反应性增强、脑干及丘脑相关核团兴奋性增加,还会导致感觉神经元对躯体其他刺激反应增加,引起牵涉痛[13]。脑区的功能异常也是内脏超敏反应发展和维持的重要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IBS患者对直肠扩张和疼痛的脑激活区域与健康人有所不同[14],且情绪和内脏感觉加工相关的脑区也有明显结构和功能连接性的改变[15]。慢性疼痛引发的不良情绪可能进一步加重FGIDs患者病情,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如何纠正“脑肠交互障碍”是治疗FGIDs的关键。
3 针灸通过“脑肠交互”治疗功能性胃肠病的效应机制
3.1 针灸对脑肠轴相关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调节作用机制
针灸的作用特点是通过激发或诱导体内的固有调节系统,即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endocrine-immunity net work,NEI),恢复机体内稳态。针刺信号在中枢经过复杂整合后,可激发自主神经通路、HPA轴调节下游免疫网络,并进一步调节肠道菌群,调节FGIDs患者胃肠稳态,恢复其胃肠功能。
3.1.1 通过交感神经脊髓反射抑制胃运动 早期研究表明,针刺腹部穴位如气户、梁门及气海能通过激活胃交感神经分支传出神经活动抑制胃运动[16-17]。
3.1.2 通过迷走-胃肠投射系统促进胃肠运动 电针足三里穴能够通过增加迷走神经活性,抑制由迷走神经胆碱能神经元介导的交感神经活性增强,进而改善FD大鼠的胃运动延迟。此外,电针刺激四肢(曲池、上巨虚与足三里)、背部(胃俞)和腹部(天枢)穴位均能通过激活胆碱能通路促进远端结肠运动[18]。进一步研究发现,电针足三里穴通过抑制迷走神经背核中突触前μ-阿片受体表达,增强了N-甲基-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receptor,NMDAR)介导的突触传递,进而增强迷走神经活动[19]。另有研究发现[20],电针胃俞同样增加了NMDAR介导的迷走神经背核突触传递,促进了胃运动,这提示迷走神经主要介导了针刺促进胃肠运动过程,且该过程可能具有相同的中枢内机制。
3.1.3 通过迷走神经-免疫途径抗炎 电针足三里穴能够抑制迷走神经背核胆碱能神经元中的γ-氨基丁酸A型受体表达,从而刺激迷走神经活动,上调肠肌中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Ach)、α7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α7nAChR)表达水平,巨噬细胞等合成和分泌细胞因子的细胞上Ach与α7nAChR结合后通过激活JAK/STAT信号通路抑制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的释放,减轻胃肠炎症反应[21]。
3.1.4 通过纠正HPA轴功能紊乱缓解内脏超敏反应 急性精神压力状态下,FGIDs患者的HPA轴常表现为过度激活状态,CRF、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hormone,ACTH)显著升高[22]。研究表明,艾灸命门穴能够降低IBS大鼠血清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RH)、ACTH与皮质酮含量[23]。电针天枢足三里、三阴交与太冲穴可降低IBS大鼠下丘脑中CRH及其受体CRH-1R在下丘脑中的表达,恢复下丘脑CRH至正常水平,同时降低胃肠黏膜中CRH-1R表达[24]。
3.2 针灸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针灸能够有效调节IBS大鼠模型肠道失衡,增加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及有益菌丰度,降低有害菌丰度[25-27]。进一步研究其机制发现炎性小体-6(Nod-like receptors 6,NLRP6)可能是针灸调节肠道菌群的关键靶点。NLRP6在肠道中高度表达,一方面其能通过抑制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NF-κB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传导通路,下调炎性因子表达进而抑制炎症反应;另一方面其能够通过促进抗菌肽分泌,参与塑造肠道菌群-宿主互作界面,调节肠道菌群稳态。Bao CH等发现[28],艾灸足三里、天枢穴能够增加IBS模型大鼠肠组织中NLRP6的表达,降低大肠杆菌丰度,升高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和普拉梭菌数量,同时降低白介素-18(IL-18)等炎症因子表达,抑制肠道炎症。然而,NLRP6是否介导针刺调节肠道菌群的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3.3 针灸对功能性胃肠病痛觉敏化的调节作用机制
针灸能够缓解FGIDs引起的腹痛和牵涉痛,在其外周机制方面,针灸一方面通过影响肠神经元——免疫细胞互作改善肠道微环境,抑制伤害性信号产生,改善FGIDs内脏超敏反应。艾灸或电针双侧上巨虚穴可降低结肠中肥大细胞数量及肥大细胞脱颗粒率[29],下调肥大细胞TLR4表达[30]。TLR4表达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肥大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中,并通过核转录因子-κB(NF-κB)/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途径启动细胞内信号转导,促进炎症介质的合成和释放[31]。因此,抑制其活化能够降低结肠炎性因子水平,缓解IBS大鼠的内脏高敏感性。此外,电针足三里穴可抑制TLR4/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通路降低结肠组织M1型巨噬细胞表达,上调M2型巨噬细胞表达,进而下调结肠巨噬细胞中NLRP3/IL-1β,抑制结肠及血清中IL-6、IL-12、IL-17、TNF-α和血清干扰素-γ(IFN-γ)等促炎因子表达,减轻肠道炎症[32]。另一方面,针灸能够通过抑制关键神经肽SP、降钙素相关基因肽(CGRP)及5-HT等表达[33],抑制痛觉信号传导。
中枢水平,艾灸天枢、上巨虚穴能够降低脊髓背角中NR1和NR2B的表达,抑制兴奋性谷氨酸盐与NMDA受体结合,减少激活的钠离子通道数量,从而抑制蛋白激酶C调节区功能,抑制中枢痛觉传导过程[34]。进一步细胞内信号通路转导研究发现电针足三里、上巨虚穴能够抑制脊髓背角中P2Y1受体及其下游PKC和ERK 1/2的磷酸化,进一步抑制星形胶质细胞的活性[35],减轻神经炎症,抑制脊髓水平痛觉信号传导,从而缓解IBS大鼠内脏超敏反应。
4 小结
脑肠轴是针灸调动多靶点、多系统调节胃肠功能的结构基础,现有研究已经证明,针灸能够激活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双向调节胃肠运动;激活胆碱能抗炎通路作用于免疫细胞,抑制肠道炎症;调节HPA轴,抑制内脏超敏反应;同时可纠正肠道菌群失衡,改善肠道微环境;并经多条途径抑制FGIDs的痛觉敏化。以上机制提示针灸能够通过调节脑肠轴交流环路中多个作用靶点改善FGIDs的相关病理进程和症状。此外,研究证实针刺不同部位腧穴可激活不同自主神经通路双向调节胃肠运动,去年发表在《Neuron》上的1项研究发现[36],后肢区域的低强度电针会驱动迷走神经-肾上腺轴,产生依赖于NPY+肾上腺嗜铬细胞的全身抗炎作用,而腹部高强度的电针通过脊髓交感神经轴激活NPY+脾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抗炎,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针灸驱动不同自主神经通路调节胃肠运动、抗炎的穴位特异性和强度依赖性,胃肠道运动功能紊乱和肠道炎症是FGIDs的显著病理特点之一,进一步探索自主神经在针灸治疗FGIDS中的作用将有助于针对FGIDs的复杂症状优化临床治疗方案。目前,对FGIDs病理机制的研究已有卓越进展,针灸调节“脑肠交互”过程,如“针刺-神经-免疫”机制也已取得初步进展,但要阐明针灸调节自主神经、HPA轴与免疫细胞和肠道菌群之间的上下游关系或可能产生的级联反应,仍需深入研究。因此,未来基于“脑肠交互”复杂作用,系统整体地把握针灸作用机制将有助于最大发挥针灸效应,提高针灸治疗FGIDs的临床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