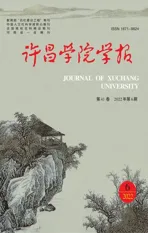论约翰·海恩斯的荒野价值观
——至善至美*
2022-02-14刘丽艳
胡 英,刘丽艳
(大理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部,北京 100083)
关于荒野价值的讨论,20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有众多的声音。福尔曼(Dave Foreman)在《一个生态战士的自白》(ConfessionsofanEco-Warrior)中声称,保护荒野是“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是一种宗教的授权”[1]3-4。克罗农(William Cronon)在其里程碑式的论文《荒野的问题》(“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中却指出,“荒野”不过是我们人类对于“已经在那儿”[2]49的一部分所给的命名而已,他强调荒野是一个概念而非实际事实。某种程度上,在他这里,荒野已沦为“文本化”(textual)(1)麦克·科恩(Michael Cohen)、塞缪尔·海斯(Samuel P.Hays)等持类似意见,对于克罗农(Cronon)的反对意见也来自《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后续文章,这里主要参考《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1996,29-46.)的概念。然而不论荒野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不受人类控制的实际存在,还是一种人类文化的构建之物,不容置疑的是,“野性(wildness)绝不是人类的构造”[3]38。因此归根结底,关于荒野价值的讨论主要还是基于实际荒野的基本特征。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对于荒野的情感日趋理性,他们虽意识到荒野具有独特的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但没有像浪漫主义者那样一味地强调保存纯净的荒野,使其不受任何干扰。很多文人来到荒野亲身体验,他们从荒野中找到灵感与顿悟,并尝试客观地记录他们在荒野的经历与感悟,从而发展出一种荒野美学。有的发现沙漠生活的宁静之美,如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1927—1989)的《大漠孤行》(DesertSolitaire:ASeasonintheWilderness)帮助人们改变了对沙漠的传统看法,并且提出“自然不是为人类而存在,而是为其自身而存在”[4]228的观点。有的退居山林,体验荒野,如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1945—)、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约翰·海恩斯(John Haines,1924—2011)等。他们运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来发现荒野之美,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客观地呈现荒野,对他们来说,荒野与其说是无人践踏之地,还不如说是一种心态、一种野性的力量,所以他们提倡在自己的后院中去发现自然的野性。海恩斯更是彻底放弃文明生活,来到阿拉斯加的荒莽之地过着狩猎、种植的自给自足的简朴生活。他生活在阿拉斯加长达二十余年,那里的荒野“使他获得重生”,荒野既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也是他作品描述的对象。
一、传承与突破——亲历荒野的桂冠诗人
海恩斯是美国最后的边疆——阿拉斯加——的桂冠诗人。他一生有二十余年住在人迹罕至的阿拉斯加的理查逊外围,在那里他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猎人、农夫和自由撰稿人。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来进行诗歌和散文创作,视阿拉斯加荒野为家,认为这片荒芜之地是令他重生之地,让他的身体与精神能安稳扎根。海恩斯的诗歌就如他所生活的阿拉斯加一样纯净而简洁,那里独特的环境造就了他寒冷而具有穿透力的诗歌风格。
海恩斯的一生是追求稳定性的一生,他欲寻求一个安身之所、精神之根。他就是在阿拉斯加广袤的荒野中找到了这种稳定性,因为在他看来,“城市的生活缺乏某种重要的东西”[5]12,而“与城市相反的荒野生活是至善至美(summum bonum)的”[6]43。在海恩斯看来,荒野就是避难所,令其平静,可以思考。他强调个人与荒野的接触,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一个“内在深处”(nterior place),需要在实际风景中寻找一个“对应之处”(counterpart),而阿拉斯加就是他的对应之处。荒野之于海恩斯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近乎完美的品质:“至善”在于其野蛮而简单,包容而开放,自由又令人自律;“至美”在于其古老而深沉,丰富而和谐,纯净而富有活力。
说到海恩斯关于荒野的看法,首先就要提到对他影响深刻的前辈杰弗斯。在海恩斯的诗歌中,沉默的风格非常明显。“如果说杰弗斯的‘非人类主义’的衣钵传承下来的话,那么一定是传给了海恩斯。”[7]91在海恩斯最好的诗歌中,似乎人类比较少见,非人类的其他事物倒做了主角,某种程度上,他的诗歌好像是一部地理的编年史。比如诗歌《家园》(“Homestead”)的开头描述了诗人在阿拉斯加的家:
自我来到理查逊山
已经近三十年
黑暗中将一捆木板
搭成帐篷,生起火
在一个发黑的锅中
用勺子搅拌古老的豆子[8]128(1-6行)(2)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中提及的诗句均为作者自行翻译。
这个家看起来平凡而古老,完全没有20世纪末文明社会的气息,反而让人想起几千年前生活在自然当中的古老的人类。接下来诗人说:
我来这儿干吗呢?
来看看摇曳和跳动的阴影,
听听水声,
和睡眠中的鸟,
还有老人呻吟中的颤抖。
这片土地慢慢地交出它的意义……[8]128(7-12行)
海恩斯诗歌中的“我”总是显得非常自然,毫不突兀,诗歌听起来像是在低吟,他自己往往不是中心,而生活的细节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灰烬”“火花”或是“小小的稳定的火焰”才是一切的中心。渺小的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不过是“一小撮浆果在矿工提桶中/跌倒时的声音”(42-43行)。他的诗歌是一种温和的敦促,提醒我们自然事物的平衡与人类贪婪的徒劳,并让我们意识到“土地不会原谅我们”的掠夺。
关于杰弗斯,海恩斯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迎接天启:作为预言家的诗人:关于罗宾逊·杰弗斯说略》(“Welcome to Apocalypse:The Poet as Prophet:Some Notes on Robinson Jeffers”)(3)此文收录在海恩斯的散文书信集《后裔:精选文章,评论和信件》(Descent:Selected Essays,Reviews,and Letters.Fort Lee,New Jersey:CavanKerry Press Ltd,2010.),第23-33页。的文章。一开始海恩斯就承认说:“在诗歌方面罗宾逊·杰弗斯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榜样,我在刚刚开始认真写作时就发现了他的作品,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我一直喜欢的现代诗人之一。”[9]23海恩斯在文中并非以一个批评家或学者的角度来评判杰弗斯,而是以一个诗人的角度来探讨他如何受到前辈诗人杰弗斯的影响。他指出,杰弗斯用他那经典的、具有《圣经》般权威感的诗歌,像一个预言家一般对人类说话,话题包括人性与上帝之间、人性与自然之间以及人性与人类本质之间的争斗。“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有人在其作品中展示了天启的主题,那么一定是他(杰弗斯)。”[9]24
也许是受到杰弗斯的影响,加之海恩斯自己在阿拉斯加荒野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他对于自然荒野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感受,对于人类文明也有了更加深刻的反思,因此在海恩斯看来,我们所熟悉的生活就如“一辆行进在黑夜中的火车,/它已断裂,没有刹车,/不断加速,在黑暗中冲向山谷”[8]115(《滚回来》“Rolling Back”)。他就这样对人类文明的将来做出了预告,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提出了警示。正如诗人缪尔在其重要著作《诗歌的身份》(TheEstateofPoetry)中所言:“伟大的主题被伟大地述说,也许能令诗歌回归其古老的地位。”[9]33(4)转引自海恩斯散文《迎接天启:作为预言家的诗人:关于罗宾逊·杰弗斯说略》(“Welcome to Apocalypse:The Poet as Prophet:Some Notes on Robinson Jeffers”),散文选自海恩斯·约翰所著《后裔:精选文章,评论和信件》(Descent:Selected Essays,Reviews,and Letters),第23-33页。杰弗斯和海恩斯这种叙述人类与地球命运的诗人也许就是令诗歌恢复其伟大地位的诗人。
然而,比起杰弗斯那种极端的“非人类主义”思想,海恩斯显得更加客观和理智,他通过自己亲历荒野的独特体验,从阿拉斯加这个特定的地方出发,将视野投放在整个地球甚至整个宇宙。由于海恩斯与阿拉斯加的独特联系,人们往往聚焦于其作品中的阿拉斯加元素,将他削减为一个地方作家,然而这种做法误解了海恩斯作为散文家与诗人的地位。作为一个散文家,他是一个地方作家,他的作品《星,雪,火》通过记录他在阿拉斯加将近25年的生活点滴,成为与《瓦尔登湖》《沙郡年记》并列的世界三大自然随笔。但是作为一个诗人,海恩斯却是一个从地方出发走向宇宙与普遍存在的重要诗人,“如果说他是地方诗人,那也仅仅是从一个次要的意义上来说”[10]185。的确,海恩斯诗歌具有强烈的地方性,但这并不能成为将之归为地方诗人的原因,因为在他看来“一流的文学”,“不论小说或诗歌,多少都和某个地方或者环境相关联,从而有了它独有的特征”[11]87,所以只能说地方性特征是海恩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标志。海恩斯一开始是个自然诗人,其诗歌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及其在经验中所体现的精神联系[11]84-97,[12]107-112,地方、环境对于海恩斯写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阿拉斯加是海恩斯诗歌创作的源泉,但是海恩斯后期的作品不再局限于阿拉斯加,而是转向更为广阔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可以说海恩斯的诗歌发源并成长于阿拉斯加,最终落脚于整个自然和宇宙。
二、荒野至善——荒野中重建家园
荒野“至善”的观念首先缘于海恩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失望。曾经亲历二战的海恩斯看到现代社会严重的生态危机,他认为“这是一场意识的危机,是人类心灵最终将要面临的一种意识危机”(5)批评家海登·卡鲁斯(Hayden Carruth)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中如是说,转引自爱德华·罗迪蒂(Edouard Roditi)的《约翰·海恩斯,亚北极环境诗人》(“John Haines,Poet of the Subarctic Environment”),文章选自凯文·贝兹纳和凯文·沃尔泽(Kevin Bezner,Kevin Walzer)编著的《约翰·海恩斯诗歌中的荒野视角》(The Wilderness of Vision On the Poetry of John Haines),第163-164页。。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海恩斯试图寻找一个令他身心得以宁静的安身之处,直到1954年,当他来到阿拉斯加时,那里的冰天雪地与一片荒凉让他大受震动,他仿佛找到了自己一直寻求的生命之根;从诗人的角度,海恩斯也试图通过亲身体验来感受荒野生活与城市生活的本质区别,并通过诗歌形象深刻地将之表现出来,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与生态意识,以期实现一个诗人对于社会的责任。经过在阿拉斯加冰天雪地十几年的生活,他从一个文明人的角度发现了荒野自然的巨大价值,并将之以冰雪般简朴而纯净的诗歌语言表现出来。他的诗歌对于生活在现代城市的文明人有一种魔性般的魅力,就如荒野本身之于海恩斯一般。这种魅力一方面来自海恩斯独特的体验本身,另一方面则来自他质朴而纯真的语言表达,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诗歌填补了现代都市人心灵深处对大自然的向往。
由于对现代社会反感,海恩斯试图在荒野中寻找家园。然而,他对荒野的理解却有别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荒野热中的大多数荒野爱好者。1964年美国通过《荒野法案》(后文简称《法案》),带来了美国荒野热的最高潮。《法案》对于荒野的定义主要着眼于“未被人类干扰”(undisturbed)的自然区域,也就是说《法案》的基本理念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分离的基础之上。与此相对,海恩斯却认为人类乃是荒野中永久存在的一个部分,他甚至认为人类可以在荒野之中找到归属感与家园感,这一理念在其诗集《冬日消息》(WinterNews)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中《忘却之诗》(“Poem of the Forgotten”)的开头写道:“我来到这个地方,/一个年轻的新手独自来到。//远离社会,/我支起一座青苔与木头的房子,/称之为家。”[8]5(1-5行)诗人独自来到这荒野之地,目的并非像一般的荒野爱好者那样来此享受美景,放松心情,借荒野的纯净与美好暂时逃离喧嚣的城市生活,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一个家,一个可以安置其身体与心灵的家。海恩斯逃离现代生活的做法已经超越浪漫主义者,他从被动的、暂时的逃离转变成主动地寻求永久的家园。套用里奥·马克斯(Leo Marx)的话,海恩斯所寻求的不再是浪漫主义者寻求的“简单田园”,而是后工业时代的“复杂田园”[13]35,在这里,重建已经取代逃离成为主要因素。
在荒野中重建家园的过程就是海恩斯发现荒野“至善”价值的过程。《冬日消息》中很多诗歌都是关于海恩斯在阿拉斯加荒野中的狩猎经历,诗人在黑暗中潜行、围捕,思考死亡。他认为:“长时期独自住在森林,……人类与动物,(你自身)与森林世界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9]40长期的荒野生活会令人学会谦卑,发现自己和动植物之间存在一种如兄弟姐妹般的关系,从而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真正安置身体与心灵的家园。就如诗歌《一只麋鹿的叫唤》(“A Moose Calling”),其实是诗人与麋鹿之间的对话:
“你是谁,
在暮色中叫唤我,
哦,黑色的暗影
带着沉重的角?”
“我既不是母牛
也不是公牛——
我直立行走
而且手中
掌握你的死亡。”[8]12(1-9行)
诗人注意到自己两足动物的本性,人类是动物世界的一部分,是食物链与生命循环中的一环,在海恩斯看来,人类与麋鹿是平等的,类似朋友。
这让我们想到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的名诗《麋鹿》。在她的诗中,“麋鹿代表自然之子,它误入人类文明之中,令人突然感受到来自自然的快乐的感觉”。对比这两首诗可以发现两位诗人对于自然与动物的不同理解,比起海恩斯这种将动物视为兄弟、与自然合一的态度,毕晓普更多地发现了动物所代表的大自然的浪漫、纯真之美;海恩斯虽然猎杀动物,但从情感上尊重动物甚至感激他们,因为他本身便是荒野之子,毕晓普则是从文明之子的角度敏感地发现自然之美,并因此受到震动。
海恩斯对于荒野“至善”的描述是基于他对自然环境的视觉感知与个人化的玄学理念的结合。这也许要归功于他早年专业学习绘画的经历,以及他对东方古诗尤其是中国诗歌有所研究的事实。其实,一开始海恩斯正是试图通过绘画来抓住阿拉斯加的荒野,然而在与他周遭的荒野环境斗争的过程中,他转向了诗歌,并意识到语言是他唯一能够充分表现他与荒野之间关系的媒介[14]29。《冬日消息》中经过多次修改的诗歌《冬季渔夫之歌》(“Poem of the Wintry Fisherma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诗中写道:
在十月的脚下
水流变窄,
鲑鱼等待,
在浅滩燃烧——
血红,绿色与橙色,
在冰蓝的冰川水中。
听!你能听到
对岸的淤泥
长长而缓慢地拉拽
石头深沉的隆隆作响。
我独自站在如烟的
雾中,……
沿着黑暗的河流,
乌鸦紧握钢铁般的树枝,
饥饿,发抖的夜晚
的影子。[15]34
诗中前两节如画般地描述了冰天雪地中安静而寒冷的河流,但是语言的力量似乎超越了画面感,场面如此寂静,以至于可以听到河里“淤泥”与“石头”的声音。也许正是这种绘画无法呈现的寂静感让海恩斯选择诗歌来表现荒野吧。此外,从整体来看,诗歌呈现出一种类似中国古代山水诗的感觉:自然景物+寂静+人影。这种模式将人很自然地带入一种冥想的境界,似乎可以走进诗歌所描绘的画面,感受其中的寂静与隐隐的动静。正因此,海恩斯的诗歌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也产生了启发的功效。
三、荒野至美——艺术与生活的交汇
阿拉斯加的“至美”生活来源于海恩斯对荒野生活的深刻认识。通过独自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生活十几年,海恩斯认识到人类在自然界生存的两种形式:为生存奋斗、为和谐相处。正是荒野中艰苦的生存斗争让海恩斯体会到人类与周遭的动物、植物及环境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在海恩斯看来,在荒野中人往往处于孤立状态,这种状态有助于理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海恩斯有三首关于麋鹿的诗歌,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一首《角》(“Horns”)描述了作者在夜晚的荒野中与麋鹿相遇的场景:
在陈旧的白色帐篷里我睡着了。
十月的月亮升起,
宽阔而冰冻的河流下
麋鹿咆哮而来,
声音沙哑,带着愤怒和欲望
当他缓慢地绕行营地,
我醒来,站在寒冷中。
他的角在树丛中爆发
干树破裂
倒下;他的鼻孔张开,
脖子肿胀,挑战
的气味,他从我身边走过。[8]13(8-19行)
这里的麋鹿散发着“野性的魅力”(第30行),因为人类来到这荒野之地,在孤立的状态之下变得更加谦卑,能够用心与身边的动物进行平等的交流。
第二首《鹿头》(“The Moosehead”)和第三首《受害者》(“Victims”)则是以写实与幻象相结合的风格呈现麋鹿死亡与死后的情形。《鹿头》中写道:“剥除角和皮,/鹿头垂下。//……//在这头骨的小屋中,/大脑曾运行/如红润的队长,/现在只有一汪黑水/和微弱的磷光。”[8]14(1-2行,10-14行)海恩斯似乎带着一种怀念之情观察死去的麋鹿的头颅,此刻,这里的麋鹿不仅仅是诗人的猎物,还具有某种神圣的意味,让人怀念它那如队长般充满精神与活力的形象。可以说,正是通过荒野中独自生存的经验,通过与麋鹿的亲密接触,诗人对作为猎物的麋鹿产生了一种近乎印第安人之于动物的敬畏与感激之情。
第三首《受害者》一共四节,第一节只有两行,从观察者写实的视角开始:“在肉上留下长长疤痕的小刀/让骨头暴露——”接下来第二节滑入一种冥思:“血液森林中苍白的树/在那里生命与死亡之鸟/用痛苦的稻草/不断编织着鸟巢。”第三节过渡:“在那里,猎人与他的猎物……”第四节的视角切换到猎物本身:“树枝断裂,劫数难逃的/动物呼吸阻塞,/就如在红色的雾中,看到/他自己滴血的尸体。”[8]15这首短诗由于视角的切换加上强烈的画面感,向读者鲜活地呈现了猎物本身的感受,并将猎物的牺牲归结于大自然中生命与死亡的循环。作者通过具有冲击力的画面与独特的视角表现了荒野之中一种野蛮而简单的暴力之美。
海恩斯的美学来源于生活与艺术的交汇之地。他指出:“当一首诗歌与这种活生生的、永恒的、部分显露的形式相符合,诗歌便会自我证明、自我辩护,并经过超越其构想时刻而存在。我们称之为恰当、合适,或美丽,就如形容一所适合居住的房子。”[12]7海恩斯将这种诗歌美学与阿拉斯加这片特定的荒野结合起来,写出了既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宇宙普遍意义的诗歌。他靠着耐心、力量与非同寻常的智慧在阿拉斯加的荒野过着几近原始的简朴生活。荒野给他提供的梦幻般的隐居让他深深体会到独处的重要性——在这里,海恩斯离开城市生活的节奏,进入冥想世界。因此,海恩斯的诗歌充满神圣感,他对阿拉斯加的追寻有如早期基督徒在埃及沙漠的寻求:从永恒的角度建立真实生活的机会。也许是因为童年时期接受的天主教义仍然留在心中,精神上追求自我实现一直都是他成年后的生活导向。
荒野之于海恩斯之所以是“至善至美”的,首先是因为荒野的伟大让渺小的人类学会谦虚,其次是因为荒野给人类提供独处的机会,使人能进入一种冥思状态,获得智慧而非知识。在海恩斯看来,“智慧存在于知识之前”,需要感知与体验才能获得。此外,通过在荒野以收集、狩猎等原始手段生活并建立家园的经历,海恩斯深深感受到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乃至非生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将之以倡导生态观念的诗歌形式表达出来。当然,海恩斯也意识到当今这个时代大部分人都无法亲历荒野,因此他通过诗歌讲述荒野,以此来打动人心。关于当代诗歌,他认为:“应该转变观念,抛弃一直以来的‘边疆’思想,是时候让作家和诗人与古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重建联系了,而这些生活方式和文化在这个地球的某些地方仍然活着。”[11]96他所身处的阿拉斯加的荒野便是这种地方,就如海恩斯在诗歌中写道:“虽然荒野消失了,但荒野存在于露营/我们已经将之内化。”[9]32在绝对荒野已经消失的当代,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来获得从荒野而来的精神和安慰。
四、结语
20世纪以来,随着实际荒野的不断消退,人们对于荒野的定义也在不断改变。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环境主义者似乎模糊了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与界限,他们开始将荒野视为处于自然与文化这一连续光谱上最末端的位置。在这样的理念下,人们不用非得去人迹罕至的原始荒野才能感受到荒野之美,而是可以从自然与文化这一谱系中找到靠近自然这一端的位置来发现自然的野性之美,可以说荒野的概念已从实际存在的“荒野”(wilderness)逐渐转化成为一种相对意义上的“野性”(wildness)。
20世纪的美国诗歌就见证了这一重要转变。20世纪初期的荒野诗人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1887—1962)如预言家般地指出了非人类荒野的价值所在,他的非人类主义哲学极端地否定人类、抬高非人类。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恩斯既摆脱了浪漫主义的简单自然观,也不像杰弗斯那样极端地面对荒野,海恩斯显得更加理性。通过在阿拉斯加冰天雪地的荒野独自生活十几年的亲身经历,海恩斯用诗歌与散文指出了荒野的价值在于它本身因天然而淳朴的状态显示出何为至美,而荒野中真实而残酷的环境又让生活于其中的人类有可能回归到一种至善的状态。面对当今实际荒野几乎消失殆尽的情况,人们需要从人类与荒野对立的圈子跳出来看问题,既然人类与荒野是一体的,那么荒野的核心不再是“未被人类干扰”,而在于其本质的特征——“野性”,这也是荒野最重要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