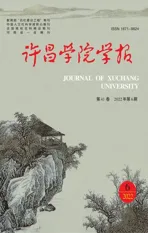明清之际长洲文氏家族文人笔下的家国之思
2022-02-14毛艳秋
毛 艳 秋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长洲文氏家族,明清时期为吴中地区文化巨族,也是江南文化世家的彪炳,家族人才辈出,成就灿烂。其族“自涞水公至书深先生为九世中,如温州之廉明,待诏之德艺,文肃之公忠,炳在明史不具论。其有集行世者十有八人,书画笔札擅名者又二十八人,可谓盛矣”[1]2。清初名家吴伟业曾评价其族:“自成、弘以来,一郡方雅之族,莫过文氏。”[2]21如此文化盛族,其家渊源必是绵亘流长。
长洲文氏源于衡山(湖南衡州)文氏,宋咸淳年间,祖文宝授衡州教授,文宝之子翔彪于宋元丰三年(1080)官吏部尚书,封金紫光禄大夫。后南宋政权灭亡,衡山文氏也就此没落。然而,历史的变迁不仅会带来挑战,也会带来机遇。元明之交,衡山文氏随时代之变发生更迭,家族内蕴也多有变化,原本的书香门第逐渐演变为武弁之家。翔彪重孙俊卿“仕元为镇远大将军、湖广管军都元帅,镇元昌。明兴,授衡州千户”[3]16。俊卿生六子,其中,三子文定聪迁杭州,后定聪之子文惠又由杭州迁苏州,是为文氏苏州之祖、长洲文氏之源。文氏虽以武弁起家,然而自定居苏州开始,便重拾祖先的诗书之风,坚持“以文传家”。二世祖文洪更是“笃行勤学,雅好吟咏”,并以此奠定了其家诗书相传的家学基础。自此之后,文氏愈加重视对后辈子孙在诗书文化方面的培养。时至明中,通过前代积累,文氏已经成为吴中诗文之家的典范。同时,随着江南地区文学文化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家族在文艺方面的积淀也逐渐焕发光彩。依吴地之风灵玉秀,文氏逐渐走向文学文化的巅峰。明朝中叶,随着文徵明成为文坛翘楚,文氏的文艺家声逐渐显露,也是从文徵明名冠吴中开始,文氏文艺家族的地位被完全确立。
然而文学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烙印,尤其是依附于时代的文学文艺世家。晚明泥沙俱下、国势沉沦的时局,使得江南文化家族也随之呈现出余晖晚照之相。在这段山雨欲来的岁月里,文氏家族逐渐从风雅之家走向忠烈之族,晚明跌宕的时局不仅导致了家族剧变,也带来了家族文学文风的改变,原本风雅不拘的文学个性逐渐被现实消磨,取而代之的是因家国颓丧而产生的悲怆之感。文学主题也在此背景下有了新的变化,文氏文人开始了以史谏之笔诉时代悲歌、以家国之思代诗情画意的文学书写。
一、忧国之思
晚明文氏族内功名最显者当属文震孟,其高中进士,官拜内阁,达到了家族在科举功名方面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晚明的危重时局,并未让文震孟感受到太多功名带来的喜悦,作为极具家国情怀的文人士子,目睹国家社稷逐渐走向穷途,家国安危始终为其心中所念,家国之思自然也成为其文学文章之旨。早在登科之前,文震孟即著《姑苏名贤小纪》两卷,共四十九篇,约成书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小纪》中每篇记述一名苏州本地贤达事迹,文后附加议论,抒陈己见。文震孟在《序》文中明确阐述了创作初衷,是为消除四方之偏见,令“吾苏之士揽先贤之遗风而兴起焉,洒濯磨砺,毋甘为当世所轻”[4]738。时值万历末年,明王朝正处在大厦将倾的危机之中,社会在时事的推动之下也日渐变化,久被金钱享乐主义浸润的吴中,风气日益颓靡,文震孟感此颇深,心生忧虑,欲借此书达到发扬姑苏的风雅礼韵,从而再兴地方士气之目的。书中所作纪文传主多为吴地贤达,比如以吴宽为对象的《吴文定公》篇:“宽然长者,恬于荣进,然至于昌言守正,引经定礼,使朝典无颇,又何侃侃凿凿耶?公别号匏庵,言匏不食不材,以自况也。而八音克谐,神人以和,匏且适宗庙朝廷无用者,未必不有大用矣。太祖称:吾取士欲得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者。呜呼!吴公乃不负圣祖设科意哉!”[4]750文中对匏庵先生的赞誉,也是对吴地风雅的颂扬,言之切实,正合初衷。虽然文章旨意还未上升到家国大义的深刻层面,但是已经有了反思现实、期冀未来的趋势。
天启二年(1622),文震孟得中进士,授翰林院修撰。此时恰是明王朝急速衰落,走向崩坏的关键时期。阉党把持朝堂,党争激烈,疑案重重;国家内忧外患,起义频生,边境纷乱。面对朝政之积弊以及社稷在危机中不断沉沦的现实,文震孟内心充满了愤慨和忧虑。他在同友人的书信中写道:“守史局已三阅月,轮蹄驰逐于黄埃赤日中,绝无所事事,见时政龉龃,议论倾诐,衷怀郁郁,又绝不能有所挽回驳正,以故木天一席,世号清华,心颇厌之。”[5]78作为始终心怀天下的正统知识分子,文震孟渴望挽救社稷之危,因此迫不及待地要将对国家的担忧上陈君主。虽然此时文震孟只是一位初涉官场的翰林编修,但他仍积极把握这来之不易的上达天听的机会,将自己对朝政、国政的忧思、对时局的思考和期待陈于《国步綦艰疏》中,向上呈递:“今日之势,岂惟厝火,几于燎原矣。奴贼凶氛正炽,羁虏隐祸方深,徐淮一震,则江北江南将为蹂躏之地;黔滇不守,则东楚西楚复虞恇扰之忧。济济班行,未见腹心爪牙之足寄;纷纷兵饷,惟闻疮痍沟壑之堪悲。蹙地丧师,无岁不有;败军杀将,所在相闻,此真大小臣工勠力同心、尝胆卧薪之日。”[6]654奏疏直指当下国家态势之利害,详细分析了外患四起、内政堪忧的危机局面,言辞可谓恳切之至。尤其是奏疏末尾的赤心诚谏:“焚心臣史官也,本无言责,不必深言是非以挑争辩,但念世受国恩,更蒙宠拔,目击时事阽危,人心玩愒,每自当食长叹,中宵涕零……倘蒙省览,稍见施行,臣虽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6]655短短数言,字字入心。文震孟不顾自己新进的翰林身份,甚至不惜以罪责自身为代价谏言天子,以求拯救国家于穷途之中。疏中对时弊的揭露、对国家社稷的忧虑、对天下苍生的悲悯,皆是其家国情怀的殷切表达,更是其家国之思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奏疏中的家国之思是作者鉴于身份、处境的必要发挥,那么文集中的家国之思则应视为其内心的真实写照。《药园文集》为文震孟贬谪居乡之际所著散文集,共二十七卷,存二十二卷。集中有大量传状碑记,传主多是正直廉明的官员、勇于抗争的斗士,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而对传主的歌颂,也是作者人格精神在文学叙写中的投射。虽然此集主旨是褒扬清正刚直之士,但作者真正的用意是借对传主的赞誉揭露社会之凋敝、士风之堕落的现实,期待以朴实清劲的士风对抗华而不实的社会风气,以一地之世风振家国之气象。如在《万邑侯寿序》一文中,作者生动且深刻地描述了民生如何因吏治不善而凋敝的过程,其辞之恳切,发人深省:“余所居氓可二十余家,皆治田灌园,春采茶,夏刈麦,秋冬稻谷采芝烹伏雌,熙怡恬然,略如桃花源中人。亡何令有善扰民者,催科之吏,剥及空山,幽岩绝壑,无所不遍。民有储钱刀布,缕给公家正供者。吏呼一怒,辄弭耳,拱手听其科敛。鸡犬嚣然,莫有宁宇。向所睹记暖衣饱食二十余家,皆破散逃移,甚者弃妻鬻子女,卖田庐,村墟景色,萧条聊而。”[5]109-110震孟在文中秉实揭露了从万户安宁到黎民潦倒的残酷现实,字里行间皆是痛心疾首的无奈。再如,其在《贺宪使李公进阶参岳序》中,直陈“边供日课,践更之役,既不能稍有所轻缓,人民垫隘,无所底告,而淫技末作,冶游之费、豪族恶少、扞网之奸,又外侵内蚀,譬之于人,魁然盛饰,而精已销亡,直待时而仆耳”[5]6的现实困境。身处时代危机之中的文震孟,时时以国事为忧,以文章叙时局之困,始终将家国之时运与己身紧紧相连,无论是身体力行还是以翰墨寄之,拯民于水火,救国于倾颓,成为他矢志不渝的坚持。
家国之思不仅寄托在济世良疏的直陈谏言中,也感慨于赞许忠直的传书纪文中,更践行在挽救家国社稷之危的不辞劳苦中。文震孟代表了明季剧变时局下文氏家族文人的家国情怀,同时也代表了士大夫中忠直之士的家国意志,虽然其中不乏无力回天的悲凉,但更有锲而不舍的执着。历史无法改写,也不容假设,但是他们托举家国的勇气,值得后世推许和思考。
二、故国之思
文震孟饱含家国情怀的文学书写,对文氏族内其他文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文震孟的引领和文氏文化世家的社会地位,家国之思成为其家族在明清易代之际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继文震孟之后,其长子文秉紧承父志,所著笔记十之八九浸满家国情怀,家国之思的主题,在其笔下愈加强化。
文秉(1609—1669),字孙苻,号大若山人,国子监生。文氏发展至文秉,门楣之盛已渐呈衰势,其父在朝堂之上的速起速落未能为文氏带来再兴的机会。父亲的遭遇、国家的败落以及朝廷的难以复起,所见所历都让文秉心生感慨。在亲人离散和家国破碎的悲痛中,文秉承担起承继家学的责任,将关于时代的思考寄托到文章之中。文秉在明亡之后选择隐居竺坞,致力著述,先后完成《先拨志始》《烈皇小识》《甲乙事案》等笔记作品,悉数记载明末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还原了明末朝局与时局的诸多历史细节。虽然笔记的内容和体式各有特点,但家国之思是笔记始终围绕的情感主题。文秉作品中的家国之思与其父笔下所寄亦有不同,这不仅是基于身份之差,更缘于时代背景的变化。文秉亲历了易代的历史关节,政权颠覆、文化剥离的苦楚,让文秉对家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将痛失至亲的悲痛、国破家亡的感慨诉诸笔端。在客观严谨的历史叙述背后,蕴藏着他对家国破碎的无限感怀。
文秉的家国之思,一部分是借助笔记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来抒发的。在叙述历史的同时,借人物塑造来表达内心对故国君主的怀念,其中尤以崇祯帝的塑造为最。《先拨志始》中他通过对比的手法,间接塑造了崇祯帝的明君形象。继而在《烈皇小识》中,作者更加强化了对崇祯帝英主形象的刻画,不仅对这位年轻帝王在社稷沉沦之际继承大统、铲逆举忠、励精图治的种种作为给予中肯评价,还通过奏疏批复和君臣对话等具体内容,突出崇祯帝内心求贤若渴、重安社稷的期盼。文秉对先君主的感念之情,在笔记序文中已经有所表露:“不肖十七年中,备集烈皇行事,以致尧舜吾君之恩,又以致有君无臣之叹,集成巨帙数十册,可备一朝史料。”[7]2然而文秉并非只是为单纯歌颂君主而塑造崇祯帝的仁君形象。一方面,对于君主的赞颂和怀念,是其内心家国情怀的抒发,是其家国之思的寄托。另一方面,对于文秉这种世家文人来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观念是根植于心并始终坚持的价值取向。加之其父文震孟“东林”成员的身份,文秉心中的家国之思与传统的“明君贤相”的历史观存在一定程度的暗合。虽然其父已逝,家族荣耀不再,但是其“东林后裔”和“前朝遗民”的身份,更加深化了文秉心中的家国之念。然而无论是“明君贤相”还是“东林”诸君,都无法改变国破家亡、山河涂炭的境况,文秉也早已看透现实,所以在笔记中,文秉并不耽于怀念过往,而是通过史实的还原以及内在意义的挖掘得出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借以警示后人,这也是其借史笔抒发家国之思的目的所在。
《先拨志始》序文有言:“辨之于早,后之君子浏览于此其作邪正之辨,得失亦洞若观火。”[8]1作者直接点明著书存史的初衷,即做正邪之辨,还历史之本真面目以警后世之来人。文秉透过明末复杂的时局看清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有忠直之士前赴后继,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仍被历史无情地淘汰。面对权宦祸乱朝纲导致言路阻塞的现实,他不禁发出深沉的慨叹:“呜呼!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廉耻道丧,谄附成风,孰甚于逆贤时?教猱升木,翼虎而食,孰甚于赞导逆贤?”[8]2此时国家面临内忧难解、外患难纡的局面,而朝堂之上,仍旧党争不断。天启年间的阉党之乱一直绵延到崇祯朝,其父文震孟在激烈的党争中不断起落。崇祯八年(1835),因为内阁首辅温体仁所嫉,文震孟被温氏借贬黜都给事中许誉卿一案逐出内阁,贬黜归乡,终不复起。震孟去后,朝政紊乱,奸佞当道,朝中党羽之争愈演愈烈。佞臣掌局,倾轧激烈的朝局,父亲为奸臣所构陷而遭贬黜的经历,皆让文秉悲愤难持,不禁一抒胸中之恨:“逆珰遗孽,唯知力护惨剧,不复顾国家大计,即废籍诸公,亦阅历既久,情面渐深,无有赞皇魏公其人。我先臣以讲筵辱蒙圣鉴,优被超拔,上虽有虚己听之之意,然两月居席,一语招尤,负神明之特达,致无所报。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7]2如此局面之下,文秉对于国家败亡的结果有着清醒的认识:“虽圣主日渐其忧勤,而群上日流于党比,痼疾已成,不复可药矣。”[7]2即便是贤君再世,家国覆灭的结局也在所难免,虽然现实不免令人唏嘘,但文秉这段引人深省的总结,的确有着警世大于悲悯的深刻意义。
文秉在笔记中对明季历史的还原与解读,以及由此而生的无限感怀,皆是其内心家国之思的具体表现。相比于其父文震孟家国之思中所蕴含的不甘与执着,文秉的家国之思更具无力挽回的破碎之感。这与其饱受朝代更迭之苦的经历不无关系,也正是基于此种遭逢,文秉笔下的家国之思才显得愈加悲壮。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在如此浓烈的家国情感中还保有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知。时代阴霾之下的家国之思,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怀,更有高于个人情感的历史意义,而文氏文学史笔之光彩也正在于此。
三、家国寄予
文氏传至明末,人才虽不如往昔之盛,但是除文震孟、文秉父子之外,也不乏才学兼备之人。震孟次子文乘,弟震亨,震亨子文果等,皆是承继家族文脉遗风之后劲。彼时正值历史转折、朝代更迭的特殊时期,身处其中的文人诸士饱经离乱之苦。面对山河剧变的现实境况,文氏族内的赤诚之士不禁将心中的家国之思表之于书。
文震亨,字启美,以贡生拔中书舍人。虽非同其兄一般官居高位,但是作为世家文人,震亨一样胸怀家国,坚志不移。山河易主、故土涂炭的易代之悲,使其收敛起往昔的清雅之气,取史笔之深刻道出内心的家国之念。文震亨所著历史笔记《福王登极实录》,记录了南明弘光政权起覆的过程,叙述了以史可法为代表的明王朝遗臣在南京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弘光政权,以图社稷重兴的史实。笔记内容不繁,言简意赅,家国不复完整的忧愤和悲戚,一一被作者带入笔记之中,字句间处处皆是作者内心家国之思的真实流露。
笔记所取史实的时代背景是气数将尽的南明时期,此时的朱明王朝仅能偏居一隅做垂死挣扎,南明君臣身处困境而无力回天的亡国之悲,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监国素袍角带,对百官恸哭,百官行礼,手掖之,寻赐茶。言及宗社震惊,大行异变,复哭失声。”[9]1虽然明政权已经是大势已去,但是文震亨依旧对国事存有一丝希冀:“若诸臣思祖宗三百年德泽在人,大行十七载焦劳求治,洗涤肺肠,以事新主,扫除门户,以修职业,何事不可办,何罪不可讨,亦何功名不可就哉?”[9]2在这段陈述中,既有对过往的感慨,也有对南明政权新政改革的鼓励和告诫。铿锵数语,吐露出内心对于国家的忧虑和期待。篇末云:“边镇诸宿将,无不投袂奋剑,以报国仇者,中兴大业,岂灵武草次、靖康偏安之足比哉?”[9]3借今昔之对比,生发出对社稷中兴的憧憬。笔记虽仅千字之余,却满篇皆是对国家零落的痛惜遗憾,以及对恢复河山的殷殷之期。可惜最终,文震亨因国家陷落而心生绝望,绝食而亡。虽然这种自毁自戕的极端方式令人唏嘘,但对于文震亨这样心怀家国、忠直不二的文人来说,这样的结局也许正是一种解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其家国之念的一种残酷表达。
文氏文人在家国沦陷的绝境中做出决绝之举的并非文震亨一人。其侄文乘,文震孟次子,字应符,诸生,生性豪爽刚毅,颇有豪杰气。文乘岳父为“后七君子”之一的周顺昌,内弟周茂兰、周茂藻皆为复社中坚。生逢多事之秋,受家族忠直之风影响的文乘,面对家国沦落的境况,不甘束手,始终积极投身于抗清活动中,坚持为故国再兴之事奔走,最终为清廷所杀。关于文乘殉难之事,其兄文秉在所著笔记《甲乙事案》中亦有提及:“予自遭仲氏之难,列在官府者,幸荷宽政,而托在至诚者,反罹密网,孑然数口,屏迹深山,吸风茹霜,莫可诉语。”[10]526“仲氏之难”,即言文乘身死殉国之事。清顺治初年,清王朝已经入关,并统一大部分中国,但恢复旧朝的斗争在江南地区依旧不绝如缕。文乘一直处在反抗新政权的前沿之地,在为恢复旧国奔走的过程中,文乘对亡国之痛感受深刻,诗歌成为其抒发内心郁结的出口:
紫皇诠次繁华位,四时秩秩司花吏。排红篡紫总无讹,秋花错与春花字。
此花虽柔性颇烈,骄矜不向炎阳发。翠佩姗姗倚女垣,商扬送凉来木末。
小沐香霖黛光妩,三葩五葩静中吐。闲情独立对高秋,未许尺英相尔汝。
有客愁鬓新霜华,手握清泪埋黄沙。不是断肠心事切,何缘心死断肠花.[11]375
作者以开于深秋的孤傲的秋海棠为意象,表达自己身处国破家亡的绝境而不肯折节而生的意志。“此花虽柔性颇烈,骄矜不向炎阳”,正是其刚烈之性的自比;“有客愁鬓新霜华,手握清泪埋黄沙”,则暗喻自己为故国复兴奔走呼号而仍不得不面对“断肠心事切”“心死断肠花”的现实。顺治三年(1646),文乘亡于吴易抗清的斗争中,时年二十八岁。同其叔父一样,文乘身死殉国的人生归宿令人感慨,然其坦然赴难的决绝,正是其以生命为代价对家国之思的现实阐释。
从文震孟到文乘,文氏家族文人以手中毫墨与胸中热血,阐释着不同时代背景下家国之思的含义,不仅再现了明季世家文人的身心处境,也展现了他们对家国情怀的坚守。文氏家族文人只是明季历史变迁中文化世家的一个缩影,他们不仅代表自身,更代表了处于时代巨浪中世家文人的普遍境遇。他们或奋起反抗,为恢复旧国奔走,或执笔为矛,将愤慨诉诸笔端,不论哪种选择,都是世家文人在江山陆沉之际,内心家国之思的真实再现。
历史总是赋予悲剧以深刻的意义,正因为身处时代困境,世家文人对家国之思的书写,才为世人带来拨开迷雾、揭示真相、总结历史经验的机会。世家文人在跌宕中凝视现实,感受自我,将内心的家国之思寄寓于诗文翰墨,使得经过情感洗练的史实,在静穆的历史长河中折射出独特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