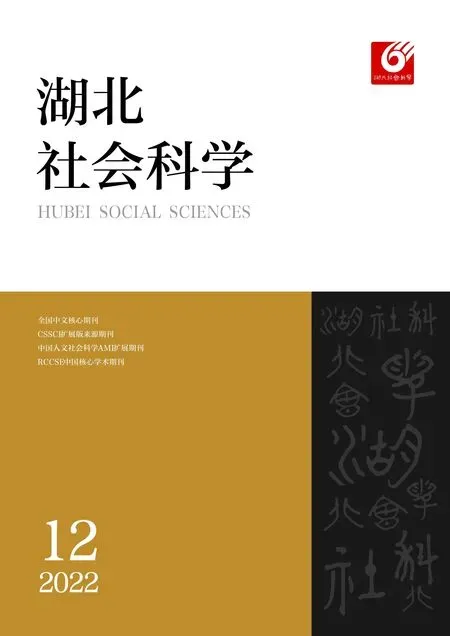中古时代的江汉隐逸
2022-02-13陈君
陈 君
从地域角度观察中古时代的隐逸传统,可以看到东晋以前隐逸士人多出自关陇、青齐与河东地区,北方高士是隐逸传统的主流。①可参拙文:《中古隐逸传统中被忽略的一环——关陇高士及其对隐逸传统的建构》,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8—26页;《汉晋之间的青土隐逸及其文学与学术影响》,载《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第36—44页。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江汉、江州、吴会地区的隐逸之士逐渐增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南方高士在新的地域和时代环境刺激下,不但继承了汉晋时期北方隐逸传统的一些特点,还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北方高士的超越,树立了新的隐逸范式。
在中古时代的隐逸传统中,江汉隐逸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这里所说的江汉地区主要包括今河南南部与湖北地区,以汉代为例,主要指荆州七郡中南阳、南郡、江夏三郡所辖的地域。②广义的江汉地区,包括今天的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本文取狭义的理解,指汉代荆州南阳、南郡、江夏三郡所辖的地域范围。据班固《汉书·地理志》、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所载,汉代荆州刺史部辖有南阳、南郡、江夏、长沙、武陵、零陵、桂阳七郡(国),东汉末年又由南阳郡析置章陵郡,故史籍中又有“荆州八郡”的说法。曹道衡先生曾指出:“从《晋书》和‘南朝五史’等现存的史籍来看,关于当时江汉流域出身的学者文人的史料记述颇为稀少,即使提到,其中亦多数为隐逸之士。”[1](p17)笔者拟在曹先生论述基础上,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对中古时代江汉地区的隐逸士人作一全面考察,不当之处,尚祈海内博雅君子不吝赐教。
一、汉魏时期的江汉隐逸
早在西周时期,江汉地区就已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诗经·大雅·江汉》有“江汉汤汤,武夫洸洸”之语,[2](p573)《周南·汉广》有“汉之广矣,……江之永矣”之对。[2](p282)春秋以后,处于楚文化核心区域的江汉地区,一方面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战国时期楚辞的兴起和繁盛就是显例。两汉时期,江汉地区的文化有了长足进步,涌现出一批学者文人,如东汉中期江夏郡的黄香,南阳郡的刘珍、张衡,南郡的王逸、王延寿父子,以及东汉后期南郡的胡广,南阳郡的朱穆、延笃等等。
就隐逸传统而言,楚国屈原被放逐后,“游于江潭,行吟泽畔”[3](p179)所遇到的渔父,虽有虚构成分,但也可谓江汉隐逸的先驱。①东晋谢万《八贤论》将渔父、屈原与司马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并列,称为“四隐四显”,“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似是将渔父视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参见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86 页。又《世说新语·文学》第91 条:“谢万作《八贤论》,与孙兴公往反,小有利钝。”刘孝标注:“《中兴书》曰‘万善属文,能谈论。’《万集》载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谓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也。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笔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0页。确有名姓的江汉隐逸到东汉时期才登上历史舞台,顺帝时南阳赵康(字叔盛)“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4](p1463)名动一时。②《后汉书·朱穆传》云:“穆时年五十,乃奉书称弟子。及康殁,丧之如师。”(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63页。)朱穆(100—163)字公叔(一字文元),是当时的儒学名士,曾作《崇厚论》《绝交论》等。赵康生活的东汉安、顺时期,中国北方涌现出大批隐逸之士,其中关陇高士特别引人注目,隐居于武当山(属南阳郡武当县)的赵康,可视为这一时代隐逸高潮在江汉地区的回响。同时从赵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武当、岘山、云梦、沔水等山泽名胜不仅是江汉地区重要的地理标志,更具有丰富的人文因素,正如江州隐逸离不开庐山,会稽隐逸离不开越中山水一样,江汉隐逸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些明山秀水所孕育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
桓帝时的江汉隐逸有汉阴老父③皇甫谧《高士传》有汉阴丈人,与《太平御览》引嵇康《高士传》同,又有汉滨老父、庞公二人,与《太平御览》引《后汉书》之文同。,《后汉书·汉阴老父传》载:
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4](p2775)
汉阴老父生活的年代当顺、桓之间,这一时期东汉政治已显颓势,老父与名士张温的对答、议论颇有道家色彩,其对现实政治的清醒判断和清高姿态,让羁绊其中如张温者惭愧不已。
桓、灵时期有娄寿(字元考,97—174),南阳隆(当作阴,今湖北老河口)人。《玄儒先生娄寿碑》载:“父安贫守贱,不可营以禄。(寿)童孩多奇,岐嶷有志。捥发传业,好学不厌。不攸廉隅,不饬小行。温然而恭。慨然而义。善与人交。久而能敬。荣且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蔼。遁世无闷。恬佚净漠。徲衡门。下学上达。有朋自远。冕绅莘莘。朝夕讲习。乐以忘忧。郡县礼请。终不回顾。高位厚禄。固不动心。……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二月甲子不禄。”[5](p68-69)由碑文可知,娄寿行迹与赵康类似,也是崇尚儒学、教授五经的清静之士。
东汉末年则有南郡庞德公、习融、杨虑,以及客居南郡襄阳的颍川阳翟人司马徽等。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或作《襄阳耆旧传》)卷一“习融”条云:“习融,襄阳人。有德行,不仕。”[6](p27)庞德公与习融同时而更闻名,《后汉书·庞公传》云:
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4](p2776-2777)①孟浩然《登鹿门山怀古》:“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夜归鹿门歌》:“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夜来去。”(参见孟浩然撰,李景白校注:《孟浩然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25、141 页。)杜甫《遣兴》其二:“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参见杜甫撰,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80页。)
《后汉书》记载的庞公,应为庞德公。据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庞德公”条:“(司马)德操少(庞)德公十岁,以兄事之,呼作庞公也。故世人遂谓‘公’是德公名,非也。”[6](p39)庞德公“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自觉疏远城市,是山林之士的一贯选择,所谓“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7](p765)关于庞德公的隐居生活,《襄阳耆旧记》记载他躬耕田里、琴书自娱,可补《后汉书》之不足。除习融、庞德公外,汉末的江汉隐逸又有杨虑,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杨虑”条云:“杨虑,字威方,襄阳人。少有德行,为沔南冠冕。州、郡礼重,诸公辟命,皆不能屈。年十七而夭。门徒数百人,宗其德范,号为‘德行杨君’。”[6](p86)杨虑少有德行,名闻一时,可惜少年早夭,未尽其才。客居荆州者则有司马徽,徽字德操,“清雅有知人鉴”,[8](p953)世谓水镜先生。②《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参见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53页。司马徽长于古学,③梓潼涪县人尹默、李仁曾从司马徽受古学。参见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26页。博闻多识,曾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荆州破,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会其病死”。[9](p67)
虽然江汉隐逸洁身修德、少私寡欲,迥出时流之上,但此时的江汉地区,与发达的中原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可以流寓荆州的北方大族名士王粲的意见为代表,《七哀诗》其一云:“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10](p1087)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杀,关中战乱不止,王粲随同朋友士孙萌从长安往荆州避难,依附于荆州牧刘表,在诗人看来即是从“中国”远适“荆蛮”。《七哀诗》其二表达了客居荆州的羁旅之苦:“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吾心。”[10](p1087)其中愁绪,与《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10](p490)的感慨是一致的。这些诗文表明,在当时士大夫心目中,江汉地区的文化与中原地区相比仍逊色一筹。
当汉末大乱、中原扰攘之际,刘表治下的荆州地区相对安定,成为北方士人尤其是中州士人避难的首选。《后汉书·刘表传》云:“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4](p2421)这一时期的荆州可谓人才济济,许多著名学者文人流寓江汉,有繁钦、蔡睦、杜夔、杜袭、赵岐、王粲、诸葛亮、徐庶、邯郸淳、祢衡、和洽、崔州平、石韬、孟建(字公威)、颍容、尹默、李仁等。④在汉末流寓荆州的士人中,纯粹的隐逸之士几乎没有,其中最著名者如诸葛亮虽以布衣躬耕于南阳,但绝非一个单纯避难、苟且偷安的人,而是有着清醒政治头脑,在等待时机的政治家。本土学者则有南阳章陵(今湖北枣阳)人宋忠等,宋忠(一作衷)字仲子,被刘表辟为五业从事,与綦毋闿等撰定《五经章句》,[8](p212)又撰有《周易注》十卷、《太玄经注》九卷、《法言注》十三卷等。在刘表的庇护和扶植下,以宋忠为首,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结合形成了著名的荆州学派。[11]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刘表病死,次子刘琮继父位,听从蒯越等荆州士人的意见,投降曹操。十二月,曹操与孙(权)刘(备)联军战于赤壁,大败。次年,曹操北归,荆州的流寓士人大多随其回到北方,王粲也在其中。[12](p67)他在《初征赋》中说:“违世难以回折兮,超遥集于蛮楚。逢屯否而底滞兮,忽长幼以羁旅。赖皇华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践周豫之末畿。野萧条而聘望,路周达而平夷。春风穆其和畅兮,庶卉焕以敷蕤。行中国之旧壤,实吾愿之所依。”[13](p1618)由“蛮楚”重入“中国”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西晋武帝时期,名臣羊祜、杜预先后镇守襄阳,文武并重,务德崇信,化行江汉,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有突出贡献,而且留下了自己的名士风流和名山事业。羊祜作有《让开府表》,[10](p1690-1693)襄阳岘山有羊祜碑(又称堕泪碑),史载羊祜卒后,“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14](p1022)①唐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杜预博学多能,时人号曰“杜武库”,其《春秋经传集解》完成于襄阳,②《文选·卷四五》有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参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3—2037页。《〈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2](p2187)③方韬、刘丽群的《〈春秋经传集解〉书名与撰著年代考辨》(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1 期,第121—125 页)一文认为,杜预开始撰写《春秋经传集解》的时间不晚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 年),写定时间则在太康元年(280年)至三年(282年)之间。意见可从。清晰记录了杜预从武将到学者的身份转化。
总之,东汉中后期江汉地区涌现的众多学者文人和隐逸之士,汉末中原士大夫避乱南下和荆州学派的形成,以及西晋时期羊祜、杜预在襄阳的政治经营与文化建树,都为江汉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成为东晋南朝时期江汉隐逸之士繁盛及学术文艺繁荣的先声。
二、东晋南朝的江汉隐逸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琅邪王司马睿联合过江的世家大族,在江南建立起侨寓的东晋政权。与战乱不止的北方相比,东晋治下的南方相对安定,江汉地区出现了不少隐逸之士,有南阳安众刘驎之、南郡刘尚公、襄阳习凿齿、武昌孟陋。另外,从社会交往角度来看,长沙邓粲也可纳入广义的江汉隐逸范围。
刘驎之字子骥,“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泽,志存遁逸”。[14](p2447-2448)④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南阳刘子骥”即此人,事迹又见《世说新语·栖逸》第8条“南阳刘驎之”及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5—656页。又有南郡刘尚公、长沙邓粲,与刘驎之同志友善。[14](p2151)邓粲少以高洁著名,荆州刺史桓冲辟为别驾,名誉稍损,[14](p2151,1952)后以病归。邓粲应召为桓冲别驾时,刘驎之、刘尚公谓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则笑答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14](p2151)从邓粲的回答可以看出,其思想实属朝隐一类。
习凿齿字彦威,是襄阳习氏的一员,“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14](p2152)撰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对于习氏先贤,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曾不遗余力予以推举,如隐逸之士习融及其子习郁被列于《襄阳耆旧记》第一卷第二条,显示了习凿齿在经营家族名誉和社会声望方面的努力,同时也反映出江汉隐逸家族化的特征。
孟陋字少孤,武昌阳新人,“少而贞立,清操绝伦,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时或弋钓,孤兴独往,虽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14](p2442-2443)⑤《世说新语·栖逸》第10 条载:“孟万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阳新县。”刘孝标注引袁宏《孟处士铭》曰:“处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阳新人,吴司空孟宗后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栖迟蓬荜之下,绝人间之事,亲族慕其孝。大将军命会稽王辟之,称疾不至,相府历年虚位,而澹然无闷,卒不降志,时人奇之。”(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9页。)孟陋出身士族,为吴司空孟宗之曾孙,兄孟嘉(字万年)即陶渊明外祖父。
永嘉之乱后,不少南阳士族为躲避北方战乱徙居江陵,如南阳涅阳宗氏、刘氏,南阳新野庾氏等,这些家族在南朝出了不少隐士,如出自涅阳宗氏的宗炳、宗彧之、宗测、宗尚之,出自涅阳刘氏的刘虬、刘昭,出自新野庾氏的庾易、庾诜等等。
宗炳字少文,荆州刺史殷仲堪、桓玄并辟主簿、举秀才,不就。刘裕领荆州,辟为主簿,不起。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刘宋时朝廷数征,皆不应。妻罗氏,亦有高情,与炳协趣。元嘉二十年(443 年)炳卒,时年六十九。[15](p2278-2279)宗炳外弟师觉授“亦有素业,以琴书自娱”,[15](p2279)临川王义庆辟为祭酒、主簿,皆不就,病卒。炳从父弟彧之亦是隐逸之士,彧之字叔粲,“蚤孤,事兄恭谨,家贫好学,虽文义不逮炳,而真澹过之。州辟主簿,举秀才,不就”。刘裕受禅,“征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征员外散骑侍郎,又不就。元嘉八年卒,时年五十”。[15](p2291)耐人寻味的是,宗炳虽然志节高尚、不应征聘,然四子皆出仕,长子朔,为南谯王义宣车骑参军;次子绮,为江夏王义恭司空主簿;三子昭,为郢州治中;四子说,为正员郎。
到了宗炳孙子一辈,宗氏家族的隐逸之士有宗测、宗尚之。宗测字敬微,“少静退,不乐人间”。“州举秀才、主簿”,“骠骑豫章王征为参军”,“诏征太子舍人”,皆不就。“欲游名山……遂往庐山,止祖炳旧宅”,“顷之,测送弟丧还西,仍留旧宅永业寺,绝宾友,唯与同志庾易、刘虬、宗人尚之等往来讲说”。建武二年(495 年)“征为司徒主簿,不就,卒”。[16](p940-941)测宗人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泽。宋末,刺史武陵王辟为赞府,豫章王辟为别驾,并不就。永明中,与刘虬同被征为通直郎,和帝中兴初,又被征为谘议,仍然不就。寿终。[16](p941)
出自涅阳刘氏的有刘虬、刘昭。刘虬字灵预,“少而抗节好学,须得禄便隐。宋泰始中,仕至晋平王骠骑记室,当阳令。罢官归家,静处断谷,饵术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为荆州,教辟虬为别驾,……不应辟命。永明三年,……诏征为通直郎,不就。建武二年,诏征国子博士,不就”,其冬卒,年五十八。[16](p939)刘昭与虬同宗,“州辟祭酒从事,不就。隐居山中”。[16](p939)
出自新野庾氏的有庾易、庾诜。庾易字幼简,“志性恬隐,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为骠骑参军,不就。临川王映临州,独重易,上表荐之,饷麦百斛。……辞不受。永明三年,诏征太子舍人,不就。以文义自乐。……建武二年,诏复征为司徒主簿,不就”。[16](p940)庾诜字彦宝,“幼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而性托夷简,特爱林泉。十亩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产业”。[17](p750-751)中大通四年(532年)卒,时年七十八。
南朝时期的江汉隐逸,还有南郡枝江刘凝之、凝之兄盛公,武陵汉寿龚祈,武昌郡武昌县郭希林、希林子蒙,南阳宛县张孝秀。刘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妻为梁州刺史郭铨女,“遣送丰丽,凝之悉散之亲属。妻亦能不慕荣华,与凝之共安俭苦”。“元嘉初,征为秘书郎,不就。临川王义庆、衡阳王义季镇江陵,并遣使存问,凝之答书顿首称仆,不修民礼。”元嘉二十五年(448 年)卒,时年五十九。[16](p2284-2285)龚祈字孟道,“谢晦临州,命为主簿,彭城王义康举秀才,除奉朝请,临川王义庆平西参军,皆不就。……又征太子舍人,不起”。元嘉十七年(440 年)卒,时年四十二。[16](p2285)郭希林,“少守家业,征州主簿,秀才,卫军参军,并不就。元嘉初,吏部尚书王敬弘举……希林为著作佐郎。后又征员外散骑侍郎,并不就”。元嘉十年(433 年)卒,时年四十七。[16](p2292)“子蒙,亦隐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兴宗辟为主簿,不就。”[16](p2292)
刘盛公、刘凝之兄弟,龚祈及郭希林、郭蒙父子均为南朝刘宋时人,梁代则有张孝秀。孝秀字文逸,南阳宛人,“少仕州为治中从事史”,后“为建安王别驾。顷之,遂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孝秀性通率,不好浮华,常冠谷皮巾,蹑蒲履,手执并榈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于石。博涉群书,专精释典。善谈论,工隶书,凡诸艺能,莫不明习。普通三年卒,时年四十二。”[17](p752)
东晋以迄齐梁时期,江汉隐逸的繁盛与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有关。江汉地区处在南北陆路交通和长江东西水运的主要干道上,这是“中古时代最繁荣之交通路线”,[18](p1040)①在政治军事上,江汉地区所在的荆州与都城建康所在的扬州同样重要,荆扬之争几乎贯穿了东晋南朝的终始。四方辐辏、商贸繁荣,经济、文化非常发达,成为孕育隐逸之士的丰沃土壤。从汉晋时期的历史经验来看,隐逸士人常常出自经济文化发达的区域,北方关陇、青齐、河东地区隐逸之士的繁盛即是如此。南方也不例外,除了江汉地区,盛产隐逸的江州与吴会地区也都在南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江州地区有著名的以释慧远(334—416)为核心的庐山佛教文化圈,而文学史上著名的“吴声”与“西曲”,则分别与隐逸之士繁盛的吴会、江汉地区相映照,这些都非偶然。
南北朝后期,北强南弱的形势日益明显。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爆发的侯景之乱,给南方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严重破坏,更加速了北方统一南方的步伐。侯景之乱中,梁武帝的孙子萧詧驻守襄阳,因害怕被江陵的叔叔萧绎吞并而归附西魏,西魏政权乘机派兵进驻襄阳。梁元帝承圣三年(西魏恭帝元年,554年),西魏攻破江陵,梁元帝萧绎君臣出降,萧绎被缢死。绍泰元年(555年),萧詧在江陵称帝,建立后梁,成为北朝卵翼下的傀儡政权。此后,长江中游地区逐步为西魏周隋政权所侵夺,江汉隐逸渐趋消歇。
三、江汉隐逸与中古隐逸传统
在中古时代的隐逸传统中,江汉隐逸是一个较小的士人群体,他们远离政治中心而追求一种名教之外相对自由的生活,甚至对权力有一种自觉的抵抗意识。如刘凝之在给临川王刘义庆、衡阳王刘义季的信中“称仆,不修民礼”,①《宋书·刘凝之传》载:“人或讥焉。凝之曰:‘昔老莱向楚王称仆,严陵亦抗礼光武,未闻巢、许称臣尧、舜。’”同传又载,与刘凝之同时的戴颙与衡阳王义季书亦称仆。参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2285页。显示了士人抗礼王侯的姿态,可以视为隐逸之士的一种觉醒。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彼此可以相互慰藉,如东晋时期的邓粲“与南阳刘驎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14](p2151)又如齐梁时期宗测只与庾易、刘虬、宗尚之等往来,从中可以看到,江汉隐逸的生活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孤寂。很多隐逸之士在幽栖乐道之余,还有很多善举,如刘驎之为孤姥料理后事,刘凝之分钱与饥民,张孝秀率部曲力田以供山众,②《晋书·刘驎之传》载:“去驎之家百余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闻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殡送之。”(参见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48页。)事又见《世说新语·栖逸》第8条“南阳刘驎之”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宋书·刘凝之传》载:“荆州年饥,(衡阳王——笔者注)义季虑凝之馁毙,饷钱十万。凝之大喜,将钱至市门,观有饥色者,悉分与之,俄顷立尽。”(参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5页。)《梁书·张孝秀传》云:“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参见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52页。)种种事迹都堪称道德表率,显示江汉隐逸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藏匿在角落的逃避者,而是常存仁爱慈悲之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之人。与独善其身的青土隐逸和关陇高士相比,他们的担当意识更加鲜明。
南方的秀丽山水也成为江汉隐逸的审美对象,[10](p1028)[19](p90-97)为其生活增添了许多亮色,他们或隐于武当山(赵康),或居岘山之南(庞德公),或“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刘驎之),[14](p2448)或“特爱林泉。十亩之宅,山池居半”(庾诜),[17](p751)或“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隐居衡山之阳”(刘凝之)。[16](p2285)最有名的当数宗炳,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16](p2279)图画山水于私人生活空间,不仅能够唤起往日“西陟荆、巫,南登衡岳”的美好回忆,而且可以使主人超越季节之轮替、空间之限制,欣赏永久恒在的自然之美——抚琴动操,众山皆响,可谓音乐与山水之间的美妙互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山水画之于宗炳,既表达了隐逸的渴望,也营造了一个精神独立的世外桃源。
隐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难免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从两汉时期进入东晋南朝,江汉隐逸出现了一些比较显著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家族化、宗教化、文艺化,这些特点的形成与东晋南朝以后士族影响力扩大、佛教为士大夫阶层广泛接受以及各文艺部门日益繁荣的历史趋势是一致的。
首先是隐逸的家族化倾向很明显。隐逸不仅是士人的个人选择,有时也是一种家族传统,受到家族成员的熏陶和感染,如龚祈“从祖玄之,父黎民,并不应征辟”;[16](p2285)郭希林“曾祖翻,晋世高尚不仕”。[16](p2292)又如宗炳、宗彧之、宗测、宗尚之出自南阳涅阳宗氏,与涅阳宗氏通婚的南阳师氏也有隐逸之士,如师觉授;刘虬、刘昭出自南阳涅阳刘氏,刘盛公、刘凝之兄弟出自南郡枝江刘氏。妻子更是江汉士人选择隐逸的重要精神支持,如宗炳之妻罗氏,“与炳协趣”,又如,刘凝之妻为梁州刺史郭铨之女,却能与凝之共俭苦。与自嘲“室无莱妇”的陶渊明相比,[20](p235)宗炳、刘凝之显然是幸运的。另外,隐逸所出的士族之间也多有交往,如出自颍川鄢陵庾氏的庾承先曾受学于南阳刘虬。[17](p753)有些时候,江汉隐逸虽然自己选择归隐之路,却未阻断子弟的仕进之途,如庾易之子黔娄仕至梁散骑侍郎、荆州大中正,[17](p651)宗炳四子皆出仕,龚祈、刘凝之、师觉授之子亦然,[16](p2285)这显示了隐士的现实考量——他们希望给子弟多一种选择。
隐逸家族之间常有联姻,如南阳宗氏与南阳师氏、襄阳罗氏,襄阳习氏与罗氏之间的通婚。宗炳之母出自“同郡师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16](p2278)宗炳外弟师觉授“以琴书自娱”,亦当有其家族渊源。南阳师氏也是汉晋名族,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 年)置鸿都门学,其时善书之鸿都文学南阳人师宜官当即善书师氏之先驱。①王永平先生据唐张怀瓘《书断》中“妙品”条,认为南阳人师宜官曾应灵帝之征入鸿都门学,为鸿都文学之一员。(参见王永平《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及其原因考论》,载《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第11—17 页。)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就有“师宜官鸿都为最,能大能小”的记载。(参见严可均辑:《全梁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31页。)宗炳之妻所出的襄阳罗氏,为两晋南朝时期的名族,东晋时罗氏与习氏通婚,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势力。②《晋书·习凿齿传》载:“初,凿齿与其二舅罗崇、罗友俱为州从事。及迁别驾,以坐越舅右,屡经陈请。温后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继为襄阳都督,出凿齿为荥阳太守。”参见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3页。南朝时罗氏与宗氏通婚,是襄阳大族联姻风气的延续。
其次,东晋南朝的江汉隐逸多有信仰佛教的倾向,与汉晋隐逸尊崇儒学或崇尚道家思想不同。从战国屈原笔下的渔父到东汉顺桓时期的南阳赵康、汉阴老父,再到东汉末年南郡的庞德公、习融,隐逸之士或守道家之无为、和光同尘,或以经传教授,习圣人之遗业,主要受到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影响。东晋以后,佛教思想逐渐成为塑造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江汉地区而言,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 年),释道安为避北方战乱率徒众南下襄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21](p179-191)自道安南下直到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前秦苻坚攻破襄阳,道安被遣送长安,道安在襄阳生活近十五年,弘扬佛法、导引僧俗,对江汉佛教的兴盛起到巨大推动作用。③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第三章“东晋时代佛学大师之宏佛地域”、第四章“东晋南北朝高僧之地理分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2页。
与此同时,江汉隐逸儒、释、道并重,开启了由儒入玄、儒玄合流的趋势。至南朝这一特点更加明显,如南阳宗氏与高僧交往密切,宗炳曾从庐山释慧远游,并撰有《明佛论》。[22](p10-16)宗炳妻“罗氏没,炳哀之过甚,既而辍哭寻理,悲情顿释。谓沙门释慧坚曰:‘死生之分,未易可达,三复至教,方能遣哀。’”[16](p2279)④南阳宗氏同样重视玄学,如宗测善《易》《老》,归隐庐山时,持《老子》《庄子》二书自随。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41页。齐梁时期亦然,刘虬“精信释氏,衣粗布衣,礼佛长斋。注《法华经》,自讲佛义。”[17](p939)庾诜晚年以后,“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礼忏,六时不辍。诵《法华经》,每日一遍。”[17](p751)张孝秀“博涉群书,专精释典”。[17](p752)宗测“善《易》《老》”。[17](p941)
最后,江汉隐逸多有著述,且雅擅文艺。如习凿齿撰有《汉晋春秋》。孟陋“博学多通,长于《三礼》。注《论语》,行于世。”[14](p2443)邓粲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乃著《元明纪》⑤从题名看,邓粲《元明纪》当是对东晋元帝、明帝两朝史事的编年记录,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曰:“晋江左史,自邓粲、孙盛、檀道鸾、王韶之已下,相次继作。远则偏记两帝,近则唯叙八朝,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参见刘知几:《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页。)浦起龙《通释》曰:“按东晋凡十一帝,起元、明,尽安、恭。邓粲止撰《元、明纪》,是远两帝也。”(参见刘知几:《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邓粲又有《晋纪》,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5—286页。)《隋书·经籍志二》载:“《晋纪》十一卷,讫明帝。晋荆州别驾邓粲撰。”(参见魏徵、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58页。)《晋纪》或与《元明纪》为一书,多出一卷者当为目录或序传。又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晋纪十一卷”条云:“《世说》注引粲《纪》二十余事……《赏誉篇》注:‘咸和中,贵游子弟慕王平子、谢幼舆为达,卞壸欲奏治之。’按咸和,成帝年号。是粲所纪,不止讫于明帝。”(参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十四卷·隋书经籍志考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9 页。)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云:“岂粲初撰元、明二朝事,既而又扩充称《晋纪》耶!粲书亡佚,彦和所云,无可征实矣。”(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02页。)姑录以备考。十篇,注《老子》,并行于世。[14](p2151)庾诜经史文艺,多所贯习,“撰《帝历》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续伍端休《江陵记》一卷,《晋朝杂事》五卷,《总抄》八十卷,行于世”。[17](p751-752)文艺方面,如张孝秀“善谈论,工隶书,凡诸艺能,莫不明习”。[17](p752)又如文学、音乐、绘画是涅阳宗氏的文化符号,宗炳“妙善琴书”,“古有《金石弄》,为诸桓所重,桓氏亡,其声遂绝,唯炳传焉。太祖遣乐师杨观就炳受之”,宗炳澄怀观道、卧游山川,“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16](p2279)又撰有《画山水图序》。宗测亦善画,“自图阮籍遇苏门于行障上,坐卧对之。又画永业佛影台,皆为妙作”,且“颇好音律”。[17](p941)
江汉隐逸的撰著,如习凿齿撰《襄阳耆旧记》,宗测游衡山七岭,著《衡山》《庐山记》,庾诜续伍端休《江陵记》一卷等等,成为江南地域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环节。江汉隐逸还以自己的高士传记和人物图画,丰富旧有的隐逸传统。习凿齿撰有《逸人高士传》八卷,宗测又续西晋皇甫谧《高士传》三卷,积极参与隐逸传统的建构。宗测曾写祖炳所作尚子平图于壁上,又自画阮籍遇苏门先生图于行障上。尚长(字子平)①尚长,《后汉书·向长传》作“向长”,章怀太子注:“《高士传》‘向’字作‘尚’。”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58—2759页。是两汉之际的著名隐士,苏门先生是曹魏时期的著名隐士孙登,②《三国志·阮籍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籍少时尝游苏门山,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名姓,有竹实数斛,臼杵而已。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生萧然曾不经听。籍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苏门生逌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参见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5页。)苏门先生当即孙登,《晋书·阮籍传》曰:“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参见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2页。)事又略见《世说新语·栖逸》第1条及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对前代高士的图写,反映了涅阳宗氏对汉魏以来隐逸传统的自觉体认。
从学术文化角度观察中古隐逸传统的演进,不难发现,秦汉以来的隐者,多有意而为之,儒家或道家思想是他们隐逸生活的重要凭借。汉代的关陇高士以儒道兼综为特征,挚恂、法真、任棠、姜岐、安丘望之、高恢、矫慎、王符等,或擅长儒学,以《五经》教授,或崇尚道家,好黄老之术;汉晋之间的青土隐逸则是在青州浓郁的儒学氛围中孕育而成,薛方、逢萌、邴原、王烈、徐幹、氾毓、刘兆、徐苗等,服膺六艺,尊崇儒学,可谓以儒学而为隐逸。关陇高士与青土隐逸还以经学撰著作为自己的生命寄托,开启了魏晋以后高士以学术和创作传名后世的传统。东晋以后,高士与高僧比肩、隐逸与沙门同行,中国固有的隐逸传统改变了原来的面貌,③六朝时代许多高僧贞风迈俗、岩栖山居,与隐士无异,故现代史学家陈垣谓慧皎之《高僧传》,“实为一部汉魏六朝之高隐传,不徒详于僧家事迹而已”。见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8页。东晋南朝的隐逸之士呈现出礼玄双修、学尚博杂的文化风貌,其所赖以“立言”不朽者也由经学撰著转向文学艺术。这些特点在江汉隐逸身上表现得也十分突出——从汉阴老父到庞德公,从习凿齿到宗炳,江汉隐逸士人远离权力与纷争,托庇于家族,寄心于宗教,内娱琴书、外赏山水,图写高士、续修传记,激浊扬清、荡滓去秽,不仅促成了隐逸传统的丰富和生长,而且自身也已成为中古文化史上美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