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英雄叙事
——中国搪瓷制品中的刘胡兰形象研究
2022-02-11孙晓庆孙洪伟
孙晓庆 孙洪伟*
(齐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各类搪瓷制品深受青睐,甚至成为很多人记忆中的时代标志。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时期,素以经济、实用著称的搪瓷是人们生活中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这才使它能够跨越阶级与身份的限制,广泛地存在于各类人群的日常生活中。搪瓷的这种广泛性还体现在其突破了应用场景的限制,可以毫无障碍地在私人空间(如家庭)与公共空间(如办公室)中来去自如。在事实上证明了当时的搪瓷实现了对自身“物/功能”的超越,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且广阔的空间,并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这正是很多人对搪瓷念念不忘的原因。
进入社会文化领域的搪瓷,在“美观”的层面发挥着作用,一方面构成了“经济实用美观”的最后一环,另一方面也满足了特定时期人们的审美需求。然而,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搪瓷的重要意义绝非仅局限于此,它还在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章拟以中国搪瓷制品及其中刘胡兰形象为研究对象,集中探讨以下问题:①搪瓷制品刘胡兰形象的主要特征;②搪瓷制品上刘胡兰的经典形象是如何被建构的;③刘胡兰形象与日常生活中英雄叙事之间的关系。
1 搪瓷制品中的刘胡兰形象
抗战爆发之初,在毛泽东“用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 的思想号召下[1],出现了对英雄事迹宣传的热潮。基于当时各类文本的描述,艺术家创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形象,其中尤以刘胡兰形象的搪瓷制品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刘胡兰形象的塑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跨媒介英雄叙事的典型。
塑造刘胡兰形象,首先是基于文本叙事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小学语文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刘胡兰的英雄故事依然是小学语文课文中不可或缺的一节。通过这类文本,刘胡兰为了严守党的机密,面对凶残的敌人英勇不屈、顽强斗争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播。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席为刘胡兰亲笔题写的悼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这一英雄叙事的传播提供了关键的意识形态基础。
其次对于图像叙事的角度而言,刘胡兰的英雄形象建构大致可分为3 个阶段:“文革”前(1948—1966 年)、“文革”中(1966-1976 年)和“文革”后(1977 年至今)[2]。最早的刘胡兰形象见于1948 年安明阳创作的木刻连环画《女英雄刘胡兰》[3]。在这件作品中(图1),刘胡兰被塑造成一个圆脸单眼皮、头上裹着毛巾、稚气未脱的农家女形象,贴近一个15 岁孩子应有的样子。到“文革”时期,刘胡兰的形象发生了较大变化。以1972 年版山西人民出版社的连环画《刘胡兰》为典型(图2)[4],其中刘胡兰的形象有着利落的短发、醒目的红色上衣、坚定的眼神、严肃的表情以及昂首挺胸的肢体动作,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刘胡兰形象的巨大转变是这一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需要塑造一个成熟的、保卫国家的英雄形象,从而激发群众的斗志。“文革”之后,刘胡兰形象没有太大发展,大致是“文革”时期的延续。

图1 木刻连环画

图2 连环画《刘胡兰》封面
最后从发展过程来看,文革时期是刘胡兰形象发展的关键节点,建构了刘胡兰的典型英雄形象。从中国搪瓷制品中刘胡兰形象的发展来看,也大致遵循了这一规律。然而由于搪瓷的特殊性,即在日常生活中兼具功能与装饰的双重属性,搪瓷制品中刘胡兰的形象往往会搭配一些装饰性的元素——仰望的视点、红色的背景、黄色的光芒、松柏的装饰以及左侧毛泽东的题词(图3)。从刘胡兰的个人形象角度而言,大致遵循了文革时期文本图像的范式,采用“丰碑式”构图。这种构图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象征性,如图3 中刘胡兰的形象采用仰视角度,人物高大耸立,表情庄严,气氛静穆,色调深沉凝重,在画面构成形式上是顶天立地,形如泰山,宛如一尊坚如磐石的雕塑,很好地塑造了刘胡兰“崇高”“悲壮”“永恒”的英雄气质,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2 刘胡兰英雄形象建构中的影响因素
作为革命英雄的刘胡兰,其英雄形象根植于中国革命。从一个心向革命的普通农家女到一个备受敬仰的革命英雄,少不了艺术的加工与塑造。然而,在刘胡兰英雄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中国革命艺术也受到了大量外来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木刻以及波兰招贴艺术。因此,在刘胡兰的典型英雄形象建构中,能清晰地发现这些艺术影响因素。
2.1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秉持了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国与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交流,包括艺术领域。当时的苏联成为中国艺术界认识外部世界为数不多的窗口之一。苏联艺术传入中国后,作为一种垄断性的文化资源,几乎伴随着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对中国的艺术设计也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点表现在3 个方面:①注重题材的选择;②表现生活光明的一面;③围绕思想主题强化艺术处理。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中国美术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革命题材的选择与创作。现实主义主张再现现实生活,正确的艺术思想决定正确的阶级立场,因此,这一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达到了高峰。其次是在作品中表达革命精神,尤其是与中国革命紧密相关的英雄形象的塑造,逐渐成为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方面,因此,工农兵中的先进人物、革命斗争中的典型人物开始成为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中涌现了很多典型的英雄形象,例如雷锋、刘胡兰、白求恩等,其中,刘胡兰的形象最具代表性。在刘胡兰经典形象的塑造中,王朝闻在1951 年创作的《刘胡兰》雕塑发挥了重要作用(图4)。他选取了刘胡兰走向铡刀的一瞬间,刘胡兰目光坚定,双拳紧握,充分展示了刘胡兰英勇就义时的英雄形象,这一形象被广为接受和传播。1957 年,冯法祀油画作品《刘胡兰就义》(图5)中,刘胡兰形象便接受了这一作品的重要影响。

图4 《刘胡兰》雕塑
从创作手法的角度来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深刻影响了刘胡兰英雄形象的塑造。在冯法祀的作品中,刘胡兰的形象从受刑到向群众告别场景的转变,正是苏联艺术创作模式影响的结果。就搪瓷这一载体中的刘胡兰形象而言,苏联政治宣传画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其以埃尔·利西茨基的作品为典型(图6)。如果将图3 中经典的刘胡兰形象与图5 中的人物形象相比较,便会发现二者之间的紧密关联。首先,两件作品都选择了青年男女的形象,形象朴素却又兼具社会代表性;其次,都采取仰视角度,目光坚定且目视前方,饱含坚定的革命意志;同时,在色彩的选择上,以红、黑二色为基调,简洁有力又充满革命色彩。从画面中的主体形象来看,二者有极高的关联度。但是在主体形象之外,二者又有鲜明的差异:埃尔·利西茨基的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下方是极具构成主义特色的建筑结构,而与刘胡兰形象搭配的则是中国气息浓厚的青松红日。

图3 搪瓷盘

图5 《刘胡兰就义》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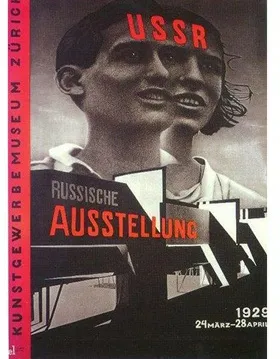
图6 埃尔·利西茨基海报招贴
因此,苏联艺术对搪瓷制品中刘胡兰英雄形象创作的影响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刘胡兰的主体形象的塑造受到了苏联政治招贴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在刘胡兰英雄形象的塑造中,中国并非完全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融入了很多中国文化元素,或许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最好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特色”艺术创作理念的生动诠释。
2.2 延安木刻版画的影响
“延安美术以木刻版画为主要面貌,吸纳了20 世纪30 年代上海新兴木刻运动中的一批左翼美术家的创作特点,反映出战时美术作为抗战时期一种‘不可缺少的力量’为现实服务的特征”[5]。延安期间的美术作品产生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环境中,其形式以大量的连环画、木刻版画以及少量的油画作品为主,其题材以对战争场景、劳动生产、英雄事迹的真实记录为主,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
延安木刻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延安木刻版画刀法粗犷、线条稚拙且硬而短,多见带着尖锐棱角的黑块。在造型方面,延安木刻版画常用变形、夸张、概括和抽象的方法,配合以简单倾斜的构图和对比强烈的明暗关系(图7)。搪瓷制品上的英雄形象深受延安木刻版画的影响,人物形象扁平,突出大色块之间的对比,以线、面造型为主,不追求透视与景深,几乎就是木刻版画的翻版。如图8 中刘胡兰的形象即是这一影响的直接反映。图中刘胡兰的形象简洁,身体左侧的大色块与右侧的空白形成鲜明对比,辅以粗壮的线条;背景是大面积的方形色块。尽管画面的主体是红白二色——不同于木刻版画的黑与白,但是在造型手法和视觉效果上,二者如出一辙。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图9、图10 中体现得更为直接,雷锋和白求恩的形象直接以黑白木刻的效果呈现,辅以红色的点缀或大面积的色块。

图7 木刻(鲁迅)

图8 刘胡兰搪瓷杯

图9 雷锋搪瓷盘

图10 白求恩搪瓷盘
2.3 波兰招贴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除与苏联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外,我国同时也与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增强了友谊。1955 年,波兰宣传画和书籍插图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对于新中国而言,招贴画是一个新事物。同年在《美术》杂志12 月专门刊登了刘迅的《艺术——创造性的劳动:从“波兰宣传画和书籍插图展览”所想起的》和史记的《记波兰宣传画和书籍插图展览》两篇文章进行研讨,对中国设计的发展影响巨大。
波兰招贴画在题材上表现劳动人民、领袖、英模形象,但在形式手法上却并未被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框架所左右,而是偏爱采用西欧广告招贴流行的新潮风格,即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为严格的素描比例所拘,也不追求照相般的视觉真实,而是强调大胆概括、适当夸张并且追求单纯明快的色彩效果。翁逸之在《爱海洋爱舰队,就是爱祖国人民》中(图11)采用的是“洋办法”:侧重对象的立体结构和光影关系,使画面更具“民族化”气息。同时,他还坚持平面化、概括性的绘画语言,着重塑造厚重坚实的体积感。
日用搪瓷制品刘胡兰的英雄形象设计以宣传为首要任务,在作品中删除一切不必要的东西,以最大的力量把主要的意图凸显出来,给人一种振奋的力量(图12)。这跟波兰招贴画《一九五五年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图13)这幅画的创作技法相似。画家突出地刻画了一个年青妇女的形象,她骄傲地昂着头,瞭望着前方,表现了对于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坚强的信念。在画面上看不见任何多余的东西,一些细节的描写也是为了凸显主题的效果。这种简单概括的手法,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得到充分、完美地表现,起到了招贴画应有的效果。波兰的招贴画为中国的设计思维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例如在表现形式上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丰富的想象力、新颖的构图、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强烈的民族风格等,中国从波兰招贴画中学习了卓越的创作经验。

图12 刘胡兰搪瓷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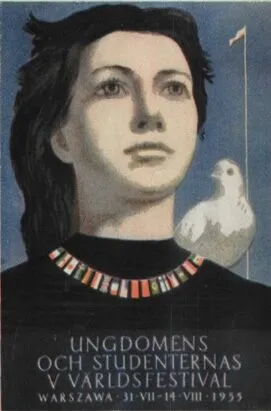
图13 波兰招贴画
3 刘胡兰形象与日常生活中英雄叙事
3.1 刘胡兰英雄形象中的叙事
1949年后中国社会主义美术的创作基本延续了延安美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传统。后来“红光亮”和“三突出”等创作原则的出现大致可视为这一传统在特殊时期的极端化发展。从艺术创作与意识形态传播的角度而言,二者几乎是如出一辙的。
从社会现实条件来看,当时中国的农村人口基数庞大,文盲率接近90%[3],这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文字阅读和理解能力。因此,图画、图像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最佳媒介手段。但是图形图像也有其天然的局限性,无法完整地复制、传达复杂的文字信息,这必定会影响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因此图像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英雄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是意识形态宣传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刘胡兰便是重点塑造的英雄形象之一。
在当时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中,刘胡兰是极为特殊的一个。首先与大多数英雄不同,她并非军人,也没有军队的经历,只是一个普通人——积极进步的年轻农家女;其次她还是为数不多的女性英雄形象。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中,任何英雄形象的选择与塑造都绝非偶然,一定是慎重思考的结果。刘胡兰年轻、女性、平民化的特点使其与一般的英雄形象构成差异化,从而能够在特定的人群中产生群体共鸣。在革命战争时期,意识形态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军队、战士,因此需要战斗英雄。然而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意识形态的主要宣传对象转向了社会大众,作为大众化的英雄——刘胡兰的英雄形象便应运而生。
然而,任何英雄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仅凭图像是远远不够的,需借助于文本和叙事。在刘胡兰英雄形象的塑造中也是如此,首先要确立与其相关的英雄叙事。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亲笔为她写了挽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每个人对这两句话都无比熟悉,因为它被写入小学教材,成为每个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必学的课文。通过这样的方式,刘胡兰的英雄事迹被每个中国人所熟知,也构成了刘胡兰英雄叙事的社会基础。
于是,伴随着刘胡兰故事的社会传播,刘胡兰的英雄形象不断被建构。在这个过程中,雕塑、绘画等艺术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使一个只存在于故事、文本中的英雄以视觉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让刘胡兰的英雄形象真正深入大众,最大化地实现其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其与日用搪瓷制品的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3.1 搪瓷与刘胡兰英雄叙事大众化
艺术作品的传播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即使是借助于印刷技术,在当时的条件下,成本高昂的彩色印刷品也不可能真正深入千家万户。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观看”而非“拥有”。观看行为只能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进行,而“拥有”则意味着可不受限制地“观看”,这便意味着传播的日常生活化或大众化——区别于艺术的特殊化。在刘胡兰英雄形象传播中,真正使其实现日常生活化的关键是搪瓷制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日用搪瓷制品是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标志性器物。它可以是喝水的茶缸,也可以是洗脸的面盆;它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器皿,也可以是婚嫁赠送的贺礼;它可以在家庭空间中随处可见,也可以毫无违和感地在各类工作空间中自由穿梭。这使搪瓷具备了绝佳的深入日常生活的基础。与此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这时的搪瓷并非纯粹的功能之物,还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尤其是搪瓷器皿所具备的光洁平整的表面是天然的图形图像与信息的载体。
尽管现在已经很难追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日常生活中,英雄形象的塑造与搪瓷制品的结合是有意为之,还是纯粹的偶然意外。但是依旧可以确认,两者的结合为英雄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提供了深入日常生活的重要途径。甚至国民可以假设,若没有搪瓷这个关键媒介,意识形态宣传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刘胡兰英雄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便是这一大背景中的产物。
从媒介的角度而言,搪瓷制品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有先例的。尤其是在五卅运动后的抵制洋货、提倡国货运动中,搪瓷制品在唤醒国民身份的认同和民族意识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后,除了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之物外,搪瓷制品还一度是重要荣誉的象征,作为重要评比、活动的奖品、纪念品。这类搪瓷制品上往往印有特殊的口号或宣传语,如“赠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为人民服务”“劳动模范奖”“先进工作者奖”等。作为奖品、纪念品的搪瓷,表面来看是对个人的奖励,但是在各种奖励名目的背后,实则是对意识形态的宣传。无论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劳动模范奖”,都是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认识到这一点,再去审视刘胡兰英雄形象与搪瓷制品的结合,便能更深刻地理解其中意识形态含义。
然而,与那些作为奖品、纪念品的搪瓷器皿相比,饰有刘胡兰形象的搪瓷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皿。尽管这似乎降低了这类搪瓷制品的象征价值,但是却极大地拓展了刘胡兰英雄形象的传播空间,使其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在此,搪瓷是作为“功能之物”而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可能并不是其首要考虑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如同其他装饰题材一样,某件搪瓷制品与刘胡兰英雄形象的结合可能是一个偶然,也可能不是。然而对大众来说,借助于搪瓷出现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刘胡兰形象,可能是一种装饰,但绝无可能是一种普通的装饰,他们一定能够认识到其饱含的革命色彩。这便是刘胡兰英雄形象真正的大众化,即仅凭图像本身,无需多余的文本阐述便能实现大众认知,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实现英雄叙事。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实现这种英雄叙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①先行性的文本叙事——在大众中普及英雄事迹;②一个能真正深入大众日常生活的物质载体,就主题而言是搪瓷。
4 结语
塑造英雄形象的目的就是塑造国家形象、展现民族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塑造了一系列“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刘胡兰的英雄形象便是其代表之一。
从视觉形象的角度来看,刘胡兰的英雄形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到1949 年后才逐渐固定为大众所熟知的形象。在此过程中,既传承了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风格,也接受了苏联、波兰艺术的影响。然而,任何英雄形象的社会认知与传播都需要借助英雄叙事,尤其是深入大众日常生活的英雄叙事。在刘胡兰的英雄叙事中,日用搪瓷制品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在文本叙事的基础上完成了图像叙事; 另一方面使刘胡兰的英雄形象以搪瓷为媒介深入大众日常生活,并且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