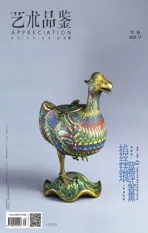格里塞作品《调制》的时间结构与音高组织
2022-02-11董笑萱上海音乐学院
董笑萱(上海音乐学院)
格里塞的作品《调制》是一部经典的频谱音乐作品,笔者在本文中对其结构、音色、音高展开分析,并通过“偏离音”的概念将频谱音乐分析与传统音乐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为频谱音乐中的微分音找到其结构归属及本质内涵。
在笔者的《法国频谱音乐音高组织理论与分析实践》一文中,已经介绍了频谱音乐音高组织的几种常用方式——音高素材的来源途径与其组织过程。而事实上,如该文中指出的那样,从作曲家的角度还原作品,并不属于音乐分析本身,分析者应当从乐谱中逆行倒推分析出具有音乐分析视角特色的信息,以便总结该类作品的创作规律、提炼其创作内涵,进一步引发理论创新。
在上述文章中没有解决的问题是:频谱作曲家通过分析乐器音高得出频谱数据,然后将其分配给不同的乐器演奏,在这个过程中,为何要选用某个乐器作为采样源?又是以怎样的原则将分析得出的数据分配给不同声部的呢?这些音高组织原则与传统音乐作品的音高组织方式有哪些异同呢?下文以格里塞的作品《调制》中的部分片段为研究对象,来解答如上问题。
一、结构布局
频谱音乐作品的宏观结构往往呈现一种“演进式”的状态,如果不是作曲家刻意为之,它很难像共性写作时期的作品那样可以以二分性、三分性划分结构,也不像序列音乐作品那样有一个(或多个)既定的程序来设定作品的走向,它呈现出的是一种天然的结构,符合声音本身物理特性的自然演进过程,它与共性写作时期作品的“生态”一样,从听觉和心理上来说,这种演进是可预测的,(如贝多芬音乐作品中紧张-解决的关系是符合听众的听觉预期的),而不同的是,频谱音乐作品的“紧张-解决”关系,或“明-暗”/“暗-明”的对比是一个相对来说更为漫长的过程,也就是说,这种“紧张-解决”的关系在横向线条上被拉长了,而这种“被拉长”的演进结构正是来源于作曲家们对于声音时间过渡性的认识。
《调制》是格里塞套曲《声学空间》(《Les espaces acoustiques》)中的第四首,《调制》前的两首作品《周期》 《分音》都是室内乐作品,而其后的作品《瞬间》是管弦乐作品,因此该作品在《声学空间》套曲中起着重要的规模过渡的作用。
格里塞的作品《调制》从宏观结构和微观音高组织上都体现出声音时间过渡性的加持作用,在部分结构布局中,它起着必然的导向作用。下文将以“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来反应该作品随时间演变的自然结构态,由于时间结构是一种自然状态,结构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完全清晰的,会出现结构间覆盖或重叠的现象。
在分析作品并且划分时间结构时,要根据每个阶段的“起音”和“释放”点作为分段的依据,此处笔者以时间结构I 为例来说明时间结构的展开方式。该时间结构内部整体呈现出一个非常缓慢的演进过程,频谱由非谐波“进化”到谐波,起音用时由短到长,节奏从非周期性到周期性演变。从音响色彩上来看,此时间结构内完成了渐进的暗-明的色彩转化,从音响感知的角度上来说,它完成了紧张-解决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相对于传统音乐作品中的处理来说,需要听众更多的耐心。

谱1 (图片来源:个人自绘)
时间结构I 从管乐组和弦乐组两个乐器组的对置节奏开始(谱例1),这样的节奏制衡关系持续到排练号[5]后的第7 小节,双簧管声部在降低四分之一音的G 音离开了管乐组加入弦乐组的已有的节奏模式中,从此处开始,由两个乐器组音色对置的模式转换为音色分界清晰的三个乐器组。
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将《调制》划分出八个时间结构,这八个时间结构分别都是从一个音高的谐波/间谐波进而走向另一个音高的模式。如果要以二分或三分性的方式来划分曲式结构,我们只能参考该作品的响度曲线以及这八个时间结构对该作品进行划分,下图为《调制》的结构图示:虽然时间结构之间是重叠的,但包含时间结构的曲式结构间有明显的段落界限。第一部分从一个频率范围较大的间谐波谱开始,经历了bE、F,E 为基波的频谱,一直到排练号[22]处,一个打击乐的单音和被延长的休止符标志着这部分的结束。第二部分从低音鼓的弱奏开始,响度逐层增加,一直到[44]处以响亮且短暂的爆发结束,第二部分的响度曲线与第一部分是扩大对称的关系,并以[22]处的休止符为对称轴,[44]从ffff 的力度突然回到pppp 的力度,标志着第二部分的结束。第三部分从基音为E 的谐波谱开始,最终以间谐波谱结束,这部分与第一部分的谐波结构也呈现出轴对称的关系。
二、采样乐器的选择与“音高-音色”宏观布局
(一)采样乐器选择
《声学空间》整部套曲建立在长号频谱基础上完成,笔者总结格里塞选择长号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克劳德·里塞于1976 年在美国声学学会上题为《小号音高的计算机研究》的演讲以及1969 年出版的《计算机合成声音导论》等研究通过大量基于铜管乐器的实例揭示了合成音色的分析方法——通过了解频谱每个分量的包络线来了解音色,这些计算机音乐早期最重要的声音合成技术在当时对格里塞以及其他频谱作曲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至此,格里塞的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开始深入到声音的核心,从声音的组成元素(时间、空间、频率)展开来进一步研究声音组成成分与音色之间的联系;此外,格里塞在分析了各种铜管乐器的频谱后,选择了频率范围相当广泛的长号作为研究对象,用ff 力度吹奏长号可以产生接近可听范围极限的分音;从时间过渡性方面来看,长号的起音时间短、延留时的状态稳定,释放的状态与起音状态接近。
(二)“音高-音色”宏观布局
作品的第VII 段时间结构集中体现了作曲家在时间结构中组织音高的技术手段。在这个时间结构中,格里塞将乐队分为A、B、C、D 四组乐器组,每个乐器组内包含五种乐器,每一组都是一种复合音色,也就是说,A、B、C、D 是四种新的人造乐器,最低音乐器担当了该人造乐器基音的角色,上方四个声部作为基音上方的“分音”(在这里实际演奏得到的效果是复杂音),格里塞通过全新的四种“乐器”,创造了人为的间谐波谱,通过控制单个乐器的音高从而改变乐器组的整体音色,形成ABCD四组乐器间的“频谱复调(spectral polyphony)”。
乐器组从[30]后的第三小节开始以不完整的形式出现了两次,然后在[31]后的第三小节以完整的形式出现,从这里开始的每一组都呈现出高斯曲线的形态(见谱2),接下来B、C、D 组依次先后以相同的形态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每组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包含的音符却越来越多,因此产生了加速的效果,同时,每个乐器组进入的时间差也越来越小,一直到[37]的高潮处,差值缩小到了最小,越发密集的音符和越来越强的力度共同创造了这个时间结构中的高潮点(谱3)。

谱2 A组的两次不完整形式和一次完整形式(图片来源:个人自绘)

谱3 排练号37前四个乐器组中最低声部的节奏(图片来源:个人自绘)
段落高潮过后,前面加速的状态开始发生反转,每组的持续时间开始增加,组与组之间的间隔时间被拉长,分音在每个乐器组中逐渐对齐,一直到A 组中的五个乐器完全对齐,其他组别内部也趋于齐奏状态,组与组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明显,力度在[42]前陷入谷底。
如前文所说,第VII 段中的四组乐器组之间是“频谱复调”的关系,而《调制》整首作品的时间结构之间是一种“结构复调”(参考表1)。无论是使用了频谱还是结构的对位,其本质都是在模拟乐器的动态频谱图。

表1 《调制》的结构图示(部分时间结构之间重叠或覆盖)
三、偏离音(微分音)与“音高-音色”微观布局
笔者在本节中将用“偏离音”代替“微分音”的说法对作品进行分析。“偏离音”一词受到理论家哈里森的启发,哈里森在其著作《当代调式音乐分析》中指出:“亨德米特曾说‘(大小三和弦的两个三音)标志着同一声音的高与低、强与弱、明与暗的形式’。”他认为,亨德米特没有指出的是,在这两个和弦的三音之间是存在着一个模糊区域的,见图1。

图1 小三和弦与大三和弦之间的“模糊区域”(图片来源:个人自绘)
哈里森认为,在泛音调性系统中形容三音所处的位置时,用“带宽”来形容比用一个确切的“点”来表述要更确切。笔者引用哈里森的理论试图解释频谱音乐中使用的那些微分音,微分音是十二音基础上的偏离,因为这些偏离音的存在,使得音与音之间过渡的过程被放大,使得一个纯粹的音得到了颜色的渲染。
如《调制》排练号1 后的7 个小节,乐器组I 与乐器组II 以节奏和音色对位引动了全曲,1-7 小节的大号声部进行如谱4 所示,虽然在纵向的和声结构上作曲家使用了大量的偏离音以及非传统形式的和弦结构,然而我们依然能从大号声部找到调性和声的影子(或者说调性和声的和弦结构与和声进行符合泛音列的结构)。F-A-C-bE 每一个和弦音都在高八度(或高两个八度)的音区得到大号或别的乐器的支持,而这个属七和弦中的三音与七音(决定属七和弦性质的两个音)都获得了其偏离音的加持,这大大扩充了该属七和弦的分音含量。

谱4 (图片来源:个人自绘)
再如,排练号14 后三小节出现的和声音响,是在大小七和弦结构E-#GB-D(见谱5)的基础上,加入两个偏离音(降低四分之一音的A、降低六分之一音的D)构成的,其中,降低1/4音的A 相当于升高3/4 音的G,它是E-#G-B 和弦中以#G 音为原点的偏离音,降低1/6 音的D 则是B-#D-#F 和弦中以#D 音为原点的偏离音。

谱5 (图片来源:个人自绘)
如果以偏离音的概念来理解微分音音乐、频谱音乐,我们就能将其纷杂的音高有序的组织起来,以三度结构和声的概念来理解频谱音乐中的音高排列方式。
四、结语
格里塞本人认为《调制》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塑造“连续体”的过程,是实现音色转换的过程。听众对于音色的感知来源于他们对于音高(频率)、响度(振幅)等概念的认识,格里塞通过控制频率、振幅以及音符密度等信息来塑造他想象中的音色和音响效果,进而影响听众的听觉感受。还原作曲家的创作过程能够直接解答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而在了解基础的相关技术知识之后,作为分析者,我们应当回归乐谱本身,提供一种分析者视角的解读。本文从结构、音高、节奏三个方面对《调制》中的部分片段进行了分析,无论是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出声音的特性(如时间过渡性、和声-音色连续体)对作品创作的重要作用。而在音高分析方面,笔者引用哈里森的“偏离音”理论,为看似无法用传统音乐分析方法来解读的频谱音乐找到了分析的切入点——“偏离音”是十二音基础上的色彩渲染。如果说共性写作时期的作品符合我们的感性直觉认知,序列音乐反映了一种绝对的理性系统,那么频谱音乐,或基于频谱思维所创作的“后频谱音乐”则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它以理性(物理声学)为材料,以感性(心理声学)为其材料重新组织方式的参考,铸造了一种接近天然的结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