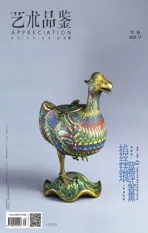体育舞蹈叙事初探*
2022-02-11吴文君伍孝彬谭晓雪南京体育学院武术与艺术学院
吴文君 伍孝彬 谭晓雪(南京体育学院武术与艺术学院)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现实主义题材舞蹈作品的爆发式发展,对舞蹈的“叙事”研究也在不断完善,从单一的对“叙事性舞蹈”的舞蹈作品进行研究,进一步拓展到涵盖了所有舞蹈作品的“舞蹈叙事”研究。“叙事为舞蹈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框架”,但并不是随意填充的框架,需要一个完整的统一性,并在线性时间内有序进行。简单来说,“舞蹈的完成过程就是舞蹈叙事”。
体育舞蹈即有舞蹈艺术性,也更强调体育竞技性,通过与音乐节奏的配合达到观赏性抑或某种情感抒发的功能性。在体育舞蹈中本就存在技术性体育舞蹈(以动作表演,展现舞者技术能力为主要目的)和体育舞蹈艺术表演舞(有主题、人物形象等元素在内,以作品内容呈现为主要目的)两种表现形式。
前者对于叙事的需求甚少,遂本文旨在后者语境下对体育舞蹈叙事进行探究。
二、“二分法”下的体育舞蹈
“二分法”的概念主要源于西方经典叙事学中,是指对一个作品(任何形式,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等)进行对“话语”与“故事”的区分。不同的叙事作品存在不同的“二分法”形式,包含“故事”与“话语” “内容”与“形式” “素材”与“手法”等。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一书中指出:“无论是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还是说文学创作中的虚构,故事事件在叙事作品中总是以某种方式得以再现。再现手段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电影镜头、舞蹈动作等。也就是说,可以区分所表达的对象和表达的方式。西方叙事学家一般采用‘故事’与‘话语’来指代这两个层次。”
在探究体育舞蹈叙事性时,笔者选择厘清“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如申丹、王丽亚在其书中所言:(1)有利于关注超出遣词造句但结构技巧;(2)有利于分析处于“语义”这一层次的技巧。
(一)体育舞蹈中的“故事”与“话语”
体育舞蹈属性更偏向于竞技性舞蹈,其艺术特征特性对于舞蹈“故事”的概念本较为单薄,肢体语言具备赛事规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话语”的发挥。似乎看上去“故事”与“话语”在体育舞蹈作品中并无用武之地。但随着体育舞蹈本土化发展,可以看到大量作品融入了中国元素,如中国传统故事、先锋人物、经典文学等,或编导以个人经历经验虚构“故事”的作品也层出不穷。竞技性舞蹈已不再简单追求“技艺”,更多转向作品意义的表达与传递,由此可以看出,该舞种已经存在叙述需要及叙述对象。那么,在探究之前,需厘清什么是“故事”,什么是“话语”。
故事是指利用书面、口头、文字、电影等,按照时间因果排列等事件。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文本。过滤了主观带来的时间、空间与其他修饰,是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语表达出来的部分。话语是指对叙述事件不同素材的艺术处理和形式的加工合成,可以理解成为完成叙事,所采用对各种叙述方式,对事件的重新布局、编排的叙事手段或技巧;即“故事”为骨,“话语”为血肉。此外,也有学者将“话语”用“情节”指代,但无论是分析还是创作作品,“话语”的范畴显然更加广泛。以南京体育学院体育舞蹈原创作品《家园》(编导:吕园欣;表演:南京体育学院)为例,进一步讲明“故事”与“话语”。
森林里有一群鸟儿,他们快乐、勇敢、无忧无虑,每只鸟儿都在肆意挥舞自己美丽的翅膀,在森林里徜徉,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预示了危险的来临,打破了原本的宁静。所有的鸟儿抱作一团,警备地看向周围的一切,寻找这一声刺耳,具备危险性的声音。“嘭”,又是一声,一只鸟儿被击中,原本的快乐与安宁,不复存在,只有悲伤,他们跳起悲伤的舞步,连翅膀的挥动都显得极为吃力。可是他们要保护他们唯一的家园,他们要振作,要互相帮助,坚持下去……
这个作品就是一个借助“话语”构建起来的“故事”。从“故事”看,可以概括为:一群鸟儿保护家园的事儿。再缩简便是一群鸟儿的家园,甚至可以是鸟儿的家。这部作品参与了2013 年的桃李杯,并在后期参与多个比赛、展演获得嘉奖。正因为有了叙述者即编导的“话语”使得原本单一、单调的“故事”更加具有人性色彩,同时也赋予了“故事”的起承转合。
常规的体育舞蹈作品,大多是以舞种(拉丁或摩登舞种下的五支舞)展示为目的,是一种利用动作堆砌和节奏更迭来表达情绪和情感体验的表演,冠以一个题目。而此类体育舞蹈作品的出现,无疑是大胆的、创新的。其一,需要编者除了对本专业的至高理解,也需要有一定跨领域的交叉了解,以此完成作品所需的时间、空间安排以及其个人编创视角注入和情节层次架构;其二,将体育舞蹈作品引入“意义表达”的层面。
(二)“人物的思维风格”叙述
在创作舞蹈时,首先要确定舞蹈的“文本”,确立这个作品的基调、属性,以及“内容”的呈现方式。简单来说,“内容”为不变量,其他要素是以编者的愿望进行相应创作,从而达到同一种“内容”,可以采用不同舞种、方式方法去表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叙述视角”。
作品创作本是编导:“我要做什么(故事),我要怎么做(话语)。”但除此之外,在作品的架构里,即赋予虚构人物的眼光及“叙述力”,是展现剧中人物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以第三人称为叙述视角的作品,简而言之,最终呈现出的是表达编导想表达的,但是以表演者或剧中人物为叙述媒介,传递信息的。这种的叙述方式即是在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框架下,所说的“人物的思维风格”叙述手法。
申丹、王丽亚在其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是英国当代小说家威廉·戈尔丁《继承人》一书中所采用的这一突出手法。(1)一根棍子竖了起来,棍子中间有一块骨头……棍子的两端变短来,然后又绷直来。洛克耳边的死树得到了一个声音“嚓!”(2)一个男人举起了弓和箭,洛克还以为是一根棍子竖了起来,他不认识箭头,以为是棍子中间的一块骨头……当那人将弓拉紧射向他时,他还以为是棍子两端变短后又绷直来。射出的箭击中来他耳边的死树,他只觉得从那棵树传来了一个声音“嚓!”(3)一个男人举起了弓和箭……他将弓拉紧箭头对着洛克射了过来。射出的箭击中了洛克耳边的死树,发出“嚓!”的一声响。
《继承人》中的主角洛克是原始部落的一员,他不认识武器,也不能理解智人的进攻行为。(2)和(3)均是采用传统的叙述手法,即以作者的直观体验和文笔进行描述内容,而(1)则是以洛克的思维方式作为内容本身。洛克的思维,“一根棍子竖了起来”;常规叙述,“一个男人举起了弓和箭”,如此对比,便很明晰了。
从“内容”的层面分析,以上都是描述洛克看见了智人攻击,但是同样的内容运用不同的样式表达,“故事”与“话语”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效果。
在不违背体育舞蹈特性的原则上,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人物的思维风格”的叙述方式可以丰富其内容材料的多样性,强调“话语”的叙述手段,可以有效避免为动作而动作的状况。
三、体育舞蹈的情节结构
(一)情节的安排
亚里士多德对于情节的认识为现代小说叙事理论的情节管理奠定了重要的认识基础,促进了人们对叙事理论中情节的认识。江口隆哉对舞蹈创作的机理也有着很深的认识,对于我国舞蹈编创有着较大的影响。在小说故事情节结构的分类中大致又六种,即线状结构、网状结构、画面结构、象征结构、写实结构、散文结构。这些结构为舞蹈作品创作提供了借鉴,即内在表达和外在形态的关系,“形式”与“表达”。
任何舞种,舞蹈情节的构建、重塑、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情节结构是联通“故事”的血脉。在体育舞蹈作品中,由于肢体语汇及舞种性质的限制,更应了解情节、选好情节。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是以悲剧和史诗作为分析对象,但夯实了叙事“情节观”的理论基础。他“把情节看作悲剧艺术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把情节界定为对‘事件’的安排”。他对这方面的安排,实际上是从故事层面上对事件结构本身的建构,而不是在叙事话语层次对事件的重新设定。
谈论情节,首先解决第一个层面,即“情节安排”。亚里士多德认为,“事件的安排”包含“人物”和“行动”两个层面。人物决定了行动,行动创造了人物。一部作品,需要什么样的人物,就会相应出现什么样的行动,行动——行动反应,形成连锁的环节,成为情节的首要要素。一切的创作“人物”“行动”,需立足于“人物”显要特征,而“行动”的安排是否符合“人物”的性格、职业、精神、内心状态等,是作为编者考虑的,也是传递信息于观众的显性表达,即作品中舞蹈形象的构建取决于舞蹈动作。
以万素老师创作的国标舞舞剧《长恨歌》举例,其舞剧是以人物为先,铺散开的关系与故事发展。讲述了女主王琦瑶与男主李主任、男二康少爷、老克腊等人的恩爱情仇。一生善良,却未能触摸到爱情的归属的故事。
在万素老师分享的文本中,可以看到细致的“情节安排”:银色聚会(景片纯舞)、上海小姐(五色聚会)、灰色聚会(分别)、黑色聚会(解放)等幕、章节的安排,在各幕中安排了对应的人物行为行动,在多人行动的过程中,碰撞出“情节”的矛盾,刻画展现人物的特殊性、特征性,又符合事件的合理安排。此外,亚里士多德也在其论述中一再强调事件的情节结构必须完整,其因果关系、联系必是串起故事的钥匙。
(二)故事性
体育舞蹈的“故事性”作为强调动作性质和表达而存在,意使原本纯技术的肢体变得具备语言功能,凸显作品的结构性、故事的感染性,提升作品的对话感。那么可以理解为,先有了故事事件,再根据舞种舞蹈动作特点对情节结构进行重新安排,着重于整体事件的逻辑关系,利用这种逻辑关系,推出舞蹈作品的整体结构。万素老师在进行剧情介绍时讲述到:“利用舞种的已形成态,衬出舞种的美学特性和价值,并促成这一舞剧的形态风格和对人物刻画的独特性,从而完成此舞剧的独特意义,乃至对艺术种类的探索尝试和作品的创造性。”编者利用舞步性质的变化,刻画女主王琦瑶情感特征,以架构了的人物性格出发,构建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及“遇见”时产生的心理状态而推动着事件发展,以此完成情节结构的安排。似乎在说人,其实这些“人物”均是“情节”“故事性”的打工者,是为主题思想、舞蹈内容、情感表达做的铺垫起着推动发展、完成高潮及收尾的作用。
一部作品的诞生,并不是有了想法便可以编起“故事”。作品的情节结构是具有完整性的,在确立故事主题,对事件的空间与结构的设计架构、人物小传的描绘、形式的注入等之后,意向便有了,故事性也应运而生。在舞蹈创作中,除了“事件”、舞蹈动作外,其中还包含了“戏剧语言”“符号特征” “逻辑约定” “表情暗示”等,此类体育舞蹈作品的出现,拓宽了这项艺术运动的维度。
四、体育舞蹈作品中的人物观
舞蹈作品的人物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舞蹈作品的承载体——演员;二是舞蹈作品中舞蹈演员的构建体——作品人物。由于是在编创视阈下进行的分析,遂着重对作品人物进行分析。
(一)具象型人物
“具象”对于舞蹈作品而言,是作品中所表达的人物是有具体形象特征、内心状态的,是一种以刻画人物为主的编创倾向。这类人物可以是有具体名字的一个人,例如熟知的《阮玲玉》《祥林嫂》等;也可以是指代某一类人,例如《同行》 《胡同印象》等。是单纯用肢体动作描述其心理、个性的。在作品《孔乙己》中,从长衫的破烂不堪,乱糟糟的头发,躬身、缩脖,表情的浮夸无不为书生的形象服务。舞蹈独、双、三人作品通常6—7 分钟,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铺垫,在出场的一瞬间,就需要用准确的肢体动作抑或服化道帮助建立“人物”。
以体育舞蹈作品《胡同印象》(编导:吕梓民;表演:北京舞蹈学院)为例,出场时,女演员身前裹围裙,身体前倾,搭配舞步左右探寻,老太形象一眼即出,随后一帮大爷背手、二位大爷蹲弓背,迈着舞步出现,手提着鸟笼配合着旋转,以遛鸟这一行为刻画胡同大爷,清晰明了。任何一次动作的变化均是围绕人物形象出发。
到此,体育舞蹈似乎又进入了一个难题。规定性的肢体动作如何建立具备独一性“人物”?当你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已经进入了固有的行业模式、习性里了。作为西方舞种在进入中国之时便扎根地定性了它为竞技项目,可事实真是这样么?舞蹈本身是以“动”为前提,“乐”为收获的,共鸣传递为最终意义的。无论是竞技型还是表演型,叙述和表达的欲望一直都在。至于因“人物”或作品“事件”或“情感抒发”而改动的部分动作耿耿于怀,界定它是否还是原本的体育舞蹈,暂可交由观众及时代评定。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每一样事物都需要时代的推敲。比赛体验派和艺术表演派本无矛盾,只是在不同领域展示各自理解和让与自己同一认同认知的人进行分享的不同途径。
(二)意象型人物
相对“具象”,意象则是抽象的,没有具体的人物内心描绘和性格特点。是利用对时间、空间的联想完成虚构的人物形象塑造。“意象”一词本就具备极强的中国文化内涵。从刘勰的“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神思》)开始,意象逐渐被审美范畴使用。意象中的“意”应是创作主体的情意和心灵活动的内容,但这种精神之意是寄寓在象之中的,可以说无象则意就无所凭依。对于审美活动来说,“象”还应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舞蹈作品中的意象型人物更多是体现“尚象”精神,是一种经过主体审美选择,虽未言它,但仍能给观众带来震撼、共鸣、感动和回味的作品人物。此类人物形象塑造具有典型性的便是各文工团、部队的作品了。利用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体现集体的精神风貌或讴歌主旋律的主题意义,使得在强烈的动作伸展冲击下,感受浓郁的集体意识;再例如体育舞蹈团体舞《同一心跳》,提炼了“心跳”瞬间的悸动为主体,用层出不穷的调度队形变化及诸多托举动作,完成对作品“同一”“心跳”时人群凝聚力的魅力。
五、体育舞蹈中的音乐
在舞蹈的世界里音乐的功能不容忽视。音乐由节奏与旋律组成,是一种听觉上审美感受。在体育舞蹈中,其舞种的变化即带来音乐的变化或节奏的差异,有其固有的符号性。此外,当选择带有词的乐曲时,其叙事诉说的功能再次强化。如《梁祝》,你会体会到乐曲中的情节。小提琴代表祝英台,大提琴代表梁山伯,相恋时大、小提琴合奏,愉快舒缓;离别时大小提琴二重奏,紧密结合难分难舍,这就是音乐的叙事性。
六、小结
由于东西方审美差异,体育舞蹈用作叙事是受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审美需求,也是西方舞种本土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如今不缺好舞者的时代里,技术性的比拼并不完全概括其需求,业内人士开始将该舞种向意义表达做尝试。越来越多体育舞蹈艺术作品的产出足以说明。有了目的,便会需要承载体,这个承载体便是“事”,有了“事”便有了叙事者(编者和作为叙事媒介的作品、演员)。行文至此,研究内容尚未详尽,既囊括体育舞蹈本体发展的部分概述,也是为“我们”答疑解惑,意在研究分析之中厘清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