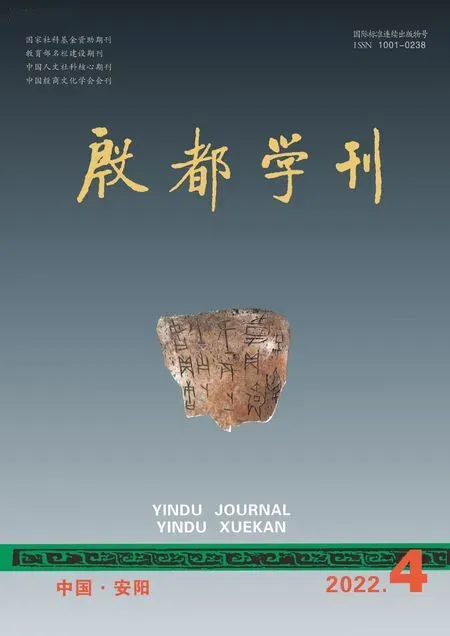辽金荐举制度
——兼论辽金贵族政治与皇权的关系
2022-02-09关树东
关树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中国历史上官员选任的荐举制度源远流长。历代王朝荐举官员的制度化程度、运作方式、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辽金政治体制具有鲜明的贵族政治特色,贵族阶层居于权力结构的顶层。辽金也是皇权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通过不断吸收中原王朝的制度文化,规范贵族的权力,强化皇权。辽金的荐举制度,兼采唐宋,并各具特点。本文侧重讨论辽金在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的历史过程中,荐举制度所体现的贵族政治与皇权的矛盾统一关系。(1)武玉环:《辽金职官管理制度研究》第二章《辽代选官制度》,指出荐举是辽代选官的途径之一,包括朝官举荐、亲属荐举、自荐、基层推荐四种方式。但论述简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页。王世莲:《论金代的考课与廉察制度》(《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总结金代廉察制度的特点,其一就是廉察与察举相结合。对金代荐举制度的研究,有孙孝伟:《金朝荐举制度初探》(《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袁成、宋卿:《金朝荐举制度探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里景林:《金代荐举制度研究》(渤海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关于辽金贵族政治,参见张帆:《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载王晖等主编《学人》第1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拙文《辽金元贵族政治体制与选官制度的特色》,载李华瑞等主编《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
一、贵族政治色彩浓厚的辽代荐举
辽代的荐举制度,受到中原王朝荐举制度和契丹世选制度的双重影响。辽代中期以来,有的世选职位如二府宰相、部落节度使被纳入铨选,人选并不限于世选之家。贵族子弟的任职范围亦远远突破了世选职位,他们可以通过入值御帐充任护卫、祗候郎君以及荫补、荐举等途径入仕,继而担任中央和地方官府的要职。辽兴宗重熙十六年(1047),“诏:世选之官,从各部耆旧择材能者用之。”(2)《辽史》卷20《兴宗本纪三》,中华书局,2016年修订本,第271页。在世选制不断被削弱的背景下,诏令重申世选传统,即由“各部耆旧”从世选之家择贤而用。世选制包含推举、荐举成分。
仅据现有材料,不见辽朝对荐举要素,如举主的身份、资格、荐举人数、频率、举主的权力与义务、举主与被举人的关系、被举人的条件、失举是否追责等,有具体的规定。也不见辽朝有官员上任或致仕时举官自代的规定。辽圣宗统和九年(991),宰相室昉请求致仕,举韩德让自代,(3)《辽史》卷79《室昉传》,第1402页。是很罕见的记载。
和历代王朝一样,荐举官员,选贤任能,是辽朝南北两面官宰辅的重要职责。辽兴宗时的北院枢密使萧孝穆说:“枢密选贤而用,何事不济?若自亲烦碎,则大事凝滞矣。”(4)《辽史》卷87《萧孝穆传》,第1466页。南面宰相杨佶,“居相位,以进贤为己任,事总大纲,责成百司。”(5)《辽史》卷89《杨佶传》,第1489页。辽道宗即位后,“诏宰相举才能之士。”(6)《辽史》卷21《道宗本纪一》,第288页。此处所谓宰相应包括南北二枢密院、北面二宰相府、南面中书省的长贰官。契丹贵族基本垄断了北枢密院长贰官、南府宰相和北府宰相的人选,南枢密院长贰官、中书省宰相则契丹贵族、汉人世族并用,辽中期以后参用进士出身的汉官。(7)参见拙文《辽圣宗时期的宰执群体》,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11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5—99页;《辽道宗时期汉族士大夫官僚群体的崛起》,《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84—197页。宰辅的用人权、荐举权,实际上起着维护契丹贵族特权的作用。出身于契丹贵族的宰辅,荐举的对象首先是契丹贵族。
辽代契丹贵族荐举亲族之风比较盛行。这突出体现了辽朝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贵族政治特点。如后族(国舅帐)萧阿古只五世孙萧柳,辽圣宗统和中,“叔父恒德临终,荐其才,诏入侍卫。”后来其伯父萧排押任东京留守时,又“奏柳为四军兵马都指挥使”。(8)《辽史》卷85《萧柳传》,第1449页。“奏”即奏举、奏荐。辽圣宗太平中,惕隐耶律弘古荐举同出皇族横帐孟父房的“刺血友”耶律马六“补宿直官”。(9)《辽史》卷95《耶律马六传》,第1528页;参见同卷《耶律弘古传》,第1527页。皇帝也会特诏契丹贵族官僚荐举族亲。辽道宗清宁初,六院部人萧图独“以事入见,帝问族人可用者”,乃荐举其弟萧兀纳,召为祗候郎君。(10)《辽史》卷88《萧兀纳传》,第1555页。
皇亲国戚、贵族官僚的荐举,对官员的仕途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结交权贵,成为官员选任、升迁的捷径。辽太宗会同九年(946),后晋官员高勋降辽,授四方馆使。此人“性通敏”,入辽后,“好结权贵,能服勤大臣,多推誉之。”这里“权贵”、“大臣”主要指契丹贵族官僚,所谓“推誉”,就是向皇帝荐举他。辽世宗任命他为南院枢密使,辽穆宗时历任上京留守、南京留守、知南院枢密使事。(11)《辽史》卷85《高勋传》,第1449—1450页。辽朝的皇太后、皇后、王妃有摄政、问政的传统,她们也往往荐举官员。如辽景宗时期,皇后之姊、故齐王妃、皇太妃萧氏录用本宫永兴宫宫分人、南京军官高嵩为宫官,保宁十年(978),她又“奏超授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辽圣宗统和中,“皇太妃以侍从以来,岁月弥远,遂具章疏,荐为表仪。八年(990),授永兴宫汉儿都部署。”(12)《高嵩墓志》,向南等:《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页。辽景宗幼女魏国公主和驸马都尉、枢密使、北府宰相萧排押(萧曷宁)之女秦晋国妃,“延纳群彦,士之寒素者赈给之,士之才俊者升荐之。故内外显僚,多出其门。”(13)《秦晋国妃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1页。《墓志》亮丽辞藻的背后,是契丹贵族荐举门人故旧任官升官的风气。契丹贵族也通过荐举官员培植个人和家族的势力。
当然,契丹贵族荐举的官员,也确实有德才兼备、政绩突出者。这符合契丹贵族和辽朝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如萧思温荐举的耶律斜轸,后来成为一代名将、名臣,官至北院枢密使,忠心辅佐辽圣宗,实现了政治稳定、边防稳固。又如辽景宗的叔叔耶律隆先,“数荐贤能之士。”(14)《辽史》卷72《耶律隆先传》,第1336页。辽兴宗时的北院枢密使萧孝穆,“所荐拔皆忠直士”。(15)《辽史》卷87《萧孝穆传》,第1466页。
辽帝出于治国理政、加强皇权的需要,鼓励中央和地方官员举荐人才。辽圣宗统和九年,“诏诸道举才行、察贪酷。”(16)《辽史》卷13《圣宗本纪四》,第153页。这或属于常程荐举令。统和年间,科举状元出身的张俭任云州幕职,经节度使荐举,进入中央任职。“故事,车驾经行,长吏当有所献。圣宗猎云中,节度使进曰:‘臣境无他产,惟幕僚张俭,一代之宝,愿以为献。'……召见,容止朴野,访及世务,占奏三十余事。由此顾遇特异,践历清华,号称明干”,终成一代名相。(17)《辽史》卷80《张俭传》,第1407页。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北府宰相刘晟(刘慎行)奏荐“殿中高可垣、中京留守推官李可举治狱明允”,诏令“超迁之”。(18)《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第188页。刘晟即刘慎行,见同卷校勘记[三二],第202页。通过荐举,一些出身平民而有真才实干者得以进入官员队伍。这有利于拓宽辽朝选官的范围,扩大统治的基础。如突吕不部人萧合卓,本部吏胥出身,“谨恪”,“明习典故,善占对”。统和中,北院枢密使韩德让“举合卓为(御史)中丞”,后累官北院枢密使。(19)《辽史》卷81《萧合卓传》,第1418—1419页。韩德让还曾荐举医术高超的宫分人耶律敌鲁为官,官至节度使。(20)《辽史》卷108《耶律敌鲁传》,第1627页。
不少有才干的官员因为没有高官举荐,只能依资序循迁,久淹常调。以汉官孟有孚为例。辽道宗春水之行道出泰州属县,闻知泰州乐康县前任知县孟有孚有佳政,于是由辰渌盐院使擢升同知泰州军州事,“未几,特旨改(长春州)韶阳军节度副使。上方急用之,当涂无有力者推挽,改知卢龙县、锦州节度副使。至磨勘、监临、解由,凡五任,上复记其能,用为大理正。”(21)《孟有孚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470—471页。有些官员出于私利,妒贤嫉能,刻意不举贤。如辽圣宗太平中,平民出身的北院枢密使萧合卓病笃,对前来探视的北府宰相萧朴说:“吾死,君必为枢密使,慎勿举胜己者。”(22)《辽史》卷81《萧合卓传》,第1418—1419页。
辽朝廉察、廉举的出现可能比较晚。辽圣宗统和中,遣参知政事邢抱朴“按察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23)《辽史》卷80《邢抱朴传》,第1409页。这是所见辽朝最早的按察地方官员的记录。圣宗太平六年(1026),“诏北南诸部廉察州县及石烈、弥里之官。不治者罢之。”凡“大小职官有贪暴残民者,立罢之,终身不禄;其不廉直,虽处重任,即代之;能清勤自持者,在卑位亦当荐拔。”(24)《辽史》卷17《圣宗本纪八》,第226页。“北南诸部”泛指北南两面官系统的政务、监察部门。辽兴宗、道宗时期见有中京路案问使、辽东路按察使。(25)《邓中举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489页;《辽史》卷89《耶律和尚传》,第1490页。史称辽朝“历世既久,选举亦严。时又分遣重臣巡视境内,察贤否而进退之。”(26)《辽史》卷105《能吏传》序,第1607页。廉察、廉举是整饬吏治、限制贵族官僚非违、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的措施。
二、皇权主导下的金代荐举
金代初期,在军事占领辽境和中原的过程中,女真军事贵族被赋以“承制除授”新附部落、州县官员的权力。这大致属于辟举。但金太宗已刻意对军帅除授官员的权力予以限制。山西都统完颜宗翰获赐一百道空名宣头,太宗诏谕:“寄尔以方面,当迁官资者,以便宜除授。”授权范围仅限“官资”,即文武官阶。完颜宗翰奏请:“先皇帝时,山西、南京诸部汉官,军帅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旧制。惟山西优以朝命。”金太宗作出让步,允准“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诏敕从事,卿等度其勤力而迁授之”。(27)《金史》卷74《完颜宗翰传》,第1801—1802页。天会十一年(1133),颁诏:“比以军旅未定,尝命帅府自择人授官,今并从朝廷选注。”(28)《金史》卷3《太宗本纪》,第71页。金朝的军事将领主要出自女真贵族,“承制除授”权的变化反映了贵族政治与皇权的博弈。
金前期“承制除授”以外的荐举,也是女真贵族特权的表现。宗室完颜宗弼任都元帅,南征收复河南,“表荐(仆散)忠义为猛安。”(29)《金史》卷87《仆散忠义传》,第2057页。宗室完颜亮任职宰相,“徼取人誉,荐大臣子以为达官。”(30)《金史》卷82《萧拱传》,第1966页。因此,金前期举人唯亲、攀附权贵的问题比较突出。当时渤海、汉人官员多依附于女真军事贵族,堪称女真贵族的政治代理人。
金熙宗颁布天眷官制,特别是金海陵王颁布正隆官制后,随着皇权和中央集权的强化,金朝官员的铨选也规范化、制度化。官员的任命主要通过朝参赴选。“金制,文武选皆吏部统之。自从九品至从七品职事官,部拟。正七品以上,呈省以听制授。凡进士则授文散官,自余皆武散官,谓之右职,又谓之右选。文资则进士为优,右职则军功为优,皆循资,有升降定式而不可越。凡铨注,必取求仕官解由,撮所陈行绩资历之要为铨头,以定其能否。”(31)《金史》卷52《选举志二》文武选,第1237页。参见卷55《百官志一》吏部,第1302—1303页。尚书省和吏部分层除授、循资历、取解由,金朝的铨选制度完全取法唐宋。
金世宗正式将荐举纳入铨选制度,使荐举成为皇权主导下选任官员的制度性安排。大定二年(1162),“诏随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各举廉能官一员。”朝廷遣员对被举荐人进行考察。大定三年定制,“若察得所举相同者,即议旌除。若声迹秽滥,所举官约量降罚。”(32)《金史》卷54《选举志四》举荐,第1287—1291页。这是对举主职品、连带责任的规定。金章宗即位后,改革选官制度,进一步完善荐举制度。如明确规定了岁举、举人自代、任内举荐僚属等义务,规范举主的资格,放宽被举人的条件,制定考察被举官员的程序。(33)详见《金史》卷54《选举志四》举荐,第1288—1291页。参见袁成、宋卿:《金朝荐举制度探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15—17页;里景林:《金代荐举制度研究》,渤海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7—37页。这显然是皇帝和中央政府规范官员荐举权、加强人事管理的措施。金朝后期推行“辟举县令法”,此处“辟举”与“辟署”不同,实际就是保举、荐举,而且并不限定由路官、州官保举管辖的县令,县令的遴选和任命权仍在尚书省和吏部。(34)参见里景林:《金代辟举县令法探赜》,《保定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43—47页。
金世宗、章宗特别倚重宰执荐举人才。金世宗对宰执们说:“荐举,大臣之职。外官五品犹得举人,宰相无所举,何也?”(35)《金史》卷88《唐括安礼传》,第2087页。这里所说的“大臣”就是指宰臣、宰执。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荐举人材,常若不及”,“荐举往往得人”,受到金世宗的嘉奖。(36)《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第2077—2078页。金章宗曾诏令宰执“举奏中外可为刺史者”,并亲自“阅阙点注,盖取两员同举者升用之”。(37)《金史》卷107《高汝砺传》,第2489页。论者以为宰执操纵荐举权和选拔官员的权力,极大地妨碍了其他官员对荐举的积极性,(38)里景林:《金代荐举制度研究》,第43—44页。不无道理。金世宗、章宗时期宰执的任用,女真贵族仍占优势比例,体现了皇权和贵族政治利益的一致性。但这个时期皇权能够比较有效地制约贵族的权力,保证贵族特权不会损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况且当时出身于女真官学、女真进士科的女真宰执以及进士出身的汉族宰执不少,他们多数来自普通官僚和平民家庭,是维护皇权的力量。(39)参见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第十四章《世宗、章宗时期任用宰执的政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4—291页。
更重要的是,金朝效法唐宋的铨选制度,有一套程序繁琐、循资格升迁的制度设计,即便女真人有超迁格,但仍然受章法制约。无论是制度设计的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效果,金世宗、章宗确立的荐举制度本质上是服务皇权而非贵族政治。比如,金代铨选制度规定循资序晋升职务职级,由于资考的限制,致使州县官员严重阙员,所以金世宗、章宗多次下令荐举、廉举可任刺史、县令的官员,破格提拔使用。(40)《金史》卷54《选举志四》廉察,第1284页、1285页、1288页。
如果说金代中后期的荐举制存在种种弊端,难以收到广揽人才的功效,(41)金代荐举制度的弊端及影响荐举制运行效果的原因,参见里景林:《金代荐举制度研究》,第38—44页,50—55页。那么荐举的特殊形式,基于廉察制度的察举、廉举,在金代形成了有效的运作机制,对整饬吏治,维护皇权、制约贵族特权,还是颇具积极意义的。
察举(廉举)建立在廉察制度的基础上。金朝的廉察,始见于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九月,遣行台尚书左丞耨盌温敦思忠等赴“诸路廉问”。次年四月奏报,“得廉吏杜遵晦以下百二十四人,各进一阶;贪吏张轸以下二十一人,皆罢之。”(42)《金史》卷4《熙宗本纪》,第83页。参见卷84《耨盌温敦思忠传》,第2001—2002页。《本纪》作温都思忠。皇统八年(1148)四月,金熙宗“遣参知政事秉德等廉察官吏。”(43)《金史》卷4《熙宗本纪》,第92页。完颜秉德罢免了中京留守裴满忽睹、太原尹徒单恭等“污滥至甚”的官员;雄州永定军节度使完颜宗贤以“廉能”超迁。(44)《金史》卷120《裴满忽睹传》,第2757页,参见同卷《徒单恭传》,第2758页;卷66《完颜宗贤传》,第1666页。这是廉察、廉举的肇始阶段。
金海陵王篡立之初,曾遣使廉问;正隆二年,“有廉罢官复与差除之令”。(45)《金史》卷73《完颜阿邻传》,第1786页;卷54《选举志四》廉察,第1284页。他在位时期有关廉察的记载不多,或与他热衷大兴土木、穷兵黩武有关。金世宗重视廉察制度建设。大定二年,世宗采纳了尚书左丞翟永固“请依旧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污”的建议。(46)《金史》卷89《翟永固传》,第2098页。三年,遣户部侍郎魏子平、户部郎中曹望之、监察御史夹谷阿里补等“分道劝农,廉问职官臧否”。(47)《金史》卷92《曹望之传》,第2160—2161页。同年,颁布了廉察州县、猛安谋克所得廉能官、贪赃官的奖惩令。大定四年,颁敕擢升、黜降河北、山东等路廉察出的清廉、贪赃官员,并宣谕天下。(48)《金史》卷54《选举志四》廉察,第1284页;卷88《移剌道传》,第2090页。
察举是一种特殊的荐举制度。金世宗时期,吏治相对清廉,廉察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史称“自熙宗时,遣使廉问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49)《金史》卷73《完颜宗雄传》附《完颜蒲带传》,第1786页。廉问是不定期的。廉察使由皇帝派遣。廉察的对象是地方官员及势要,公开巡视与微服私访相结合。廉问使既要弹劾违法乱纪及不称职者,也要奏报朝廷嘉奖升迁勤政廉洁的官员,朝廷另派官员复查核实。廉察、廉举收到一定的成效。不少骄横跋扈的女真贵族官员被罢免,政绩突出的官员得到升迁重用。金朝后期的御史中丞李英认为考课法徒为虚文,主张恢复大定年间“当时号为得人”的“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之制。(50)《金史》卷101《李英传》,第2370页。
三、辽金荐举制度的消极影响
辽代的世选制、荐举制,存在裙带之风和结党营私之风是不可避免的,并对皇权和中央集权构成威胁。辽圣宗时,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荐举国舅帐萧敌烈,称“其材可为枢密使”。当时,辽圣宗拟擢拔萧合卓为北院枢密使,王继忠进言:“合卓虽有刀笔才,暗于大体;萧敌烈才行兼备,可任。”但“帝疑其党”,“不纳,竟用合卓。”(51)《辽史》卷88《萧敌烈传》,第1474页;卷81《王继忠传》,第1417页。萧合卓出身突吕不部平民,部吏出身,“时议以为无完行,不可大用。”(52)《辽史》卷81《萧合卓传》,第1418—1419页。辽圣宗疑忌朝臣与国舅帐萧敌烈结党,排挤萧合卓。这说明官员荐举中的党同伐异并非空穴来风。辽道宗清宁间,同知北院枢密使事、国舅帐萧胡睹与族弟北剋萧敌烈、国舅详稳萧胡笃“倾心交结”,萧胡睹“奏胡笃及敌烈可用,帝以敌烈为旗鼓拽剌详稳,胡笃为宿直官”。(53)《辽史》卷114《萧胡睹传》,第1664页。皇太叔耶律重元权势显赫,图谋篡位,萧胡睹是叛党的重要成员。北院枢密使萧图古辞,“为枢密数月,所荐引多为重元党与”。(54)《辽史》卷111《萧图古辞传》,第1645页。这是契丹贵族利用荐举特权树立党羽,结党营私,挑战皇权的典型案例。
金代的荐举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私门请托、结党营私现象。金世宗时期,同知西京留守曹望之认为“荐举之法虚文无实。宰相拔擢及其所识,不及其所不识。内外官所举亦辄不用,或指以为朋党,遂不敢复举。”(55)《金史》卷92《曹望之传》,第2160—2161页。金世宗也承认“今用人之法甚弊,其有不求闻达者,入仕虽久,不离小官,至三四十年不离七品者。而新进者结朝贵,致显达。”(56)《金史》卷54《选举志四》部选,第1276页。金代的廉察制度,实际运行中也存在各种弊端。如“廉问使者,颇以爱憎立殿最”。(57)《金史》卷73《完颜宗雄传》附《完颜蒲带传》,第1786页。又多弄虚作假。如单州刺史石抹靳家奴,“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使作虚誉,用是得迁同知太原尹。”(58)《金史》卷91《石抹荣传》,第2152页。
四、结论
辽金的皇权专制与贵族政治既相互依存,又有矛盾冲突。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必然与贵族政治形成博弈。辽金荐举制度的运行与影响,既体现了皇权与贵族政治的对立统一关系,也见证了辽金政治、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辽朝的皇权专制中央集权程度比金朝低,金朝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辽朝更彻底。辽朝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北面官掌控军政大权和部落事务,其主要官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契丹贵族,更多地保留了契丹传统的政治文化。辽朝的铨选制度不够健全,荐举也比较随意,缺乏制度性规范,带有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金朝的荐举制度则带有更多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色彩,制度比较规范,是严密的铨选制度的组成部分,主要为朝廷延揽人才服务,虽然有各种弊端,但确实较少受制于贵族政治。
辽金荐举制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消极影响严重。辽代契丹贵族利用荐举培植个人和宗族的势力,严重威胁皇权。金代铨选循资格、荐举请托营私,致使官员奔竞苟且之风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