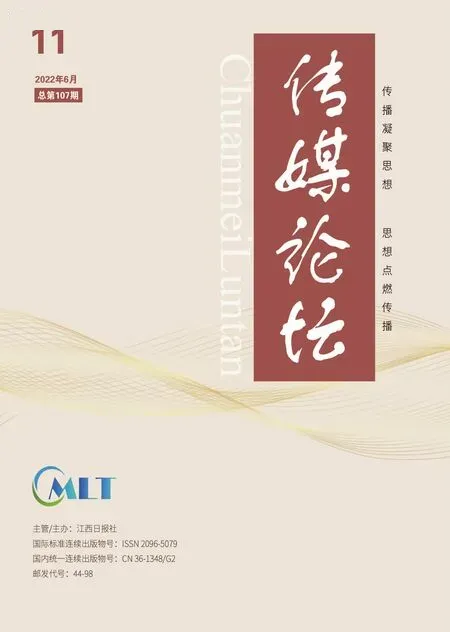中国古典诗词在英语世界传播的障碍及因应之道
——以唐诗误译为例
2022-02-09薛嘉欣
薛嘉欣
诗歌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式,贯穿中国文学发展始终,从未断绝。诗歌承载着中国人骨血里最原始的情感与渴望,见证着中华民族悠悠数千载的兴衰沉浮。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唐诗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的艺术巅峰,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因此,要将中国文学引入世界文学之林,唐诗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那么阻碍中国古典诗词在英语世界中传播的障碍有哪些呢?中国学者应该如何扫清这些障碍呢?笔者认为,世界文学评价体系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译介过程中的文化误读现象和接受过程中的受众范围狭窄这三个问题亟待解决。
一、世界文学的定义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最早由歌德提出。十八世纪的德国在政治上封建割据,城邦林立,各自为王。政治上的分裂带来各邦文化上的隔阂。欧洲市场初现雏形。正是在德国文化割据与欧洲世界市场形成的背景下,歌德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歌德说:“民族文学现在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因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1]对歌德而言,世界文学是应对德国民族文学缺失的手段。这并不是说,世界文学可以完全取代民族文学。事实上,歌德强烈反对跨国文化交流导致的同质性。在倡导世界文学的同时,歌德强调必须保留独特的民族特质。朱光潜先生认为:“歌德对于世界文学的主张是辩证的:他一方面欢迎世界文学的到来,另一方面又强调各民族文学必须保存它的特点。懂得这种辩证观点,我们就可以理解歌德在这一问题上一些貌似自相矛盾的言论。”[2]韦勒克将歌德对世界文学的定义解读为“所有国家的文学能够融合在世界文学中,同时又保有自身特色。正如各音部音色不同,却能合奏出一曲和谐优美的交响乐”。[3]换言之,在保有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世界各国文学平等交流,友好对话。
在二十世纪全球化的语境下,大卫·达谟罗什为世界文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他将世界文学定义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在翻译中获益的写作”和“一种阅读方式”[4]。他主张世界文学不应停留在各国文学作品的简单汇总,更是一种传播、翻译和生产的方式。与歌德不谋而合的是,达姆罗施也认为世界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交流。
二、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在殖民主义,甚至是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欧洲中心主义深深植根于世界文学评价体系。在此思维模式下,世界文学成为西方文学的代名词,默认非西方文学本质上或先天性劣于西方文学。
为了更好地理解欧洲中心主义的态度,我们需要回溯东方和西方的划分方式。在《东方学》中,赛义德揭开了东方学家如何利用话语霸权,构建东方这一他者意象。他者,是自我的对立面,与自我相互映照。东方学家建构的东方意象与实际上的东方相距甚远,其存在的唯一价值只在于巩固西方的中心地位。在西方的表现形式中,东方人被简化为抽象的刻板印象。根据这些刻板印象,东方人是色情的、神秘的和危险的。为了消解对神秘和未知东方的恐惧,西方殖民者将东方同化到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中。
世界文学延续了萨义德所言的政治划分。世界文学也大致分为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西方的评论家们对东方文学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例如,阿拉伯文学被认为是当地政治的记录簿。对于西方人来说,阿拉伯只是一个常年政治动荡的混乱地区。西方人很难相信这片土地上会诞生出举世瞩目的文学作品。
人类学家弗朗茨·鲍尔斯(Franz Boas)认为,不存在对各种文化的绝对评价,因为每种文化本身都是独特而珍贵的。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因此只能在该文化的体系框架内进行评判。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比较,区分高低优劣是不合理的。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鲍尔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可比较性。他认为:“中非黑人、澳大利亚人、爱斯基摩人和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与我们自己的社会理想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他们对同一人类行为的评价体系不具有可比性。一个人认为好的东西,另一个人可能认为是不好的。”[5]鲍尔斯的学生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z)也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文化差异的包容度。他将文化相对主义定义为“人们应该采取的关于世界事实以及我们与这些事实的关系的态度”[6]。与鲍尔斯一样,赫斯科维茨也抵制“任何相对主义思想的哲学普遍化,以支持国内外的不公正”[6]。师徒二人均不认为存在某种评估不同文化的普世标准。
这一原理也可以应用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在后殖民时代,先前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消退。因此,与此相对应的世界文学评价体系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定式不再具备合法性。在后现代语境中,世界不再是由东西方组成的。相反,这是一个否定中心性、整体性和绝对真理的世界。在评估世界文学的过程中,用东方主义简单粗暴地取代欧洲中心主义,其一元中心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正如萨义德所言,“旧的权威推翻后,不能简单地用另一个新的权威取而代之。一种跨越国界、类型、国家和本质的新型同盟正在迅速进入视野”[7]。如果我们用东方中心主义取代欧洲中心主义,二元划分仍然存在,随之而来的不平等和歧视根本无法消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文学之间仍然不可能实现异质性和多样性。推翻二元划分的评价体系之后,各国人民强烈呼吁一种多元主体、平等交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型世界文学评价体系。
三、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和异化翻译策略
乐黛云先生在《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中,解释了“误读”一词的涵义。“所谓‘误读’是指人们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人在理解他种文化时,首先自然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对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产生了难以避免的文化之间的误读。”[8]人们基于以往的经验和思维模式产生对外国文化的误解,由此导致文化误读现象的出现。不论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人们易于忽略不同文化之间在思维模式上的差异。因此,文化误读成为跨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译者是典型的跨文化沟通者。文化误读是翻译中的常见现象。龙云教授认为:“误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无意识误读和有意识误读,误读产生的具体类型表现在文体、语言、意象、伦理道德标准和译者动机等方面。”[9]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每一种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语境,同一意象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如果迁移到另一种文化语境,诗歌中的一些意象甚至会完全失效。由于本文篇幅有限,下文将以禽鸟意象与庞德的《华夏集》,具体阐释诗歌译介中意象的文化误读。
(一)禽鸟意象的文化误读
鸟的意象在中英文化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英语诗歌中,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中,“传统意义上,鸟儿的意象体现了诗人对艺术的理想化”[10]。此外,鸟类意象还可以代表人类灵魂、爱情、大自然和自然而然流露的创造力。夜莺颂通常以欢乐、希望和充满活力的基调结束。中国诗歌中鸟的意象除了抒发个人情感,还寄寓了诗人对政治局势的判断和对国家前途的期待,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之处。所以,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在读这类中国禽鸟诗时,可能感到晦涩难解,因为他们很难理解禽鸟如何与国家命运产生联系。
中国禽鸟诗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两汉时期和唐宋时期。禽鸟的意象最初出现在《诗经》中,鸟的意象常用以表达爱情、思念或惜别之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11]这是传唱数千年,咏唱爱情的佳句。这首诗以鸟儿的叫声起兴,引发爱慕之思。在《楚辞》中,禽鸟也是君子或谗佞小人的化身。例如,在《九章·涉江》一诗中,有“乱曰:鸾鸟凤凰,日已远兮。燕雀乌雀,巢堂坛兮。”[12]在这几句诗中,鸾鸟和凤凰等血统高贵的善鸟被排挤在外,燕子和麻雀等品格低下的恶鸟却占据了朝堂。屈原意在借禽鸟讽喻当时黑暗不公的政治环境,反映了诗人对奸臣当道的愤懑不平,以及政治抱负难以施展的苦闷忧郁。
如果说先秦时期的禽鸟意象主要出现在民间文学中,那么汉、魏、晋时期的禽鸟诗通常由知识分子创作,禽鸟意象也逐渐成熟定型。在《赠白马王彪》一诗中,曹植使用归鸟的意象表达了被迫远行、骨肉分离的感伤。“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13]夕阳西下,鸟儿奋力振翅,成群结队飞回林中巢穴。一头离群的野兽匆忙寻找兽群,连停下咀嚼草根的时间都没有。这首诗是在曹操刚逝世时写的。新帝曹丕登基,迫害手足,曹植被迫与弟弟曹彪分居。因此,曹植把自己比作孤鸟与离群的孤兽。此时的曹植失去了父亲的庇护与弟弟的陪伴,情绪低落,心情复杂。
唐宋时期,禽鸟诗走向成熟。禽鸟意象超越了个人情感和宫廷生活,与更加宏大的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杜甫在《春望》 中借禽鸟抒发山河破碎、家国失守的痛苦之情。“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14]爱国情怀和鸟类之间的联系在英语诗歌中并不常见,所以英语母语人士可能会感到困惑,无法理解二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在读这首诗时,一个非中文母语者可能会问:“究竟为什么鸟儿的叫声会惊动诗人的心?”[15]如果读者了解中国诗人的政治追求,就不难理解他们缘何在禽鸟和国家之间建立起联系。英语诗人大多是受贵族资助的职业作家,很少直接参与政治。中国的读书人也称士大夫,主要身份是政治家,因此他们心怀天下,借诗谴怀。字面直译禽鸟意象并不能传达意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二)庞德《华夏集》中意象的文化误读
由于缺少文化背景知识和语言障碍,庞德对唐诗意象的误译比比皆是。接下来,笔者将以《华夏集》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庞德对唐诗意象的文化误读。
在《江上吟》中,庞德将“兴酣落笔摇五岳”翻译为:“But I drew pen on this barge causing the five peaks to tremble.”[16]庞德对五岳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抹去了五岳的文化内涵。首先,五岳包括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和嵩山,是古代帝王与神通灵的媒介,象征天子受命于天。中国古代的帝王均在泰山封禅,祭天仪式成为君权合法性的佐证。因此,五岳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政治权力的表征物。其次,五岳也是道教的圣地之一。古希腊天神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中国的仙人则住在三山五岳(三山指蓬莱、方丈、瀛洲)。如果读者不了解这些背景知识,根本无法理解诗人摇笔赋诗时藐视世俗、不畏权贵的狂放不羁。庞德也将“诗成笑傲凌沧州”译为:“And I have joy in these words/ like the joy of blue islands.”[16]在中文语境中,沧州指隐士的居所。但庞德将其翻译为蓝色岛屿,无法传达李白逃离政坛、隐居避世的愿望。许渊冲的译本更好地展现了李白在世俗社会之外无忧无虑的生活。许渊冲将这句诗翻译为: “Hearing my laughter proud, the seaside hermits wake.”[17]许译本化地名为人物,点明隐士身份,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人避世的意图。同样地,庞德将“五云垂晖耀紫清”翻译为: “five clouds hang aloft, bright on the purple sky.”[16]在中国文化中,五峰是和平的标志,在此处象征帝王居所。庞德忽略了该词的文化内涵。此外,庞德将“天回玉辇绕花行”翻译为:“The emperor in his jewelled car goes out to inspect his flower.”[16]辇是指古代宫廷的出行工具。庞德将辇翻译为“car”,易于让读者联想到冷冰冰的现代机器与尘土飞扬的都市生活,很难展现此物的古雅之美以及闲适慵懒的宫廷生活。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庞德将“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译为:“And got no promotion, and went back to the East Mountains.”[16]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东山是隐士的住所。晋代著名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谢安抛弃政治地位,以隐士的身份隐居在东山。在国家危难之际,谢晋重回宫廷,肩负起救国的重任。庞德的直译处理丢失了此意象的文化内涵,难以将李白隐居避世的愿望传达给读者。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庞德将“晋祠流水如碧玉”译为:“To the dynastic temple, with water about it clear as blue jade.”[16]此处,庞德将“晋祠”译为“dynastic temple”(朝庙)。庙宇通常是宗教祭祀的场所,但晋祠并无宗教色彩,而是与祖先崇拜有关。因此,庞德的译本会让读者产生误解。
在《长干行》中,庞德将“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译为:“Forever and forever, and forever./ 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 out?”[16]在英译本中,庞德漏译了抱柱信的典故,仅对望夫台进行了字面直译。抱柱信象征至死不渝、忠诚守信的爱情。相传尾生与爱人相约在桥下见面,但是到了约定的时间爱人未至。即使天降大雨,尾生也坚定地等待,最后抱着约定见面的梁柱而死。望夫台则是指妻子送别远去的征夫,思念过度以致化成人形立石。庞德的处理磨灭了原诗蕴含的爱人间至死不渝的爱情。在本诗中,庞德将“猿声天上哀”译为“The monkeys make sorrowful noise overhead.”[16]然而原文中的猿与庞德译本中的“monkey”完全不是同一物种。 猿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往往是悲伤的意象,能够唤起听众内心最深处的哀愁。而猴子仅是滑稽逗笑的玩物。猿的意象最早见于先秦诗歌。屈原可能是第一位将此意象引入中国诗歌的人。他在《山鬼》中吟诵道:“靁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12]雷声轰鸣,大雨倾盆,愁猿夜啼,狂风呼啸,草木摇落。此情此景如何不让人心神俱哀。刘义庆在《世说新语》“黜免第二十八”的故事中,同样使用了长臂猿的意象。“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19]许渊冲将“猿声天上哀”一句译为“Where gibbons’ wails seemed coming from the sky”似乎更为恰当[17]。长臂猿(gibbon)是一种亚洲树居猿类。从生物学角度讲,这是一个比猴子更准确的选择。因为欧美读者对于亚洲猿猴比较陌生,所以也可以借此创造出一种审美距离。
由于庞德不通中文,只能依赖日语译文理解唐诗,因此他在英译本中经常将中国地名、朝代或人名张冠李戴。第一,是地名的误译。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庞德根据日语发音将“吴宫”翻译为“the dynastic house of the Go”[16]。在《送元二使安西》中,庞德将“阳关”译为“gates of Go”[16]。为什么庞德将“吴”和“阳”都翻译为“Go”呢?《华夏集》的修订者蒂莫西·比林斯(Timothy Billings)在注释中解释道,庞德拥有的日文译本为日本学者费诺罗萨(Fenollosa)的手稿。因为费诺罗萨倾向于使用花体字母“Y”,所以庞德可能会把“Yo”误认为“Go”,由此产生误译。如果庞德对汉语有一点了解,就不会犯这么肤浅的错误。第二,是朝代的误译。在《送友人入蜀》中,庞德将“秦”翻译为“Shin”[16]。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庞德将“晋”也译为“Shin”[16]。秦朝和晋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朝代,但庞德采用了相同的译法,同样是受到日语发音的干扰。第三,是人名的误译。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庞德将“故人西辞黄鹤楼”译为:“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16]此处,庞德将故人译为日语发音“Ko-Jin”难免令英美读者产生误解。故人在中文指旧友或熟人,显然不是一个需要音译的专有名词。可能因为庞德不懂中文,不明白“古人”的意思,因此直接借用了日语的发音。同样,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庞德将“紫阳之真人”译为:“And there came also the ‘True man’of Shi-yo to meet me.”[16]在此,庞德将“紫阳”误译为地名“Shi-yo”。实际上,紫阳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人。他是唐代的道士,也是李白的好朋友。以上种种文化误读源于庞德对源文化缺乏了解。
最后,庞德在英译本中也未能清楚区分颜色的差别。他一直将青译为“blue”(蓝)。例如,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庞德将“晋祠流水如碧玉”中的“碧玉”译为“blue jade”[16]。在《送友人》一诗中,庞德同样将“青山横北郭”中的“青山”译为“Blue mountains”[16]。蒂莫西·比林斯也注意到庞德在翻译颜色时的混淆现象。他评论道:“几十年后,当庞德在学过一些中文后回顾手稿,他仍然无法确定‘青’这个汉字的确切含义。在费诺罗萨手写的魏武帝《短歌行》手稿边缘,庞德写下:‘青/?/green/blue’”[16]。
那么,译者如何避免文化误读,填补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呢?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读者的期望,还是应该为源文化代言?在我看来,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者应该采用异化翻译,坚持原文中意象的选择。异化翻译有助于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开阔读者的期望视野,为世界文学的异质性作出贡献。
四、受众狭窄与诗乐结合
虽然唐诗已收录至诺顿世界文学选集,也已被引入美国大学的文学课程,但相对于英语和其他欧洲国家语言来说,中国诗歌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唐诗的读者仍然局限于专业学者和语言学习者。那么该如何增加唐诗的海外读者数量,扩大读者覆盖面呢?
近代学者认为,缺乏音乐基础是诗歌流行度不高的原因。诗歌的传统载体是纸质书籍。但在某些情况下,书籍可能不便于携带,且只能用眼睛去看。此外,书籍的受众只局限于受过教育的人。这一载体本身给人一种学院派和精英主义的感觉。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诗歌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较小,是“诗与乐分之所致也”[20]。他甚至根据能否可以入乐评价诗歌优劣。他认为:“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在吾国古代有然,在泰西诸国亦靡不然。”[20]1934年,穆木天在《歌词的创作》中也提出“诗歌是应当同音乐结合一起,而成为民众歌唱的东西”[21]。1934年,鲁迅在给窦寅夫的信中也说:“歌有二:一是看;二是听。另一个是被唱的。后一个更好。令人失望的是,中国现代诗歌属于前者。”[22]龙云生也认为音乐有助于诗歌“通下情而消戾气”[23]。
虽然能否入乐并不一定是衡量诗歌好坏的标准,但诗乐结合确实能够扩大受众。无论是名门望族,还是劳动人民,都能欣赏音乐。以唐诗为例,唐诗往往通过歌唱和器乐表演流传。音乐连接创作者和受众,在诗歌流通和接受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唐代,将诗歌改编为歌词传唱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唐朝的诗人也非常重视这种流传方式。诺贝尔奖获得者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歌也是诗乐结合的典范,取得极大成功。2016年,鲍勃·迪伦因“在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意的表达”获得诺贝尔奖[24]。毋庸置疑,诗歌与民谣的结合成就了鲍勃·迪伦在美国文学和音乐史中的传奇地位,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中国诗歌中诗乐结合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诗经,此后一直延续到元曲。《尚书》记载:“诗言志,歌永言”[25]。然而,这一伟大的传统在当代文学中已经销声匿迹了。当我们翻开《古今乐录》时,书中的许多诗歌会在结尾处标注“今不传”或“今不唱”[26]。除了中国诗歌的音乐传统之外,自荷马以来的英语诗歌也与音乐相伴而行,当代非裔美国年轻人群体中流行的表演艺术也将有韵律的歌词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由于中英诗歌中共同的音乐传统,采用诗乐结合的艺术形式推广唐诗更容易为英语母语者欣赏与接受。
虽然大部分中国古代诗歌的乐谱已经失传,但当代的中国音乐家已经大胆尝试重新音乐化古典诗歌。在中央电视台上演的《山居秋暝》就是一次诗乐结合的成功尝试。在这次演出中,王维写的诗句伴随着霍尊的歌声、舞者的舞蹈和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娓娓道来。跨媒介的艺术形式忠实再现了王维诗歌中描绘的宁静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此次演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使古老的诗歌韵味在音乐的帮助下重新焕发生机。 《诗意幻想曲三首》也是诗乐结合的一个范例。长笛代表高悬的朦胧月影;中提琴代表醉酒摇晃的诗人;竖琴代表诗人的影子。虽然这首曲子没有采用李白的《月下独酌》作词,但是作曲家巧妙地运用长笛、中提琴和竖琴三种乐器再现了诗人月下伴影独自饮酒的如梦如幻的意境。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为改变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文学框架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中国学者需警惕世界文学评价体系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定式,运用异化翻译策灵活应对外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误读,采用诗乐结合扩大中国古典诗歌的海外受众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