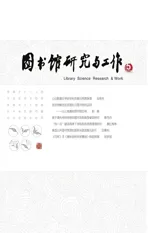方苞集外诗文六篇考释*
2022-02-08任雪山
任雪山
(合肥学院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方苞(1668—1749年)为桐城派三祖,清代著名文学家,理学名臣,其学精于《三礼》《春秋》。由于各种原因,方苞不少文章没有收入其诗文全集,殊为遗憾。笔者近来查阅清代文献资料,发现方苞佚文六篇,为刘季高校点的《方苞集》、徐天祥和陈蕾点校的《方望溪遗集》、彭林和严佐之新编的《方苞全集》所未收,也与学界新发现的佚文不同①。内容涉及曾巩、方以智、尹会一、姜橚等人,对了解方苞、桐城派以及清代文学发展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现叙录如下,并加以考释,以备研究之用。
1 隐玉斋
前贤读书地,古迹久湮埋。空过中禅寺,谁知隐玉斋?
径荒碑复没,地胜境仍佳。经眼重新日,游观澹客怀。
这首五言律诗见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杨受廷修、马汝舟纂的《如皋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志二》,题名“隐玉斋”。 隐玉斋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019—1083年)的读书旧地。宋明道元年(1032年),曾巩之父曾易占出任泰州如皋知县,14岁的曾巩随父至如皋,在中禅寺寄读。多年之后,曾易占幼子曾肇知泰州,来到如皋中禅寺,触景生情,题字“隐玉斋”,寄托对亡故父兄的深情。方苞何时到中禅寺,已无从知晓。但曾肇对父兄的感情,以及曾巩古文,一定都曾在方苞心中掀起波澜,不能看出,方苞对唐宋八大家之曾巩的推崇。
该诗的另一层意涵或与明遗民有关。隐玉斋并非一处独立所在,而是位于如皋水绘园内。水绘园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为如皋冒氏别业,后经冒襄修整完善。冒襄(1611—1693年),字辟疆,号巢民,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入清不仕,长期隐居故园,同遗民诗酒唱和。方苞之父方仲舒,一生不仕清廷,亦与遗民常相往还,方苞耳濡目染,“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1]174,因此在《方苞集》中,提到冒襄时多有推崇之意,在《释兰谷传》中更言及冒襄结社之事。此外,与方苞家族三代关系密切的遗民杜濬,与冒襄颇有往来,并有多首诗描写水绘园。因此,方苞途径此地,其心中的“前贤”与“胜境”,应该不止是遥远的曾巩,还有眼前的冒襄,以及江南遗民往事。
2 方以智小传
先叔祖文忠公,讳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前明祟祯庚辰进士。弱冠负盛名,与云间陈子龙投分最久,复社诸公皆以声气名节相推尚。释褐时,贞述公抚楚,忤时相,被逮下狱,具疏请代。上称其孝,冤明白。甲申南奔,仇憝柄国,遂流离岭表,出世外。尝被絷,环以白刃,终不屈。晚乃遁迹匡庐、青原间,从游士称无可大师,更号药地。叠逢患难,谈笑自如。卒于万安,归葬浮渡。所著有《通雅》、《炮庄》、《物理小识》、《鼎薪》、《浮山》诗文集数十种行世。谥文忠。江子长先生尝称为“四真子”云,盖谓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也。此幅乃为摄山中峰张白云先生作也,笔墨高古绝伦,藏之名山,得垂不朽,亦幸矣哉。康熙壬午秋日,族孙苞谨识。
方以智(1611—1671年),字密之,桐城人,“明季四公子”之一,明遗民的标志人物。此文为方苞给方以智《无可和尚截断红尘圆轴》的画外题跋。画作见于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至乐楼藏明遗民书画》中。此文创作时间为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方苞时年34岁。方苞与方以智同属于桐城桂林方氏,而且崇祯七年(1634年)桐城民变之后,方以智与方苞曾祖方象乾等迁往南京,两家时有往来。
表面上看,此文只是题跋,实则为一篇完整的方以智小传,叙述了方以智传奇的一生,表达了方苞对方以智声名气节的推崇,有着极重要的学术价值。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中曾提及方苞此文,他主要是以方苞与方以智家族的亲近关系来辅助论证“方以智病死说”之不可信[2]。任道斌在《方以智年谱》也提及此篇题跋,他认为方苞“年青时颇具反清思想”[3]。饶宗颐素重方以智,在撰文讨论遗民画时,专门考证此跋语:“白云即张怡,字瑶星,张大风即其仲也。怡与程端伯书尝言及《白云砦图》事迹。望溪集卷八有《白云先生传》。”[4]三位先生在论及方苞题跋时,皆关涉明遗民问题,由此观之,此文不仅揭示方苞与方以智的关系,也表现了方苞对明遗民的文化认同,对于评价方苞的出处态度及其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皆有启示意义。
3 琅屿姜公传
公讳宗吕,太原保德人,赠特进荣录大夫,右都督讳名武之子也。都督以武功显于边疆,而使公治文术。颖悟绝人,受书一见,辄了大意。沉毅有干略,自都督及旅属、乡人、宾客,见者皆谓于世将有大造也。方是时,贼势益张,内外以文法相遁,而武臣拥劲兵者,多放骜持两端。都督平居慨慷,誓致死礼以报国。公常泣谏,以谓一人致死不足以支国势之倾坏,而诸季方稚弱,世乱将何依。都督曰:“吾自计已审,且汝在,吾何忧。”崇祯十五年春,保定总督杨公文岳,部诸将会援开封。朝命尚书侯恂驻河上,以致左良玉诸镇兵皆壁朱仙镇。良玉夜半放兵大噪,诸营皆溃。都督血战力尽以死。时公年二十有二,闻变,独身前求父尸。既至,无息耗,遂诣阙上书请恤。或自贼中来言,都督被执,骂贼不屈,至柳树坡脔磔以死,公闻复往。先是贼决河水灌开封,城尽没,白骨被野,聚落无鸡鸣,而公往返数四无所怖。公干躯伟杰,膂力过人,善骑射,督帅杨公奇焉,欲疏请以公续父职,公以母老弟弱力辞不就。于杨公所得都督故衣,招魂以还。而前上书所得恤典,不应法,复诣阙上书以讼,未得命,闻贼警遽,归视母弟,甫至家,而太原等郡邑已陷矣。逾月国变。公家居,诵书史,课群季。戊子举于乡,而其冬姜襄反大同,州守备牛化麟杀守,据城以应之,与官兵相持逾年。而公在危城中,贼以公为州人之望,屡为卑礼甘辞以致公,公不为动。久之贼怒,一日坐泽宫,陈剑铍阶除下,迫公与孝廉陈大谟、诸生王宗本、张射斗。至盛怒,将加害。公前诘之,气扬扬如平常。贼忽阻丧,手足动摇,口嗫嚅不能出声,久之曰:“无他事,军无粮,欲与诸君共计之耳。”公遽率众以退。越日,贼独召张,杀之。贼校有妖言以媚贼者曰:“吾梦神人告我,城中有三直臣,得之大事可济。”贼曰:“必某也。”因就公强受职。公曰:“神有命,宜卜于神。”使贼遍书邑中士人名数十,告于神,而筮取之,所得乃庸妄。贼遂止。及兵渡河,城破论罪,凡受伪职及乡兵从吏令者,皆坐诛。而公与陈、王诸族,独得免。陈、王每语人曰:“方陷贼中,吾曹实不知所为?恃姜君多智略,与为向背,今得全宗党,皆姜君力也。”或问:“何恃不恐?”公曰:“吾料避就皆死,义不可昧,而贼无定情,悦以赂遗,御以术数,或可于死中得生,故也。”由是,征西大帅无不啧啧奇公才,州人与守丞皆重焉。每编审及州郡有大事,必咨于公。公开陈,悉得其条理。以己亥成进士,丙午当选期,丁母忧。己酉授潍县令,未之官竟卒。公爱诸弟,同居食,食口数十人。辛卯岁大寝,戚属贫无依者,皆待公举火。先业荡尽,是后常客游,或贷于州人以治饔。及公之殁,遗负数千金,而家居与诸弟未尝有一食之离也。公未举进士时,就教石楼邑子弟,经公指画,文章皆有法度。诸弟及子未尝有师承公之学,皆以文艺知名于时。公为文淳古朴厚,得汉人气体。其请都督恤典前后二疏,皆卓然可传久远。有《癢癢斋文集》十卷藏于家。
赞曰:百年之木,必于牺尊。天能生材而不能用之使不枉,岂非理之不可诘者欤!观公之蒙难艰贞,履虎尾而不咥,以当天下国家之变,其功谋可胜道哉。然竟不得效于一官以死,惜也。古人有言,颜子终日不违如愚人,未尝施于事,多见于言辞,而自古以为不可及。然则公之逾远而存者,何必以功名显哉!
此文见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王克昌修、殷梦高纂的《保德州志》卷十《艺文上》。文中所言“琅屿姜公”,即姜宗吕,字琅玙,山西保德人,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年)进士,康熙八年己酉(1669年)授潍县知县,未赴任卒于家。其父姜名武,字我扬,天启二年(1622年)科举武举人,授大同威远守备,累迁通州副总兵。崇祯十五年(1642年),随杨文岳援开封,与李自成军激战,不屈而死,赠特进荣禄大夫、右都督。姜名武有四子:宗吕、祚吕、师吕、述吕,宗吕为其长。姜宗吕有子栩、橚、榡,姜橚为方苞乡试座师,此传应受姜橚所请而作。
此文创作时间,并不言明。按,方苞与姜橚结识的时间,据《吏部侍郎姜公墓表》记载:“余始见公于督学宛平高公使院”[1]341,而高裔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督学江南,可知二人结识应当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之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姜橚为江南乡试副考官,方苞中举为解元,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姜橚去世。因此,此文最有可能在康熙三十八年与四十三年之间(1699—1704年)。又按,姜橚当年亦请万斯同(1638—1702年)、王源(1648―1710年)为其祖姜名武作传,万斯同、王源皆为方苞好友,或许他们在大致相近的时间接受姜橚之请,因此可以推断,方苞此文写作时间当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前后。
此文的意义,一方面固然是表达方苞与座师姜橚的师徒感情;另一方面也表达对明末战争以及明朝灭亡的看法。方苞在多篇文章讨论明亡问题,认为其最主要原因是奸臣当道、忠臣搁置和良将败死②,而此文写的姜名武正是明末的一位忠臣良将,参与多次大的战事,尤其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明军与李自成的开封之战。与其他文章不同,方苞此文认为明军失败主要是因为“武臣拥劲兵者,多放骜持两端”,具体来说,就是总兵左良玉心持两端,不肯作战,终致败绩,这与好友万斯同、王源为姜名武作传时所持观点一致,可见为时人比较普遍的看法。此外,文章还对李自成军掘开黄河、水淹开封的后果进行了生动描述:“先是贼决河水灌开封,城尽没,白骨被野,聚落无鸡鸣,而公往返数四无所怖”,对其给百姓造成的伤害持批判态度。
从文章写作技法来看,此文亦为方苞义法理论践行的典范。方苞所言“义”就是言有物,“法”是言有序,其中“义”是基础,“法”随“义”变,同时对“义”也产生反作用。苞文中抒写姜宗吕天生之才而不能用的悲壮,文章通过其在两次战乱中的不凡表现,彰显其优于常人的卓越才华与能力,本应大展抱负用于世,不料想未赴任而卒,让人感叹唏嘘。更为悲壮的是,姜氏一家三代,几乎都是如此命运,从姜名武到姜宗吕再到姜橚,概莫能外。虽然原因有所不同,但皆才华出众,英年早逝。本来这类事情的解释,极易落入怨天尤人或宿命论的漩涡,但方苞却给以积极的回应,以颜回超越事功、立于言辞的范例予以开解,既表现他作为士人受儒家淑世情怀的影响,也表现他作为文学家以辞章立命的抱负。
4 介山记序
向尝职掌翰林院,时文之暇,未尝不课及于诸君子之诗词曲调,而无如其气骨之不古朴,词义之不新惊也。至欲求其以风华之笔,发潜德之光,而且出入于骚人韵士之心坎间者,益空谷足音矣。盖近日非无院本,而其中无一段精光不可磨灭之气,是犹取隔宿之尘羹,以充新饥者之空腹,鲜有不出哇者。偶值三晋松崖世兄以其夙搆之诗词,请质于余,余亦嫌其陈腐。而世兄遂道及三晋有《介山记》之一书者,乃西河竹溪氏宋子所作也,大义阐介推之廉静,而绘以新声,“此从未经人道者也,先生岂犹以陈腐目之耶?”余闻其名、想其义,不禁改容曰:“此书之号果新惊矣。但恨未窥半豹。子归,为余购访之。”乃世兄还定羌,不数月而已登鬼录。呜呼!《薤露》《蒿里》倏忽百变,故人长逝可胜浩叹!因想前言,不禁出涕。然言虽在耳,料其付之东流矣。不意余解组后,卧泣西风,而忽来世兄之遗札,并所称《介山记》全稿以惠余,余始知世兄之不寡信轻诺,而種意骚坛也。睹物怀人,苍凉何似苐。余病沉疴,不能仰视,因命书奴为余朗诵,则见其修词立格,亦不出元明诸家之藩篱。而其词义新惊,则实是有一段精光不可磨灭之气。余因口趿数语,命童子录之,并回札附去,一以答泉下人依恋之意,一以鼓后进者激昂之才。虽余墓木将拱,不及见此书之流传海内也,而亦何伤焉。古吴方苞望溪氏题于集贤斋之东轩。
此文见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刻本《介山记》之首,署名方苞望溪序。据文中“向尝职掌翰林院”“不意余解组后”等数语,可推此文作于方苞致仕之后,查苏惇元《方苞年谱》知,方苞于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辞官归金陵,因之,此文应作于乾隆七年(1742年)或稍后。
《介山记》为清代一部优秀的传奇剧作。作者宋廷魁,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山西介休人,少有隽才,未获功名,著有《竹溪诗文集》。《介山记》为其代表剧作,时人称赞“卓乎其关(汉卿)汤(显祖)之再生,而不朽之慧业也”(卷首李文炳序)。该剧以春秋名士介子推为原型,书写了介子推随晋文公重耳出亡十九年,后协助其灭奸复国,最终隐居绵山的故事,着重歌颂了介子推忠孝廉义、不慕名利的高贵节操。
从现有文献看,方苞与宋廷魁并无直接往来,从文中信息可知,主要是通过“三晋松崖世兄”相识。“三晋松崖世兄”为何许人?在《介山记》卷首,有署名“定羌姜基松崖氏拜题”的题诗一首,由此可知,“三晋松崖世兄”即山西定羌(保德)人姜基。关于姜基与方苞的关系,有人称姜基为姜橚的族人[5]。姜橚(1647—1704年),字仲端,号昆麓,山西保德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为江南乡试副考官,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工部右侍郎迁吏部左侍郎,未几病卒,方苞撰有《吏部侍郎姜公墓表》。古代一般称主考官为座师、同考官为房师,而座师、房师之子为世兄。姜橚为方苞乡试座师,松崖世兄姜基应为其子,但从《方苞集》《介休县志》《保德州志》《山西通志》等文献未发现直接证据。方苞的《吏部侍郎姜公墓表》和仇兆鳌的《姜昆麓先生墓志铭》都提及姜橚有一子姜宏焯,不知与姜基是否为同一人,抑或有其他子,皆未详。
赵景瑜称方苞“不完全重视小说、戏曲的作用,因而评价未能批郤导窾,抓住要害”[6],此言不确!方苞序文明确称其“未尝不课及于诸君子之诗词曲调”,只是方苞文名太盛,而戏曲方面留下的文字又少,但不难因此就推论方苞评价未能“抓住要害”。其实,此文的学术价值,除了体现方苞的人生与交游而外,恰恰在于,它是方苞现存的唯一戏剧评论,表现了方苞的戏剧理论。方苞称该剧“其修词立格,亦不出元明诸家之藩篱。而其词义新惊,则实是有一段精光不可磨灭之气”。这里方苞提到两个戏剧评价标准:一是“修词立格”;二是“精光不可磨灭之气”,前者属于言语层面,后者属于意蕴层面,特别是以气论文,尤为重要,它是对前人相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明代公安派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评徐渭:“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7]唐宋派古文家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二》一文提出,宇宙中之绝好文字莫不出于“本色”,本色之文“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8]。由此可见,“精光”与“不可磨灭之气”正是前人论文之法则,尤其是方苞推崇的唐宋派古文家的创见。方苞的意义在于,把两者结合,用来评价戏曲,并作为文艺的最高标准,而实现这一标准的方法,即“以风华之笔,发潜德之光,而且出入于骚人韵士之心坎间”。可以说,“神气”论是方苞“义法”论之外的又一贡献,并且在桐城派得以发扬光大,后来刘大櫆、姚鼐等人皆有相近主张。
5 致尹嘉铨书
贤尊年谱,汎览一过。付儿兴,授以指意,使删截大体不失。乃命孙辈,别录一稿。老生再阅读一过,又截去字句冗设者,可以信今传后矣!大概此本所删,原本中更无应补,如论学语,当入语类,不宜多入谱也。闲尊孝德纯全,居官多善政而无过行。虽未尝特治一经,以精神日力为官事所夺耳。前年过我,告以功令不得与绅士见曰:“某计之熟矣!万一有弹奏,则某明奏愿罢官,从先生学礼。”此种心胸,非今人中所有贤。若能以老生所阅定制仪礼注疏,并所学析疑抄本,编为一书,择贤尊所订丧祭之礼纂入,与安溪、高安、张尔岐、李耜卿之说并存,乃继志述事之大者。愚自入夏,气息奄奄,念惟贤性质笃厚,可读古圣贤书,老生未竟之业将有望焉。乾隆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期望溪笔。
此信见于《尹健余先生年谱》之首。该年谱为光绪五年(1879年)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本,后来的版本将这封信移除了。尹嘉铨(1711—1782年),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尹会一之子。尹会一(1691—1748年),字元孚,号健余,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历任吏部主事、扬州知府、河南巡抚等职,乾隆十一年(1746年)授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十二年(1747年)造访方苞,执弟子礼。
方苞与尹会一皆为清代著名庙堂理学家,二人晚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尹会一早方苞一年去世,这封信为方苞去世前几个月而写,主要讨论尹会一年谱的编修以及从学三礼等问题。方苞的意见应该很重要,年谱出版时署名方苞审定。
从信札可以看出,方苞与尹会一家族两代人的深厚情谊,同时还揭示了方苞对清初礼学的观念,他希望自己的三礼学作品,能够与“安溪(李光地)、高安(朱轼)、张尔岐、李耜卿(李光坡)”诸人之说并列于世。
6 尹太夫人年谱序
自古非常之人,元德、显功、奇节见于本传,未尝别有谱。盖德与功惟要其成,节见于一时一事,欲编年而谱之,无以举其辞。下逮唐宋诗人文士之尤著者,后人好其文辞,就集中所云,按其身所经历,序次其年月,而于人心世教非有所关,则其于言也为赘矣。惟伊川程子、考亭朱子历年多而或出或处,一言一动皆可为学者法。故伊川则朱子谱之朱子则蔡仲默谱之义法,盖取诸孔子世家而可以兴起乎百世者也。自古女妇,虽有圣德,列于风雅,播诸乐歌,用之闺门、乡党、邦国,以化天下,而未尝特为记传。盖以阴德女教,具载内则,虽善尽美备,而辞事皆同。故韩欧诸家,凡志妇人,第条次、族姓、生卒,及夫与子仕隐、学行,而约略其风徽,以为之铭。若志稍详,则铭更略,此立言之体要也。博野尹副宪会一之母李太夫人,为女为妇为嫠笃孝苦节,既可为女妇师。而自会一贵盛守官行政弥珍济艰,凡大事太夫人必为经画,授以节制,其禄赐非请命子妇不得取锱铢,而办尽于官中,以恤军振穷,建桥梁设津渡,为民长利,半以付族姻且义仓义学,以裕乡人,教邑之子弟。凡所为皆士大夫之事,而非女妇之事也。又其高识远见,更有士大夫所不能及者。故其生也,余既以入闻见录,卒铭其墓。而会一谱之,以质于余。以志与录皆举其大略,不能每事而详之也。事有古人未尝有而可以义起者,其此类也。夫故特为序论,兼著传、谱、志、铭之源流,俾士大夫据高位、持厚禄以终其身,而无一可称,其子孙徒志其官阶、锡命、恩赐以为荣,或构虚迹、饰浮言,以益人之诟病者,知所愧耻,岂唯女妇宜闻而兴起与?乾隆十年冬十有二月桐城方苞撰。
此文见于《尹太夫人年谱》之首,署名方苞。该年谱与《方望溪先生年谱》一起收录在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9册,之前学界罕有提及。
尹太夫人为尹会一之母,此文作于乾隆十年(1745年),为方苞致仕以后,属于晚年作品。尹会一曾就家谱之事求教于方苞,方苞建议其母亲之事不宜详载家谱,“而仆谓宜为年谱者”[9]。古代为女子作年谱,实属罕见,方苞此举有开创意义,后来尹会一采纳了方苞的意见,确为其母作年谱,请方苞为之序,也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序文内容对了解中国古代年谱理论与女性的关系,以及方苞对女德女教的看法,皆有一定价值。此文后世颇有影响,被节选收录在民国《嘉业堂丛书》所收蔡显的《闲渔闲闲录》卷三。蔡显(1697—1767年),字景真,号闲渔,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雍正七年(1729年)举人。《闲渔闲闲录》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刻成,蔡氏因记载南山集案、钱名世案等被告发处斩。该书多记传闻,而此信却为作者亲见。
在该年谱方苞序之后,还附录了方苞一篇短文《论编年谱书》,其内容如下:
得手教,一切具悉。为母编年谱,古未之有;而太夫人志事与贤士大夫略同,乃妇女中特出之人,不惟今世希闻,即在古亦罕见。则孝子创例以为世法,播流海内,可兴可观;人不能訾也。如苦窭艰时事,皆琐细不可条举。则总计家道息耗、人事凶吉改移,或数年或十数年而括之曰:太夫人于是年几何矣。此史记、孔子世家义法也。略者略之,详者详之,唐宋名贤年谱多如此,不必以前事简略为嫌也。望溪方苞白。
此文在恩露所藏方苞逸文集名为《答尹元孚》,后收录在戴钧衡编纂的《方苞集·集外文》。综合这两篇文章,结合上一篇《致尹嘉铨书》,可以大致见出方苞的年谱理论,即:一是以义法为指导。二是注重人心世教。三是年谱与传铭、语类不同,传铭举其大,年谱叙其详,语类重其学。四是男女两性平等。年谱内容只看事迹,不唯性别。当然,方尹两家关系好、彼此了解也是写作的基本背景。
综上所述,通过方苞的六篇佚文,展示了方苞人生与文章的不同方面,对于了解方苞的家族关系、人生游历、文章创作和理论主张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 比如:钟扬,顾海.则桐城《戴氏宗谱》中戴名世、方苞佚文两[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2):37-40;袁鳞.方苞佚札六通考释[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1):104-109;朱春洁.稀见明清诗文辑考六则[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0-56(内含一篇方苞逸文)。
②《方苞集》中讨论明代灭亡问题比较集中的篇章,比如《书卢象晋传后》《书杨维斗先生传后》《书泾阳王佥事家传后》等,基本观点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