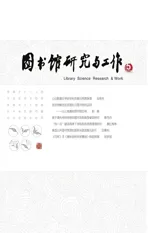图书馆视角下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年鉴》的学术价值探析
2022-02-08刘劲松
梅 影 刘劲松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南昌 330022)
《中国教育年鉴》在民国时期出版了两次。《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于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于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部《中国教育年鉴》均由中华民国教育部(以下简称“教育部”)组织人员编写,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教育事业、图书馆事业的看法,丰富了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研究。然而,该年鉴图书馆部分的学术价值,至今没有受到重视。了解《中国教育年鉴》图书馆部分的学术价值,对深化近代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1 《中国教育年鉴》的特色
我国关于图书馆事业的研究起步较早。1909—1910年,孙毓修撰写的《图书馆》一文在《教育杂志》连载[1-2],对我国图书馆事业进行了概述。该文从建置、购书、收藏、分类、编目、管理、借阅7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清末图书馆事业概况。这是我国第一篇图书馆事业研究成果。1928年后,中山大学图书馆金敏甫对近代以来的图书馆事业展开研究。他的《图书馆事业之发展》《中国现代图书馆教育述略》《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概况》等文章陆续发表,勾勒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概貌,包括图书馆的趋势、图书馆法规、图书馆行政机关、图书馆会议团体及其议案、图书馆经费、图书馆藏书、图书馆建筑等。金敏甫的论文为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研究奠定了基础。马宗荣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功力颇深。1920年代初即有撰写《图书馆概论》计划[3],随后相关论文论著不断问世。马宗荣把我国图书馆事业分为古代、秦汉、晋及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民国10个时期展开论述,内容极为广泛[4-6]。此外,杜定友、洪有丰等人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也都有零星的研究。不过,上述研究都是私人撰述,代表了学者个人对图书馆事业的看法。
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出版,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阶段性总结,官编图书馆著作正式出现。《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从沿革和概况两方面简述了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沿革上,揭载了《图书馆通行章程》等公共图书馆法规。图书馆概况上,主要阐述国立图书馆和各省市县图书馆情况:概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沿革、组织、经费、建筑、藏书和职员等方面的情况,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概述。重点介绍了各省特别市的图书馆情况,包括沿革、组织、经费、建筑设备和图书等内容,并绘制了《全国图书馆统计表》[7]798-799。
1948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出版。这次教育年鉴关于图书馆事业的撰述,与《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衔接,并进一步完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图书馆部分共九个子目,分别为行政与组织、建筑与设备、经费与藏书、分类与编目、馆员之训练与待遇、图书馆出版物之编刊、战时损失及胜利后之清理与接收、孤本秘笈之搜购与影印、国立图书馆概况。其关于图书馆事业的材料较为丰富全面。
《中国教育年鉴》由教育部组织人员编写,其图书馆部分的特色主要有:
一是注重全国视野下图书馆事业的整体性描述,无论《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或《第二次全国教育年鉴》,都是如此。如介绍图书馆行政与组织时,胪列了近代中国主要的公共图书馆法规,包括《图书馆通行章程》、《图书馆规程》(1915年)、《通俗图书馆规程》、《图书馆条例》、《图书馆规则》(1947年)等。图书馆法规是图书馆运作的法律依据,是图书馆权利的法律保障,也是教育部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式。《中国教育年鉴》把图书馆法规作为图书馆部分的起点,地位使然。
再如图书馆概况。《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专门编制了《全国图书馆统计表》,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省市别、普通图书馆、专门图书馆、民众图书馆、社教机关附设图书馆、机关及团体附设图书馆、书报处、学校图书馆及私家藏书楼8类,而前7类又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类。该表是1931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公布的《十九年度全国公私立图书馆一览表》的修改版。根据《全国图书馆统计表》,截至1933年底,我国公立图书馆中,民众图书馆为558所,普通图书馆为827所,专门图书馆为40所;私立图书馆中,民众图书馆为17所,普通图书馆为67所,专门图书馆为18所,各类图书馆总数达2 935所。我国历来有图书馆调查统计的传统,不管是私人的还是官方的,局部的还是大规模的,图书馆的调查统计活动一直都存在。其中著名的调查主要有中华图书馆协会在1925年、1928年、1930年、1931年,接连4次公布的《全国图书馆调查表》,调查以省为单位,内容包括华北、华中、华南、华东地区各省市图书馆的馆名和地址,并分类总计了各省和各种类图书馆的数量。《全国图书馆统计表》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调查统计相互补充,丰富了我国的图书馆调查研究。《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同样绘制了《全国图书馆统计表》,分别为1936年和1948年的统计数字。
二是资料使用较为全面。教育部编写年鉴时,常常使用档案资料,这是其特色之一。如第二次年鉴介绍图书馆行政时,开头即谓:“大学院成立之初,内设行政处,主持全国教育行政事宜,处分六组,图书馆亦占其一,掌理下列事项:(一)关于国立图书馆事项;(二)关于学校图书馆事项;(三)关于公立图书馆事项;(四)关于保存文献事项;(五)关于钞印稀有图书事项。不久图书馆组并入文化事业处,迨大学院改为教育部,遂将图书馆事项,归并社会教育司,不复独立成一部门矣。”[8]1104教育部管理图书馆事业的机构多为社会教育司。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实行大学区制,设立了大学院。不过,大学院管理图书馆的行政部门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对该机构的介绍,为深入研究国民政府初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教育部档案资料在《中国教育年鉴》中运用最为成功的地方,集中体现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孤本秘笈之搜购与影印”部分。该部分着重提出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中央图书馆的文献收购活动:“国立中央图书馆于二十九年收藏吴兴许氏善本书七十余种,三十年在沪港两地收购,历年所藏已达一五三、四一四册。罕见之品有金崇庆间刊本之泰和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元至正间徐氏一山书堂刊本之礼部韵注(前附科场条例),元刊本之新编阴阳足用选择龟鉴,元溪隐书堂刊本之新编年月集要,前至元十八年刊本之涓吉成书,至正间刊本朱墨套印本之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明刊本之高皇后传,寰宇通志及嘉隆新例等。此外尚购有宋版书二十余种,六朝及唐人写经四十余卷,永乐大典数册,宋本中之南宋群贤小集及十二行本之陆宣公奏议等书,成批入藏者则有张氏韫辉齐大批珍本图书,计二百六十种,其中最珍秘者有金刻之云齐广录,明建文齐刻本之元音,明抄本之廷枢纪闻,述右堂钞本,钱遵王密校之怀陵流寇始终录,曹倦圃手抄黄荛圃手跋之方澜、郭升、刘埙郑铭四家诗,元钞本之敦交集及建文、天顺、弘治、嘉靖、万历、崇祯各朝之登科同学录等。又明代大统历,自景泰以迄崇祯,都凡三十九部,尤为大观,而宋元刻本,亦达十余种。关于金石拓片古今兴图曾于三十三年购入天津孟氏旧藏金石拓片一千五百种,三十一年购入番禺商氏所藏金石拓片七百余种,总共已达一一、一三九件。”[8]1116细绎这些书籍入藏时间和收购区域,均为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的沦陷区。国统区机关在沦陷区收购书籍,本身就值得玩味。随着《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9-11]《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12]《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13-14]以及台北大学方国璇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战期间古籍抢救与古书业》[15]等一系列论文的发表,我们始知国民政府中央图书馆战时收集沦陷区文献活动的惊心动魄。这些材料当时不可能公布,而教育部已经把相关情况编入《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资料的独特性成就了《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的学术价值。
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身上。《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来入藏罕见书,数亦不少。举其要者有明张凤鸣辑旧抄本桂胜,明杨芳詹景风纂修万历刻本殿粤纂要,康熙初年刻本盘州盘江铁桥志,康熙刻本松江府志。嘉庆刻本扬州府图经,乾隆刻本泾渠志,明赵琦美抄校本东国史略,明末刻本逊国正义记,朱丝栏精抄本清文宗穆宗实录,明归有光等修隆庆刻本三吴水利录,宋罗从彦撰元刊本罗豫章集,明万历刻本常熟文献志,明谢肇浙撰万历刻本文海披沙,明刊本程氏、金氏、方氏、汪氏、洪氏家谱,明戚继光撰明刊本戚少保兵书,明刊本河南河内县志,明万历刊本四川赋役书册,明文林撰弘治正德间精刻本文温州集等。又孤本元曲凡六十四册,每册载元明剧三种左右,共二百种,皆为元曲选所未刊者,其中以明抄者为多,亦间有元刊本,末有陈眉公,黄荛圃,丁初我诸家之跋;为也是园钱氏旧藏,政府正拟价值购,案存平馆。”[8]1117这些书籍多为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收购。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购这些书籍时,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至多在《图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等刊物上略载一二。如乾隆刻本《泾渠志》信息发表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16]。其收购过程直到最近几年才有学者揭示出来[17]。不过,《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已经在1948年展示了这些战时成果。这是其他私人著述所无法比拟的。
当然,《中国教育年鉴》的价值远远不止上述所述两类,其他如更正错误等,均属荦荦大端,不再一一罗列。
2 《中国教育年鉴》的不足
因为宏大,《中国教育年鉴》也存在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是观点与学者高度相似。《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评价民国初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趋势时,提出5点:“由保存而趋于使用”“由贵族而趋于平民”“由深奥而趋于实用”“由简单而趋于复杂”“由散漫而趋于联络”[7]788。金敏甫有一篇文章叫《中国现代图书概况》,指出图书馆发展的趋势为“由保存的趋于使用的”“由贵族的趋于平民的”“由深奥的趋于实用的”“由主观的趋于客观的”“由形式的趋于精神的”“由机械的趋于专门的”[18]。两者比较,差异仅在于后面两点。金敏甫的文章发表于1928年,而《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出版于1934年。显然,后者大篇幅地借鉴了前者,有掠美之嫌疑。
《中国教育年鉴》中这类情况不止一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众教育馆纷纷成立,成效显著。《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叙述民众教育馆沿革时,提出:“民众教育馆,为国民政府成立后之一新兴教育事业。其前身为通俗教育馆。设立最早者,当推民国四年成立之江苏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馆。”[8]1096我国的通俗教育开始于民国四年(1915年)吗?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在北京设立通俗教育调查会,调查北京有关通俗教育各情形。根据该会的调查,京师学务局设宣讲所8处,通俗图书馆1处。同年,河南等省也都开始筹设通俗图书馆”[19]。也就是说,我国通俗教育至少开始于1912年,甚至可能更为提前。《中国教育年鉴》的说法,与著名学者陈训慈的观点较为接近。陈提出,1915年《通俗图书馆规程》的颁布,标志政府对于图书馆的目光,由硕学士子已及于民众的身上,“可说是民众图书馆的张本,中国的民众图书馆运动自此抬头”,“当时各省民众图书馆,以江苏最为发达,如南京民教馆图书馆在民国四年三月”[20]成立。陈训慈的文章发表于1936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出版于1948年。或许其他学者更早提出类似观点也未可知。不管如何,教育部的观点肯定落后于学者,且与学者观点高度相似,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是机构介绍残缺不全。国民中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只是公布《图书馆通行章程》等图书馆法规,还设立了机构,专门负责图书馆事宜。这些机构是全国图书馆事业的管理机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虽然介绍了大学院管理图书馆事务的组织机构,但却遗漏了其他时期中央教育主管部门设立的图书馆管理机构。
清末,中央设立学部,学部又设五司十二科。学部下设专门司庶务科,“凡关于图书馆、博物馆、天文台、气象台等事均归办理”[21]。专门庶务科,“员外郎一员,主事一员,办理科务”[21]。专门司庶务科推动了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清末管理地方教育事务的机构是提学使司。每省设一员提学使,秩正三品,为督抚之属官,总理全省学务,包括图书馆事务[22]。劝学所和教育会也在各地纷纷兴起,劝学所为全境学务之总汇,各厅州县于本城择地设劝学所;教育会则与劝学所、学务公所联络一气,其宗旨为“补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23]。它们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都有助益。
提学使衙门下的学务公所分为六课,图书课占其一,“掌理编译教科书、参考书,审查本省各学堂教科图籍,翻译本署往来公文书牍,集录讲义,经理印刷,并管图书馆、博物馆等事务”[22]。在各地的教育总会和分会中,其应举事务包括“筹设图书馆、教育品陈列馆,及教育品制造所,并搜集教育标本,刊行有关教育之书报等,以益学界”[23]。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设立了教育部。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管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项社会教育事务。社会教育司所掌事务包括:“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关于通俗图书馆巡行文库事项”[24]。社会教育司一直到1927年才被大学院替代。不过,大学院为时不久,1929年又恢复为社会教育司。《中国教育年鉴》仅介绍大学院行政处,显然不够。
三是史料问题。《中国教育年鉴》中图书馆材料方面有很多问题。如《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收录了《图书馆通行章程》,然而到“第十九条”时,全文结束。1910年,《政治官报》刊载了《图书馆通行章程》全文,两者对照,发现《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遗漏了第二十条:“图书馆办事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应随时增订。在京呈由学部核定施行,在外呈有提学使司转详督抚核定施行。”[25]1981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了《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其附录一为图书馆法令,第一个即为《图书馆通行章程》。不过,该章程也只有19条[26],第二十条完全遗漏。这两者的巧合,可见《中国教育年鉴》确存在材料遗漏问题。
又如《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民国十四年十月教育部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十一条如左”[7]788,又载“同年十一月,教育部又颁布《图书馆规程》十一条,照录入下”[7]788。而《通俗图书馆规程》原文,其第二条为“通俗图书馆之名称,适用图书馆第三条之规定”[27],第三条“通俗图书馆之设立及变更或废撤时,依图书馆第四条之规定,分别具报”[27],第四条“通俗图书馆主任员应依照图书馆第五条之规定,分别具报”[27],第六条“公立通俗图书馆之经费预算,适用图书馆第八条之规定”[27],等等。这些条款都提到“图书馆”一词。那么,这个“图书馆”是什么呢?显然是《图书馆规程》。而《图书馆规程》一定和《通俗图书馆规程》同时公布,或在其前公布,而绝对不应该在其后公布。事实上,《图书馆规程》[28]和《通俗图书馆规程》[27]在《教育公报》上同时公布了。这个谬误流传更广。《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春秋至五四前后》将它们收录,《通俗图书馆规程》后面的记载为“一九一五年十月”,《图书馆规程》后面的记载“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还言之灼灼来自《教育公报》1915年第8期[29]。或许它们出错的渊源完全相同。
再如,《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编制了《全国图书馆统计表(二十五年及三十六年)》。根据该表,1936年时,我国单设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机关社团附设图书馆、民教馆图书部,共5 196所。1947年时,我国这些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共为2 702所。这些数据来自哪里《中国教育年鉴》没有说明。1936年7月27日,教育部通过《中央日报》公布了截至1936年底全国图书馆统计表。根据该表,学校类图书馆为1 967所,私立类图书馆为20所,普通类图书馆为576所,专门类图书馆为11所,流通类图书馆为37所,机关类图书馆为175所,民众类图书馆为1 255所,总计4 041所[30]。显然,《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没有采纳教育部公布的调查数据。那么,这5 196所图书馆书籍来自哪里?1936年,《申报年鉴》发表了和陈训慈合作编写的《全国各省市各种图书馆数量统计表》(计二十八省,六直辖市区,西藏及外蒙未及调查)。根据该表,全国图书馆分为四类,单设图书馆1 502所,民教馆圕990所,机关附设圕162所,学校圕2 542所,共计5 196所[31]。比较这两个统计表,不难发现,全国图书馆总数完全相同。不过,在各种具体图书馆数据上,又有很大差异。如数据合计问题。《全国图书馆统计表(二十五年及三十六年)》中的统计对象比《全国各省市各种图书馆数量统计表》要多,西安、大连、天津、汉口等地区图书馆数据均为《全国各省市各种图书馆数量统计表》所无。蹊跷的是,两者的合计数据是一致的。其中原因耐人寻味。只能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编制的《全国图书馆统计表》合计数据有问题。《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还存在数据誊抄错误。《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和《申报年鉴》都对1936年的单设图书馆、民教馆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机关附设图书馆进行了数量统计,但两者的表格中,学校图书馆与机关附设图书馆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在《申报年鉴》中,学校圕为2 542所,机关附设圕为162所;《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学校图书馆为162所,机关社团附设图书馆为2 542所,这是不可能的。当时都没有那么多机关。根据教育部1936年7月27日在《中央日报》公布的数据,截至1935年底,机关类图书馆为175所[30],抗日战争后突然增加到2 542所,完全不可能。此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关于1936年各省市学校图书馆的数据与《申报年鉴》中机关附设圕的数据完全一致,而《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机关社团附设图书馆的数据又与《申报年鉴》中学校圕的一致。以江苏省为例,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其学校图书馆为7所,机关社团附设图书馆为44所;而在《申报年鉴》中,其学校圕为44所,机关附设圕为7所。又如浙江省,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其学校图书馆为21所,机关社团附设图书馆为125所;而在《申报年鉴》中,其学校圕为125所,机关附设圕为21所。由此可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将1936年中学校图书馆和机关附设图书馆的两类数据抄反了。
3 结语
《中国教育年鉴》是由中华民国教育部组织人员编写,其关于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描述,反映了教育部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看法。这种看法,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中国教育年鉴》中使用了一些当时没有公开的文件,在材料上也有新颖之处。这是《中国教育年鉴》极具价值之处。然而,《中国教育年鉴》在很多细节上存在雷同、讹误等问题。尽管如此,《中国教育年鉴》图书馆部分依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