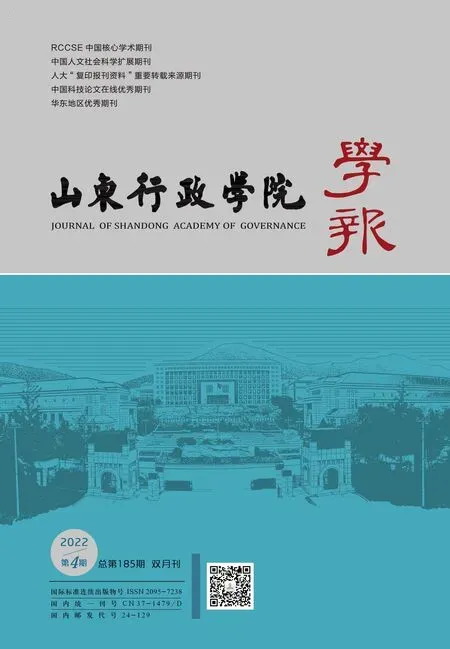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的反思与完善
2022-02-04黄晨阳
黄晨阳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一、问题的提出
“有权利便有救济”是一条古老且普世的法谚。在现代人民主权理念的指引下,知情权被视作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知情权正式成为我国公民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或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单从理论层面看,认定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与认定行政诉讼被告不应存在太大差别,但实际情况是,随着政府信息公开事业的不断推进,信息公开主体越发多元,法院在认定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方面争议频出,直接影响着相对人知情权益的救济与实现。经判例检索,目前常见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争议主要指下列四种情况。
(一)行政机关内设机构的被告资格之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条、第4条规定,为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观察地方政府实践,主要指定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公室,或设立专门的政务办公室负责本行政机关、行政区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一般以本机构名义作出答复行为。但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答复行为,能否以此类政府信息工作机构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意见。持否定立场的裁判理由主要为“被诉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不是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也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因此不能作为行政诉讼被告”(1)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4020号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10429号行政裁定书、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行终105号行政裁定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行终1057号行政裁定书。。持肯定立场的裁判理由则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第1款的规定,被诉机构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承办和负责机构,应当对自己的答复行为负责”(2)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8行终46号行政裁定书、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9行初54号行政裁定书、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2020)豫0202行初23号行政裁定书、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行初345号行政裁定书。。
(二)管委会、派出机构的被告资格之争
地方政府设立的各式管理委员会、政府职能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对某一行政事务或某区域内行政事务的管理而设立的行政组织。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第21条规定,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开发区管理机构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外,其他地方政府设立的各式管理委员会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政府职能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作为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并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而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做法是,以被诉机构是否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授权来认定其是否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但也有法院不以授权与否作为判断标准,如在“沈耀云诉湘潭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湘潭昭山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作为湘潭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虽然通常不能独立承担行政责任,但其具有负责相应信息公开的资格,且对于其在征收过程中制作或掌握的相应征收行政行为的政府信息,亦有进行相应信息公开的能力,是本案的适格被告”(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3行初129号行政裁定书。。
(三)事业单位的被告资格之争
事业单位是国家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供公共服务而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按职能分工承担相应的行政事务、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以被诉单位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没有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授权等为由,否定其行政诉讼被告资格(4)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288号行政裁定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行再19号行政裁定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行终499号行政裁定书。。但也有法院认为,“事业单位是人民政府全额拨款依法成立的法人组织,承担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其社会公共服务行为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被告单位是所申信息的制作、备案或保存单位的,能够独立承担职责范围内信息公开的法律责任,属于行政诉讼适格被告”(5)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行再19号行政裁定书、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7行终3号行政裁定书、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陕71行初265号行政裁定书。。
(四)公共企事业单位的被告资格之争
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于2019年4月15日正式公布,将原条例第37条替换为第55条,规定教育、卫生健康、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不再参照“新条例”开展信息公开活动,而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的规定,公开其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救济模式也由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调整为可以向有关主管部门和机构申诉。有学者称,此次修订实现了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活动的“脱条例化”(6)彭錞:《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审查之道:基于108件司法裁判的分析》,《法学家》2019年第4期。。但这是否意味着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活动不再接受司法审查,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意见。在“郭正诉沧州体育管理中心案”中,郭正向沧州体育管理中心申请公开:沧州体育馆房屋及室外场地非税收入征收依据;公示沧州体育馆房屋及室外场地具体出租合同及租金。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沧州体育管理中心并非行政机关,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审法院则撤销了原审行政裁定,认为沧州体育管理中心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行政法规的授权下,其行使了执收单位的职能,收取的款项为政府非税收入,属于非税收入执收单位,可以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进而认定郭正的起诉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7)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9行终247号行政裁定书。。当然,也有法院直接依据“新条例”第55条,认定被诉单位属于公共企事业单位,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驳回(8)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行终847号行政裁定书、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行终683号行政裁定书。。
除上述争议外,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背景下,划入党的机关、机构的行政部门能否继续以党的机关、机构的名义开展信息公开工作,成为行政诉讼适格被告,也是当前实务界、理论界经常讨论的问题(9)实务界、理论界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有“名义说”“授权说”和“实质行政说”。“名义说”以党的机关对外是否加挂行政机关的牌子作为认定标准。程琥:《新条例实施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若干问题探讨》,《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授权说”以法律法规规章有无授权党的机构行使国家行政职权为标准。陈征:《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与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实质行政说”即不强调行为主体的性质,也不强调法律是否授权,认为只要某一主体行使了原本应由行政机关行使的国家行政管理权,影响了特定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利益,就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黄先雄:《党政合设合署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回应》,《中外法学》2020年第2期。。有鉴于此,为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事业,更好地保障公众知情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实现,本文将以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为据,重新检视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并就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提出建议,求教于大方。
二、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的实践反思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救济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自身权益而提起的行政诉讼。认定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原则上应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进行。《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2款规定,对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原告有权起诉。但是,被诉组织、机构没有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或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依“行诉解释”第20条的规定,不能成为行政诉讼被告。据此,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认定条件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行政诉讼被告应当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二是行政诉讼被告应当具有与被诉行为相关的法定行政职权;三是被诉行为必须是行政诉讼被告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作出的;四是行政诉讼被告能够独立承担行为的法律责任。然而,前述争议表明,这套认定标准与政府信息公开实践存在不适应之处,故需进一步讨论。
(一)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并非都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在于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实践中主要看重申请对象是否制作或保管了有关政府信息,其主体是否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一般不会影响知情权的实现。一方面,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可以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4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可以指定专门机构负责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指定的专门机构一般是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负责接收、处理、答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等工作。例如,上海市人民政府指定市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办公室承办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事宜。另一方面,公共企事业单位可以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修订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公开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参照本条例执行。虽然“新条例”删除了“参照适用条款”,但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主体地位并未因此改变。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公共属性较强、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仍然负有信息公开义务,只不过信息公开活动的法律依据由《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替换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的规定执行,或是依照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的专门规定执行。
(二)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的公开职责不必然基于法定授权
一般情况下,被诉主体具有与被诉行为相关的法定职权是判断行政诉讼被告适格的重要条件。但司法实践中认定的适格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除部分行为主体因属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而具有法定职权外,存在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也可能被认为具有公开职责:一是行为主体是行政机关指定的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在“新乡市中盟置业有限公司诉新乡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4条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行归口管理,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应当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申请,这是畅通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便于申请人及时准确获取政府信息的制度保障。被告新乡市人民政府已成立专门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且该机构已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的,原告坚持认为新乡市人民政府应作为答复主体、新乡市人民政府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的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10)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7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二是行为主体是所申请信息的制作、保存或管理主体。在“胡某诉秦安县兴国镇人民政府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案”中,胡某向兴国镇政府申请公开征收补偿协议的相关信息,兴国镇政府未予回复,胡某以兴国镇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被告与原告就补偿事项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由秦安县房屋征收补偿管理中心负责对协议条款所产生的费用兑付、收缴、结算,并保管补偿档案材料。秦安县房屋征收补偿管理中心是本案所申信息的保存单位,被告虽然与秦安县房屋征收补偿管理中心是共同实施单位,但是其并没有对涉案的信息进行制作和保存,故原告应当依据释明变更秦安县征收与补偿管理中心为本案的适格被告”(11)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5行终25号行政裁定书。。三是行为主体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在“戴伟诉济南市槐荫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政府信息公开案”中,被告槐荫区征收中心是公共事业单位,受槐荫区城乡建设委员会委托,承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法院认为,“被告槐荫区征收中心作为事业单位,其社会公共服务行为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是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能够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1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行再19号行政裁定书。。
(三)政府信息公开主体与诉讼责任主体存在分离情况
我国行政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具有行政主体身份或地位是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认定基础(13)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条件之一,系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行政主体地位。姜明安:《行政诉讼法》(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140页。何海波教授认为,行政诉讼被告应当是依法成立、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机构。何海波:《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204页。叶必丰教授认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是行政主体,不是行政主体就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叶必丰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6页。。所谓“行政主体”,即依法成立的、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在诉讼中,当事人有能力对行为后果负责是诉讼目的实现的基础,因此行政诉讼被告被要求应当具有行政主体身份或地位。然而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要是各级人民政府或其职能部门指定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若严格按照行政主体标准认定行政诉讼被告,则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往往不能成为被诉主体,政府信息公开主体与诉讼责任主体便会产生分离。例如,在“许某、高某诉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简称‘拆迁办’)信息公开案”中,拆迁办是被诉《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的作出者,也是征地拆迁安置方面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负责机构。但法院认为,“拆迁办系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内设机构,而该管委会属于西安市人民政府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为其派出机构。因此,许某、高某对拆迁办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不服的,应当以西安市人民政府为被告”(14)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陕71行终1514号行政裁定书。。
综上所述,政府信息公开活动区别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活动,尤其是不再强调信息公开主体的行政主体性,更加重视从实质层面保障和满足相对人的知情需要。究其原因,有学者指出,“信息公开主体之所以游离于行政主体理论之外,主要原因系行政主体理论是秩序行政的产物,秩序的维护要以限制公民权利为代价,特别强调主体的资格以及权力的来源。而政府信息公开属于给付行政范畴,是授益和提供信息服务的,所以没有必要受行政主体理论的桎梏”(15)余凌云:《政府信息公开的若干问题 基于315起案件的分析》,《中外法学》2014年第4期。。在司法实践中也有法官持类似观点,即认为“没有直接对外管理职能的内设机构不能直接实施影响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主要是针对损益性行政行为而言的,对于属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政府信息公开未必完全适用”(16)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007号行政裁定书。。因此,继续以“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地位”为标准审视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是否适格,恐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性质、实践情况脱节。
三、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的完善原则
虽然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直接适用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可能会产生不适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确系行政诉讼的特殊类型。因此,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既不能是“另起炉灶式”的背离行政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也不能无视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特殊性。故在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之前,有必要就完善原则进行说明。
(一)符合《行政诉讼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
立法目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法律制度构建、运作的准绳,对法律制度的后续修改、完善也会起到指引性作用。《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是“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设法治政府,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经比照不难发现,在保障社会公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基本权益、督促政府依法行政等方面,《行政诉讼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具有立法目的上的一致性。因此,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在设置上是否有助于前述立法目的的实现,是判断该认定标准是否妥当的关键。
(二)遵循诉讼经济原则
诉讼经济原则是指以最少的诉讼成本实现最大的诉讼效益,现已被各国广泛运用于诉讼程序中(17)牟逍媛:《谈诉讼经济原则》,《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在微观层面,诉讼经济原则要求借助繁简分流、程序简化等制度改造,尽可能减轻诉讼主体在具体个案中的诉讼负担;在宏观层面,诉讼经济原则要求尽可能节省司法资源、避免挤兑诉讼资源情况的出现。体现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这个问题上,即要求适度放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的起诉条件,进而降低申请人的起诉成本,避免申请人因找不到适格被告而反复提请诉讼。具体而言,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中,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一般是实际接收、处理、答复公开申请的行政部门。至于公开机构是基于行政系统内部的授权还是委托才承担公开职能的,处于行政系统外部的相对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知晓。因此,倘若严格要求相对人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诉讼,其结果要么是相对人为保证起诉被法院受理而起诉多个可能的行政主体,要么是起诉被法院裁定驳回后相对人重新提起新的诉讼。如此一来,紧缺的司法资源便被无意义程序空转消耗,相对人的诉讼成本也随之抬高。
(三)有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是最高人民法院“五五改革纲要”确立的现阶段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之“解决行政争议”立法目的的时代阐发。“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在理论内涵上强调对案涉争议进行整体性、彻底性的一揽式解决,实现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正当诉求的切实有效保护(18)章志远:《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法理解读》,《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据此,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之完善,应当以助益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为遵循,避免行政审判“口惠而实不至”情况的出现。如前文所述,信息公开主体欠缺行政主体资格、公开义务主体与诉讼责任主体脱节等是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故在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被告可能以“未实际持有政府信息”为由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即使法院最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也有多种办法阻却判决的执行或造成执行不能,例如以判决执行需要具体行政机构配合,或内部行政机构管理不善导致信息灭失等理由“搪塞”判决的执行。与之相对,放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认可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被告资格,则在实践层面有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因为“信息是否存在、能否公开、有无错漏”是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争议的主要内容。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作为政府信息的制作、保存、管理和统筹主体,直接参与诉讼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司法裁判的执行。
四、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的完善路径
应当承认,以行政主体理论为基础构建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对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但由于该标准对政府信息公开活动缺乏全面、深入的关照,故在司法实践中引起诸多争议。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以旧条例为解释对象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亟待更新、调整,这也成为完善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的重要契机。需要强调的是,完善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传统标准,而是以传统标准为基础,针对信息公开的特殊情况作适当调整。笔者认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不必囿于形式意义上的行政主体身份,只要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组织负有信息公开义务或具有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就应以“行政主体”对待,允许启动行政诉讼程序。
(一)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应当具备组织性
在我国,行政诉讼只能以特定机构为被告提起,既不能告国家,也不能告个人,组织性是行政诉讼被告最基本的特征。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被告应当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组织当中的任何个体或是其他个体不能成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被告。因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在于促进公共利益和监督行政,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主体是组织而不是个人,个人是以信息公开机构的名义实施行为。另一方面,具备一定组织形式并不要求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必须具有法人主体资格。实践中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要是行政机关指定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政府职能部门设立的专门机构。作为行政主体的组成部分,这类行政机构虽然不具有法人主体资格但具备组织性,能够独立负责信息公开申请的接收、处理、答复等工作,也常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信息公开行为。因此,对于在事实上已经具备行为能力的政府信息公开机构,无需要求原告寻找公开机构的组建机关或归属机关来作被告,因为以公开机构为被告并不会影响相对人诉讼目的的实现。
(二)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应当具备外部性
所谓“外部性”,是指根据信息公开行为以谁的名义作出来认定信息公开诉讼的被告。因为,被告适格本质上是起诉便宜的问题,目的是为了确定作出被诉行为的主体是谁,而不是谁有权作出被诉行为,故不应当用复杂的行政结构和“正确的被告”提高公民的起诉负担(19)[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一方面,明确行政行为的权力归属是比较困难的问题。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作出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可以源于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也可以源于行政机关的委托,还可以来自于上级行政机关的批准。要求原告在提起行政诉讼时知晓复杂行政结构背后的权力归属关系,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是十分苛刻的。另一方面,谁是正确的政府信息公开主体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修订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信息公开主体判断标准。“新条例”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初始责任人公开”规则和“牵头制作人公开”规则。前者是指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后者是指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制作的政府信息,由牵头制作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如果认为被诉行政机关必须是正确的公开主体,否则法院审理实体争议不具意义,那么在答复主体与义务主体不一致的情况下,公民的起诉负担也会相应增加。
(三)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应当具备公益性
被诉主体具备行政性是认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核心条件,因为行政机关属于法律执行机关,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保障法律的优先地位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任务。然而,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趋势上看,用公益性替代行政性更加契合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实践。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践初期,政府信息公开被视作“行政权的防腐剂”,通过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相对人申请公开两种形式,将行政权暴露在社会公众的目光之下。随着公共事务范畴的不断扩张,行政管理活动的能效比、专业化程度、服务质量亟待提升,行政机关开始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公共管理服务中来。由于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也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故有受社会公众监督的现实必要。从域外经验来看,许多国家也将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实施机关,只是在称谓上有所区别。例如,日本的独立行政法人、丹麦的(电力、煤气、供热等)公共服务管理企业、法国的从事公共服务管理的私法组织等(20)李广宇:《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受案范围与当事人》,《人民司法》2010年第5期。。在此背景下,固守被诉主体的行政性标准将会把公共企事业单位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虽然,“新条例”删除了“公共企事业单位参照适用”条款,规定“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活动”属行政监管范畴。但笔者认为,现代行政法已经迈入公私合作时代,大量的公共管理事务、社会福利供给任务已经通过行政协议、行政委托等多种方式交由公共企事业单位履行,公共企事业单位与行政部门的关系在频繁的交往、合作中也日趋紧密,倘若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活动免于司法审查的监督,恐导致大量政府信息借公共企事业单位之名隐匿于阳光之下,不利于政府信息公开事业的进步。
(四)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可以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在实体上是否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不会影响诉讼结果的承担。一方面,“实体上是否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与“诉讼中能否成为被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在逻辑上也不相通。“实体上是否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是判断行为主体在行政法上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必要标准,强调行政主体行使权力与承担责任的一致性。而“诉讼中能否作为被告”强调的是被告的确定性问题,即被诉行为由谁实际作出。至于被告是否需要承担最终的诉讼结果,须经法院实体审理后才能确定。因此,被告在实体上是否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与其是否需要承担最终的实体责任不具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实体上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依据与信息公开诉讼中所要承担的责任形式也不匹配。我国行政法学界通说认为,“有独立支配的财产”是行政主体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依据(21)杨小君:《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之检讨》,《法商研究》2007年第1期。。原因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起源于民事诉讼制度,在实体法层面亦受民事理论影响,故认为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一样,责任能力的依据都来自于“有独立支配的财产”。2020年5月28日正式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将“有独立经费”作为认定机关法人的要件。然而,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第10条、第11条的规定,被告所要承担的责任形式并不只是赔偿责任,还包括行为责任,如撤销公开决定、更正信息内容、履行公开职责等。显然,行为责任的承担与被告是否具有独立的财产并无关系。综上所述,以被诉主体是否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作为认定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被告资格的条件与实践情况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