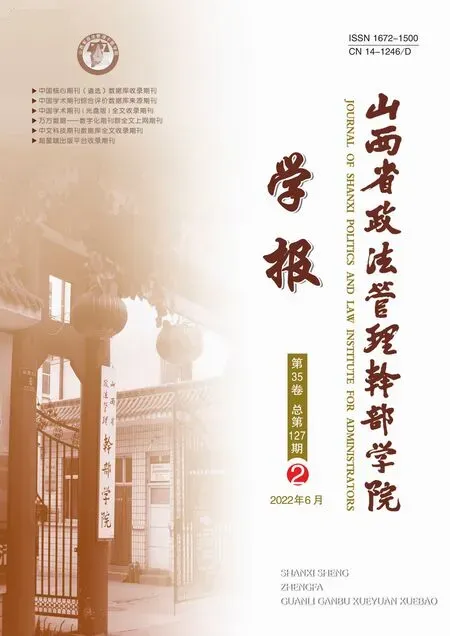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的完善
——以秦岭为例
2022-02-04王柏洪徐文勇
王 林,王柏洪,徐文勇
(1.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3;2.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检察院,浙江 金华 321000)
秦岭是一座自然生态之山,秦岭—淮河是公认的中国南北季风区分界线,秦岭还是中国植物区系的南北交汇地和世界动物地理上的东洋界和古北界的过渡带,狭义上的秦岭是限于陕西省境内的山脉。在执法监管方面,陕西省加大对涉秦岭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2019年至2020年11月,共侦办各类破坏秦岭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刑事案件73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95人,打掉犯罪团伙41个。秦岭有非常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其中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杀害、乱捕、乱猎野生动物不但严重损害秦岭的野生动物资源、破坏生态平衡,而且非法交易野生动物、滥食野生动物有造成病毒传播的危险,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更是会危害公共卫生安全。自2018年8月以来,陕西省查处秦岭区域乱捕乱猎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544只(件),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已由全面整治转为生态修复和常态化保护阶段。[1]笔者认为,秦岭生态环境特别是野生动物资源的常态化保护需要建立综合治理的机制,而综合治理机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建立和完善检察机关主导的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诉讼机制。
一、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现状
秦岭野生动物资源是国家所有的,它并不是任何个人的私有财产。乱捕、乱猎野生动物不但侵害了国家利益,而且由于生态平衡被破坏,最终也会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需要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一)检察机关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的角色定位
具体到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检察机关也要充分发挥其法律监督机关和公共利益代表的角色定位。一方面,监督相关行政机关履行其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定职责或者纠正其违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提起或者支持相关组织、机关提起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保护被损害的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而维护公共利益。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检察公益诉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需要进行扩大解释,不但包括检察机关自己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还包括支持相关环保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以及行政公益诉讼前的诉前检察建议。[2]虽然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和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是不同类型的检察建议,也要发挥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二)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
一项制度是否科学合理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其效能,野生动物保护的检察公益诉讼机制也要在野生动物保护的实践中不断进行修正完善。有学者统计,截止到2020年,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全国可查询的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共453件,其中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385件,占比94.5%;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为17件,占比3.75%;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7件,占比1.55%。[3]可见,上述三种类型的检察公益诉讼是不均衡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而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占比都非常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我们发掘导致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机制调整和完善。
陕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促进秦岭野生动物保护,积极和省秦岭办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信息平台对接、信息共享。截止到2021年7月,陕西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破坏秦岭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1件349人,起诉456件688人;受理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民事行政案件278件,提出检察建议237件;摸排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线索2791件,立案2675件,提出检察建议2542件,起诉141件,而且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检察监督专项活动。[4]近期,陕西省检察机关发布了9个秦岭生态保护检察监督典型案例,其中有3个是涉野生动物保护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到的罪名有非法猎捕、杀害、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和非法狩猎罪(依据2021年3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上述前2个罪名已经统一修改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虽然上述数据并没有将野生动物保护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情况单独列出,但是也能看出检察机关在保护秦岭野生动物资源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考察上述3个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都是要求被告人赔偿野生动物生态资源损失费和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而且对公益损害赔偿金的执行方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通,如果被执行人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赔偿金,可以采取劳务代偿的方式执行,也可以采取替代性修复的方式执行。
二、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存在的问题
(一)检察公益诉讼类型不均衡
从上文可以看出,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类型严重不均衡,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占比过大,而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的占比过小,这不利于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长远发展。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占比过多主要是因为发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有一定的便利性,民事公益诉讼是对刑事案件的再利用,由于公安机关前期的侦查工作,基本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证据也很确凿,解决了检察机关提起单独的民事公益诉讼过程中存在的案件线索发现难、固定证据难、损失鉴定难等问题。行政公益诉讼占比小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通过发放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行政机关纠正了违法行为或者积极履行了职责,没有必要再发动公益诉讼;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法治国家的建设机关,再加上检察机关的经费预算并没有完全独立,这些都会潜在影响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而检察机关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除了上文提到的“三难”问题,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组织也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是一个潜在的原因,诉讼主体的非唯一性也会限制检察机关的积极性。
(二)法律法规间存在衔接问题
规制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在国家层面主要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刑法》,其中《野生动物保护法》是综合性法律,主要为野生动物提供预防性保护;而《刑法》主要是惩治涉野生动物犯罪,在打击犯罪行为的同时震慑潜在的涉野生动物犯罪行为,起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作用。《刑法》中涉野生动物的罪名主要有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和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地方性法规层面,陕西省出台了《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西安市也出台了《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致力于保护秦岭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资源,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同时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做到安全和发展同步、协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为了从源头上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打击非法的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提高公共卫生安全的治理水平,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站在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制定《决定》的,特别强调总体国家安全中的生态安全、生物安全,而且以维护人民安全为宗旨。
(三)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互联网、自媒体等信息化工具和媒介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也不可避免给执法、司法带来新的要求,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要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创新办案手段,用高科技武装自己。在涉野生动物犯罪中,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寻找买主或者卖主,并且在互联网上完成付款等交易活动,再通过快递物流完成交付。互联网野生动物交易的隐蔽性给司法机关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行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利于司法机关发现犯罪分子和固定犯罪证据。
检察机关在智慧检务、科技检务方面还有待加强,特别是在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发现案件线索方面存在短板。在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中,野生动物的物种和保护等级鉴定以及生态损害鉴定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关系到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也关系到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公益赔偿金数额的确定。但是无论是保护等级鉴定还是生态损害鉴定都存在鉴定机构、鉴定专家缺乏和鉴定费用昂贵等问题,“鉴定难”也是需要检察机关急切解决的时代难题。
三、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的完善
野生动物保护的常态化要求保护机制化、制度化,而不能是短视化、运动式。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机制要求处理好野生动物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二者只有均衡协调发展,野生动物保护才能可持续发展。
(一)构建野生动物保护大安全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看待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时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野生动物保护关涉到总体国家安全中的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也要构建野生动物保护的大安全格局。要用系统的思维考虑野生动物保护,避免孤立地看待野生动物保护问题。
1.建立野生动物保护治理共同体。建立治理共同体是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治理主体上的要求,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机制也要求贯彻治理理念、构建治理共同体。检察机关发挥其法律监督和公共利益保护的作用,不但要和行政机关协作,加强执法和司法的衔接,形成保护合力;还要积极让广大民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强化民众保护野生动物的主人翁意识,通过案件办理,积极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增强民众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意识。鼓励公众通过“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举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邀请公众参与重大案件的听证,完善听证制度,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公益组织协作。[5]例如,在秦岭野生动物保护中,陕西省检察机关积极和省秦岭办、发展改革部门、资源规划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城市管理部门等部门开展合作,建立合作平台,并且自觉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深入推进秦岭野生动物保护。
2.平衡野生动物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很好诠释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同样也可以适用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安全格局是综合安全、均衡安全和共同安全,[6]平衡野生动物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平衡安全和发展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没有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就无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而没有经济社会发展就无法为野生动物保护提供经济基础。因此,在这种大格局理念的指引下,要消除人和野生动物的对立,人和野生动物要和谐共生,要让民众特别是野生动物保护地的民众认识到,通过保护野生动物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而通过杀害、猎捕野生动物获取经济利益是最低劣的方式。例如,陕西省建立秦岭大熊猫国家公园,同时发展生态旅游,实现了生产生活和生态保护的“双收益”就是成功的案例。[7]此外,损害野生动物资源公益赔偿金的执行方式要灵活多变,考虑到涉野生动物犯罪的犯罪人很多经济状况不太好,如果机械地执行公益赔偿金,一方面达不到目的,另一方面对生态修复来讲也不是最佳方案。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因素,不能因为执行公益损害赔偿金导致犯罪人致贫返贫,应该积极引入替代性修复和劳务代偿等替代方案,达到既教育了违法犯罪行为人又修复了被破坏的野生动物资源的效果。
(二)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间的衔接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间的衔接主要是协调《野生动物保护法》《刑法》和《决定》的关系,合理解释三者不一致的地方,形成合理、科学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由于立法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不同,再加上立法技术的限制,调节同一类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可能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情况。由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范围只限于“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以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总体来说被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范围是比较窄的,这和立法时我国的国情是相适应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再加上滥食野生动物成为一种很流行的陋习,而且滥食野生动物有很大几率引发公共卫生风险,有必要在立法上保护一般的野生动物,同时用法律手段打击非法交易和滥食所有野生生物的行为。考虑到上述情况,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笔者认为,应当加强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法律法规间的衔接。立法上的变化,不可避免会影响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要顺应立法变化和民意变化。检察机关要扩大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将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作为检察法律监督的重点对象,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以及发放检察建议的形式革除民众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
(三)均衡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类型
要改变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占比过大,而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占比过小的现状,检察机关就要在均衡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类型上下功夫。一方面,检察机关要积极主动探寻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线索,发挥司法检察权的能动性。检察机关的职能具有很强的主动性,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机关需要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司法检察权的能动性有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8]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部门要和刑事检察、民事检察和行政检察部门建立沟通机制,充分发现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线索。除了在内部发现公益诉讼线索,检察机关还要主动出击,深入实地进行调查,获取一手线索资料,牢牢掌握公益诉讼线索获取的主动权。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要对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转变观念,要克服为难情绪,改变不敢监督的局面,在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程序无法实现法律监督目的的情况下,要果断提起行政公益诉讼。[9]
关于民事公益诉讼,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定,除了检察机关外,法律规定的其它机关、组织也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可以提供支持,而且还规定检察机关要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需要履行告知或者公告程序,只有在没有合适原告或者原告放弃起诉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10]法律如此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适格原告的诉讼权利,同时考虑到民事公益诉讼“不告不理”的私法自治原则。但是,侵害了公共利益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私事”,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进而破坏生态平衡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因此也不能再一味地坚守“不告不理”原则,检察机关要发挥其职权的能动性,主动作为,主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没有必要再履行诉前公告程序。笔者主张将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权收归检察机关独有,权利受到侵害的民众有申请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一方面,权利过于分散不利于集中优势资源,而且民事公益诉讼耗时耗力,动物保护组织等环保组织在物力、人力、调查权等方面和检察机关相比并不具有优势,这些也导致它们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笔者通过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法律规定的机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例极少,这本身也是对权利的浪费。
(四)创新野生动物保护互联网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保护互联网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针对行为人利用互联网作为工具交易野生动物作出的应对举措,也是检察机关紧跟时代发展、自我变革的体现。由于利用互联网作为违法犯罪工具,传统的犯罪行为地、犯罪结果地很难被清晰地界定,再依靠传统的诉讼体制就无法实现法律监督的目的。我国在杭州等地设立了互联网法院,而设立互联网检察院也在调研论证中。考虑到利用互联网交易野生动物的行为越来越普遍,检察机关需要积极向互联网法院提起野生动物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同时思考设立互联网检察院的可能性,合力打击野生动物互联网交易行为。[11]
(五)充分发挥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的作用
除了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检察建议还包括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检察建议、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要达到保护野生动物的目的,不但要适用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还要发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办理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或者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发现相关行政机关在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监管漏洞,则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要求其弥补监管漏洞,最终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形成野生动物保护的长效机制。在2021年7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公布的9件秦岭生态保护检察监督典型案例中,案例四“眉县检察院诉王某甲等6人非法猎捕、杀害、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指出,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监管漏洞,眉县人民检察院向眉县林业局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建议其分析、掌握辖区内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情况,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协调相关单位共同做好林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的推动下,眉县建立了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制度及网格化巡护制度。[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