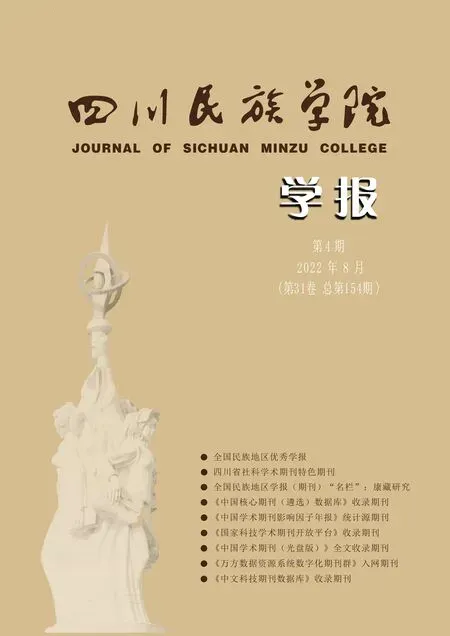《围城》英译本中的“非强制明晰化”翻译技法研究
2022-02-04何爱琳
何爱琳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00)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现代中国小说的代表之一,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围城》这部作品令人愉悦,是精心创作而成的,或许可谓最伟大的一部作品[1]441。《围城》的英译本Fortress Besieged是珍妮·凯利(Jeanne Kelly)以及茅国权(Nathan K. Mao)合作翻译而成的,自1979年在美国首次出版以来,该译本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并得到了广泛研究。比如,从整体角度出发,学者孙艺风探讨了《围城》英译本中存在的问题[2]。而具体来看,也有不少学者从翻译理论、文学理论、语言学、符号学等多个角度出发,研究了《围城》英译本中的幽默翻译、修辞手法、文化、注释等。虽然如此,却少有学者讨论《围城》英译本中频繁出现的明晰化翻译技法(explicitation)。因此,为丰富现有相关研究,本文对《围城》英译本中的“非强制明晰化”(optional explicitation)翻译技法展开了描述性翻译研究(DTS),希望能为中国现代小说或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译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走出国门的《围城》
《围城》是文学研究家、中国现代作家钱钟书先生的著名作品之一。该作品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风格独特,讲述了男主人公方鸿渐留学回国后的故事,展现了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像。上文已提到,夏志清曾于1961年在自己的作品中高度评价《围城》,这使得以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3月版为模板的《围城》盗版在海外大受欢迎,《围城》因而也在国外受到了关注和研究,被各国引进并翻译[3]65。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围城》多个语种的译本陆续出现。其中,英译本Fortress Besieged的底本正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3月版《围城》[3]66,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于1979年首次出版。该译本由珍妮·凯利完成初稿,后由茅国权进行修订。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称赞凯利和茅国权的译本充满活力、清晰明了,有时还很浪漫,并认为该译本将立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4]。截至2021年10月12日,《围城》英译本 (New Directions版本)在全球最大的图书推荐网站goodreads.com上得分为4.30分(满分为5分)。不难看出,Fortress Besieged是成功的。
二、非强制明晰化翻译技法
“明晰化”(explicitation)这一术语是法国语言学家让-保罗·维奈(Jean-Paul Vinay)和让·达贝尔内(Jean Darbelnet)提出的,指的是一种文体翻译技法,即译者可根据语境或相关情况获取源语中隐含的信息,并在目标语中将其明确[5]。非强制明晰化(optional explicitation)则是匈牙利罗兰大学语言学及翻译研究教授金加·克劳迪(Kinga Klaudy)划分的明晰化类型之一。根据克劳迪的描述,非强制明晰化取决于语言间文本建构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若译者不使用非强制明晰化,目标语语句的语法仍然正确,但译文在整体上会显得笨拙且不自然[6]。换言之,非强制明晰化体现了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一种自我选择。 学者卡丹斯·塞吉诺特(Cadance Séguinot)指出明晰化在翻译中可以三种形式存在,分别是(1)译文表达了原文未表达的信息;(2)原文暗示的信息或原文中需要通过预设来理解的信息在译文中得到了明确表达;(3)通过聚焦、强调或词汇选择,原文中某信息在译文中更加受到重视[7]108。由于非强制明晰化是明晰化的一种类型,故也适用于这三种形式。
三、《围城》英译本中的非强制明晰化
《围城》英译者在翻译中频繁运用了非强制明晰化翻译技法。通过比对《围城》的原文和英译,本文对《围城》英译本中的非强制明晰化情况进行了举例分析,并探讨了译者使用这些非强制明晰化的动机。
(一)非强制明晰化译例
一是文化负载项层面。《围城》原文中有不少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比如习语、成语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这些内容的含义进行了解释,而非照搬其字面意思:
“准备碰个软钉子(1)文中划线部分为译者运用非强制明晰化之处。。”[8]23
“he braced himself for a polite rebuff.”[9]27
译例原文中的“软钉子”即为一俗语,而“碰软钉子”便指某人遭到了他人的婉拒。译者在译文中将其译作“a polite rebuff(礼貌的拒绝)”,对该俗语的语义进行了明晰。
二是口语化表达层面。译者同样运用了解释的方法,通过将被明晰对象替换为解释性内容,明确了原文口语化表达在语境中的语用含义:
“拿我的去,拿去,别推,我最不喜欢推。”[8]25
“Here, take mine. Go ahead and take mine.I hate being refused.”[9]30
该译例来自重要角色苏文纨和主人翁方鸿渐之间的互动。方鸿渐正在用自己的手帕擦手,而苏文纨见其手帕卫生状况欠佳,便立即将自己的手帕予其使用,并说出了该译例的内容。而从苏文纨这句话也可看出,方鸿渐做出了将手帕推回的动作,表明了其拒绝的态度。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这一场景将苏文纨此处的口语化表达替换为了“I hate being refused(我不喜欢被拒绝)”,解释并明晰了该表达在所处语境中的语用含义。
三是文字游戏层面。文字游戏是《围城》文本的一大特点,译者运用了补充的方法,通过在译文中补充少量信息,向目标语读者突出展示并解读了作者所设置的文字游戏:
“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8]190
“Heretofore,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lay in ruling the country and pacifying the land; now ruling the country and pacifying the land lies in the Way ofthe University (literally, great learning)”[9]2
可以看出,译者在准确翻译该译例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添加括号对“the University(大学)”进行了补充说明,用“literally(照字面含义)”一词表示“the University”和“great learning”在汉语中的字面表达是一致的,均为“大学”,因此向目标语读者明晰了原文作者在此处设置的文字游戏。
四是逻辑关系层面。英文以形合为特点,而中文以意合为特点。在中文中,分句之间或许不存在任何连接词,但在语义上却有着因果、转折等逻辑关系。《围城》的英译者注意到了这一点,通过补充连词以及改变原文语句的顺序凸显了原文的逻辑关系:
“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8]2
“Relying on man′s ingenuity and entrusted with his hopes, but loaded with his clutter”[9]4
该译例原文由三个分句构成,第一个分句和第三个分句均为褒义,而第二个分句则为贬义。译者在译文中调换了这三个分句的顺序,将同为褒义的第一个分句和第三个分句并列,而将贬义的第二个分句置于了句末,且在第二个分句前补充了连词“but(然而)”以突出其相反的感情色彩,故也明晰了其与另外两个分句之间转折的逻辑关系。
上文已提到,塞吉诺特认为明晰化有三种形式,而以上四个层面的非强制明晰化即可被归于第二种形式——原文暗示的信息或原文中需要通过预设来理解的信息在译文中得到了明确表达[7]108。也就是说,文化负载项、口语化表达暗含的意义在译文中得到了明确表述,文字游戏的设置被直接展示于译文中,隐藏的逻辑关系得到了显现。
除以上内容外,《围城》英译中的非强制明晰化翻译技法还存在于多语言层面。在《围城》原文中,中文和英文在某些场合下同时出现,译者在译文中将原文的英文部分变为了斜体:
“Sure!值不少钱呢,Plenty of dough。”[8]41
“Sure! Worth quite a lot of money,plenty of dough. ”[9]48
在该译例的原文中,“sure(当然)”和“plenty of dough(很多钱)”均为角色在用中文交谈时夹杂的英文,译者在译文中将这两处的字体更改为了斜体。加布里埃拉·萨尔达尼亚(Gabriela Saldanha)认为在译文中添加强调性的斜体表示着“a tendency to facilitate readability”[10]30(一种易于阅读的倾向),而安奈利·阿德尔(Anneliedel)则将斜体和黑体这类排印标记视为“元话语(metadiscourse)”,用于提供额外含义[11]28。译者此举起到了强调与提醒的作用,帮助目标语读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语言,辅助了目标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最后是角色内心独白层面。译者再次使用了改变字体的策略,以提醒读者斜体部分为角色的内心活动而非口头的言语表达(这一点与上述多语言层面的非强制明晰化相同,故相关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晚饭后翻看的历史教科书,影踪都没有了。该死的教科书,当学生的时候,真亏自己会读熟了应考的!”[8]36
“but as for the history textbooks he had skimmed through after dinner, there wasn′t even a trace left.Those confounded textbooks! It′s amazing that I could have learned all that stuff for examinations when I was a student! ”[9]42
同样基于塞吉诺特的“明晰化三形式”理论可知,多语言层面和角色内心独白层面的非强制明晰化均属于第三种形式,即通过聚焦、强调或词汇选择,原文中某信息在译文中更加受到重视[7]108。译者通过改变字体对部分译文进行了强调,使读者能够重视原文的相应信息。
(二)译者运用非强制明晰化之动机
克劳迪与另一位学者克里斯汀娜·卡罗伊(Krisztina Károly)曾在她们的共同研究中表示明晰化通常是翻译策略(translation strategy)的结果[12],而翻译策略指“an overall orientation of the translator”[13](译者的总体目标),比如采用意译或直译、使用归化或异化等。换言之,正是译者的翻译策略决定了其在目标语文本中使用明晰化翻译技法的行为。
因此,要探寻《围城》英译者运用非强制明晰化之动机,需先了解其翻译策略(即总体目标)。本文借助了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的“翻译规划(translation project)”理论模型以展开讨论。贝尔曼认为,“翻译规划”可被视为翻译所携带的明确目的,研究者不仅需要通过阅读译文对其进行分析,还应参考译者参与的副文本[14]。
在《围城》英译本的译者序中,译者表明希望该译本能激发人们对钱钟书及其作品更浓厚的兴趣,这句话足以视作《围城》英译本的“翻译规划”或明确目的。因此,为了达到该目的,《围城》英译者需在总体上采用以目标语读者为导向(TL reader-oriented)的翻译策略,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需求。
《围城》英译本的目标语读者由不同群体共同组成。学者余承法在其研究中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并总结道,《围城》英译本已被世界各地不同等级的图书馆收藏,如社区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由此可知,《围城》的目标语读者群是包括普通读者的,不仅仅只有学者、专家等专业人员[15]。而在《围城》英译本的前言和后记中,小说的背景和作者钱钟书都得到了详细的介绍,因此可以推断,《围城》英译本更精确的受众为普通目标语读者,因为对目标语专家学者(如海外汉学家或“钱学家”)来说,这些信息已为他们悉知,译本大可不必再大费周折对其作出详尽介绍。
因此,既然《围城》英译本主要针对的是普通目标语读者,那么译者则需运用非强制明晰化的翻译技法来达到其“翻译规划”,即产生一篇“照顾”普通目标语读者的译文。具体来讲,译者使用非强制明晰化翻译技法以达到以下目的。
一是确保普通目标语读者对原文的基本理解。语际翻译跨越两种不同的文化,而原文中与源语文化相关的内容往往给目标语读者造成阅读障碍,根据塞吉诺特的观点,这些内容通常是暗示性的,或需要借助预设来理解。一些非强制明晰化(如文化负载项明晰化)则可通过提供最少量的信息,使读者即使不清楚语义含义,也能理解词项的功能[10]26,为普通目标语读者理解原文提供了保障。
二是进一步优化普通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在保证普通目标语读者对原文的基本理解后,或扫清了源语文化造成的障碍后,译者所使用的非强制明晰化也使得部分原文内容在译文中更合乎逻辑、易于理解。例如,逻辑关系明晰化使译文较原文拥有了更突出的逻辑关系,而口语化表达明晰化则直接向普通目标语读者展示了这些内容在原文语境中的实际含义,使得原文更易于理解。
三是保留原作者打造的语言效果。《围城》中的诙谐语、双关语等是该作品的显著特点之一,形成了一定的语言效果。然而对于翻译来说,夏志清承认,译者无法在目标语中找到相应的诙谐语和双关语使原作的喜剧性篇章保持生动[1]459,也就是说,原文中的诙谐语和双关语对翻译造成了难点,翻译很难保留其幽默的效果。而《围城》英译者所使用的相关非强制明晰化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比如通过文字游戏明晰化解说原作者设置的文字游戏,即可让普通目标语读者体会到其趣味性。
四、结语
《围城》英译者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在翻译过程中针对原文的不同层面,通过解释、补充、调换译文语句顺序、更改相关译文字体的方法使用了非强制明晰化翻译技法。这些非强制明晰化翻译技法分别存在于文化负载项层面、口语化表达层面、文字游戏层面、逻辑关系层面、多语言层面,以及角色内心独白层面,且可基于坎迪斯·塞吉诺特的“明晰化三形式”理论进行分类。两位译者使用非强制明晰化翻译技法的动机则与其以目标语为导向的翻译策略有关,他们需借助非强制明晰化翻译技法以产生一篇适合普通目标语读者的文章,并引发人们对钱钟书及其作品的兴趣。
此外,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而本文的研究发现也可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外译提供一些启示。比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除了顾及源语与目标语的语言表达差异外,还应充分考虑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此外,译者可根据自己的翻译策略针对原文不同的场景适当采用恰当类型的明晰化翻译技法。最后,一部作品可由目标语译者和源语译者共同完成,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也可积极向权威学者乃至原作者本人征求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