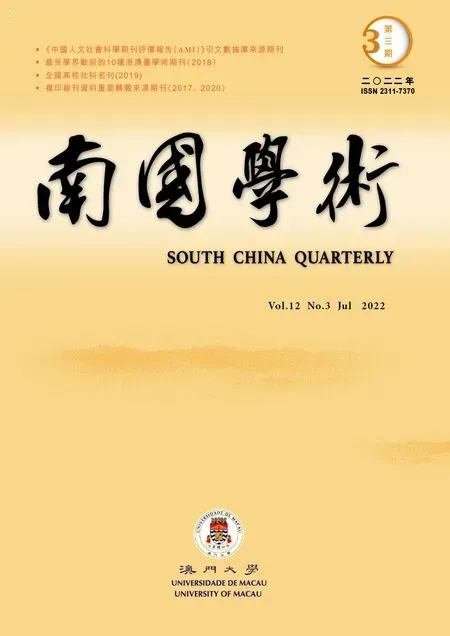“休閑”中的文化記憶
——以日本的“花見”爲例
2022-02-02王曉葵
王曉葵
[關鍵詞]休閑 文化記憶 花見 日本文化
引言
一般意義上的“休閑”指兩個方面:一是解除體力上的疲勞,獲得生理的和諧;二是贏得精神上的自由,營造心靈的空間。因此,“休閑”的本質特徵應該是“自在、自由、自得”①潘立勇:“休閑與審美——自在生命的自由體驗”,《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6(2005):6。。從這個意義來說,與人類其他活動相比,休閑是最具個體性選擇自由的行爲。但是,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其一切行動都受到所處社會文化環境的制約以及傳承文化的影響。休閑自然也不例外。無論是遊戲、觀光、藝術鑒賞,還是收藏、交際、度假、節慶活動,都是在具體的時空中通過身體行爲實現的。在近代,具有國族認同的“均質的國民”的生產,成爲民族國家成立的基礎。這個過程中,“休閑”“娛樂”也被作爲塑造“國民精神”“國民性”的一環,納入到社會管理的環節中。具體來說,國家權力與知識精英通過對休閑空間的營造、文藝作品的改編和再詮釋、儀式活動的編成等方式,將民衆的“休閑”轉換成道德教化與國族認同養成的場域。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編著的《記憶之場》一書中,將“埃菲爾鐵塔”“三色旗(國旗)”“七月十四日(國慶日)”等法國人耳熟能詳的物體、時間等作爲考察對象,分析了它們成爲喚起“法蘭西的”記憶表象物的建構過程。他將這些物體、紀念日等定義爲“記憶之場”。這裏的“場”,並非是專指物理空間的場所,而是社會共同體集體記憶的所繫之處。這些自然的和人工的創造物,被通過紀念、彰顯以及教科書等權威性文本的編制、誦讀、觀劇、巡禮等日常娛樂活動,成爲建立國族認同的文化資源。無獨有偶,美國日裔文化人類學家大貫惠美子在其《殺人花》(Flowers That Kill)一書中,分析了日本的櫻花、歐洲的玫瑰,這些被作爲美、友愛、鄉土情感的象徵而受到人們喜愛的植物,經過政治權力的操弄,變成促使人們爲國家和理念而獻身的政治宣傳工具。大貫特別強調政治的象徵意義的把握,如櫻花成爲權力象徵的同時,櫻花的消散也用來表示權力的喪失。在歐洲,玫瑰象徵愛與純潔,其凋落的景象象徵死亡。而抵抗納粹的“白玫瑰”,則成爲反體制運動的表象。
大貫在她的另一部著作《神風敢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歷史上美學的軍國主義化》一書中分析了櫻花是如何由自然物轉變爲政治民族主義的象徵符號的歷史脈絡。大貫特別強調,雖然在個體和集體的層面,櫻花成爲日本人自我的表徵,但是象徵主義不能被看作是一個封閉的表徵場域。相反,每一個櫻花的概念表徵,如死亡,都在時間中經歷持續的變化,社會行動者會根據不同的情境賦予櫻花不同的意義。②[美]大貫惠美子:《神風敢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歷史上美學的軍國主義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石峰譯,第22、26~27頁。
大貫用“歷史化”(historicizing)這個概念推進了巴特(R. Barthes, 1915—1980)、布迪厄(P. Bourdieu, 1930—2002)、福柯(M. Foucault, 1926—1984)使用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對“文化任意性”(cultural arbitrariness)的理解。她通過對日本的櫻花表象史的梳理,提出了“再造傳統”“美學化”“象徵誤識”這三個促進象徵自然化過程的機制。大貫認爲,“再造傳統是社會行動者共同使用的一個策略,目的是希望提供一個被更改過的文化制度來作爲‘我們出自遠古的傳統’,以使民衆把它當作‘自然’來接受”。她還進一步指出,單純創造傳統是不夠的,還需要“從視覺和概念上使文化實踐和象徵顯現變得美麗的過程”。也就是說,“美學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爲,“美”會很容易導致“誤識”,“社會行動者未意識到,他們正從同一個象徵符號讀出了不同的意義”。大貫的核心觀點是,這種無意識的“誤識”,會使象徵符號和意義之間被操控。③[美]大貫惠美子:《神風敢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歷史上美學的軍國主義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石峰譯,第22、26~27頁。
本文在接受上述論點的基礎上,試以“花見”爲例,進一步討論“花見”這個“遠古的傳統”在被創造出來的時候,所需要的“資源”“過程”是什麽?因爲,雖然這個“傳統”是“再造”的,但是,要想社會行動者的大多數人接受這個“傳統”,並認同它是“我們的”,則絕非“無中生有”可以做到的。而最爲有效的方式,是通過挖掘一個民族的“過去”,將其塑造成一個從古到今、連綿不斷,而且是“獨有”的記憶。這種通過文化符號建構起來的意義系統,記憶理論學者阿斯曼夫婦使用“文化記憶”這個詞來表述。“文化記憶”指所有通過一個社會的互動框架指導行爲和經驗的知識,都是在反復進行的社會實踐中一代代地獲得的知識。①陶東風 (執行)、周憲 主編:《文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11輯,第2頁。換言之,人類爲了長久保持特定的價值和意義,將帶有個人體驗的鮮活的記憶,轉化成一種“由媒介支撐的記憶,這種記憶有賴於像紀念碑、紀念場所、博物館、檔案館等物質的載體”②[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第6頁。。關於文化記憶的特点,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指出:“在個人那裏,回憶的過程往往是隨機發生的,服從心理機制的一般規則,而在集體和制度性的層面上,這些過程會受到一個有目的的回憶政治或曰遺忘政策的控制。由於不存在文化記憶的自我生成,所以它依賴於媒介和政治,從生動的個人記憶到人工的文化記憶的過渡卻可能產生問題,因爲其中包含着回憶的扭曲、縮減和工具化的危險。”③[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第6頁。因此,對“花見”的文化分析,不僅是一般意義的娛樂方式研究,也是文化政治研究的一部分。
一 何謂“花見”
所謂“花見”,是日本人春天櫻花盛開的時候賞櫻的休閑活動。其歷史久遠,《日本風俗史事典》專設“花見”詞條:
在我國,“花”單用的時候,一般指櫻花。“花見”作爲春天最盛大的娛樂活動,有悠久的傳統。《萬葉集》中就有很多相關的詩文,在平安時代已經成爲詩與和歌的好題材。平安貴族們“花見”的樣子,在繪卷和繪畫中多有表現。賞櫻的時候“鷹狩”“櫻狩”等活動也蔚成風氣。從那時起,吉野山就成爲觀櫻的勝地,被描繪在屏風上,並出現在西行的和歌而聞名天下。鐮倉時代之後,從吉野移植了櫻花,嵐山成爲觀櫻的勝地。……足利義政1468年(應仁二年)在花頂山、大原野舉行的“花見”,極盡華美奢靡,名滿天下。豐臣秀吉於1594年(文祿三年)的古野花見,1598年(慶長三年)的醍醐花見,都以豪華絢爛留名於世。從桃山時代到江戶時代,“花見”逐漸在庶民中普及。與都市較早就娛樂化的傾向相比,農村更多與三月節、四月八等初春的節日相配合,人們到山野遊玩,賞花摘花,也被稱爲“花見正月”,作爲農耕儀禮來舉行。④日本風俗史學會 編:《日本風俗史事典》(東京:弘文堂,1994),王曉葵 譯,第526~527頁。
可見,“花見”是日本人欣賞櫻花的習俗,歷史悠久,而且從單純的出外觀賞自然生長的櫻花,發展成爲創作歌頌櫻花之美的詩文,以及成爲屏風和繪卷繪畫的題材;進而與節日、節氣結合,成爲人們生活習慣的一部分。
“花見”的習俗,從現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比如,日本從最南端的沖繩到最北端的北海道,都有“花見”勝地。每年到了三四月的花季,日本電視臺播放的天氣預報中除了報告天氣狀況之外,還會告知“櫻花前綫”的位置,也就是櫻花開放的地點由南往北推進到了什麽地方。對於日本人來說,“花見”是他們一年休閑生活中最爲隆重的節目。據說,在4月份,公司新職員報到後的第一項任務,是爲公司前輩們到公園櫻花樹下佔位。在日本人心目中,櫻花與日本文化、日本式審美、日本精神融爲一體,成爲日本表徵的代名詞。“花見”的名所,很多是全國知名的觀光勝地,如東京的上野公園、京都的嵐山、名古屋的名城公園等;而各地的神社、寺院、公園、古城、河岸等,也往往是當地住民的“花見”之處。“花見”時節,這些名所張燈結綵、遊商雲集,猶如中國的廟會。家人、朋友、同事或在花下鋪席佔地、宴飲聊天,或者遊走花樹之間,品嘗各種美味小吃,帶孩子撈金魚、玩彩燈,其樂融融。春天的“花見”和秋天的賞紅葉,是日本春秋兩個重要的休閑娛樂活動。
在“花見”時,人們還喜歡穿和服,和服的色彩和花樣也多迎合春和日麗的季節,明朗而華美,櫻花的圖案也不少見。除了服裝之外,日本的繪畫、和歌、演歌、俳句、雕刻等藝術中,櫻花是必不可少的題材。日本人生活與櫻花的關係,還滲透到語言中。日本諺语中有“花より団子”一句,字面意思是說:“與衹能看的櫻花相比,能吃的糰子更實惠。”比喻追求實惠的心理。櫻花盛開的三四月份,也是日本舊年度結束、新年度開始的時節。學校開學,公司新人入社,很多迎新的活動都是與“花見”結合在一起的,代表着新年度的新人新氣象。甚至有傳說說,本來爲了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學制統一,日本也曾將新學年開始時間改到9月份,但沒有持久,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人無法接受在“花見”之外的季節履新。
總之,一方面,“花見”是當代日本人重要的休閑活動之一,是日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的歷史悠久,在日本的文化心理中有深厚的積澱。這兩者的並存,爲“花見”文化記憶的建構提供了前提。
二 “花見”習俗的形成
櫻花的象徵意義深入日本人心的歷史過程,早有日本人關注。1931年5月,山田孝雄出版了一本叫《櫻史》的書。有關此書的內容和性質,作者在序言中寫道:
櫻花是我國國民性情的表徵,外國雖然也有這類植物,但是我們大和櫻之美,冠絕於世。此花對我國國民的心性的薰陶涵化之功不可估量。如果說在我國櫻花古已有之,那麽,櫻花在國史中留下了哪些記載和痕跡?將朝日下盛開的山櫻比作敷島的大和魂,是如何在國民的意識中形成的?“花數櫻花,人數武士”的諺語,如何流傳至今而經久不衰?啊,櫻是我們大日本國須臾不可分離的花。要瞭解我國的國民性,與其去窮理索文,不如體會日本人爲什麽對朝日下盛開的山櫻充滿摯愛。瞭解這一點,就會得到正確的結論。最近,“國花”成爲流行語。大家都說,櫻花是我們的國花。但不可忘記的是,“國花”這個詞對我們意義遠遠比外國來得緊密。①[日]山田孝雄:《櫻史》(東京:講談社,1990),第19頁。凡涉及該書文字,均由王曉葵翻譯。
由上可知,在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社會中,櫻花已經與日本“國民性情”“大和魂”“國民意識”“國民性”有了關聯。撰寫《櫻史》的目的,就是要將一個植物如何成爲日本民族的象徵符號的過程講清楚。
這本《櫻史》將日本歷代詩文中關於櫻花的表述,分爲上古、中古、近古、中世、近世(卷一)、近世(卷二)、現代七個時期,並且與櫻花有關的著名事件、著作、愛櫻人士、櫻的品種等內容作了介紹,可視爲關於櫻花文獻的集大成者。爲了更直觀地瞭解櫻花是如何成爲日本表徵的文化記憶的,這裏依據《櫻史》提供的史料,對其從“花宴”到“花見”的歷史過程作一梳理。
櫻花本來生長在野外,人們到山野中賞櫻,也是非常自然的,由此誕生了很多有名的賞櫻勝地,如關西地區的高園山、香具山、佐紀山、佐保山、龍田山等。在日本文學的古典《萬葉集》中,有人用“越過龍田山,映入眼簾的櫻花何其絢爛”,“掐算好今天定能看到山頂盛開的櫻花,果不其然。大喜過望”等詩句,表達在野外看到櫻花的喜悅之情。這些山的名字,也隨着《萬葉集》等作品經典化而逐漸爲日本人所熟知。
人們喜愛山野的櫻花,自然會想將其移植到庭院之中。《萬葉集》第八卷中,刊載了一位王侯寫給心愛的人的和歌:“你移植過來的櫻花,今年定會盛開吧?但想到櫻花被松風吹落,心痛不已。”奈良時代的天平年間(729—749),有位官員在自家院中移種了櫻花,後來他轉任他方,原來住處的朋友寫了三首和歌給他,其中一首《屬物發思》寫道:“您早前移種到牆根的櫻花,已經含苞欲放。賞花時節,睹物思人,君尚安否?”①[日]山田孝雄:《櫻史》,第39~40、252頁。
大量史料表明,在平安、奈良時代,不僅僅是私家,就是宮廷、寺院的庭院中,也逐漸有了櫻花的身影。例如,平安時代,皇宮內紫宸殿便有櫻花。《三代實錄》貞觀十六年(874)八月條記錄:“二十四日庚辰。大風雨,折樹發物,紫宸殿前櫻,東宮紅梅,侍從局大梨等樹木有名皆吹倒。”說明當時櫻花、梅花、梨花並存於宮中,也說明當時櫻花尚未獨佔鰲頭。這也可以從《續日本後記》承和十二年(845)二月的條記中得到佐證:“庚寅朔,天皇御紫宸殿賜侍臣酒,於是攀殿前之梅花插皇太子及侍臣等頭爲宴樂。”在皇宮中,距離紫宸殿不遠處的清涼殿也有櫻花種植。被後世奉爲學問之神的菅原道真②菅原道真(845—903):日本平安時代中期公卿,學者;877年,任貳部少輔,並爲文章博士,深得宇多天皇、醍醐天皇的信任和重用;901年,因左大臣藤原時平讒言於天皇,被貶爲大宰權帥,調往僻遠之地,不久死於貶所;編著有《類聚國史》《菅家文草》《新撰萬葉集》《日本三代實錄》等。曾作文介紹:
承和之代,清涼殿東二三步有一櫻樹,樹老代亦變,代變樹遂枯。先皇製曆之初,事皆法則承和,特詔知種樹者移山木備庭實。移得之後,十有餘年,枝葉惟新,根莖如舊。我君每遇春日,每及花時惜紅豔以敍叡情,玩熏香以迴恩盻。③[日]菅原道真:“春惜櫻應制”,轉引自《櫻史》,第47頁。
可知從山中將櫻樹移入宮中,花開季節賞花怡情,在平安時代已經開始成爲王侯們的習慣。
《櫻史》一書認爲,櫻花取代梅花獨步天下,應該始於宮廷內“花宴”的普及。所謂“花宴”,就是一邊賞櫻一邊賦詩作賦的宴飲。由嵯峨天皇首創,《日本後記》弘仁三年(812)二月條記載:“辛丑,幸神泉苑覽花樹。命文人賦詩賜祿有差。花宴之節始於此矣。”有很高漢學教養的嵯峨天皇也曾在花宴上賦櫻花詩:“昔在幽岩下,光華照四方,忽逢攀折客,含笑宜三陽。送氣時多少,乘陰複短長。如何此一物,擅美九春場。”④《淩雲集》,轉引自《櫻史》,第50頁。
在平安時代(794—1185),由於天皇的愛好,賞櫻儼然以成風氣。吉野的山櫻,奈良的八重櫻,均已成爲賞櫻的勝地,而公卿貴族也爭相模仿皇家做法,在家中種植櫻花,由此,山野,宮廷,寺廟,家中,賞櫻的空間無處不在。到了江戶時代,“花見”的場所大爲增加。記錄京都一年中每月每日之活動、風俗的書籍《日次紀事》卷三對京都的賞櫻勝地有詳盡介紹:
凡春三月有櫻花處,東方則白川、吉田、黑谷、若王寺、禪林、粟田口、神明山、山科、毘沙門堂、知恩院、丸山、安養寺、長樂寺、東漸寺、雙林寺、祇園寺、建仁寺、觀勝寺、高臺寺、靈山正法寺、清水寺、大谷勝久寺、若宮八幡、豐國山;南方則泉湧寺、稻荷、深草、藤杜、墨染寺(有墨染櫻)、宇治平等院、同興正寺、同白川金玉山;洛西南,壬生寶幢寺、遍照心願、東寺、久我、雞冠木、向日明神、粟生光明寺、大原勝持寺、世所謂花寺是也,小鹽山、三鈷寺、善峰寺、西鹽倉金藏寺、山崎、離宮及寶積寺、石清水八幡;西山則北野、平野、鹿苑寺、真如寺、等持院,龍安寺、妙心寺、御室仁和寺、鳴瀑妙光寺、福王寺、三寶寺、栂尾、槇尾、高雄、月輪山、愛宕山、嵯峨清涼寺、小蒼山二尊院、往生院、三寶院、大覺寺、野宮、天龍寺、寶幢寺、臨川寺、三會院、法輪寺、嵐山、千光寺、太秦廣隆寺、法金剛院、梅津長富寺、西方寺、松尾;北山則下賀茂、松崎、山鼻一乘寺、修學寺、赤山、長谷、花園、岩倉、八瀨、大原、鞍馬、鬼船、嚴屋、上賀茂、西賀茂、鷹峰、千本。其中,一重櫻花以知恩院爲最;八重櫻,仁和寺、清水寺、大谷高臺寺爲壯觀。凡每年清水寺堂前八重櫻花與和州吉野一重櫻開落同時,是寒暄異處故也。南都春日社並八幡宮、興福寺、東大寺櫻,今年爲觀。⑤[日]山田孝雄:《櫻史》,第39~40、252頁。
從上述地名來看,寺院據大多數。由於佛教在日本近世的巨大影響,寺院是幾乎所有日本人生老病死不可不去的地方。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祈福禳災,以及諸如夏季的盂蘭盆會等重要的民俗活動外,都與寺院密不可分,而喪事也通常是由寺院主持操辦。因此,在寺院植櫻,營造出日常生活中賞櫻的自然環境,可以看作是櫻花進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一個標誌性結果。
在江戶時代(1603—1867)的京都、江戶,“花見”已經從上流社會普及到民間。《日次紀事》有如下記載:
凡京俗,春三月每花開,良賤男女出遊,是稱“花見”。其時多新製衣服,俗謂“花見小袖”。男女每出遊,必折花枝而歸。市中兒童追跡而慕之,各高聲請之曰:“須賜花一枝欲與啼兒,等賜之則可賜好花。”是華洛兒童之諺,而遠境鄙里之所不識之也。織田信長公三月入洛,始聞斯言,大感之謂。實都下兒童之詞也,然歸江州安土城則教城下兒童而唱之云。①[日]山田孝雄:《櫻史》,第282、124、278、399~400頁。
幕府末年,著名儒者齋藤拙堂對京都的“花見”勝地還有如下點評:
天下名花,古今首推芳野。余以爲,芳野有山無水,未若嵐山之最佳也。嵐山花之多,雖遜芳野嚴槎牙而水清駛。方花時,望之槎之泛,橋之臥,人之來往坐立,宛在畫圖中。余謂,梅花以月瀨爲最,而櫻花以嵐山爲最,皆兼山川之勝故也。②[日]山田孝雄:《櫻史》,第282、124、278、399~400頁。
齋藤拙堂對江戶的賞花勝地也有評論:
江戶名花首屈指飛鳥山墨沱川,然形勝既不及嵐山,而遊人猥多,又頗爲殺風景。唯東叡山廣袤數里,雖遊人衆不損風景。山儘早櫻,又多老杉古松,殿閣宏壯,麗而不靡,皆足與花映發矣。京師以早櫻名者,華頂山爲最,以未能比此地也。山舊爲我藩別墅,故或稱上野,而清水、黑門、車阪等名又皆襲伊賀、上野云。③[日]山田孝雄:《櫻史》,第282、124、278、399~400頁。
從上幾段描述可知,“花見”在江戶時代已成爲京都、江戶市民休閑活動的一部分。這裏的“良賤男女”所指雖然不甚明瞭,但可推測爲三教九流無論身份貴賤都有賞花的習慣。“花見”時節,要調製新衣,也說明與一般性的出遊相比,更具儀式性和非日常性。而織田信長來到京都纔知賞花之俗已入童諺,感歎之餘,將其傳播到他的領地。由此也可知,“花見”的習俗從京都、江戶這些文化中心向“遠境鄙里”擴散的可能性很大。
三 “花見”意義的重構
日本的賞櫻名所,在明治維新後發生了巨大變化。明治維新初期,有過一段否定自身歷史文化、全面肯定西學的過程,櫻花的命運也受到影響。《櫻史》如是評價這段歷史:
這種崇拜西洋的風氣日漸濃厚,將本國的文物制度全面否定,一概斥之爲野蠻舊弊。……古建築古雕刻被廢棄淪爲柴薪,日本書和漢籍被當作裝裱字畫匠人的墊紙。……在這樣的時代,天下的名園被改造爲農田或菜園,更有甚者被當作練兵場和射擊場。我等明治二十九年去著名的吉野山遊玩,看到這個著名的賞櫻勝地的櫻花樹居然是那麽幼小,一問纔知道,明治維新這些櫻花樹被當作沒有經濟價值的植物砍伐掉了,那些古代的神木,哪裏抵抗得過所謂文明開化的威力。直到後來,人們纔漸漸知道過激政策的弊害,這些櫻花就是那之後新近栽種的。④[日]山田孝雄:《櫻史》,第282、124、278、399~400頁。
這段文字所表達的事實極爲重要。“花見”的歷史雖然悠久,天皇、貴族、寺院、學者文人等都留下了讚頌櫻花的詩、歌和其他文字,“花見”的空間、儀式性行爲也都存在,但這些並不足以自然而然地形成有關櫻花的文化記憶。當政治的價值判斷發生變化的時候,櫻花依然可能面臨被砍伐毀損的命運。正如阿萊達·阿斯曼所說,文化記憶的形成过程,“會受到一個有目的的回憶政治或曰遺忘政策的控制。由於不存在文化記憶的自我生成,所以它依賴於媒介和政治”。⑤[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第6頁。因此,當政治發生變化的時候,記憶還是遺忘,就取決於當下立場的意義和價值判斷。櫻花和“花見”的價值發生的曲折變化,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經歷了短暫的全面西化、否定自身歷史文化的過程之後,日本社會開始反思自身文化的價值,皇室開始恢復了“花宴”制度。明治三十六年(1903),男爵細川潤次郎著《明治年中行事》對此予以介紹:
觀櫻會每年四月舉行,但是日子不確定。如果選定的時間下雨,就推遲到次日。如果次日還是下雨,就會取消當年的活動。觀櫻會舉行當天中午一過,天皇皇后兩陛下駕臨,親王大臣外國公使及五等以上高官及其夫人一起在櫻花樹下的接受賜宴。
此會第一次於明治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吹上御苑舉行,第二年在同樣的地點舉行。從明治十六年開始移到濱離宮舉行。①
除了在宮中舉行賞櫻會之外,天皇還以“行倖”之名到各地的觀櫻勝地視察。小金井雖然櫻花保存較好,但是因爲交通不便,前去“花見”的一直很少,明治十六年(1883)四月二十三日,天皇來此地賞花,小金井名聲大噪,不久就遊人如織。此事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二十年後,明治三十五年(1902)四月十五日,天皇恩賜部分皇室人員及大臣往小金井賞花,包括內務大臣、司法大臣、學習院長等從宮內省出發,上午11點到達小金井,賞花之後,下午4時回到東京,並向天皇奏報了經過。爲紀念此事,天皇當年行跡處的一個松樹旁勒石立碑,碑文如下:
小金井堤老櫻夾流,橋頭望之若雲若雪。維新明治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車駕臨幸,賞花賜宴群臣。洵爲昭代嘉眖矣。里人某等表玉座栽松。海岸寺僧玄恪建碑求銘。余曾爲神奈川大書記官,奉引先導,咫尺天顏,忝陪宴霑天盃者。乃作銘曰:
玉川金井,花麗春晴,昔芳山櫻,今三里櫻。
宸賞攸及,臣民攸榮,題松勒石,行倖之名。
從四位勛四等 磯貝靜藏謹撰並書
隨着天皇爲代表的上流社會的提倡和鼓勵,加之各地的櫻花愛好者的努力,櫻花的種植和“花見”的習俗逐漸得到恢復。但是,正如大貫指出的那樣,在明治初期,櫻花被用來強調日本的獨特性和“大和魂”,因此,僅僅是作爲文化民族主義的隱喻。這與政治民族主義並不是一回事。②
至於明治後期到二次大戰結束之間的半個多世紀,櫻花是如何變成了“帝國的景觀”,日本文化史學者高木博志有過詳盡的研究。他分析了明治以來日本朝野對櫻態度的轉變,揭示了在經歷短期的西洋文化至上而砍伐櫻樹種植經濟作物的時期之後,由於部分知識精英和皇室的推動,日本社會迅速恢復了對櫻的喜愛和推崇,進而將櫻花與富士山稱爲“帝國的景觀”的歷史過程。高木特別提到,1919年日本公佈《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護法》,將傳統的櫻樹(一本櫻)以及京都的嵐山、吉野山的山櫻盛開的景觀,用法規的形式予以保護。與此相對,作爲改良的品種而大量種植的染井吉野櫻,則成爲日本文明開化時代“開發”與“近代”的象徵。“1920年之後,染井吉野櫻和傳統櫻兩者分別被用來表徵不同的景觀意義。這不同的櫻樹構成的空間構造,隨着大衆文化(1920—1930年間)的普及帶來的觀光熱,最後以名勝地和國立公園的形式固定下來。”③
四 櫻與梅
櫻花雖然在日本有着悠久的歷史,但作爲文化象徵符號,它在漢文化佔據主流的古代日本,並非是文人最爲推崇的。在古代日本文學中,最爲常見的春天的象徵是梅花和桃李。
以日本最早的漢文詩集《懷風藻》①《懷風藻》是日本最早的漢詩集,天平勝寶三年(751)成書,收錄64名詩人的120首作品,編者不詳。爲例,在全書一百二十首詩歌中,歌詠櫻花的詩僅有兩首。其一:
淑景蒼天麗,嘉氣碧空陳。葉綠園柳月,花紅山櫻春。
其二:
景麗金古室,年開積草春。松煙雙吐翠,櫻柳分含新。嶺高闇雲路,魚驚亂藻濱。激泉移舞袖,流聲韻松筠。
在中華文化還佔據日本精英階層主導地位的時代,中國文人喜愛的梅和桃李,自然也成爲日本文人詠讚的對象。對此,《櫻史》作者感歎道:“我們看到在當時的詩人花必稱梅、桃李的時代,這兩位卓然而出,歌頌我國花——櫻花,實在令人感佩不已。”②[日]山田孝雄:《櫻史》,第42、262、262頁。
建立櫻花的文化象徵意義,擺脫梅、桃李這些來自中國的文化象徵符號的“壓力”,是日本知識精英不可迴避的問題。他們的策略之一是,借中國人之口,褒櫻貶梅。《櫻史》特別舉出明遺民朱舜水喜愛櫻花的情節,日本文人安積覺的記述如下:
文恭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每花開賞之,謂均等曰:“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廼知或者認爲,海棠可謂櫻花之厄。”義公環植祠堂旁側,存遺愛也。③[日]山田孝雄:《櫻史》,第42、262、262頁。
這裏被強調的“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一句,鮮明地體現出將中國作爲“他者”的對抗意識。另一位日本著名文人中村顧言更是賦詩如下:
獨對山櫻感歲華,東風戚戚舊煙霞。川棠洛牡皆羶氣,故愛扶桑第一花。這裏對代表中國的“川棠洛牡(四川海棠、洛陽牡丹)”的否定和對“扶桑第一花”的讚美更爲明顯。山田孝雄對此評論道:明室孤忠的遺臣和扶桑第一之櫻花肝膽相照,說明櫻花絕非僅僅是日本人的象徵,它也代表了純忠至誠的普遍精神。這一點,從明人朱舜水對櫻花的共鳴上可見端倪。④[日]山田孝雄:《櫻史》,第42、262、262頁。
另一位也是明末爲躲避戰亂來到日本的陳元贇所寫的讚美櫻花的詩,被《櫻史》收入:
滿樹婀娜簇淡英,梨花是友桃是兄。粉紅淺帶微醺色,湘碧全含別樣情。
羅綺香嬌長樂女,珍寶實飽上林鶯。憑軒坐對芳叢下,落照斜窺豔信生。
詩中的“梨花是友桃是兄”,雖然隱喻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的平等關係,但櫻花已從原來的邊緣位置,逐漸與梅、桃李平起平坐,進而淩駕其上,也是不爭的事實。
明治十二年(1879)三月,著名啓蒙知識人、明治政府官員平野之秋在《洋洋社談》雜誌第55期發表《櫻賦》,全文抄錄如下:
往年寬永寺大伽藍,悉罹兵燹,片瓦不存;所謂三十六房,亦皆化爲蔓草,蕩爲冷風者蓋十八九,東臺風色一時極荒涼矣。而至盛世之今日,鋤理荒蕪,斫去榛莾,作皇京公共之遊園。於是,櫻樹數千章,喜林丹楓,依然不改舊觀,換當年修羅之相,爲貴賤男女燕遊之安樂土。今玆三月三十一日,余往遊焉。時櫻花盛開,所見無非花,園丁灑掃不懈,花下一塵不飛,可謂林園之勝冠皇京也。乃作《櫻賦》一篇:
何波幽豔兮,維神州之芳。既顯名於異域兮,獨專美於東方。晻曖乎吐葩兮,咇茀乎發香。旖旎以紛容兮,綽約以炫煌。單弁以純白,如姑射之冰肌兮;重弁而濃郁,似淑姬之靚妝兮。牡丹之富貴兮,尚將泥首讓花王;況桃李之俗豔兮,執鞭而在弟子之行。宿雨霽而朝暾映射兮,熀熀然閃彩浮光。若夫蛺蝶之紛紛兮,來飲鮮美之湛露。既欺彩翩之捲舒兮,或疑問文繡之展佈。而乃當風雨之淒涼兮,落英飄飄以幡纚;又翾以翻空兮,仿佛玉屑之霏霏;其鋪地如千堆之雪兮,沒搢紳之馬蹄,而払遊人之春衣。或作山觜自花間望街衢兮,眼界豁然以無涯。乃忘沈疴在身心一何快爽兮,定有出炎火而登春臺之思。嗟乎!雖霸業已息兮,依然尚存廟屋,長松老杉,蓊然以深兮,金碧熒熒隱見於其間,以映帶花木。既知德澤之無窮,又見朝恩之隆渥,且夫我皇統之一性兮,歷萬祀而不變更也。維萬邦之所欣慕兮,秋津洲之所由以尊容也。宜矣彼蒼蒼者兮,畜清淑之氣而產斯櫻也。此非天翁之故爲淫巧兮,爲祥瑞是呈也。①[日]山田孝雄:《櫻史》,第406頁。
“洋洋社”是明治八年(1875)由一批在東京的漢學者、洋學家組成的學術社團,與著名啓蒙團體“明六社”並存。與全力普及介紹西方文化的“明六社”相比,“洋洋社”的言論兼具對傳統文化的介紹,在東西文化關係上持較爲中庸的立場。他們發行了社刊《洋洋社談》,在上面普及科學知識,評論社會問題,有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平野之秋是洋洋社重要成員之一,原爲幕臣,主張開放國門;明治二年(1869)九月,被新政府任命爲新政府官員;明治四年(1871)因病辭職;三年後,擔任太政官修史局歷史課官員;明治十年(1877)一月,再次因病隱退;明治十六年(1883)二月五日,因病去世,享年七十歲。他在《洋洋社談》共發表論文二十三篇,內容涉及歷史、漢學、自然科學、宗教、文學等。
平野的這篇《櫻賦》文體是漢文體,表明在明治初期,中華文化並未隨着日本的對西方開放而喪失其影響力,它依然是日本知識精英不可或缺的基本教養。另一方面,文中表達的富貴之花牡丹、俗豔之桃李,均要俯首櫻花:“牡丹之富貴兮,尚將泥首讓花王,況桃李之俗豔兮,執鞭而在弟子之行”,對中國文化的對抗意識也躍然紙上。在文末,作者將櫻的美與“萬世一世”的天皇制聯繫在一起:“且夫我皇統之一性兮,歷萬祀而不變更也。維萬邦之所欣慕兮,秋津洲之所由以尊容也。宜矣彼蒼蒼者兮,畜清淑之氣而產斯櫻也。此非天翁之故爲淫巧兮,爲祥瑞是呈也。”這段表達,作爲明治思想啓蒙言論的一部分,無疑爲後來日本軍國主義將櫻與“爲天皇戰死”的美學價值產生“誤識”埋下了伏筆。
1918年4月,日本的一批愛櫻人士在帝國飯店成立“櫻之會”,被稱爲“日本工商業之父”“日本近代經濟領路人”的澀澤榮一擔任會長,侯爵德川賴倫、男爵阪谷芳郎分別擔任名譽顧問和顧問,會員中的大多數是日本文人學者和上層人士。“櫻之會”還創辦了會刊《櫻》,在發刊詞中介紹了櫻一度被日本社會擯棄的狀況:“櫻花自古被稱爲我國國花。……最近急劇的物質上的進步,削弱了人們對櫻花的關心和熱愛,名木凋零,尤其是東京及其近郊,因爲煙毒等其他原因,櫻樹大量凋殘萎謝”,主張要振興日本文化,就應該恢復櫻花的地位。結合前文所論述的櫻在日本社會的意義的變遷,不難理解文化記憶形成過程中的主體建構性與當下性特徵。
無獨有偶,在文化象徵符號的對抗中,逐漸被邊緣化的代表中國文明的“梅”,在日本卻有了一段不同尋常的被“傳統化”的歷程。1933年,日本的“梅之會”創刊了雜誌《梅》;1943年,《櫻》與《梅》合併,在《梅與櫻》合併創刊號中,刊載了主辦者花守人撰寫的卷首語,其中寫道:“櫻花和富士山是我國風土自然的代表,是我國民精神的象徵。與此相對,古代傳來的象徵中國倫理思想精髓的梅花,作爲神代以來的日本精神的代表而被種植和鑒賞,兩者共同成爲國民精神文化基礎上的國民思想的反映。”②[日]高木博志:“桜”,《アジアの記憶の場》,第274頁。櫻花與梅花的結合,被作爲日本固有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結合而形成的日本國民精神的表徵。如果將這一事實還原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昭和日本,不難想象,出於建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化同一性的政治目的,將一度被排斥爲文化“他者”的梅,重新納入到“大日本帝國”的文化傳統之中,是因應昭和時代日本殖民統治的文化建構的需要。這一點形成了和明治時代側重發現或發明“原生性”文化因子潮流的差異。它作爲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值得今後進一步探求。
結語
按照大貫惠美子的分析,如果說明治維新之後的櫻花崇拜與軍國主義的結合是日本近代的“再造傳統”的話,那麽,本文的梳理表明,任何“傳統的再造”都不是“憑空”而成的。美麗的櫻花能夠成爲“殺人花”,絕非一蹴而就的政治宣傳可以輕易實現的。一方面,櫻花從自山野的植物受到日本人的喜愛,然後移種到家園寺院,進而插到花瓶和髮髻上,逐漸走進日本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從實物的櫻花,變成繪畫、服飾的素材,進而進入和歌、戲曲等文學世界,這個過程在心理和情感上營造出了一個“悠久”的歷史過程。在這樣的源自上古的櫻花傳說、詩歌文學、服飾、繪畫所構成的“日本自古以來”的固有“傳統”的基礎上,權力與知識精英主導的“文化記憶”的建構得已實現。這個建構的手段包括了經典創造,如詩文的編輯和誦讀①例如,《源氏物語》《萬葉集》以及後來印有櫻花圖案的教科書《櫻花讀本》。,以及生活空間的文化記憶建構,如日本生活空間中隨處可見的“花見名所”,其中很多還有天皇及皇室人員的巡幸題記、紀念碑、紀念植樹等空間的營造。其結果便是,形成了櫻花—美—日本固有文化的意義鏈條。這個通過“花見”的休閑行爲實現的意義鏈條,爲近代日本發動戰爭期間將櫻花的文化隱喻納入到戰爭動員的一環之中提供了基礎。1870年,木戶孝允在靖國神社種植櫻花;同年,日本的海軍、空軍制服徽章開始裝飾櫻花。自此,靖國的櫻便逐漸演變成“爲天皇飄落的櫻”(佐佐木信綱創作的歌詞)。由於休閑往往被賦予“自在、自由、自得”的特徵,人們在這個過程中最容易形成美學化的“誤識”,因此,便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在每次櫻花盛開的時節,喧鬧的年輕人在靖國神社院內飲酒作樂,他們在其享樂休閑行爲中沒有看到悲劇性的諷刺,就如許多日本人,特別是年輕人,完全漠視了發生在塞班島和其他太平洋島嶼上的戰鬥造成的駭人死亡,現在這些地方則被日本旅遊公司作爲度假的‘樂園’來兜售。”②[美]大貫惠美子:《神風敢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歷史上美學的軍國主義化》,第35頁。
回顧歷史,人們看到了很多過去被蒙蔽的事實;審視當下,人們卻又感覺到依然沒有擺脫某種文化的宿命;進步與停滯並存,希望與悲觀參半。但是,無論如何,當我們思考未來的時候,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當下的省察,都可以而且應該成爲重要的精神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