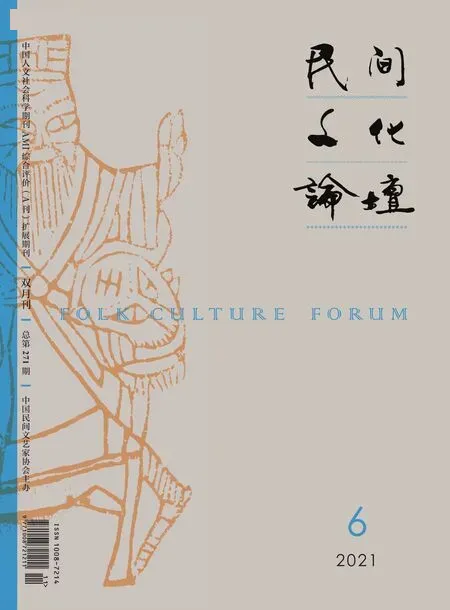重访北欧之眼: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1975—2015)*
2022-01-05挪威彼得克劳福德PeterCrawford
[挪威]彼得·克劳福德(Peter I. Crawford) 著 鲍 江 译
我介绍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NAFA)时,譬如在研讨会和电影节上,常指出它是欧洲——如果不是全世界——最老的专门的民族志电影节。严格地讲,这么说不全对,因为有几个原因。首先,NAFA 实际上不是一个电影节,而是一个协会,正如该缩写所表明的意思。1975 年以来, 它一直是一个人类学机构协会, 会员主要是北欧国家的大学科系和博物馆,覆盖冰岛、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并包括或多或少政治上自治的地区:萨米、奥兰群岛、格陵兰岛(绿岛)和法罗群岛。其二,在欧洲,人民电影节(Festival dei Popoli)比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开始组织电影节肯定要早几年,该节有相当多的民族志电影内容,但有人可能会争论说人民电影节随时间推移并不像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那样持续专注于“民族志”。放眼欧洲外部,无疑玛格丽特电影节领先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数年,该节由南加州大学的蒂莫西·阿什(Timothy Asch)于1976 年组织其首届以庆祝米德75 岁生日,致敬她在世界范围内将电影引入为人类学研究服务的先行者角色。其三,尽管其他电影节也在发展,但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与众不同。自其创始,如后文所示,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国际民族志电影节从1979 年以来(几乎)每年举办一届。 目标是每年由不同地方的在地委员会组织,首先以二十多个机构会员轮流担任组织者。在这个意义上,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不是一个电影节而是多个不同的电影节。最后,增加它的内部多样性。自2001 年起,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已经扩张超越它的“北欧”根系,现已经在北欧国家外举办多次,并计划在不远的将来在欧洲外组织举办。因此,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不是一个狭义的电影节。本文拟形成对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的描述和分析,并聚焦于是什么实际构成并定义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有幸关于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和广义的北欧国家影视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已经见诸其他著作和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的其他活动,诸如电影档案、系列丛书、通讯,因此本文仅限于它们在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历史上充当直接角色的范围。
一、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最初时光:一个努力站稳脚跟并使人类学家和电影人会上面的电影节
直到1979 年在斯德哥尔摩国立民族志博物馆举行的首届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的主要活动是建立16 毫米电影档案,其主要目的是使电影可用于北欧大学逐渐增多的人类学系的人类学家的教学和博物馆的公共展映活动。一个非常务实的议题,触发了组织一个年度性电影节的想法,那就是使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会员能看到新的民族志影片。基于电影节的年会,它们常与电影节配合举行,即可决定为电影档案买些什么影片。 那时候,放映格式是16 毫米“适当的”(胶片)影片,这意味着会前在会员中传阅一遍所有影片应该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报名影片数,或早期通常是邀请的影片数,非常有限,通常不超过6 至10 部影片。 (不断增加的)16 毫米复制费意味着我们通常只能根据片长和其他因素购买一到三部影片。
从一开始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就努力确保尽可能多的影片作者出席他们影片的放映,但不幸因为经费原因这个想法时常落空。比今天还要有过之无不及的是,作为艺术的电影与作为学术科目的人类学之间存在相当僵化的区别,这导致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变成一种脆弱的平衡行为。比方说,如果有人获得支持这个活动的“电影”部分的一些资助,这个活动几乎立马就被定义为非科学的,从而妨碍对其学术部分的资助,反之亦然。如今这个问题依然还困扰着民族志电影节,尽管艺术世界与学术的区别也许并不那么僵化固守,并且多年的经验使组织者能够在诸多支持来源中更有效地掌舵。
即使有这些实际障碍,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有时候几乎是奇迹般地、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开拓性的电影节,把影片作者和电影工业的其他代表与社会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聚在一起。从刚一开始,成功的种子大概就奠定在电影人觉得他们能从人类学家那里学到东西,特别是关于如何“与人相处”和从事田野工作,同时人类学家呢,其中的许多人明确表达成为影片作者的兴趣, 他们有时候也许甚至更无批判性地吸收他们能从电影人学到的所有知识和信息,兼及影片制作的实际方面和更理论化和概念化的制作、分析和讨论电影的方式。

图1 1990 年曼彻斯特皇家人类学会电影节上的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人际网络。克努特·埃克斯特罗姆(Knut Ekstrom)(前左)与彼得·克劳福德(前右)。背景中的三位先生是大森裕浩(Yasuhiro Omori)、保罗·克亚奇(Paolo Chiozzi)与阿森·巴里克西(Asen Balikci)(从左到右)。克努特·费舍尔—穆勒(Knud Fischer-Moller)摄影
不久就变得很清楚,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早年几乎唯一的依靠是后来变得有点流行的人际网络。奠基人之一、也是长期担任秘书长的海姆·拉帕莱宁(Heim Lappalainen),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际网络达人,他还在世时就取得了几乎神话般的地位;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的头十年左右,人际网络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笔者和克努特·埃克斯特罗姆的协助下,人际网络扩大了很多,那时候笔者还是个学生、任秘书长助理,克努特·埃克斯特罗姆任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财务主管,他也是少数几个努力在专业电影界立足的人类学家之一。 在形成期的那些岁月里,与许多民族志电影作者建立了个人关系,如大卫·麦克杜格(David MacDougall)和朱迪斯·麦克杜格(Judith MacDougall)、让·鲁什、阿森·巴里克西、伊恩·邓洛普(Ian Dunlop)、蒂莫西·阿什、乔治·普罗兰(Jorge Preloran)、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荷伯·迪·乔伊尔(Herb di Gioia)和盖瑞·科尔迪亚(Gary Kildea)。
不管怎么说,有一个来自电影圈的人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深入并持续的影响。科林·杨(Colin Young),他后来成为英国国立电影电视学院(NFTS)校长,他不仅形成了所谓“观察电影”背后的哲学,并且与沃尔特·戈德施米特(Walter Goldschmidt)一起于1966 年在洛杉矶的加州大学首创民族志电影课程,锻造人类学与纪录片制作的结合。科林成为英国国立电影电视学院校长后,他继续做这个,通过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确保资助几个学术背景的人类学家的专业电影作者培训,那时候在欧洲没有或罕有这种可能性。在早年科林的影响是巨大的,准确地说是因为他帮助我们建立起了人际网络,把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介绍给电影人,如彼得·沃特金斯(Peter Watkins),他是BBC 剧情纪录片《战争游戏》(1965 年)的制作者,还有大卫·麦克杜格,他曾经参加加州大学的民族志电影课程,并且那时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受人尊敬的民族志电影作者之一。
通过科林·杨,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与英国国立电影电视学院建立了持续多年的紧密关系,后来荷伯·迪·乔伊尔加入,他是纪录片系的头儿,再几年后是托尼·德·布罗姆海德(Tony de Bromhead), 他在那里授课,他们愿意带他们的学生来, 愿意展映他们学生的毕业影片和其他影片。观念异花授粉的结果,且不说那是美妙的交往,激励了许多北欧的人类学家投身于民族志电影并发展后来以影视人类学而为人所知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这种激励不可能只来自英语世界。因为北欧国家的人类学家和人类学学生没有电影培训途径,除非努力去某所国立电影学院开始全日制四年期课程, 那些不顾一切争取学习实践性的(和理论的)动手制作影片的人就不得不到外面的国家寻找机会。可以描述为完整的一代的北欧民族志电影作者,如佩尔·莫尔(Perle Mohl)、克努特·费舍尔—穆勒、贝瑞特·门德森(Berit Madsen)、安妮—梅特·乔根森(Anne-Mette Jorgensen)、迪特·M. 西伯格(Ditte M. Seeberg)和特洛伊尔·S. 詹森(Troil S.Jenssen),他们还活跃在民族志电影和影视人类学场域,当年他们有幸能参加巴黎的瓦兰工作坊(Ateliers VARAN)电影学校提供的短期课程培训。此外,像英国国立电影电视学院一样,瓦兰开始参加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带来他们的学生和影片。 瓦兰组织电影工作坊,在世界各地都有活动,像人类学家一样,特别是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如果在遥远的北方遇到急需大投入支持萌发中的民族志电影环境,它又与一所电影学校合作。
二、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青春期:20 世纪90 年代和21 世纪早期电影、理论和影视人类学的发展
早期的电影节成为人类学家与电影人的会见场,节目通常仅由放映后讨论的影片展映组成,偶尔有各种大师班。有些活动很大,但实际上通常都相当小而温馨,1983 年布利德岛电影节,在斯德哥尔摩列岛的一个小岛上举行,也许堪称典型的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活动,一些鼓舞人心的电影人,包括科林·杨和大卫·麦克杜格应邀教我们这些对电影相当无知的人类学家如何明智地谈论电影。
在接下来的10 至20 年,许多东西影响了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首先出现了新型的活动格式,它的首个案例大概是1984 年在丹麦奥胡斯大学举办的电影节。它的理念是办一个与更典型的学术活动如研讨课或研讨会相结合的“节”,通常围绕一个具体主题组织,那一次出于多少显而易见的原因,主题是“绿岛与北极”, 并以特别影展相配合。这种格式或多或少被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追随至今(参见下文)。因为上文提到的简单理由,电影节“适当”保留了一个重要成分,那就是为档案购买的影片必须被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会员看见。
其二,随着岁月流逝,有一点变得清楚,我们的电影学校人际网络固然提供了美妙的输入,最重要的依然是英国国立电影电视学院和瓦兰工作坊,但是有些东西遗失了,遗失了那些与“理论”和“学术”更紧密相关的东西,或许那是因为参加电影节的电影作者罕有人写文章谈论他们的影片和影片制作,以此贡献给更主流的处理学术理论的途径。那时候,关于“民族志电影”的文章非常少,但这种局面很快就改变了,人类学家展示了日渐增长的兴趣并开始写相关文章,与此同时,电影理论家,而不是电影作者,对被称作民族志电影的现象也发展出了兴趣。比尔·尼科尔斯(Bill Nichols)大概是后者的最佳例子,因此1991 年在奥斯陆的电影节上他被邀请作为主旨发言人,这在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是一件新鲜事,那次活动被称作“大会”,尽管也有常规的民族志电影新作展映。 它的一个表明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如何(再次)变得更学术的直接结果是,开启了着手一套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丛书的想法,几年后出版了该丛书的第一卷,包括比尔·尼科尔斯和大卫·麦克杜格在内的许多人对此做出了贡献。

图2 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选片。2015 年5月曼彻斯特格林纳达中心NAFA 电影节遴选委员会最后会议上,奥西·维拉特(Orsi Veraart)(前左)与洛塔·格兰尼伯姆(Lotta Granbom)(前右)正在紧张地工作。背景中的先生是另一位评委。克努特·费舍尔—穆勒摄影
最后,在这个时期,我们开始经历录像的来临,这当然以各种方式对电影节和展映有深远影响。其中必须处理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之一,比如以往必须处理16 毫米影片的沉重包裹、花费一大笔运输费用的噩梦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个噩梦:必须找到播放所有不同的录像格式的办法、并且首先得习惯我们多数人认为影像质量绝对一塌糊涂的东西。但是我们不久也发现这项新技术可能也有一些优势,首先,它也许提升了可及性。这意味着,比如以前在发展中国家或原住民群体中不能在工作中使用影片的群体和个人,如今能生产我们能在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展示的有趣的材料。明显的例子是特伦斯·特纳(Terence Turner)与卡亚波人(Kayapo)制作的影片①Crawford, Peter I.“Nature and Advocacy in Ethnographic Film: The Case of Kayapó Imagery.”In Advocacy and Indigenous Filmmaking. Intervention, Nordic Paper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1, edited by Hans Henrik Philipsen, and Birgitte Markussen, Hoejbjerg: Intervention Press. 1995. pp.7–22.、文森特·卡雷利(Vincent Carreli)与多米尼克·加洛伊斯(Dominique Gallois)在巴西的开拓性的“乡村影像”(Video in the Villages)项目②Gallois, Dominique T. and Vincent Carrelli.“Video in the Villages: The Waiãpi Experience.”In Advocacy and Indigenous Filmmaking. Intervention, Nordic Paper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1, edited by Philipsen, Hans Henrik and Birgitte Markussen, Hoejbjerg: Intervention Press. 1995. pp.23–37.和阿森·巴里克西与马克·班吉尔(Mark Badger)在西伯利亚的原住民培训③Balikci, Asen, and Mark Badger.“A Visual Anthropology Seminar for the native peoples of Siberia and Alaska.” In Advocacy and Indigenous Filmmaking. Intervention, Nordic Paper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1,edited by Philipsen, Hans Henrik and Birgitte Markussen, Hoejbjerg: Intervention Press. 1995. pp.39–54.。增强的可及性无疑对大学决定建立民族志电影培训起了作用,在大学开设影视人类学课程、教学生实践性的和理论性的影像制作。忽然之间,我们收到了大量的学生影片,但不再局限于电影学校的学生,也有来自研究所的影片,如来自曼彻斯特格林纳达影视人类学中心,或几年后,来自特洛姆斯我们“自己的”影视人类学课程。
三、今日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成熟并发现了一个终极格式?
近年来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可能已经找到一个或多或少的“标准”格式,我们早在1980 年代就已经看见它的根脉苗头。这个被称作“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国际民族志电影节”的年度性活动,它的名字将作为主标题或副标题,继续保持每年在一个新的地点举行的电影节上,并且现在它通常配一个更“学术的”活动,如研讨班、工作坊、研讨会或大会,作为一项主题化组织的规则,至少有一些展映影片与该主题相符,但也有常规影展。组织结构或多或少与以往保持一致,即由在地组织者报价或(渐增的)投标组织该活动,并决定是否希望有来自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工作委员会的人直接参与或不参与。
千禧年之交以来已经有两个主要改变。首先,如引言中提到的,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现在可以在北欧国家之外举办,并且已经在外面举办过六次。第一次是在卡利亚里(2001 年),最近的一次在华沙(2015 年)。 2004 年,在塔尔图举办的那届电影节有趣,因为它帮助开启了现在我们的“姊妹”电影节,即年度性的“世界文化节”(World Culture Festival)。这不是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第一次促成一个新的电影节,2002 年在芬兰约恩苏已发生过一次,那时在那里诞生了“视觉文化节“(Viscult Festival)。
其次,随着报名影片增长,2007 年起影片遴选实际已经系统化并遵循同一组织格式。建立由5 至6名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会员组成(都是人类学家和或电影作者)的遴选委员会,报名影片寄给遴选委员会主席,由主席组织分发给其他评委。每个评委对每部影片的评审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如果经费允许,其中的部分工作通常在上一届电影节后、在遴选委员会集中开会之前即已开始,以便在入围名单基础上做最后的遴选。一旦入围名单敲定,遴选委员会即开始实际程序,允许实际程序影响最后的遴选,在这个阶段,选择在几种意义上相互配合得好的影片,比如是否符合与电影节配合的研讨班或工作坊的主题。
在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我们相信我们最终已经找到或多或少的理想格式和组织我们的年度电影节的方式。不管怎么说,回到我们的起点,虽然并不完全如此,但主要的理由还是在,那就是每年我们有新的组织者,公平地说,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坚持的一点是,无论如何,组织者必须保证电影节有一定程度的温馨和社交,它对于电影的和智识的愉悦和刺激都有传导性,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有益于对我们周围的复杂世界的人类学式理解,尽管我们在银幕前从早晨到深夜连续坐三四天之后,我们可能几乎已经忘记所谓现实的东西。我们也喜欢继续看到NAFA 作为协会和电影节激励其他人在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做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开始把活动搬到北欧之外的国家的原因,并且我们有计划不久后在欧洲之外组织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很可能在喀麦隆或马里。 保罗·亨利(Paul Henley),曼彻斯特的格林纳达中心主任,曾经描述科林·杨是“电影作者的作者”。也许对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的最佳描述方式是作为民族志电影节作者的作者。

附录 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电影节一览表

接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