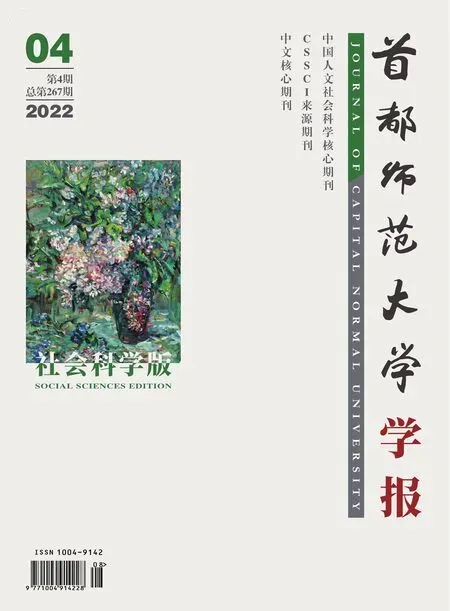唐朝的“官爵威命”与河朔藩镇
2022-01-01张天虹
张天虹
引 言
河朔藩镇与唐廷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老问题。在这个研究当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史料,即会昌四年(844)李德裕对河朔藩镇的使者所说的一句话:“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①《资治通鉴》卷248,会昌四年八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010页。据笔者目力所见,当代中外学者中,张国刚先生最先引用这条材料来说明河朔藩镇对唐廷具有依附性。张国刚先生本意在强调河朔型藩镇(不仅限于河朔藩镇)具有游离性和依附性并存的双重特点。他所说的依附性是指河朔型藩镇“不否定中央统治的特点”。②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此后,学界反复征引该史料③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页;仇鹿鸣:《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李鸿宾:《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14-215页。仇鹿鸣先生将这段话置于专著《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以下简称《长安与河北之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的封面,可见他对该史料的重视。或许这正是唐后期河北与长安之间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张力所系。,则大多将其作为论证河朔藩镇权力的合法性(legitimacy)来自唐廷的一条最核心的证据,与张国刚先生的讨论角度已有不同。那么,唐朝的官爵威命,对于河朔藩镇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起到“安军情”的作用,河朔藩镇对唐朝授予的“官爵威命”的态度,对于唐廷又意味着什么,分析上述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具体地观察河朔藩镇与唐廷互动的真实状态。
一、河朔藩镇“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的语境再分析
任何一段史料都有其原生的具体语境。李德裕讲这段话同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会昌四年正值朝廷讨伐昭义刘稹的关键之时。李德裕对河朔藩镇的使者讲这番话,目的主要还是在于笼络河朔强藩。李德裕为了论证“朝廷官爵威命”对于“安军情”的重要性,举出一例,现赘引如下:
李载义在幽州,为国家尽忠平沧景,及为军中所逐,不失作节度使,后镇太原,位至宰相。杨志诚遣大将遮敕使马求官,及为军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①《资治通鉴》卷248,会昌四年八月条,第8010页。显然,李德裕的举证没有证明河朔(特别是幽州)藩镇的节度使(亦可称藩帅,以下简称“藩帅”)可以“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只是表明对朝廷尽忠的藩帅终得朝廷庇佑,在无法“安军情”之时,仍然可以逃归朝廷,不失显官。大和五年(831)幽州军乱,兵马使杨志诚逐其帅李载义,朝廷的实际态度是“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②《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71页。,“不计于逆顺”③《旧唐书》卷180《杨志诚传》,第4676页。,授杨志诚以幽州节钺。唐廷在处理与幽州甚至河朔藩镇的关系时,并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而往往是根据形势进行调整。会昌年间(841—846)唐廷平定昭义之乱,恰恰非常需要借重河朔三镇的力量。所以李德裕的这番话虽有告诫意味,但更像是一种政治激励。在激励河朔三镇方面,李德裕更积极的表态是在会昌三年明确表示承认三镇藩帅世袭的“河朔故事”,指出“泽潞一镇,与卿(指魏博何弘敬)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④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6《赐何重顺诏》,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21页。无论是李德裕还是牛僧孺,面对河朔藩镇,他们的目标和态度是一致的,就是如何在稳定河朔局势的同时还能调动其力量为朝廷所用。在具体策略上,唐廷并没有一定之规,也不会践行具有同构性的“忠”原则,⑤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方镇骄兵》中提出“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0,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1页)。仇鹿鸣先生据此提出节度使对朝廷的“忠”与军士对节度使的“忠”在思想上具有同构性,参见氏著《长安与河北之间》第290页及该页注4。似乎并不关心如何维护藩帅的权威,朝廷对藩帅“忠”的要求,只是单方面的。
退而言之,“不能自立”的是河朔藩帅而非河朔藩镇。官爵威命是授给藩帅个人的,其对于河朔藩镇的作用也就只能通过藩帅进而发生曲折的作用。由此需要明确:河朔藩帅的身份是什么?藩帅权力的合法性到底来自哪里?谷川道雄先生曾敏锐地指出,河朔藩帅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军人“伙伴集团”中的一员,一是朝廷的使臣。⑥参见谷川道雄:《关于河朔三镇藩帅的继承》,王孀媚译,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1989年版,第912页。作为“伙伴集团”的一员,河朔藩帅必须要代表并维护伙伴集团的利益;作为朝廷的使臣,则身负朝命,代表中央。由此,其权力的合法性似乎应该在这两条线上分别进行追索。
二、朝廷的官爵威命对于河朔藩镇的作用
前面的分析启发我们,“官爵威命”对于河朔藩镇的作用可能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讨论。
(一)作为“双刃剑”的“官爵威命”
作为朝廷的使臣,河朔藩帅依靠朝廷的官爵威命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以安抚军情,的确顺理成章。魏博藩帅韩允忠于咸通十三年(872)三月廿八日为父韩国昌立碑。咸通十五年①原碑上就是“咸通十五年”无误。是年十一月僖宗方改元“乾符”。七月十五日奉唐廷颁给他封赠其祖父母、父母的恩制。其时高大的韩国昌碑已经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刻字了。但韩允忠仍然命人在铭文最后一行与带有立碑时间的落款之间用非常小的字,近乎是挤刻上了这一恩制的内容②《韩国昌神道碑》,拙文《唐韩氏父子碑的流传及相关史事考辨》(待刊)。恩制的内容是:“祖秀,表赠工部尚书。祖妣张氏赠清河郡太君。考,赠左散骑常侍改赠兵部尚书。妣赠清河郡太君张氏,改赠凉[国太夫人]”“[]”中字目前在原碑上已不可见,取自正德《莘县志》。;无疑,韩允忠要向魏博军士表明自己得到长安朝廷的认可。韩允忠碑上写韩允忠谥号的地方一直空着,允忠之子韩简似乎是一直在等待朝廷的颁赐。③《韩允忠神道碑》,拙文《唐韩氏父子碑的流传及相关史事考辨》(待刊)。
更为典型的一例则是幽州藩帅杨志诚向唐廷邀求官爵:
[大和]七年,转检校吏部尚书。诏下,进奏官徐迪诣中书白宰相曰:“军中不识朝廷体位,只知自尚书改仆射为迁,何知工部转吏部为美?且军士盛饰以待新恩,一旦复为尚书,军中必惭。今中使往彼,其势恐不得出。”④《旧唐书》卷180《杨志诚传》,第4676页。唐廷最后接受了裴度的建议,“务以含垢,下诏谕之,因再遣使加尚书右仆射”⑤《旧唐书》卷180《杨志诚传》,第4676页。。杨志诚邀求官爵的行为或有不臣之心,但这种以兵部和吏部为前行、以工部和礼部为后行的制度,已经深入到官制运作的细部,与长安颇有隔阂的幽州军士很难明白。若从藩镇内部的形势来看,杨志诚的要求很可能的确是想进一步明确并抬高自己作为天子使臣的身份。这种身份越显贵,越有利于巩固自己在军中的地位。由此恰恰证明,朝廷的官爵威命是河朔藩帅的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藩帅在藩镇维持社会声望有重要影响。
正因为“官爵威命”是朝廷使臣的象征,是塑造藩帅的合法性的一种重要资源,所以,也容易成为藩帅的潜在竞争者们之间竞相争夺的对象。朝廷的官爵威命对于藩镇中的政治野心家未尝不是一种诱惑。唐廷往往用推迟授予藩帅节钺的办法,给河朔的藩帅们制造心理压力,⑥参见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212页;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第189-191页。甚至用朝廷的官爵威命为饵来鼓动藩帅手下的将校叛帅,从而在很多时候还成为刺激藩镇动乱的一种因素。藩帅即便在主观上想完全成为朝廷的使臣,在客观上却始终要保持“两条腿”走路,而不能向朝廷“一面倒”。因为藩帅对于朝廷的“忠”并不是一种可靠的依凭。追求以土地传之子孙的河朔藩帅和唐廷之间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真正互信的君臣关系。幽州藩帅刘济对朝廷“最务恭顺”,却“竟不入觐”。⑦《旧唐书》卷143《刘济传》,第3900页。一旦朝廷的削藩政策收紧,朝廷的“官爵威命”反而成为悬在刘济头上的一把利剑。刘济之死的原因复杂。不过,立副大使(刘济长子刘绲)为藩帅的长安旌节“已到太原”“过代州”⑧《旧唐书》卷143《刘济传附子总传》,第3902页。,尽管是其次子刘总制造的谣言,却无疑成了压垮刘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幽州上层竟因此而再次出现动乱。⑨参见《旧唐书》卷143《刘济传》,第3902页;拙文《也释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最务恭顺”》,《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正基于此,幽州藩帅似乎一直在极力塑造自己的权威,向文武僚佐和军民渗透忠于藩帅的观念,而幽州军民不论是出于真心还是被迫,都在表达自己对藩帅的忠诚,这在《房山石经题记》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唐末悯忠寺《重藏舍利记》(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对幽州藩帅(李匡威)的称号里甚至有“大王”出现,其平阙的形式也僭越了对于皇帝的尊重,日本学者据此推测幽州藩帅已有推翻朝廷的意图了。①参见新見まどか:《唐末の盧龍節度使における「大王」号の出現》,《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9,2016年,101-149頁。唐廷颁赐河朔三镇藩帅“郡王”似较常见。成德和魏博内部对藩帅称王的现象也较为普遍。例如几乎与《重藏舍利记》同一时期的《罗让碑》(龙纪元年,公元889年)中也曾称呼魏博藩帅乐彦祯为“乐王”,甚至称“大河之北,太行已东,曹孟德之称孤,将成霸业;袁本初之恃众,遽创雄图”②公乘亿:《罗让碑》,收于任乃宏、张润泽、王兴校释:《邯郸地区隋唐五代碑刻校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页。。但这不一定是要推翻唐廷的企图。可能把这些现象理解成河朔藩镇与唐廷离心自立倾向的一种强化,或许更加符合彼时河朔藩镇从上到下的心态。这种塑造领袖权威的观念及过程会不断推动藩镇的割据化倾向,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河朔藩帅试图摆脱军人集团伙伴中一员的身份(但实际上并未完全实现),从而很可能形成对内和对外两套话语体系。对外“奉朝廷”,只要朝廷不干涉其权威,遵行“河朔故事”,允许其以土地传之子孙,则仍然恪守朝廷使臣的身份。但仅仅强调朝命是不够的,仅凭朝命从来就不能“家业不坠”。对于河朔藩帅而言,长安天子始终离他们太远,近在咫尺、不得不要首先面对的是军人集团。所以在对内方面,就必然要努力塑造自己在本镇的绝对权威,构建尊卑等级秩序。显然,朝廷的“官爵威命”是把“双刃剑”,正是这把利剑成为塑造河朔藩镇内外矛盾的重要推手。
(二)具有“边际积极效应”的“官爵威命”
所谓的“积极效应”,在这里是指对唐廷和藩镇稳定都有利的结果。借用“边际”这个概念则意在表示,只有在其他条件都具备时,“官爵威命”作为一种资源的增量,对于准藩帅正位、掌握藩镇局势才具有最重要的推进性意义。“官爵威命”不能独立发挥作用,似也不能首先发挥作用,这些条件实际上涉及河朔藩帅的上述两种身份,到底哪个身份是主要的呢?在朝廷和藩镇发生冲突以及有两个以上藩帅竞争者出现的时候,或许能看得更加清楚。
长庆元年(821)成德镇发生的变乱,是非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③笔者对此例曾有讨论,更多细节请参见拙著《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143页。这里仅围绕“官爵威命”对河朔藩镇的影响再作申论。彼时,先有根基深厚的藩帅王承元移镇,而秉承朝命、自魏博而来的藩帅田弘正则因其种种行为导致“河北将卒心不平之”④《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第3852页。“军情不悦”⑤《旧唐书》卷142《王廷凑传》,第3885页。而被杀。按照成德镇“将-兵”的权力结构,其余诸将很可能形成竞争藩帅之位的局面。史载“牛元翼,赵州人,材果而谋……王廷凑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出廷凑远甚”,⑥《新唐书》卷148《牛元翼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88页。“故前命为深冀节度。及是又以成德令付之,希镇州兵士望风禀令,不战而归也”。⑦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120《帝王部·选将第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34页。不过,得到朝廷官爵威命的牛元翼的结局却是:率十余骑突深州围,入朝京师,愤恚而卒,又被廷凑夷灭其家。⑧参见《新唐书》卷148《牛元翼传》,第4788-4789页。
王廷凑的上台,有深刻的内部原因。长庆元年之前,王武俊家族执掌成德节钺已历三代,成德人心“不忘王氏”⑨王承元语,见《新唐书》卷148《王承元传》,第4787页。。王廷凑曾祖为王武俊假子,故以王为氏。[10]参见《旧五代史》卷54《王镕传》,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39页。王廷凑接任藩帅,实为通过模拟血缘关系与“河朔故事”建立联系,或有几分牵强,却仍然具有某种号召力。与此同时,王廷凑具备河朔藩帅所应有的一切基本素质,例如“得士心”[11]孙光宪:《北梦琐言》卷2《骆山人告王庭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页。、善于运筹帷幄等。他最终打出有利于成德的战场形势,赢得了成德军民的支持,从而战胜了只有一纸朝命的牛元翼。此后,王廷凑还塑造了自己被推为成德节度使过程中的神异故事,①孙光宪:《北梦琐言》卷2《骆山人告王庭凑》,第34-35页;李昉编:《太平广记》卷217《卜筮二·五明道士》引《耳目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61-1662页。进一步加强了成德内部的凝聚力。
张仲武执掌幽州节钺,确实获得了朝廷的“官爵威命”来安抚军情,但仍有其前提。会昌元年九月,幽州“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权主留后。俄而行泰又为次将张绛所杀,令三军上表,请降符节。时仲武遣军吏吴仲舒表请以本军伐叛”。②《旧唐书》卷180《张仲武传》,第4677页。陈行泰、张绛与张仲武都是幽州节钺的竞争者,都向朝廷邀求过节钺。③《旧唐书》卷180《张仲武传》,第4677页。但朝廷最终将官爵威命授予张仲武,与张仲武的“上表布诚,先陈密款”④《旧唐书》卷180《张仲武传》,第4677页。有关,但也主要是基于幽州内部的现实局面顺势而为的结果。吴仲舒与李德裕的对话表明,在这场争夺幽州节钺的竞争中,张仲武具有以下两个优势:
第一,张仲武占据了妫州的军事险要,“若万一入未得,却于居庸关守险,绝其粮道,幽州自存立不得”。⑤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7《论幽州事宜状》,第389页。张仲武虽不处于幽州镇权力的中心,却已经掌握了更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先前的研究重视这条史料,从幽州镇支州对于会府的挑战来解释张仲武获得成功的历史背景,⑥松井秀一、冯金忠等先生都有讨论。新近的综合研究,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2-348页。这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张仲武收服了幽州的军心和民心。张仲武统领的雄武军只有800人,加上土团也不过1300人。⑦参见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7《论幽州事宜状》,第388页。仔细分析张仲武的军吏吴仲舒和李德裕的对话,吴特别强调的是幽州的“人心向背”:“……‘[张]绛与[陈]行泰皆是游客,主军人心不附。仲武是军中旧将张光朝之子,年五十余,兼晓儒书,老于戎事,性抱忠义,愿归心阙廷。’”⑧《旧唐书》卷180《张仲武传》,第4677页。在李德裕的《论幽州事宜状》中,吴仲舒也说“只系人心归向,若人心不从,三万人去亦无益”。⑨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7《论幽州事宜状》,第388页。“张绛初处置陈行泰之时,已曾唤仲武,欲让与留务”。[10]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7《论幽州事宜状》,第388页。张仲武在幽州的根基较深。张仲武的先世,尤其是其祖、父两代皆为幽州将校,特别是至其父张朝光这一代很可能已成为幽州的上层政治精英[11]李俭:《张仁宪神道碑》,收于杨光主编:《廊坊石刻萃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这已经为张仲武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声望。张仲武因衙内有一二百人不从,未能成行,可能另有偶然性因素。张绛和陈行泰,虽然也都有支持者,但缺乏深厚的根基。[12]按吴仲舒的说法,张绛和陈行泰都是幽州“游客”。
基于以上两点,权力的天平已经在向张仲武倾斜。陈行泰和张绛向唐廷邀求节钺,但并未输诚。在这种情况之下,张仲武向唐廷输诚,确实产生了较大的“边际效应”,但获得唐廷的官爵威命,只是扩大了其原有的优势,促使其最终于诸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在两名以上竞争者争夺藩帅之位时,向朝廷输忠进而获得朝廷支持的一方,更容易增加声望获得军众支持。但前提应该是他已在藩镇内构建起权力的基础,不能损害、出卖本镇的自治利益。
显然,成德王廷凑也好,幽州张仲武也罢,或者是魏博的田弘正,[13]关于田弘正上台经过的分析,参见拙文《重论中唐诗人王建与魏博幕府的关系——兼谈〈李仲昌墓志〉的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无论他们有意还是无心,其上台过程首先都凸显了其“伙伴集团”中一员的身份。这也再次表明河朔节度使的权力基础根植于河朔藩镇的地方集团利益之中。唐廷的“官爵威命”十分重要,其作用的发挥却往往立基于藩帅已经基本得到军众支持、初步掌控本镇局势的背景之下。
藩镇军人集团尽管跋扈,但他们始终需要一个中心人物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在唐后期,为了求得未来的保障,禁军也都会主动集结至具有崇高声望及非凡魅力的将领身旁。①参见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军人集团所面临的必然选择,从而也意味着藩镇时代,河朔藩帅的权力基础的层次比较分明。朝廷的官爵威命只是其中一源,如何把人聚集在自己身边,是一个牵涉范围更广的问题。
对河朔藩帅而言,“官爵威命”往往体现出边际上的价值,还在于“官爵威命”有时还可以事后邀求,从而不一定在程序上总是首要的。成德王廷凑接掌节钺的经过等很多事例表明,官爵威命不一定总是要通过一味地向朝廷输忠来获得,恰恰有时就是借助强大的“河朔兵力”邀求而来,所谓“以打促谈”也是河朔藩帅常用的一种手段。因此,藩镇军人集团的集体利益诉求,可能才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基础。经过安史之乱打击的唐廷并没有足够的硬实力从根本上瓦解这个集团,所以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和方法来间接保持自己在河朔的影响力。形式上由唐廷任命的节度使,甚至有时可能还会暗合通过推举产生的结果,这在河朔的义武军节度使的选任方面曾有一例。②参见拙文《唐易定镇的张氏家族与陈氏家族——“河朔故事”研究之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唐末,幽州藩帅刘仁恭也曾言:“旄节吾自可为,要假长安本色耳。”③《新唐书》卷212《刘仁恭传》,第5986页。或道出了中晚唐幽州以至河朔藩帅接掌节钺的大致情况:这里的关键在于旄节已经自为或具备了自为的条件。唐廷授予的官爵则是一种“本色”,往往是藩帅登位过程中作为最后或准最后的一道工序涂抹上去的。若其他条件不具备,唐朝的官爵威命也无法发挥其作用。构成河朔藩帅权力基础的各种因素,其权重会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
三、“官爵威命”:唐廷的“软实力”
基于上述分析,唐廷的官爵威命到底发挥怎样的影响,关键还是在唐廷与河朔强藩的力量对比以及藩镇内部的形势。安史之乱以后,唐廷的力量始终是不足的,特别是财赋主要依靠东南,以经济力量为基础、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硬实力”毕竟有限,不足以支应所有方向上的军事行动,也没有能力总是采取赏赐赎买的手段获取镇兵的支持。这是河朔藩镇能够长期存在的基本外部条件。④金宝祥先生较早地指出割据藩镇出现的特殊条件,参见氏著《关于隋唐中央集权政权的形成和强化问题》,收于魏明孔、杨秀清编选:《陇上学人文存·金宝祥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页。唐廷尽管尝试过以硬实力来解决河朔问题,但无论是“建贞危机”的解决还是“元和中兴”以及长庆初年的河朔再叛,唐廷在与河朔藩镇“硬碰硬”的军事对峙中,大多处于被动的局面;少数占据有利形势之时,也往往要依靠河朔的力量(如魏博田弘正)来牵制其他河朔叛镇。在这种情况之下,通过承认河朔藩帅的世袭权利,转而授予其“官爵威命”,则是唐廷施展其“软实力”(soft power)⑤感谢王贞平先生给我的提示和启发(2019年9月5日在王贞平先生家中的谈话)。王先生认为“在古代亚洲,弱势一方向强势一方表示政治效忠是其运用软实力的主要方式”(氏著《多极亚洲中的唐朝》,贾永会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笔者从逆向的角度,并更加宽泛地去理解“软实力”:唐廷不能用硬实力特别是军事打击手段来实现控御藩镇的政治目的之时,利用天下共主的地位,施以官爵或封贡来对某些区域施加或维持影响,都可以姑且认作运用“软实力”的行为。不过,这种“软”明显具有相对性。“官爵威命”也代表了唐廷的权威,确认了河朔藩镇为唐朝治下的地方政区的性质。在没有找到更为贴切的概念之前,姑且用之。的一种表现。授予藩帅“官爵威命”本质上是一种安抚行为。允许藩帅父死子继,以土地传之子孙,固然是一种巨大让步,但藩帅们接受这些官爵威命,则在政治上明确了唐廷与藩镇分别作为施抚者与受抚者的地位,尊卑高下之分立判;也恰恰表示了藩帅们愿意留在唐朝的政治框架之内,以唐帝为天下共主。唐廷每每还可以“官爵威命”为激励机制,引导河朔强藩为自己所用。元和元年(806),唐廷讨伐西川刘辟,先后给成德王士真、魏博田季安、幽州刘济加为使相。⑥参见《旧唐书》卷14上《宪宗纪上》,第414、415、417页。大和元年五月,唐廷欲处置沧景李同捷,“犹虑河南、北节度使构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宪诚同平章事。丁丑,加卢龙李载义、平卢康志睦、成德王庭(廷)凑检校官”。①《资治通鉴》卷243,太(应作“大”)和元年五月条,第7854页。四位被加官的藩帅,有三位来自河朔强藩。会昌年间唐廷讨伐昭义军刘稹,承认“河朔故事”适用于河朔三镇,使得平叛战争顺利推进。唐廷也往往在平定叛藩之后给河朔藩帅甚至其文武僚佐加官。例如大和五年幽州节度使李载义入觐,因平沧景有功,“册拜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宗还派中使宣赐钱物良马,“下及宾佐将吏,无不广霑恩锡”;②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385《将帅部·褒异一一》,第4582-4583页。从各种资料尤其是近年新刊唐代墓志来看,会昌年间平定昭义之役,河朔藩镇多位将校在战后得到了唐廷的加官。③参见孙继民、李伦、马小青:《新出唐米文辩墓志铭试释》,收于孙继民主编:《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69页;《旧唐书》卷181《韩允忠传》第4688页。这都是唐廷成功施展软实力的具体表现。
由此,唐河双方近似于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得到唐朝的官爵威命者,自然也就具备代理统治地方的合法性。唐廷也自然维持了作为天下共主的合法性。所以,双方实际上达成了相互借重、各取所需、共同受益的战略平衡。
张国刚先生很早就敏锐地指出,河朔藩镇对唐廷具有依附性和游离性,④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88页。与河朔藩镇相类的归义军也有这种“既欲割据自立,又仰赖于中央的双重性格”,参见冯培红:《归义军官吏的选任与迁转——唐五代藩镇选官制度之个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1年版,第104页。对于深入研究河朔藩镇的样态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唐廷与河朔藩帅之间授受官爵威命,正是双方各取所需,相互借重的反映。藩帅借官爵威命提高自己在藩镇军民中的声望,朝廷借授予藩帅官爵确认与藩镇的上下关系。这种“授受”实质上是一种相互确认的过程,表明朝廷和藩镇双方互相接收到了对方发出的善意信号,是朝廷和河朔藩镇共同维系“河朔故事”的一种具体表现,这也是长庆以后,朝廷与河朔藩镇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相安无事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唐廷硬实力不足进而施展软实力来维系形式上权威的一种表现。河朔藩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仍是唐朝后期一种特殊的存在,内部还有另外一套规则和“故事”,并不完全按照“长安的逻辑”在运行。在河朔藩镇,藩帅只有同时适应这两套规则,才能立足,也即“上下不失,然后能久于其任”⑤《何弘敬墓志》,收于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壹》第126号,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