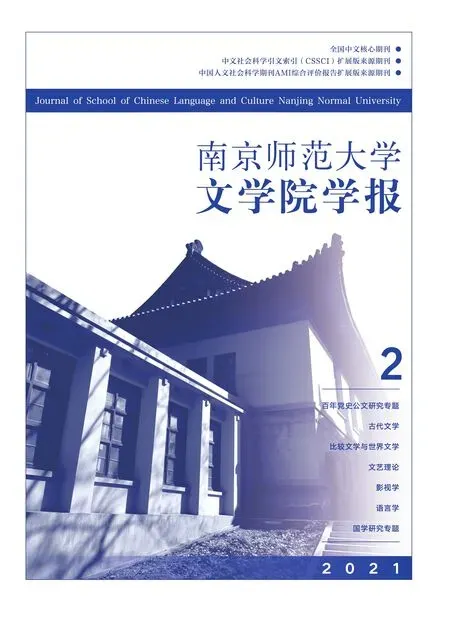“病毒电影”的类型经验与文化逻辑
2022-01-01周达祎
周达祎
(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全球性爆发,一批以流行性传染病为表现对象的电影,如《恐怖地带》(1995,美国)、《感染列岛》(2009,日本)、《传染病》(2011,美国)、《流感》(2013,韩国)、《泄密者》(2018,中国香港)等,因其与现实强烈的关联性,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广泛的传播和讨论。通过这些电影,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电影中出现的“零号病人”追溯、野生动物传播、消毒隔离、方舱医院、物资哄抢、新闻造谣、疫苗研发等桥段,竟像是现实生活的一种预演。不是电影表现了生活,而是电影照进了现实,原来现实处境下人们遭遇的对未知病毒世纪大流行的种种不安揣测,电影已经在某些程度上给予了想象性的回应。在居家隔离的幽暗岁月里,这些电影给了惊慌未定的人们许多慰藉,安抚了人们焦躁不安的情绪。而这些电影在网络世界的翻红,则促使人们对其进行重新梳理和归纳。
类型电影是商业电影机制下的一种程式化的电影创作方法,一方面它的主题、人物、情节、视听语言包含一套相对固定的形式惯例,另一方面它的故事总是反映了特定的文化,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类型电影不会凭空产生,它是依照观众的审美品味和选择偏好进行生产的,每一个类型的流行必然投射了某种社会大众心理,凝聚了大众的共享性期待。在研究“电影类型”和“类型电影”之间的区别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言语”的概念常被用以类比,[1](P7)两者是系统和个体之间的关系。类型的生产是充满弹性和张力的,类型的演化是一个历史积累的问题,是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类型电影不是一个自足的、周延的、覆盖的分类系统,它既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也没有恒定不变的子项与结构关系。类型电影的发展是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2](P76)而新类型的产生,则无意识地贯穿于这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它往往先于理论的概括发生。考察近年来频繁生产的以流行性传染病为主题的“病毒电影”,已然积累了一定体量的类型经验,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特定的文化逻辑。
一、灾难修辞:作为“超级传播体”的病毒
尽管以“病毒电影”命名一类电影的说法尚属新鲜,它是站在“后疫情”的时间节点向前回溯产生的概念,然而这些电影中出现的各种关于流行性传染病的想象业已成为其区别于其他电影的核心类型元素。学者秦喜清认为,“病毒电影”严格来说并非一个类型概念,准确地说它是按题材要素命名的电影类别,其共同点是以病毒感染作为叙事核心。[3] (P42-43)而陶赋雯认为“瘟疫电影”,或曰“病毒电影”,是灾难电影衍生的一种亚类型,并且具备了该类型专属公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和图解式的视觉形象。[4] (P52)“病毒电影”的概念,在两位学者的论述中已初显端倪,所谓的“病毒电影”指的是以流行性病毒的爆发为叙事主线,表现人类社会在应对突发的病毒传播时,政治、经济、医疗、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诸多应激反应及连锁影响的电影,是灾难电影的一种亚类型。具体而言,可纳入“病毒电影”之列的包括了:《卡桑德拉大桥》(1977,英国)、《伊波拉病毒》(1994,中国香港)、《恐怖地带》(1995,美国)、《惊变28天》(2002,英国)、《盲游症》(2008,巴西)、《感染列岛》(2009,日本)、《末日病毒》(2009,美国)、《解冻》(2009,美国)、《传染病》(2011,美国)、《铁线虫入侵》(2012,韩国)、《流感》(2013,韩国)、《全境感染》(2017,瑞典)、《泄密者》(2018,中国香港)、《尼帕病毒》(2018,印度)等。同时,可以无限蔓延的“丧尸传染”也被视为一种病毒,因此“丧尸电影”往往也被看作是“病毒电影”的一个变种而进行讨论,包括了《活死人黎明》(2004,美国)、《我是传奇》(2007,美国)、《美丽新世界》(2012,韩国)、《僵尸世界大战》、(2013,美国)、《釜山行》(2016,韩国)、《请叫我英雄》(2016,日本)等电影。
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病毒(Virus)指的是具有感染性的、严格地寄生在细胞内的、潜在的致病实体。它体型微小,结构单一,不能生长或进行二次分裂,只能通过遗传物质的增殖的方式繁衍。[5](P660)顾名思义,病毒作为“病毒电影”中最核心的、最具有辨识度的要素,在“病毒电影”的生产过程中,其生物学意义也被进行了二度加工,赋予了文化学的意义,形成了“病毒电影”专属的灾难修辞方式。
病毒最大的特征在于它快速传播的速率和无限蔓延的增殖。加拿大媒介研究者麦克卢汉曾提出一个极富盛名的论断:“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以电光源为例,电光是单纯的讯息,不具有媒介属性,然而直到电光被用来打出广告标语时,人们才注意到它是一种媒介。[6](P16-17)在这里,麦克卢汉强调了作为讯息载体的媒介的重要性,任何客观的物质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讯息的媒介。如果以传播学的观点考察病毒的传播,当年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则在病毒的传播过程中真正实现。
一方面,病毒本身就是一种超级信息,它负载的信息量虽然不大,却是一种“被加码的未知方程式”,短期之内难以破解。同时,作为一个信息源,它构成传播的条件又极为简单,传播途径又极广,通常情况下只要接触到病毒携带者的体液都会被传染,飞沫传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传播方式(在“丧尸电影”是被丧尸咬中的血液传播)。另一方面,病毒又是一种超级媒介,凡是病毒必有宿主。病毒自身的形态并不暴露在自然状态中,它是以寄生的形式在其他活体的细胞内存活下来,并继续向外增殖。所以,被病毒感染的人,通常也是病毒的携带者,是病毒传播扩散的介质。
电影《传染病》开篇就用一组微观的近景镜头细节,表现了病毒传播的这种无处不在与无时不在。例如,感染的香港男人乘坐巴士和搭乘电梯时,镜头都对准了他的手,表现了他与公共设施的接触;伦敦女人感染后,镜头表现了瘙痒难耐的她用手抓挠自己的皮肤;感染的美国女人回到明尼苏达的家中,与儿子亲昵地拥抱,两人双双感染;表现日本男人感染时,也聚焦了他在公共交通中的手部接触。电影《感染列岛》和《流感》,则以电脑特效的手段,模拟了病毒随飞沫在空气中流通的具体过程,同时也用一些近景实拍镜头表现了病毒在人体口、眼、鼻等黏膜部位的传播。同样地,《铁线虫入侵》也用特效镜头,展示了铁线虫是如何从口腔侵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蔓延的。
此外,病毒还有一大特征在于它的不可逆性。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新冠肺炎、非典肺炎、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等传染病的致死率并不高,可以通过医疗手段控制和治愈,但在电影中,为了强化故事的戏剧冲突,感染者感染病毒后往往难以控制病情,要么当即死亡,要么在短期内身体机能迅速衰退,最终也难逃厄运。即使在一些个例中,感染者尚未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也同样会被视为一个不可治愈者和传播者,遭遇歧视,甚至被强制掠夺生命权。
电影《卡桑德拉大桥》讲述的就是政府有意将一列遭遇了生化病毒侵袭的火车开向危桥卡桑德拉大桥使其坠毁,而列车上的人们察觉后发起自救的故事。《流感》中,面对病毒疫情的失控,在美国智囊的蛊惑下韩国总统执意封锁疫区,想要让感染者们和疑似病毒携带者们自生自灭。在这里,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建立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各种“安全技术”,旨在降低人口所面对的各种外在与内在的危机或风险,并用总体平衡来确保整体人口安全的一种新型“治理术”,[7](P116)却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毒爆发时瞬息变成了一种任意裁量个体生命的暴政。
这种不可逆性,在“丧尸电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丧尸病毒是起源于远古物种、邪恶宗教还是生化污染,人类一旦被丧尸咬中,就会感染丧尸病毒,沦为丧尸同类,失去人的各项生命特质,成为一具“后死亡”的“没有器官的身体”。[8](P150-154)如果想要解除丧尸病毒,只有一条路径,就是生命的终结和肉身的毁灭。而丧尸的生存机制也只有一种,就是攻击其他活体,丧尸总是以无限增生的形式存在。因此,丧尸对人的攻击与人的逃亡、反击,也成为了《僵尸世界大战》《釜山行》《请叫我英雄》等“丧尸电影”中的最为重要叙事动力和视觉图谱。
病毒“超级传播体”的特性成为了“病毒电影”的核心创意,这就使得“病毒电影”形成了有别于一般的灾难片的根基。在“病毒电影”中,灾难是被放大的,它并非个体的、局部的,灾难是可以无限扩张,乃至引发全球危机的。而相应地,“病毒电影”化解灾难危机的机制也必然是全球性的。可以说,“病毒电影”升格了灾难电影中灾难的布局,从而引向了现代社会人人都无法回避的关于全球化和共同体的哲思。
二、风险社会的集体性焦虑
类型是形式化的意义。美国类型电影研究者托马斯·沙茨认为,类型电影是一种社会力量,它虽然是个体作者风格的原创物,但必受到工业化电影制作惯例和观众期待的影响,类型电影是作者、出版者、观众三者共谋的产物,是一种集体价值和信念的仪式化表达。[9](P16)比如,西部片往往被看作是美国西部开发历史中自由、进取的拓疆精神的一种诠释和重塑,表征了文明对野蛮的征服与规训。[10](P29-31)那么,作为一种渐显类型的“病毒电影”,又体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观念呢?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现代社会称为“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的风险社会”,他认为虽然人类社会自诞生之初就始终伴面临着风险,然而进入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之后,风险的结构和特征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现代性也伴随着风险社会体现出来。[11](P1-15)文明的进步非但没有使得世界秩序变得更加稳定,反而将世界推向了危机四伏的失序状态,美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形容当今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12](P2)
风险犹如悬挂在所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不定时爆发,且一发不可收拾。风险在全球化的现代性历史转型中,也转变成了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如果说在过去,风险或者灾难还只是一种相对的亏损和伤害的话,在这个疆界消逝的科技全球化时代,风险也必然全球化了。[13] (P1)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14](P11)所谓的“世界的压缩”,是指随着交通运输、信息传播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时空观念的演变。而“整体意识的增强”,则是指随着资金、商品、人才、信息的跨国流动所带来的整个世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现代社会任何人都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因此,风险社会既是未知性的,也是整体性的,更是毁灭性的。这种对风险社会的集体性焦虑,也投射在了“病毒电影”之中。
对病毒源头的追溯和表现,成为了许多“病毒电影”中贯穿的一个跟踪性情节,推动了叙事发展。在《感染列岛》中,一种名为“诅咒”的致人器官急速衰竭的传染病,起源于太平洋某小岛,经由蝙蝠传染给禽类,再传染给岛民,最终传到了日本,疫情持续经年,造成日本3950万人感染,1120万人死亡。《流感》的病毒起源于一节运往韩国的偷渡集装箱,感染的偷渡客将病毒跨境带到了韩国,并在迅速波及了整个韩国。电影《恐怖地带》一开始,就是美国在非洲的一个雇佣兵军营发生了病毒感染,于是美军下令炸毁了整个军营,试图将疫情扼杀在摇篮之中,没料到若干年后,这个诡异的病毒却悄然升级,通过一只走私的非洲白猴,传到了美国,并于48小时内在美国快速扩散。而《传染病》对病毒起源和传播的设计则更为巧妙,作为悬念的病毒起源在影片最后一刻才被揭晓——昼伏夜出的蝙蝠叮咬了生猪,将病毒传给了生猪,香港厨师制作料理时,手指接触了生猪的牙齿,感染了病毒,厨师再和美国女人握手,把病毒带给了她,就这样一环接一环,病毒传遍了全球。
在这些电影中,机场、巴士、高铁、游轮、集装箱等交通设施频频出现,成为了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英国学者鲍曼认为,现代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无处不在的各种人的流动和物的流动,他以流体类比,将现代性称为“流动的现代性”。[15](P1-3)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希奥提出了“竞速政治”的概念,他列举了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各种“提速”,认为是速度重构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并宣称从来就没有“工业革命”,有的只是“竞速政治的革命”。[16] (P80)速度是一种权力支配的形式,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以速度政权为基础的“竞赛社会”,掌握了速度就掌握了权力。[17](P26)全球化的根基是各种不断加速的交通和讯息技术,加速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加速社会”,任何一种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病毒一旦产生,都会迅速传播开来。对速度的迷思,也演变成为了对风险的焦虑,在“病毒电影”中轮番上演。
同时,病毒的跨物种传播也成为“病毒电影”聚焦表现的一个传染特性,无论是《解冻》中北极猛犸象尸体释放的远古病毒,《釜山行》中感染的公鹿,还是《极度恐慌》中作为病毒中介的白猴,跨物种传播使得病毒的危害与爆发变得更为叵测,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给人类招致灾祸。而《传染病》和《感染列岛》中蝙蝠传播的未知病毒,与新冠疫情的爆发形成了某种现实关联性,更是指向了一种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即便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取得了诸多成绩,根本性地改变了人被动屈从于自然的关系,然而在大自然潜在的种种未知面前,人类非但不是一切的主宰,反而显得渺小无力。人类一味盲目地崇拜科技和过度地开发自然,终难逃被自然反噬的厄运。因此,“病毒电影”中大量出现的野生动物感染源并非偶然,而是体现了在科技昌盛时代人们对大自然的未知因素的忧思和恐惧。
三、 隔离与免疫:重置的人际距离与社会秩序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肺结核、癌症、梅毒、艾滋病等疾病的世俗理解,并宣称看待疾病最好的方式是尽可能地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18](P5)然而该书的风靡,却恰恰印证了一个事实,即作为身体异常的外化表现的疾病,在世俗社会的理解中往往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尤其是传染病,总是被看作一种污染,让人联想到过错的行为。患者也因此备受歧视,甚至为了切断感染源,患者常被暴虐对待。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粗暴地对待感染者显然有违人道主义和社会伦理价值,然而病毒传播又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物质化过程。如何在确保疫情不扩散的前提下,保障感染者的权益,成为了现代社会医疗卫生和行政管理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扼制病毒疫情通常需要一个过程,回顾人类与疫病的历史,黑死病、鼠疫等传染病毒在很长一个时间内是与人类社会相伴共生的,贾雷德·戴德蒙甚至将病菌、枪炮与钢铁看作是推动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三大要素。[19](P207)病毒疫情爆发时,原本现代社会所创造的人与人之间无障碍的互通将被迫中止,亲密无间的人际距离将遭遇重置。隔离与免疫作为新型人际距离的两个关键词,成为了“病毒电影”中的重要议题。
面对未知的病毒,隔离被视为防疫扩散的最佳手段。隔离是一种对物理空间的阻断,张生教授认为,在疫情中采取“封城”等隔离措施,其目的在于采用“空间冻结”的方式控制疫情传播,在此基础上对感染人群的区隔和医学监视,其实质是对病毒的区隔和医学监视。[20](P36)在《传染病》《恐怖地带》《泄密者》等“病毒电影”中,用于隔绝物理接触的护目镜、防毒面罩、防护服成为了醒目的视觉符码。在《流感》中,面对疫情扩散的失控,韩国政府动用军队设立路障将平民封锁在疫区。《僵尸世界大战》中,人类的幸存者筑起了厚厚的高墙,以抵抗丧尸的侵入。而《感染列岛》中出现的将体育馆改造成方舱医院的情节,更是让人惊诧电影是现实的一种预言。
然而“空间冻结”与不断流动和加速的全球化却存在着天然的深层矛盾。德国学者哈特特穆特·罗萨认为,国家、政治和军队,曾经是人类迈向现代的经典加速器,在晚近却变成了现代的加速障碍或制动器。[21](P395)当流行病毒爆发,加速社会被迫制动时,旧有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就被放置到一个核心的位置进行审视,原本社会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在《传染病》中,网络自由撰稿人艾伦借疫情发起了灾难财,他谎称自己感染并服用了所谓的特效药“连翘”。谣言为他带来了450万美元的收入,却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对“连翘”的哄抢,药店被偷抢一洗而空。《恐怖地带》详尽地描述了美国政府对待病毒疫情的监管模式和预警机制,无论是对病毒源头的隔离,还是对数据库的监控,亦或是最终的防御系统,不可谓不森严。然而面对病毒大流行的袭来,军方和疾控中心却总慢一步,官员们各怀鬼胎,只想掩盖真相和争夺功劳,却枉顾感染者的性命。显然,这些“病毒电影”蕴含了强烈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虚假民主制度的批判。而“丧尸电影”则更为直接使用了转喻,丧尸对人类世界下意识和无休止的攻击,可以被看作是对旧秩序本能的反抗。
从生物学角度而言,病毒的侵入必须通过活体的细胞介质。免疫作为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它能从细胞源头建构一种防御机制,破坏和排斥病毒进入细胞,以维持人体的健康。在现代医学的疫苗接种技术实现之前,人的病毒免疫抗体只能通过感染后的自愈获得。也就是说,免疫的获得可以分为自然生成抗体和人工接种疫苗两条路径,这成为了“病毒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情节。
首先,病理学上的免疫是通过自我主体的识别,排除一切异己“他者”的过程。免疫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的辩证法。免疫学上的他者是否定的,侵入自我个体并试图否定它。如果自我不能够反过来否定侵略者,它将在他者的否定下走向灭亡。[22](P7)健康人与感染者之间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让免疫成为了一种具有等级梯度的生命权力。特权阶层通过对医疗资源的垄断,可以轻易地优先获得免疫。病毒的突发和快速传播,打破了社会阶层的平衡,放大了阶层差异的矛盾。平民阶层受财阀组织和强权政治的摆布,他们无法发声,无法自述,成为了灾疫的头号牺牲品。《卡桑德拉大桥》和《流感》都控诉了强权政府在突发疫情中粗暴地牺牲无辜平民的暴政。《传染病》中,政府对首批研发成功的疫苗进行了公开的摇号分发,然而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基弗却以权谋私,为自己和妻子艾琳抢先注射了疫苗。《泄密者》更是将关注的焦点指向了医药产权垄断制度的漏洞,揭露了利益熏心的无良药商“囤积居奇,养疫自重”的丑陋嘴脸,同时也批判了大财阀对传媒的控制,触及了对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反思。
其次,免疫意味着身体属性的重塑。免疫者一方面体内携带病毒,另一方面病毒的毒性又无法完全作用于他身上,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病毒携带者是不是病人?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叫作“伤寒玛丽”,该事件发生在20世纪初的美国,主人公玛丽·梅隆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她在纽约从事家政服务工作。玛丽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但她体内却携带有高浓度的伤寒杆菌,因而导致了雇主家庭多人相继感染伤寒。“伤寒玛丽”也因此被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定义为首例“健康带菌者”。《伊波拉病毒》中,阿鸡就是千万分之一概率的男版“伤寒玛丽”,他体内含有“超级抗体”,携带大量致死病毒自己却安然无恙,“非人”的身体使阿鸡愈发疯狂最终走上了罪恶的深渊。《釜山行》中,感染了丧尸病毒的年轻情侣珍熙与荣国在变成丧尸前的最后一刻仍紧紧相拥,石宇中毒后仍用最后力气将自己和丧尸锁在车上,以此换取盛京和秀安平安的一幕更是令人动容。电影中“伤寒玛丽”的隐喻,让人注意到了人体与病菌的复杂关系,并开始反思“健康”与“疾病”二元对立的界定标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肆意污名化病毒的一种回应。[23](P423)
结 语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原本平稳运行的世界拖入了短暂的混乱失序之中。尽管中国政府率先抑制住了疫情扩散,但在全球其他国家疫情仍未见明显好转。许多专家预计,新冠疫情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人类共存。因与现实世界的强烈指涉性,作为一种新兴电影类型的“病毒电影”,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拍摄实践都将持续发展。
现有的“病毒电影”虽然通过对突发灾疫的营造,暴露了人类社会潜在的诸多问题,体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然而大量的“病毒电影”仍停留在“提出问题”的阶段,只见暴露和反思,对于灾难的解决和预防的方案仍是悬置的。对于病毒的未知性和人类未来的命运,此类电影总是流露出一种悲观的态度。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新冠疫情的抗击过程中的阶段性胜利,向世界提供了对抗病毒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事实证明,只要人类团结一心,科学应对,未知病毒并非不可战胜。期待在未来“病毒电影”形态的发展中,看到越来越多对解决问题的智慧和多元化的价值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