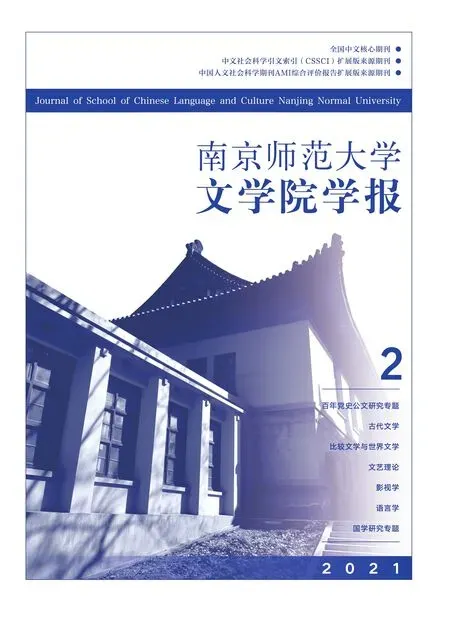巡回放映队与电影的乡村扩散
——以民国时期的浙江为中心
2022-01-01田中初郭凯云
田中初 郭凯云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上海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上海 200433)
在新电影史和媒介考古学的理论视野中,“电影不再仅仅是关于艺术美学的历史,而被更多的看成一种媒介,是世间万物媒介中的一种。”[1]放眼人类历史,可资利用的信息传播媒介确实品相万千,但其中任何一种媒介要成为大众媒介,都必须有一个逐渐与民众关联的过程,否则其存在的合法性无以生成。所以,如果以历史的眼光看,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如何与大众共存以及相互介入和运作,是一个值得拓展的问题。
电影随着西风东渐舶入中土之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走向大众的过程。相比于西方国家,近代中国是一个缺少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条件的传统社会,除少数大城市外,即便是散落各地的市县城镇,也还是与乡村差异不大,因此城市人口非常有限,绝大部分的人们还是生活在乡村环境中。在此背景下,电影向近代乡村社会弥散既有必要,但也面临更多的困难。当然,有困难并不意味着无所发展。1930年之前,电影虽然早已进入中国,但主要仍限于城市范围,所以中国电影史几乎就是城市电影史,但是,1930年代开始的电影教育,却让电影走入了乡村,开始嵌入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2]这个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民众教化、训政统治以及抗战动员等需求,推动组织了电影的巡回放映。在电影走向乡村的过程中,电影这种新型大众媒介开始了与乡村民众群体的结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政府的推力下,电影走向乡村、接近乡民如何可能?本文以民国时期浙江省的实践为样本展开回梳,试图再现中国早期电影传播史中某些未被关注的“失踪的地方”和“失踪的人”,并以此饱满电影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地方性实践”和“地方性存在”。(1)在过往的研究中,电影观众基本上就是“失踪者”,作为影片发行地和放映点的除上海之外的绝大多数城镇都是“失踪的地方”。(参见冯筱才《从问题到史料:中国电影史的重构与再写》,载叶月瑜主编《华语电影工业:方法与历史的新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4-5页。)
一
二十世纪初,电影放映在浙江的杭州、宁波等城市开始陆续出现,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批电影院。这些影院的存在,支撑了电影在城市的日常放映。然而,在政府组织的教育电影推广之前,电影在浙江乡村只有零星放映,主要以如下方式施行:一是伴随商品推广的放映。一些外国商人利用放映电影招徕顾客,借机推销农药肥料以及日用消费品等。二是地方公益放映。地方人士、地方组织或者地方政府出于满足节日庆祝、社会动员、好奇娱乐等各种需求,也会借用电影放映的形式。三是少数商业盈利放映。一些人看到电影放映可能带来的利益,也尝试到乡村进行商业放映。四是配合教会宣传的电影放映。总体来说,这些电影在浙江乡村的放映只是蜻蜓点水,既无规模,也不持续。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主导的政府一方面重视利用电影等大众媒介对民众进行启智开化,另一方面又借此加强党国意识形态的灌输。到30年代以后,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民众动员变得迫切,政府对大众媒介也就更为倚重。鉴此,电影就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新型教育工具,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1935年,教育部下令各省市教育厅组建电影巡回队,到偏僻乡村放映。[3]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指导二十多个省份成立了81个教育电影巡回施教区。[4](P1-2)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虽然教育电影推广受到较大影响,但“动员民众,首重宣传”,“电影教育,尤为各方所重视。”[5]
既然教育电影负有“接近民众”“联络民众”“教育民众”的使命,[6]那就不能忽视生活在乡村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教育对象”。然而,当时电影事业的发展范围只限于城市,“全国三万万八千万的农民都未曾得到关于电影的享乐。”[7]据1932年对浙江省的统计,农民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近70%,[8](P2)所以政府当局就把面向乡村民众进行电影教育推广提上了议程。1934年3月,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陈布雷向省政府提议成立电影巡回队到各县巡回映演,并要求“巡回路线注重农村”。[9]1936年8月,根据教育部《各省市实施电影教育办法》,浙江将全省各县依照旧府所属划为11个电影教育巡回区,每区各成立一支教育电影巡回队。[10](P38-39)1938年11月,教育部为突出电影的教育功能,改“放映”为“施教”,要求各省市改办电影教育巡回施教区。[11](P376)浙江省教育厅随之把原来的学区电影教育巡回队更改为教育厅直属的5个电影巡回施教队。[12]1941年,因部分地区陷落日寇之手,省教育厅又重新划定8个电影教育巡回施教区。[13]对于这些电影巡回队,省教育厅与各级地方政府合作,从经费、物资、人力等方面予以保障,维持电影的放映活动。正是有了电影的巡回放映,浙江的乡村民众也就有了接触电影的可能。
二
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电影借助巡回放映队的渠道开始制度化、规模化地往浙江乡村扩散。
1934年5月,省教育厅成立第一支电影巡回队后,八个月的时间里组织了五期巡回放映。这些巡回放映到达了许多乡村,其中1934年6月份的第二期巡回放映到达过的乡村有:萧山的白鹿塘、临浦、尖山、湄池、直埠、白门;诸暨的牌头、安华;浦江的郑家坞;义乌的苏溪、义亭;金华的孝顺、塘雅、竹马;汤溪的古方、湖镇;龙游的安仁、樟树潭;衢县的廿里街、后溪街;江山的贺村、新塘边等。[14]到1935年5月,省教育厅又成立了第二支电影巡回队,两队分别到全省各地巡映,产生了更加广泛的效果。1936年第一支电影巡回队在湖州地区放映时,观众达到17万人以上,第二支电影巡回队在绍兴地区映演时,观众达到20万人。[15]到1936年11月,两支电影巡回队已经到过76个县市,以至于“穷乡僻壤,莫不有电影巡回队之行踪,妇人孩提,莫不有电影巡回队之印象”。据统计,第一队的观众约170万人,第二队的观众约93万人,总共约263万人,占到了全省人口的12%。[16]
1936年,浙江省根据教育部要求,把全省各县市划分为11个电影教育巡回区,每区都有一支放映队。依据这个计划,全省各地都被纳入电影放映范围,电影往乡村空间的扩散范围更广。由于地缘便利以及经济社会条件相对优越,杭州周边以及浙北、浙东地区推广电影开展较早。1936年秋到1937年春,省第三学区电影教育巡回队先后在湖州下属各县二十多处乡镇放映电影百场以上。其中吴兴县境内共映56场,观众累计约2.7万余人。[17](P110)宁波学区的第四电影教育巡回队自1936年4月至1937年3月,前往石浦、象山、镇海、南田、鄞县、定海等地讲映电影教育106次。[18](P7-8)台州学区的第六电影教育巡回队于1936年9月10日到11月22日之间,一共在临海、黄岩、温岭放映了46场,每场观影人数达到八九百人以上,三四千人也是常有的事,总共观影人数达到11.2万人次。[19]抗战全面爆发后,浙江部分地区沦陷,经济政治社会重心往浙西、浙中、浙南地区迁移,所以,电影教育随之也往这些地区推广。1938年8-12月,省第七学区教育巡回队在金华地区8个县放映120场,放映地点遍布城乡,比如在汤溪县,就曾到过洋埠、王侠谷、伍家圩、罗埠、中戴、莘畈、厚大等村。[20]在武义县,到过白溪、东皋、苦竹、下杨、履坦等村。[21](P267)
随着抗战形势恶化,原有的学区电影教育巡回队模式实施困难,且宣传动员又愈加迫切,省教育厅就统合学区电影教育巡回队为直接管辖的电影巡回施教队,并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开展工作。1939年上半年,省第二电影巡回施教队到富阳等10县讲映,观众总人数逾13.7万。[22]1941年,省第一电影巡回施教队来到义乌,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在前流、稠城镇、前洪、夏演、上溪、江湾、倍磊、田心、毛店等村镇放映电影。[23](P524)即使在抗战形势非常困难的1942年,仅有的两支电影教育巡回施教队也放映了184场,观众人数达到18.4万人。[24]
通过电影巡回放映,大大推动了电影在浙江的扩散。据笔者统计,在现在浙江省总共65个县市中,因巡回放映而在该地首次放映电影的县共有15个,大约占全省县市数的23%。(2)根据《浙江电影纪事(1908-1990)》一书以及浙江省各地史志资料等进行统计。可以说,通过电影巡回放映的形式,电影这种新型的电子大众媒介已经在浙江实现全域化的散布,让农村成为电影传播的新领地。
三
“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施放出来一样。”[25](P42)当电影突然出现在乡村民众的生活中时,“看电影”成为趋之若鹜的一种新奇体验。1934年5月,省电影巡回队前往浙赣铁路沿线县市映演,“在各地映演时,不特当地民众空巷,且有自五十里外赶来者,在兰溪南门溪滩映演时,观众竟达两万。行踪所及,不特盛况空前,其给予民众印象,亦至深刻”。[26]当电影巡回队到绍兴下方桥村放映时,有人这样描述:“永没有映演过影戏的地方,经日中一番的宣传后,轰动得人心惶惶,掀起了一阵阵惊奇的波浪,人人俱额望着太阳的下山,祈待着夜神的速降。能容千余人的西山庙,在夜色苍茫中,已饱孕着簇簇的人头,连着壁的一角,也挤得紧紧的,其实这时离映演的时候还早哩。”[27]浙江省第三学区电影教育巡回队在湖州城乡巡映时,所到之处,观众扶老携幼,接踵摩肩,大有万人空巷感,可谓一时之盛。[28](P111)据省第六学区教育电影巡回队的一名队员回忆,“农村从未看过电影,有些地方连幻灯片也没见过,因此,放映队到来简直是天大喜事,人们老早吃了晚饭,端了凳子在广场上占了位置,迟来的只好站在后面,一些小孩子还爬到四周的墙头和树上观看。”[29](P261)1937年2月,电影巡回队来到宁波镇海小亹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村姑村妇都来了,有许多还穿着平时放在箱子里,非做客人不穿的红红绿绿的新衣服,两三个一堆一堆的站着在谈论”。[30]电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也带来了节日般的欢愉。
曾经参与电影巡回放映的周凯旋写下过这样的体会:电影放映的效果,“城市不如市镇,市镇不如农村,而交通便利的农村,又不如交通阻梗的农村。若本队在新登县属映演时,观众有身携干粮,自二十里以外赶来的。”[31]电影巡回队到达各地时,地方上“或派员挽留,或推人邀请”,教育电影之能深入民间,民众欢迎教育电影之热烈,真令工作人员“鞠躬尽瘁,死亦何憾”![32]
有学者认为,“在最初电影放映的那些年头,‘活动电影机’和‘活动影像’作为新奇的玩意儿,周而复始地震撼着一批批首次看见它们的人们。而早期电影放映的场所,其实更像一个演示新奇事物的空间,电影观众在那里,看的往往不是短片,还有被展示的影片播放的机器。”[33](P5)在乡村民众的眼里,电影放映机器本身就是神奇的装置。“马达的声音似断似续的呐喊起来,观众的心,也跟着突突的跳动着,造成全场一瞬间的静默。”[34]乡民第一次接触电影,会让他们感到十分诧异,甚至有人认为电影是鬼在演鬼戏。[35]1938年电影巡回队到偏僻的温州泰顺县放映,那里的山区民众第一次看到电影,“当银幕上的汽车从远处直奔而来,惊得银幕前的观众哗然散开,甚觉新奇有趣,于是纷纷要求放映队重放几回。”[36](P38)电影技术对乡村民众的新奇冲击,让时人对此评价甚高:“电影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山野农村的民众,对于这一机械化电气化的有声影片的享受,简直是梦想不到的幸福,因之电影的在山野农村放映,是一种传播现代文明的福音。”[37](P149)
当然,电影的内容更是让乡村民众感到新鲜并受到教育。浙江省教育行政部门希望利用电影来启迪民智、复兴农村、推进民众教育,因此当时的电影巡回放映主要以教育影片为主,分为科学普及片、技术推广片、教学片以及军教片四类。[38](P4)这些电影拓展了民众的科学知识:看了《日光的力量》之后民众明白了“一切东西,都靠太阳生长”;看了《齿的保健》之后大家懂得“牙齿是要常刷的”;看了《消化》后了解到人体内像一部机器。对以劳动为主业的乡村民众来说,教育电影更开阔了他们的农业眼界:看了《丝》的教育电影,乡民觉得“假如能照东洋人的方法养蚕,蚕丝的价值总会贵些”;看了《棉花的生长》,民众感叹国外的一个棉花絮抵得上我们的四五个;看了《农场》,乡民们艳羡外国的鸡鸭猪羊“真大,真多,真肥”![39]
对于政府利用电影来实施教育的意图,观众大多能理解。据1937年第六省学区教育电影巡回队的一份报告记录,观众认为电影是政府因为乡下人看不到电影所以特意送来的,同时也希望通过看电影能“懂得一些道理,晓得一点普通知识”。[40]对于脸朝土地背朝天的乡村民众来说,经由电影媒介传递的现代科学知识,不啻打开了原有地方知识以及传统经验之外的一扇“天窗”:“媒介抵达之处,既是世界所在之‘界’,同时也是‘新世界’敞开之时。”[41](P5)
四
民国时期政府组织的电影巡回放映始于三十年代终于四十年代,这一阶段与抗战时期大多叠合,由此,电影具有的宣传动员价值被社会各界寄予很高的期待。“在最短期内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战情绪,电影就是最有效的工具”,它会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表现为一致的行动。[42](P37-38)鉴于此,电影界的前辈史东山就认为要动员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大众,电影就是最好的工具。[43]电影评论家施焰在给中国电影界的建议中公开提出“电影下乡”的口号。[44](P4)在此种语境下,国民政府利用电影巡回放映来进行面向乡村的抗战宣传就显得非常合宜了。
在抗战早期,电影巡回放映队会选择一些诸如《防毒》《防空》之类的国防片。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电影巡回队就特别选映了一些抗战的时事片和故事片,更直接地激发民族意识和抗战情绪。1939年4、5月间,省教育厅第一电影巡回施教队在昌化、於潜、临安等地放映《保卫我们的土地》等影片宣传抗日救国,当映到汉奸、日寇受到惩处时,观众无不拍手称快。[45](P92)1939年9月,第四电影教育巡回施教队在青田放映《抵抗》《热血忠魂》等影片,“当映至《热血忠魂》日军暴行及范世芳旅长慷慨激昂奋身杀敌情形时,观众情绪极度紧张,尤其是映至日机被我机击下情形,全场观众一致欢呼,掌声雷动,热烈情况为空前未有云。”[46]电影放映还常常与抗战宣讲活动相结合,扩大宣传效果。平时举行救亡宣传会比较困难,“不是参加的群众寥寥,就是演讲者乏人,但电影队到了,就不愁没有群众”,所以巡回放映队常在放映之前举行救亡宣传会,省第二电影教育巡回施教队在1939年就结合电影放映举办了105次宣传会。[47]
电影对乡村民众抗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是明显的。第二电影教育巡回施教队的一份报告记录了观众在看完电影后的一些交谈:“还说我们中国没有飞机,你看到昨夜我国的飞机轰炸日本人吗?呵呵!真是了不得。”“刘老四这家伙太不争气了,我们中国人怎好替日本鬼子做汉奸呢?结果总不得好死。你看到么?到日本鬼子那里当汉奸,真的要打毒药针哩!该死,那些汉奸。”文章还提及,配合银幕上的播放内容,观众不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8]就这样,电影放映队通过播放救亡影片,结合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有效地激发了观众的主观情感。“感受电影画面的实际行动每一次都会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集群,一种在心理上这样或那样联系在一起的集群。”[49](P327)这种共同体的感觉,正是全民抗战的基础。
电影以其逼真以及低接受要求等特点,有利于面向乡村民众发挥宣传鼓动作用。有学者认为,“(电影)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让信息更多在口语的层面传播,摆脱了对文字的依赖,使传播的空间更加广大,信息的扩散更加迅速,打破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地域和文化隔阂,让领袖、军人、敌人这些符号的形象更加鲜明,因而在抗战时期显得特别重要。”[50]基于此,我们可以认定:电影是文化抗战的重要力量,而巡回放映队是电影抗战在乡村地区发挥效用的最重要实现路径之一。
结 语
由于国民政府组织的电影巡回队的存在,电影这种新鲜的媒介开始深入到深山僻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电影传播城乡严重不平衡的状态。同时,电影向乡村社会的“下沉”,也增进了乡村民众对电影新媒介的认知,并借此产生扩张现代新知和凝聚民族意识的效用。乡村民众和电影的初步连接,为今后的“进一步介入和相互运作”打下了基础。(3)如解放初期,金华县孝顺区某农民代表就向县政府提出“电影下乡宣传”的请求。(参见《请求政府电影下乡宣传案》,金华市档案馆C026-001-011-120。)事实上,民国时期电影巡回队也曾到过该地。
概言之,民国时期的电影巡回队对推动乡村民众与电影的关联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但冷静观之,也不能对此估计过高,主要原因有四:其一,覆盖度有限。电影巡回队数量非常有限,让电影到达每一个县城和人口较多的部分中心村镇已属不易,对大多数村庄来说毫无机会。其二,持续度有限。从整体上看,上个世纪30年代的电影巡回队工作开展得比较正常,而到40年代就慢慢开始力不从心。因此,当时的乡村民众只是尝到了“电影的味道”,还远远谈不上将电影嵌入日常生活。其三,兴趣度有限。巡回队放映的电影主要以教育类电影为主,与乡村民众的实际生活和阅看兴趣都有些距离。(4)如1936年9月第六省学区教育电影巡回队在临海巡回放映时,其中有一部《防火》的教育影片,因为时值久旱未雨,所以放映此片有一定的适宜性,但其中的内容涉及的是实验室防火、电力绝缘装置与防火、避雷针与防火等内容,“大部分的乡民,因为没有用电的经验,对本片还不够资格明了,这也不免使人有些遗憾。”(参见《联合各县市举办教育电影巡回队》,《浙江教育》1937年第3期,第92页。)相比之下,少数放映的娱乐片则更受欢迎。(5)正如某教育电影巡回队反馈的那样:“滑稽片还可以看看,教育片太没意思了!”“这种片都不好看,总是上海电影院映的那种爱情片、武侠片等来得好看!”(参见《浙江省第六省学区教育电影巡回队第一次巡回报告》,《浙江省民众教育辅导半月刊》1937年第11-12期,第661页。)其四,理解度有限。当时放映的电影基本上是无声电影,配以字幕说明和讲映员讲解。一些来自国外的教育电影大多配以英文说明,观众中不要说懂得英文的凤毛麟角,即使能听懂讲映员解说的人也不多,比如讲映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解释氧气、二氧化碳、淋巴液等名词,观众还是一片茫然。[51]对很多乡村民众来说,看电影可能更是一种视觉猎奇,而具体的内容理解与否反倒是其次了。
民国时期电影巡回队所存在的种种不足,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解决,但毕竟对早期电影的乡村传播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也对后续者提供了值得反思的价值。新中国成立之后,对电影的乡村传播更为重视,民国电影巡回队曾经存在的放映队数量少、达到乡村少、放映次数少、放映内容单调等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化解。也许,两者之间的效力不可同日而语,但政府的推动力量却是共通之处。这再次印证了近代中国社会情境中大众媒介发展的独特道路——政治驱力下的大众媒介普及化。当然,这样的一种发展路径也就决定了电影的教化功能更被重视,其宣传效果也更期待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