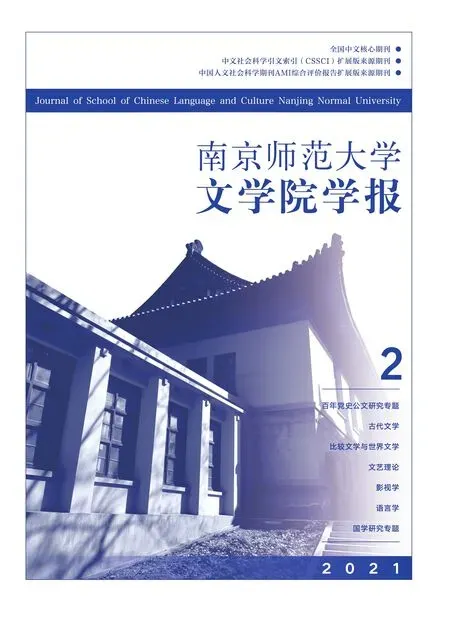论《典仪》的“现象身体”与文化转型
2022-01-01胡碧媛
胡碧媛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美国本土裔女作家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的代表作《典仪》(Ceremony)初版于印第安文艺复兴繁荣期的1977年,而20世纪70年代也见证了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界的身体转向。自柏拉图(Plato)以降,西方思想界有关身体的学说理论层出不穷,但其核心观点均对身体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或是漠视态度,发展到笛卡尔(Descartes)的身心二元论,则彻底将身体贬至心灵的对立面,固化身体的附属地位将之放逐于精神与思想体系之外。20世纪三大理论系统,即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为代表的现象学流派(phenomenology)、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为代表的人类学理论及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谱系学派,为当代身体研究奠定了关键性的理论基础,女性主义、消费主义及文化叙事等当代思潮的发展进一步推动文化研究中身体转向的到来。
《典仪》自出版后即获得学界的好评与广泛认可,丰富的研究文献旨在探讨压制族裔文化的殖民暴力文本再现,关注作家倡导文化融合的整体观和热忱的人文情怀。尽管研究者选择了时空模式、生态批评、物质文化等角度进行讨论,但大多将作品的感性化表征进行理性化阐释。需要强调的是,作品所试图传达的丰富主题均来源于身体功能失常的应对需要,即解决主人公塔尤(Tayo)二战后表现为梦魇、呕吐、视觉幻想等身体异常的创伤应激障碍(PTSD),是如何从身体出发回到身体的策略与机制问题。另外,关于小说中神秘的墨裔舞女,美国本土裔评论家宝拉·冈·艾伦(Paula Gunn Allen)认为她是象征印第安创世女神的夜天鹅(Night Swan),并指出无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或是白人,他们都害怕“改变”[1](P92)。对塔尤的创伤复原起到关键作用的药师比托尼(Betonie)认为,塔尤的治愈“是个转型问题,需要密切关注的是改变,和生成的过程”[1](P120)。那么,“转型”“改变”具有怎样的文化指向?与“文化融合”是否具有一致的文本内涵?本文认为,《典仪》的创作呼应了身体转向的文化趋势,西尔科对根植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现代理性危机有清醒的认知,其建构感性与意识结合的身体主体,旨在回归身体与世界共有共存的始源一致性,具有生成意义的文化转型。
一、混血身体的边界客体化
身为白种男子与印第安女人的私生子,塔尤的身体带给他的是三重边界冲突的文化经验。首先,塔尤面临所生长家庭环境的边界区隔。塔尤的母亲年轻时基于美好的幻想,急于摆脱印第安身份,接受欧裔文化同化,与白人男性交往并产下塔尤后,将幼子交给家人即离家不归,落得衣不蔽体、疯癫而亡的悲惨结局,“除了脚上的高跟鞋,她完全赤身裸体”[1](P65),身体的耻辱表征殖民压制与权利话语之下族裔主体之边缘性,从而将意识与身体同步客体化。塔尤生长在外婆(Grandma)、舅舅乔西亚(Josiah)和姨妈(Auntie)一家组成的大家庭之中,从小便体会到“姨妈对他妈妈所作所为深以为耻,因而姨妈也以他为耻”[1](P53)。塔尤与姨妈的儿子洛基(Rocky)相伴成长,但他的浅色皮肤时时提醒姨妈有关塔尤族裔身份的异质性。她禁止洛基与塔尤分享互动,竭力使洛基与塔尤减少交往。姨妈在家里的话语权,表明印第安族群的母系化权力结构,她与善待塔尤的外婆截然不同的态度,又代表了印第安族群内部不可避免的权力压制。然而,与族群传统具有高度认同感的西尔科尊重母系化权威,文本以姨妈的话语霸权反思的是经殖民化改写的族裔文化逻辑。姨妈“尽全力保护家人免遭村子里的谣言伤害”[1](P27),为此不得不边缘化塔尤,这种种行为源自整个家族被族群区隔的焦虑。姨妈选择从家庭内部与塔尤划分边界,旨在确保家族与拉古纳族群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塔尤自认最理解姨妈,理解她说话的“言下之意”,在塔尤看来,“她害怕陷入旧时的方式。一种古老的感性……人们共享同样的意识”[1](P62)。西尔科所表达的这种古老感性,指的是本土裔族群的古老传统与自然智慧,是对世界与生命运转方式的理解,是世界万物原初的共存共生模式。然而,“基督教将人们彼此隔绝,试图将族群个个击破使每个人孤立存在”[1](P62)。姨妈屈从于基督教的价值观,对现实产生认知障碍,这一认同危机在揭示殖民文化悖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现代进程中,对立性思维与资本的共谋剥夺了人的生存与世界秩序的本真。
其次,塔尤的混血身体也面临着欧裔文化的操控与排挤。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杂糅理论旨在以本土文化对宗主文化的反殖民,“解决被殖民者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权力话语时的抵抗能动性问题”[2],而西尔科的混血身体显然是接受同化的产物,陷入的是被客体化处理、被异化评价、福柯式的被征服困境。原生族群的边界处理并不意味着白人文化的认同接纳,殖民权力话语将混血身体利用为“铭写事件的场所”,“不断地转换、变化、改观和重组”,完全受制于“身体的控制技术学”的形塑与支配[3](P148)。征兵军官的“任何人都可以为美国而战……包括你们这群小伙子。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任何人可以为她而战”[1](P59)的宣传,试图以民族大义掩盖族裔的不平等创造认同光环,并且利用战争宣传进行身体规训,强行确立身体的客体性。塔尤和洛基等一干印第安青年在虚幻理想的指引下,为穿上军服后的归属感而骄傲。“我没穿上这身军服时,白女人从不正眼瞧我”,“双层上浆的笔挺军服,闪闪发亮的军靴”[1](P37)。军服一方面作为权力改造的工具进入到身体的规训,以表象性的意义指涉身体的塑造与控制,也即法国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所言的身体技术习得[4],通过身体的体能训练、行为培养、武器的使用等将身体演变为权力话语的实施介质。另一方面,军服具有将身体边界化的意义指涉,作为一种代表国家机器职能的外化表征,同时承担着区隔性屏障的功能。军服包裹的身体被强行纳入主流话语之下,开始接受身体的规训与改造,而褪去军服的身体带着被改造的痕迹,被迫重归遭受殖民话语和边缘人群双重排斥的异质存在。
再者,在面临原生家庭环境和白人文化两面夹击的困境之下,塔尤的混血性在族群关系中遭遇第三重危机:同为二战老兵的同族伙伴将身份危机与价值认同的焦虑转嫁于塔尤。作为出生入死的伙伴,塔尤与艾莫(Emo)、哈里(Harley)、勒罗伊(Leroy)、平基(Pinky)等人本应有着深厚的共情意识,然而,“战争结束, 军服褪去”[1](P39),尤以艾莫为典型的老兵却沉醉于对白人女性身体控制的幻想中,难以面对被权力话语抛弃而重归边缘的现实,“突然间店员让你排到最后去等,直到所有白人买好所需。车站的白种女人给你找零的时候,特别小心不碰到你的手”[1](P39)。殖民权力与战争暴力的结合进一步异化边缘族群。艾莫等人将酒精视为治疗“紧缩的腹部,喉咙哽咽的良药”[1](P37),精神毁灭的异化主体将矛盾转嫁于塔尤,“他们从不说白人给予他们那种感觉,又在战争结束后剥夺一切”,“他们只是想花点钱重回好日子,但是一个瘦弱的浅皮肤家伙却毁了一切”[1](P39)。战争作为现代理性和国家机器支配下的巨大暴力工具,摧毁人的自然本性,在西尔科笔下回到身体摧残的本身。艾莫等人的边界性,与拥有边界身体的塔尤之间形成异质冲突的悖论,充分彰显对立性思维模式统治下人的生存危机与世界的混乱无序,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历史进程与人类发展的无形障碍。
二、亲密空间的身体情感化
在身体转向的众多研究中,人文地理学通过身体来探索、培养、挖掘情感发展的机制与模式。以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为代表的情感地理学认为,“身体是与情感联系最紧密的空间尺度”[5],相关身体研究涉及身体的疾病抚慰、亲密关系的建立、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等。
塔尤战后创伤后遗症的表现之一,是他的梦境里常常出现洛基因受伤极度虚弱,被日本兵用枪托击头惨死的画面,进而叠加为“眼眶深陷的乔西亚”的面容幻象。而事实是舅舅并未参战。塔尤在惊醒后随即出现大汗淋漓、呕吐、发热的身体症状,按照心灵先于身体的理性思维解释,这是精神压抑的生理反应,“塔尤的疾病是人与土地的整体性断裂的结果,他的治愈来自重新认可这种同一性”[6]。本土裔文化中人与土地的连接可以理解为具有情感知觉的家园意识,情感地理学更将身体经验作为情感连接的先导。在段义孚看来,人在身体柔弱的状态下,比如童年或者患病期间会表现出“寻求安全感并向外部世界开放”的倾向,“在熟悉的家园怀抱和所爱之人的抚慰之下,充分感受养育的涵义”[7](P137)。塔尤的战争噩梦中夹杂着“很久以前他生病时乔西亚拿来退烧药”[1](P1)的场景。西尔科曾经谈到,“我从不认为人应该局限于某种性别经验[8],母性角色的缺失使塔尤的成长过程中,舅舅承担了更多的感性化养育责任,并与塔尤建立了亲密关系。乔西亚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身体体验带领塔尤感受自然与文化的滋养,培养生态文化感性,发展平衡和谐的生命观[9],这种源于身体知觉的情感意识进而回归身体经验加以巩固与发展,愈发将身体塑造为活生生的、具有意识、充满情感的主体。
塔尤与洛基之间的情感交流,则体现为亲密空间建构的情感联结对创伤应激的影响。塔尤的姨妈一方面让儿子与塔尤保持距离,另一方面按照白人文化价值将洛基培养成酷爱运动、成绩优异、争强好胜的学霸,但是私底下洛基“对塔尤一向友善”,兄弟俩“毫不犹豫进行调整,保持着自己的秘密”[1](P62)。之后兄弟俩并肩参战,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认同与情感交流。战场的特殊环境以最直接的身体伤害和目击者经验使亲历者获得深重的情感冲击,塔尤与洛基之间的兄弟情谊为此也遭受重创。西蒙·丹尼斯(Simon Dennis)等学者通过研究伊朗妇女家庭生活,论证了国家政治暴力所导致的心理创伤,根植于身体的亲密空间经验并产生身体间的情感流动,从而完成控制身体和精神的功能。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伊朗的政治高压导致家庭空间中的“空洞生活(bare life)”,使得女性成为“持续性空洞生活的负载身体”[10](P53),“变得高度紧张(hyper-reflexive)”[10](P52),具体表现为身处家庭空间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激发恐惧与创伤情绪。此外,丹尼斯还指出,这些波斯妇女还被迫成为某些创伤事件的见证者,并陷入创伤叙事的“失语”状态,衍生出“记忆生成的身体模式……创伤被牢记,遗忘又复现”[10](P53)。按此推论,塔尤梦境中不断出现的场景并非直接来自自我身体的战争伤害,而是目睹洛基所遭受身体暴力之后的巨大痛苦,显然这是一种情感迁移所造成的身体反应,并在记忆中不断重复而加剧身体创伤。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身体里,这体现了一种身体间的处境性。即使是不同的身体也能在相似的处境中,迅速做出与此处境匹配的自然反应和应对方式。身体的处境性带给塔尤亲历般的体验知觉,且存在于属于意识层面的记忆之中。“只要记忆与现实纠缠他就没法休息”[1](P6),塔尤记忆错乱中的时间并置表达了一种“失语”的创伤,而这种话语能力的丧失,使得身体越发浮现于意识的层面并具有主体性,“他能够理解洛基说话的逻辑,但是除了腹部发胀,悲伤如鲠在喉之外,他感觉不到什么别的”[1](P8)。
在西尔科笔下,身体经验在模糊物质与意识边界的同时,身体的性别载体进行了权力化二元对立的突破,将性别身体的亲密交流书写为身体与自然的融合经验。乔西亚与塔尤之间亲密空间的身体间性,还在于将夜天鹅带入塔尤的生命之中。在姨妈的眼中,夜天鹅是“肮脏的墨西哥风尘女”,用身体色诱男人并致使他们沦陷,乔西亚就是受她的唆使而倾尽毕生积蓄买了一批没有价值的斑点牛,并为此莫名丢了性命。事实上,包括罗伯特·纳尔逊(Robert M. Nelson)、宝拉·冈·艾伦、玛丽·爱伦·斯诺德格拉斯(Mary Ellen Snodgrass)在内的一批西尔科研究界的主流学者都一致认为夜天鹅是印第安文化中地母的化身。宝拉·冈·艾伦特别指出,夜天鹅的蓝色形象代表拉古纳信仰中具有“普遍创造性之女性特征”的女神蒂厄(Ts’eh),也是西尔科传说故事中的思想女(Thought Woman)和蜘蛛祖母(Grandmother Spider)[11]。塔拉·高赛(Tara Gausey)的论文则集中论证了夜天鹅这一角色塑造的文本功能,指出这一人物的形象具有两个突出特征:弗拉门戈(Flamenco)舞者和“以性感为表征的宇宙女性生命力量”,“扭动的身体节奏与不断提升的心灵,成为连接身体与宇宙时间精神的仪式”[12],高赛主要观点着眼于舞蹈作为揭示精神真实、表达自然赋权、恢复生命平衡的隐喻功能。回到文本中可以发现,夜天鹅确实通过舞蹈和性爱对乔西亚施加了影响力,这虽然佐证了舞蹈艺术的文本隐喻,但是也可以理解为身体实践的意义。在塔尤与夜天鹅的关系中,乔西亚是桥梁与中介,意义在于促成塔尤与夜天鹅的关系建构。塔尤到达夜天鹅的住处时并未立刻见到她,而是通过感性经验得以初步了解,“他能闻到她的气味,香水像是春天挂落树梢的象牙色刺槐花香”[1](P90)。在见到身着蓝衣的夜天鹅之后,他听到“窗帘后传来的音乐声”,但并未亲眼目睹夜天鹅的舞蹈,进而与夜天鹅迅速进入性爱,“她在他身下扭动,身体的节奏与风声融为一体,进入他身体与意识的深处”[1](P91)。塔尤与夜天鹅这唯一的交往中,身体经验占据核心地位,他对夜天鹅的感知更是对自我身体的发现与探索,他的身体已经成为联系世界的方式甚至与周遭结合为世界本身,此时的身体已然从实践的载体跃升为意识的主体,成为目的与中心而具有独立的意义。
三、地理边界的身体主体化
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将身体还原为先于意识的存在,以感觉经验的方式与世界产生联系,从而把纯粹的意识主体改造为“肉身主体”,即“现象的身体”(phenomenological body),“既是主体, 又是客体, 是一种可逆性的循环, 身体挣脱与世界紧密联系的意向之线而翻转面向自身和世界”[13]。当身体重新成为中心将世界所有之物聚合在周围时,这既是向原初世界的一种身体回归,也是不断生成变化的新一轮世界秩序和存在方式。从现象学的身体观来看,塔尤的创伤复原仪式是身体挣脱被二元对立思维物化的客体的过程,也就是完成乔西亚的夙愿找回斑点牛的旅程,是通过与世界的关系交往建构身体主体性的叙事过程。
按照药师比托尼的指引,塔尤必须找到包含“星星、牛、女人、山脉”这四种元素的地方所在。追随着各种传闻获得的斑点牛游牧的可能路线图,塔尤置身于西南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自然景观之中,他在杏树、刺柏的浓重气味和太阳花丛中骑着马,他遭遇郊狼和美洲狮,他在干旱的河谷和平顶山巅目睹日升日落星辰满天,在风沙迎面中仰望泰勒山并在它的神迹指引下邂逅地母在人间的肉身,在寻找斑点牛的路途中偶遇的神秘女子,完成与她的交合。关于文本中自然景观的疗愈作用与文化内涵问题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据此提出“文化创伤的景观治疗”观点[14],亦有学者指出,塔尤最终在“对天、地、神、人融为一体的强大力量的推崇与生态整体观不谋而合”[15]的信仰中获得复原。值得质疑的是,如果景观具有中心意义,那么如何对人的意识产生影响?人的感知与景观或是自然是怎样的一种互动关系?通过什么介质或是途径发挥作用?《典仪》重在描述塔尤被动地“置身”于景观之中的感知,他由比托尼推动着踏上寻求复原之旅,并且在旅程中时时寻找、发现、观察、认识,如果将身体之外的客观世界作为主体与中心,弱化甚至屏蔽身体感知的经验,那么什么因素或是机制能够促进塔尤的“悟性”或是“知觉”的发生?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的具体性存在使得身体的感知成为人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方式,“物体因身体感觉的整体性而呈现为整体性在场”,也就是说,“物体始终因其与身体的联系才得以显现于世界之中,世界因身体的体现而得以显现”[16]。文本之所以设立这样一个包容所有自然元素的场所,最重要的是展示身体再次作为中心与世界万物的普遍联系,并且世界也是通过身体的感知被认知和了解,从而使世界与身体形成动态的交互作用,使得世界获得具象的表达,身体也获得灵性。回到塔尤与地母交合的这个细节,对外而言既是两种身体的交融也是身体向外部世界、与自然界产生联结的过程;对内而言通过与地母交融的身体感知,塔尤以自我身体的客体达到与身体主体的融汇与贯通,获得对存在之本真属性的知觉体验。在一个自然元素的集合点和地母“显身”的场所,身体得以真正成为意识主体。
再者,这一聚合性场所具有突出的边界意义,更能说明身体回归不仅仅意味着文化融合,更是一种“文化转型”。塔尤发现斑点牛的地点,也就是药师所预言集合了“星星、牛、女人、山脉”四种元素的地方,位于拉古纳保留地与白人牧场的交界地带,“买了这片土地的得克萨斯人在周边围起篱笆墙,竖起标有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告示牌,警告不得逾越”[1](P174),并且雇佣了墨西哥人作为“边界”警卫巡逻警戒侵入者。这里的边界意义,首先是地理范围上领土和财产权利的划分,其次是文化意义上殖民入侵的边缘和区隔。乔西亚最初是通过夜天鹅的引见从墨西哥人手中买下这批斑点牛,被认为是落入异类族群的圈套。之后这批斑点牛失踪,传闻是白人偷窃或是从偷窃者手中低阶购得。围绕斑点牛的种种纠葛不仅仅是白人殖民者的“偷盗”行为,也反映出同为被殖民的族群间的异质化冲突。药师比托尼认为巫术为万恶之源,不仅将白人与其他族群分裂,“白人自身也是巫术控制的工具”[1](P122)。“巫术”意指欧美殖民文化侵入后本土裔文化的自贬之殇[17],焦点直指强势族群与弱势族群、弱势族群彼此的对立,然而文本所呈现的远非如此。族裔对立是现代思维方式与理性危机的表征之一,“毁灭者或是毁灭的力量并非单一群体或是种族的行为,控制人类陷入战争或是其他冲突是人性特质,是世界性普遍的事件”[8],现代文明所催生的历史进步,更伴随着殖民、战争、暴力、掠夺、环境污染等各种深重灾难,意味着世界与原初本真的边界与分裂。塔尤回到这样一个边界的聚合地,以“肉身”去知觉和经验,以身体去感知了解世界,也是身体突破物质的边界去表达与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
梅洛—庞蒂身体中心理论的超越性,不仅在于通过身体与世界的关系推进身体主体的建构,更在于通过可逆性循环实现身体对于世界的建构性。身体自身内部客体与主体之间可逆的同时,也在通过身体对外界的感知,和藉由姿势、行动等表意功能介入世界意义的创造[13]。乔西亚最后发现斑点牛时,它们正沿着拉古纳(Laguna)保留地和白人牧场的边界向“西南游荡”,因为“南方:这个方向深深印刻在他们的骨血里”[1](P175)。由于德克萨斯牧场主所建围栏的阻隔,斑点牛难以穿越这一回到拉古纳保留地的必经之地。按照乔西亚曾经的教导,塔尤在一处围栏剪开缺口,诱导斑点牛在此突围,“它们向西南飞奔,向着他指引的方向”[1](P183)。作为自然象征的斑点牛和作为人的塔尤之间,通过身体间性表情达意,在身体的表达活动之中,两者的行动和意义获得一致性。塔尤与斑点牛在边界地带以越界方式突破,与其说是融合不如说是一种解辖域创造新常态的过程,其根本在于回到身体与世界作为一体的始源状态,在于恢复身体与世界原初的整体与一致。人文地理学者爱德华·凯西(Edward S. Casey)的研究特别将身体姿势、行动与时空结构建立关联,塔尤与斑点牛突破围栏向“西南”方向回归,这种方向感始终以地平线为视野之边界,身体在空间运动的方向从而有着明确的时间指向,“远域(far sphere)的唯一突出特质就是地平线的天边”,“地平线是一种边界,但不是界限”[18]。在西尔科的视域中,“地平线是一种幻觉,平原向无限延伸”[1](P78),地平线作为似真似幻的存在意味着边界的现实和突破的可能,指向身体回归后,感性经验与主体心灵的融合,这种融合预示着未来的开放与多种可能,表明文化模式的不确定性和不断生成性,“平衡与和谐不断在变幻,总是需要维持与保护”[1](P120),“需要不断的转型(备注:小说中在此使用的是transition加s的复数形式)从而再次成为一个整体”[1](P157)。
结 语
回到《典仪》出版的时代背景之中,印第安文学在当代的复兴与繁盛,不仅在主题风格上标志着本土裔作家突破边缘束缚的强力发声,而且,通过小说、诗歌、散文等多元的创作形式表达文学诗意与审美感性。《典仪》以身体为对象与表现形式的感性书写,契合了文学潮流的当代走向以及本土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时在文本空间消解理性霸权和对立性思维,以文学感性启发社会结构与人类思想的思考,将文学想象融入文化模式的创造与更新。在小说的结尾,塔尤抵御住原始冲动的欲望,没有对艾莫酒醉后针对哈里、勒罗伊的暴行进行报复,哈里、勒罗伊被折磨致死,平基也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罪魁祸首的艾莫被永远放逐,这种具有道德裁判意味的结局虽然弱化了小说的诗性张力,但是以身体意识的觉醒而获得的感性中心与理性平衡,使文学化的人性再现具有跨域内涵。《典仪》的身体书写展现了一条认识身体、解放身体进而开发身体的路径,在愈发趋向于感性化经验的当代社会,有助于无限接近人性本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