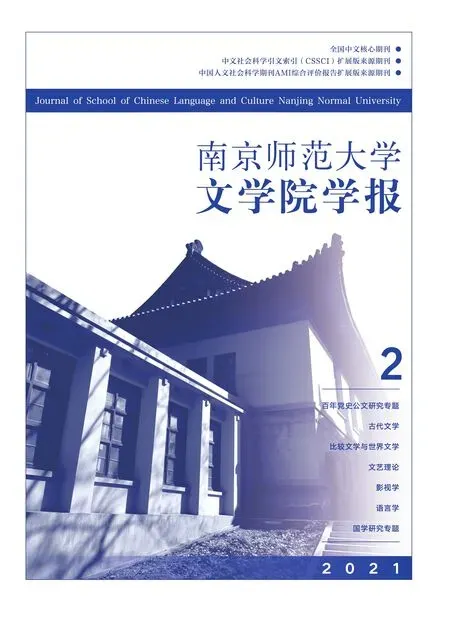在启蒙时代重构历史:司各特历史小说中的商业社会与文明精神
2022-01-01吴风正吕洪灵
吴风正 吕洪灵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是欧洲历史小说的缔造者,虽然基于历时研究的角度,学界通常将他纳入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行列,但是深入他的小说不难发现,其中的历史事件和虚构情节主要聚焦于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主导下的社会变革。爱丁堡司各特协会主席道格拉斯·吉福德(Douglas Gifford)曾这样描述司各特:“当我们接触到诸如沃尔特·司各特、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约翰·高尔特(John Galt)和苏珊·法瑞尔(Susan Ferrier)等作家的作品时,应该记住他们的创作根植于18世纪,在世纪末苏格兰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思想变迁对这批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P193)
苏格兰在18世纪,尤其是在1707年与“文雅的商业民族”[2](P1)英格兰合并后,面临着向商业社会转型的现实处境。在此过程中,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杜格尔·斯图沃特(Dugald Stewart)等启蒙学者发展出了以“理性”“法制”“商业”和“勤勉”等道德观念为核心的“苏格兰知识”[3](P1),而其在文学上的表征则体现在对优雅文化和文明社会的推崇,在文学作品中更多地展现新(商业)道德品质,摒弃过分粗俗的表达与内容。司各特的多部历史小说都是以18世纪苏格兰为背景,围绕商业体制的完善和苏格兰民族的商业诉求展开创作。他对商业社会的书写呼应了18世纪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并反映了那个时期苏格兰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克服苏格兰传统道德对英格兰商业体制的排斥,通过文学与启蒙思想的融合来为新生的商业社会提供辩护。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作为这一时期苏格兰文学的重要标识,在民族文学身份出现分裂杂乱的对立性表达之际,透过其文本中对商业社会的描绘形塑出一种现代文明精神,使苏格兰在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合力下逐渐完成文明社会的建构。
一、“商业社会”:发展的选择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瓦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指出,司各特的威弗利系列小说“包含着大量的某种形式的政治经济学。”[4](P118)以往学界常将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定义为浪漫主义小说,当代评论界则认为他的小说蕴含了丰富的现实主义因素。此种论断持之有故,因为浪漫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并存,是司各特小说的独特性之一,他在作品中对政治和经济的关注与诸多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相应和。
自1707年联合(1707 Union)后,特别是到了18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如何融入英格兰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文明”就成为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思考的问题,他们寄希望以这样的思考来解决苏格兰的现代化问题。[5](PV)对于启蒙运动和并入联合王国的态度,当时许多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都表明了态度,休谟、威廉姆·罗伯森(William Robertson)、斯密等人更是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对商业和文明的渴望。司各特深受18世纪启蒙学者的影响,他在1780和1790早些年间进入爱丁堡大学就读,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约翰·米勒(John Millar)、斯密连同其他启蒙学者的思想都对司各特处理小说中的历史和社会进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6]。吉福德在分析司各特的创作与启蒙运动关系时指出:“欧洲局势的动荡和国内启蒙学者发起的运动以及他们的开创性思维将苏格兰文化和社会推向一个分水岭……司各特和他同时代作家则尝试开创一种苏格兰式叙事,通过这种叙事来找出苏格兰历史性分裂和内部倾轧的症结,继而治愈这种自我强加的伤害。”[1](P193)
司各特经常将主人公塑造为深陷历史、政治、宗教和社会巨变漩涡中的人,再现了苏格兰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经历的挣扎。在《威弗利》(Waverley,1814)中,主人公既是英格兰公民,同时体内又流淌着苏格兰血液。他误打误撞从英格兰驻军变为詹姆斯党人,与其说是一种偶然,不如说是个体分裂在联合背景下的一种必然表达,威弗利的矛盾性格似乎表现了苏格兰人的一种创伤症候。在小说结尾,经历了高地叛乱的威弗利最终摆脱了纷争,回归平静生活,可此时的他已经褪去了稚嫩的浪漫幻想,联合、发展、进步等观念在他的心中开始扎根。布雷德沃丁庄园在遭受战乱的洗礼后,通过修缮再次矗立,但经历重修后的古宅已经没有了先前被时代遗忘的古迹,焕发出一层带有文明印记的光辉。不难看出,昔日战乱带给英格兰、苏格兰人民的创伤已逐渐消弭殆尽,抚平悲痛后,只有顺应时代的安排,分享联合带来的利益,才是对苏格兰最好的结果。
关于具体出路,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给出了对未来的构想——商业社会。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雷德冈利托》(Redgauntlet,1824)围绕捕鱼站暴动虚构了一起发生在1745年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事件,而潜藏在故事情节下的文本线索则向读者揭示了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作业方式,法治文明取代暴力动乱的过程。在小说中,以传统捕鱼方式维系生存的渔夫和代表工业革命先进生产力的捕捞站之间的矛盾隐喻了英格兰的先进性与苏格兰落后价值观的对立,这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因素。苏格兰在“达连计划”(Darien Scheme)(1)苏格兰银行家威廉·帕特森效仿英格兰的海外扩张,主张在中美洲巴拿马建立殖民地,因所选之地名为达连湾,故名“达连计划”。然而,受制于国力资金不足和英格兰的干预,计划在持续一年半后宣告失败,最终导致苏格兰政府陷入破产危机。落空后,政府为免于破产,被迫与英格兰联合,以分得帝国的商业利益。然而,“在英格兰充斥着欢庆联合的篝火与钟声的时候,贝里克郡的北部却只传来预警队进驻爱丁堡的脚步声和教堂上空响彻的悲怆哀鸣。”[7](P313)在苏格兰民间,人们认为联合是政府高层对苏格兰民族的背叛,因此对英格兰怀有强烈的敌意。索尔维湖渔夫破坏捕鱼站的行径,表面看是詹姆斯党人(Jacobite)对格迪斯个人的攻击,实则是他们抵制格迪斯所代表的新兴商业体系及与英格兰人的合作。司各特以网桩与鱼叉、商人与暴徒的对比,揭示出商业社会才是苏格兰摆脱困境的出路。当分离主义在苏格兰彻底失去根基后,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业社会才是苏格兰发展的必要保障。詹姆斯党人的政治幻想与苏格兰的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斯图亚特王朝(The House of Stuart)的衰落不仅是一个朝代更迭和军事力量的问题,它更是休谟新利益政治理论的胜利,是财产与安全,民意与正义问题的胜利。休谟、斯密和罗伯森都认为,如果苏格兰能毫无保留地融入英联邦,她就能成为现代欧洲最幸福国家的一份子,可以利用其强力的制度来确保日益频繁的思想交流和商业往来[8](P167-68)。
与《雷德冈利托》中生产力之争涉及到的政治因素不同,司各特的另一部小说《红酋罗伯》(RobRoy, 1817)通过一对青年男女冲破阻碍走向婚姻的过程,展现了苏格兰商业化进程的不可阻挡之势和高地氏族走向衰败的必然命运,并以此来寓意商业社会的正当性。小说以1715年詹姆斯党人叛乱为线索,揭示了联盟新格局下尚未稳固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其中包括作者对商业扩张的展望和联合王国影响力的关切。英国学者安德鲁·林肯(Andrew Lincoln)在其著作《沃尔特·司各特与现代性》(WalterScottandModernity, 2007)中探讨了《红酋罗伯》中的这种商业思维,他认为司各特在小说中阐述了“启蒙运动倡导的文明,它将商业看作一种优雅和高尚的德行”。同时林肯还认为:“这部小说回顾了那个重商主义目标被广泛传播和接受的时代,这种目标在当时很少受到反驳。”[9](P123)司各特为呈现小说中的商业社会,着力刻画了法兰西斯和帮助他摆脱商业困境的苏格兰人。法兰西斯作为伦敦最大商行的继承人,起初因沉迷文学,拒绝继承父业。然而在边区经历了一系列劫难后最终醒悟,他放弃了早先幼稚的想法,遵从父愿从商。法兰西斯作为英格兰商人的后代,他的形象毫无疑问地象征了代表商业社会的进步力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他的表兄赖希利,他借助在商行工作之便携款外逃,目的是为筹集资金资助复辟事业,最后却以失败告终。赖希利不仅是法兰西斯的表兄,他生活的边区诺森伯兰更与苏格兰接壤。司各特通过这组对立关系要表达的思想不言而喻,他利用正反两个角色的冲突表明了英格兰、苏格兰在联合之初面临的挣扎和困境。不同于《威弗利》,司各特在这部小说中没有花费太多笔墨渲染詹姆斯党人的叛乱,而是将其作为背景线索,通过商业纷争这条主脉络阐明了故事的主题,反映了18世纪苏格兰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者透过小说《红酋罗伯》要表明的,正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后者认为,“物质财富与高尚社会是现代的标志,传统的共和主义理论(2)共和主义是西方古老的政治传统,它认定政治权威来自人民同意的原则,拒绝接受君主和王朝统治原则。然而,这种政治构想并不符合英国商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无法合理地解释这种对财富与文雅的崇尚”。[8](P169)司各特通过赖希利等人的失败宣告:从原始族群转向高度复杂的商业社会的新格局已经逐步形成,詹姆斯党人的叛乱已化为一种政治幻想,取而代之的是商业社会对法制和贸易的普遍重视。“司各特和18世纪后期启蒙学者斯密、弗格森、斯图沃特一道认为,任何社会形态都将最终过渡为商人主导。”[10]他通过小说人物的命运和心理表现了这种社会趋势和历史前进力量,以此展现启蒙运动对历史的推动。
司各特身为作家不仅书写商业,本人也曾深深地卷入商业漩涡,故而他不单对历史有着细微的洞察力,对资本更是具有一种比肩商人的敏锐直觉。自1814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威弗利》开始,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司各特的威弗利系列小说发行量超过50万册,“整个浪漫主义时期,威弗利作者的作品销售量超过了同时期其他作者销售量的总和”[11](P103)。这也为他带来了46万英镑的巨额财富,放眼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过,司各特并不满足于创作带来的收入,颇具经济头脑的他更是尝试打通创作和流通两个环节,谋取更高的回报。投资“巴兰坦印刷厂”(Ballantyne Company)就是为了更多地染指市场运作,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幸的是,玩转于资本市场的他最终被资本反噬,182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巴兰坦印刷厂破产,这使得司各特陷入了巨额的债务中。晚年身体欠佳的他为了偿还亏空,以文抵债,高强度的写作加速了身体恶化,最终导致他过早离世。
作为英王乔治四世(George IV)授予的爵士,司各特支持联合,但他的这种立场绝非只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身为苏格兰后裔,司各特清醒地意识到苏格兰的未来出路,只有商业社会才是符合苏格兰发展的选择。无论是他在作品中的商业书写,还是个人的商业实践,都充分践行了他的这种政治立场。
二、封建与商业社会的道德观对照:以高地为例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尤其是转型时期,伴随物质条件不断演进的还有人们的道德标准。18世纪的苏格兰在经历议会合并和启蒙运动的冲击后,其政治与社会层面的断裂与重构也就不可避免。因此,苏格兰在其商业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体制和意识层面的双重矛盾,司各特小说中对高地与英格兰及低地之间的龃龉描写就形象地反映了该过程中不同社会环境显现出的文明与落后间的差异。《威弗利》以1745年詹姆斯党人叛乱的历史事件为脚本,通过主人公的高地之行以及英格兰军官威弗利、苏格兰低地贵族布雷德沃丁和高地首领弗格斯的三角关系揭示了18世纪英国由南向北展开的变革,以此来预示苏格兰在启蒙运动影响下正在形成的新世界。自此,一副画风迥异的民族图志展现在读者眼前:“代表18世纪文明风尚的英格兰、体现17世纪置身事外的苏格兰低地和处在父权结构下的高地氏族”[12]并存于不列颠王国。然而,其中蕴含着太多的矛盾冲突,小说中偷盗家畜的故事就可令人管窥一二。
威弗利对偷盗家畜行为的反应典型体现了代表文明的英格兰与“野蛮原始”的高地之间的差距。威弗利原本是驻扎在两国边境的英格兰军官,在探访其叔父旧交布雷德沃丁爵士的过程中“意外”结识了高地首领弗格斯·麦克沃伊。这里的意外是指经常发生在苏格兰边区的盗牛活动,具体来说是苏格兰高地人偷盗或抢劫拒绝缴纳保护费的低地业主。这种行为在18世纪前后曾普遍存在于高地附近,多数业主只能选择息事宁人,破财消灾,而作为回报,高地部落则对按时缴费的业主提供“保护”。布雷德沃丁爵士的家畜被盗正是因为他拒绝向弗格斯缴纳“规例”。这原本在高地司空见惯的事情却令英格兰人威弗利震惊不已,以至于他起初错把弗格斯当作“地方官”或者“治安委员会的”,还将他比作“高地的江奈生·魏尔德(3)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的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中的大盗。”[13](P127)。实际上,“高地人长久以来就被认为是低地人的威胁,但英格兰却对他们知之甚少。他们所在的山地距伦敦就算骑最快的马也要一到两周,这使得政府和民众不仅都对他们鲜有了解,更夹杂着许多偏见。”[14](P33)
这背后的深层问题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英格兰、苏格兰迥异的社会环境下的道德观差异。英国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南部的英格兰率先形塑出以财产、法制、理性和社会分工等概念为核心的商业人道德。反观北方邻居苏格兰,尤其是高地地区却还停留在封建阶段,道德观的转型明显滞后。当靠近英格兰北部的格拉斯哥凭借其地理优势发展为英国最大的贸易港口时,在苏格兰北部的高地地区,敲诈勒索(偷盗牲口行为)仍在人们的生活中盛行。在小说中,布雷德沃丁和家人还在就用武力或法律途径夺回牲畜而争执不下时,弗格斯的手下便登门拜访提出愿意帮助他们找回被盗的家畜。曾有外来观察者估计,在任何一段时间里,普通族长手下的战士有一半正在偷盗邻居的牲口,而另一半正在努力找回被邻居抢走的牲口[5](P122)。对于这种现象,苏格兰人邓肯·福布斯(18世纪30年代辞去议员身份后便转而担任高等民事法庭的首席大法官,其庄园就坐落于卡洛登战役(4)1746年卡洛登战役是詹姆斯党人在不列颠岛上的最后一次挣扎,也是苏格兰高地部落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结果以英军对詹姆斯党人和高地部落的大屠杀告终。地点德鲁莫西荒原)带着批判的眼光观察高地部落,认为他们“沉溺在旧时懒散的生活方式不能自拔,仍然固守野蛮的习性与信仰。他们惯于使用武器,适应艰苦生活,对社会安定是一个威胁”[14](P33)。休谟、斯密等对此则从哲学层面各有所言。休谟从正面解读,他认为“在迄今尚为充分经验到仁爱、正义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性德行带来好处的一切未开化民族中,勇敢是最卓越的优秀品质,最为使人们所讴歌、最受父母和导师推崇、最被全体公众钦佩”[15](P15)。斯密则引用《奥德赛》中俄底修斯被人问及是强盗还是商人的故事,从商业角度来表明在未开化社会,商人是人们最瞧不起的人物,而强盗却因为尚武得到人们尊重。巧合的是,在威弗利初次到访高地后,作者也将他受到的族长待遇比作《奥德赛》中英雄享受的待遇,以此来表现18世纪高地的风土人情和他们崇尚的道德观念,这也不难看出司各特对休谟、斯密等人观点的承袭。他在1780年间就读爱丁堡大学期时师承斯图沃特,主修了道德哲学课程,[16](P35)而后者的哲学思想则直接来自斯密、弗格森等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他们对道德的剖析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威弗利》中对高地人品性的塑造。
小说中,高地和低地间的龃龉在那年11月的行军队伍中也可见端倪。当查尔斯王子的六千军队挥师南下,准备直捣英格兰中心时,弗格斯和威弗利却对战争的前景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弗格斯完全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态势,认为武力可以征服天下,满脑子只想距离伦敦又近了几步;而威弗利则看到在他们宣告詹姆斯三世驾到的城市,没有人高喊上帝保佑他”[13](P289)。低地群众对王上的军队表现出一副冷漠的态度,就算政治立场趋于保守的托利党人也避之不及,唯恐与他们扯上干系。其余民众则对他们粗野的外貌、晦涩的语言和古怪的服装怀有恐惧、吃惊甚至厌恶的心情。据史料记载,查尔斯王子的军队进驻格拉斯哥时,他们完全没有受到民众的欢迎[17](P19)。究其原因,彼时的格拉斯哥已经发展出大量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中有商人、进步地主、温和的长老会教徒,当然也包括启蒙学者。这些人都是汉诺威王朝的支持者,他们的拥护并非出自坚定的信仰,而是现实利益。利己主义是他们忠于新政府的最强保证[5](P142)。《1707年联合法案》带给低地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汉诺威家族为苏格兰注入了完善的法律制度、健全的商业体系并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而斯图亚特王朝主张的天主教专制主义则可能再一次将苏格兰带入封建纷争和王朝更替的循环往复中。因此,“当1745年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带领叛军攻占爱丁堡时,苏格兰启蒙学者已经准备好理论武器,随时准备以‘科学’的态度粉碎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图谋,彻底清算庸俗的党派利益”[8](P167)。从某种意义上讲,1745年的叛乱更像是一场苏格兰内战,而不是英格兰、苏格兰间的战争。这种冲突实质上是文化间的隔阂,更深层则可以归因于不同社会形态所代表的道德观分歧。这就为苏格兰的未来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可能:詹姆斯党人无法帮助苏格兰走向现代文明,他们只能殊死一搏,推翻代表工业资本的辉格党政权;而后者则要誓死捍卫他们建立起的现代商业体制和价值观,阻止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
苏格兰在并入联合王国和融入其构建的现代体系过程中,其传统社会形态慢慢解体,与之伴随的是现代商业社会的逐渐成型,“文雅”“理性”“法制”和“财产”等符合商业社会的道德哲学观也得以浮出历史。司各特透过人们对高地商业活动和落后原始风俗的反应,表现出高地与低地乃至英格兰、苏格兰之间的不同道德观念,让“高地传奇与启蒙理性主义在他的小说中得到融合”[18]。以新型的商业价值观取代落后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充满阵痛的过程,却也充分反映出苏格兰对文明精神的向往。
三、司各特小说中的“文明精神”
司各特所处的时代极具动荡,法国革命及其后的余波对欧洲政治的影响让司各特感到不安,他担心这会波及苏格兰的稳定性。如果说司各特在世时的政治立场经常被批评者以保守主义论调所诟病,那么在他去世同年,自治市改革(Reform Acts of 1832)引起的激进派不满,以及1843年苏格兰教会分裂(Disruption of 1843),还有铁路和工业化进驻高地对原有生活生产方式的破坏仿佛都印证了他的担忧。司各特深切感受到了社会稳定性和秩序的脆弱,他不仅看到了苏格兰数个世纪以来内部倾轧带来的弊端,更是对法国大革命从开始的理想主义退变为屠杀记忆犹新。[1](P206)他对历史的清晰洞见使他对极端社会变革产生了怀疑,由此引起他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新思考。他在小说中虚构那段历史,除反思动乱带给苏格兰的伤害,还阐明了自己的一种立场:只有彻底抛弃封建专治信仰,拥抱代表现代性的文明精神才是苏格兰繁荣富足的必要保障。
正如吉福德对司各特的评价,深陷二元论(dualism)和分裂中的司各特始终坚持着自大学建立起来的价值信仰。他汲取了斯密和里德的常识派(Common Sense)哲学思想,摒弃了以往狂热和抱残守缺的思维,利用建立在理性与和解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来为长久以来饱受分裂和自毁的苏格兰奠定其改革与复兴的根基。“他的早期小说在着眼苏格兰内乱时更多地聚焦在那些思想与感情相互矛盾的人物,他们既饱含对传统忠诚的坚守,又怀揣着各自的诉求。”[1](P206)《红酋罗伯》中,强盗罗伯·罗伊对逝去忠诚的向往、对破旧苏格兰部落的追随和对消逝语言的怀念与代表着苏格兰未来的格拉斯哥商人尼克尔·贾尔维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尼克尔掷地有声地强调联合法案(1707 Act of Union)将苏格兰带向光明时,其实也表明了司各特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务实精神的支持。尼克尔解构了罗伯所代表的价值体系,但他同时也是后者的堂亲,在这层隐喻下英苏间的关系显得更加不言自明。伊万·邓肯在评价英苏联合对不列颠王国的影响时曾指出:“英国现代化进程内部并非是一个完全统一和文明的整体,而这种内部断裂历史的重叠正是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19〗因此,身在不列颠共同体内的苏格兰同时具备了守旧、田园、部落的性质和现代、城市、商业的潜质。这两种苏格兰在司各特的笔触下得到融合,展现给读者一个既统一又对立的民族形象。
司各特将苏格兰刻画为一个从封建、落后、贫穷的国家转变为19世纪中期走在工业化进程前端、充当大英帝国殖民先锋的形象。苏格兰民族也是一样,一边痛恨着联合、悲叹在不列颠王国中的地位,同时也在英格兰和欧洲的影响下走向文明。苏格兰和欧洲启蒙学者都曾对社会发展进行过分析,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认为,人类的原始状态是最真实的;托马斯·布莱克韦尔(Thomas Blackwell)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每个社会都是从前代社会不断完善而来,而司各特的小说将两者融合,在他和许多苏格兰知识分子看来,对文明的皈依是社会发展历程的必经之路,这一点也契合了亚当·斯密提出的人类发展模型理论。他在1762年的法学讲座“发展之四阶段”(Four Distinct States, 1762)中提出:人类社会都会经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是捕猎时代,第二是畜牧时代,第三是农耕时代,第四是商业时代”。[20](P35)随着每一个阶段的发展,社会都会更加文明。在司各特的小说中,无论是难以割舍高地理想和怀旧情绪的罗伯·罗伊,还是沦为明日黄花的索尔维湖渔夫,都无法阻止苏格兰在启蒙运动后大步迈向文明的步伐。
作为苏格兰启蒙时代文学的重要表征之一,当时的文学和哲学在展现一种对古老苏格兰价值观尊重的同时,也反映出一种对苏格兰语和行为方式的自卑。这种分裂即使现在仍然有迹可循,它表现为一种对古语、传统和信仰的坚持与一种摆脱混沌、未开化过去的欲望之间的冲突。究其根本,苏格兰在构建商业社会和经历道德观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封建制度和思想的束缚,它只有与因循守旧的过去彻底划清界限,才能逐步走向文明。自联合后,苏格兰文人开始逐渐接受英国化表达并对苏格兰本土表达产生疏离,这就关系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理念,即文明的目的(teleology of civility)。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等苏格兰文人认为:“启蒙运动带来的‘文明’不仅是自我实现的目标,更是他们国家历史的目标”。[8](P260)换言之,苏格兰在商业社会和新道德观确立后,也应该促进对更高层次文化品位的不断追求,这种更高层次主要体现在英格兰式的言谈举止和文化规范方面,而以爱丁堡为中心发展起的启蒙运动充分证明了苏格兰同样具有承载文明的土壤。罗伯森在《苏格兰史》(HistoryofScotland, 1759)中曾用例证指明,“苏格兰是一个知识社会,具有高雅的文化和宽松的政治环境”。[8](P260)同时,罗伯森也保留了对苏格兰传统的忠诚,比如苏格兰人的勇敢和热情,但他的这种忠诚主要体现在情感上,即对苏格兰传统价值观的赞同仅限于情感和怀旧范畴。“这就为后来沃尔特·司各特等人把詹姆斯派(Jacobitism)仅作为一种文化态度来看待的作法奠定了基础”。[21](P530-31)在罗伯森重构的文明目的论中,苏格兰成熟的标志就是她已褪去幼年苏格兰的样子,具有了成年英格兰的部分特点。他认为苏格兰的历史只有被终结之后才能被正确书写,这句话很能体现他和休谟等启蒙史学家对苏格兰历史的理解。英国可以进化到文明社会,但苏格兰靠自身却难以做到。究其原因,在于苏格兰通往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无法摆脱封建贵族对权力的争夺,封建制度让苏格兰陷入严重的倒退。
司各特在其历史小说中对詹姆斯党人叛乱的反复书写,抛去本身的浪漫主义外表,作者本人要表达的立场不言而喻,即抛弃苏格兰封建贵族阶级的残暴和任性,向文明的英格兰社会靠拢。“苏格兰自1707年后,她的历史身份、书写方式和思维习惯在融入大英帝国工业化的进程中逐渐被英格兰中心主义所取代,苏格兰的历史也降格为地方史,成为英国历史的一部分”。[22](P7)英苏联合后,“苏格兰用牺牲政治自治换取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23],她的社会机构、文化和语言都被迫向彰显文明精神的英格兰转向,虽有反对之声,但随着1746卡洛登之战的失败而愈发羸弱。一旦精英圈子(苏格兰启蒙学者)接受了这种转变,那么作为圈子一员的司各特,继承这种观点并将其表现在作品中也就顺理成章了。
18世纪的苏格兰深受内战、宗教纷争、部落厮杀和贫穷的摧残。商业、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改进已刻不容缓。苏格兰作为失去政治自治的政体,她的智力精英阶层必须努力应对如此重大的社会政治动荡。斯密、休谟、罗伯森等人都将注意力放在探索人类从野蛮到文明过程中经历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作为爱丁堡精英阶层的一员,司各特在其19世纪历史小说中一再展现的,正是上个世纪启蒙思想家关注的问题——对野蛮本性的排斥和对文明精神的向往。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乔治·卢卡斯(George Lukacs)曾指出的:“直到启蒙运动尾声,对过去的一个世纪进行艺术反思才成为文学要表达的中心”。[24](P2)在司各特笔下,无论是因沉浸浪漫主义幻想而给自身招致灾难的威弗利,还是因意外卷入新旧生产力争斗中的格迪斯,亦或是深陷各方角逐而落入危险境地的法兰西斯,都是那个动荡时代的见证者。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共同的“文明精神”。司各特通过这些人物的遭遇表明了他的观点——封建制度的消亡才是苏格兰走向现代文明的前提。他和启蒙史学家一致认为,卡洛登战役彻底摧毁了苏格兰守旧势力,而接下来1747年世袭管辖权的废除(The abolition of heritable jurisdictions)则标志着高地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而为文明精神在苏格兰的发扬扫清了障碍,这其中盖尔语在高地的消逝和英语的普及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点,象征着高地对文明的皈依。在小说《威弗利》的结尾,当詹姆斯党人的叛乱平息后,站在审判席上的埃文在为自己辩护时忽然陷入了窘迫,这种窘迫并非来自对叛乱行为本身的愧疚,而是源于“他所思考的语言不同于他用以表达的语言”。[13](P465)苏格兰作家埃德温·缪尔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过解释,他认为“苏格兰人用一种语言思考,用另一种语言去表达,这种分裂使他们的情感与理智很难得到统一”。[25](P21)苏格兰在18世纪经历了联合与叛乱的洗礼后,吟游诗人口述相传的盖尔语故事逐渐被人们淡忘,而英语作为承载英格兰价值的表达方式则被普遍接受。这不仅改变了苏格兰人的思考方式,也促成了他们礼仪举止向文明的转变。这一点也得到了高地协会的佐证,该协会曾在报告中写到:“高地风貌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人们变得勤奋起来,不再像过往一味地沉迷于聆听传奇或英雄歌谣了”。[26]
司各特和启蒙学者一道,在变革时期反映了各种新旧思维和对立,他的历史小说在重构苏格兰性的基础上确立了对不列颠性的认同,其中对于苏格兰文化身份分裂的描述令人深思,而这种身份的彷徨逐步使苏格兰转向对不列颠和大英帝国身份的认同。
四、结 语
苏格兰文学著名研究学者伊万·邓肯在阐述历史小说兴起与启蒙运动关系时曾这样说道:“也许苏格兰启蒙运动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提出了脱离国家和政治的公民社会构想,这是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组成的独特社会。它可以避免臣民因王朝更迭、种族隔阂和教派纷争陷入极端狂热。虽然这种构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很难实现,但历史小说的出现却让人们可以认真思考这种构想。司各特的小说将公民社会构想呈现于我们眼前,他将历史供我们参考”。[11](P107)回顾司各特历史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个时代,苏格兰虽然在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合力下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笼罩在帝国阴影下的苏格兰表现出一种自然和文化空间的断裂脱节。司各特以其特殊的个人经历和对历史的清晰洞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的历史动向,在18世纪苏格兰建立商业社会和形塑新道德观的过程中,他借助历史小说的形式将启蒙学者的哲学思想导入苏格兰商业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在溶入不列颠性的同时,勾勒出苏格兰民族极具辨识度的文化身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