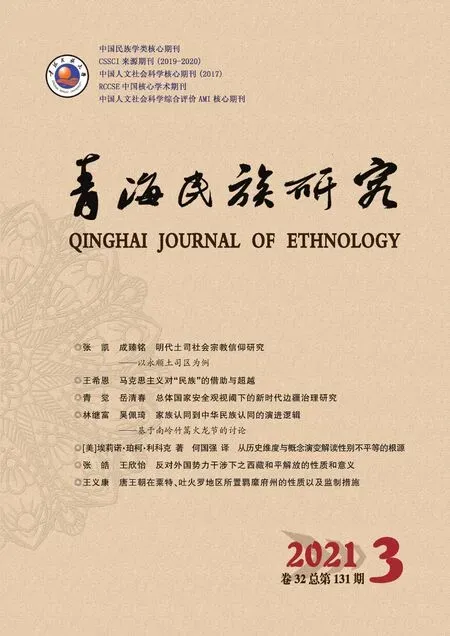再论土司制度的终结
2022-01-01郗玉松
郗玉松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6)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即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的贵族为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各族人民进行管理,以达到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目的。土司制度创建于元代,这在学界已获得多数人的认同。对于土司制度终结的时间学界却有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看法,以致于我国在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中采取了模糊的提法:土司制度始于13世纪,终止于20世纪初。应该说,土司制度终结于何时,这是摆在土司研究者面前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带有理论性的问题。
关于土司制度终结的时间与标志,当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为清代雍正朝改土归流说,如于玲认为,“清朝初年的改土归流正是土司制度的必然归宿”;一种为辛亥革命说,如杨庭硕指出,“辛亥革命才是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李良品也认为辛亥革命是土司终结的根本标志;一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改革说”,如罗群认为,“土司制度的终结,是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过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团结改造包括土司在内的民族上层人士等措施才完成的。”成臻铭、王文成等专家也认为土司制度终结于1956年的民主改革。[1]此外,还有专家认为土司制度终结于民国,2020年,学界发表两篇关于土司制度终结的文章,再次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李超坚持民主改革说,指出,辛亥革命后“逐渐瓦解了土司制度的承袭、土地、土民三个核心基础,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边疆完成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等政策才彻底终结。”[2]贺益、陈季君从清朝“大一统”思想的强化以及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视角入手,论证了土司制度终结于清末的历史必然性。[3]
土司制度的实质是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为中央王朝职官制度的一种,且为双轨制的管理制度。1911年3月,民政部发布《各省土司一律改设流官》,民政部代表清政府管理地方行政,这一公告明确指出将所有土司改设流官,这一公告成为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中华民国国体为民主共和国,从法律上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而基于专制制度为基础的土司制度失去了其法理学上的依据,民国中央政府从未承认土司制度。民国时期,仍有许多报刊、杂志甚至政府公文都用到土司制度一词,也经常出现废除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等用语。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用语所针对的仅仅是土司个体,并非整体意义上的土司制度,不能与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推行的土司制度混为一谈。
一、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准
目前对土司制度的终结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改土归流说”,一是“辛亥革命说”,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改革说”。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土司制度终结于民国。这几种看法似乎都有各自的道理,至少土司个体的存在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改土归流说”欠妥,改土归流只是废除了部分土司,并未触及土司制度本身;“辛亥革命说”提法欠妥,这容易产生误解,辛亥革命的对象是清王朝,而不是针对土司制度,不如说“清亡,土司制度不复存在”;“民国说”似乎太笼统,没有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民主改革说”只是对最后一位有土司身份者的安置。
要搞清楚土司制度的终结,首先要明确判断土司制度是否存在的标准,这个标准当然要包括土司制度的建立。我们认为,这个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土司制度的实质。换句话说,只有明确土司制度到底是一个什么制度,才能确定它的始建时间和终结时间。比如说,科举制度的实质是选官制度,土司制度的实质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统治者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体现了国家对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是在行省之下的双轨制,纳入国家的职官管理体系。以这个标准来考察,土司制度的建立在元代,终止在清朝灭亡。
明清两朝在建国之初,均因袭了前朝的土司制度,不论是明朝的“大为恢拓”,还是清朝的改土归流,对土司的权力加以限制,但明清两朝土司制度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这一点是始终没有改变的。实际上,清朝灭亡,这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已不复存在。民国政府并没有像明清两朝那样继续将土司制度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也没有设置过土司,而是通过设治局不断废除土司。因此,民国时期只是土司个体的残存,而不是整体制度的保留。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土司个体的存在,是否意味着土司制度的存在?这是解决土司制度终结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毫无疑问,民国时期的确还有许多土司个体的存在。那么,他们的存在就一定说明土司制度仍旧存在吗?恐怕未必。
首先,那些土司是在清亡之后自然保留下来的,但其生存的环境已然改变。他们没有像自己的祖先那样,在经历朝代变更后,被新政府所承认,他们并未得到民国政府的认可,更没有纳入民国的国家官职体系,而成为新政府的一员。他们实际面临的是被民国政府逐一废止。尽管有些土司得到不错的待遇,那不过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而民国政府从未宣布过要继续推行土司制度,民国时凌纯声曾言:“土司政治之现实情形既难详知,即国内现存土司之总数究有几何,迄今尚无可靠之调查报告。”[4]连民国学者都以为土司与政府之间已无任何关系,且不清楚残存之土司到底有多少,这就清楚地表明,民国时期未曾将元明清的土司制度继承下来,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继续推行。因此,不论民国时期有多少土司,都不能说明土司制度的继续存在。看来用凌纯声所称之“土司政治”概括民国时期的土司问题,似乎比用“土司制度”更为稳妥。
其次,元明清时期的土司,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中的一员,即朝廷任命的世袭地方官,是一定要管理地方事务的。在雍正改土归流之前,所有土司,都有自己管辖的领地,即使是从九品的小土司,也要管理村寨,并在吏部或兵部注册备案。改土归流以后,清政府对已改流之土司,特别是自请改流的土司及其后人,授以土职,多属安抚措施,无实际意义。尽管他们也可以世袭,但相当一批人已不管理村寨,即不再管理土民。嘉庆《大清会典》卷五,非常明确地指出:“土官,则府厅州县辖之,以治其土民。”同时在列举土官数目后,又列出云南等省21位土官,称,“不管理苗番村寨,不与其数。”而广西思恩府辖从九品土官一人,也列在政府的登记册中,原因是因为他“系管理土峝”[5]。而光绪《大清会典》卷四十五亦列有土弁之数,并称,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其土官不管理邨寨者(共95人),不与此数”。[6]有些土司的官名逐渐被废除,如“辩土官之等,土府、厅六等(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土推官、土经历、土知事凡六等。土推官旧有贵州镇远府土推官一人,乾隆四十九年,因不管理番苗村寨,改为七品土官。土经历旧有云南开化府土经历一人,嘉庆二年,因不管理番苗村寨,改为正八品土官。今土官已无此二项。)”朝廷对土官、流官的管理日益趋同,“治之皆如流官焉”[7]。可见,在清中期以后,不参与地方管理的有名无实之“土司”已不再属于制度之内的人员了。以此观之,民国时期的土司似更不应视为土司制度中的成员。因此,他们的存在也不应视为土司制度的存在。
另外,还要清楚朝廷设置土司制度的目的。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统治者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绝非统治者本意,也非其终极目的,只是权宜之计,正如鄂尔泰所说,“窃流土之分,原以地属边檄,入版图未久,蛮烟瘴雾、穷岭绝壑之区人迹罕到。官斯地者,其于倮俗苗情实难调习。故令土官为之钤制,以流官为之弹压。开端创始,势不得不然。”[8]鄂尔泰所说“开端创始,势不得不然”,说明推行土司制度为形势所迫。岳钟琪认为土司制度是权宜之计,“窃臣伏查土司之设,原以番蛮苗倮之属远处边荒,向居化外,故释其中之稍有功者授以世职,俾其约束,此历代权宜一时之计也。”[9]鲠葊认为土司制度创设是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因地制宜采取土司制度可以解决治理的难题,“原前代之所以设此特别制度(土司制度)者,因其地山川险恶,人民蛮野,设官则艰于治理,驻兵则殚于饷项,故即举其地之豪姓大户,使之镇抚弹压,以靖边患而固蛮疆。”[10]土司制度重要的特征为世袭制,土司“世其土,即世其民”[11],而且土司对土民的专制统治“主仆之分,百世不移”[12]。
土司统治下的区域有封闭性、割据性等特征。从本质上看,土司制度是土司对辖区内属民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性的特征带有分权性,与中央王朝加强中央集权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不断通过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特别是雍正朝改土归流后,土司的势力已经大大削弱,之后,像明代那些对抗中央王朝的土司势力已经不复存在。雍正朝改土归流后,土司势力大为削弱,但仍有一部分土司存在,没有一次性完成改土归流,后人曾为之遗憾,“当雍乾之世,国力方强,亦即冞兵深入,何不挟全盛之势乘胜荡平之,将所有境内各土司一律变更,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迄今尚有未改流之数十土司,为沿边患。”[13]
清廷还通过分袭制不断削弱土司势力,“令各土司之长庶皆得承恩袭爵。如一土司有五子者,不拘嫡庶,将彼所属地方计数分管,剖而为伍,各分其一。”并且不断降低土司爵位,“其土司之爵,降父一等。如父为宣慰使者,子袭为长官司;父为长官司者,子袭为副长官司;父为副长官司者,子袭为土舍。”“则土司之大者渐化为小,小者化为里长、头人,土司之田土、丁口皆入册籍。然后改土为流,分设州县,一二十年而各土司之蛮民皆为良民。”[14]
当然,改土归流并非一帆风顺,在具体的改土归流过程中,在一些条件还不成熟的地区,明清王朝通过设置土司或者改流复土等方式,继续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但从整体上看,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不断通过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加强对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此外,为加强对土司的控制,中央王朝不断完善土司制度,使得土司制度日益严密,土司的权力逐渐缩小。中央王朝规定了土司的职衔与品级,制定了严格的承袭制度、朝贡制度、赋税制度、征调制度等。再加上中央王朝不断将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渗透到土司地区,以致于土司不愿意继续当土司,而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流官。雍正十二年,贵州学政晏斯盛到黎平主持科举考试,当时,黎平府亮寨长官司正长官龙绍俭请求参加科举考试,在当地引起轰动,土司是世袭土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龙绍俭认为当土司“致山鸡戢翼,莫同威凤云翔”,同时,他认为“以汉官之前途远大,而土职之上进无阶”,请求参加科举考试,“冀与汉人同列绅士”[15]。雍正皇帝曾专门降旨,准许土司参加科举考试。乾隆时期,土司参加科举考试的越来越多。从这一点不难发现,土司制度已经日趋没落了。
综上所述,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不断废除土司,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日益衰落。关于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准,应看中央王朝是否继续使用土司制度管理少数民族地区。
二、从制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特征看土司制度的终结
要弄清楚土司制度终结的时间,还要清楚土司制度的内涵,《辞海》中对土司制度是这样解释的,“南宋元明清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明清两代曾在部分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国民党政府时期,部分地区土司制度仍然存在。解放后,土司制度已被彻底废除。”[16]《辞海》所认定的土司制度起止时间并不准确,土司制度始于元朝,已成为学界共识。土司制度终结的时间,学界尚有争议,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外,还应该弄清楚制度一词的内涵,《辞海》第2750页对制度一词的定义有三层表述,“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旧指政治上的规模法度。”土司制度的制度内涵应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具体到土司制度来说,就是在元明清时期形成的中央王朝管理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政治制度,其本质是中央王朝管理地方的行政制度。
从政治制度的系统性来看,政治制度存在上位制度与下位制度的问题,上位制度的终结,与其相关的下位制度都会终结,这比较好理解。比如,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与科举制度相关的乡试、会试、殿试等一系列的制度就都废除了。明初废掉丞相制度,与丞相制度相关的如丞相的议政制度、决策制度、用人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也都废除了。
如果我们从制度的系统性、完整性上看,下位制度的破坏乃至终结,也会影响到上位制度,甚至会使上位制度终结。土司制度是一个整体,土司制度作为上位制度,其下位的制度包括土司的品级制度、朝贡制度、土兵制度、承袭制度、纳赋制度、奖惩制度、征调制度、科举制度、文化制度、改土归流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从元至清,土司制度经历了产生、发展并逐步完善到日益没落的过程。明代,土司制度的内容日渐丰富,土司制度的下位制度逐步完善并确立。清代,特别是雍正朝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的下位制度多被破坏乃至废止。到清末,与土司制度相关的一些下位制度已经流于形式。
研究土司制度终结的时间,还要考虑土司制度的整体性与土司个体之间的关系,民国以后,土司个体继续存在,并不代表土司制度的存续。比如,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我们说皇帝制度终结于1912年。但之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并把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我们不能认为这时候皇帝制度还继续存在。我们可以说袁世凯当了80多天皇帝,但不能说这时候还存在皇帝制度。因此,要充分认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研究土司制度终结的时间,还要充分认识制度影响的延续性等问题。任何一项政治制度终结后,都有其后续的影响。比如科举制度,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下诏废科举,科举制度戛然而止。因此,科举制度的废止时间是没有疑问的。但实际上,科举制度废止后,对业已取得生员、贡生、举人身份者之安置如举贡生员考试,持续了好几年。其后对留学归国者授以“医学进士”“文学举人”,颇似科举制,但毕竟不是科举制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推翻了帝制,与专制制度相关的许多下位制度也都寿终正寝了。专制制度被推翻,土司制度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土司的个体继续存在。受历史传统的影响,民国建立后,许多地区的土司在区域管理中还发挥着一定作用,其功能与之前类似,但此时作为一项整体的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其系统性遭到破坏,许多下位制度已经被废止,或者是不健全了。仅存的制度也遭到破坏,比如土司制度最基本、最核心的承袭制度,明清时期,关于土司承袭,中央王朝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了土司承袭制度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土官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照例承袭,移付选部附选司勲贴黄考功,附写行止类行,到任见到者,关给札付,颁给诰勑。”[17]“承袭须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18]清末,土司承袭制度已经遭到破坏。民国时期,政府曾多次下令严禁土司承袭。
清朝后期,土司制度中的赋税制度也遭到破坏,同治九年,黎平府知府发布告示,不许土司征收赋税,土司的职责变为协助粮差征税,所征钱粮要迅速上交官府,不准土司染指,“照得每年应纳钱粮乃朝廷正赋,例应随征随解,不容丝毫侵蚀,久经遵办,并出示晓谕在案。兹查潭溪正土司所征本城潭溪、蒙村、平滴洞并四寨九溪等处钱粮,胆敢私收侵蚀抗不解缴,乃混指未完之处,以为抵搪急应严切,根究照律惩办,以警劣弁。除饬追缴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所属军民花户人等知悉,尔等应纳本年分钱粮务须粮差协同土司随收随解,不准私交土司,以杜挪用。倘仍通同作弊,一经查出,或被粮差禀覆定除,将该土弁参革严提重究,另行加倍议罚以示惩警,决不姑宽!”①土司的经济特权被废除,土司制度中的赋税制度遭到破坏。
宣统三年二月(1911年3月),民政部发布《各省土司一律改设流官》,指出“此为筹边要策”,并分析了各省土司情形,“除湖北、湖南土司已全改流官外,广西土州县、贵州长官司等名虽土官,实已渐同郡县,经画改置当不甚难。四川则未改流者尚十之六七,云南土司多接外服,甘肃土司从未变革,似须审慎办理,乃可徐就范围,拟请饬下各该省督抚暨边务大臣详细调查,凡有土司土官地方,酌拟改流办法,奏请核议施行,其实有窒碍暂难拟改者,或从事教育,或收回法权,并将地理夷险道路交通详加稽核,绘制图表,以期稍立基础,为异日更置之阶,似于边务不无裨益。”[19]清末,清政府已明确将各省土司一律改设流官,从王朝中央来看,已经废除土司制度。但由于各省情况不一,个别省份的土司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清末,民政部代表清王朝管理地方行政,它发布的公告代表国家意志。因此,民政部发布的将土司一律改为流官,应视为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
1911年2月12日,民政部上奏《各省土司拟请改设流官折》,内容包括将各省土司改设流官,还考虑到土司制度推行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区域差异性等问题,指出,“督抚暨边务大臣详细调查,凡有土司、土官地方,酌拟改流办法,奏请核议施行。其实有窒碍,暂难拟改者,或从事教育,或收回法权,并将地理、夷险道路交通详加稽核,绘制图表,以期稍立基础,为异日更置之阶,似于边务不无裨益。”[20]1911年3月31日,民政部通过《申报》发布《各省土司一律改设流官》。
综上,从民政部的奏折和在《申报》发布的通告来看,清政府已经不再使用土司制度管理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而将土司全部代之以流官。土司制度的本质是中央王朝统治者管理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其施政主体是中央王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土司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考虑到土司制度推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区域差异性,不可能一次性废除所有土司,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部分西南省份仍用土司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土司个体长期存在,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主改革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1911年3月31日,土司制度终结,但土司个体仍然存在。
三、从法理意义上看土司制度的终结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3月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于3月11日公布。其中第一章《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从法理意义上宣布了专制制度的终结,全国范围内专制制度的终结,标志着与专制制度相关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的终结。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人民》第六条规定,“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项之自由权:一,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三,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四,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五,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六,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人民的各项自由权,而土司制度实施期间,土司统治下的土民毫无自由可言,土司对土民“生杀任意”。
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是封建王朝的根本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基础,也是其它专制制度的上位制度。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专制制度,其本质特征是专制,即土司对其统治区内的土民进行专制统治。中华民国成立后,宣布了专制制度的终结,规定国家的权力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人民》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从法律上宣告了专制制度的终结。土司制度的专制性表明,土司贵族掌握了土司地区的政治权力,土司依靠中央政府授予的政治权,控制了土司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特权,对土民实施专制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司对土民残暴统治的事件屡有发生。土司政治权利的来源,是专制的中央王朝,专制是土司制度的根本特征。中华民国成立后,从法律上规定了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由此可知,民国政府不可能承认以专制制度为基础的土司制度。
总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待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任何一项政治制度的终结,都有其长期性的影响。元明清时期在中国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土司制度,历经600余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历史的惯性,土司制度终结后,西南地区许多省份仍使用土司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土司个体继续存在,并在处理民族地区的事务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四、民国时期的土司问题
民国时期的许多报纸、杂志刊载了大量关于改土归流和废除土司制度的文章,许多专家认为民国时期还存在土司制度,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之所以民国时期仍发表大量的关于改土归流和废除土司制度的文章,是因为土司制度由来已久,许多研究者一直在使用土司制度一词,这时期的改土归流和废除土司制度,实际上针对的并非整体意义上的土司制度,而是土司个体。
中华民国成立后,许多专家即认识到帝制下的土司制度与民主共和建国理念不能兼容。1912年,天津《大公报》发表《地方理由官制草案》,第十条指出:“民国肇造,人民权利、义务概为平等,故有土司省分,宜即改土归流,同受共和之法治。”土司制度的专制性与共和制度的民主性不兼容,土司制度根植于专制制度,作为一套完整体系的土司制度在清末已经土崩瓦解,名存实亡了。但土司制度行之久远,作为残余,尚有大量的土司个体存在,如何处理土司问题,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惟更张旧制,摠宜行之以渐故,如此等省分于首辖土司事宜可设专司,此亦因地制宜之意。”[21]
民国政府不承认土司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地区纷纷响应,取消土司的统治,如四川会理州出台《会理州取消土司》的文件,“四川会理州近以共和成立,不应再有土司存留,阻碍进步,于是欲将所属土司者保、披砂、通安、苦竹各土职取消,将其田产归公。”[22]可见,中华民国成立,政府不承认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已无存在的可能。
民国中央政府不承认土司制度,1931年,内政部重申要改革土司制度。当然,这时期他们提出改革土司制度,针对的是土司个体,并非整体意义上的土司制度,“内政部以土司制度有碍行政统一,不容存在,特咨行川滇甘各省,筹议改革办法,或归并县治,改置设治局,以符现制。”[23]所谓以符现制,就是说土司制度是专制的制度,在中华民国民主共和体系内不能存在,政府不予承认。这一时期,甚至土司自己请求废除土司名号,“寄居青海之土司李承襄等因中央对蒙藏各项制度力加改革,惟土司制度系捍卫边防,不宜遽撤藩篱。特呈请蒙委会转咨内政军政两部,将蒙藏王公千百户及内地各土司制度另易相当名称,以避免封建名号,所属兵队由中央予以改编。”[24]土司自身对土司制度已不再认可,要求废除土司名号。由于历史上的影响,土司个体仍将存在。随后,甘肃省取消土司名义,“甘省府通令临洮各县取销土司名义,永远革除。”[25]从这里可以看出,民国中央政府从未承认过土司制度,许多地方政府也要求废除土司制度。
1934年,西康土民要求恢复土司制度,被中央政府拒绝,在《西康土司制度中央不允恢复》中指出:“西康德格五县民众向中央要求恢复土司制度,中央据电后,以土司制度久经废止,无再恢复必要,碍难照准,将转饬刘文辉向德格等五县民众解释。”[26]文中所说土司制度久经废止,可见,民国中央政府从未承认土司制度。《西康省政府公报》称:“边省土司,原为前清遗制,民国以来,多已改土归流,旧有土司头人,亦由地方政府酌畀新职。”[27]说明土司是清代的遗留问题,并且多改土归流。民国时期的土司,是残余势力,土司应由政府任命新的职务,成为政府的办事人员。
罗英发表《滇黔土司存废问题之检讨》指出,土司制度不存在,但废除土司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有针对性的分别废除,“土司制度既不容于今日,废除自属当然!但是如何去废除土司,却要分析他内部的情形与环境关系而斟酌缓急,分别废除。”[28]1931年,行政院发布法令,取消青海省内土司,并禁止各省土司承袭,“各省政府如有呈报土司补官袭职之事,并请勿遽核准,以谋改革而昭画一。”[29]并再次重申,土司是专制制度,民国政府一律不予承认,且不准土司袭职:“土司本为封建时代之一种不良制度,现有各省土司,久已名存实亡,所辖人民,早与汉族同化……改土归流之政策,自前清末叶,即已实行。现值刷新政治之时,尤不应保留此封建制度之污点!本部自成立以来,对于各省土司补官袭职之事,概未办理。”[30]
1945年,云南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李国清发表《关于废除土司制度意见书》,从十个方面提出废除土司制度,其中第一条指出:“土司系封建产物,此种封建遗物何能容于民主时代,为实行民主,此土司制度之应废除。”李国清这里说要废除土司制度,实际上是废除土司残存个体,并非整体意义上的土司制度。第十条说:“设治局制度将近三十年,尚无成效者,蓄因土司势力大、财多、坐地凶狠。”他说的土司制度实则指土司个体。与此同时,云南省民政厅有《关于废除土司制度的批复给省政的报告》,第一句话即指出:“查土司制度,在现行法令中,已不符存在,即应渐次废除,以符现制。”从法令方面说明了土司制度已经不存在,渐次废除的是残余的土司个体,并非土司制度。并规定:“凡本省所属现任土司逝世,即将其职衔取销,不再准其子孙世袭,以期陆续淘汰。”[31]
综上,民国时期仍有许多关于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的讨论,但这些内容均针对土司个体,并非整体意义上的土司制度。民国时期,从国家层面来说,政府从没有承认过土司制度。民国时期政府的各类政治制度中,均未发现有类似明清《会典》中对土司制度的相关制度规定。部分西南省份仍用土司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说明土司个体长期存在,但这并非整体意义上的土司制度。
结 语
土司制度终结的时间应为清末。从法理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的国体是民主共和国,从未承认以专制制度为基础的土司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全体国民一律平等,土司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从制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来看,清末,土司制度的许多下位制度均遭破坏,土司制度已名存实亡。1911年3月31日,民政部在《申报》发布的《各省土司一律改设流官》,可以看做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民国时期许多关于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的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土司个体,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土司制度,已不复存在。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统治者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体现了国家对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从未承认过土司制度,因此,土司制度理应终结于清末。至于民国时期还存在大量土司的个体,则是土司制度影响的延续,是土司制度的残余,并非土司制度本身。
感谢吉首大学成臻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世愉研究员对本文的指导,文责由作者自负。
注释:
①此布告存于黎平县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