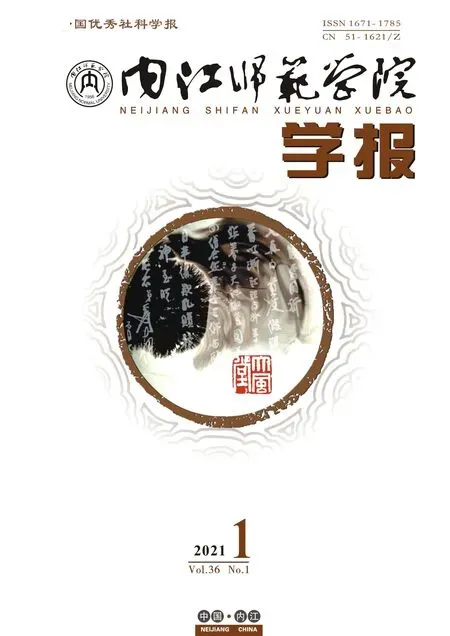现代与传统的双重规训:晚清重庆地区女性的放足与节烈旌表活动
2022-01-01惠科
惠 科
(四川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31)
清末的革新运动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女性的存在与发展问题。文章聚焦于性别与政治议题,以清末重庆女性的“放足”和“旌表”问题为例,试图突破当下较为单一地论说近代女性解放的研究藩篱。通过个案的深描,结合宏大时代背景的叙述方式,细致地分析、论证在变革时代女性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女性解放等议题。同时审思在社会精英主导下的所谓“女性解放”是否真实体现为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一、天足与种族:戒缠足、放足活动的开展
清代女性在身体上最显著,也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双“三寸金莲”,有外国人甚至将其列为中国除科举制度、宦官制度外的第三大奇习[1]。在中国历史上,“小脚”长期作为对女性审美的评判标准之一,不乏文人骚客作诗吟和。到了近代,在“强国”“强种”话语的影响下,废除缠足行为成为时人的普遍呼吁,以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
(一)社会精英与渝城天足会的成立
清代川省缠足之风尤盛。早年在山西担任巡抚一职,后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有过比较后言:“此邦(四川)缠足之风比山西更甚。”[2]英国冒险家立德夫人随丈夫立德乐在西部游历中发现“四川全省妇女,无不缠足”,为了缓解疼痛往往吸食“洋烟”[3]。1898年,英国探险家毕晓普女士溯江而上,前往中国西部,游历至四川时,她的游记中也留有“四川省的妇女全部都缠脚”[4]189的记录。在当地妇女看到毕晓普女士的“天足”时,反倒成为了一时“奇谈”[4]310。
“全省”的记载,强调的是普遍性,并不一定是包含“所有”。据考,四川的“天足”情况,“仅冕宁、邛崃、大邑、西充、南部五县有之”[5]。意味着,除去这五县外,其他府、州、县具存“缠足”之风。由此可见,重庆地区的妇女基本是以“小脚”示人的。清光绪九年(1883),立德乐到重庆考察,频频发现重庆女性那双经过“人工作用”的小脚[6]。作为近代中国的“见证人”莫理循1894年在川省的旅途中,看到妇女们的小脚后,更是感叹这是一种让人难受的“畸形”[7]。
来华的外国人,不少还撰写下大量文字,揭露缠足对中国女性身体上带来的伤害[8]。戊戌维新时期,在西方刺激以及国内开明官绅的倡导及《万国公报》《时务报》《大公报》等现代媒体的舆论鼓吹下,一些地方开始成立“不缠足会”,引导妇女革除陋习。当下研究目光普遍聚焦于上海、广州的不缠足会,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亦为当时最早成立“不缠足会”的地方,引领了地方革新的潮流。
1901年,重庆巴县的潘清荫、梅际郇、朱之洪和江津县的许廷瑞、李继沆,加上富顺县的陈公焘、奉节县的邹熙、营山县的罗庆昌、长汀县的江尔鹏等人商议在重庆成立“渝城天足会”,以“广为利导”,革除积习[9],明确订立了十四条规章[10]。从章程条款的内容可看出,渝城天足会考虑较为周详,而且组织较为严密。该会成立不久后,还得到了西方人的支持。立德夫人在1901年3月21日召集本国在渝的男、女教士以及渝城绅董到英驻渝领事署中开会,询问渝中设会的规模,并“嘱请该国驻渝友人,亦宜出为赞助”[11]。渝城天足会的创办较成功,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04年,入会人数达到200余人,还陆续有分会的创办,“辗转劝戒,以期大开风气”[12]。甚至对邻近地区产生了辐射效应。比如,涪陵县的徐某听闻重庆创设不缠足会后“颇获效果”,因此在本县“广为劝导,组织一强种会,先自其家人解放以为之倡”[13]。
诚然,地方精英是革除陋习、规制民风的重要力量,却也因自身条件的局限,注定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推进有所困难。行政官员作为地方一切事务的主要负责人,恰恰能够弥补民间力量的不足,使各项活动的规模和影响更为扩大。尤其是清末“新政”以来,不缠足作为国家的革新措施,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重视的活动之一。
(二)官府的劝谕与禁令
1902年,清廷下达谕旨:“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搢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14]政令既出,民间又多有开明之士设立不缠足会,风气已然渐开,整治缠足的活动已是势在必行,地方官吏以各种姿态参与其中。截止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15]。
川省在岑春煊等总督的大力倡导下,不缠足活动收效好,可以说是领先全国。《大公报》评论:“惟一岑云帅其在署川督任内,所刊发之白话示谕,近已流传殆遍,故川省之戒止缠足者较他省为多。”[16]岑春煊所作的《劝戒缠足示谕》[17]文字通俗、畅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个人的健康谈到国家的强弱。1904年,岑督仍恐“未能尽执途人而告知”因此“撰成官话浅说之戒缠足文,刊印5万本,颁发其所属之各官绅”[18]。也就难怪天津的绅矜曾建议地方官仿照此“示谕”出示告示[19]。
结合上文可知,重庆绅矜组织的天足会确取得不少实质性进展。这对渝城放足风气的推动,甚至邻近其他州县地区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民间力量始终有限,不借助官方的支持,或者说寻求“合作”,这类民间组织难以长久维持。就连在华的外国的传教士也认识到:“查该会(天足会)之兴盛,其第一最大之助力,实当感谢中国明理之诸大员”[18],强调了官员的重要角色。且官为民之表率,“官先抗旨不遵,民自无从照办”[20]。
光绪三十二年(1906),巴县举人冯渐逵、伍名钊、文国恩等人就在民众放足问题上遇到难题,不得不求助于巴县衙门出面解决。
绅矜们指出渝城百姓“习染既深,骤难改革”。加之各种原因,部分民众并不知晓官府的态度,因此对于放足一事摇摆不定、相互观望,“间有愿解放者,亦以县主无示,疑信参半”,生怕绅矜们说谎,受了蛊惑[21]。这在当时确为常见现象。如浙江绍兴府的几位绅矜起初在余姚县设立了一个劝放足会,吸纳了部分人员,后打算在绍兴府城设一分会,民众参会者寥寥无几,询问缘由,百姓告知:“皇上没有叫百姓放脚,官府也没有出过告示。”[22]可以发现,地方社会对官府的依赖性,故而绅矜们不得不到地方衙门具禀,请出示告示支持。本例中,冯渐逵等渝城绅矜们特别强调“保章中之文告不如父母官之晓谕为尤亲切”[21]。其意在请求知县出示晓谕。同时,他们还希望通过奖赏制度来引导民众,实现风气大开。兹列其禀文如下:
凡强民种、卫民生、勤民事、阜民财端自放足始。是以举等协恳示谕,令互相劝勉,限三月内,将各团遵示放足之家造册呈辕。恳恩赏批嘉奖,以示鼓励。务期人皆天足,而后已似此,民知定向,风气大开,一切行政肇基于此矣。[21]
霍知县同意了他们的禀请,采纳了他们提供的方案,作为劝告民众放足的办法。
实际上,沿袭上百年的旧习,早已幻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若试图从世人习以为常的思想观念中将其剥离,趋使其向相左的方式发展,注定是漫长的。所以,尽管“川中放足之风数年以来”,也“经各处志士先后提倡”,无奈“积习太深,难以骤剔”,到1906年仍旧面临“不肯释放者,总居其多数”的问题。[23]故而,地方政府必须保持长久的耐力,常年累月地进行引导、规劝。
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二十六日,县衙发布了晓谕告示,明令重庆各地妇女一定摒弃缠足的陋习。归纳起来,告示透漏出如下几方面的信息:
首先,从国家、民族立场出发,将国家前途与女性放足结合论说。“保国必先于强种,兴利莫急于革弊”。“际此时局艰难,外忧迭起,其原因虽极复杂,而缠足一端,实为致弱之渐,内贼害其种族,外贻讥于天下”,强调“倘能依限解放,使百年痼习一朝翦除,自强之基即在于是”。并说明朝廷已明令取缔缠足的陋俗——“朝廷知缠足种弊,屡须明诏,各大宪亦纷纷出示助禁”,从而打消百姓的疑窦,防止民众观望不前的态度。
其次,从城乡差异、女性解放及道德层面展开论述,以此加快革陋的步伐。具体而言,告知城中已经有不少女子自愿放足,“女界中之放足者已属不少。各乡离城较远,风气较迟于城内”。缠足导致无辜女子,永沦苦海,“不惟贻害国家,抑且大乖人道”。
第三,强调县衙早已发布禁令,县议事会也设有禁止缠足会,进而增进百姓的认知。
最后,为了防止引起百姓的恐慌或旁生事端,知县特别指出,所采取的措施并非出于干涉民众正常生活的目的,只是出于“身弱国危”的考虑,“须知处竞争之时,不能有孱弱之族”,借此取得百姓的理解和认同[24]。
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彰显官府的威严,“示谕”最后强调违者将会受到惩处,并且具体到以县议事会所拟定的禁止缠足会规则十二条为标准。比如第五条规定“前奉之限期只许提前不准移后,限满放延者,得由分会科以五角以上、二元以下之罚金。每月罚金一次,总以罚至实行放足为止。前项罚金数目由分会酌定,该户主缴出以充本地分会公用”[24]。
县议事会是清末地方自治的产物,作为地方自治组织机构,负责地方各项公益事业。负责人董事由地方官任命,各种活动也受地方官的监督。在地方治理上以相互配合、合作的形象出现,“官率于上,绅应于下”。衙门对议事会制定的规则的认可是出于有利活动的开展与落实而考量,也是在官绅权力调适过程中寻求合作的方式。必须正视的是,衙门的这些“明文”劝谕也存在局限。比如,社会识字水平低下的问题。生活在乡村的百姓大都目不识丁,告示的价值不大。加上地处偏僻,消息流通不便,所以缠足现象依旧如往昔。这一问题也引发地方精英的注意。因此,在方式上他们建议县衙同时注重“宣讲”方式的采取。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文生吴鸿志、监生李鲜九等人为“地方公益事”向巴县衙门提出禀请,重点谈及“农桑”“地方自治会”和“放脚”三件当下亟待解决又多有困扰的事。应国家振衰起弊的决心,巴县衙门曾三令五申地要求地方落实各项政令,“几于大声疾呼,舌敝唇焦”,最终面临的却是百姓多置若罔闻的尴尬局面,“狼跋其胡,载踬其尾”便是县令此时内心的写照[21]。
地方精英们查觉出百姓之所以表现出疲顽的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民之识丁者鲜而又不得里正为之演说”[21]。尤其谈到“放脚”的问题,即便衙门多次发出告示,也在各处要道张贴,以使民众知晓。怎奈百姓识字水平低下,尤其是乡村的妇女,无法知晓文本要传达的意思。另外,存在部分里正“阳奉阴违,不为实力开导”,“放脚”活动的正常开展受限,效果自然无法彰显。为此,士绅将拟定的建议告知知县,望能采纳:
生等冒昧早夜以思,谨将放脚各端恳恩札饬四乡里正集期演说,申明公益,庶颓风可挽,足勷圣明,是否有当?理合协恳札饬各里正演说,以明公益,黎庶均沾伏乞大老爷台前赏准施行。[21]
一言蔽之,请求衙门下令让各乡里正选定日期、地点,将百姓召集一处,向他们宣讲衙门戒除“缠足”弊端的决心。针对禀请,知县经一番考量,觉得“据禀不为无见”,后作出批示:“仰即传谕各场里正各就地方情形”,“演说宣讲以补文告之不逮,□不得藉端派索”[21]。
演讲,将无声的文字转化成生动的话语,又通过与百姓日常交往频繁的里正来主持,平白晓畅的话语、地方熟悉的人,既能在最大程度上让百姓“听懂”,又具有可信性,自然会减少阻力,推动“放脚”活动在乡村的开展。
概而述之,近代中国女性日常生活方式的“缠足”被迫与国危民弱的时代特征捆绑在一起,国家到地方号召以女性形体的解放为媒介,试图达到摆脱“病夫”的偏见,实现保国强种的目的。通过上述考察,发现晚清重庆的放足运动得到了官府和民间力量的有利配合,采取了多项措施——劝谕、禁令,借此要求民众戒除束缚身体、束缚国家发展的这一块“裹脚布”。在他们的共同致力下,重庆出现过“放足之风盛行,无须立会”的情况,故有人建议将天足会的经费挪用作学堂日常开支[25]。最后,对于女子来讲,被束缚的身体将得到解放,活动的空间扩大,女性地位随着社会发展得到提升。然而,我们稍作思考,不论是“缠足”还是“放足”,体现的仍是男性对女性的“管理”,女性又再次走向男性精英试图建构起的社会秩序中。
二、传统女性形象的坚守:贞女、烈女(妇)的表彰
从国家话语体系来看,在传统社会,以建坊、赐匾为特征的“旌表”活动是维持社会风俗教化的重要手段。而从性别的角度来观察,对贞女、烈女(妇)的旌表,对女性实则是一种“残害”。为换取国家意识主导下的“道德”完整性,女性由被动到主动地利用这一套“标准”对自己思想以及身体进行禁锢,真实地反映了女性在传统社会的地位与角色扮演。难以想象的是,这一活动在清末社会改革的背景下继续开展,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出现大规模、大力度的旌表现象①。
(一)贞女的旌表
关于女性贞节的话题,在中国很早便有论述。《周易》中记:“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26]。《礼记》又载:“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27]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对女性保持贞节大力倡导,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旌表条件的进一步放松[28]。
巴蜀之地“民质直而彪悍”,民风淳朴,为人耿介,自古多忠烈之士、贞节之妇,在朝廷的倡导下更是大量涌现。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在清末进入重庆境内,发现“每闾有节孝坊,坊皆华表,两柱刻兽,上题联句。又揭扁额,镂金施彩,最为壮丽。”这位外来观察者还捎带提及旌表的程序问题:“若节孝坊,则其子若孙请诸官,官以闻于朝,合格辄赐旌表。”[29]
关于清代守贞女性旌表的程序,早在雍正时期就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各直省督抚饬所属州县,将一应合例旌表之节妇,并贞女孝子,详细条例,遍示乡城士民。令本家开载事实具呈,并饬乡邻族长于具呈日一并据实投递甘结。该学该州县核其事实确据,即行加结详报该督抚确核存案,据实汇题,毋庸往返駮诘,致滋弊端。”[30]
从巴县档案的记载来看,重庆城的贞女、节妇旌表基本是按照这样的规制进行,下面举例实例简要说明。
宣统元年(1909),巴县儒学训导廖文成具陈了邑内节妇商彭氏请求衙门予以旌表的文书。其呈文原文如下:
卑学遵将已故节妇商彭氏系本邑处士彭正有之长女,生于道光贰拾年庚子伍月初玖日吉时……膝下无子,过继氏夫胞兄光凤之子,更名明孝,承祧为嗣。光绪陆年庚辰病故,时年伍拾壹岁,计守节叁拾肆年,与例相符合。已故节妇商彭氏奉养翁姑,生则尽食,殁则尽哀,理合登明。
右具
宣统元年十二月□日
署巴县训导廖文成[31]
同时,受旌节妇的家人也很快开载了节妇的相关信息具呈县衙,以为相互印证。本例中,商彭氏的儿子商明孝向县衙具陈:
民母商彭氏生于道光贰拾年庚子伍月初玖日吉时……民母于光绪陆年庚辰病故,计守节叁拾肆年,中间不虚,亲供结,是实。[31]
除此之外,与请旌人在地缘上“亲近”的乡邻、族长相应的也向县衙提供了真实情况,以供县令参考,决定是否上报旌表该节妇[31]。
待各方人员具禀、保结事宜完成后,巴县令对节妇的守节年月、守节事实进行严格审核,发现所请无虚后,县令向宪台提出了给予旌表的请求:
该氏等心坚金石,志凛冰霜,年例均符,旌表扬宜及,理合将赍到册结,加结粘鈐,具文详请宪台俯赐察,核转详示遵。[31]
待宪台审核通过,就上报朝廷,等待最后的定夺。以上繁琐的消息汇报、核实等程序的进行,明显是为了防止谎报、误报等不实情形的发生。类似的例子在巴县档案中不胜枚举。再如,宣统元年(1909)三月,巴县儒学训导屈鑫为廪生欧阳杰之女已故的欧阳贞氏及现存节妇牟吴氏恳请旌表[32]。考虑到请旌文在内容上大同小异,故不再罗列说明。
关于旌表的形式,由于档案保存的不完整性,所查案例皆难窥见。不过,从方志中,可以发现建立贞节牌坊是常见形式。如巴县的龚节妇高氏,“苦节逾五十年,建坊入祠”。李国靖妻罗氏,“苦节五十余年,建坊入祠”[33]401。早在清顺治时期,就有明确的规定:“凡旌表节孝在直省、州、府、县者,官给银三十两……听其自行建坊。”[34]
总之,审视晚清重庆的节妇旌表活动,在程序上符合朝廷的制度要求,体现出繁复性的特征,出发点则是保障请旌活动的真实性。此外,对旌表信息的层层审核、上报,既是旌表制度系统化的表征,也突显了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沟通民众和上级官府的角色。而观测作为活动主体的女性,在其中扮演的不过是一种被道德观念牵引下的“她者”,实际的参与感并不强,家人、家族、地方政府显然是凌驾于“她们”之上。除对节妇表彰外,女性旌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则是对烈女的旌表。
(二)烈妇的旌表
烈妇或者烈女常指通过结束自己生命的惨烈方式表明志节的女性。清初国家对此种行为并不倡导,康熙曾明谕,曰:“夫亡从死,前已屡行禁止……人命关系重大,死亡已属堪怜,修短听其自然,岂可妄捐躯体?况轻生从死,事属不经,若复加褒扬,恐益多摧折。嗣后夫殁从死旌表之例,应行停止。自王以下以及小民妇人,从死亦应永行严禁。”[35]继任者雍正沿袭康熙的“意志”,1728年颁布谕旨:“著地方有司广为宣布,……俾愚民咸知孝子节妇之自有常道可行,而保全生命之为正理,则伦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负国家教养矜全之德矣。儻训谕之后,仍有不爱躯命蹈于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闾阎激烈之风,长愚民轻身之习,思之思之。特谕。”[34]
实际上,对烈女、烈妇旌表行为的禁止并不彻底,朝廷多是采取“弛禁”态度。如1730年,江西巡抚为两位因夫亡而从死的未婚女子请旌,“经部具题请旨”,雍正帝竟也准予旌表[34]。此类现象并不是独例。究其缘由,烈妇、烈女的旌表是国家引导基层社会道德的重要一环,是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形式,自然不可能完全杜绝,甚至在清末依旧频繁见于各地。
重庆地区的烈女现象在清代也是较著名,我们从清代畅销的画报——《点石斋画报》中便可发现重庆烈女的身影。画报描绘出重庆东川书院旁曾住有一田姓女子,貌美而稳重,一富家子弟见其起淫心,欲强以酒奸污之,女子怒詈,自缢而死。后人有闻者,立碑表彰其贞烈之风[36]。地方志的相关事例记载更多。譬如,渝城杨氏女夫徐骞因屡试不第在京旋殁,女听闻后自尽殉夫。再如,1862年,“太平军自涪入,所过淫掠”,彭昌洲妻恐不免于难,遂自杀[23]404。查询光绪年间的巴县档案,大量记载了清末重庆地区频繁的烈妇旌表现象。
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廪贡生候选汤文炳之妻赵烈妇殉夫的事迹被访得。廪生许元瑞、孙熺、尹德明、曾世文等人向巴县衙门提出请旌要求。
禀文中首先讲述了两个“典故”,一为唐代郑义宗的妻子卢氏在家遭盗贼时,面对持刀而入的贼匪,家人悉数逃走的情况下,卢氏独自一人为保舅姑周全,几被贼人锤击的事例。另一例为东汉女史学家班昭,即后世称的“曹大家”作《女诫》的典故。以此引出“从来贞廉忠孝非烈,无以玉其成”的论点,进而希望衙门能准予赵烈妇的旌表[37]。
关于赵烈妇的生平、事迹,绅矜们告知知县,“幼娴姆训长,适儒生,大节不夺芳烈,可重”。关于其殉夫的“烈迹”,禀文写得更是详细:
光绪二十九年,该氏夫文炳赴北闱乡试,侨寓汴梁,身染重疾。氏七月闻耗,痛不欲生,哀将逝于所天,愿相随于地下。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即于本年九月二十六日三更后,仰药而死。[37]
服毒方式的选择预示其抱着必死的决心。绝食、上吊、跳井等方式或许还有生还的可能,而服毒,一旦毒性发作,药石无效矣,由此足见女性强烈的贞烈观念。
此外,绅矜们在禀文中强调“夫颠沛阽危,惟烈乃能奇其事”,“父台化行俗美,巾帼乃多完人,微显阐幽阎,始生观感”,因此请求“老父台大人”为烈妇赐匾,并书上“矜怜表扬”四字旌其门楣。并表明此举可达到“恤苦衷而敦风化”的效果。赐匾,同建牌坊一样,都是属于朝廷肯定的精神上的奖励形式,而且经费负担相对较轻。
最后,巴县令认为“赵氏义烈可嘉”,同意了绅矜等提出的赐匾要求,并书上“矜怜表扬”四字,“以示旌扬”。且将相关事迹收录于衙门档案中,作为地方风气民俗的榜样[37]。
至于“建坊”的表彰方式,在档案中也有体现。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对烈妇郭刘氏的旌表,便是采取巴县衙门出银30两,然后“听本家自行建坊”的办法[38]。
综上,清末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朝廷为振衰起弊,制定、出台涉及各个领域的改革办法,追求现代民族国家之建立。但是,不论从改革的方向、力度、还是内容上,都与期望的效果有很大差距。以上述考察的主题为例,对女性有禁锢影响的旌表行为并未中止,反而继续得到基层政府和士绅的支持。若追问此种现象这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什么?结合上述事例,稍作分析便可得出答案。旌表制度对于女性,是她们在逐渐失去对知识、技能的掌控力后,只得依赖国家、地方精英标榜的“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途径。而此种个体价值的彰显与实现,实际是以忽略女性个体真实的声音,甚至牺牲生命为代价的。即便是到了清末鼎革之际,依旧作为女性的生活经验并指导她们的思维、行动,以此达到维持整个社会共同遵守的性别制度和道德规范的目的。
三、结语
本文通过巴县档案保存的文本,考察了清末重庆地区女性的旌表和反缠足问题。奇怪的是,在追求现代化、文明化的近代中国,这两类相矛盾的活动出现在同一时空。一般认为,通过“天足”运动的倡导,追求现代的文明生活方式,引导中国传统女性的解放;至于地方的请旌活动,对女性而言,是一种思想、身体的继续束缚,甚至摧残。究竟该如何理解在这特殊时代背景下,同时存在的女性“解放”和“束缚”问题?
笔者认为这组表面上看似矛盾、冲突的现象,背后蕴含着高度的统一性或者说合理性。一方面,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时代挑战,实现由大一统的帝制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转型的艰巨工程打造,女性成为了重要的一环。故而,重庆地区官绅积极互动、广泛开展的放足运动是被赋予了强国强种的政治意涵。在这一意涵的感召下,女性甚至被塑造成“国母”的形象,她的健康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地位得到了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得到了觉醒。相反,这一套说辞不过是社会精英借助“国家”话语,换了形式的社会控制行为。或正如福柯的论说:“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形式和发出某些信号。”[39]即便不少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保持着相当坚持的态度,也不过是被国家塑造的结果。
另一方面,同样是地方乡绅和政府紧密配合运作下的女性“旌表”活动,秦汉以降,便是国家引导风俗、教化民众,实现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到清代更是盛行,法律手段也常运用其中,对“守节”行为进行强制性保护。比如规定:“妻妾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40]如前文所述,晚清不仅面临严重的外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不断激化,呈现出“内外皆轻”②的权力格局,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继续正常运转,国家权力不断渗透,传统的措施不断强化、新的政策又不断颁布。而旌表制度是被国家和地方精英共同认可的道德评判、秩序维护的重要手段。曾在中国居住长达半个世纪(1861—1910)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雅德就发现:“在这地域跨度如此之大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儒家的道德规约和意识形态在维系和凝聚着这个国家的精神”,为旌表而建的牌坊是中国人臣服皇权的重要象征[41]。
一言蔽之,以上两类活动的开展,是国家在社会秩序面临失范的情况下,借助“女性”达到强化社会控制的目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帝制时代,中国女性的地位和处境问题。从女德的“旌表”到形体的“解放”,女性再次被形塑为稳定和固化社会秩序,国家实现对基层社会控制的载体。故而,作者认为,在“近代化”和“伦理道德”双重压力塑造下的重庆女性,不过是不断变化的政治需求的载体,知识精英倡导的女性解放只是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建构目标。
注释: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张雪蓉.晚清女性贞节礼俗社会教化功能的强化及其变化探微[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3);祁艳伟.晚清旌表制度变迁初探[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1.
② 有关清末呈现出的“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特征可参见李细珠.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J].近代史研究,2012(3);李细珠.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J].清史研究,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