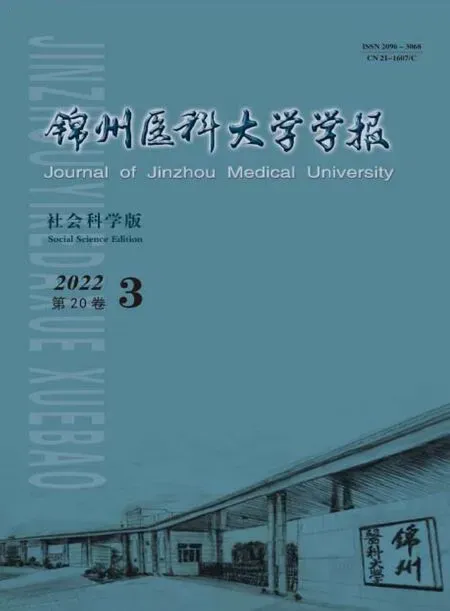“新医科”教育改革需要“群医学”三大体系创新
2022-01-01杨善发
杨善发
(安徽医科大学 卫生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新医科”是2018 年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的[1]。2019 年4 月,教育部、科技部等13 个部门联合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启动大会,要求全面实施“卓越工程师、卓越医生、卓越农林人才、卓越教师、卓越法治人才、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新农科,同时公布了“四新”学科建设工作组名单,其中,新医科工作组组长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王辰担任,北京大学詹启敏、中国医科大学闻德亮、复旦大学桂永浩、上海交通大学陈国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包信和以及四川大学张林担任副组长,另外还有其他高校的16位成员[2]。
2020 年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以“新医科”统领医学教育创新,提出“到2030 年,建成具有中国特色、更高水平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医学科研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服务卫生健康事业的能力显著增强”的远景目标[3]。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其全球蔓延,使“新医科”教育改革成为更为紧迫的任务。
一、“新医科”与“群医学”发展概述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世界医学教育深受美国《弗莱克斯纳报告》的影响。1910 年发表的《弗莱克斯纳报告》将医学教育引入生物医学时代。2006年,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医学院库克(Molly Cooke) 等在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发表《弗莱克斯纳报告之后的美国医学教育100 年》一文,认为医学教育需要根本变革,改革的路径也是明显的,即更多强调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方面。然而,一旦涉及课程改革、临床教学改革以及医学教育经费等具体问题时,改革就面临诸多挑战[4]。
2016 年,哈佛医学院卡斯珀(Jennifer Kasper)等介绍了哈佛医学院2007 年开始的对所有一年级学生开设“社会医学”课程的情况,指出此举可以推进医学院校课程体系超越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预防与治疗以及本土与全球的传统界限,使学生具备应对美国与世界复杂健康问题的知识与技术[5]。2017 年1 月,《学术医学》杂志出版了新医学教育改革专辑,并邀请美国纽约大学的汉森(Helena Hansen) 与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墨茨尔(J.M.Metzl)教授发表题为《为美国卫生服务体系构建新医科:培养医生具备结构性干预能力》的评论,指出医务工作者通过与医学以外的专业领域(包括社会科学与法学等) 合作,有助于提高人口健康水平。该专辑的系列文章表明,认识疾病的结构性原因,提出结构性干预措施,培养与非医疗卫生机构联合实施结构性干预的能力,使其可以与相关部门人士合作,就能够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减少健康不平等[6]。韦恩斯坦(Ronald S.Weinstein) 等认为,在第二个弗莱克斯纳世纪,医学教育的重心应从医学生向社会大众转变,推进医学知识的民主化。为此,要面向社会大众开展四种健康素养教育,即全生命周期健康素养、疾病知识素养、药学知识素养和医疗过程素养教育[7]。
2019 年11 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有效应对流行病需要一门21 世纪的新科学》的文章,认为随着快速变化的生态、城市化、气候变化以及旅行的增多与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流行病将变得更为常见、更加复杂,也更难预防与控制。因此,需要将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整合起来,不仅包括流行病学,还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与开发、外交、物流与危机管理等。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培养未来的流行病预防与应对的领导者[8]。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哈佛医学院的两位学者在《社会学前沿》杂志发文指出,新冠肺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疾病,因而仅通过生物医学技术措施应对是不够的,需要全球领导者研究制定并分享基于社会医学的应对措施[9]。
国内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新医科”与“群医学”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顾丹丹等认为,新医科旨在探索全球工业革命4.0 和生命科学革命3.0 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模式,实现医学从“生物医学科学为主要支撑的医学模式”转向“医文、医工、医理、医X 交叉学科为支撑的医学模式”转变,培养能适应新一代技术革命、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医学领域前沿问题的高层次医学人才[10]。何珂、汪玲指出,新医科是从人的整体出发,将医学及相关学科领域最先进的知识理论和临床各专科最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有机整合,并根据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等方面进行修正、调整,使之成为更加符合、更加适合人体健康和疾病诊疗的新的医学体系[11]。2020 年5 月,面对新冠疫情的蔓延,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邀请部分专家召开新时代医学教育发展与改革研讨会,认为必须推进医学教育多层次、全方位改革,为健康中国2030 保驾护航[12]。李凤林提出,新医科是一个广义的、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是高等医学教育顺应新时代要求而提出的。新医科建设需要强化学科基础性、交叉性,增强科技融合性,深化医学人文性,突出医学贡献性[13]。
新医科建设工作组组长王辰院士则倡导群医学的发展。与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将西方的“社会学”(sociology) 译为“群学”相类似,王辰院士研究团队将“population medicine”译为颇具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群医学”,并指出群医学是融合、运用当代医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和原理,基于现实可及的卫生资源条件,统筹个体卫生行为与群体卫生行动,指导公共卫生实践,实现人群整体与长远健康效益最大化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2019 年初,王辰、单广良教授等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申请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并于同年5 月获得批准;2020 年6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协和医学院增设交叉学科“群医学”;2020 年7 月16 日,协和医学院正式成立“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2021 年4 月,《群医学》中英双语译本正式出版,该书译自群医学主要倡导者——牛津大学穆尔·格雷(Muir Gray) 爵士的代表作《群医学》 (Population Medicine),王辰院士和杨维中教授担任主译、张孔来教授主审,作为群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卫生管理等专业学生教材、参考书目使用[14]。
综上可见,“新医科”的发展还处于初步探索期。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医科”的内涵尚无统一的界定,甚至对“新医科”的名称也还没有一致的主张,是将其命名为“群医学”?还是将其称为樊代明院士所倡导的“整合医学”[15],或将其称为陆家海教授[16]和陈国强院士[17]等所倡导的“全健康”(One Health)?或是将其命名为汤钊猷院士倡导的中西医结合“新医学”[18]?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一些共识已基本达成:新医科强调新理念指导下的医学教育改革,是高等医学教育的一场“质量革命”;新医科建设的核心要义是要打破学科壁垒、突出交叉融合,推进医科与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新医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从以生物医学为支撑的医学模式转向以医学与文、理、工等其他学科交叉为支撑的新医学。
二、推进“群医学”三大体系建设
从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团队的定义看,群医学超越了传统医学的范畴,它既是一门交叉学科,也是一种价值取向,还是一种方法学;既具有自然科学属性,又具有人文与社会科学属性,因而就其本质而言是医学哲学与社会医学的当代创新。2016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19]由是观之,群医学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新医学”,也需要推进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建设和创新。
1.群医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学科体系是基础。不同的学科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同时又因其对象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而相互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包括多个学科的、更高层级的学科或学科群。
从社会医学发展史看,群医学是社会医学的当代发展。欧洲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人口聚集、传染病与职业病频发等诸多公共卫生问题,国家与社会都迫切需要保护人口健康,因此,政治医学和社会医学的出现成为19 世纪医学史上最有特性的事件之一[20]。但社会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学界多认为是由法国医师盖林(Guerin,1801~1886 年) 1848 年提出的,而美国学者罗森塔尔明确指出:社会医学的创始人是恩格斯,而不是盖林、魏尔啸等人[21]。的确,恩格斯的社会医学研究比盖林、魏尔啸都要早。早在1843 年,恩格斯就在英国进行了长达21 个月的实地调查,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于1845 年出版,从英国工人阶级卫生状况恶化的表征、领域、成因等方面完整地构建了早期社会医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共卫生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对西欧社会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华德·韦茨金在其代表作《第二疾病》中也明确指出,魏尔啸的思想受到恩格斯的影响[22]。
1974 年10 月,法国哲学家福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作的《社会医学的诞生》 讲座中指出,进入18 世纪,人口成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群体,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要从数量上、还要从质量上来理解;医学也不再仅仅是围绕个体健康组织起来的话语,而更加是一种政治话语,是一种可以促进国家力量增长的政治机制,是一种以国家名义展开的政治行为,是一种为了国家健康和国家力量而实施的干预措施[23]。亨利·西格里斯特(Henry Sigerist)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工作,1937 年出版《苏联的社会化医学》一书,倡导苏联的社会医学模式,1947 年该书再版;英国一群激进社会主义医生受其影响成立了社会主义医学联合会(Socialist Medical Association),对战后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1943 年,牛津大学成立第一个社会医学研究院,标志着社会医学学科的正式建立。然而,由于受冷战及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英美等西方国家将“社会医学”等同于苏联的“社会化医学”和“社会主义医学”,因而,西方国家的社会医学教学研究机构不得不改头换面,以“社区医学”“公共卫生”等名称而艰难地延续下来。西格里斯特也被迫于1947 年离开美国[24],西方国家社会医学的学科发展受到了严重阻滞。
因此,时至今日,社会医学的学科地位仍然有待巩固和提升。群医学作为社会医学的当代形态在21 世纪初的兴起,其内涵与外延比19 世纪的社会医学更为宽泛,不仅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康复医学等医学学科,还融合了哲学、社会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因而它是一个由哲学、医学(包括西医和中医学) 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构成的宏大学科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学科之“群”。
2.群医学学术体系的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学术是核心。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之间互有交叉、互相渗透。但学术体系是对一个学科内部逻辑关系和原理性问题的探讨,是围绕特定对象形成的学理性知识,是按照一定的内在学理逻辑与叙述次序形成特定的学术认知体系,主要体现为一系列学术命题、学术观点、理论学说所构成的体系。
医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从科学史上说,20 世纪50 年代初才是“医学科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时期”,所以,美国杰出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把医学称为“最年轻的科学”[25]。此后,医学学术研究聚焦于生物医学。生物医学的迅速发展使社会医学日渐衰落,生物医学与社会医学模式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世界性难题。1977 年4月,《科学》杂志刊发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乔治·L·恩格尔教授的文章——《呼唤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挑战》[26],倡导“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但四十多年来,这一“新医学模式”的影响力并不明显,医学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变化的却不是“新医学模式”的建立,而是生物医学模式的不断强固。如今,人们常常感叹,生物医学模式的“城堡”太精致、太坚实、太雄伟,我们根本无需去“撼动”它,只需在“城墙”脚下为“心理”“社会”的医学旨趣搭建两间“偏房”,作为人们闲聊或论争的“茶室”与“咖啡吧”,也成就了恩格尔的“理想”[27]。据此,笔者认为,现代医学发展需要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只有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颠倒为“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创新发展群医学,才能推进医学模式的根本变革与创新。
群医学的学术体系与传统医学的学术体系有很大不同,它是人民群众(包括医学专业人士和社会大众) 对卫生健康与医学认识的概括和总结。实际上,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之间的裂痕之所以久久难以弥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物医学与社会医学模式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造成的。20 世纪70 年代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西方福利国家不断萎缩、国民健康差距不断扩大。新冠肺炎患者遭受差别对待,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生物医学模式长期盛行的必然结果。面对百年罕见的新冠疫情,中国政府用很短的时间遏制了疫情蔓延,取得了疫情防控的决定性成果。但西方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政策长期扭曲了民众的价值观与抗疫认同,致使疫情蔓延至今。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人民生命健康至上与资本利润至上的鲜明对比,不仅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政治优势[28],也昭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西方政治制度与生物医学模式的严重缺陷。
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赫拉利指出,医药之所以能在20 世纪使群众获益,是因为20 世纪是群众的时代。20 世纪的军队需要几百万的健康士兵,经济发展也需要几百万的健康工人。因此,各国都建立起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确保国民的活力和健康。但这种群众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而针对大众的医学也将随之走入历史。20 世纪,因为穷人有军事和经济价值,精英阶层必须为穷人解决问题。但到了21 世纪,就算会有许多医学突破,我们仍然无法肯定穷人到了2070 年一定能享有比今天更好的医疗保健,因为国家体制和精英阶层可能根本不想再为穷人提供医疗保健[29]。
或许正是针对医学发展的这一危险趋向,有识之士在21 世纪初大力倡导群医学的发展,呼吁以“群”之方法关注“群”之健康,推动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提高群体健康水平。群医学要研究“患者之群”“高风险者之群”“常人之群”“医者之群”“学科之群”乃至“界别之群”[30],创建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新医学。因此,群医学的学术研究应该有大视野、大气度、大胸怀,需要一种大医学观、大卫生观、大健康观。在群医学学术体系建设中,要注重将大医学观、大卫生观、大健康观具体地体现在相关科研课题的规划、申报、评审、管理体制和机制,医学人才培养、学位授予体制机制等多方面,注重处理好群医学与原有的医学学科与学术体系的关系、群医学相关研究成果的评价等重要问题。
3.群医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话语是关键。话语体系是一定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内在所指内涵的外在符号能指系统,一定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语言表达系统和载体。福柯指出,话语即权力。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将医学话语转变作为主线贯穿始终,揭示了医学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其话语权理论是对西方国家抢占思想意识制高点和主导权的深刻反映,具有广泛的影响力[31]。可见,群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尤为重要。
然而,当今医学的发展使其与病人的距离越来越远,病人的话语权日益弱化,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因而亟待从生物医学模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向群医学迈进。人们都熟悉特鲁多医生的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表明,要解除患者病痛,很多时候并非依靠医术,而是依靠医生的帮助和安慰。近年来,国内外医学界都提倡“叙事医学”,要求医务人员必须学会和患者沟通,其根本原因在于,叙事医学就是要求医务人员以情说话,带情倾听,用情看病,创新应用群医学话语体系。
群医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要求着力推进人文医学与医学科普事业的创新应用,着力培养医学生与医务人员的人文素养与交流技能,着力提高医务人员的话语能力与人际交流水平。穆尔·格雷在《群医学》一书前言中明确指出,群医学是21 世纪的必需品,我们需要会“双语”的临床医生,他们既可以说自己专业的语言,也可以说人群医疗保健的语言。群医学还要求注重群众参与医疗卫生服务过程,推进医患共同决策与医学的民主化进程。[32]
总之,群医学三大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涵盖生物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众多学科的“学科集群”,因而,应借鉴德国以“卓越集群”建设为重点的“卓越大学”建设经验,聚焦重大研究问题,淡化学科界限,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与整合,注重为跨学科研究团队的组成创造一些制度性条件[33],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群医学三大体系创新平台。
三、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群医学”
群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现实的迫切需要。我国有一种完全源自本土思想、后被严复等人称为“群学”的社会学系统,也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医学的传统中医药学,因此,我国群医学的发展应具有中国特色。对于西方的相关理论、概念和术语,我们不能全盘套用,即使对国外生物医学的成果也不能照单全收,而是要注重以中国国情与社会医学实践为基础,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群医学。
韩启德院士指出,目前的诊断标准基本上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但我国人在生理和病理上可能有所不同;而且,每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能用于医疗的投入也有明显差距。因此,我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来确定自己的诊断标准,如将降血压治疗的门槛和治疗的目标定在哪里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除了医学因素外,还有卫生经济学和社会学因素。我国2000 年对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做了改变,正常血压由原来160/95mmHg 变成了世界统一的140/90mmHg。2017 年,美国又把高血压诊断切点降到130/80mmHg。按此标准,我国将陡然新增至少1 亿高血压患者。韩启德院士认为,我国最新的高血压指南没有跟随美国,而是维持原来的切点不变,这是“明智的决定”。我们的医学技术如果沿着“用更昂贵的治疗方法,治疗更少数人疾病”的方向发展,对整个社会是有害的。我国人口众多,拥有丰富的临床医疗信息资源,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加强医学大数据和人群及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不要盲目迷信西方发达国家订立的标准和方法,开拓创新,把我国对危险因素的控制和疾病筛查牢牢地建筑在有效促进公民健康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34]。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指出,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包含着中国社会学的基因,深藏着解释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密码。我们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合群、能群、善群、乐群[35]。同样,我们要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就要建设“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群医学”。青年哲学学者吴冠军在《现时代的群学》一书中借用严复在《群学肄言序》及《译余赘语》的观点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学”者,远非涵盖群学,仅仅是“治群学之涂术”,而群学,乃关涉人道之本[36]。
由上可知,我国的群医学与西方国家的“population medicine”虽然都是当代医学的新发展,但我国的群医学应该具有中国特色。创新中国特色群医学的三大体系,需要把握历史、现实和理论三大逻辑,通过医学教育、医学实践与医学理论的互动探索,通过学理传承、社会联系、知识系统、研究方法和学术平台的协同融汇,实现中国特色群医学三大体系创新建构,为全面深化医学教育改革、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