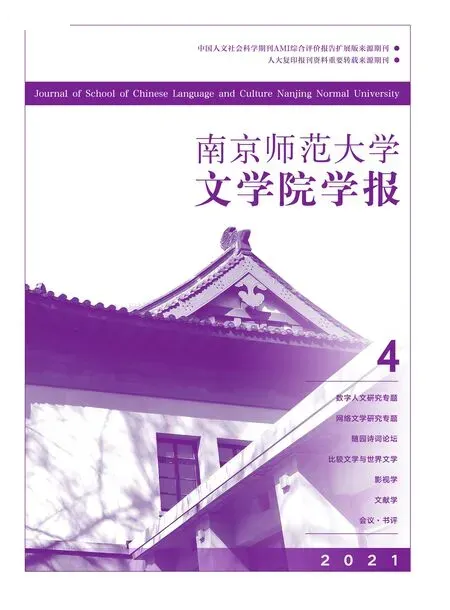泛娱乐时代玄幻电影的叙事深度问题
—— 以《悟空传》为例
2021-12-31姜悦周敏
姜 悦 周 敏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0;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从2005年前后“泛娱乐化”问题的凸显到2015年“泛娱乐”成为“互联网发展八大趋势之一”,一个泛娱乐的时代已经来临。对文化娱乐产业而言,这意味着要想迅速发展,就必须加快文化艺术的商品化步伐。为此,业界探索出了一条“打造以明星IP为核心”的泛娱乐发展战略,而IP 的实质则是“经过市场验证的用户的情感承载”,借此情感承载与情感共鸣最终推动粉丝经济。既然需要“经过市场验证”,那么依托和借鉴那些已经拥有粉丝号召力的作品、概念或者形象,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此背景下,《西游记》及其塑造的一系列经典人物形象,由于兼具民族传统性、人物性格多元性以及文学想象的丰富性,再加上各种改编和衍生作品的合力打造,近些年来一直是电影产业竞相追捧的大IP。从2013年《西游·降魔篇》开始,西游题材的电影一直热度不减,如《大闹天宫》(2014)、《大圣归来》(2015)、《孙悟空三打白骨精》(2016)、《悟空传》(2017)等,且尽皆斩获了相当惊人的票房成绩,其中有多部超过10亿元。这一成功,除了作为大IP的“西游”自身在电影文化产业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外,还应归因于它们几乎都采取了明星阵容、酷炫特效、高成本、大制作的方式来撬动粉丝经济。不过与巨额的票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它们普遍口碑偏低,豆瓣评分基本在5分左右(满分10分)。唯一叫好又叫座的是动画片《大圣归来》,它以扎实的故事情节以及对大圣在“丧”与“热血”之间扎挣的内心世界的合理呈现引发了观众追捧,一举成为票房高达9.56亿元的现象级国产动画电影。
上述“西游”电影都可归入近些年开始强势崛起的玄幻电影这一类型当中,并为玄幻电影的兴盛贡献了力量。至于如何理解玄幻电影中的玄幻,实际上可以参考对网络玄幻小说的定义。叶永烈曾经指出,玄幻小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始于黄易,他的小说是包含了道家玄学、修真成分的幻想小说,而广义的玄幻则是指一切脱离现实、科学范畴的幻想、玄想小说。[1]就广义而言,它又等同于“奇幻小说”或者西方语境下的Fantasy(幻想小说)。本文所说的玄幻电影更偏向于狭义的理解,指的是依托中国文化传统、以中国元素为主导的奇幻电影,且这类电影往往改编自中国传统的神仙志怪故事以及网络玄幻小说。上述“西游”电影就是如此,2018至2019年先后上映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山海经之伏魔正道》以及《诛仙1》等也属于该类型。
这一类型除了共享“玄幻”设定之外,也基本上遵循同样的商业片运营模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叫座不叫好(有些也并不叫座)也是“通病”:它们在豆瓣上的评分几乎无一例外的“惨不忍睹”。而之所以如此,最突出的毛病就是因叙事上的敷衍,造成叙事深度的不足。
所谓叙事深度,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在本文看来,这才是娱乐的根本。有“编剧教练”之称的美国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曾经说:
娱乐即是沉浸于故事的仪式之中,达到一种知识上和情感上令人满足的目的。对电影观众来说,娱乐即是这样一种仪式:坐在黑暗的影院之中,将注意力集中在银幕之上,来体验故事的意义以及与那一感悟相伴而生的强烈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情感刺激,并随着意义的加深而被带入一种情感的极度满足之中。[2](P5)
深度叙事就是能够提供意义与情感的双重满足,而玄幻电影却往往在游戏化、明星与特效等商业化元素交织的目眩神迷之中,相对忽视了这一叙事深度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解读电影《悟空传》,具体分析玄幻电影的叙事表现及其症候所在。之所以选它为对象,是因为它最为集中也最有张力地展现出了这一症候,可以作为衡量其它玄幻电影的一把尺子。《悟空传》有着多重互文性,既是西游题材的延伸,又改编自今何在的同名网络玄幻小说,后者一向以渲染苦苦追寻理想自我并不惜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悲壮氛围而为世纪初那一代青年网民所称道,正如作者所说:“西游就是一个很悲壮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群人在路上想寻找当年失去的理想的故事,而不是我们一些改编作品里面表现的那样,就是打打妖怪说说笑话那样一个平庸的故事。”[3]其特殊正在于原本可以拍出一部很有“情怀”和深度的作品,却最终变成了今何在所不愿看到的“打打妖怪说说笑话那样一个平庸的故事”。其中所引发的问题相当具有普遍性,是一种趋势的集中呈现。影片上映之后,围绕着原著与改编、商业片与文艺片等问题产生了较大的争议,这些讨论都涉及到玄幻电影共通的问题,这也为本文的讨论打开了空间。
一、从情怀型小说到商业化电影
还是先从《悟空传》原著说起,作品在2000年连载于新浪金庸客栈,一经发表,就“吸粉”无数,后被誉为“网络第一书”。从2001年首个纸质版发行,到2011年的《悟空传·完美纪念版》推出,先后共有8个版本,迄今累积销量达几百万册。在2018年相当权威性的“网络文学20年20部优秀作品”评选中,更以高票排第3位。可以说,《悟空传》逐渐奠定了其在网络文学上的经典地位,并确确实实做到了《悟空传·完美纪念版》封面广告语中所说,“影响了千万人青春”。它对一代人青春的影响,不在于如86版《西游记》电视剧那样为人们提供了师徒四人一路降妖除魔的新奇体验与正义战胜邪恶最终修成正果的快感,而是接续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将神魔妖怪打入凡尘,借用痞气与油滑消解掉一切假正经和伪崇高。同时又赋予师徒四人强烈的自我意识,让其以清醒的姿态挣扎于寻找与迷失之间,于是就出现了“大智若愚坚持理想的唐僧,深深掩藏感情与痛苦的猪八戒,迷失自我狂躁不安的沙僧,还有那只时狂时悲的精神分裂的猴子。”[4]这就让小说在精神气质上致敬了《大话西游》电影那种“在内核的伤痛无奈与喜剧性的情节细节间,形成了强大的张力”[5]的特色,从而也让小说笼罩在一种比较强烈的抒情氛围之中。由于这种特色恰好契合了世纪之交网络一代既自我意识张扬又感受到社会压力无处不在从而个体的无聊与孤独难以摆脱的情感结构,并为其赋型,《悟空传》不仅把自己写入时代与青年文化之中,又获得了一定的叙事深度。
为了营造这种抒情性,小说采用了相对意识流的表达方式,场景在五百年前与五百年后来回切换,用限制性的视角叙述故事,时常有大段独白,使主体情感充盈在对每一段故事的讲述之中,并用短句、警句以及文艺性腔调散落在各个角落,此外还适当使用无厘头做调味,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不过这种方式的缺点在于故事性比较松散,小说名为《悟空传》,但实际上线索比较多,悟空与阿瑶、紫霞,唐僧与曾是龙宫公主的白龙马、天蓬与阿月等,每一个线索都可以是独立的故事。这种由抒情为耦合方式所散发开来的文艺气息在被改编成电影时就难免遭遇转化的困难。这一困难在一开始就为制片方所预见,2017年7月13日影片上映当日,原著作者同时也是影片编剧的今何在就在豆瓣发文倾诉改编上的艰辛,其中就说到,“《悟空传》小说不是纯通俗,也不是纯文学,它介于两者之间,但它骨子里是文艺气质的。它的结构是完全跟着情绪走的,甚至不考虑情节”,所以“《悟空传》小说的情节要全拍完至少得六个小时,如果拼命赶情节一幕就几分钟,那电影就没法看了”,而“电影必须讲好一个故事。”[6]出于这样的考虑,电影做了较大的增删修改,如删掉了“太抢戏”的唐僧,增补了杨戬这一“形象鲜明的反派”作为男二号等等。作为制片方,他们对这些改动是比较满意的,在上映几天票房一片大好之际制片人刘闻洋就很是自信地说:“虽然剧情从原著的意识流改编成电影的三段式,也加了很多具体的故事情节,但我们保留了孙悟空不羁反叛的精神,所以它仍然是属于《悟空传》的。”[7]
但做了这些改编之后,电影就真把故事讲好了吗?很显然,影片整体上所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发育不良的故事,每一条线索都不够结实饱满,彼此松垮地交错在一起。所谓的“准文艺作品”只能妥协于视听艺术特点以及商业片故事逻辑的合力之下,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借口。商业片与叙事深度的强行对立导致了这一面的缺陷。
二、在故事与奇观之间暧昧
影片叙事深度的不足,最为突出地体现在故事讲得好与坏已经不再取决(或者说不再主要取决)于在线性演进上的逻辑轨迹完美不完美以及与之相起伏的演员的情绪表达充分不充分,而只是取决于某个瞬态是不是激发了感官上的愉悦(或者说刺激)。在影片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表现。第一,主要人物的登场与亮相几乎都带有一种强行耍帅扮酷的生硬,如紫霞(倪妮饰演)出场时那种纨绔式的腔调、如猴子一般摇头晃脑的姿态,再如悟空(彭于晏饰演)多次极其自恋地想要说出那句“从今以后一万年,你们都会记住这个名字”但无一不被打断与打脸等。这些强行搞笑,只会让人想起“中二病”,而非《大话西游》或者《悟空传》里的“无厘头”,因为后者所包含的反崇高、市井气以及小人物在自我解嘲与自我解构后的顽强和执着与影片(小说)的主题和风格是相一致的,而本片中的耍帅与搞笑则游离于情节之外。用这种碎片化的方式,目的不过是催动粉丝与明星之间的情感联系,属于明星与粉丝之间的隔空“尬聊”。第二,原著中那个压制个体自由、无形无质的天与地被具体化为运转不息的“天机仪”实体及其代言人和捍卫者天尊(俞飞鸿饰演),并将打破天机仪作为个体反抗的终极目标,看似具体和可视化了,但实际上是更加概念化和空洞化,使影片变成了如“王者荣耀”般的攻守游戏。绚烂的游戏成为主角,“人”反而淡化甚至消失了。第三,充分利用玄幻电影的玄幻色彩,在施法与斗法上将特效发挥到极致,把影片变成一场视觉盛宴,有时候甚至有为特效生造情节的嫌疑,如在悟空等人从“结界桥”掉落花果山凡人小村庄失去仙力后,非要安排一场用与现代枪炮相似的武器与“妖云”相斗的戏码,就是典型的强行增加视觉奇观。这三个特点,在其它玄幻电影中亦多有体现,如《诛仙1》开场的张小凡做梦与炒菜情节,不仅有强行诙谐的生硬,而且显得主次不分,相当破坏叙事的流畅度与整体感。观众更多地是在看明星,而不是在看演戏。此外,剧中的特效也常给人一种很强的游戏感,难以和主题有机相融。
做出这样的安排,自然不是编剧和导演的个人行为,而是体现出他们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娱乐的理解。随着泛娱乐时代的来临,人们(尤其是玄幻电影的主要受众青少年群体)对观影的娱乐期待正在发生可见的变化,体验好故事现在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观影期待,明星的一颦一笑以及各种影像奇观,都可以带动观众的情绪以及为影片买单的意愿。到影院通过3D乃至4D感受大制作特效,更是不少人的购票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故事本身反而变成一种附带,这自然又会影响到制片方对一部电影各元素的关注与投入比重。更何况,电影作为一种倚重现代科技的视听艺术与文化娱乐,它原本就更易受到非故事元素尤其是技术的影响,罗伯特·麦基在回顾电影发展时就曾不无辛辣地指出:“每隔十年左右,技术创新便能孵化出一批故事手法低劣的影片,其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开发奇观场景。”[2](P19)而对于玄幻电影,开发奇观原本就是理所当然。
因此,与打造故事相比,《悟空传》无疑在选角和特效上花了更多的心思。所以,对于故事,郭子健、刘闻洋、今何在等人只能不断地解释他们已经尽力,而对于特效和画面,他们则充满了信心。在一次访谈中,刘闻洋就曾对影片的特效制作方式——即把钱花在特效细节而非大场面渲染上,从而取得了既节省成本又画龙点睛的效果——进行了高度肯定,并认为这一经验“无法复制”。[8]然而,在故事上他们真的就尽力了吗?显然不是,尽管在某些方面也确实自有其新意(后文将作出分析),但基本上只是一种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尽力”,而这座“五指山”就是所谓的商业片叙事模式。在某种意义上,特效之所以能出奇效,正在于它与商业片的契合。
这种漫不经心的商业片叙事模式,只能让故事类型化与套路化,正如一位豆瓣网友所言,无外乎“彭于晏、余文乐和欧豪三位负责卖帅耍酷,倪妮、郑爽、俞飞鸿三位负责美艳和动人,而乔杉和杨迪则负责插科打诨卖笑点。”[9]采用如此配方,制片方本就没打算调出好口味,让多数人不反感,愿意进影院就已符合预期。只不过由于太想在商业上成功,火力不均之下,把故事烧得糊了一些。
三、碎片化叙事与当下青春文化
当然,之所以这样安排故事,除了上文所说的制作影片的重心有所转移之外,在更深层面上,还与娱乐业对青少年这一主要受众的理解以及对青春文化的判断有关。从这一层面来看,影片尽管在叙事上有所不足,但也与我们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青春文化保持着某种对话关系,影片也有着一些叙事上的亮点和形式上的创新之处。通过分析其叙事以及无论在原著还是在影片中都想努力表现的那种不羁反叛的精神,正可以看到其“症候性”以及潜藏其中的某种超越性。
2000年今何在在写作这本小说时,刚刚大学毕业不久。从象牙塔到社会,在这个过去与未来汇集于现在的转型时刻,如何在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关系构建自我就成为了青春主体必须要独自面对的关键问题,由此产生的迷惘、痛苦和创伤也往往是一个人告别青春完成成人礼所必经的过程。今何在的写作无疑受到这一生命体验的影响,所以他不是写理想的一往无前,没有像之后的网络小说那样为我们讲述一个一路打怪升级最终成神成圣的爽感故事,而是看破了理想的脆弱易碎后,仍留恋其七彩祥云的光环。他要用个体的反抗去捍卫理想,同时又通过反抗的徒劳把理想处理成青春旧影与青春无悔。如此的“成长”,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或可解读为个体对外部世界的适应,解读为纯洁心灵对‘丛林法则’的服膺,……前提正是对既有秩序的认可。”[10]这也意味着青春世界开始逐渐离我们远去,成年人的世界已经不可抗拒的到来。
而电影《悟空传》则有意让自己显得更为稚嫩一些,如果说小说展示的是成人礼的过程,那么电影则是在做成人礼的准备。电影从天机塾开场,有意把故事限定在青春校园的框架之内,而之后的花果山小山村降妖之旅,也更像是一场由天尊校长精心安排的郊游与试炼,连500年前的“大闹天宫”(所谓“天妖之战”)也强行缩短为300年前……一切都在提醒观众它更年少,所以刘闻洋才只会从“不羁反叛”来理解电影与原著的内在一致性。但如此的不羁反叛更像是青春期的“叛逆”。尽管影片也尝试突破,让青春的叛逆与成长变得稍微厚重一些。
这些突破是影片除了特效之外最为人所称道的地方,其在叙事上的具体表现是,它借菩提老祖之口,对孙悟空做了一次“真正”的“唤醒”:悟空终于明白了,原来“感到无能为力”才是自己成长与觉醒的先决条件,同时“这一世走过的路,遇到的人,放不下的这一切”才是自己足以战胜天庭的力量源泉和武器,因为这种“无法割舍”的情感性力量才是天庭的真正“他者”和禁忌。此外,电影又通过视觉语言以及借助特效的方式,把悟空的成长“意象化”为金箍棒的最终定型。如果说刚出场时金箍棒还只是一根虽可像岩浆一样燃烧但威力有限的黑铁棍,那么到结尾处随着阿紫和天蓬的死去、阿紫头上的金箍化成绕在铁棒两头的花纹以及从二人消散的身体上所衍生的能量凝聚为铁棒的光泽,金箍棒则彻底完成“变身”。[11]这种发生金箍棒上的进化,实际上就是将“走过的路,遇到的人,放不下的一切”注入其中并赋予其灵魂的结果。这既是一次对特效的有效使用,又是一次将目光从过于关注自我掉转到他人、伙伴和“类”上的有益尝试,因此那个一直模糊空洞的主体也得到了一丝凝实。所以当悟空对妖云说“你我都是妖,带我飞上天吧”,是要比影片结尾用文字的形式强行植入原著的金句“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更令人感动。
但这不过是碎片化的片段,并不与影片构成有机整体。当金箍棒获得灵魂时,更多的人则是功能性的存在,像游戏世界里的NPC(即由电脑程序制造的虚拟人物)。当悟空说“从今以后一万年你们都会记住我的名字”、当阿月对天蓬说“无论过了多少年,我都记得你”,实际的情形却是如200年后重生的阿月重逢天蓬时所说,“过去真的那么重要吗?对我来说,和你在一起的这几天,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所谓过去或者未来都是无所谓的,“活在此刻”就好。因此所谓反抗也不过是制造当下爽感的一种游戏,因此它可以不断重启,永远在此刻。结尾处当被杨戬告知“就算毁了天机仪,也改变不了这一切”时,悟空说出了今何在的名句,“我来过,我战斗过,我不在乎结局”,然后以背影对着杨戬又回头补充了一句“下次见面时,我们都拼尽全力吧”。这就不再是对青春一去不复还的缅怀,也非西西弗斯式的反抗绝望,而只能是对“再来一局”的新期待。一切都游戏化了,意义于是也就自行消解,或许玩游戏本身就是意义吧。
四、结语
如果说电影《大话西游》、小说《悟空传》都因契合了所属时期的青年文化特点与精神并为其赋形,而把自己推向了某种意义上的“经典”地位,那么作为玄幻电影的《悟空传》,尽管它取得了票房上的成功,也可看作泛娱乐时代的代表,却明显无法被经典化。影片尽管在选角和特效以及一些细节处理上特别用心,但并不能整体提升艺术水准,它在叙事上的套路化、碎片化以及强行的四处缝补与拼贴,给人一种以明星代替人物、以奇观代替叙事之感。这些特点则几乎是当下玄幻影片的共通问题,玄幻甚至成为粗制滥造的代名词。由此而造成的空心化、游戏化以及低幼化,实在难以用“后现代”自圆其说。作为中国后现代电影代表作的《大话西游》于2017年重映时,十多年的时光未能减损其魅力,仍旧斩获了1.8亿的票房,而再过十几年《悟空传》及其它玄幻电影会成为当下青年观影者的青春回忆吗?
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以电视为例,指出了“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泛娱乐化”的特点[12]。近些年泛娱乐化趋势越发明显,文化娱乐业也抓住了这样的契机,进行了以IP运营为核心的产业升级,使产业规模得到了爆炸式增长。但在此成绩的背后,波兹曼所担忧的由电子媒介的普及所引发的负面影响——即传播者将关注的重点从如何担起各自领域的职责移向了如何使自己更加“上镜”,而受众越来越不愿做抽象的思考,只追求能让人产生愉悦的外在形象——也在急速扩大,这在以青年群体为主要目标受众的玄幻电影中表现尤其明显。在此背景下,如何兼顾商业片和好片,真正做到“内容为王”?通过分析《悟空传》所呈现的难题和可能,确实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思考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