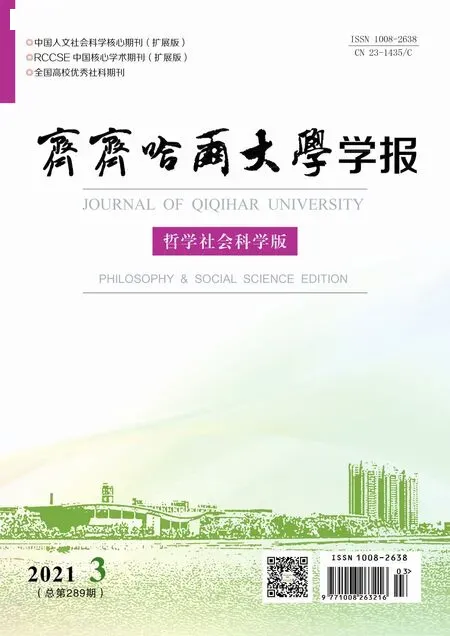试论过程性信息的本质
——以(2018)最高法行申265号裁定为起点
2021-12-31沈开举胡蝶飞
沈开举,胡蝶飞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内部性信息、过程性信息、行政执法案卷排除在“应当公开”之列。《条例》修改之前,过程性信息是什么以及能否公开的问题,只在国办发(2010)5号文件(以下简称《意见》)以及各地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中体现。实务中,以河南省为例,在2019年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表中显示,以属于过程性信息为由不予公开的有167件;以属于内部性信息为由不予公开的有226件。[1]即使修改后的《条例》有了相对清晰的界定,但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过程性信息仍然没有统一,说理规范也不尽相同。本文以(2018)最高法行申265号裁定(以下简称宋曹案)入手,纵向分析法院将信息公开申请认定为过程性信息的论证说理以及过程性信息的本质。
一、案情简介及裁判要旨
宋某、曹某因本村土地征收之事,分别向区政府邮寄申请,请求公开某地产公司与区政府签订的委托征地协议。区政府分别作出被诉答复书表示:宋某、曹某要求公开的委托征地协议与其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而且该信息属于内部管理信息,故不予提供。二人不服,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均以涉案“委托征地协议”为内部性信息、过程性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以及二人无法证明该协议与其生活、生产和科研有关,驳回二人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判断当事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否属于内部管理信息或者过程性信息的流程,不能仅以该信息符合内部管理信息或者过程性信息的某些特征,就认定为是属于可以不公开的内部性信息或者过程性信息,如该信息是行政机关内部工作安排中产生,仅在内部流转,没有向外部送达。被征地村民的社保方案就是依据本案的征地协议而制定,并非行政机关内部事务的信息,也并非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已经影响到相关人员的实际权利义务,属于《条例》规定的应当公开的信息。
二、“驳回”判决的几个常见问题
由于没有规定统一的认定方式,即使《条例》新增了“4+1”的限定,但是“过程性”的特征和属性没有改变,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况:行政机关认定涉案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而不予公开,但法院认为不属于过程性信息反而应当公开。产生的疑问是:是否只要是应当公开的,就一定不是过程性信息?什么情况下才是过程性信息?笔者在无讼案例网上挑选出新《条例》实施前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共9件,论证行政机关与法院在认定所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行政机关与法院认定不一
一种情况是,法院与行政机关都否认过程性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在蒋某诉某市自然资源局案((2019)桂05行终11号判决)中,蒋某申请公开《X地规划设计要点的函》,行政机关认为该函属于过程性信息且不属于政府信息;法院认为该函属于内部过程性信息,法院模糊处理内部性信息与过程性信息的区别,或者说将二者合为一种东西,有待考究。另一种是,行政机关认为是过程性信息,但法院认为既非过程性信息、也非内部性信息。如某城市综合管理局与某公司信息公开案((2019)粤71行终284号判决)中,涉案《工作方案》被被诉机关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一审法院采纳过程终结无过程说,认为该方案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否定过程性信息属性,承认政府信息属性。二审法院认为,涉案《工作方案》是为推进城市管理工作而制定,规定了工作措施、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有相关附件等,因此既不属于过程性信息,亦不属于内部管理信息。
(二)不区分或混淆内部性信息与过程性信息
由于《意见》并未清晰界定过程性信息,所以适用的时候也全凭法官的理解。如宋曹案中,两审法院直接将涉案协议的属性界定为“内部性信息、过程性信息”。再如,李某诉镇政府案((2019)京02行终1943号判决)中,行政机关给出类似“关于您申请的‘XX会议纪要’信息,会议纪要是行政机关的内部公文,具有过程性和决策性的特点。根据X条文的规定,告知您该申请事项不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这样的答复,该答复将涉案会议纪要界定为内部公文。令人不解的是,若根据《党政机关会议纪要处理条例》规定,内部公文具有“过程性和决策性”的特点,不具有可公开性。但在行政诉讼中,对相对人有权利义务实际影响的会议纪要具有可诉性,那么同理,含决策性的“内部公文”也应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同样的情况在(2020)卾01行终560号判决中也能体现。刘某申请公开《X会议纪要》,行政机关以该会议纪要属于《条例》16条中的“讨论信息”,不予公开;两审法院专门搬出“纪要”的特征和属性,赞同其“讨论信息”的身份。以上两个案例的问题在于,法院并未审查涉案信息的实质,将内部公文定义为过程性信息,也未判断涉案信息是否对相对人有权利义务的实际影响,直接不予公开的过程是不可取的。
还有互相混淆的情形。如(2020)辽02行终384号判决中,王某申请公开X年度绩效工资的相关信息,卫健委以《意见》第2条的内部性信息以及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一审被告败诉;市卫健委在上诉过程中自称混淆了两种信息的属性,称涉案信息为内部管理信息。二审法院支持该观点,以内部管理信息可以不公开为由支持了市卫健委的上诉请求。
(三)论证过程简单,甚至模糊不清
我国裁判说理往往是按照“三段论”式进行的,信息公开案件又多审查行政机关的程序合法性;被告只要提供程序合法的证据即可。而文书内容的丰富性都要求机关实质审查涉案信息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属于何种过程性信息。在(2020)京行终3397号裁定中,市政府《答复书》的主要内容为“经查,你们所申请信息为过程性信息。根据…的规定,现告知你们所申请的信息不予公开。”多数情况下,法院会将《条例》第16条、《意见》第2条或者把当地的信息公开规定的相关规定列明,再点明过程性信息并非政府信息公开和行政诉讼调整的范围,故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里就比较矛盾,政府信息本就有不予公开的范围,如若否定不予公开的过程性信息的性质,明显有违政府信息公开的本质。再如,(2020)津01行终216号判决中,卫健委以《条例》34条第4款拒绝公开;一审法院以《条例》36条第3款驳回一审请求。二审法院将过程性信息纳入,认为涉案《通知》属于过程性信息,但未明确属于何种类型,引申法条是《条例》第33条。
(四)未说明申请的信息属于哪一种过程性信息
过程性信息种类繁多,法条只具有概括性,故不说明到底属于哪种过程性信息的案件占多数。比如,杨苏二人诉区住建局案中((2019)浙10行终325号判决),杨苏二人申请公开某被征收房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被诉行政机关及两审法院都将之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但是均未说理论证涉案风险评估报告属于《条例》16条中的哪一种。但(2019)卾01行终683号判决中,张某申请公开批前公示阶段规划方案修改听证会的全部内容,被诉机关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但二审法院认为绝对符合16条的四类信息才能认定为过程性信息。此类案件数量较少。
综上,行政机关与法院在处理过程性信息案件上都发挥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带着对过程性信息的理解审查案件。法院在审理过程性信息案件时,几乎都把行政决定作出之前的政府信息列为过程性信息,而其能否公开,取决于不同法院对过程性信息的理解。本部分的9个案件中,也只有一个案件指明了涉案信息需要同16条的4种严格对应,以及指出能否对应上。涉及过程性信息的信息公开案件,大部分还是以程序审查为主的路子,这样来说,《条例》新增的16条凸显的作用并不大。
三、过程性信息的本质
过程性信息到底是什么?这是判断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能否公开的关键,本部分接下来从是否属于政府信息、“过程性”代表了什么,以及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的目的是什么三点入手,推演出过程性信息的本质。
(一)是否属于政府信息
立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对于过程性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这一问题均有不同见解。《条例》16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表明,过程性信息是由行政机关制作或获取,为了发挥行政职能而产生,属于政府信息。《意见》第2条将过程性信息排除于政府信息之外,又由于《条例》的修改,将生产、生活以及科研活动的规定删除,也算是间接为过程性信息的政府信息身份正名了。
有学者认为,过程性信息属于政府信息,且具有过程性和行政性两大特点,[2]这里的过程性和行政性比较好理解,前文也有提到过。杨小军教授认为,满足制作主体、产生过程、方式,以及存在的形式这样的构成要素,即构成根据《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概念;过程性信息符合政府信息的组成要素,因此属于政府信息。[3]肖卫兵教授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过程性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也有待讨论;而实践中对于过程性信息判断不一、混乱,首先需要明确过程性信息的属性。[4]
《条例》修改前的实务中,法院引用旧《条例》第2条以及《意见》第2条,以行政相对人申请的并非政府信息,认定行政机关不予公开是合法的案件有很多。笔者认为,不考虑过程性信息是否应该公开的问题,如政府信息的含义所明,过程性信息符合行政机关为主体、为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为目的、以一定的形式制作或者保存的要素,应当属于政府信息。
(二)“过程性”指什么
“过程性”一词表面上限定了该类信息的范围。有学者认为,政府信息并非行政行为本身,过程性信息的制作或获取实质上不等于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过程。[5]《意见》第2条第2款的“处于…中”,以及多地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正在…中”等的类似表述表明了,该类信息是为了行政行为的作成而产生,时间节点限定在“现在进行时”,行政行为处于不成熟、不确定的阶段,比如为了作成行政行为而产生的会议纪要、行政批复、意见函等等,此类信息叫做过程性信息。同时,《条例》从字面上也更倾向于强调时间节点。[6]同样,最高法在宋曹案中认为,判断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不应当只看信息未向外部送达生效,就直接认定其“过程性”仍有留存,而应当看是否对行政相对人有权利义务的实际性影响及后果。
但是行政行为作成后、执行中甚至执行完毕后,过程性属性还在不在,这就产生了“过程终结无过程”一说。在(2020)卾01行终634号判决案中,涉案征收材料即使处于执行中,法院仍认定其为过程性信息。相反,杨小军教授认为,只要行政行为作成后或者处于执行中甚至执行完毕,该类信息自然而然就不再处于过程中,也即不再是过程性信息。[3]部分基层法院也持该种态度,在(2019)渝05行初397号判决中,市政府以涉案请示属于过程性信息为由不予公开,但是法院认为,由于该请示已经得到批复并且实施,即使该信息是在行政决定作成之前形成的,但“过程性”特征已消失,不再属于过程性信息。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过程性信息虽然形成于行政决定作出之前,是作出行政行为的环,但该类信息不因为“过程”终结而改变自身属性,也不能因为它们可以公开而否定其是过程性信息的属性。因此有学者认为,判断“过程性”应当关注信息的自身状态,[7]即看是否对外产生效力,如果纯对内,则是内部行政行为;如若尚未对外产生效力,则可以用来判定“过程性”。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也并没有否认可公开的过程性信息的过程性属性。
(三)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的目的是什么
信息公开是知情权的保障。[8]从有效利用行政与司法资源的角度考虑,所申请的政府信息都是应当能“为己所用”的。过程性信息作为法定豁免公开的一项,不予公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其在行政行为作出前达不到“行政成熟”标准,这算是过程性信息的特性之一。宋曹案中,最高法认为宋曹二人虽然不是涉案协议的直接当事人,但是协议的内容包含了被征地农民社保方案的制定,宋曹二人是被征地农民,协议内容当然允许被征地农民知晓,便不属于过程性信息。这一点与上文学者观点和法院观点也有不一致之处。
过程性信息一般应当具有非正式性、不完整性的特征,且不具有使用价值。不公开这类信息表明,它们不应当对外有权利义务的实质影响,与行政相对人或者相关人的特殊需求也无关。但是若按照行政决定作成前的政府信息均为过程性信息的话,过程性信息并非都不对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比如,征收补偿协议一般都是在征收决定作出之前签订的,必然会增加或减少被征收人的实际权利义务;行政决定根据某批复作出的。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虽是国际通例,[9][10]在英国属于绝对豁免之列;美国将过程性信息称为“备忘录”,可以拒绝公开。会议纪要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正式性的要求,但内容上并不一定都符合不完整性或者不准确性的特征。[11]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将行政决定作出前产生的会议纪要均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也是不严谨的。
综上,过程性信息是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作成之前,为促成该行政决定所产生的对外不发生效力的政府信息;其实质是政府信息的一类,且不因行政行为所处的阶段而改变其“过程性”的属性。新《条例》首次对“过程性信息”的范围作了明面上的规定,将之按照“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4+1”形式定义。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这四种文件都符合“过程性”特征;“等”字依据同义解释,也应当与上述四种文件属于同类。那么,实践中保存政府信息的形态多种多样,如何界定“等”字所涵盖的政府信息,将是一个庞大而重要的任务,还需要行政机关和法院实质审查涉案信息是否符合、以及符合到哪种程度的“过程性信息”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