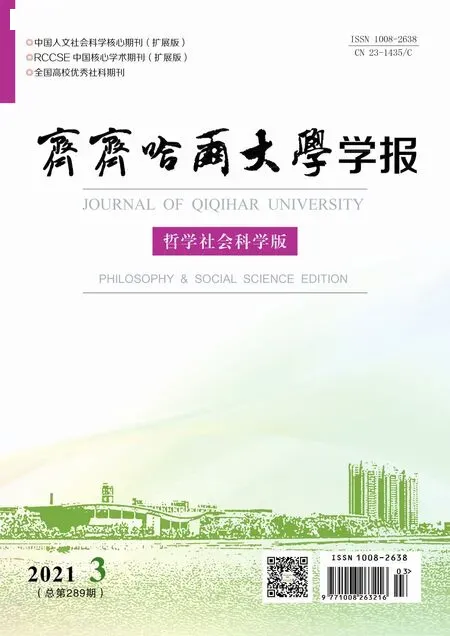论汉代宫廷鼓吹乐专属性质的演变与权力建构
2021-12-31谢芳
谢 芳
(莆田学院 音乐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汉代鼓吹乐的权力问题,相关讨论并不多。从研究内容看,研究者主要依据历代文献,对汉代鼓吹的渊源、类型、曲辞、制度、雅俗归属等方面进行考证与区辨。此类梳理史实的研究方式,对于认识汉代鼓吹是相当必要而且不可逾越的,但进入宫廷并广泛用于各类重要政治活动的汉代鼓吹,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和文化意义,如通过“鼓吹”物件建构君臣关系的“鼓吹赏赐”活动;代表皇帝形象与权力的“黄门”鼓吹等,其特殊的功能与性质却没有在研究中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西汉时期的鼓吹赏赐与“鼓吹”、“黄门鼓吹”的使用权
据载,西汉年间赏赐鼓吹仅两次,都是汉武帝之举。据载,汉武帝南平百越,置交址等七郡,于交州设刺史。后因交州地处边远,且“山越不宾”,为了“加威重”,便令刺史“假节”,且“七郡皆加鼓吹”,[1]2562交址等七郡的持节刺史及其“加鼓吹”,营造出犹如皇帝亲临一般的实际效果。汉武帝灭朝鲜后,在此设置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并以高句骊为县,“赐鼓吹、伎人”。[2]815这里可看出,汉武帝的鼓吹赏赐,意在治理边疆异族。汉武帝之前,南越、朝鲜只是汉朝的“藩臣”、“外臣”,他们与汉朝之间仅有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实际情况却是,尽管南越与朝鲜对大汉王朝俯首称“臣”,他们作为“臣”的地位和享有的权力远高于同级别的汉朝诸侯王。[3]126-127汉武帝即位后,在武力征伐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对南越、朝鲜等藩属地区的郡县统治,使此处转变为直接接受西汉王朝统治的臣民。[4]194.3126南越、朝鲜变为郡县后,汉武帝在此设置郡县官长与刺史。对于这些新建立的“以州边远,山越不宾”的边远辖区,如何强化皇权在此地的有效统治?武帝一朝实行的是“加(赐)鼓吹”的管理手段。西汉时期的“鼓吹”,是天子专属之物;作为一种符号,它象征着皇权,象征着皇帝本人。将“鼓吹”置于远离中原的偏远辖区,可视为是统治者试图利用此一象征符号实现“加威重”之治理目的的具体措施。
由此可见,西汉鼓吹赏赐并非皇帝对个人的赏赐,而是针对已被“内地化”的异族。在他们日常生活的边远辖区,象征皇权、象征天子的“鼓吹”符号,时刻向他们传递着一种讯息,强化着他们与大汉皇帝之间的臣属关系。
西汉将“鼓吹”塑造为天子专属之物的具体举措有二:其一,天子对鼓吹的频繁使用;其二,朝廷对鼓吹严格管控,对擅用鼓吹的大臣,一律严惩不怠。
据文献记载,西汉诸帝中数汉武帝的“鼓吹”使用频率最高。《三辅黄图》关于汉武帝大肆修建昆明池的介绍文字中有一段池中宴乐景象的描述。池中设一龙首船,武帝常令宫女、乐人泛舟池中,舟上“张凤盖,建华旗”,还有“棹歌”杂“鼓吹”的音乐表演,武帝本人则亲临豫章观观赏。[5]249.252这里提到,汉武帝在昆明池设宴并安排“鼓吹”表演是常有之事。之所以选择昆明池频繁表演鼓吹,主要归因于此处的独特景致。昆明池,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修建,规模非常宏大。据载,该池开凿之初是为训练水军、练习水战以征讨昆明国,故取“昆明”之名。因其独特、壮阔的湖光美景,也成为帝王喜爱的游乐之所。[6]8-12池中的壮阔美景,配以激越震天的鼓吹乐,营造出宏大的“声”、“景”,堪称绝佳,正如东汉班固《西都赋》关于汉武帝时期昆明池中“鼓吹”演奏场景与效果的如下描绘:“激越厉天,鸟群翔,鱼窥渊”。[4]148
西汉“黄门鼓吹”文献记载不多。据《西京杂记》载,甘泉郊祀大驾卤簿中设有黄门前部鼓吹,共十三人,乘坐四马之驾。[7]218-220结合甘泉、汾阴郊祀始兴于汉武帝时期,我们据此推知,“黄门鼓吹”作为全新的音乐表演形式,应始于汉武帝时期,且汉武帝仅将其用于郊祀出行的卤簿仪仗中。此外,史丹向汉元帝谏言时曾提及黄门鼓吹乐人,“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服虔注曰:“(陈、李)二人皆黄门鼓吹也。”[4]3376-3377这里说,陈惠与李微都出自黄门,且是演奏“丝竹鼓鼙”的高手。由此可知,西汉时期的黄门鼓吹,不仅用于郊祀卤簿仪仗,也用于帝王的怡情悦性享乐活动。但无论如何使用,其“黄门”标签,已向世人昭告:此乃皇帝专属之物。
“黄门”,原初义是指“禁门”,即“宫禁之中”。杜佑《通典·职官三》:“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8]549“禁中”,是指宫内的禁区,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省中”。早有学者指出,汉代宫中设有禁区“省中”,“省中”应有围墙,并以门闼管制出入,和宫中其他地区形成区隔,由此形成宫外、宫中、省中三重空间。“黄门”作为“禁中”之门,即区隔皇帝“公”、“私”活动空间的门,将已是禁区的“省中”区域划分为“省中”外围与“省中”内部的“禁中”两个部分。前者是皇帝日常处理政务及商议机密政事、召见个别官员的地方,后者是皇帝与亲人、宠臣聚会的私人空间。由此可知,作为皇帝的私人空间,“非侍御者不得入”。[9]1-3汉代典籍中,“黄门”不仅指称皇帝“燕居”之地的禁门或禁内,同时也指称设于禁门附近的官署以及天子近侍官宦,[10]1此类官吏与皇帝的亲近关系非同一般。[4]199、2217由此可知,由“黄门”乐人演奏的“黄门鼓吹”,是专供皇帝使用的表演形式与音乐组织形式。
“黄门鼓吹”的专属性建立,一方面依赖于皇帝本人的频繁使用,另一方面则需依赖于禁止他人使用的惩戒之举。西汉时期,曾出现两例因擅用鼓吹遭严惩的事件。一是汉昭帝时期的韩延寿,二是汉废帝刘贺。《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在东郡时,擅自“建幢棨,植羽葆”,并在仪仗中设“鼓车歌车”,“鼓车歌车”,正是天子郊驾时用于搭载鼓吹乐人的车。[4]3214-3215又《汉书·霍光传》载,昌邑王刘贺曾召令泰壹、宗庙乐人,以“鼓吹歌舞”、“并奏众乐”。[4]2220由韩延寿的定罪之辞与刘贺的弹劾奏章中,前者的擅用鼓吹被定为僭位越分之举,后者的擅用鼓吹被视为荒淫无度之举。
西汉时期关于“鼓吹”乐使用权的严格管控,并非始于建汉之初。据《汉书·叙传》记载,高后、惠帝时,班壹曾“避地于楼烦”,在“与民无禁”的政策下“以财雄边”,以“出入弋猎”设“旌旗鼓吹”的方式雄霸边疆。[10]4197-4198班壹,楚国王室后裔,趁秦末汉初四处战乱之际,远避至清净地楼烦,在此安顿修整,大力加强物资储备,“以财雄边”,以图成为“边地之雄豪”。熟谙礼乐之道的班壹,称雄一方的途径与策略也颇为讲究,他看中了先秦“恺乐”对于建威造势的独特功效,于是“出入弋猎”之途,都配备大量“旌旗鼓吹”。班壹以旌旗导从“鼓吹奏乐”彰显身份地位与财势并雄霸边疆的做法,显然是僭越体制、趁乱而目无王法的做法。无疑,这种情况仅存在于“国家不设衣服车骑之禁”、朝廷尚未出台严格、完整的车服制度的特殊时期才得以存在。
二、东汉时期鼓吹赏赐与“鼓吹”、“黄门鼓吹”使用权的变化
至东汉,鼓吹赏赐发生了明显变化。相比西汉,东汉鼓吹赏赐的对象、目的、功能更加复杂。赏赐的具体情况有如下四种:第一,异国藩臣。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秋,南匈奴单于遣子入侍汉朝廷,朝廷沿袭西汉旧例,给予丰厚赏赐,赏赐物件中就有“乐器鼓车”;[2]2943第二,分封的诸侯王。《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楚王刘英因造作谶纬等物以谋反罪名被废黜时,汉明帝以亲亲不忍杀之,将其迁徙至丹阳泾县,即便是被贬迁徙,诸侯王的气势犹存,仍设仪仗鼓吹以从行。[2]1429由此事件可知,楚王刘英身为诸侯王时,曾受赐鼓吹乐。《后汉书·梁节王畅传》载,永元五年(公元93年),梁王刘畅的从官卞忌在祠祭求福时有谄媚忤逆之辞,刘畅因此事被弹劾后遭削县惩戒,曾试图通过“归还其余所食四县”及诸多受赐之物以表深自刻责之心,刘畅拟归还的受赐物件中也有鼓吹乐。[2]1676《后汉书·济南安王康传》载,济南简王刘错,相中其父刘康的鼓吹妓女宋闰,令张尊前去招来却未得逞,一怒之下,“以剑刺杀尊”[2]1432由此可知,身为诸侯王的刘康,也曾受赐鼓吹乐。第三,军事将领。《后汉书·班超传》载,建初年间,乌孙国蠢蠢欲动,班超谏言遣使者前去招慰,于是,汉章帝拜班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2]1577在此过程中,班超身为军事将领,其受赐鼓吹的原因有二,一是军功奖励,二是作为大汉帝国宣扬国威与皇权的象征符号威慑异域。据《后汉书·百官志》载,东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皆有官骑三十人与鼓吹二十人(一部)的军容,此乃常制。受赐鼓吹,有如下规定,“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2]3564第四,大臣死后赠鼓吹。自东汉以来,皇帝赠给鼓吹的内容,相比前朝而言还多了一项,“及葬,给鼓吹”,位尊大者给赐鼓吹导从。如光武年间的耿弇,终其一生驰聘沙场,并立下赫赫战功,死后被给赐“朱棺玉衣”并“假鼓吹”,还有五营骑士三百余人的送葬队伍。”[2]718再如灵帝时期的杨赐,中平二年(185)去世,灵帝服丧服并三天不临朝,特令侍御史持节送葬,送葬队伍中设“前后部鼓吹”。[2]1785
由此可知,东汉的鼓吹赏赐与西汉明显不同。首先,就赏赐对象而言。西汉时期少有的鼓吹赏赐,也只是赐予区域,而非个人;东汉赏赐对象都是个人,既有异国归附的君主,也有刘氏诸侯王,还有军事将领。其次,就赏赐目的而言。西汉赏赐鼓吹是为了镇抚边地,加强区域统治。至东汉,赏赐目的相对复杂。对于南匈奴而言,赏赐鼓吹是大汉王朝削弱、瓦解匈奴的政治举措。[11]70对军事将领而言,赐鼓吹是委以军事重任时通过“鼓吹”营造声势,如“假(班超)鼓吹”;耿赐与杨赐,作为东汉受赐鼓吹的两位大臣,他们既非王公也非重臣,而是驰聘疆场的将军,此类鼓吹赏赐,藉由表彰生前军功显赫的死者以激励生者;而楚王刘英、梁节王刘畅、济南安王刘康等刘姓宗室的鼓吹赏赐或罚没,表现的则是皇帝作为刘氏大宗之位所拥有的收族之权。
结合东汉鼓吹赏赐情况可知,“鼓吹”的使用权已不再专属皇帝个人。在赏赐的过程中,诸侯王、军事将领、归附的异国藩王,都拥有“鼓吹”的使用权;即便是生前驰聘疆场的已故大臣,在崇尚“谓死如生”与“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等观念的汉代人眼中,也能使用鼓吹。
随着“鼓吹”使用权的下移,东汉皇帝的鼓吹使用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皇帝主持的各类重要礼仪活动中,不再出现“鼓吹”,而一律采用“黄门鼓吹”。天子举行正旦朝贺大典,典礼结束之前有“小黄门吹三通”之仪;[2]3131册封皇后大典,皇后称臣礼毕,也有“黄门鼓吹三通”之仪;[2]3123天子郊祀、田猎出行的乘舆法驾中,“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吹”;[2]3649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前往蚕宫行亲桑礼,所乘舆驾中也有黄门鼓吹;[2]3110永平七年(公元64年),阴太后驾崩,汉明帝行举哀发丧礼,发丧前有“黄门鼓吹三通”之仪;[2]3151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扶馀国王朝贡京都,汉顺帝特意安排黄门鼓吹与角抵戏以飨遣之。[2]2810上述明确记载东汉“黄门鼓吹”使用场景的文献,呈现出一个明显特征:所有使用“黄门鼓吹”的礼仪活动,无一例外都是皇帝(后)主持。从天子受大朝贺、天子册后、天子举哀发丧、天子遣送前来朝贡的藩王,到天子郊祀与田猎的出行卤簿仪仗,无论是宫内还是宫外,“黄门鼓吹”出现的所有活动现场,主角都是至尊天子。即使是皇后亲桑出行卤簿中的“黄门鼓吹”,也是为了强化皇后在后宫中的“至尊”之位。
两汉期间“黄门鼓吹”的皇帝专用属性从未变化,“鼓吹”则逐渐失去了皇帝专用的属性。随着鼓吹赏赐的变化,臣下开始拥有“鼓吹”使用权,西汉“鼓吹”的皇帝专属性质不再。与此同时,在各类皇帝亲自主持的国家重要礼仪活动中,开始频繁采用“黄门鼓吹”而不再用“鼓吹”。
综上所述,汉代宫廷鼓吹用途十分广泛。作为宫廷音乐的主体,汉代鼓吹乐不可避免的开始了与王权、与政权统治的相互勾连,参与到权力塑造与身份建构的政治运作之中。西汉中期,随着车服制度的逐渐完善,鼓吹乐成为天子的专属物件:皇帝频繁使用“鼓吹”的同时,严格控制和禁止臣下擅用“鼓吹”,有效强化了“鼓吹”的专属性质,塑造了“鼓吹”作为王权之象征的社会意义。对于象征王权的“鼓吹”符号,汉武帝可谓“物尽其用”:通过少有的“加鼓吹”、“赐鼓吹”等赏赐方式,将“鼓吹”用于统治新征服的藩邦异族,显耀国威的同时,重构君臣关系;通过昆明池的“鼓吹”宴乐,利用昆明池的辽阔无边与“鼓吹”乐的激越震天,营造出世间罕见的宏大“声”、“景”,向臣下炫耀大汉王朝的强大与大汉天子的至尊;通过郊祀卤簿仪仗设置“黄门鼓吹”,藉由浩浩荡荡的队伍与“天动地岋”的鼓吹乐,彰显帝王 “尊”、“威”之仪,使途中观者心生肃敬畏怯之心与臣服归属之心。
至东汉,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东汉诸帝调整了“鼓吹”以及“黄门鼓吹”的利用方式。一方面,鼓吹赏赐成为常用的统治手段,在加速匈奴的分化瓦解、加强军事斗争与军队建设以及奖惩刘姓宗室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鼓吹赏赐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鼓吹赏赐的增加,“鼓吹”使用权下移,极大削弱了“鼓吹”的皇帝专属性质。于是,皇帝在各类亲自主持的重要礼仪活动中频繁使用“黄门鼓吹”,试图用“黄门鼓吹”取代“鼓吹”,强调“黄门鼓吹”的帝王专属性,将其与臣僚使用的“鼓吹”区辨开来。在此过程中,“黄门鼓吹”与“鼓吹”它们不再只是音乐组织形式或表演内容的区别,而是权力与身份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