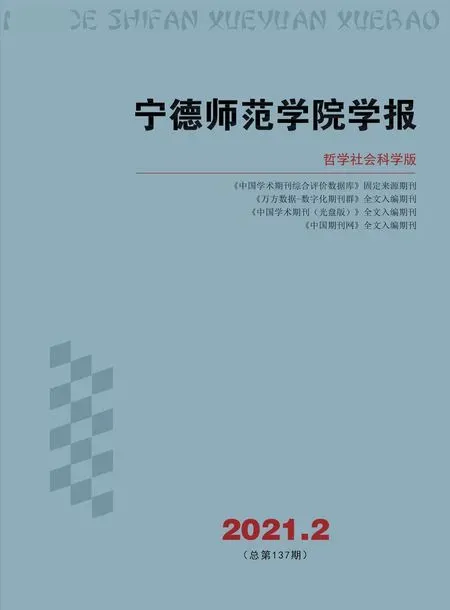家园意识:闽东诗群的生态美学立场
2021-12-31许陈颖
许陈颖
20世纪以来,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精神焦虑的加深,人们在获得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也普遍产生一种失去家园而无所依从的精神茫然。海德格尔在这个背景之下,第一次提出“家园意识”这个概念。他指出:“在这里,家园意指这样一个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惟在其中才能‘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已要素中顾在。”[1]中国生态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曾繁仁,在融合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当代存在论的基础上,用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剔除其唯心与不合理的成份,打破了主客二分的审美传统,并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归乡意识”和“宜居”等理论相融合,在恢复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审美关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家园意识”的内涵。他指出“家园意识在表层上有维护人类生存家园、保护环境之意。”“在深层次上更加意味着人的本真存在的回归与解放,即人要通过悬搁与超越之路,使心灵回到本真的存在与澄明之中。”[2]由此可见,“家园意识”不仅是对个体生存场所及所形成的文化认同的思考,更是对人与自然这对“元问题”的本源性追溯与回望。让万事万物回归自然本源,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也是对现代性损伤的修正。
福建闽东依山傍海,造就其独特的海洋文化。海上闽东的家园体验启蒙了诗人生态审美意识,形成以“自然”为出发点的“家园意识”。在现代化进程中,诗人们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家园意识”伴随着他们的精神联系和文化身份的变动逐渐内化为他们的精神视点,从而走向整体主义的生态美学立场。在大踏步向前的生活中诗人通过回望家园,以心灵家园的诗意构建实现精神上的返乡,抵达了深层次的“家园意识”。
一、海上闽东:“家园意识”的源发点
“自然环境与世界观密不可分。除非来自外来文化,世界观必定由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突出的部分建构而成。”[3]海上闽东作为诗人生命出发地,也是是诗人们初心的容纳场所。他们把目光投向海洋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确立“家园意识”的源发点。
(一)海上闽东的文化地理
闽东诗群兴起于上个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从50 后至90 后的每个代际都涌现出数位全国知名的优秀诗人。作为地域性的文化现象,其产生必然与地理文化相关。闽东的海洋是诗人笔下的重要题材,也构成闽东的地缘特色。但是,闽东的海洋又是与山相连,形成区别与其他海域的海洋文化,显示了这方水土独有的地域魅力。
1.开放性。福建闽东濒临太平洋,属于东南沿海地区。在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长期的相对作用中,闽东海域形成海岸线漫长(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县就在闽东霞浦)、300 多个岛屿棋布、良港众多的特点,并因此成为福建乃至中国东南沿海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比如闽东诗歌重镇霞浦,早在公元3 世纪中叶,孙吴政权在此地开设了造船工场“温麻船屯”,开通了沿海航线。辽阔的福宁湾成了闽东走向海洋的第一站。蕉城三都澳、福鼎沙埕、福安下岐、霞浦三沙等优良港口的存在,扩大了闽东对外的交流,开阔了当地民众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生命体验,使闽东具备了传统海洋文化的开放性、重商性、外向性等特征。
2.农耕性。闽东的海又是与山相连的。洞宫山、鹫峰山、太姥山、天湖山等几大山脉从不同方位环绕、贯穿闽东,形成陡峭、险峻的沿海多山的地形。复杂的地势条件影响了闽东陆路交通的便利,使闽东因为疏离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相对落后。海边的山民们择地而居发展农业,形成了闽东的另一种文化形态,农耕文化。地域文明是在人文地理相互交流、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一方面,海洋与农耕两种不同生活方式彼此影响、相互交汇,使闽东既保持着面向海洋的开放、冒险与创新,又吸纳了朝向土地的踏实、内敛与守正。另一方面,靠海吃海、靠山吃山的传统生存规律,使闽东人的人生观与自然观融会贯通,形成闽东原始的生态审美观:顺应自然。换言之,“自然”作为一种对世界的态度和生存感悟,始终是闽东“家园意识”出发点,也是一个制高点,对闽东的地域诗学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海上闽东的诗学传统
海上闽东作为闽东诗群繁衍生息之地,其“家园意识”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流淌在历朝历代的诗人笔端,他们笔下的诗歌始终与故乡的“海”相关。
1.悠久的“海洋诗”传统。闽东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从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到宋代谢翱、元末诗人张以宁,再到五四时期的“九叶派诗人”杜运燮,包括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宋代大诗人陆游等在闽东的游宦和讲学,彰显闽东悠久又深厚的人文传统,对闽东的诗学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朝历代的诗人们的笔锋集中指向了哺育家园的大海。唐代的陈蓬的《谶诗》说闽东之海是“东去无边海,西来万顷田。”[4]宋代谢邦彦笔下则是“十里湾环一浦烟”[5],清代张光孝的《咏官井》里说“四月群鳞取次来,罾艚对对一齐开。千帆蔽日天飞雾,万桨翻江地动雷。征鼓喧阗鱼藏发,灯光闪烁夜潮回。”[6]他们笔下的“海”是自然界中的海,既是地域疆界的标志,也散发着日常的烟火气,与民间生活形成相互交融的一体化形象,正是王一川先生所说的中国古典海的形象“中国古典‘海’是自我可以容纳和融入其中的平常之海。”[7]
2.当代繁荣的诗学景象。古朴的“家园意识”一直漫游到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到90 年代初,汇聚到闽东一批新时代的年轻诗人身上,形成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诗歌群体。四十多年来,闽东诗群从个体的闪光到群体的互动,形成了闽东当代诗歌的繁荣景象。个体频繁获奖,比如2018 年汤养宗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2020 年谢宜兴获得诗歌网“十佳诗人”,叶玉琳、刘伟雄多次获得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等。2019 年,诗刊社携手地方政府举办“青春回眸”,2020 年“青春诗会”再一次在闽东举办,引发众多学者对闽东海域上生长的诗歌与梦想进行关注。
二、走向整体主义的诗学反思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之下发生了快速变化,多元并存的审美格局构成新的文化语境。闽东诗学的家园体验也处于历史经验与当下经验的相互审视与调适中。诗人立足于家园体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质疑与反思,从而走向整体主义的生态美学立场。
(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
“人类中心主义”思潮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强调人类的能力高于自然,并带来了科技与理性的巨大飞跃,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但是,随着传统意义上的贫穷与苦难被现代工业文明征服,人们发现期待中的幸福与快乐并没有完全来到。面对家园环境的受损与个体精神焦虑的加深,闽东诗人在诗与思的对话中拓展了诗歌创作的内在主题。
1.对家园生态受损的反思。上世纪90 年代初,过度的开发以及欠合理的整治措施导致了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诗人们敏锐地发现家园生态的受损,并在诗歌中得以表达。“作为海洋的伐木者/我们看到一颗桑树/是怎样的秃掉的”“无路可走恰因为身下的路太多”“这个海空了,鱼荒”汤养宗在他的长诗《鱼荒》中,把海洋与当代人的命运结合起,对以人类以个体欲求为目的盲目捕鱼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闽东官井洋作为全国唯一的大黄鱼产卵洄游基地,80 年代初因为“敲罟”的残酷式捕鱼方式(渔民在岸上用力后敲击船帮上的竹竿,声波导入水中将大黄鱼震昏)导致了野生大黄鱼的鱼汛消失。面对这个现象,谢宜兴痛心疾首地写下《官井洋》系列组诗,以拟人化的手法表达了对趋利性商业的批判“为什么我的头晕痛欲裂/这是谁在哭泣/我的腮边流出鲜血/一个少年在岸边听到的全是哭声”(《敲鱼》)。张幸福、伊路、刘伟雄、周宗飞、王祥康等诗人都不约而地把眼光转向快速发展背后的家园,在避开现代文明遮蔽的同时,反思工业文明及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恶果,潜在地对“唯进化论”进行了质疑。
2.对现代精神困境的批判。曾繁仁教授指出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关怀是生态美学最终的落脚点。“生态美学虽然否认实践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但并没有无视人的存在;恰恰相反,生态美学追求生态系统之美,正是从维护人的生存出发。所以生态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8]闽东诗人以心灵在场的方式,在日常的经验中发现诗性并有效的表达它,使他们的诗歌获得进入存在的深处。“大山犄角里,田园渐荒,野物无声阔延/有些事物逃离家乡又藏身于城市犄角旮旯/比如娼妓,吸毒者,同性恋和网络水军。”(哈雷的《犄角之物》)在商品经济蓬勃的生机之下,诗人捕捉到它对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另一位女诗人伊路,在其系列组诗《人间工地》中以智性的思考中重新整合其生态美学立场,借用隐喻产生的暗示性,唤醒读者看清到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残酷事实,即社会文明的进步与人性中自在状态的受损是同时并进。
(二)实现整体主义的诗学立场
“生态整体主义最主要的表现形态就是当代深层生态学,其核心观点就是‘生态’平等”,也就是主张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包括人类内在万物都自有其价值而处于平等地位。[9]把生态整体主义作为诗歌写作的指导原则,是闽东诗群对人类中心主义原则的自觉超越,同时也是“家园意识”从浅层抵达深层的重要体现。
1.生命平等的生态观。闽东诗人不再是科技理性至上的鼓吹者,他们对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与非人类环境之间的关联模式有着深刻洞察与思考。诗人的价值判断是基于生命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意识到相互依存、相互平等的生物环链所有生命的福音。当人类以万物之长居高临下并肆意对其他生灵进行控制与杀戮时,诗人反问“如果大自然也抡起复仇之刀/谁能护住我们身上的鱼鳍?”(谢宜兴《残鲨》)。
现代化进程中家园环境的恶化与家园伦理的迷失,究其根源是因为人们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我们,有着自己的骄傲/每一朵浪花也有其追寻/谁能说得清谁的生命更为高贵或卑微”(韦廷信《求情》)“善待海水。这是我们的家园把裂隙/重新放回岩石。湿漉漉的斑纹里万物生长。”(张幸福《一只海豹边舞动边松开平安夜的琴弦》)类似韦廷信、张幸福这种体现生命平等观的诗歌在闽东诗歌中俯拾皆是。可以说,正是海洋的自然性赋予了闽东诗人这种生命平等的生态观,以此去感知海洋及自然界中的各种生命,使万物获得了尊严。
2.故乡、祖国、地球的一体家园观。闽东诗人在与海洋的持续对话中,诗人的“家园意识”已经从身后的故乡扩大为祖国乃至宏阔地球上的自然万物,呈现出独特的经验表达与想象的能力。“海只是/地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形成的大水坑/地球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毁灭它”(《总有东西不是海》)。在伊路的眼里海洋虽然拥有生生不息的历史姿态,但也只是组成地球整体的一个部分,表达对自然万物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90 后女诗人陈小虾的《屯头暮色》中用了四个“之上”和一个“之下”,把滩涂、跳跳鱼、网、流云、长空、以及“我”叠加起天间万物形成一个整体,暗示人类的渺小与短暂。地球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家园,它滋养和激活了各种生命,他们彼此平衡、互相依存。只有认识到这点的人才能放弃“征服自然”的想法,在天地之间找准自己的位置。
三、心灵家园的诗意构建
海洋赋予闽东诗人更开阔的视野,也加深了他们对生命的理解与认知。但是,“这些水泥森林林立的路障将遮蔽/所有回乡的路”,刘伟雄在《倒在南方街头的马》中暗示着曾经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的“家园”已经逐渐远离现代人的生活,诗人唯有在大踏步向前的生活中不断地回望家园,以心灵家园的诗意构建实现精神的返乡,以此回应现代生活,重建生态诗学的出发点。
(一)家园回望中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本土传统的积累,使日常之物的实用功能退化,成为审美习惯的潜在标准;另一方面,文化认同的形成又与外来文化的参照、比较是紧密相关的。“海洋”作为开放的文化意象和文化原型,古今中外的诗人们耕耘其上、各得其所。闽东诗人在背靠大山的同时,与自然的大海对话,颠覆了海洋文化的虚构性想象,形成美学立场上的精神同构。
1.对虚构性海洋文化的颠覆。“海洋”作为开放的文化意象和文化原型,古今中外的诗人们耕耘其上、各得其所。五四之后,西方海洋文化的强势涌入,使中国的海洋诗在日常模式之外开拓出“美好”“自由”等新的文化内涵,大量的文学创作以虚幻性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它的原貌。20 世纪80 年代,朦胧诗塑造了前所未有的海洋神话。以韩东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开启海洋诗的写实风,以亲眼所见的“大海”瓦解了前者所赋予的海洋文化想象的虚幻性,从而使当代海洋诗的写作呈现出多维度的风貌。闽东海域的生活实践构筑了闽东诗人的文化认同,他们的海洋诗是从真正的海洋中长出来的,有着亲见的可靠性与真实性。比如刘伟雄《沉船在静静的海上》中,他写世人熟悉的海洋“风清月白的美丽大海呵/笼罩四周的沉静是多么富有诗意”。另一方面他也写出海洋的另一面“八位渔民/从此和支离破碎的船身/承载了悲惨的故事漂向四方”,诗人以直觉去抓取形象,以日常体验消解了前人加在大海形象上的虚幻想像,就他所在对话录中所说的“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时不时击碎了我诗歌中非常美好的内核”[10]
2.建构“家园体验”式的海洋诗传统。依山傍海的生存环境恢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更大程度上避免诗歌抒情中的凌虚蹈空。汤养宗说:“作为一个血缘来自渔村的人,当我还来不及意识自己介入诗歌的姿势,就有一种被支解感,于是诗歌的博大迫使我返回原地缅怀最初青葱的梦想——这就是万古不变的海洋。”[11]以海洋生物“寄居蟹”自居的刘伟雄,“用海水喂养自己一生”最终又归入大海的诗人张幸福等,可以说,以海洋为中心的自然万物是当代闽东诗人的精神原乡,并形成了闽东诗人在生态美学立场上的文化同构。
当代闽东诗人自觉地把艺术感受、诗学想象与海上闽东的家园体验联结在一起,写出大量优秀的“海洋诗”。汤养宗早期以“海洋诗”闻名于诗坛,他的视野荡开现在的文化结论,在自然的海与社会的海之间探索、思考。他的海洋诗集《水上吉普赛》在20 世纪90 年代初的中国诗坛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引起关注;叶玉琳以“元诗”写作接日常大海体验的秘密通道,语言与海洋互相阐释、相互指涉,实现了诗人对诗歌写作技艺的反思。伊路、刘伟雄、谢宜兴、张幸福、俞昌雄、林典铇,陈小虾,韦廷信等,他们都把目光转向生于斯长于斯的海上闽东,并因此唤醒了他们对这个世界最初的生态认知与审美感受。
(二)诗意栖居中的心灵回归
“诗意的栖居”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的诗性化表述,强调人的生存状态。鲁枢元先生说“诗意栖居,是人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域,是精神价值在审美愉悦中的实现,是人生中因而也是天地间最可珍贵的生存状态,然而这种状态长期以来却被种种现实功利的、技术的、物欲的东西遮蔽了。”[12]
1.心灵的返乡。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着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的天性受损。在闽东的诗歌中,“自由自在”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集中体现在诗人对自然万物的摹与中。“那些呼朋唤友流动过来的/银鱼,巴浪鱼,大白鲳/它们在阳光照耀的海滨/告诉我自由、白和晶亮”(叶玉琳《在城澳》)“大海里的鱼多么自如/丛林中的鸟儿多么欢快/大海和丛林/是没有墙的家”(伊路《童话》)“我美丽的家乡西洋岛啊/那样沉静地躺在东海之上/自由自在地把岁月读成/一片片飘逝的云朵”(刘伟雄《西洋岛上》)。在这些诗歌里,各种生命因为顺应自然而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舒展。诗人们并不是简单的状物或追忆,而是借助物质生命的描蓦唤起心灵的隐秘体验,从而为人的生存提供一种方向。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闽东诗人对充满生机、自在的生命状态的诗性形象呈现不仅是他们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也是他们基于家园体验的现代审美向往。回归生命的自然运转,灵性得以闪光,心灵才能真正返回根基。
2.文化的返乡。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作为生存根基的自然,一个是作为文化根基的祖国。回归生命的自在,不仅要顺应自然本性,也要回归文化的根基。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铸就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一切劳作与活动,建造和照料,都‘文化’。而文化始终只是并且永远就是一种栖居的结果。这种栖居却是诗意的。”[13]叶玉琳诗歌中“唐诗宋诗”的风韵,刘伟雄诗歌中的“乡愁”,谢宜兴诗歌中的“祖国的根脉”等,王祥康的“身体里的祖国”等,共同的文化传统成为闽东诗人及至全球华人之间增添情感的精神纽带。回归自然,回归传统,才能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然而,传统文化只有依靠当代的精神激活并真正进入生活,才能形成有意义的传统。比如汤养宗,他把古典“互文”手法融入现代口语叙事诗,赋予文本流动的语感,使得现代诗的抒情有了更坚实的质地。同时他还复活了传统“白描”手法,比如“桃李不言,下自有手。迟早落果,再聚首”。这些白描句式鲜明有力、参差交错,在节奏的控制中推动主体情感的变化。面对着纷繁芜杂的外来文化思潮,扎根传统文化并对外来的思想进行中国化改造,以创造性的精神激活传统文化,从而使闽东的诗歌获得可读性与历史感。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说“闽东的锦绣河山就是一种光彩。闽东的灿烂文化传统就是一种光彩。闽东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14]这种光彩贯穿在闽东诗群的文本中,从早期聚焦地域文化生活、注重海域风光的呈现,逐渐过渡到在“家园意识”关照下的对人与自然的伦理思考,并以整体主义的生态哲学立场,打开一条诗意栖居的路径实现精神层面上的“返乡”。诗歌作为艺术化的哲学,诗歌的美好之处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播,而是通过人心与世界的审美沟通,从而探求世界的本源。多年来,闽东诗人立足于海上闽东的家园体验,以持续的影响力和成就在诗学层面和现实层面实现“闽东之光”的生态诗学建构与多维传播。
注释:
[1][13][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15、107 页。
[2]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335 页。
[3]宋秀葵:《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83 页。
[4][5]苏孝敏编:《铁马风声——霞浦古代诗词、楹联民谣赏析》,福州:海峡出版集团,2015 年,第7、14 页。
[6]福建省霞浦县志编纂委员会,《霞浦县志》(内部资料),霞浦:福建省霞浦县印刷厂承印,1986 年,第228 页。
[7]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上海三联文库,1998 年,第240 页。
[8]祁志祥.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及其创新意义》,《学习与探索》2017 第12 期。
[9]曾繁仁:《生态美学》,青岛:山东文艺出版社,2020 年,第46 页。
[10]刘伟雄:《平原上的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年,第192 页。
[11]汤养宗:《水上吉普赛》,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 年,第163 页。
[12]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31 页。
[14]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