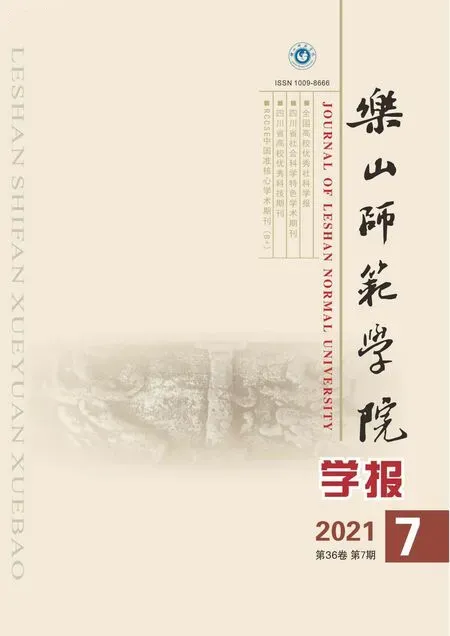公与私:晚明社会秩序的变动与观念变迁
2021-12-29李双利
李双利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重庆 400715)
明代中期以来的社会以急剧变化为特征。[1]8若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进行观察,明代社会的转变是由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带来的。土地进一步商品化、国家放松对户籍的控制以及农民阶级进行反抗斗争[2]6-22等因素造成阶级关系的复杂化,这是明末社会秩序变动的重要方面。森正夫从地域社会的角度观察明末社会秩序的变动,认为当时地方志中反映秩序意识淡化的事物已占四成,而依然维持着固有秩序的只有六成,危机确实在潜伏。[3]晚明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商业化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农业社会秩序的崩溃。在新旧社会秩序的交替中,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的公私关系出现了。如果从新公私观的角度审视明末社会的变化,这种秩序的变动就更为直接而深刻的体现出来。
一、晚明社会秩序的变动
对社会进行整体分析,可以从规范型结构入手。在帕森斯(Parsons)的社会学理论中,他认为社会的规范型结构由四项有秩序排列的要素组成:价值观念、社会规则、集体活动和个人分工。[4]93当这四个要素发生变化时,社会原有的规范性秩序被打破,社会有序与社会变革之间会产生巨大的张力,从而使得这四者产生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有益变化。同样地,埃利希认为,社会秩序的主导表象即是相互制约前提下的协作表象。[4]36也就是说,在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里,社会的各个有机子系统处于协作运转状态。但当这个基础被打破,即原有的子系统内部发生变化而不能有效整合,社会秩序就会不可避免的陷入不稳定状态,直至新的可以相互协作、稳定运转的各个子系统形成,社会秩序方能重新处于稳定状态。而在这一变动的过程中,价值观念、社会规则、集体活动与个人分工这四个构成社会规范型结构的要素子系统的变化,是观察社会秩序变动与重建过程的最好窗口。晚明社会呈现的诸多面象,是社会秩序发生深刻变动的表现。将其置于明清时期漫长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去审视,以“价值观念”这一全体社会成员所认同的社会构想为线索,这种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秩序变动才能被清晰而深刻的揭露出来。
明自建国始,太祖即以其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创制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洪武体制”,力求建立一种“四民分业”的简单朴素的农业社会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太祖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皇权、固化社会及控制思想等。而这种安土重迁、乡里和谐的社会规则,恰好适应了明初生产力恢复和发展的需要,明初社会在这套尚有生命力的体制规划中缓慢而有序地发展着。然而这种凝固化、扁平化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逐渐变得面目全非。[5]334明朝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洪武体制”对思想施加高压,这使得思想界基本处于沉寂状态,精神文化充满了严谨而深奥的色彩。但自成化、弘治以后,随着统治的宽容与开明,社会思想逐渐变得活跃,不再时刻处于生存边缘的明朝人开始追求思想自由与个性独立。王学恰逢其时,故在民间大行其道。这一时期,社会流动加速,商业致富机会增多,民间各种集体活动开始繁荣,个人分工也不再固化,出现了“四民混业”的趋势。原有农业社会的调节乡里纠纷的规则也逐渐被打破,“争讼”“好讼”的商业社会现象层出不穷。以上诸多变化也带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的变迁,人们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开始往肯定欲望、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向变化。对这一变化最集中的反映,就是对“私”的价值的发现与肯定。
事实上,明代后期社会的诸面像,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是社会规范性结构的四个有序排列的要素发生变化,是社会秩序变动的表象,绝非能一言蔽之。仅就晚明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来看,此时已呈现出无力姿态。《龙图公案》卷六《夺伞破伞》中有“五分银物,亦来打搅,衙门一处虽设十个官,亦理不得许多事。”[6]事实也是如此。明清官员数量之少,已是众所周知之事,根据社会学家瞿同祖统计,在清代,平均每2万人仅有一名官员,平均每1万人也仅有3名官府属员。[7]9与人口激增、事务繁杂的地方行政实况形成鲜明对比。官员数量的稀少,属员作用的有限,使得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常常处于失控状态。这就给地方上以“士商相混”为特征的新地主阶层提供了发展和壮大的机会。他们在灾害频仍、政府无力的背景下,开始尝试寻求自身的政治权益,而对天下之“公”的重新定义,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二、晚明公私观念的变迁
(一)私的价值的再发现
在《韩非子》中,私为“自怀”;《说文解字》中私被解为“奸邪”之意。至宋代,随着“天理”“人欲”等观念的引入,私又与“人欲”联系在一起,成为与“天理之公”相对立的“人欲之私”而受到抨击。可以说,“私”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被否定的地位。直到明代,私的价值才真正得到肯定。可以说,私的价值的再发现是由王学的现成派完成的。阳明学兴起的背景有着诸多方面,包括随着乡村的地主制社会结构发展而产生的所有制关系的变化、随工商业的发展而产生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等。[8]6-9《龙溪集·天泉证道记》中有“阳明夫子学,以良知为宗。梅与门人论学,提四句为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氏后学皆以此为本,共用“良知”的概念,从其“无善无恶”的内核入手进行改造。其中现成派可以说将“无善无恶”四字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样一来,既无善恶之分,那么现成派的世界观就由原先理学的二元对立转向一元论,由此自然造成人们对许多固有观念的重新诠释。原先与“公”处于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的“私”被重新定义,也就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自明朝中叶以来,生存的艰难和经济机会的扩大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的属于农业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道德观念开始变得混乱,这促使人们当时重新审视自己的个人价值。罗近溪的语录中有“盖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机。故人之为生。自有天然之乐趣。”[9]28人的存在,首先与“生机”“乐趣”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什么“天命之性”。这是明代人对于私的价值的再发现踏出的第一步,即开始对人的主体性欲望采取正视、认可的态度。何心隐指出“孔子言无欲而好仁,似亦言无欲也。然言乎好仁,乃己之所好也。惟仁之好而无欲也。不然,好非欲乎?”在这里,他通过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方式来证明人不可能无欲,“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佚,性也。乘乎其欲者也。”[10]40-42这样一来,在承认人天生的主体性欲望之时,将“味”“色”“声”“安逸”等社会性欲望也纳入肯定之列,“私”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了。李卓吾可以说是对“私”的价值的再发现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11]他将“私”提到与“心”同样的高度,人生来便是一个心,而有心必有私,无私必无心,这便将私作为人存在的必要条件了,是对私的价值的高度肯定。但就此认为他赞扬所有的“私”未免过于草率。“学道者病在爱身而不爱道,是以……徒为自私自利之计。”[12]可见,他并不是对私不加批判地一味肯定,而是辩证地看待私的内涵。这样一来,他的学说就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他对于与道相对的私持否定态度,他所肯定的的私,在《答耿中丞》的信件中明确提出只有“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为之道。”
除了将“私”作为人的欲望来肯定之外,晚明也出现了另一种引人瞩目的倾向:开始为争取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而发声。何心隐与袁了凡的主张最具代表性。何心隐关于个人命运的观点与王艮大致相似,即愚夫愚妇与圣人本质上并无不同,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善生活。“主其大而小不人焉,可也。主其小而大不入焉,是不见大而狙于小也,而可乎?有为农工而见于商贾者,商贾之求之议论得人焉。有为商贾而见于士者,士之求之议论得入焉。有为士而见于圣贤者,圣贤之求之议论得人焉。”[10]53-54这里虽然有“农工”、“商贾”、“士”等传统的阶层高低区别,但更重要的是其中体现了一种鼓励个人向上奋斗的精神。在这里,何心隐并没有明确地表现出对于私人物质利益追求的支持。袁了凡更明确地倡导并践行了这种思想。作为16世纪最著名的善书家,袁了凡的《功过格》即是对私人物质利益追求的最大肯定。通过每天记录自己的善行以达到改善个人生活的目的,这种精致的操作方法无疑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个人价值确认和追求的深度。在袁黄的“立命篇”出现以后,整个17世纪至少又有10种功过格得以刊行;除这些现存的功过格外,我们还能从时人的著作中发现许多冠以其他名目的功过格。[13]166袁了凡《功过格》以后大量类似善书的出现和流行,证实了晚明时期肯定和追求“私”的思潮的影响范围之大、程度之深。
(二)公的内涵的再思考
公在《说文解字》中被解为“平分”;在《诗经》中,公是对于“共”所表示的众人共同的劳动、祭祀场所——公宫、公堂,以及支配这些场所的族长的称谓。在统一国家成立后,“公”成为与君主、官府等统治机关相关的概念。[4]6到西汉,贾谊的《新书·修政语下》有“天下扩扩,一人有之;万民丛丛,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通过“有道”而使君主拥有天下成为正当,有道之君成为天下之公。至宋代,又引入“天理”观念,君主统治加上了“天理之公”的庇护,君主个人独裁似乎更为不可撼动。直到晚明,随着商业化和白银化的迅速推进,由唐宋继承而来的农业社会秩序逐渐崩溃。随着社会秩序的变动,公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诠释和延伸。
《明史·神宗本纪》中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论断,可见万历时期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一方面,晚明自然灾害频发,加之国家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却又加派矿监税使,使得诸多矛盾集中于无政治特权的中小地主阶层;另一方面,则是新地主阶层对以皇帝专政为特征的权力结构进行批评,以神宗(宦官)集团为代表的皇帝专制统治秩序与以东林学派为代表的新地主集团对权力下放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越发明显。他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符合自身利益的社会秩序,而最开始要做的,就是对以往高高在上的“公”进行改造。
对公的内涵的再思考,首先是将天理之公与天下之公分离。天理之公更接近于自然之公,仍然备受推崇。例如吕坤曾说:“拂其人欲自然之私而顺其天理自然之公。“[14]与之相对的,是原先由天理之公渗透到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代表君主“一家一姓”之私的天下之公受到质疑,如“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14]对君主代表天下之公提出质疑,则有“去南臣而出于上意,则皇上之独揽,未必协于天下之公”[15]。这些观点已经将君主专权式统治与天下之公分离。在此基础上,这群中小地主的代言人即东林派人士开始寻求构建以自身利益主导、分权式的新统治秩序。“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周,必分而治之,要使同归于大顺。”[16]此时的天下之公所指,是由东林派人士为代表的地主阶层整体利益,而非原先代表“公室”的皇帝宦官集团。而他们所渴望建立的,正是在这种新的“公”的统治下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与农业社会追求道德伦理和安土重迁的秩序不同,它是属于商业社会的、肯定欲望与追求利益的秩序。当然,此时的“公”的观念的变化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其真正内涵意义的变革,必须在更深刻的社会秩序变动中才能实现。
三、公私互动关系的重构
在明代以前,公与私基本处于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礼记·礼运》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在理想的大同社会中,“公”也是不包括“为己”之“私”的。《论语·尧曰》中“公”的意思为“是为是,非为非,无偏私”,公与私的对立关系更为明显。到了宋代,这种对立关系更为显著,朱熹有“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里,灭人欲”[17]。公私之间的简单对立,直到明中期最后才逐渐有所改变。随着私的价值的再发现与公的内涵的再认识,公与私在明清鼎革之际形成了新的的良性互动关系。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亲身经历了明清鼎革这一惊天动地的时代变革。代表农业核心地区文明的明朝灭亡与代表游牧、半游牧区文明的清朝建立,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重构和文化精神的重新定向。在当时,君主与地主、特权地主与平民地主以及地主与自耕农、佃户、奴仆、商人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显露出来。生活在不同地域、经历不同的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等人却清晰地感受到了同样的社会秩序变动,并对公私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进入晚明以来,灾害频仍。根据详载灾害的崇祯《吴县志》卷十一《祥异》,即使是当时引领全国风尚的苏州,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一百二十一年间,苏州府属吴县的大约发生了五十九次灾害。[18]26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得小民生活难以为继,民变、佃变、奴变等在各地不断出现。此时,官民、上下之间的冲突已经十分激烈。随着农村内部网络的崩溃(里甲制度逐渐失去作用)和一条鞭法的实行,朝廷对乡绅地主阶层的控制得以放松,乡绅地主阶层随之拥有更大的地方权力和自由。明朝初年,朝廷强制推行了各类乡治制度,包括行政管理、赋役等方面,这一制度设计的整体度、清晰度令人印象深刻,而政府的执行能力更是如此。[19]63地主阶层可以通过许多较低级别的管理者,诸如保甲之保长、里甲的甲长、乡约之约正等,加入国家统治秩序,以期拥有更大的权力。这些措施是明太祖为了构建人民安土务农的理想秩序所进行的努力。但是随着国家对地方管理逐渐失控,地主阶层在这种状况下也发生了内部分化。一方面是豪强地主拥有“优免”等特权,通过兼并迅速富裕起来;另一方面是中小地主困苦衰落。当时安徽歙县“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20]就是典型的明代务农的地主以及佃农贫困生活的缩影。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等的随意加派也给地主造成巨大灾难,“矿尽又穿他穴。凡入穴,必祈祷于神,不幸而覆压者有之。既得矿,必先烹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炼者、取钩砂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番换……搜取殆尽。[21]再加上以抗租、抢攘为代表的各种“暴动”,使得诸多矛盾集中于中小地主阶层。这促使他们为保住自身利益而努力和斗争。而这些矛盾并没有因明朝灭亡而随之消失,反而更加激烈地爆发出来。官宦之争、文武之争、农民起义、抗清斗争等等,这些自下而上产生的压力变革,与清朝想要迫切建立稳定有序的社会规范性结构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对立。而反映这一秩序变动与重构的社会基础表象,即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为代表的新地主阶级内部引发的对公私互动关系的讨论。
首先是明朝灭亡引发的当时人对专权式君主统治秩序的批判。“后为之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22]在此处黄宗羲明确指出君主专权是“大私”而非“天下之公”,过去的道德标准也已不再适用,而是直击君主,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重新构建公私关系。“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下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为天下治。……故天下之私,天下之公也。”[23]先指出古代圣王之所以代表“公”,乃是因其以“天下之私”为前提,而私与公的关系,则是“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建国亲族,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24]即“合私为公”四字。顾炎武将公私关系的重新定义为“天下之私,天下之公”的互动关系。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中有:“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这与顾、黄等人对于公私关系的论述大致相同,即公的实现要以私为前提,当私成为群体或者社会性需求时,它就变成了公。这其实是明末地主阶级为维护自身整体利益而发声。顾炎武对此有详细解释,“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一旦有不虞之变……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纵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下之公也。”[25]可以发现,明末士人所高呼的分权式政治基础的“私”,主要是指以“士商相混”为特征的新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层的整体利益。
关于明末士人提出的分权式统治秩序的构想在清代的实现,或者明清易代带来的社会制度的重构和文化精神的重新定向,人们已有充分讨论,这里就简单举其一二进行论证。首先是雍正时期推行的“摊丁入亩”,使得国家对土地的控制以征收白银为主,放松了对人口尤其是无地农民的控制,并将这种控制权转交与中小地主阶层。这样一来,明末士人所追求的“自私自利”得以更大程度地保全,由此合私为公,新建立的清朝的统治的公正性得到承认。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乡绅地主的超经济特权受到打击。清代前期,土地占有者身份地位变化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功名官爵的“特权地主”的垄断地位有所削弱,无功名官爵身份的“庶民地主”有所发展。[26]国家放松对佃农的控制以及加强对特权地主的打击,使原先处于种种矛盾之下的中小地主阶层得以喘息和发展,符合地主阶层的整体利益。可以说在历代集权国家中,清朝政权是最符合地主政权之实质的。[27]188在政治层面上,清代最具特色的“秘密奏折”制度,也正是因皇帝希望通过心腹大臣及时得知地方的真实情况而设立的,这正是乡绅阶层或者中小地主阶层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得到更多的官方重视的表现。
四、结语
总之,自明中期以后,伴随着社会变革加速,王学中开始明确地出现对“私”的价值的伸张。王学在承认人的自然欲望的同时,对于财货声色等社会性欲望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并逐渐引发了对于“公”的内涵的重新思考。君主“一家一姓”式的统治秩序受到批判,以东林派人士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层开始以自身的集体利益作为新的“公“的内涵,并在社会秩序剧烈变动与重构的明清鼎革之际,通过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等新地主阶层内部引发的关于公私观念激烈讨论,新公私观逐渐得到社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社会秩序的构建。
社会秩序的变动并非简单地由无序到有序的整合过程。在这之中,价值观念的变化最为深刻地反映着社会规范性结构的有序与变革。在明清两代漫长的历史画卷中,伴随着社会秩序的变动,人们逐渐产生对公私观念重新思考与定义的要求。公私价值观念的变迁,是观察这一时期诸多历史面象的重要窗口,是社会有序与社会变革相对压力下社会自发调节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