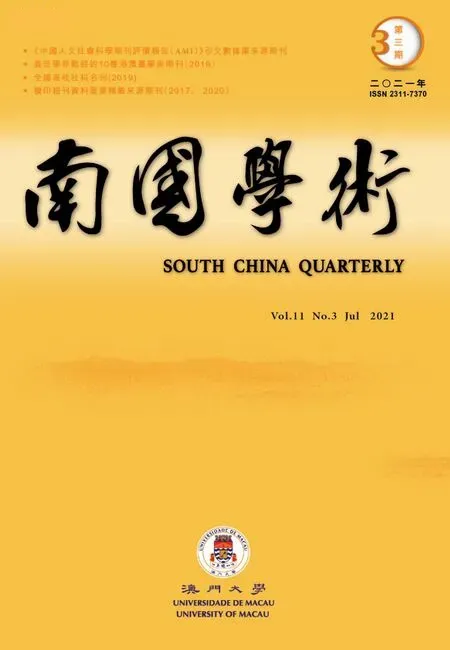明清時期的府縣社會治安管理制度
2021-12-29柏樺
柏 樺
[關鍵詞]明清時期 府縣 民間組織 官民相得 社會治安
在明清時期,朝廷對府縣社會治安管理制定的原則是,以官府爲主導,將一切可以利用的民間力量納入其中,構建官民相得的社會治安防範體系,以實現對地方社會的全面管控。①柏樺:“清代律例規定的官方治安責任”,《晉陽學刊》4(2009):73—80;柏樺、吳愛明:“清代律例規定的民間組織治安責任”,《學術交流》1(2009):45—51;柏樺、吳愛明:“官民相得社會治安體系的構建”,《戰略與管理》4(2015):91—98。這種社會治安管理原則,一方面具有鮮明的制度設計特點,另一方面也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使得運行效果總達不到統治者的預期,有時甚至與王朝離心離德。之所以出現如此結果,既有制度設計者的失誤,也有執行者的掣肘,更脫離不開社會的發展。
一 制度設計理念
明清時期,府縣社會治安體系在制度設計方面,吸納了歷代王朝的基層治安防控制度經驗,具有獨到的特點;與此同時,制度自身也存在較爲明顯的設計失誤,運行過程中又受到一些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直接導致實際施行效果並不理想。
首先,具有多元主體參與治理思想雛形的制度設計與實施的困境。公共管理學中的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理論認爲:對於國家社會的管理,既可以是公共組織,也可以是社會組織,還可以以公共與社會組織合作方式進行。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組織與社會組織的合作、強制與自願的合作是有效治理實現的條件。對國家公共問題的解決,主要通過不同主體之間合作、協商、構建夥伴關係、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來進行實施。“爲此,需要利用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多種手段,保障危機治理中多元參與主體的功能耦合。”②夏志強:“公共危機治理多元主體的功能耦合機制探析”,《中國行政管理》5(2009):124。明清時期,對府縣社會治安的制度設計,體現了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思想理念,注重文官、軍隊、社會等多元主體在維護社會治安中的作用,試圖建立以官方爲主導,以民間各種力量都能夠參與,並以相應政策與法律爲保障的社會治安制度。從制度設計看,重點在於推行教化,在倡導良好社會風俗的同時,將統治階級的政治理念灌輸到民衆中;而在維護社會治安措施方面,以官方爲主,要求民間組織配合,且負責本地教化、巡防、相互救護、呈報與協助緝捕罪犯等事務。在制度設計中,官方與民間功能不同、權力不同、責任不同,所期望的是能夠官民相得,共同維護府縣社會秩序穩定。這種設計無疑是比較嚴密的,但忽略了具體實施上可能遇到的問題。因爲,在強調各方面責任與義務的時候,沒有賦予各方面以相應的權利;而自上而下的推行,本來就很難考慮到下層的意願與困境。尤其是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僅存在地區差異,也存在民族差異,更存在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差異,制度設計如果沒有考慮這些差異,不能因地制宜,那麽,在具體實施上所面臨的困境就會凸顯,也必將影響到實施的效果。
其次,具有程序理性思想雛形的制度設計與實行中的落差。明清王朝統治者在力保王朝權威的情況下,能夠將朝廷政令落實到每個角落,其程序設計有其獨到之處。爲防止執行時的隨意性,它要求官方與民間各司其責、相互制衡、層次分明、上下有序。以律例及制度所規定的盜案處理而言:一是將防盜責任訴諸事主的家族、鄰佑和保甲,要求他們在盜案發生時共同抵禦盜賊侵擾;二是鼓勵呈報盜情,不僅要求事主真實而及時地呈控盜案,而且要求事主的親屬、鄰佑、保甲、汛兵、居停、房主等也要及時報盜;三是府縣衙門必須及時受理盜案,立即前往失盜處所勘驗,及時組織追捕及緝拿;四是失盜地方的文武官必須及時向上司匯報盜情,不允許逼迫事主諱盜爲竊,逃避疏防責任,主動開報有相關責任的職官姓名,以備上司題參;五是上司衙門接到有關盜案的報告後,一方面要督促下屬儘快破案,另一方面要積極採取協緝措施,事後還要做出獎懲決定。從這些程序設計看,其本意上就是希望減少官員遇事推諉扯皮的惡習,促使其在遇到盜劫案件時,能夠互相配合,各司其職,共同採取積極的態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官方及民間責任人的隨意性行爲。然而,程序上的公正,並不意味着實質上的公正。因爲,每個程序都有相關責任人所要承擔的責任,那麽,當治安案件發生後,責任人優先考慮的則不是如何處理治安案件,儘快地消除治安案件的影響,恢復當地正常的社會秩序,而是關注個人的得失,所造成的惡果也是令人深思的。例如,明萬曆初年,地方盜賊縱橫,地方撫按官爲了推卸責任,便請增設專官予以管理,萬曆帝則認爲:“近來各撫按,每於地方失事後,即議增官、議更調,不知從前所作何事。今若不以實責成,將來又未免有失,且本省盜劫官銀,有旨令速捕賊贓,並究解官溺死之故。今俱未報,止將各司道更置一番,不過虛文了事,推諉常套,何有懲前慮後之實。”①《明神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2016),萬曆四年八月辛未條。當時,“財力困竭,盜賊縱橫,人情畏怯,上下相矇,以賊爲諱。其初出劫,勢不甚大,則以爲常事而不必報,此地方官隱諱積習”②〔明〕張岳:“極陳地方苗患並論征剿撫守利害疏”,陳子龍 等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1996頁。。清咸豐帝在檢討太平軍之所以能夠成功起事時講:“推原禍始,總由地方官不得其人,撫綏無術,而大吏又不能澄清舉劾,以致養癰成患。”③《清實錄•文宗》(北京:中華書局,2008),咸豐元年夏四月丙寅條。爲什麽會出現推諉責任、諱盜爲竊、撫綏無術、難以澄清舉劾呢?因爲,在程序中都有責任問題,府縣官如果承認“盜賊”橫行,就要丟官卸職,乃至於問罪;督撫按等大員如果進行舉劾,也難逃失察的責任,罰俸、降級,乃至於革職。在衆多的案例中,所看到的家族、鄰佑隱而不報,保甲地方不來呈控,捕役兵丁不實力緝捕,府縣官諱盜,督撫按瞞報,未免不是在追求程序公正過程中,失去實質上的公正。從府縣社會治安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爲府縣社會治安關係到地方社會秩序的穩定,如果不以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爲第一要求,所構建的社會治安防範體系也就失去了根本。
再次,具有效率精神追求的制度設計與實際效果脫節。明清時期,爲維護府縣社會治安,在程序設計上追求的是效率,重視破獲盜賊、人命案件的數量和質量,這原本是合理的,但是,制度注重效率卻失去了維護府縣社會治安之本。以盜案發生之後的報盜規定爲例,如果能及早報盜,盜犯尚未遠遁,贓物尚未銷盡,現場尚未被破壞,緝拿盜犯相對比較容易,於是,報盜時間規定,盜案發生後,於當日或次日呈控,府縣正印官應立即受理,前往現場勘驗,在限期內不能破案,處分較重;如果事主在事隔二十日以後纔呈報,追捕期限和追究處分要寬鬆得多,而事主承擔的責任要重。由於盜案破獲情況對於文武官前途均有影響,於是,府縣官爲了儘快破案,採取種種措施,提高破案效率。按照當時的問責制度,通過題參、二參、三參、四參,督催文武官積極偵破盜案,務求必獲,整個程序對於效率的追求始終一貫。但是,注重效率而忽略效果,也必然會影響到效率,故督撫往往“於二參屆限時,州縣規避處分,上司意存瞻徇,大率升調離任,延不開參”,最終在部院疊次奏催下而“置若罔聞”④〔清〕王慶雲:“戶部會奏籌議節流各款疏”,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戶政》,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思刊樓刊本。,總會逃過處分。這種巧於避而精於諱的方法,對官員來說是規避處分,而對破案及穩定府縣社會秩序而言,則難以說是有效率。由於他們不是以強盜是否能夠緝捕、府縣社會治安能否穩定爲出發點,最終還是以失去社會穩定爲代價。
再其次,具有績效管理精神雛形的獎懲制度設計。明清王朝對府縣社會治安的官方與民間責任人實施獎懲,達成某種目標者予以獎勵,在追究責任的時候予以懲處,總的目標是維護府縣社會治安,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以盜案而言,對事主報案與府縣官處理都做了時間上的規定,以期將禍亂消弭在萌芽之中。對於事主報案的細節,諸如盜賊人數、是否明火執仗、是否有拒捕、是否失財、是否傷人、錢財多少,都要一一講明。在具體處理的時候,若是發現隱匿及不實,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對於事主及官方與民間責任人捕獲盜賊,則有一定的獎賞;府縣官必須弄清細節,失錯要承擔責任,若是在規定的限期內破獲案件則有獎勵。在治安案件處理過程中,對於責任的區分也較爲明確,舉凡鄉村、道路、城市、江河、湖泊、海洋等處,一旦發生治安案件,民間要追究鄰佑、里甲、保甲是否救援與如期協助事主報案的責任;官方要以駐軍、官員離事發地點遠近而追究失防及緝捕的責任。盜案發生以後,必須要擒獲盜賊,在任者爲承緝官,接任者爲接緝官,都有明確的考核標準,務使盜案儘快處理。民間組織擒獲盜賊按名給賞,官員、捕役、兵丁擒獲盜賊,以盜首、過半及是否在限內來考核,分別予以升遷、加級、記錄、賞銀的獎賞,或革職、革役、降級、罰俸等處分,以期使這種危害社會治安的案件及早得到處理。
最後,具有社區警務管理思想雛形的制度設計與社會各階層的權利義務。當今社區治安管理,是以防禦犯罪和密切治安部門與社區民衆關係爲主旨,要求治安責任主體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區,與社區居民建立長期夥伴關係。在明清時期,因府縣管轄城鎮與農村衆多,要想實現有效管理,就必須明確區域。統治者深刻認識到:“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自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始。”①〔清〕陸世儀:“論治邑,《清經世文編•吏政》(北京:中華書局,1992),第545頁。朝廷“慮以一邑之大,民之衆,上與下不相屬,政令無與行”,因此關注基層組織建設,“於是里有長,鄉有約,族有正,擇其賢而才者授之,然後縣令之耳目股肱備也。縣令勤於上,約與正與長奉於下,政令有與行矣”。②〔清〕張望:“鄉治”,《清經世文編•吏政》,第592頁。以清代而言,“州縣形勢,廣狹不一,約分四鄉。小州縣一鄉約五千戶,四鄉約三萬戶。中州縣一鄉約一萬戶,四鄉計四萬戶。大州縣一鄉約三萬戶,四鄉計十二萬戶。大小相衡,通約一鄉二萬,總四鄉計八萬”③〔清〕晏斯盛:“推廣社倉之意疏”,《清經世文編•戶政》,第987頁。。各府縣也可以因地制宜,如明代福建惠安縣,“每數村則會爲一保,推衆望所服者一人長之,有警輒鳴螺遞報,各束裝以出,相爲應援,故雖在山谷間,而盜賊鮮少”④〔明〕張岳 等:《嘉靖惠安縣誌•風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43)》(上海:上海書店,1982),第1頁。。清代山東郯城縣,“各鄉之鎮,宜設一鎮長,之集宜設一集長,之村宜設一村長,之莊宜設一莊頭”⑤〔清〕黃六鴻:《福惠全書•保甲部•建築柵濠》,收入《官箴書集成(3)》(合肥:黃山書社,1997),第465頁。。而“邑分四鄉,鄉立一長,謂之保長。不曰鄉而曰保者,以鄉別有長,所以管攝錢穀諸事,而保長乃專司盜逃姦宄,不與乎其他者也”⑥〔清〕黃六鴻:《福惠全書•保甲部•選保甲長》,收入《官箴書集成(3)》,第451頁。。這種設計體現了社區治安管理思想,官府與社區共同承擔責任,轄區之內由官府負總責;社區之內由民選官任的里長、保長、甲長、鄉約、鄉長、鎮長、集長、莊頭、村正等負責;讓社區內居民,諸如鄰佑、家族、宗族、鋪行業主等也承擔相應的責任。從制度設計來看,試圖將治安工作落實到每一個人。值得注意的是,將民衆都納入社會治安防範體系之中,並沒有賦予他們知情的權利,衹要求履行各自的義務,用嚴刑峻法將他們套在這架馬車上,而不在於發揮各階層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很難得到各基層的積極協助。
明清王朝試圖通過官民結合的方式,構成官民共同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治安體系,達到王朝所支持和維護道德、社會和文化秩序,期望天下和諧與太平。應該說,將民間組織與官方組織都納入社會治安維護體系,並通過王朝的強制力加以推行,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些則是王朝政體自身難以克服的。
二 官方責任的利與弊
明清時期,維持府縣社會治安的主要力量是三班衙役、衛所及汛兵,這不但在制度上有明文規定,而且在律例中也有細密而嚴格的賞罰之條。但是,由於這些規定衹重其表而不及其裏,也就難以從根本上消除所存在的弊端。例如,清代律例在規定府縣社會治安的官方責任時,捕役兵丁待遇低下而人員混雜;文武官弁素質不一且事務繁多,不能也沒有能力將主要精力用於維護社會治安;府縣用於社會治安方面的經費不足,既難以支付緝拿人犯後的賞賜,也難以支付捕役的工食及公差費用;刑罰與處分規定嚴苛,上下在規避刑罰處分的同時,一方面相互隱匿,一方面殘忍暴虐。⑦柏樺、劉立松:“清代律例規定的官方治安責任”,《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009):50—57。除此之外,府縣官諱盜爲竊、官僚政治下的權力濫用也對府縣社會治安制度造成負面衝擊。
以府縣社會治安而言,強盜是治安的最大威脅。若是大盜結夥山居而據有巢穴,則府縣勢單力薄,難以應對;要是小盜三三兩兩散處,乃是出則爲盜、居則爲民,府縣捕役額少人單,難以摸底排查。即使有捕役可用,也容易形成貓鼠同眠,“夫捕役,亦賊也”①〔清〕黃六鴻:《福惠全書•刑名部•賊盜總論》,收入《官箴書集成(3)》,第400頁。。捕役不良,衹好藉助軍隊,“夫營兵不過藉賊以擾民”②〔清〕黃六鴻:《福惠全書•刑名部•緝捕》,收入《官箴書集成(3)》,第403頁。,以至於民間傳言:“賊來猶可,兵來殺我。”③〔明〕林雲程 等:《萬曆通州志•風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12)》,第53頁。結果是,捕役不可信,軍隊又不可依賴,緝盜之難可想而知。
緝盜不但困難,而且危險,更容易壞官。因爲,朝廷令典規定,府縣不能夠有強盜存在。一旦因強盜失事,無論是捕役兵丁還是文武官弁,都會受到嚴厲的刑罰與處分;即便是保甲、捕役、兵丁與下級官弁出問題,上級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以緝盜處分而言,如果一件盜案府縣官不能捕獲盜首,便要降級或調任;三年之內發生三件盜案不能捕獲盜首、或不能夠捕獲一半,就要被革職拿問。既然府縣官對捕盜過程無法掌控,那就應該加強防盜,但談何容易?盜賊生發除了自身轄域因素外,也受制於社會大環境,府縣官豈能以自身能力改變?府縣官既不能防範於前,又無力抓捕於後,更不願意因此毀掉自己的前程,諱盜不報與諱盜爲竊便成爲首選了。
身爲一地行政長官,府縣官諱盜有其便利條件,既能一手遮天,又有擅長索財詐民的捕役輔助,還有擔心盜案牽連的上司庇護。在多數情況下,府縣官衹要對報盜的百姓略使小技,就可以讓一件盜案消弭於無形。最爲突出的手段,就是抑勒事主,使其不敢報盜,“有失主首告,而有司即脅之以刑”,逼迫事主自行諱盜,“諱則僅失其財物,不諱則並蕩業產”,“諱則死者固不得其死,不諱則生者並不得其生”,④〔清〕鄭端:《政學錄•弭捕盜賊》,收入《官箴書集成(2)》,第317頁。事主基於利害關係,不得不諱。總的來看,官吏畏懼處分,抑勒事主諱匿是一弊;捕役人等對事主進行需索是二弊;強盜重案三推六問,使事主守候,棄業拋家,甚至苦累淹禁致死是三弊。⑤〔清〕李之芳:“嚴飭諱盜累民疏”,《清經世文編•刑政》,第3300頁。除了抑勒事主不敢報盜之外,改盜爲竊、減報盜數、化重爲輕、匿不通詳、縱放盜犯、誣良爲盜等,也是府縣官常用的諱盜手法。無論使用什麽手法,目的在於保住自己的官職,以求平安一任或升遷。
在王朝君主政體下,主賣官爵,臣賣智力,君主以國爲家而以官爵與臣下交易,臣下爲了取得並保住官爵,也不會真心爲君主賣命,彼此都不可能誠實。故此,“各處盜賊生發,所在官司往往隱匿,不行奏報,以致滋蔓難制”⑥〔明〕王瓊:“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明經世文編》,第1016頁。。衹要府縣社會治安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從地方里甲、保甲、府縣官,到守巡道、督撫按,乃至朝廷大員,無不以諱盜而尋求自保,可以說是奸僞叢生,君與臣、上司與下屬之間,根本就沒有互相信任感,也缺乏基本的品德,就很難指望他們確保府縣社會治安了。
王朝君主政體與官僚政治有不解之緣。在這一政體之下的官僚政治,決定着府縣官不會對國家和民衆負責,衹是對君主及上司負責,因此取悅君主和上司是府縣官們的首務。伴君如伴虎,即便是府縣官們千方百計地取悅君主和上司,也隨時有危險發生。既然是對君主和上級負責,府縣官們的工作重心就是如何搞好與君主和上級的關係了。他們很少有機會見到君主,所以對上司往往竭盡阿諛奉承之能事,一旦上司巡視所在地方,便“萬里可行,裹糧迎候,而經旬不已,是其所用者,皆民之力也”;上司有慶賀,“則糜費不經,帳用美錦,字以泥金,玄纁稠迭,食前方丈”;上司巡遊,“則炫耀太甚,旌旗蔽野,士馬如雲,盡鼙清笳,金銀鉦果”。⑦〔明〕王邦直:“陳愚衷以恤民窮以隆”,《明經世文編》,第2636頁。因爲,這些上司往往能夠決定他們的官運與命運。當獻媚求寵成爲官場風氣時,即便真有才能而不會獻媚求寵,也不能夠立身於官場。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府縣官“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①〔明〕羅倫:“與府縣言上中戶書”,《明經世文編》,第894頁。。官場的現實也是“佞己者以爲賢,直躬者以爲不肖”②〔明〕張時徹:《芝園外集•負暄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123冊,第670頁。。更何況,“今之守令豈賢於聖人乎?兼且奔走之日多,而治事之日少,欲其政平訟理,惡可得乎?”③〔明〕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22冊,第498頁。官場風氣敗壞,民衆深受其殃,社會治安也就缺乏穩定的基礎。
明清府縣官因缺乏行政自主權,故稱爲“微員”,但作爲一級行政區劃的行政長官,必定有行政權力,他們的權力行使則關係到府縣社會治理。正如朱元璋所講:“朕設置百官,各司厥職,以分理庶務,惟郡守、縣令爲牧民之官,凡賦斂、徭役、訴訟皆先由縣,次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歛平,徭役均,訴訟簡,一縣之事既治,則府可以無憂矣。”④《明太祖實錄》(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洪武六年春正月乙巳條。府縣官所管的事務,舉凡“戶口、田糧、農桑、學校、倉場、庫務、牢獄、刑名,俱要一一究心,隨時發落,開闔伸縮,自有機軸”⑤〔明〕汪天錫:《官箴集要•職守•正官》,收入《官箴書集成(1)》,第268頁。。府縣官不可能有不受限制的權力,但也擁有許多實際權力,不同的府縣官會充分利用這些權力,當然也會導致權力的濫用。以府縣盜賊緝捕而言,“緝捕之役,在內有番手,在外有巡快,固地方爪牙。然緝獲賊人,未必俱實,稍見影響,即恣擒捕,設爲棚吊、拷掠諸法,有智者繃繒、善財拜觀音、四馬倒攢蹄、箍腦、撾筋名色,名曰私拷,使人求死不得,其間吐實者固多,自誣者亦不少”⑥〔明〕李豫亨:《推篷寤語•毗閭閻之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28冊,第425頁。。維護府縣社會治安,乃是府縣官的重要職責,而奉上安下的體制,往往使他們不能夠認真履行職責,卻在破壞府縣治安。“切惟盜賊之興,其實有所自也。大抵管民者侵漁克害,管軍者貪暴豪猾,軍民窘於衣食,不得已而爲盜。”⑦〔明〕張純:“復仇疏”,《明經世文編》,第178頁。官方責任在於維持府縣社會治安,而確保府縣社會治安的根本在於解決民生問題,衆多的府縣官罔顧這個根本,一味地剝民以奉上,也就破壞了府縣社會治安的基礎。
王朝的中央集權制度決定了設官分職的原則,官員必須擁有權力,但不能夠有不受限制的權力。然而,君主政體本身就是建立在以家天下計的基礎上,也就不可避免造成官吏以私家權益計而入仕的事實,更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官僚政治的弊端。在官僚政治下,欺上瞞下本來就是常態,各種虛假信息傳來,必然會導致君主與上司在決斷上的失誤。官僚政治很容易惡性發展,形成官僚之間的“庇護制的網絡結構”,進而構成政治關係網,招權納賄、任人唯親、裙帶關係以及饋贈和小恩小惠就成爲中國古代官場的通病,“而這種事實是被接受,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是被體諒的”。⑧[美]費正清 等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第108頁。君主政體下的權力私有和層層分配,正是庇護制政治關係網的制度根源。
相對於朝廷所寄予的職責,大小官員更熱衷完成其庇護者要求的效忠義務。因爲,這種官員之間的相互衛護更能在嚴苛的法律責任面前帶來安全感。故此,府縣官依託政治關係網破壞制度,官官相護之積習牢不可破。府縣官不能夠盡心於民事,卻剝民以奉上,就不可能得到民衆的支持。“閭閻之休戚繫於守令,守令貪縱而弗禁,民無所訴則思亂,土崩之變所由作也。”⑨〔明〕方弘靜:《千一錄•客談八》,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26冊,第397頁。長此以往,“百姓視上官如仇讎,一旦有事,可獻城則獻城,可從賊則甘心從賊,計不反顧也”⑩〔明〕劉宗周:《劉子文編•敬修職掌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4冊,第167頁。。以官方爲主導的維護府縣社會治安制度,難以克服各種弊端,非但不能夠發揮官方應有的責任,卻常常破壞現行制度,以至於逼民爲亂,何談維護府縣社會治安!
三 民間組織存在的問題
明清律例將維護府縣社會治安作爲重要職責賦予家族、宗族、鄰佑,以及民間自己選舉的“集長”“鋪長”“廂長”“區長”“村長”“鄉約”“里正”“莊頭”“莊約”“營總”“寨主”“保董”“總理”“耆老”等,把他們都納入維護府縣社會治安體系當中,並在律例中明確他們的責任;而作爲准基層行政組織的里甲、保甲,更是主要依靠的力量,因此,律例對他們要求更嚴。清代中後期,特別是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地方士紳興辦的團練,攫取了超乎尋常的地方權力,從維護治安到徵收賦役,無所不歸其控制,而王朝局勢稍微穩定後,在試圖收回團練權力的同時,也沒有忽略團練維護府縣社會治安的作用。
應該承認,民間組織在參與維護府縣社會治安方面,起到了維持王朝社會秩序的作用。爲了完善和維護府縣社會治安體系,明清王朝也花費了不少氣力。例如,嘉靖年間,倭寇困擾沿海,廣東潮州海陽縣紳士劉子興,“謀諸鄉耆,建堡立甲,置寨設堠,鼓以義勇,申嚴約束,相率捍禦,民賴以寧居”。正因爲他們嚴爲防備,“以故倭寇之肆掠於鄰近村落者,警報日至,獨於是鎮迄不敢犯”。①〔清〕冒澄:《潮牘偶存•潮陽縣地輿圖說》,清光緒五年(1879)刻本。又如,甲午戰爭時期,日本派遣奸細刺探延邊的軍情,俄國也觀釁而動,延邊地方軍政當局便組織“越墾韓民”團練,不管是在訓練過程中,還是在反對日本奸細鬥爭中,越墾韓民都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並與朝鮮咸鏡道官府密切合作,保證了雙方邊界地區的安寧。②李洪錫:“甲午戰爭時期延邊‘越墾韓民’團練及其反對日本奸細的鬥爭”,《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002):106—109。
在肯定明清民間維護府縣社會治安體系作用的同時,也不能忽略所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對後世在調動民衆積極性、整合民間社會力量、與國家機構共同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鏡鑒意義。
其一,對民間進行組織,存在各種困難。以編立准基層組織而言,各地居民聚散不一。“北方人民聚居,保甲容易編立,還有許多堡寨可以用於防禦,以是而行保甲,豈不甚易。”但在南方,民多散處,即使勉強編甲,還有許多畸零戶,“室中惟細弱兩三人而已,貧民傭工負販,早出晏歸,爲糊口計而不足;富民惟以謹啓閉,不與戶外之事;市廛之民,株守本業”,很難組織起來進行救護。此外,山寮、流寓、土戶、縉紳、旗人、流民、商販等,或因地處偏僻,或因人口流動,或因身份特殊,“如此等人而欲其約束鄉里,晝則稽查,夜則巡行,固宜其囂然不樂也”③〔清〕黃中堅:“保甲議”,賀長齡 等輯《清經世文編•兵政》(北京:中華書局,1992),第1820頁。。組織困難,便不宜推行保甲,以致許多地方官認爲:“蓋法之不善,有擾而無安;人之不得,名存而實亡,謂保甲之無益於民也。”④〔清〕黃六鴻:《福惠全書•保甲部•選保甲長》,收入《官箴書集成(3)》,第450頁。“弭盜莫如保甲,自昔人人言之,各衙門亦屢屢申飭之,然行自行,盜自盜,曾未見有得尺寸之益者,而點查騷擾失盜繫累之害不與焉,此何也?法難必信,而衆不可概也。”⑤〔明〕許維新:“平陽兵事略”,《明經世文編》,第5010頁。不能普行保甲,准基層組織的作用就很難發揮,而府縣因爲財政無措,也不願意推行保甲,再加上吏役藉機需索,民間也有很大的抵制,所以,保甲“行之不善,則民累滋甚矣。如,舊例朔望鄉保赴縣點卯守候,一累也;刑房按月兩次取結索錢,二累也;四季委員下鄉查點,供應胥役,三累也;領牌給牌,紙張悉取諸民,四累也;遣役夜巡,遇梆鑼不響,即以誤更恐嚇,饋錢乃免,五累也;又保甲長託情更換,倏張轉李,六累也;甚而無名雜派,差役問諸莊長,莊長問諸甲長,甲長問諸人戶,藉爲收頭,七累也”⑥〔清〕彭鵬:“保甲示”,《清經世文編•兵政》,第1828頁。。有此七累,民間如何承受,避之猶恐不及。爲了防止弊端,有些地方大員則要求:“該府縣務要實心奉行,造冊呈送,以備查考。其冊籍紙張書寫工費,各該縣自爲捐備,不得私派鋪民。如有經營胥役,串通保甲,科斂鋪民分釐者,或被告發,官則飛章參處,役則立斃杖下。”⑦〔清〕張伯行:“通飭清釐保甲檄”,《清經世文編•兵政》,第1828頁。氣勢不小,可是經費從何而來?本府縣籌自何處?大員們不予考慮,僅靠一紙令下,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有些府縣官認爲,保甲之法,“原爲保安富戶起見,一切冊報往來之費,既不能取給公帑,若按戶科派,即貧民不能不受其累。地方官宜勸各鄉殷實富戶捐貲輸公,即於本鄉設局存貯,公議一人司其出入會計,以備領牌報冊,及修理寨柵公事車馬之費,其有給賞,亦出於此,收貯開銷,皆聽本鄉經營,地方官一切不問”①〔清〕張惠言:“論保甲事例書”,《清經世文編•兵政》,第1825頁。,便可以解決問題。然而,如何讓富民樂意捐輸,何人進行管理,諸多問題還是無法解決。百姓未見保甲之利,先見保甲之害,欲要他們真心爲府縣維持社會治安,實在是難於上青天。
其二,保甲組織的事務繁多,使本來爲維持府縣社會治安而設的組織承擔過重的雜務,而嚴格的要求又容易使之懈怠。“保甲行而彌盜賊,緝逃人,查賭博,詰奸宄,均力役,息武斷,睦鄉里,課耕桑,寓旌別,無一善不備焉。”②〔清〕彭鵬:“保甲示”,《清經世文編•兵政》,第1828頁。然而,有些府縣官圖省事,“傳集徵召,不用公差;查報拘催,不煩牌票,而悉聽保甲之自爲承稟”③〔清〕黃六鴻:《福惠全書•保甲部•保甲總論》,收入《官箴書集成(3)》,第450頁。,將大量的事務交保甲去辦,而保甲卻因爲負擔過重,且株累不少,“欲其檢察無隱,固已甚難;即使檢察得實,告之官,則干涉公庭,爲累不少。告之保長,則保長未必不徇庇。告之本鄉紳士,則彼不任其責,誰肯力爲主持。然則莫能以他日不可必之連坐,而博目前不可解之深怨也決矣”。這正是:“今以無事之時爲迂遠之備,愚夫見邇豈肯盡心。”④〔清〕張惠言:“論保甲事例書”,《清經世文編•兵政》,第1815頁。事務繁多再加上民心不齊,保甲居民都欲避免連坐之禍,何人肯專心維持社會治安,其不破壞社會治安已爲府縣之幸矣。
其三,缺乏相應的待遇,僅有付出而無酬勞。作爲鄉民組織,雖然府縣官介入選拔保甲長的過程,“其選任者,至期官升大堂,先備燒金銀花綢酒榼鼓樂,命約地等伴領,新保長由東角門進至滴水簷下排立,鼓吹舉樂,陰陽生爲之簪花披紅。縣官起立,新保長先行庭參,後四叩,縣官出案傍答揖。禮畢,陰陽生執壺、把盞、捧榼,縣官親爲遞酒,斟三巡畢,新保長稱謝,免行禮,鼓樂前導,由中門而出,印給優免夫差票”⑤〔清〕黃六鴻:《福惠全書•保甲部•選保甲長》,收入《官箴書集成(3)》,第451頁。。從待遇上講,最多是優免夫差,平常並沒有任何酬勞。沒有法定的收入,卻要承擔府縣官交辦的各種事務,不肖府縣官將他們鄙爲奴隸,衹是役使,卻不認真督促。“有司視爲迂闊常談,率以具文從事。各鄉設保甲長,類以市井無賴之徒充之。平時並不實心查察,雖督撫考課,有力行保甲之條,不過故套相沿,毫無裨益。”⑥〔清〕胡澤潢:“敬陳保甲二要疏”,《清經世文編•兵政》,,第1837頁。府縣官對保甲失去監督,真正實心辦事的人不能充當此任,無賴棍徒勾結官府卻能夠殘害百姓,欲使他們維持社會治安,無異於緣木求魚。
其四,由官方興辦團練,需要經費,“士無甲,倉無儲,其何能禦,民壯如何團練?”⑦〔清〕闕名:“蒞任求言示”,《清經世文編•吏政》,第521頁。府縣財政本來就捉襟見肘,更何況,“懼此法一行,彼無所匿,從中造捏訛言,妄稱抽丁,恐嚇愚昧”⑧〔清〕于成龍:“申明保甲諭”,《清經世文編•兵政》,第1833頁。。百姓也畏懼官府無償佔有勞力,而得不到任何報酬,即便是勉強組織團練,往往是“冗濫充數,替冒缺額,多設防卡,虛縻脂膏”⑨〔清〕徐有珂:“練勇議”,《皇朝經世文編續編•兵政》。。至於太平天國時期興辦的團練,是以社會動亂爲背景,士紳階層以舉辦團練爲契機,權勢得到空前的擴張,“藉名辦團,把持公事,恃符武斷,干預錢漕及一切非分之事”⑩〔清〕李瀚章 等:《光緒湖南通志•學校志六•學額》,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一年(1885)刊本。,“團總、團長藉以漁利,淩弱暴窮,魚肉一方。幸而勝賊,恃功驕橫。小之獄訟賦稅,官不得問。大之施虐吏民,法不得加”⑪〔清〕吳兆熙 等:《光緒善化縣誌• 續藝文志• 論兵》,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年(1877)刻本。。他們以“藉盤查奸細爲名,殺人奪貨,行旅視爲畏途”⑫〔清〕陳其元:《庸閑齋筆記• 團練害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42冊,第150頁。。這種紳權的惡性膨脹,已經嚴重危及地方官府的行政職能,雖然有官僚認爲,“團練之弊,此中過誤不在民,而在吏”,希望能夠“進君子之真團,而退小人之僞團。團練可張虛聲、杜奸細、追敗賊、絕擄掠”①〔清〕方浚師:《蕉軒隨錄•讀胡文忠遺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第137頁。,但對清王朝來說,團練在發揮維持社會治安的作用的同時,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已經非王朝能夠左右了。
其五,紳士、地主層組織的民團,雖然不爲官府所承認,但迫於政治形勢,官府也不得不默許。但是,“不通秀才皆望得官,無知窮民皆望得錢,拖欠錢糧者皆望蠲免”②〔清〕計六奇:《明季北略•自成西奔》(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490頁。,這是亂世百姓的普遍心理。紳士、地主層可以協助王朝的統治,爲王朝維護府縣社會治安,但自身具有的離心力,又可能成爲王朝的反對力量。從清代律例中所見的刀匪、土匪、馬匪、臺匪、會匪、回匪、奸匪、邪匪、私匪、梟匪、苗匪、竊匪、逆匪、鹽匪、積匪、慣匪、撚匪、教匪、族匪、綹匪、幅匪、遊匪、緬匪、賭匪、鍋夥匪、嘓匪、瑤匪、籖匪、髮匪等諸多的匪徒名目,就可以看出王朝的憂慮。而當有新的政治勢力能夠左右政局的時候,他們則渴望得到重用,希望能夠在順應新的支配秩序的同時,進入統治支配層的行列。這也是明清王朝在處理紳士、地主層的武裝時,最爲懼怕也最爲頭痛的問題。
四 制度實施的運行邏輯
在明清五百多年歷史發展過程中,府縣社會治安制度的實施既有優長又有短缺,不是一成不變的,往往也會互相轉化。隨着社會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舊的體制必將受到衝擊,府縣社會治安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當朝廷失去對地方社會的控制時,必然會走上覆亡之路。
——在王朝制度下所構建的府縣社會治安防範體系,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社會發展所促成的。這五百多年間,從大規模的戰爭,逐漸轉向社會穩定,而在社會穩定的前提下,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劇增,白銀貨幣化,物價持續上漲,再加上自然災害頻仍,社會不穩定的因素越來越多,從局部地區的社會動盪,到大部乃至全國的社會動盪,也使社會治安面臨巨大的挑戰。君主政體雖然以其強有力的手段來維持社會的穩定,但給社會發展也帶來很大的阻力,不但壓制了社會民主因素,而且造成政治腐敗、社會資源配置失衡、階級壓迫的深重,最終演化爲整體國力的衰弱,府縣社會治安體系也難以發揮效能。
——明清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東部與西部、內地與邊疆及沿海的經濟文化差異增大。爲了維持王朝的“本業”,必須加大黃、淮、漕及東南沿海的水利投入,而自然災害又使王朝不得不展開大規模的賑災及救荒活動。自然災害與沉重的賦稅徭役,使大量的流民遊動到各地,不但給官府管理帶來很大的困擾,也使社會不穩定的因素與日俱增,原有的府縣社會治安防範體系也面臨着衝擊。經濟發展不平衡,土地兼併,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再加上政治日益腐敗,不但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突出,民衆與官府的矛盾也日益加劇,有如火山爆發前的地下岩漿,一直蓄勢待發,統治者所構建以鎮壓爲主的府縣社會治安防範體系則很難發揮功效。以嚴刑峻法來對待民衆,不但不會使民衆配合官府,還會把民衆推到對立面上去,地方社會的失序,民衆反抗鬥爭一浪高過一浪,最終也會推翻王朝統治。
——明清時期府縣社會治安防範體系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官府幾乎沒有財政投入,卻對下進行勒索,也就很難取得民衆的信任,更難得到民衆的配合。以明代而言,地方“每遇使客入境,一切夫馬供應,皆額外取之里甲”③〔明〕吳桂芳:“條陳民瘼疏”,《明經世文編》,第3664頁。。府縣官們“止論里甲科派,其有錢糧,近上人戶,類有役佔,反不與焉。所以窮民逃竄,閭里或空”④〔明〕桂蕚:“請修復舊制以足國安民疏”,《明經世文編》,第1836頁。。朝廷有事則責成地方,“至於陝西十萬之稅,皆係各州縣裁減各役工食,科派各行銀錢,間架之括,無分城鄉;蔬果之微,莫逃徵索”⑤〔明〕余懋衡:“惡璫荼毒乞正國法疏”,《明經世文編》,第5171頁。。府縣官向里甲科派名目繁多,里甲負擔很重,“一身衆役,一事衆害,而貧者愈貧。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貲,誣以多贓則互攀親識,宅一封而雞犬豕羊大半饑死,人一出而親戚骨肉不敢收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百姓因爲“一字相牽,百口難解”①〔明〕呂坤:“憂危疏”,《明經世文編》,第4498頁。,無論是里甲還是民衆,都苦不堪言。不僅僅是府縣官,就是京官也勒索百姓,“各衙門官雖無事權者,亦皆出票令皂隸買物。其價但半給,如扇子值二錢者衹給一錢,他物類是,鋪戶甚苦之”。他們派皂隸去買,“其票上標出至本衙交納,其頭次來納者言其不好,責十板發出,此皂隸持票沿門需索。其家計算,若往交納,差人要錢。至衙門中,門上皂隸要錢,書辦要錢。稍有不到,又受責罰,不如買免爲幸,遂出二三錢銀與之。一家得銀,復至一家。京城中糖食鋪戶約有三十餘家,遍歷各家,而其人遂餍所慾矣”。②〔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史八》(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98頁。明代如此,清代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公私一切費用,皆取給於里民,“若日用之米蔬供應,新任之器具案衣,衙署之興修蓋造,宴會之席面酒肴,上司之鋪設供奉,使客之小飯下程,提事之打發差錢,戚友之抽豐供給,節序之賀慶禮儀,衙役之幫貼工食,簿書之紙劄心紅,水陸之人夫答應,官馬之餵養走差,與夫保甲牌籍,刊刷由單,報查災荒,編審丈量等項”,名目繁多,“無事不私派民間,無項不苛斂里甲,而且用一派十,用十派千,以飽贓官婪蠹之貪腹”。③〔清〕湖南巡撫趙申喬:“禁絕火耗私派以甦民困示”,《清經世文編•吏政》,第510頁。在地方,“有當月里長,有值日里長,凡有司日用、心紅紙張、油燭柴炭,一切供應食物及答應往來差使,慶賀節令生辰,皆取給焉。乃至各衙門雇募胥役,取用夫匠,無一不派諸里甲”④〔清〕蔡毓榮:“敬陳治滇實政疏”,《清經世文編•治體》,第303頁。。對於這些科派,“封疆大吏亦心知其不合而徐原之,甚至上下相矇,莫能究詰”⑤〔清〕趙青藜:“耗羨請仍歸公疏”,《清經世文編•戶政》,第669頁。。強行科派必然引起民衆強烈不滿,有些府縣官則採取籌集經費的辦法,以爲從地方殷實富戶那裏募捐之後,讓他們自己管理,就可以消除科派之苦,實際上是讓殷實富戶盤剝貧民,最終民出費用,百姓沒有從中得到實惠,卻要承當維護社會治安的責任,又如何讓他們配合官府去維護社會治安呢?
——以官府爲主導的府縣社會治安體系,有治人,無治法,對官員的個人能力要求很高,所需要的是人治。在人治的情況下,典章制度與實際執行情況往往會出現很大的偏差。人存政存,人亡政息,人治的隨意性和可變性也就決定事在人爲。從明清時期府縣社會治安維護情況來看,有些府縣官在任期間能夠認真推行,“行之半年,四境之內,夜不閉戶,雞犬不驚,儼然太平景象”⑥〔清〕黃六鴻:《福惠全書•刑名部•土番點卯》,收入《官箴書集成(3)》,第419頁。,有些府縣官在任期間不能夠認真推行,“欺誑上司,以卸己責,而盜賊因得以肆志,無所忌憚矣”⑦《清實錄•高宗》,乾隆七年三月己丑條。。正因爲如此,爲政貴在得人,乃是當時的普遍認識,“若所在牧守得人,政務修舉”⑧《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二月壬子條,“牧民之官苟非其人,則賦役不均而貧弱者受害”⑨《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七年秋七月乙卯條。。爲政在人而不在制度規範,也就使明清時期府縣社會治安防範體系缺乏穩定的基礎,與之有關的制度也容易爲人治所左右。
——王朝政體在社會發展的時候,往往不能夠在制度上尋求變革以適應之,而且還會將自己推向絕境。隨着社會的發展,士紳階層參與地方事務,對社區組織的控制力也得到加強,但他們並不擁有不受官府控制的自治權,也缺少自律性與自治性。也就是說,國家權力與民間社會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是同心的,但在具體利益方面還是有衝突的。面對日益發展的民間社會,統治者並沒有將他們引導入共同秩序之內,一方面牢牢掌控賦稅徵收、維護治安、水利建設等事關國家命脈的事務,一方面將一些無關國家權力卻關乎社會穩定的事務交與民間社會,期望國家權力與民間社會能夠互補。這種理念及具體措施,應該說是符合社會發展需求的,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官府與民間缺乏最基本的互信。官府的事務,諸如司法、行政、財政等,均不讓民間參與;官府難以承辦的事務,諸如收養孤老、賑恤災民、修橋築路、醫療救助等,卻交與民間辦理。民間沒有政治參與權,衹有出資協助承辦權,還要接受官府的稽查,這就打擊了民間的積極性。由於官府與民間不能相互信任,所建構的官民相得的府縣社會治安防範體系,不但很難發揮作用,還容易產生矛盾。在政治日益腐敗的情況下,民間與官府相脫離,甚至成爲王朝的反抗者,社會秩序也遭到破壞。
總之,明清王朝在府縣構建的社會治安防範體系,從理念上看,是將國家與社會結合在一起,試圖在官民相得的基礎上,實現彼此共有的共同秩序。但是,官民相得需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而在王朝中央集權制度下,國家的權威不容質疑,以官府爲主導,這就難免盛氣淩人——府縣官員視民間組織如奴僕,呼來喝去,敲詐勒索,根本沒有把他們當成平等的人,日久天長,也就失去了官民相得存在的基礎。即便如此,從中國國情和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觀察,明清時期的府縣社會治安防範體系還是發揮過積極作用的,曾經有效地維護了府縣社會的穩定,但也不能忽視這一體系的缺陷,以及所起的消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