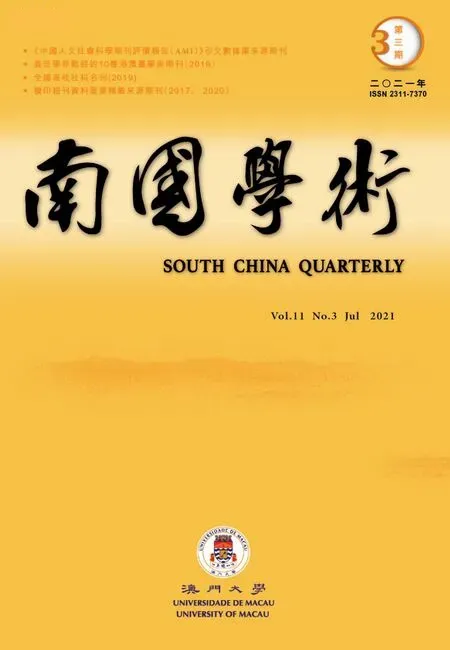文學與節日雙重事下的情感基調
——屈原精神是如何被弘揚傳播的
2021-12-29胡大雷
胡大雷
[關鍵詞]儀式 話語 五月端午 屈原精神 傳播
屈原以其高潔品質、勇於與惡勢力鬥爭而被後人稱頌,東漢王逸總結爲:“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①〔漢〕王逸:“楚辭章句”,洪興祖《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48、197、216、197頁。“行義”與“文采”,既是屈原的生活方式和行爲價值的具體表現,也是屈原精神的原始載體。本文所要討論的是,屈原精神是如何通過文學敍事、節日敍事來實現傳播與弘揚的?在此過程中,兩種敍事又各自有着怎樣的情感基調。
一 招魂:祈禱式話語與屈原精神的早期宣揚
屈原精神的文學敍事之一,是祈禱式話語的運用。
屈原生前就受到世人的崇敬,王逸稱,宋玉的《招魂》是爲屈原招魂:“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②〔漢〕王逸:“楚辭章句”,洪興祖《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48、197、216、197頁。此是稱招生魂,“憐哀”成爲其情感基調。《招魂》起首爲假託屈原自敍: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
屈原自稱“廉潔”“服義”而君上卻不察此“盛德”,讓自己遭罹殃愁;這是講招魂儀式的必要性——屈原有着高潔的品質。接着是,天帝與巫陽的對話: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上帝知道屈原魂魄離散,命巫陽用筮法占卜屈原靈魂所在。巫陽則說:“我掌夢司,你卻讓我卜筮屈原之魂在何處,我難以聽從,況卜筮了再去招魂,恐已遲誤。”於是,天帝讓他徑直去招屈原之魂。這是講招魂儀式的合理性——巫陽是招魂的專司,其神聖性在於天帝委派。《招魂》“亂曰”:
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顔蒸。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祈禱屈原之魂歸來,將陪侍楚王,竭忠盡智;把向屈原表達“憐哀”、崇敬並“盡愛以致禱”提升到忠於楚國的高度,對招魂的正當性做出說明。
楚人重祭祀,楚地民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屈原《九歌》也是“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的“祭祀之禮”的“歌舞之樂”。《招魂》的祈禱式話語,即是承襲屈原的“行義”“文采”而來。《楚辭》有《大招》,有人認爲作者不是屈原,但王逸稱《大招》是屈原所作:
屈原放流九年,憂恖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③〔漢〕王逸:“楚辭章句”,洪興祖《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48、197、216、197頁。
古代楚辭學者晁補之、黃文煥、林雲銘、姚培謙、吳世尚、屈復、顧成天、周中孚、陳本禮,與當代楚辭學者孫作雲、陳子展、殷光熹、趙逵夫、吳廣平等都認爲,《大招》的作者是屈原;但無論誰作,此爲招楚懷王之魂而作則無疑。《大招》竭力渲染四方如何可怕,家鄉如何可愛,以誘導和呼喚楚懷王之魂回歸家國,王逸也稱《招魂》“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刺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④〔漢〕王逸:“楚辭章句”,洪興祖《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48、197、216、197頁。;朱熹稱,這是一種“盡愛之道而有禱祠之心”的祈禱式話語⑤〔宋〕朱熹:《楚辭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133頁。。屈原爲什麽祈禱楚懷王之魂歸來?宋玉爲什麽祈禱屈原之魂歸來?都是在稱說家國情懷,要勵精圖治,振興楚國。屈原本人以“招魂”弘揚愛國精神而創作作品,宋玉作爲屈原的弟子,也運用如此文字來宣揚屈原的愛國精神、家國情懷,以天帝、君王與屈原本人都認同的儀式化話語來表達對屈原的崇敬。
宋玉承襲屈原而作的《招魂》,突出了屈原精神中的家國情懷!“魂兮歸來”“何爲四方些”?“東方不可以託些”“南方不可以止些”“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北方不可以止些”“君無上天些”“君無下此幽都些”;魂歸何處?衹有回歸家國,屈原《橘頌》自稱爲“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回歸家國爲什麽?《離騷》稱爲“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漢代對“招”的儀式有所延續,所謂“以章其志也”,其意味更重在向屈原“魂歸家國”表達崇敬,這就是淮南小山的《招隱士》。王逸曰:
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伇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①〔漢〕王逸:“楚辭章句”,《楚辭補註》,第232、48頁。
這個儀式,是招屈原之魂從“身沈沒”之處歸來,衹因“身沈沒”“與隱處山澤無異”,故稱爲“招隱士”,朱熹曰:“說者以爲亦託意以招屈原也。”②〔宋〕朱熹:《楚辭集註》,第167頁。回歸何處?“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還是要回歸家國。
二 弔文:實地儀式與再現苦難式話語
屈原精神的文學敍事之二,是再現苦難式話語的運用,苦難是其情感基調。
先秦的各種史籍不見屈原記載,或許因爲屈原及其作品衹在楚地流傳。再加上“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③〔漢〕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686頁。,屈原記載更不見流傳。追溯其原因,首先是楚國的高層對屈原的不認同,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滿篇是“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絀”“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之類。《襄陽耆舊傳》載:“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④〔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771頁。楚王對屈原的不滿還連累到宋玉。王逸對屈原事迹在先秦不見記載有過些許說明,其《離騷敍》云:“周室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⑤〔漢〕王逸:“楚辭章句”,《楚辭補註》,第232、48頁。他稱屈原之作不如諸子之作那樣合乎時宜,所以是“獨依”,不被楚國君王“省納”,也不被戰國時其他君王“省納”。所以,郭建勳說:“在漢王朝建立以前,屈原的辭作主要在楚地的範圍內發生影響,其流傳主要是通過非官方的渠道,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在民間進行的。”⑥郭建勳:《漢魏六朝騷體文學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第21頁。
屈原及其作品在漢王朝的流傳,據今所見材料,最早是賈誼的介紹。《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其《弔屈原賦》稱:“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側聞”一作“仄聞”,都是聽說的意思,也就是說,作爲中原人士到了長沙,纔對屈原有了深切的瞭解。《屈原賈生列傳》又載: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賈誼回京,向文帝匯報長沙見聞,其中不可能不說起屈原——是賈誼令屈原文化在中原得以廣泛傳播。作爲受到貶謫的文人,賈誼所起的文化傳播作用有二:一是把中心地區的先進文化傳播到邊遠地區;二是以其先進文化地區培育出來的文化底蘊、敏銳眼光,發掘、發現邊遠地區的特質文化乃至某些先進文化,把它傳播到中心地區。賈誼的祭弔屈原與介紹屈原,成爲屈原盛名在漢代興起的時間點。
屈原《離騷》中稱:“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賈誼《弔屈原賦》則檃栝屈原的遭遇,“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再現屈原遭受的苦難以突出其不向惡勢力低頭的精神。顔延之《祭屈原文》稱:“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嬴、羋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①〔南朝梁〕沈約:《宋書•顔延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1892頁。世人的祭弔之文,也大都是檃栝屈原生平中最不幸的那一面,歌頌其永不低頭的高尚。“古之祭祀,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贊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②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第154頁。以稱說人物的精神面貌來表達哀傷之意,世人祭弔屈原之文充分表現此意。
賈誼聽聞了屈原事迹並參與了楚地的弔祭屈原活動,纔寫下《弔屈原賦》,明確化了祭弔屈原的儀式。一是要到“屈原所自沈淵”實地弔拜屈原。如此行爲,引起人們的關注與效仿。例如,《屈原賈生列傳》載司馬遷也說:“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到長沙去,是要憑弔屈原自沉之處的,還要觀覽前人憑弔之文。甚至漢代鄧榮自稱:“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③〔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631、1170頁。欲在屈原投江之處以從屈原。二是“投書以弔屈原”。重要的是,要有“弔文”。賈誼是這樣做的,很多人也是這樣做的。《水經註•湘水》載:“汨水又西爲屈潭,即汨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昔賈誼、史遷,皆嘗徑此,弭楫江波,投弔於淵。”此稱司馬遷也有“投弔於淵”的行爲。又如,漢代梁竦“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④〔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631、1170頁。。再如,顔延之出爲始安太守,“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⑤〔南朝梁〕沈約:《宋書•顔延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1892頁。,其《祭屈原文》稱:“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原之靈。”唐代柳宗元《弔屈原文》稱:“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攬蘅若以薦芳。”⑥〔宋〕朱熹:《楚辭集註•楚辭後語》,第287頁。都是到汨羅而致弔文。不能親到汨羅,則改換儀式地點爲投書江流,如“(揚雄)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文中稱,“因江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累”⑦〔漢〕班固:《漢書•揚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3515—3516頁。;這是期望其弔文能夠順江流而到達屈原自沉之所,以表達對屈原的崇敬。後漢蔡邕《弔屈原文》也稱:“迥隔世而遙弔,託白水而騰文。”⑧〔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北京:中國書店,1989),第391頁下。
《禮記•曲禮上》:“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孔穎達正義曰:“弔辭乃使口致命,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弔”一定要到達現場,無論爲口頭致辭還是書面表達。故《文心雕龍•哀弔》稱:“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投弔於淵”是出自“禮”對“弔”的規定,一定要“至”“到”,“弔文”一定要讓屈原親自收到,如此與屈原交流而爲知音。
世人到現場去弔祭屈原,或到屈原故居,或到屈原廟。“歸鄉縣有屈原宅,女須廟,搗衣石,猶存。”⑨〔南朝宋〕庾仲雍:“荊州記”,歐陽詢《藝文類聚》,第108頁。屈原宅、女須廟,也是弔祭、紀念屈原最合適的場所。明董斯張《廣博物志》:“項羽遣英布弑義帝,武陵人哭於招屈亭下。”漢代確實已有屈原廟,史載,後漢人延篤“遭黨事禁錮,永康元年,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①〔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延篤傳》,第2108頁。。延篤爲南陽郡犨縣人,爲楚地,“鄉里”爲屈原立廟,是對屈原的崇敬。《水經註•湘水》載:“(汨羅)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有《漢南太守程堅碑》,寄在(屈)原廟。”《後漢書》有郎中南陽程堅,如果就是漢南太守程堅,那麽此廟亦建於漢時。
祭弔屈原,以再現屈原遭受的苦難,抨擊對美好事物的嫉妒與壓制,抨擊社會醜惡現象,表達對屈原“九死不悔”奮不顧身鬥爭精神的崇敬。以屈原自沉之處、屈原故宅、屈原之廟等爲祭弔館所、紀念館所,令屈原祭弔儀式的舉辦有了固定的場所,屈原祭拜成爲常態,也令屈原精神的弘揚與傳播成爲常態;以儀式作爲形式、作爲媒介弘揚與傳播屈原精神,由此奠定了基礎。
三 代屈原“立言”的自述式話語與文人表現自我
屈原精神的文學敍事之三,是自述式話語,“追愍”是其情感基調。
楚國本崇仰屈原的創作,“(屈)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②〔漢〕班固:“離騷贊序”,《楚辭補註》,第51頁。;楚國本多有追隨屈原的創作,《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稱:“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原之從容辭命”。賈誼以後,漢代興起《離騷》崇尚,如淮南王劉安入朝,武帝“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③〔漢〕班固:《漢書》,第2145頁。;“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④〔漢〕王逸:“離騷後敍”,《楚辭補註》,第48頁。;苟悅《漢紀•孝武皇帝紀》及高誘《淮南鴻烈解敍》稱劉安作《離騷賦》。爲“離騷”作註、作傳、作解,衹是理解與詮釋屈原“立言”;漢代文人又多撰文紀念屈原,其行文特點即“祖屈原之從容辭命”,又是代屈原“立言”,王泗原稱“那就是追愍屈原而章明屈原之志”⑤王泗原:“自序”,《楚辭校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第5頁。。王逸編《楚辭章句》,把屈原作品全部歸於“離騷”之名下,“離騷”成爲集合體,“騷”已儼然成體;又把漢代文人上述作品全部歸於“楚辭”;其《九思序》稱:“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游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爲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之徒,感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贊其志。則皆列於譜録,世世相傳。”
按照王逸所列,這一騷體賦的“譜録”依次是:(1)賈誼《惜誓》開風氣之先。陳子展說:“《弔屈原賦》,作者用己意、作己語弔之;《惜誓》,作者用屈意、作屈語惜之;其語意有同,而口吻則異。”⑥陳子展:《楚辭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第390頁。(2)淮南小山《招隱士》,已見前述。(3)東方朔《七諫》。“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4)嚴忌《哀時命》。“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嘆而述之。”(5)王褒《九懷》。“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污瀆。遭世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6)劉向《九嘆》。“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嘆》。嘆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嘆息無已,所謂讃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7)王逸《九思》。“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⑦〔漢〕王逸:“楚辭章句”,《楚辭補註》,第236、259、268—269、282、314頁。這些作品,都是“追愍屈原”而“用屈意,作屈語”,代屈原“立言”,是一種自述性話語。
或是以屈原爲榜樣抒發自我情懷,甚或是傍屈原作品而作,如揚雄“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⑧〔漢〕班固:《漢書•揚雄傳》,第3515頁。;或直接以“騷”爲名,“及黨事起,(應)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①〔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應奉傳》,第1609頁。。桑弘羊稱:“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賢智之士,闒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②〔漢〕桓寬:《鹽鐵論》(北京:中華書局,1984),馬非百 簡註,第58頁。漢末曹操說:“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③〔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孔融傳》,第2272頁。說到底,漢代文人看到了社會的黑暗之處,其集體“代屈原立言”,表達自己的生活態度。漢代文人以實現“美政”理想的屈原精神爲榜樣,以“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爲激勵,表明自己渴望能用於世的心願,期望像屈原一樣,即《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謂“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既實現“美政”又實現自我用世。《孟子•離婁下》“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倡導“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代屈原“立言”自述式話語,則提出人人可爲屈原,用世便可實現“美政”理想。
又有從代屈原“立言”到以其行爲爲榜樣。後漢馮衍“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於是作《顯志賦》自勵:“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賦中講到,自己學習屈原,“鑿岩石而爲室兮,託高陽以養仙”,在那裏“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④〔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馮衍傳》,第987—999頁。不僅志向、行爲以屈原爲榜樣,而且在服飾、飲食上也以屈原爲榜樣,儼然自己就是屈原。
四 屈原精神的節日事
在屈原之前,已有端午節的某些活動。據史料記載,某些地區早於屈原就有五月五日的習俗,各地的端午節本有各種因素,如屈原之前有介子推、孟嘗君,其後曹娥祭拜等,中土之外龜茲國以五月五日彌勒下生等。但自屈原自沉以後,楚地固有的這一節日活動則以屈原爲專屬或核心,其標誌性事件是以食物祭弔屈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區)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區)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並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⑤〔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林家驪《吳均集校註》(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234—235頁。
因爲祭品“爲蛟龍所竊”,於是就改爲“作粽,並帶楝葉、五花絲”,一定要讓屈原能夠收到,這也是“弔”的“至”“到”的意思。
其一,楚地在伍子胥、越王勾踐時已有競渡活動,屈原《涉江》也有龍舟競渡的敍寫,但自屈原的祭拜活動興起,“競渡”活動便成爲“招屈”專用。《荊楚記》載:“屈原以是日(五月五日)死於汨羅,人傷其死,所以並將舟楫以拯之,今之競渡,是其遺迹。”“競渡”爲“將舟楫以拯之(屈原)”,此源自於招魂儀式的祈禱屈原歸來。《隋書•地理下》載:
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馳,棹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
此述在楚地“敬鬼,尤重祠祀之事”的習俗下,爲屈原而舉辦的“競渡之戲”,並和之以歌唱與呼喊。“競渡”活動爲“招屈”專用,則是以《招魂》之類文學爲引領與核心的弘揚屈原精神。唐劉禹錫《競渡曲》,其題下註曰:“競渡始於武陵,及今舉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義。事見《圖經》。”詩首四句曰:“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彩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末二句:“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龍舟競渡的“招屈”,成爲吟咏屈原精神的載體。還有其他的屈原歸來的傳說,如《水經註》卷三十四載:“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即《離騷》所謂女媭嬋媛以詈餘也。”“父老傳言,原既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
其二,自潔其身與對惡勢力的“禳災”。唐元稹《表夏》詩之十:“靈均死波後,是節常浴蘭。”端午節日“浴蘭湯”以自潔其身,來自屈原《九歌•雲中君》“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賈誼《弔屈原賦》述及屈原的苦難與時代的黑暗時道:
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
對社會惡勢力迫害屈原而大聲鳴不平。端午節日則以積極的活動的“禳災”來應對社會惡勢力。《太平御覽》錄《鄱陽記》載:“懷蛟水,一名孝經潭,在縣南二百步,江中流石際有潭,往往有蛟浮出,時傷人焉。每至五月五日,鄉人於此江水以船競渡,俗云爲屈原禳災,前郡守縣懸彩以賞之。”《荊楚歲時記》載“禳災”活動:
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床席,及忌蓋屋。五月五日,謂之沐蘭節。四民並蹋百草,今
人又有鬥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以菖蒲或縷或屑,以泛酒。是日競
渡,採雜藥。以五彩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①〔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宋金龍 校註,第46—50頁。
“採艾”“採雜藥”“以禳毒氣”“以五彩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既是對抗惡劣的自然生態的措施,也是象徵着如何對抗惡劣的政治生態。節日話語是由屈原遭惡勢力的迫害而擴張出爲屈原“禳災”的內容,期望人們能夠安然度過“惡月”,寄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願望。
其三,全民參與。前述士人以自述式話語代屈原“立言”,表達與屈原在一起,而端午節的採艾、彩絲繫臂的“以禳毒氣”“辟兵”、競渡等,完全是全民與屈原在一起的活動。南朝梁王筠《五日望採拾詩》“長綵表良節,命縷應喜辰;結蘆同楚客,採艾異詩人。折花競鮮彩,拭露染芳津”,說的是節日裏採艾折花;而家家戶戶包粽子,更是五月端午的盛景。另外,《荊楚歲時記》載有五月五日競渡,“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而觀之”;《太平廣記》錄《逸史》載有唐代端午活動的盛大場面:
端午日,盛爲競渡之戲,諸州徵伎樂,兩縣爭勝負。綵樓看棚,照耀江水,數十年未之有也。凡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得預焉。
其四,屈原精神的節日敍事的情感基調與文學敍事的“憐哀、苦難、追愍”不同,是以歡快、樂觀爲基調的。這一切的産生,在於節日中的全民是以向前看、追求美好生活的目的來弘揚屈原精神的。節日敘事與文學敘事如此的情感基調轉換,或就是《招魂》《大招》“魂兮歸來”前後的差異,天地四方鬼怪險惡,而回到故居,不僅衹是富麗堂皇的室家之樂,而且還有實現竭忠盡智政治理想的願景,此即《招魂》“亂曰”中所述:“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敍寫的是與楚王狩獵,而寓意即所謂“來吾導夫先路”。於是,競渡意味着能夠召回屈原,禳災意味着天下的清明,全民參與意味着大家的共享。這一切,本來都是理想中、願望中的,現在都實現了,那麽,怎麽能不是全民的節日呢!
五 雙重事與兩大情感基調的文學史意義
弘揚屈原精神的雙重敍事與兩大情感基調,凸顯出典型的文學史意義。
其一,從儀式到文學與文學的獨立。招魂的祈禱式話語、實地祭弔的再現苦難式話語,原本出自於儀式,但一旦生成而定型,則獨立發展。宋玉《招魂》以儀式而生成,朱熹稱:“故宋玉哀閔屈原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猶古人之遺意也”。①〔宋〕朱熹:《楚辭集註》,第133頁。而《招隱士》也有以招魂儀式來“閔傷屈原”“以章其志”的意味。於是,文學史視宋玉等《楚辭》作家的出名不在其儀式行爲而在其文,所謂“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於是,便有劉勰稱文學發展了儀式文字,其稱作爲儀式的祝文本該“降神務實”,但《招魂》的“木夫九首,土伯三目”爲“譎怪之談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歡”爲“荒淫之意也”,稱《招魂》是主動追求“耀艶而深華”②〔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詹鍈 義證,第148、156、375頁。,具有充分的文學性。但至代屈原“立言”的自述式話語出現後,雖然是充滿儀式感但卻是脫離儀式而獨立的文學,說明文學是可以脫離儀式而獨立生成的。
文學脫離儀式的根本原因在於,作家以自我抒情言志而不是以儀式抒情言志。當賈誼過湘江以儀式祭弔屈原時就有“追傷之,因以自諭”③〔漢〕班固:《漢書•賈誼傳》,第2222頁。,故班固稱之爲“自諭”就是要獨立抒發情感;因此,司馬遷、班固稱賈誼的弔文爲“賦”,就是突出其“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性質。而到蕭統之時,文體辨析追溯起源,纔稱其爲“弔屈原文”。那些代屈原“立言”的作品,衹是受儀式感的驅動而創作,更是突破儀式、脫離儀式而成爲文學的自主獨立作品,不僅其抒情意義與文學性得以強化,更爲重要的是其作者的主體性凸顯出來。
其二,文學的魅力與對節日的引領。屈原祭弔、屈原紀念的祈禱式話語,再現苦難式話語,代屈原“立言”式話語,其靈感的源泉、構思立意的出發點,都是因屈原感發並承襲了屈原作品而生成話語體系的,對其起着引領與規範作用。於是,端午節本有的某些因素就被排斥而遺落了。例如,《隋書•地理下》載,端午節“二郡又有牽鈎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鈎初發動,皆有鼓節,群噪歌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其事亦傳於他郡”,令本來具有駁雜內容的端午佳節重塑爲屈原精神的節日敍事,規範、一統於屈原精神的弘揚與傳播上。如果不規範、一統於屈原精神,便得不到弘揚與傳播,如《鄱陽記》載:在五月五日競渡時,“刺史張栖真以人之行莫大於孝,懸《孝經》標竿上賞之,而人知勸俗,號爲懷蛟水,或曰孝經潭”,但至今已不見其蹤迹。
其三,“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爲屈原”。人們活動在現實世界裏,依想象做出了一系列的模擬行動,就能夠與古代的屈原在一起,把拯救美好事物的願望、與美好事物在一起的願望一起付諸於現實活動,屈原精神由此實現了最大化的傳播與弘揚。節日活動擴張了屈原精神的內涵與外延,也爲文學開拓出更廣闊的空間與更廣泛的受衆,産生出許許多多把屈原與端午節結合在一起的作品。端午節日,以大衆集體活動豐富、強化了對屈原的情感表達。節日敍事話語與文學話語不同,它是結合大衆的種種身體活動與行爲來抒發情感的,集體的身體活動比起“言”的文學話語更強化了情感抒發。節日活動的大衆參與,升級、升華了屈原精神的影響力,由此而令屈原精神有着更深廣的弘揚與傳播。
其四,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文學對於士人來說,擔當是第一位的,所以司馬遷《報任安書》稱“發憤著書”,韓愈《荊潭唱和詩序》有“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音易好”之說;那麽,屈原精神的節日敍事,其歡快樂觀的基調對文學則是另一種影響,即如何滿懷熱情、歡樂地去追求美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