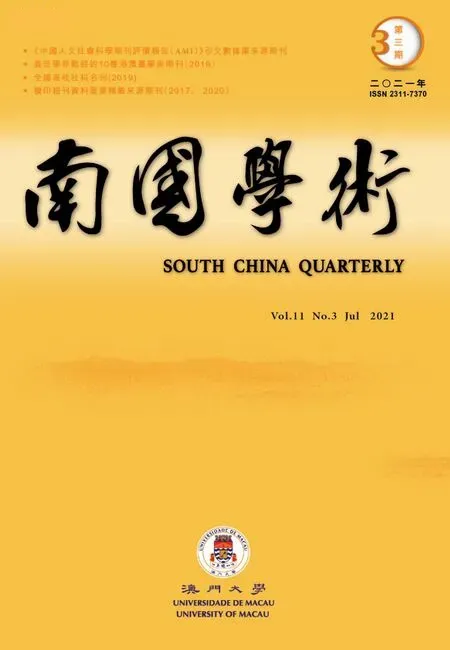海德格爾存在論滿足存在論需求了嗎?
——對新時代主客體關係的深層思考
2021-12-29王曉升
王曉升
[關鍵詞]存在論的需求 存在論 主體性 辯證法 海德格爾
儘管海德格爾(M.Heidegger,1889—1976)在政治上留下了污點,但卻並未妨礙人們對海德格爾哲學的熱情。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海德格爾哲學都是許多學者關注的對象。但是,海德格爾哲學決不可能與他的政治傾向無關。對這樣一個暗藏着法西斯主義傾向的哲學,人們的追捧一定包含了它的某種不爲人知的奧秘。如果海德格爾的存在論不能夠滿足人們的存在論上的需求,那麽,它也不會如此受到追捧。然而,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果真滿足了人們對存在論的需求了嗎?這種存在論的需求究竟是什麽樣的需求?在這種存在論的需求中是否存在着對哲學的一種錯誤期待?如果海德格爾的存在論不能真正滿足人們的需求,如果存在論的需求包含了一種意識形態要素,那麽,究竟應該用什麽樣的哲學來滿足人們的需求?社會應該如何端正它對哲學的需求?這正是本文想回答的問題。
一 海德格爾要滿足怎樣一種需求?
按照德國哲學家沃爾夫(C.Wolff,1679—1754)的說法,形而上學包含了四個方面的要素①[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賀麟、王太慶 譯,第4卷,第210—211頁。,存在論是其中之一。這表明,作爲哲學要素的存在論,它要給人們提供穩固可靠的東西。人們之所以有此期待,源於哲學自身的內在要求。按照康德(I.Kant,1724—1804)的說法,這是人的理性上的自然傾向②[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鄧曉芒 譯,第276頁。。由於人有這種自然傾向,所以就要追問最終的、最完備的東西。即使這種追求導致二律背反,人也不會放棄。儘管如此,哲學上所進行的存在論的建構也不是純粹理性上的行爲,也受到一定歷史條件的影響。比如,在中世紀末期,各種不同形式的存在論復興起來,它滿足了當時人們一種精神上的需要,即恢復秩序的需要;因爲,當時的社會秩序受到了挑戰。甚至在古希臘時期,也有類似的情況。③Theodor Adorno,Ontology and Dialectics (Cambridge:Polity Press,2019),151-152.海德格爾的存在論也是如此。如果它沒有滿足人們一定的需求,那麽,這種存在論就不會受到如此關注,甚至海德格爾政治上的劣迹也沒有阻礙人們對海德格爾哲學的熱情。
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不同時代的人們都有對存在論的需求,都有對穩固的東西的需求,但是,這種需求的具體內容是不同的。在中世紀末期,人們需要穩固的東西,是因爲這個社會的秩序面臨解體的危機;而在今天,海德格爾的存在論顯然不是要恢復“一種不需要意識加以確證的秩序”④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 (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8),Band 6,S.70.。這是因爲,在海德格爾的存在論中,“存在”概念是空洞的,沒有確定的內容。這個不可捉摸的存在,無助於恢復那樣一種確定的秩序。那麽,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在今天要滿足什麽樣的需求呢?或者說,今天的存在論需求有什麽樣的特點呢?
歐陸自啓蒙運動以來,主體和理性的作用被凸顯,但隨着現代文明的不斷發展,主體和理性卻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這表現在,人們在理性的旗號下懷疑一切,並藉此來確定主體的地位。由此帶來的惡果是,信仰被否定了,真理受到了懷疑,共同遵循的道德規範也失去了可靠性,人們生活在一種無根基的狀況中,甚至對生活的意義本身也産生了懷疑。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重新確立對真理的信念、對道德準則的信念,就成爲當代哲學的重要課題。這種惡果,使當代社會的人們産生了一種對可靠根基的渴望,而存在論的需求就是這種渴望的表現。海德格爾希望,通過存在論來確立人們對真理的信念,以生存意義的執著追求來滿足人們的需要。對海德格爾來說,這是要彌補現代社會中主體自身失落所導致的問題。
那麽,海德格爾提供穩固東西的方法是怎樣的呢?在觀念論中,思維的內容就是思維本身提供的。如果可能的話,它甚至努力把一切思維內容都從它自身中推導出來。當觀念論這樣做的時候,它就能夠像數學中的純粹演繹推理那樣,從觀念中設定條件,提出問題,並最終解決問題。這樣,觀念論就可以提供最終的、可靠的東西。但是,海德格爾試圖超越觀念論,始終不給“存在”下定義。他所說的存在,是指概念所不能把握的內容。也就是說,海德格爾要把握思維本身之外的某種內容,把握概念所不能把握的內容。這是海德格爾超出觀念論的地方。但是,海德格爾思想的根子卻沒有能夠離開觀念論。按照觀念論,世界上的一切東西都存在於它的觀念之中,或者說,一切東西都在它的觀念的掌握之中。而這種觀念論的企圖,從啓蒙運動以來達到了頂端,這就是把自然界中一切偶然的東西都置於自己控制之下,把一切不確定的東西都置於自己控制之下。啓蒙思想家認爲,衹要依靠科學技術,人們就能夠達到這種目標。而海德格爾吸收了現象學,吸收了這種具有科學精神的思路,用現象的直觀把握存在。雖然世界中有不能被概括在概念(在德文中,概念就是從把握“greifen”這個詞根中發展起來的)中的東西,但這些東西都被他把握在存在之中了。從這個角度說,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滿足了人類把握絕對的、最終東西的企圖。而這種企圖自啓蒙運動以來被極大地調動了起來。
當然,海德格爾的過人之處在於,他一方面像觀念論者一樣,試圖把一切都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另一方面又認爲,在他掌握之中的東西即存在本身還是不確定的。也就是說,他提供了一個可靠的答案,這個答案滿足了人們對絕對的、可靠根基的需要。但是,他又承認,這個答案之中包含了問題。對海德格爾來說,一方面他對哲學問題提供了最終的答案,但另一方面又認爲,這個答案中還包含了問題。這就意味着,他所提供的答案是以問題的形式出現的。
如果哲學的答案都是以問題形式出現的,那麽,哲學就不可能給人提供可靠的東西,也不能滿足人的存在論需求。一方面,海德格爾看到了問題與答案的關係,看到了哲學不能爲它所提出的問題提供最終的可靠的答案。另一方面,海德格爾又希望滿足人們對存在論的需求,希望提供可靠的東西。於是,海德格爾的辦法就是把問題本身絕對化。對此,阿多諾(T.W.Adorno,1903—1969)評論道:“存在論也受到先驗體系的不良影響。這種存在論按照過去的德國傳統,把問題看得高於答案。凡是這種哲學未兌現承諾的地方,它都從它那個方面把這種失敗安慰性地提升爲生存狀態。”①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Band 6,S.71,73.海德格爾在他的《存在與時間》一開始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存在的意義。可是,存在的意義在概念上是無法被規定的。也就是說,存在的意義的問題是沒有最終答案的。如果沒有最終答案,那麽,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怎麽給人提供可靠的東西呢?海德格爾的辦法是,追問存在的意義就是人的生存狀態,人是通過理解存在而生存的,“此在”的生存本身就是最終的、可靠的東西。在“此在”的生存中,真理就會展現出來,生存的意義也可以得到理解。對海德格爾來說,如果他的存在論提供了人的生存的可靠根基,那麽,現代性的問題就得到了解決。
二 海德格爾如何滿足這種需求?
海德格爾的聰慧之處在於,他獨闢蹊徑,繞過了主客體的二元論,繞過了精神與肉體的二元論,用追問“存在”的意義來回答人生的意義問題。於是,表面上看,他的這個回答就克服了近代哲學的缺陷,也滿足了人對於存在論的需求。
對海德格爾來說,“此在”的生存超越了主觀與客觀的對立,超越了觀念論與唯物論所確立的那種最終的可靠的東西。如果說,現代性問題是主體的極度擴張所產生的後果,那麽,海德格爾試圖直接超越主客體來克服這個缺陷,把存在(包括此在)變成超越主客體的第三者,通過這種超越來滿足存在論的需求。然而,這種超越,其實是通過一種獨斷論的方式來提供答案的。
海德格爾強調,此在是通過理解存在而生存的。他用“此在”(意爲“在此存在”。在這裏,他把特殊的存在者即“此在”存在論化)來取代主體。這種超越主體的做法,也是現代社會特點的一種體現。在現代社會,功能性聯繫已經取代了實體。一個東西本身的規定性不是由它本身所決定的,而是由它在功能性聯繫中所決定的。存在着的東西與它自身無關,而與他者有關。②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Band 6,S.71,73.功能性的聯繫決定了存在者的存在。於是,在現代社會中,主體作爲一種實體的地位被解構了,而功能性的聯繫開始取代這個實體。按照盧卡奇(G.Lukács,1885—1971)的分析,在這裏,人變成了功能體系中的角色。而存在就是在最抽象的意義上表達了這種功能性聯繫。當海德格爾用聯繫來取代實體的時候,存在作爲一種聯繫本身卻獲得了實體的特性,變成了超越主客體之外的第三者。
那麽,這個第三者是如何獲得優先性地位的呢?這裏包含了一種獨斷論的因素。海德格爾繞過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係,他要直接把握存在本身。在主客體關係中,主體是不能全面把握客體的。如果停留在主體和客體而試圖藉此給人們提供可靠知識的話,那麽,這一定存在着相對性的缺陷。這樣就無法滿足人們對於存在論的需求,無法滿足人們對可靠根基的需要。於是,海德格爾要把握主客體模式所無法把握的東西,把握不能被概念所把握的東西。在這裏,海德格爾藉助於胡塞爾(E.G.A.Husserl,1859—1938)的本質直觀和範疇直觀的方法來把握“存在”。本來,胡塞爾也想用直觀的方法來描述分類概念所不能把握的東西,但他最終還是拘泥於分類概念,試圖用分類概念來描述它所無法把握的東西。所以,阿多諾批評胡塞爾,既想吃掉蛋糕,又想保留蛋糕。①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Band 6,S.77,77,78,97,70.而海德格爾則不同,他放棄了被直觀到的東西與概念之間的聯繫。用阿多諾話來說,他“犧牲了與話語性的概念的聯繫”②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Band 6,S.77,77,78,97,70.,並因此而走向神秘主義。於是,對海德格爾來說,不能用概念來表示的存在直接顯現出來了(在這裏,我們姑且忽略“存在”概念與存在本身的關係)。這個自身顯現出來的東西,是不能用概念來描述的,是不能說的。如果一定要說存在是什麽,那麽衹能說存在就是存在本身。在這裏,“存在”模糊不清的特點已不是一種缺陷,而成爲一種優點,它直接把最根本的東西顯現出來。阿多諾曾經因此挖苦海德格爾說:“獨斷論成爲更高的智慧。”③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Band 6,S.77,77,78,97,70.對海德格爾來說,存在作爲最根本的東西是在人的生存之中直接顯現出來的。
儘管海德格爾的哲學有這種獨斷論特點,但卻顯得非常科學,因爲他藉用了現象學的方法,而現象學方法是實證主義方法的一個變種。本來,胡塞爾是想用嚴格的科學方法來把握真理的。而海德格爾卻藉助這種方法來提供某種可靠的、穩固的東西,使他的這種獨斷論似乎有了科學性。他不願意承認知識的相對性,把相對主義的批判推向極端,總是要找到最終的、基礎性的、穩固性的東西。④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Band 6,S.77,77,78,97,70.其實,人的認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海德格爾卻要繞過主客體關係,直接克服這種局限性,從而直接達到真理。這恰恰表現出一種獨斷論。
對於海德格爾來說,如果這種獨斷論要獲得成功,是不能依靠“常人”的。常人是沉淪在主客體關係中的人,這種人無法直接讓真理顯現出來,而衹有他說的那種此在,那種通過理解存在而生存的此在,可以在自己的生存中把真理顯現出來:“揭示活動本身的生存論存在論基礎首先指出了最源始的真理現象。”⑤[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陳嘉映、王慶節 譯,第306、307頁。“‘此在’在真理中。”⑥[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陳嘉映、王慶節 譯,第306、307頁。在這裏,此在不僅能夠把握概念所把握了的東西,而且能夠把握概念所不能把握的東西。於是,此在通過自己對存在的意義的理解而把真理直接展示出來了。海德格爾是要通過人的生存來滿足人們對存在論的需求。因爲,對他來說,“生存”總括性地預見到了“最高處的真實情況”⑦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Band 6,S.77,77,78,97,70.。
三 海德格爾果真滿足這種需求了嗎?
海德格爾把存在作爲優先的東西,從而滿足人們對可靠根基的需要。即如果人們把握了存在,就把握了根本的東西,就把握了真理,由此,通過理解存在的意義而進行的生存也就是有意義的生存。然而,海德格爾衹不過是虛假地滿足了人們的需求。這與他所提出的存在以及對“存在”意義的理解有關。
首先來看海德格爾的存在“概念”。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說:“‘存在’這個概念是不可定義的。”①[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7、6、64、80—82頁。理由是,“存在”這個概念是最高概念。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對“存在”概念屬性的另一個說明②[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7、6、64、80—82頁。。按照他的說法,“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但是,這個“普遍性”不是屬上的普遍性,即不是屬種意義上的那種普遍概念,是不能用概念來概括的東西,否則的話,海德格爾就可以用概念闡明“存在”了。在這裏,海德格爾還借用了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的說法來說明存在,即“無規定性的直接性”,如同人們通過感官獲得了關於某種東西的特殊的經驗。也就是說,某種東西的特殊性直接被提供出來了,但這種直接的東西是無法用概念來概括的。因此,這種東西就可以被說成是“無規定的直接性”。如果海德格爾的“存在”是這樣意義上的東西,是這樣一種無規定的直接性,那麽,這種存在顯然是無法滿足人們對穩定性的需求的。因爲,人們所獲得的這種直接的感性材料是稍縱即逝的東西,它不能給人提供可靠的基礎。當然,海德格爾的存在不拘泥於這一點,他所說的“存在”是指一切存在者賴以存在的中介。然而,問題在於,一切中介都是依賴被中介的東西存在的——“存在”是存在者的中介,存在者也是“存在”的中介。如果沒有存在者,“存在”就不再能作爲中介而存在了。可是,海德格爾的“存在”是把這個中介從被中介的東西中獨立出來。當“存在”從存在者中獨立出來時,“存在”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基礎,這個獨立於存在者的“存在”幾乎成爲虛構的東西了。而海德格爾恰恰是把這個“存在”獨立起來,使之獲得一種優先地位。這個具有優先地位的“存在”,就是要把這個無法被規定的東西作爲可靠的基礎。
其實,海德格爾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如果把存在作爲絕對第一的東西確立起來,那就陷入了他所批判過的形而上學。在哲學史上,各種形而上學都試圖提供絕對第一的東西。海德格爾試圖藉助存在者與存在關係的各種說辭來避免這種第一哲學的困境。可是,他不是在辯證法意義上強調兩者之間的依賴關係,而是從現象學意義上把存在作爲“無規定性的直接性”確立起來——存在首先是作爲獨立的第一的東西被確立起來。他也感到,如果這個絕對第一的東西被確立起來,勢必會毫無內容;於是,他又偷偷摸摸地以一種變換了的形式把存在者轉運到存在之中。然而,當海德格爾把存在者偷運到存在之中的時候,存在其實也就失去了他所期待的那種絕對第一性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海德格爾本人無法把存在作爲絕對第一的東西確立起來。所以,他也無法用某種穩固的東西、絕對可靠的東西來滿足人。
由於海德格爾的存在論還要滿足人們對生存意義的需求,因此,海德格爾強調,“此在”是通過理解存在而生存的:“此在的‘本質’在於它的生存。”③[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7、6、64、80—82頁。而人的生存,就是人的可能性的展開,即人在理解存在的過程中展開自身。從這個角度說,海德格爾也看到了,人的存在的意義是在人的生存的展開過程之中。海德格爾是從人的肉體與精神的統一中來說明人的生存的,試圖超越笛卡爾(R.Descartes,1596—1650)的身心二元對立模式來理解人本身和人的生存。這是海德格爾哲學克服近代哲學缺陷的一個重要嘗試。例如,在分析“在之中”的時候,他強調,這個“在之中”不是人在房間之中,不是水在杯子之中,而是此在的一種存在建構。海德格爾把這種“在之中”理解爲“居而寓於……”“同……相熟悉”④[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7、6、64、80—82頁。。海德格爾所說,其實就是人在世界之中的獨特的生存體驗。而海德格爾的“世界”,也不是我們日常所說的那種“世界”。它所說的這個“世界”是此在的一種存在方式,不是某種存在者存在於世界之中。如果從存在者存在於世界之中的角度去理解“世界”,那麽這是從日常的意義上去理解世界,是從主客體關係的角度理解世界。海德格爾的這個“世界”,是在人的獨特的生存體驗中所顯現出來的世界。其實,這個世界不是一個在人之外的某種實體,而是把自己融入這個世界之中。所以,這個世界嚴格說來應該叫“世界性”。在海德格爾對空間的理解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點。人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空間是人生活於其中的客觀的空間,但海德格爾不是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空間,而是從人的生存體驗中來理解空間。因此,他把空間理解爲“去遠”和“定向”。從這個角度來說,他所說的這種意義上的空間其實是人的一種空間體驗。因此,海德格爾對此在的生存結構的描述是從一種超越了精神與肉體的對立的意義上來理解人的生存,特別是人的生存體驗。海德格爾對於這種生存體驗的直觀描述是有一定意義的。
然而,問題在於,海德格爾把自己的這種研究與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學區別開來,並脫離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學來討論人的這些生存體驗。也就是說,海德格爾把他的存在論的研究與具體科學完全割裂開來。他說,如果要對“人是什麽”進行研究,那麽這種研究就必須見到“先天的東西”。而對於這種先天的東西的把握,是“先於”任何心理學、人類學和生物學的。①[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68、18、20頁。這樣,海德格爾就在人的研究中剔除了具有經驗意義上的東西、肉體意義上的東西。那麽,這個先天意義上的東西是什麽呢?我們可以從海德格爾對“生存”概念的理解中看到這一點。海德格爾說:“此在無論如何總要以某種方式與之交涉的那個存在,我們稱之爲生存。”②[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68、18、20頁。並且說:“此在由於以生存爲其規定性,故就它本身而言就是‘存在論的’。”③[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68、18、20頁。人要與存在打交道,當然也要與存在者狀態打交道,人由此而生存;或者說,人由此而獲得自己的特殊性。這是人的生存方式。但是,在海德格爾那裏,由於存在是從存在論意義上被理解的,於是,人與存在打交道就變成了“存在論的”。人有意識,人是存在者,當人的生存變成了“存在論的”時候,這個人就不是肉體意義上的人,而是純粹精神意義上的人。正是由於此在是這樣意義上的人,於是,這個人就可以勇敢地“向死亡存在”。因爲,海德格爾所說的這個“死亡”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死亡,而是純粹精神意義上的死亡。這就是說,雖然海德格爾試圖克服笛卡爾的二元論,強調人是精神與肉體上的統一,但是,他的存在論的研究最終還是讓他把人的生存精神化了,人的生存變成了脫離肉體的精神上的生存。當人的生存變成精神意義上生存的時候,海德格爾試圖在肉體與精神統一的意義上去理解生存意義上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失敗了。
四 海德格爾對虛假需求的虛假滿足
海德格爾提供絕對可靠的東西的努力不可能獲得成功,因爲人們永遠也找不到絕對第一的東西;如果沒有第二,絕對第一的東西永遠也無法被確立起來,但這並不妨礙人類在不同歷史時期對絕對第一東西的追問。那麽,在現代社會,人們爲什麽還要進行這種追問呢?爲什麽會產生這樣一種存在論上的需求呢?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來看,海德格爾存在論的提出不是孤立的,它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即人們存在着一種對存在論的需要。在現代社會,由於主體自身無限的自我膨脹,主體懷疑一切,甚至懷疑他自身的存在,因此需要從純粹的思想出發來論證自身的存在,把肉體與精神絕對地對立起來。當然,近代哲學所出現的主客體對立還是有歷史原因的。人類從誕生的一開始,就把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作爲自己生存的首要任務。在這種改造外在自然、控制外在自然的過程中,人越來越用自己的理性來改造自己的內在自然,甚至把自己的內在自然作爲自己的敵人。例如,人爲了認識外在自然和改造自然,需要藉助理性的方法,但人的感性的內容是與理性的原則相對抗的,衹好用理性的原則來改造人的感性的內容。也就是說,爲了改造自然,人還需要不斷地約束和改造自身的自然,越來越傾向於用理性的原則來改造自己的身體。在對人的身體的改造中,人的需求也會發生變化。而現代人對於存在論的需求就是在這種變化中發生的。
人無論是對物質的需求還是對精神的需求並不都是天然合理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種社會要素的影響。甚至人的最自然的需求也不是完全天然的,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上被塑造起來的。例如,食物的需求是天然的,但並不是任何一種能給人提供營養的東西都被當做食物,文化規定了什麽是可吃或不可吃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對文化上被規定爲不可吃的東西就沒有需求。反過來,人還會產生某種虛假的需求。例如,在現代社會,產能過剩成爲社會中的常態;爲了維持生產過程,社會必然會不斷刺激人們的需求。這也促發人們對某種看似有用、實際上無用東西的需求。這種需求就是一種“虛假”的需求。當然,這種需求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例如,一些人對時尚品的需求,其實就是對某種符號而不是對實際使用價值的需求。但是,這些時尚品也不純粹是符號,也有使用價值。但人們對時尚品的需求並不是爲了滿足對這種東西使用價值的需要,而是滿足對另一種東西如“面子”的需要。而時尚品也不會真正地滿足人們對“面子”(地位平等)的需求,而是給這種需求提供了一種替代品。一個真正有面子的人大概也不需要藉助這種替代品來維持自己的面子。這裏顯然存在着虛假的需求與虛假的滿足。正是由於社會阻礙了人們實現社會平等的可能性,使平等成爲不可被獲得的東西,而冒充卻是可以獲得的,於是,那些穿上時裝的人感覺自己與富人一樣,從時裝中獲得了一種虛假的滿足。
本體論的需求就是一種被文化所規定了的需求。在現代社會中,人被束縛在一種功能系統中,“合理化”觀念是這個社會中佔主流的觀念。如果按照此觀念來認識和改造社會,那麽,一切現象都可以找到最根本的原因,一切偶然的東西都可以在合理化的原則中被控制。而本體論的需求,就是對這種最根本的原因的追求。這種追求類似於人們對時裝的追求,背後是一種生存競爭原則在起作用。穿時裝的人感到,他們在生存競爭中成爲獲勝者。合理化的原則其實就是生存競爭原則的變種,所追求的是使一切東西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正如對時裝的需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樣,對存在論的需求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問題就在於,人們認識不到這種需求中所包含的不合理的要素。這就如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市場交換規律決定人的行爲,但人們卻認識不到或者不願承認市場交換規律決定了人們的行爲,他們還需要在市場規律之外的某種穩定性。這種對穩定性的需要,其實也包含了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要素,也是一種虛假的需求,是社會無法滿足的。因爲,現代市場經濟用一種新的秩序取代了傳統社會的秩序,如果今天還期望回到傳統社會的那種秩序,這是不可能的。而存在論的需求中對穩定性的需求就包含了這樣一種要素。
現代社會的發展不斷動搖傳統的秩序,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面對這種趨勢,人們產生了一種秩序的需求。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提供的秩序不是傳統社會的秩序,而是恢復到一種更原始(源始)的秩序。對他來說,在這種源始的秩序中,那些無法被概念把握的東西也被直接把握了。在這裏,人們貌似獲得了一種滿足,獲得了某種最源始、最根本的東西。其實,這是一種替代性的滿足。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秩序不斷被動搖,不確定性不斷增加。這是現代社會的標誌,它已經從根本上阻止了那種確定秩序的可能性。正如時裝不能使一個人成爲富人一樣,存在論也不能讓社會獲得一種穩定的秩序,它衹不過給人們提供心理的安慰。正如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對時裝趨之若鶩一樣,海德格爾的存在論也成爲現代哲學中的“時尚”。存在論如同時尚品一樣,給人提供了一種替代性的滿足。
現代社會以追求平等作爲自己的旗幟,但是,不平等卻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普遍出現。“時尚”就是這個現代社會中平等與不平等遊戲中的一部分。同樣的道理,社會越是趨向於不確定性,人們對於確定性的追求就越是強烈。海德格爾哲學的詭譎之處就在於,它總是用“畏”“無”等等不確定的東西來威脅人,而又讓人感到這種“畏”“無”已經完全在他的存在論的控制之中。他越是用這種東西來威脅人,人們對他的存在論的需求就越是強烈。所以,阿多諾說,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是按照受徹底毀滅之威脅的社會的眩暈形象而設計出來的”①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Band 6,S.100.。它總是不斷地提醒,人生活在毀滅性的威脅之中,現代技術的發展讓人處於毀滅之中。從這個角度來說,這種存在論是絕望和渴望的統一。顯然,如果威脅被消除了,人們對於存在論的渴望也就消除了。
於是,問題就在於,如何看待現代社會所出現的不確定性,如何看待真理被否定、價值被解構、意義被終結的狀況。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力的不斷進步,總是會不斷挑戰既定的各種秩序。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來說,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動搖上層建築,必然要對各種既定的秩序提出挑戰,任何想阻止這種趨勢的企圖都必然失敗。而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恰恰顯示了一種保守主義的文化趨勢。對他來說,如果人們回到這種源始的方式上,那麽存在就可以被直觀地把握。海德格爾的哲學趨勢就是要找到最穩固的東西,從而給不斷變化的社會中的人們提供支撐。然而,“如果一個人沒有受到外在或者內在的壓制,那麽他就不會尋找支撐,甚至也不會在自己本身之中尋找支撐”。①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Band 6,S.102.現代社會中的問題恰恰在於,人們的主體力量被削弱。
主體的力量被削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主體被束縛在功能系統中,成爲功能系統中的一個要素。二是在合理化的功能系統中,人習慣於用合理化的思維方式進行思考。在這種合理化的思維方式中,理性與經驗完全對立起來,身體與心靈完全對立起來。在這裏,理性的思考排除了任何肉體的、情感的要素。當然,這不是要否定純粹理性思考的意義,而是強調它必須與經驗的要素結合起來。冷冰冰的理性之中,還必須給肉體的要素留下空間。如果理性是純粹的理性,那麽理性所進行的系統性、邏輯性的思考甚至是計算機都能進行的工作。而包含了肉體的理性是一種創造性的理性。衹有肉體的力量纔具有自發性、不確定性和衝動的力量,衹有這種肉體上的衝動纔使理性具有了思想和意志力。如果沒有這種肉體的衝動,那麽,主體就是軟弱的主體、缺乏意志力的主體。現代的合理化社會恰恰把人變成了純粹理性的主體,變成軟弱的主體。這個主體在純粹思想的領域看起來力量無窮,其實軟弱無力。這種理性的主體被去主體化,變成了純粹理性系統中的一個要素。克服二元論的困難恰恰就是如何要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應該說,海德格爾在理論上也有這樣的思想趨勢,但卻不夠徹底。也正因如此,對他來說,“此在”作爲存在者是“存在論上的”。
五 如何真正地滿足真正的需求?
人們對存在論的需求,顯示了當今社會對哲學的一種錯誤期待。海德格爾存在論的流行表明,一方面,今天的哲學還不能滿足大衆以及學者們對哲學的渴望。另一方面,西方社會所出現的功能系統、社會的不確定性,在中國也出現了。於是,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學術界如何以真實的方式滿足人們對哲學的真正需求?或者說,如何建構自己的哲學來滿足社會對哲學的需求?
在這裏,主要討論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克服海德格爾哲學的缺陷來建構當代哲學,二是如何看待人們對哲學的需求。
從哲學理論的建構方面來看,海德格爾哲學試圖藉助現象學方法爲存在論的基本問題提供答案。他因此提出了存在,並把存在作爲源始的東西。這使他好像獲得了一個牢固的基礎,超越了傳統主客體哲學的局限性。其實,這不僅在理論上是一個倒退,而且也不能真正地提供可靠的根基。從哲學的發展來看,人類最初無法把主客體區分開來,無法把概念與概念所涉及的對象區分開來。這是人類最初的野蠻狀況。儘管海德格爾的這個源始是從存在論上來說的,而不是歷史意義上的,但這個存在論也不是完全脫離原始狀況的。這就如同海德格爾所說的存在那樣,儘管這個存在是區別於存在者的,但總是要讓人想到存在者;儘管存在是脫離具體的歷史的,但還是讓人想起原始的狀況。另外,海德格爾所提出的這個存在也是空洞的,是無法被規定的。所以,它表面上滿足了人們對穩定的東西的需求,但這個穩定的東西並不牢固。
從這個角度來看,現象學方法並不是給人們提供牢固基礎的有效方法。因爲,這種方法其實是從自然科學特別是數學方法中吸收過來的。它是要用自然科學的那種實證方法來解決哲學問題。而海德格爾所要解決的存在的意義問題,是無法用這種方法加以解決的。這是由存在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作爲存在論思考的對象,“存在”涉及的是概念所無法把握的東西。凡是可以用概念來把握的東西,都是存在者,是實證科學研究的對象,而存在是無法用概念來概括(嚴格來說,非同一的東西不能被概括,而衹能被綜合)的。如果能夠用概念來概括,那麽,海德格爾就非常容易地給人們解釋“存在”的含義了,存在的意義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人們可以像實證科學那樣用概念來描述、定義“存在”。但是,海德格爾卻排除了這種可能性。於是,存在的意義衹能通過此在的生存來加以解釋。解釋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涉及辯證法。所謂的解釋學循環,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總體與局部之間的辯證關係。但是,對海德格爾來說,“存在論衹有作爲現象學纔是可能的”①[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51頁。。由於他堅持現象學方法,他就無法從辯證法的角度來處理存在。既然存在是無法用概念來把握的,而人的思維又必須藉助概念纔能思考——無概念的思考就是所謂的純粹形象性的思考,衹是雜亂的感性材料在頭腦中的匯聚,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思考。所以,用純粹現象學的方法、純粹直觀地思考存在是不可能的。作爲一種辯證法,人們必須藉助概念,但又必須看到概念思考所存在的局限性。海德格爾的解釋學觸及這種概念的辯證法,但現象學的思路阻止了他走向辯證法。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海德格爾意義上的那種存在論是可能的,那麽,這種存在論必須是辯證法的。雖然辯證法不提供最終可靠的東西,但辯證法是逼近存在的有效方法,是逼近實證科學所無法逼近的東西的有效方法。
從主體的角度來看,海德格爾要給人們提供的最終可靠的東西,其實就是默認主體被弱化的現實狀況。如果主體足夠強大,那麽主體就不需要任何支撐。本來,海德格爾哲學是要批判現實的,批判現實社會中主體的發展所導致的主體弱化的情況,但當他尋找可靠的基礎時,又默認了社會現實,向社會現實低頭。在這裏,有人會說,海德格爾對常人的批判、對“此在”(特殊的個別存在)的崇拜表明,他也希望有足夠強大的主體。但是,這個強大的主體不過是在主體自身內部的自我確認。正如海德格爾所指出的,他的那個此在是“存在論的”。一個強大的主體不應是在主體內部的自我確認,而應是在主客體關係中來顯示主體的力量。而海德格爾在看到主體的弱點時,想要超越主客體,不願在主客體的相互作用中克服主體的弱點。對他來說,超出常人的人(此在)直接超出了主體,從而能夠真正地理解存在本身。也正因如此,海德格爾纔把此在的生存本身看做是真理,纔強調“此在在真理中”。雖然海德格爾哲學中的此在也要“操勞”,但這是作爲存在論的要素而被理解的,而不是在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中,從唯物主義角度去理解這種操勞。從這個角度說,脫離了主客體的相互作用來討論強大的主體總是有走向觀念論的危險。雖然海德格爾試圖超越觀念論,但觀念論的要素卻一直困擾着他。
在當今社會,主體已被弱化,成爲功能系統中的一個要素。要改變這種狀況,既不是要放棄主體,回到某種源始狀態,也不是要把主體變成“存在論的”,而是要在主客體的相互作用中提升和反思主體。對這種主體的理解是一種新的唯物論,它不否定主體的作用,也不是把主體變成純粹理性的主體,而是馬克思(K.H.Marx,1818—1883)、恩格斯(F.Engels,1820—1895)所說的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②[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卷,第73頁。這個人纔是主體。當然,這種新的唯物論對主體的強調也不是要否定客體,不是把主體從客體中孤立起來,成爲純粹思想上的自我決斷的主體。這是建構新的存在論的基礎。但是,這個存在也不是物質同一性意義上的存在。如果這樣來理解存在,那就重新回到蘇聯教科書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了。而海德格爾所說的存在,是超越存在者的存在,所意味的東西是無法用概念來表達的。儘管我們也可以使用“存在”這個概念,但它不能像海德格爾哲學那樣以肯定的形式出現,這是非同一性的東西。而海德格爾的問題是,把非同一的東西納入具有同一性特徵的“存在”概念之中,而不是從否定性的角度來理解存在。當他這樣做的時候,把握非同一東西的道路也被他堵塞了。
這種對非同一性東西的把握,也是科學發展的要求。科學的方法就是,用概念來把握自己所面對的對象。但哲學研究卻告訴人們,在概念所把握的對象之外,還有概念所無法把握的東西,這是非同一的東西。正如海德格爾所指明的那樣,這種非同一的東西(存在)可以動搖傳統科學基本概念,推動科學的發展。海德格爾的錯誤在於,這種非同一的東西仍然可以按照實證主義的傳統(現象學是這種傳統的變種)來把握。當辯證法被理解爲用概念來把握非同一東西的時候,這個辯證法也就克服了其詭辯論的缺陷。
當然,辯證法由於不能給人們提供穩固的東西、不能滿足人們對於存在論的需求而受到質疑。然而,現代社會的不斷發展使從前被看做是理所當然的東西都受到了質疑,所以纔會用“日新月異”來說明所發生的急速變化。這種變化對人們的心理也產生了巨大的衝擊,產生了一種害怕過時的心理恐懼,求新求變成爲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這種對不斷變化的追求本身,也會使變化越來越形式化,如同時尚用品一樣,以純粹形式的變化來適應時代的變化。科學研究也同樣如此,本來是要不斷追求創新,要把握非同一的東西,但現代人卻把創新形式化,使“新”變成純粹形式性的東西。例如,過去一直強調經濟基礎在社會中的決定地位,但被謬稱爲“經濟決定論”,被人當做過時的“舊”,於是有人就“創新”出“文化決定論”“制度決定論”等等。從“經濟決定論”到“文化決定論”“制度決定論”。“決定論”的基本思路沒有變,同一性的思維方式沒有變,非同一性的社會歷史要素被納入到同一的思想框架之中。這就如同時裝設計師的系列時裝一樣,既然有時裝系列,當然也可以有“存在論”系列。如果沒有對“非同一東西”更切近的把握,那麽,任何一種所謂的存在論也必然會成爲“時尚”。它可以虛假地滿足人們對存在論的需求,就好像時裝滿足了人們趕時髦的心理追求。
而這種對時尚的追求、形式的變革,也必然會使人們產生一種對“無根基”的恐懼,面臨“深淵”的恐懼,必然會使人們尋找某種可靠的基礎。而這種對可靠基礎的追求,就會走向所謂保守主義乃至復古主義。人們在追求時尚與復古主義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徘徊,這使海德格爾存在論給兩個極端之間的人們提供心理上的安慰有了生存空間。在今天這個功能化的世界中,由於一些人失去了主體性,失去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決斷的能力,因此,存在論的任務不是要給人們提供任何形式的安慰劑,不是要給人們提供一個避風港,不是要鼓勵人們隨波逐流,而是要激發起人們自我反思的精神和能力。而這種反思能力不是自我純粹的內在反省獲得的,而是在與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在對非同一的東西的自覺意識中獲得的。衹有當人們意識到非同一的東西,人們纔不會走向保守主義或者趕時髦,纔會更加堅定地探索真理、追求真理,雖然這種真理不會像現象學所祈求的那樣通過直觀而被把握。這就是哲學給人們提供的可靠根基。沒有唯物論、辯證法,這種可靠的根基是不可能的。在當代,社會越是系統化、功能化,不確定性就越是突出;人們越是想全面地控制世界,這個世界就越變得無法控制。承認世界的不確定性,承認世界上存在無法被把握(控制)的東西,並不是要屈服於這種東西,而是在承認它的合理性的同時,提升主體的反思和實踐能力。
如果從解決現代性問題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那就是,不放棄主體的作用,不恢復到某種源始的狀態,在主體與客體的矛盾中,在主體(包含了肉體的主體)的反思中,不斷克服矛盾。哲學不可能給人們提供一勞永逸的真理,如果它真要提供這種東西,那麼所提供出來東西就會像海德格爾那樣,是空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