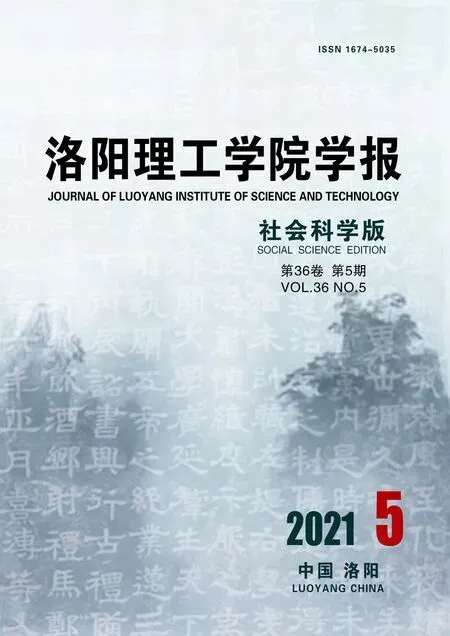论中晚唐文人的“隋堤柳”书写
2021-12-28李静
李 静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唐以前,柳树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意象。《诗经·小雅·采薇》已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离别意象;陶渊明作《五柳先生传》,以柳自比,柳与高尚品格挂钩;六朝的柳树,不仅如人一样依依有情,而且被纳入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与人一起成长,与社会一起盛衰,是一个活泼完整的生命主体[1]。作为文学意象的柳,出现频率非常之高且意蕴丰富。中晚唐是“隋堤柳”作品出现的高峰期,并且多以感慨物是人非、怀古伤今为主题,“隋堤柳”被赋予亡国之意。
一、运河两岸的“隋堤柳”
隋炀帝时期共修筑4条运河即永济渠、汴河(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并在河畔修筑御道,树之以柳。但只有通济渠和邗沟两岸的御道被称作“隋堤”,道上所植柳树称之为“隋堤柳”。
“隋堤柳”的著名与汴河、邗沟重要的交通地位有关。《隋书·食货志》云:“(隋炀帝)始建东都……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2]686但《隋书》所载并没有明确说明汴河的流经路线。唐人李翱的《来南录》详细记载了他于元和四年(809)从洛阳出发,乘船由洛入河、由河入汴、由汴入淮的过程。书中提到汴河两岸的地名有:汴州、陈留、雍丘、宋州、永城、甬桥、泗州。然后李翱“假舟,转淮上河,如扬州”[3]6443。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的 “汴州”“宋州”“宿州”“泗州”条均有汴河流经的记载,与李翱所记吻合。隋唐的汴河流经线路自汴州以东河阴县的黄河之口,经宋州、宿州、泗州入淮水。但汴河并不直达江南地区,想要沟通南方,还需依赖邗沟的运转。邗沟虽短,却十分重要,江淮物资只有经过邗沟才能到达京城。《旧唐书·崔融传》记载:“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4]2998可见汴河与邗沟交通运输之繁荣。
“隋堤柳”是指汴河和邗沟两岸的柳树。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云:“汴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5]307李吉甫所说的“御河”“御道”较为模糊,汴河入泗达淮,而江都宫在江都(扬州),汴河不可能自江都宫入海,必然经过邗沟。李吉甫的记载显然是将邗沟省略了。又白居易《隋堤柳》诗云:“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6]427根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扬州在京师东南2753里,至东都1749里[4]1572;汴州在京师东1350里,东都410里[4]1433。由此可见,扬州至汴州的距离约为1300里,与白居易诗中“绿阴一千三百里”的说法吻合。因此,唐朝文人所吟咏的“隋堤柳”指的是汴河和邗沟两岸的柳树。在唐宋诗词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叙述:
平明择钵向风轻,正及隋堤柳色新。(皎然《送僧游扬州》)
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枝杨柳不胜春。(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其六)
扬子江头烟景迷,隋家宫树拂金堤。(刘禹锡《杨柳枝》)
日照蒹葭明楚塞,烟分杨柳见隋堤。(许浑《送上元王明府赴任》)
隋堤杨柳烟,孤棹正悠然。(温庭筠《送淮阴孙令之官》)
舳舻溯隋堤,积潦涵楚甸。(陈舜俞《遇便风》)
参差歌吹动离舟,宫女张帆信浪流。转尽柳堤三百曲,夜桥灯火看扬州。(刘子翚《汴堤》)
隋堤旧事无人问,两两垂杨系客舟。(王阮《北固山望扬州怀古》)
二、中晚唐文人的“隋堤柳”吟咏
李德辉在《唐代交通与文学》中指出了唐代文人及第与未登第者在考试后的不同流向,“屡试不爽者,其中部分人放弃了举业退隐园林,或改而出家,或学道游方,经商南北,另一部分则奔走于方镇使府间以求职谋生,部分人下第后拜访亲友,到处漫游,发展社会关系,以图再起,最常去的地方是扬、益两大经济都会”[7]32。唐代文人东出长安后,往往自洛、汴上船至淮南、两浙,甚至江西、岭南等地区,有些往返于长安与荆楚、巴蜀之间的文人,也多取道运河,至扬州而入长江。如李白浮游四方,北抵赵、燕,西涉邠、岐,历商於,至洛阳,南游淮、泗,再入会稽,而家寓鲁中,故往来齐鲁间,前后10年中唯游梁宋最久[8]1594。其长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有“东浮汴河水,访我三千里”[8]750,虽写魏万浮汴千里寻访李白的不易,但却是李白自己一生漫游、往来运河之间的真实经历。崔颢离开家乡漫游20年后,经汴水返回汴州,留下了《晚入汴水》之作:“昨夜南行楚,今朝北溯河。何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晴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9]433白居易得罪权贵,仕途几度沉浮,终于长庆四年(824)五月罢杭州刺史,取道江南运河、邗沟、汴河返回洛阳。面对久违的故土河流,白居易有感而发:“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绕身新眷属,举目旧乡关。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见山。啼襟与愁鬓,此日两成斑。”[6]515
除此以外,运河也带来了城镇和商业的繁荣。洪迈《容斋随笔》云:“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10]123王建的《寄汴州令狐相公》写有“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秋日梁王池阁好,新歌散入管弦声”[11]3406,描绘了一幅汴河之上商船南来北往、茶馆桥市兴盛、商业一时繁荣的画卷。《汴路水驿》中“晚泊水边驿,柳塘初起风。蛙鸣蒲叶下,鱼入稻花中”[11]3390则描写了汴河夜景,与白天两岸的繁忙喧嚣不同,柳塘上吹来的微风、蒲叶下的蛙声、稻花中的游鱼令人感到汴河夜晚的静谧与美好。温庭筠在扬州逗留期间,孙令沿运河乘舟北上,温庭筠作《送淮阴孙令之官》赠之,诗云:“隋堤杨柳烟,孤棹正悠然。萧寺通淮戍,芜城枕楚壖。鱼盐桥上市,灯火雨中船。故老青葭岸,先知虙子贤。”[12]684该诗描绘了一幅隋堤两岸杨柳繁茂如烟,白昼桥市热闹喧嚣而夜晚雨中灯火闪烁的风景图画。
悠悠运河,舟来车往,或载着闯南走北的商人游子,或载着出游玩赏的达官显贵,或载着失意落寞的文人墨客,他们感受过运河的晨昏午夜,记述着沿岸的寒来暑往。“隋堤柳”作为运河两岸的独特景观,自然成为承载人们特殊情感记忆的载体,随之进入文人的视野,成为吟咏的对象。皎然的《送僧游扬州》抒发了留别愁绪之情:“平明择钵向风轻,正及隋堤柳色行。知尔禅心还似我,故宫春物肯伤情。”[11]9225王建的《汴路即事》写道:“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11]3391此诗记录了诗人的所见所闻:千里长河、青槐夹岸,奔波于运河之上的人们来自天南地北,说着各自家乡的方言,草市、津桥等交易场所不仅有江货,还有来自海外的海商,贸易往来十分兴盛。诗人虽重在突出运河的繁荣之景,但结尾“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使整个诗笼罩着一种物是人非的惆怅伤感之情。
三、“隋堤柳”的亡国意象
隋炀帝好大喜功,在位时大兴土木,奴役人数以百万计,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最终国破人亡。因穷奢极欲而亡国的隋炀帝一直是唐朝人所批判和引以为戒的对象。处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唐朝文人乐观而向上、积极而进取,整体呈现出一种昂扬蓬勃的精神面貌。短命的隋王朝的历史教训并不能影响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反而以更加饱满、更加热情的姿态迎接挑战。所以充满着衰颓凋零气息的“隋堤柳”难以进入初盛唐文人的视野。目前可考最早借“隋堤柳”怀古伤今的诗歌是盛唐时期王泠然所作的《汴堤柳》:
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穿地凿山开御路,鸣笳叠鼓泛清流。流从巩北分河口,直到淮南种宫柳。功成力尽人旋亡,代谢年移树空有。当时彩女侍君王,绣帐旌门对柳行。青叶交垂连幔色,白花飞度染衣香。今日摧残何用道,数里曾无一枝好。驿骑征帆损更多,山精野魅藏应老。凉风八月露为霜,日夜孤舟入帝乡。河畔时时闻木落,客中无不泪沾裳。[11]1173
尽管初、盛唐时期咏“隋堤柳”警醒世人的作品只有王泠然一篇,却能窥见唐朝人对隋炀帝开凿河道、游幸江都而最终“功成力尽人旋亡”的批判态度,为后人吟咏“隋堤柳”提供了范本。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藩镇割据问题十分严重。唐宪宗即位后,“以法度裁制藩镇”[13]3190,并发动兵力讨伐。从元和元年(806)讨蜀始,到元和十五年(820)成德镇王承宗病死后,其弟王承元上表归降止,唐宪宗结束了自代宗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13]3240的局面,史称“元和中兴”。然而,“元和中兴”只是唐王朝政治上的一次回光返照。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这内外两大矛盾使国家长期处于一种特殊微妙的状态,整个社会都处于“风飘飘兮雨萧萧”的欲倾之势中。元和时代的文人虽渴望中兴、积极参与政治,但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兴表面下蕴藏着的社会矛盾与危机。怀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美好愿景的文人士大夫却因官小位卑无法左右政治局势,甚至会因进谏而遭到贬谪。这些敏感又脆弱的文人士大夫,悼念昔日的繁华美盛,而现实使他们感到无限哀伤与落寞;憧憬中兴,期待中却夹杂着对梦想的焦灼与迷惘。政治理想的破灭与仕途的坎坷加剧了当时文人的危机感和焦虑感。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正是在这种满怀期望与痛苦的复杂的时代氛围中长大成人的。白居易创作《隋堤柳》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带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性,其在诗题小序中就开门见山地点明诗歌主旨——“悯亡国也”。白居易正是看到了国势的日渐衰微,敏锐地感受到唐王朝即将步隋亡的后尘,才会用“悯亡国也”如此沉重之语警戒当朝统治者。《隋堤柳》既是白居易出于谏官职责所作,也是白居易发自内心的所感所想。全诗如下: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煞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酅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6]427
白居易开头先写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的枯萎残败的现状,追忆大业年间下令开凿河道、夹岸种柳的盛况,“绿阴一千三百里”“柳色如烟絮如雪”与如今的凄凉冷落形成鲜明对比。接着点明隋炀帝大兴土木导致财力衰竭、上荒下困,宗社之危迫在眉睫,然而炀天子却视若无睹,自言福祚无穷而实则自欺欺人,以致亡国,客死他乡。“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曾经盛极一时的王朝已化作尘土,而隋堤两岸的柳树两百年来朝朝暮暮屹立在这里,经历一轮又一轮的人歌人哭。白居易在诗歌最后总结“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至此,“隋堤柳”不再是文人笔下批判隋炀帝开凿运河时的附属品,而是王朝盛极而衰的见证者、亲历者。李山甫《隋堤柳》云:“曾傍龙舟拂翠华,至今凝恨倚天涯。但经春色还秋色,不觉杨家是李家。背日古阴从北朽,逐波疏影向南斜。年年只有晴风便,遥为雷塘送雪花。”[11]7362言明隋堤柳的荣枯变换象征着朝代的更迭,曾经煊赫一时的隋炀帝化作一堆白骨葬于雷塘,而如今日薄西山的李氏王朝和隋朝又有何分别?罗隐也认为唐王朝已然步上隋朝后尘:“夹路依依千里遥,路人回首认隋朝。春风未借宣华意,犹费工夫长绿条。”[11]7553
韦庄生长于晚唐,前后经历过藩镇割据、黄巢起义等混乱政局,忧国忧时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光启二年(886)夏,韦庄时隔3年再次经行汴堤,然而“朝见西来为过客,暮看东去作浮尸。绿杨千里无飞鸟,日落空投旧店基”[11]8022,尸浮于水,骨暴于野,曾经绿阴千里的隋堤柳竟然连一只飞鸟都没有,荒凉无比。其《过扬州》云:“当年人未识兵戈,处处青楼夜夜歌。花发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风多。淮王去后无鸡犬,炀帝归来葬绮罗。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11]8021锋镝鸣响,往昔的二十四桥“处处青楼夜夜歌”,尽是风花雪月之景,如今却一片空寂凄凉,只剩下静静流淌的大运河和河边饱受摧残的绿柳。两首诗歌均借隋炀帝战争之事,暗示唐末的烽火连天与山河破碎。韦庄的《河传·其一》也表现了繁华旧事、今非昔比、人去楼空之感:
何处,烟雨,隋堤春暮。柳色葱茏,画桡金缕,翠旗高飐香风,水光融。
青娥殿脚春妆媚,轻云里,绰约司花妓。江都宫阙,清淮月映迷楼,古今愁。[11]10078
昔日隋炀帝驾龙舟巡幸江都,运河之柳色朦胧,锦帆过处,香闻千里,而今行宫冷清破败,只有清冷的月光仍照今楼。烟雨凄迷的现实与隋炀帝在江都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今昔对比的表现手法更能抒发唐朝文人吊古伤今之意与盛衰兴亡之感。汪遵《汴河》云:“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还待春风锦帆暖,柳荫相送到迷楼。”[11]6955同样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永恒的运河之水和春之柳色与人的有限的生命形成对比,抒发了诗人岁月变迁、物是人非的惆怅之情。古人认为,水是万物之本原,人的生命与水息息相关。而柳在古诗词里又有象征春天之意。两者的结合会引起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顿生“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经过此地的文人墨客都亲眼见证了唐王朝从繁华跌入动荡、由兴盛走向衰亡的社会现实,充分体会到时局变化之大、落差之大。诸多士人以恢复盛世为己任,面对风雨飘摇、摇摇欲坠的国家,在诗中自然流露出忧国伤时、吊古伤今的情感。
文人曲调的使用强化了亡国意象。韦庄所使用的《河传》一调,创始于隋炀帝开运河所制之劳歌也。宋王灼《碧鸡漫志》引《脞说》云:“水调《河传》,炀帝将幸江都时所制,声韵悲切。”[14]176可见《河传》创制之初,其基调就是悲切哀伤的,再加上隋炀帝身死国灭的凄惨下场,其内蕴更加悲痛凄厉。韦庄以《河传》为词牌写隋堤柳,其用意可见一斑。同样的,还有以《杨柳枝》为题的诗作。《杨柳枝》古题所谓《折杨柳》,唐玄宗开元年间入教坊曲,经白居易、刘禹锡整理改编,依旧曲作词,翻为新声。《杨柳枝》一曲原意是抒发离别行役之情,但中晚唐文人创作了大量讽鉴隋炀帝开河栽柳、劳民伤财以致亡国的《杨柳枝》作品,逐渐奠定了《杨柳枝》为亡国之曲的审美内蕴。如刘禹锡《杨柳枝词·其六》:“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株残柳不胜春。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15]360又《杨柳枝》:“扬子江头烟景迷,隋家宫树拂金堤。嵯峨犹有当时色,半蘸波中水鸟栖。”[15]562何光远直接将《杨柳枝》归为“亡国音”的范畴,其《鉴诫录》云:“《柳枝》者,亡隋之曲,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号曰隋堤,有是曲也。胡曾咏史诗曰:‘万里长江一带开,岸边杨柳几千栽。锦帆未落西风起,惆怅龙舟去不回。’又韩舍人咏柳诗曰:‘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那堪更想千年后,谁见杨花入汉宫’。”[16]164
到了晚唐,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已是积重难返,唐王朝的没落不可逆转。此时文人关于“隋堤柳”亡国意象的写作甚至连一丝警示意味都没有了,而是对即将亡国的直白的慨叹。吴融《隋堤》云:“搔首隋堤落日斜,已无余柳可藏鸦。岸傍昔道牵龙舰,河底今来走犊车。曾笑陈家歌玉树,却随后主看琼花。四方正是无虞日,谁信黎阳有古家。”[11]7904叛乱频起,昔道牵龙舰,今来走犊车,当年的盛况与今日的萧条形成强烈对比,一个国家正在走向消亡,而当朝统治者依旧沉浸于歌舞升平的幻象之中,吴融既感慨痛心却又无可奈何。又如秦韬玉《隋堤》云:“种柳开河为胜游,堤前常使路人愁。阴埋野色万条思,翠束寒声千里秋。西日至今悲兔苑,东波终不返龙舟。远山应见繁华事,不语青青对水流。”[11]7659方壶居士的《隋堤词》:“当意江都大业秋,曾随銮跸戏龙舟。伤心一觉兴亡梦,堤柳无情识世愁。”[11]9749运河和隋堤柳又一次见证了一个王朝的盛衰与覆灭。
四、余 论
中晚唐文人的“隋堤柳”书写在后世有着颇为广泛的影响。五代十国时期的文人名士与中晚唐文人面临着相似的社会环境,不少文学作品延续了“隋堤柳”的写作手法和文化内涵。“隋堤柳”成为他们吟咏的对象。毛文锡《柳含烟·其一》云:“隋堤柳,汴河旁,夹岸绿阴千里。龙舟凤舸木兰香。锦帆张。因梦江南春景好,一路流苏羽葆。笙歌未尽起横流,锁春愁。”[11]10087词中主要使用了今昔对比手法,上阕写汴河隋堤,绿阴千里,隋炀帝乘龙舟锦帆,游幸江都的奢靡盛况;下阕写笙歌未落,横流尽起,隋王朝遽然灭亡的悲惨现实。词作写隋堤柳寄寓盛衰兴亡的惆怅之感,具有一定的讽刺借鉴意味。此外还有江为的《隋堤柳》“锦缆龙舟万里来,醉乡繁盛忽尘埃。空余两岸千株柳,雨叶风花作恨媒”[11]8448,翁承赞的《隋堤柳》“春半烟深汴水东,黄金丝软不胜风。轻笼行殿迷天子,抛掷长安似梦中”[11]8092等。隋堤年年柳色新,而一个又一个王朝在变换的柳色中崩塌湮灭于历史的尘土之中。朝代的更迭无法影响隋堤柳的生长,但是国家兴亡、世事变迁会影响时人看待隋堤柳的心态与眼光。
北宋又进入到承平盛世,北宋人的“隋堤柳”吟咏以抒发离愁别绪为主,如张先的《江南柳》、周邦彦的《兰陵王·越调柳》等。金兵南下,宋室南迁。汴河为金人所把控,逐渐枯涸淤塞,几与岸平。后代的文人虽也借“隋堤柳”喻古今兴亡事,却不如中晚唐及五代时期如此密集。
总的来说,中晚唐文人面对山河破碎的国家,不复盛唐时的浪漫进取精神,变得清醒、焦虑,充满忧患和批判意识,这种心态反映到诗歌创作上就形成了“隋堤柳”独特的亡国意象。“隋堤柳”的吟咏,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文学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