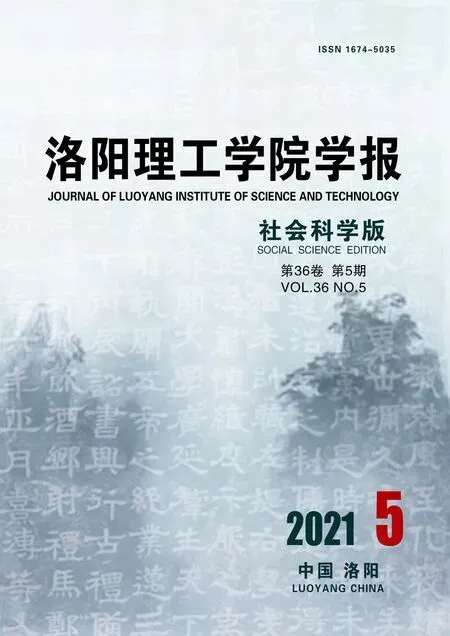论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三重维度
2021-12-28刘寒菲
刘 寒 菲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马克思理论活动最初指向的是共同体与人的自由实现的关系问题,这从他在“莱茵报”时期钟情于以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来观察人的自由的实现就可以明确地看出。但是,在“莱茵报”时期的后期,因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与摩泽尔河畔农民贫困的现实,使得马克思窥见物质利益问题所决定的某种客观的社会关系对观察法与政治国家等社会问题的制约作用。由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产生了基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到底是谁决定谁的“苦恼的疑问”,这发端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基于主奴关系辩证法所讲的苦恼的意识——奴隶劳动基础上所造成的自由的自我意识在绝对自由的普遍性与个体自由的特殊性之间因分裂而不能够实现统一而产生的痛苦的情绪。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黑格尔的苦恼的意识在市民社会所诉求的个体自由(利益)与政治国家所代表的普遍自由(利益)之间矛盾的现实表现。围绕着“苦恼的疑问”的释疑,在共同体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在黑格尔所窥见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的矛盾现实并力图通过伦理国家(伦理共同体)的创建以消除这一矛盾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共同体”(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资本家共同体”(商品交换形成的“货币共同体”的最高阶段)、“自由人的联合体”(无产阶级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等概念,并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内在矛盾及其扬弃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论考察;另一方面,马克思从个体利益与共同体利益之间是对立还是统一关系的性质的意义上提出了“虚假的共同体”(个体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对立)与“真正的共同体”(个体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统一)的概念,并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扬弃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论考察。总体而言,首先马克思以法哲学分析的立场考察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经由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者间关系的反思,证实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从而在对政治解放造成市民社会(诉求的是个体自由与利益)与政治共同体(代表共同体的普遍自由与利益)分离的认识的基础上,指出政治解放还不是最终的人类解放,它必须发展为人类解放。这是因为,政治解放实现的是有产者的特殊的私人利益,它所确立的政治共同体是人与人对立意义上的虚幻的共同体,而人类解放代表的是真正的普遍利益,它所确立的共同体是人与人之间自由的、平等的联合劳动意义上的真正的共同体。而由于法哲学考察是对法、政治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考察,因而马克思若想对政治共同体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分析,则必然绕不开以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对“资本家共同体”进行考察,即通过对构成资产阶级社会运行的矛盾焦点——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的考察,指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货币共同体”的最高阶段——“资本家共同体”是非永恒的,其内在矛盾驱使它由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最终将被自由人的劳动联合体所扬弃。法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坐标式”结合,最终使得马克思以历史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把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一“人体解剖”看作是对以前生产方式的“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强调共同体的演变是生产方式变迁基础上的展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自然史的过程。其肯定阶段就是,在自然生产力的支配下由血缘关系所决定的个体与共同体自然的浑然统一的自然共同体;其否定阶段就是,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体现的交换价值的发展最终造成个体与共同体分裂基础上的货币共同体(其最高阶段是资本家共同体);其否定之否定就是资本家共同体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促成自由的联合劳动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一、政治共同体的法哲学考察:诉求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统一的真正共同体
马克思对政治共同体的法哲学考察源于他最初所钟情的黑格尔伦理国家观与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之间的冲突。黑格尔的伦理国家理论所要解决问题的核心就是将国家看作绝对精神在为实现这一政治共同体社会中普遍利益与私人特殊利益以及客观自由与个体的主观自由相统一的符号。初涉世事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的影响,针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对人的自由的轻蔑,强调“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1]217。然而,思想总是被物质利益所纠缠,林木所有者对林木的利益与贫苦农民对枯树枝生活依赖的生存权利之间的冲突使得映照在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身上的理性光辉顿时黯然失色。但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打算放弃黑格尔的伦理国家,即使他将该理论斥为“下流的唯物主义”,仍寄希望用该理论来解决私人利益冲突带来的问题。随着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发现政府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即虽然承认摩泽尔地区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却没有真正力图从根本上改变种植者贫苦的现状而只是试图缓解他们的贫苦现状时,开始在理应代表普遍利益的政治国家与实则代表个别利益的市民社会之关系问题上陷入了“苦恼的疑问”,即对普遍利益与个别利益能不能实现统一而发出的疑问,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自由的自我意识由于自身分裂为普遍性与个别性而不能统一所讲的“苦恼的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再现。此时马克思已朦胧地意识到对于国家法的研究,不能用人的意志来解释,而必须重视人的意志背后的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对于这种决定社会关系的客观本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把它明确为私人利益。由此出发,马克思着眼于私人利益,开始追问共同体(现代国家)构成的基础、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中个体成员之间及其作为其表现的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关系。
对于共同体(现代国家)构成的基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指向为私有财产。其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所指出的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事实表示赞赏,但并不苟同黑格尔以共同体(政治国家)来统摄市民社会的主张,相反,他看到的是颠倒过来的事实,即市民社会(私人财产、私人生活)对政治国家(国家制度、政治生活)的决定,也就是说,政治国家作为共同体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中个体成员的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使得世俗社会发生了分裂,过去依附于政治国家的市民社会从现代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经济共同体,而现代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2]172确立并保障市民社会成员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以及私人利益。伴随着现代政治国家的建立,市民社会成员也完成了双重身份的确立,一方面是现代政治国家中参与政治生活的“公人”,另一方面是市民社会中进行着经济生活的“私人”。因而个体过着双重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是“天国的生活”,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的生活”,个体是“尘世存在物”。“天国的生活”以抽象的自由人权为原则,个体作为抽象的公民被吸纳进去,因而是“唯灵论”或是虚幻的;“尘世的生活”以现实的利己主义为原则,个体作为私人等级而自发组成,因而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还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只是私有财产的解放,因而在人的普遍解放与物的丰富关系上发生了颠倒,也就是说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私有财产因封建羁绊的打破而随着个体自我意识的张扬而膨胀,而政治国家鼓舞的就是这种以自由人权为核心的原子式的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因而,政治国家只是市民社会成员在政治上的共同参与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目的是保护市民社会成员个体的私人利益。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批判的继续。马克思从中着眼于政治解放所造成的普遍利益(共同体所维系的)与特殊利益(个体所诉求的)对立,对资产阶级政治共同体的“乌托邦式的梦想”进行了批判,指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是作为市民社会的一部分的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以社会的普遍解放的名义自己解放自己,结果是,政治解放所确立的政治共同体就是虚幻的,它只能实现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而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普遍利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汲取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关于自我意识欲望(需要)相互满足而形成整体性事业并从这种整体性事业获得自身的发展的思想的基础上,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利益的虚假性。这一虚假性的根源在于“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2]296,资本是雇佣工人进行整体性的共同性劳动的根源,也是资本家共同地进行自由竞争的力量所在。但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事实却没有如同国民经济学家所描绘的遍地自由竞争与普遍交换的那般,而是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支配造成了劳动的异化。因而,在自由竞争与普遍交换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普遍意识只是追求资本私人利益的现实生活的极端抽象,而这种抽象恰恰是与资本追逐私人利益而造成的劳动异化这一现实生活相敌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曾明确表示,由于国家是建立在以普遍利益与私人利益矛盾的基础上,所以,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仅仅是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它无法真正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普遍利益,而只能在形式上消极作为。于是,国家的虚幻性连同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全都暴露无遗。马克思正是洞察到了现代国家是以私人生活的冲突为基础建立的,是资本家共同体的现实代表,因而指出工人不能在资本家共同体内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享受的人的本质,马克思希冀的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2]394而真正的共同体则是个人利益平等地实现的共同体,而不是个人之间利益对立而相互反抗的共同体。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把建立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政治国家称之为“虚假的共同体”[1]199,因为它是阶级对立中的联合,强调要实现共同体所维系的普遍利益与个体所诉求的特殊利益的真正统一,就必须消灭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及其所确立的雇佣劳动,在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共同体”[1]199。这一主张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22的“联合体”。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集中体现的资本家共同体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关系,论证联合劳动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对资本家共同体的扬弃,以诉求普遍利益与个体利益的有机统一。
二、资本家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追问联合劳动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1848年欧洲革命后,基于对现实问题的考量,马克思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蕴含的矛盾进行全方位剖析,其关注点逐步转向专注研究政治经济学,“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3]597。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从实质上讲就是论证资产阶级所创造的“资本家共同体”的内在矛盾——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能动的矛盾关系所造成的雇佣劳动的异化及其异化的扬弃,最终指向联合劳动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对资本家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源于“德法年鉴”时期的《论犹太人问题》,其指出资产阶级政治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市民社会的原则是个人需要与自私自利。在创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过程中,马克思明确提出“资本家共同体”[2]296的概念,指出“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2]296,反对国民经济学家单纯地把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理解为有产与无产之间的对立的做法,明确强调必须把有产与无产的对立理解为资本与劳动的能动的对立关系,即能动的矛盾关系。马克思的这一立场受到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奴关系劳动辩证法的深刻影响。主人把生产资料交给奴隶去陶冶事物,通过奴隶的劳动间接地尽情地享受物质,而奴隶陶冶事物的劳动使得他的潜在的主观任性的自由意识转化为独立的自由的自我意识。而资本与劳动间的能动的矛盾关系就是,资本作为“主人”依靠作为“奴隶”的工人的劳动来增殖财富,而工人却在劳动中不仅丧失了自己所创造的劳动成果,而且也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与现实性,也就是说,资本所驱使的劳动发生了异化,但与此同时,异化劳动使得工人也意识到了自身的“非现实性”处境。马克思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异化劳动理论的论证来激励工人自觉地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来扬弃资本所造成的异化劳动。由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形成整体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意识,消灭资本统治下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自由的联合劳动中实现劳动的自主性。
对于资本与劳动的能动的矛盾关系,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明确地表述:“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1]343对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了更为具体的界定,作为活劳动的雇佣劳动是同自身相对立且以作为异己的权力存在的资本的劳动。这一界定揭露了雇佣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是替作为价值的资本这一死劳动增值的,它在赋予资本死劳动以活的灵魂的同时发生了异化,资本作为支配劳动的权力在积累财富的同时,雇佣劳动作为活劳动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但是,资产阶级社会是以生产交换价值——货币为目的,因此,从形式上讲,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4]178而随着交换价值的发展,资产阶级社会作为“货币共同体”的最高形式,掩盖了这一形式下所隐藏的资本与劳动交换的不平等性。这就是说,从使用价值的交换的角度讲,雇佣劳动和资本都是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形式,二者之间在形式上遵循着商品交换的最一般的规定,即自由与平等的交换。但是,马克思对此做出了更高明的见解,他认为这本身是一个颠倒的现实而必须对其加以重新审视,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活动实质上存在着两个质上不同且前后相继的过程:其一是劳动力作为商品,在买卖市场上双方作为特殊的使用价值进行着形式上平等的交换;其二是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活劳动作为使用价值,通过自身生命力的消耗从而作为一种生产力来保值与增值资本,而资本的使用价值则转换为对由雇佣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的无偿占有。这两个先后的过程清晰地演绎了商品所有权规律所遵循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转换为资本所有权规律所遵循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4]463。这里,“异己性的否定”讲的就是工人劳动自主性的丧失,也是工人劳动不幸之所在。所以,当亚当·斯密发出劳动是不幸的而不劳动才是幸福的感叹时,马克思深刻地感受到现代工人劳动不幸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因而,唯有消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唯有彻底铲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即完结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的旧式的分工与私人性质,继而实现以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劳动的科学性(自主性的劳动)与社会性(联合劳动)相统一的真正的共同体,才能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共同体作为社会力量失去了它的政治性质因而不再是政治力量,而作为失去政治性质的“社会力量”就是无产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通过联合劳动所形成的社会整体的力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表达了对罗西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所说的“最完美的自愿联合”的赞赏。马克思专门做了如下引用:“社会的进步不可能在于解散任何联合,而在于以自愿的、公正的联合来代替过去时代的强制的、压制的联合。……最完美的是自愿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团结一致而增强了力量;同时对个人力量来说,既不能排除它的能力,也不排除它的道德感和责任感。”[4]593马克思把这种“自愿的、公正的联合”称之为“真正的共同体”。
三、共同体生产方式基础的历史主义分析:由血缘共同体到货币共同体再到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指出:“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者注)的真实历史。”[4]453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的永恒性与自然性作辩护,竭力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历史性予以否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4]452,这使马克思敏锐地感觉到,不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真实的历史与发展进行阐述,就不能从根本上颠倒国民经济学家将历史终结于自由与平等的交换制度这一定位的愉快想法,因而也就不能真正搞清楚资本主义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马克思“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就是考察和推断资本的生成条件与生产条件以及资本生产条件未来的先兆——“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4]453。换句话说,就是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与未来走向。这里,马克思曾把对资本的生成条件与生产条件的考察比喻为“人体的解剖”,把对孕育资本的胎胞的封建社会的考察比喻为“猴体的解剖”,前者是理解后者的一把“钥匙”。这就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经济社会形态问题所遵循的历史主义方法,其基本观点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立足于个人总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是阶级关系与利益的承担者的论断。马克思主张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自然史的过程,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它有其生成、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并且它既是以此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也是预示着自身作为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即预示着未来的先兆。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不仅表现在为学术界所熟知的关于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社会生产关系)演变的“五形态说”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交往方式演进的“三形态说”的表述中,而且还表现在为学术界所不熟知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立足于劳动者与不同的生产条件的关系所形成的共同体的演变表述的“三种历史状态”的提法。第一种历史状态的表现形式为“劳动的个人把土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劳动、而生产的”[4]490,其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由原始的公有制演变成奴隶制与农奴制;第二种历史状态是“劳动者把工具看作是它自己的东西,……劳动者作为工具的所有者来进行劳动”[4]491,这种历史状态随着交换价值的不断发展而在封建社会晚期城市内部的行会制度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第三种历史状态是劳动者“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4]109。
在第一种历史状态下,劳动者以土地作为自然的生存与生产条件,因而,建立在人与土地关系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由于其地域性与交往的狭窄性,在社会关系上造就的是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的依赖关系。最初,土地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劳动者基于血缘与种族关系相互依赖而形成部落共同体,人作为某个部落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并以共同体为中介,共同耕作土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天然的或部落的共同体,这是共同体的原生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只是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4]477然而,马克思指出,这种天然的或部落的共同体“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4]488,进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与解放,或部落共同体之间的利益争夺,演变成天然共同体的逐步瓦解及奴隶制与农奴制的兴盛,这是共同体的次生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与农奴作为活的劳动能力,“作为这种生产的客观条件被人占有,因而是奴隶或农奴”[4]491。或者说,“奴隶同他的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4]481。于是,土地的劳动者与私人占有者就有了明确的区分。然而,不管是天然的或部落的共同体,还是其解体而成为的奴隶制与农奴制,都是在对土地进行劳作的基础上存在着的,以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由此造成的是人的生产在狭窄的范围内孤立地进行,因而就决定了人的生存状态最初形式是“人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把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的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称之为“古代共同体”[4]178。
第二种人类历史状态最初是“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4]491。这种生产方式最初是行会同业公会制度,行会师傅作为劳动主体成为工具的所有者,并且雇佣有学徒与帮工;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演变推动人类历史的迈进,使得人类历史演变为第二种历史状态。而伴随着行会同业公会制度的发展,货币以其作为财富的储藏手段、商品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及其流通的规定而迅速膨胀,“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4]175,与交换价值直接相关的商人与高利贷者等逐利群体也应运而生。这就是说,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代表导致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内容的古代共同体的次生形态——封建社会没落的同时,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货币共同体在其城市内部得以产生。货币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把劳动者变成了生产的客观条件的一无所有者,也就是说,劳动者与生产的客观条件相分离,最终“导致劳动市场的形成”[4]503。
资产阶级社会是“货币共同体”的最高形式。随着货币关系发展到“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4]105,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的一般意义(马克思称之为简单商品交换)上讲,“每个个人作为货币的所有者,他本身都经常在进行着交换价值的交换,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4]106。这种以建立在货币占有为基础的社会权力同社会联系对于作为主体的人而言,就是其相对于社会的个体的独立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进步性,即形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新的演变,展现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第二大形式且只有到18世纪才逐步趋向成熟,表现为每个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由此,马克思把货币这一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视为一切人的共同产物的“现实的共同体”[4]178。然而,比国民经济学家更为机警地嗅到这一问题的是,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交换并不是如表象那般体现为一般商品之间的交换,而是将会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与资本进行交换,也正是这种交换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根本的矛盾源泉,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作为统治阶级整体体现的资本家共同体与作为被统治阶级整体体现的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焦点,因为雇佣劳动生产的使用价值是作为交换价值来进行生产的,而资本作为“酵母”激发着雇佣劳动的生命活力如机器一般为其创造交换价值,资本无偿地占有雇佣劳动所创造的交换价值中的新价值,这种矛盾导致劳动发生异化——资本财富增值的同时劳动在贬值。与此同时,这一矛盾又必然会使引发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劳动者购买力不足之间的对立,其结果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爆发。
马克思指出,一方面,经济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非人类生产方式的最终形态,“而只是历史的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的有限发展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5]462。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将成为向自由的联合劳动这一新的组织形式过渡的历史起点。因此,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资本家共同体的基础上,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共同享受自身劳动成果的第三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产形式将会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