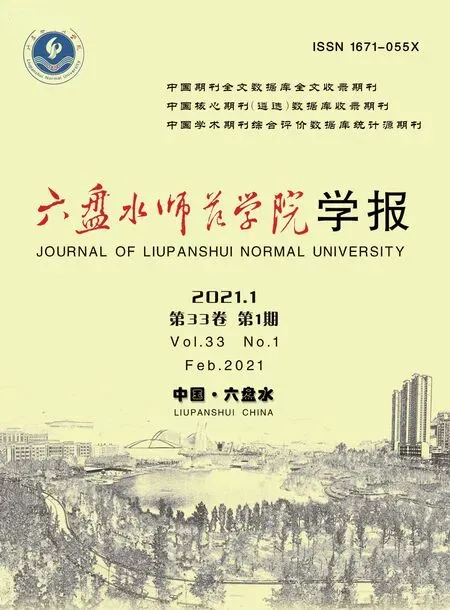孟浩然的摇摆人生及其形象的误读
2021-12-28杨和为卫佳
杨和为 卫佳
(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贵州六盘水553001)
盛唐诗人孟浩然(689—740)因其仕隐矛盾而倍受关注,但其身份定位一直存在争议。闻一多先生说他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1]28。乔象钟、陈铁民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史》认为:“孟浩然并非纯粹的‘隐逸诗人’。”[2]301有人说他是“以隐为仕”“读书、隐居是为了求仕,漫游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求仕,他应举是为求仕,献赋也是为了求仕。……积极求仕,贯穿了他的一生”[3]43。有学者提出折衷的意见,认为孟浩然隐逸思想与仕进思想并存,“仕进思想是他思想的主流,而隐逸思想只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4]40-42。此外,也有学者说他“终生在亦仕亦隐中痛苦前行”[5]84-88。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在推进孟浩然研究的同时未免失之笼统,在方法论上亦未能做到动态的把握。
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或隐居鹿门,泛舟洞庭,或干谒求仕,赴京应举,或漫游吴越,归卧襄阳,或爽约韩朝宗,入幕张九龄,进退出处之间,好像杂乱无章,难以把握。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孟浩然不过是在仕隐两极之间摇摆的诗人罢了。可以说,“摇摆”是打开孟浩然矛盾世界的一把钥匙。正如日本学者芳村弘道所说的,孟浩然“既心怀脱俗的愿望,同时又不舍为官的志向。……诗人摇摆于脱俗与出仕两个极端层次上。于是,诗人便将摇摆幅度内的所有一切均吟诵于诗作之中”[6]40。不过,芳村弘道只指出孟浩然在“脱俗”与“出仕”这两极之间的摇摆性,未能深入挖掘诗人在人生轨迹、日常生活、禀性趣尚及思想倾向等层面的摇摆性,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一、孟浩然的人生轨迹:在求仕与慕隐之间摇摆
从整个的人生轨迹来看,孟浩然既不是一个完全的隐士,也不是一个汲汲于功名富贵的俗人,而是在求仕与慕隐两极之间摇摆着的一个状态。当其摇摆状态尚未发生的早年,就其本心来说应是慕隐的。我们从孟浩然早年的《题鹿门山》不难窥见其慕隐的本心:“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纷吾感耆旧,结缆事攀践。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探讨意未穷,迴艇夕阳晚。”[7]66刘文刚先生认为这首诗“标志着浩然独特的诗风基本形成。……诗对庞德公表示的景慕之情,说明浩然隐居鹿门有坚实的思想基础”[8]12。此外尚有《夜归鹿门寺(歌)》《听郑五愔弹琴》《初春汉中漾舟》《岘山作》《赠道士参寥》《张七及辛大见寻南亭醉作》《与诸子登岘山》《北涧浮舟》《过融上人兰若》《山潭》等诗,描写家乡的自然风物,清幽醇美,清旷脱俗,可以说都是他的慕隐本性的自然流露。
种种迹象表明,孟浩然之所以动念求仕,开始在求仕与慕隐之间摇摆,很大程度上跟好友张子容有关。据《唐才子传》载:“子容,襄阳人,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仕为乐城令。初,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为死生交,诗篇唱答颇多。”[9]60约作于708年的《寻白鹤岩张子容颜处士》诗,仍在表现隐居生活的单纯的妙处:“白鹤青岩半,幽人有隐居。阶庭空水石,井(当作“林”)壑罢樵渔。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疏。睹兹怀旧业,迴策返吾庐。”[7]40但数年之后,情势悄然发生了变化。张子容于先天元年(712)冬进京赴举,孟浩然作诗相赠:“茂林余偃息,乔木尔飞翻。无使谷风诮,须令友道存。”[7]298虽然孟浩然仍以一个幽居的隐士自命,但对于友人的赴京应举,心里已有点不是滋味,“偃息”“飞翻”云云,说明孟浩然内心已然波动。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孟浩然25岁的时候,隐逸的本心犹占上风。但到了开元五年(717),也即孟浩然29岁的时候,因为行将而立,加上“家贫亲老”,他仕宦的愿望开始变得强烈。作于是年八月的《岳阳楼》一诗,被认为是他早年干谒岳州刺史张说的重要诗篇:“八月湖水平,含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7]132诗将写景和干谒杂糅在一起,多少有点不伦不类,但其实正可表明孟浩然摇摆的开始。自那以后,孟浩然就在求仕与慕隐两极之间摇摆起来,原先相对静态的隐居状态被打破了。
一旦孟浩然萌生求仕之心并开始行动,便免不了与自己慕隐的本心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便是在仕隐两极之间摇摆不定,终其一生都是如此,而他的所有诗作都只是在此摇摆幅度内的产物。大概是因为“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7]212的家境,加上“三十而立”的儒家信仰,三十岁之后,孟浩然求仕的愿望愈加强烈,所作诗篇多流露怀才不遇的感慨,并渴望得到位高权重者的举荐。《书怀贻京邑同好》云:“三十既成立,吁嗟命不通。……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7]212《田园作》诗亦表达了求仕的强烈愿望:“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冲天羡鸿鹄,争食嗟鸡鹜。……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7]458开元八年(720)暮春,孟浩然在襄阳抱病,“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翼”[7]207-208,当死亡的阴影随疾病降临,孟浩然因仕途不达而心生恐惧。开元十三年(725),37岁的孟浩然前往洛阳,栖身白社。遗憾的是,赴洛数月,除了结识贺知章、袁仁敬、卢鸿一、包融等文人学士外,仕途毫无任何转机,心情遂变得黯然失落。是年秋,孟浩然前往洛阳香山寺访湛然,《寻香山湛上人》诗云:“平生慕真隐,累日求灵异。……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7]3“平生慕真隐”一句,跟几年前的“执鞭慕夫子”“冲天羡鸿鹄”已有所不同,显示出此时的孟浩然因干谒无果而向着慕隐一极摇摆的思想动态。让人意外的是,心无坚守的孟浩然不久之后就又向着求仕一极摇摆了。开元十五年(727)冬,39岁的孟浩然赴京应举,主动寻求机遇,而不再像先前那样将希望寄托在干谒名流显宦上。如我们所知的,孟浩然竟然落第,这应该是诗人最感到屈辱的一次求仕经历,成为他此后十多年拂之不去的一个心结。
落第之后的孟浩然在长安继续献赋,乃是向着求仕一极摇摆的惯性使然。开元十六年(728)九月,献赋仍无任何回音,孟浩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渐渐又萌生出慕隐与归家的念头。既说“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7]145,又说“跃马非吾事,狎鸥宜我心”[7]134。开元十七年(729)寒食卧病李氏家中,归隐之念愈炽:“我爱陶家趣,园林无俗情。……伏枕嗟公干,归山羡子平。”[7]437其后孟浩然漫游吴越,直到开元二十年(732)五月才回到襄阳,开始了隐居家园的日子。《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邑》诗云:“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徵君。……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7]425-426从求仕到慕隐的摇摆昭然可见。孟浩然在乡园隐居的日子,不乏抒发隐逸生活的佳作,《登望楚山最高顶》充分表达了诗人对于襄阳风物的热爱:“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7]94《过故人庄》则显示出诗人归隐乡园的至高境界,历来被视为孟浩然田园诗的代表作:“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7]439但这样的隐逸生活并没过多久,孟浩然就又向着求仕一极摇摆了。作于开元二十一年(733)新年的《田家元日》流露出无禄尚农的思想:“我来(年)已强仕,无禄唯尚农。”[7]419到了这一年的秋天,可能是因为张九龄在位的缘故,让他又看到了求仕的希望,遂再次萌生求仕的念头。约作于本年冬的《送丁大凤进士举》说:“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弃置乡园老,翻飞羽翼摧。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7]294孟浩然在求仕之念的支配下,第二年(734)春夏时节就再上长安求仕了。但依旧未获成功,于是孟浩然再次向着慕隐一极摇摆。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他前往终南翠微寺游玩,《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一诗又吟出慕隐的调子:“翠微终南里,雨后宜返照。……遂造幽人室,始知静者妙。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7]48岁末回到襄阳,作《岁晚归南山》诗,其中“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7]428数句,正说明孟浩然再次从求仕向慕隐摇摆。经过这一次的铩羽而归,他似乎看透了求仕不果的必然性,决意以隐者的形象终老,是以爽约韩朝宗。按照摇摆的惯性,他的求仕也好,慕隐也好,都只是短暂的存在状态,持续时间一定不会太长,就会自然而然向着另一极摇摆,这才是真实的孟浩然。纵观孟浩然一生轨迹,由早年的隐而求仕,到中年的求仕不得而慕隐,再到晚年的入幕荆州与辞归养病,看似复杂,其实不过是在仕隐两极之间反复摇摆而已。
二、孟浩然的日常生活:在出游与归家之间摇摆
孟浩然“放情山水,喜作漫游”,终其一生,经常辞乡远游,“东到吴越,西至巴蜀,北上长安、洛阳,南下三湘、赣江。足迹所至,几达半个唐帝国,而且其中很多地方还三番两次游历过”[8]前言3。从诗作看来,孟浩然的生活相对比较简单,大略可以分为出游与归家两个方面,发而为诗,也多在此摇摆的幅度之内。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早年孟浩然虽家住襄阳涧南园,因为热爱襄阳的秀丽山水,读书之余也常常游山玩水,寻访僧道友人,“在襄阳周围,特别是襄阳以南广泛漫游”[8]前言3。孟浩然集中较多出游的诗篇,且多以归家收束,这构成孟浩然诗的一大特色。如游岘山的《与诸子登岘山》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7]23游万山潭的《(万)山潭作》云:“垂钓坐磐石,水清心益闲。……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7]43游鹿门山的前引《题鹿门山》《夜归鹿门寺(歌)》即是。诗人还常常四处寻访僧道逸人和待举士子,如与王迥交游的《游精思观迴王白云在后》云:“出谷未停午,至家日已曛。……衡门犹未掩,伫立望夫君。”[7]92-93又《同王九题就师山房》云:“晚憩支公房,故人逢右军。……归途未忍去,携手恋清芬。”[7]226寻访西山兰若明禅师的《题明禅师西山兰若》云:“西山多奇状,秀出倚前楹。……日暮方辞去,田园归治(冶)城。”[7]70寻访景空寺融公的《题融公兰若》云:“谈玄殊未已,归骑夕阳催。”[7]122游凤林寺的《游凤林寺西岭》:“共喜年华好,来游水石间。……莫愁归路暝,招月伴人还。”[7]489访逸人别业的如《夏日浮舟过张逸人别业》:“水高凉气多,闲棹晚来过。……幽赏未云遍,烟光奈夕何。”[7]123寻访待举士子的《寻白鹤岩张子容颜处士》云:“白鹤青岩半,幽人有隐居。……睹兹怀旧业,迴策返吾庐。”[7]40皆是其摇摆于出游与归家之间的明证。
第二,中年之后的孟浩然更是经常辞乡远游,有时漫游或达数年之久。前引干谒张说的湖湘之游可以说拉开了远游的序幕,此后游历的地方越来越远,“足迹所至,几达半个唐帝国”[8]前言3。《孟浩然集》中虽有在家闲居而渴望远游的诗篇(如《晚春卧病寄张八》),但更多的却是远游在外而思归的作品,这可以说是孟诗最鲜明的特色。开元十六年(728)诗人赴京应举,才到长安就想着及第回家,《长安早春》结尾云:“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7]299其后应举不第,遂漫游吴越,而多思归之辞。如《初年乐城馆中卧疾怀归作》:“往来乡信断,留滞客情多。……归来理舟楫,江海正无波。”[7]397又《永嘉别张子容》:“旧国余归楚,新年子北征。”[7]323《溯江至武昌》:“家本洞庭上,岁时归思催。客心徒欲速,江路苦邅回。”[7]248《归至郢中》:“远游经海峤,返棹归山阿。日夕见乔木,乡关在伐柯。”[7]278诗人漫游吴越数年之久,终于回到襄阳家中,又过了一段时间隐居乡园的生活,如《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云:“予亦何为者,栖栖徒问津。……归来当炎夏,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7]425-426除此而外,另有北游京都而思归返家的诗篇,如《答秦中苦雨思归而(赠)袁左丞贺侍郎》:“泪忆岘山堕,愁怀襄水深。……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7]134
即使是他暂时归隐乡园的诗篇,亦可见其在出游与归家之间的摇摆性(当然摇摆的幅度较小)。出游在外的如《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7]439《登望楚山最高顶》:“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暝还归骑下,萝月映深溪。”[7]94闲居在家的如《裴司士员司户见寻》:“府僚能枉驾,喜醖复新开。……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谁道山公醉,犹能骑马回。”[7]421我们发现,孟浩然既不能长时间闲居在家,也不能长时间漫游于外,终其一生都是在出游与归家之间摇摆。
三、孟浩然的禀性趣尚:在好静与躁动之间摇摆
关于孟浩然的禀性趣尚,朱起予先生曾在《孟浩然隐逸趣尚论》一文中有过论述,他认为孟浩然具有“好静慕隐的性情”,并借此说明其“疏淡简远的诗风”形成的原因[10]45-50。朱先生提出这一说法是在二十多年前,难免有一定的局限。事实上,孟浩然不仅有“好静慕隐”的一面,也有“躁动随性”的一面,或者说,他的性情常在“躁动随性”与“好静慕隐”之间摇摆,这样的说法也许更贴近真实的孟浩然。
说孟浩然性情具有“好静慕隐”的一面,估计一般人都不会反对,因为这在他的诗里多有表现,如《云门兰若与友人同游》:“谓予游迷方,逢子亦在野。……所居最幽绝,所佳皆静者。”[7]9-10《(万)山潭》:“垂钓坐磐石,水清心益闲。”[7]43《涧南即事贻皎上人》:“弊庐在郭外,素产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朝市喧。……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7]434-435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慕隐的趣尚,《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友》即是。又如《寻香山湛上人》:“平生慕真隐,累日求灵异。……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7]3当然,最能表现他“好静慕隐”一面的,还是他早年写鹿门山的两首诗,“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樵径非遥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夜归鹿门寺》),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1]29
“好静慕隐”只是孟浩然性情之一面,在他身上还有“躁动随性”的一面,但不易为人所察觉。《新唐书》本传说他“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11]5779,似乎能看出一点躁动而非好静的影子。相较之下,王士源的说法也许更接近真实的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灌园艺圃以全高。交游之中,通悦(脱)倾盖,机警无匿(疑)。”[7]557其中“散”字很关键,是说孟浩然“不受拘束、潇洒自然的样子”[12]103,也就是说,孟浩然的性情并非一味好静,还有不受拘束、随性放情的一面,所以王士源又说他“救患释纷以立义”,这跟《新唐书》本传的说法意思相同。王士源在序文中,还提及孟浩然的为人,“行不为饰,动求真适,故以(似)诞”,也即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虚伪,一举一动都不装饰,待人很真诚,以致在世俗的人看来好像有点放诞。所谓“似诞”,实际上正是随性放情的表现。王序又说他“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是说孟浩然的交游不是为了某种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是随着自己天性的自然,喜欢谁就是谁,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很洒脱也很随性。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孟浩然何以会爽约韩朝宗了。此事件王序载之甚详:“山南采访使太守昌黎朝宗,谓浩然闲深诗律,……先扬于朝,约曰引谒。后期,浩然叱曰:‘业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久(夕)不赴,由是闻(间)罢。既而浩然不之悔也。”[7]557按闻一多先生的解释,孟浩然不会为了韩朝宗而背弃庞德公,但在我们看来,这恰是孟浩然性情中有“躁动随性”一面的明证。正因为孟浩然有此性情,开元二十八年(740),当诗友王昌龄遇赦来访的时候,他才会不顾背疽尚未痊愈而与之浪情欢谑,最终“食鲜疾动”而卒。《孟浩然集》中大量的宴饮赠答诗也为我们的推测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如我们所知的,孟浩然常常参加各种官员文士的雅集宴会,如《襄阳公宅饮》云:“手拨金翠花,心迷玉红草。谈天光六义,发论明三倒。座非陈子惊,门还魏公扫。荣华应无间,欢娱当共保。”[7]389《寒食张明府宅宴》云:“瑞雪初盈尺,闲霄始半更。列筵邀酒伴,刻烛限诗成。……醉来方欲卧,不觉晓鸡鸣。”[7]387-388颇能窥见诗人喜欢热闹的性情。除此而外,我们从孟浩然送人从军及醉后赠人的诗里,也不难发现诗人并非一味地好静慕隐,而有一种豪侠壮逸的气概,如《送王宣从军》:“才有幕中士,宁无塞上勋。隆兵初灭虏,王粲始从军。……平生一匕首,感激赠夫君。”[7]450可以说,孟浩然兼有好静慕隐与躁动随性这两个面向,并随着周遭环境(政治形势与交游对象)与仕隐心念的变化而在此两极之间摇摆,当其渴望求仕或热衷宴集时,便向着躁动随性一极摇摆,而当其求仕受挫之后,则又本能地向着好静慕隐一极摇摆。需要注意的是,正因为孟浩然常在求仕与慕隐之间反复摇摆,其禀性趣尚亦相应地在躁动与好静之间反复摇摆,这才是孟浩然真实的状态。
四、孟浩然的思想倾向:在儒家与释道之间摇摆
孟浩然在行为方式上的摇摆,本质上而言跟他在思想倾向上的摇摆性密切相关。刘文刚先生认为:“孟浩然的思想相当复杂。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他都有明显的影响。他谙熟释道经典,喜欢谈玄。曾表示要皈依佛门,……又向往成仙,……可是,对他一生发生决定影响的,却是儒家思想。”[8]前言5这话大抵不错,但失之笼统。在我们看来,与其说孟浩然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倒不如说他其实是在儒家思想和佛道思想之间摇摆更为切近,其中,儒家思想是刺激他积极求仕的根本动力,一旦求仕受挫,则本能地逃向释道与山水,以实现心理的自我疗愈。无论是对于儒家思想,还是对于佛道思想,孟浩然其实并没有很深的见解,更多的只是与代表儒家入世思想的官吏士人和代表释道出世思想的僧人羽客交往密切,并在不同时机和不同对象面前表露出诗人在某一个方面的热爱与倾慕而已。
早年在襄阳隐居读书的时候,孟浩然就同时表现出对儒家思想和释道思想的热爱,尚处于摇摆之前的萌芽状态。一方面,他与弟兄们一起闭门读书,《洗然弟竹亭》说:“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7]543或跟襄阳那些待举的士子如张子容、丁大凤和辛之谔等过从甚密。另一方面,他也跟湛上人、皎上人、云表观主、白云先生王迥、道士云公、道士参廖子、梅道士等佛道中人时相过从。一旦他动念求仕,他就向儒家摇摆以表明心志,“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7]132“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7]458“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7]212“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丝。……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翼”[7]207-208。一旦求仕受挫,他就本能地逃向山水,寻僧访道,“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7]145“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7]3“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旧潭”[7]151“倘因松子去,长与世人辞”[7]192“愿从功德水,从心灌尘机”[7]96。孟浩然在儒家和释道之间如此摇摆不定,很多时候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更倾向于出世还是入世。为了解决出处之间的矛盾,他有时试图调和两者,如在《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中说:“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7]48在《陪柏台友共访聪上人禅居》中亦说:“出处虽云异,同欢在法筵。”[7]52在调和的过程中,有时也不免因求仕受挫而对孔子心生怨怼,如《云门兰若与友人同游》云:“四禅合真如,一切是虚假。……依此讬山门,谁知效丘也。”[7]9-10流露出弃儒而就佛的念头。尽管如此,诗人并未从佛道那里获得心灵的安慰,越到晚年,他越是哀叹自己的不遇,“壮图哀未立,斑白恨吾衰”[7]291云云,说明他对于自己的仕途受挫一直耿耿于怀。总之,孟浩然对于儒家也好,对于佛道也好,其实并没有很深的见解。他援引儒家,不过是为自己找一个必须求仕的理由;而当其求仕受挫,就本能地逃向佛道山水,但也不过是为了精神的自我疗愈,仅此而已。
五、结语
纵观孟浩然一生,“摇摆”也许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人生轨迹上,他摇摆于求仕与慕隐之间;在思想倾向上,他摇摆于儒家和佛道之间;在性情趣尚方面,他摇摆于躁动与好静之间;甚至于在游山玩水方面,他也常常在出游与归家之间摇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孟浩然之所以总是处于摇摆的状态,归根结底源于他内心深处的迷惘。无论是对于玄宗朝的政治形势,还是对于悄然而至的盛唐氛围,乃至于对其自身心性和身体疾病,孟浩然都做了种种误读,而产生出内心深处的迷惘。正如诗人在《还山诒湛法师》中所感叹的:“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心迹罕兼遂,崎岖多在尘。晚途归旧壑,偶与支公邻。……念兹泛苦海,方便示迷津。”[7]156正是因为诗人内心深处的迷惘,才使其充满摇摆,并因此种摇摆而坠入更加迷惘的深渊,“心迹罕兼遂”,只是其内心迷惘的必然产物。孟浩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都未能实现和完成,晚年的孟浩然实际上有一种“仕隐两失”的“落空的悲哀”[12]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