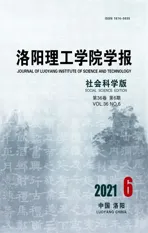由“三教融通”的文化背景解读唐宋以后关公信仰的发展与兴盛
——兼论当前关公信仰发展根源的研究状况
2021-12-28翟爱玲
翟 爱 玲
(洛阳理工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自中国传统社会中后期以来,关公信仰与崇拜的迅速发展与广泛传播成为中国文化领域极其引人注目的一种现象。关羽的形象从一个三国时期普通的历史人物不断向着“神”“圣”的方向发展演变,并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从文人、士大夫到村妇、民夫皆崇而信之的,包括儒、佛、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派别皆争相推崇的圣人与神灵,其祠庙遍及都市庙堂及穷乡僻壤,以至于海外。这种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事件或现象早在传统社会后期已引发人们的思考与探究。时至今日,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对于关公形象演变发展的根源及影响因素的论述也可谓无所不及。然而,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似极为繁兴的学术争鸣与研究热浪,也极易造成人们的认识盲点,使人在众说纷纭与眼花缭乱中失去对问题的根本的把握,而将注意力置于繁芜的枝叶之中。这便是为何至今人们在认识关公形象演变时仍存诸多迷惘的根本原因。为此,要想获得认识的深入与准确,就应当跳出热浪的细节,用一种超越的眼光重新、全面地考察推动和影响关公形象演变的种种因素,并将其放置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框架中来认识,才能使人们获得对这个问题的根本的把握。
一、对关公形象演变发展决定因素的考察与学术研究欠缺
有个时期,人们在谈论对历史的看法时很流行这样一句话: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用来形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演变、发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其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只看到了历史在后人那里被改造、改写的情形,只看到或强调了后代人以符合自己时代精神和现实的需求来重新诠释、解读历史文化,却忽略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贯性、历史与现实的传承性和一致性。某种历史(文化)之所以能被后代人用符合他们时代精神的观念来重新解释,必定是由于这种历史(文化)本身含有适合后代社会需要的某种精神基因或含有已积淀为历史文化基因性的价值观念。
同时,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的传递与承接、演变与发展过程中,后代人对于以往历史文化的重新解读或改造的情形,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与作用,而不仅仅是历史文化内含基因和后代社会需求的简单结合。具体到关公信仰与崇拜的兴起与发展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说,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这些因素,众多学术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涉及与论述。如佛、道等宗教对关羽的神化,上层统治者对关公信仰的推崇与利用,文人、士大夫在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推演与美化,民间传说对关公事迹的铺排与演绎,等等。有些学者从历史纵向或同时代空间范围的横向角度研究关公信仰的兴盛,从而将根源归结于不同时期文化氛围或不同地区民俗风尚;有些学者从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军事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解读关公信仰的兴盛,从而将其归结于社会生活各种领域中的众多因素。但从发挥作用程度上来看,这些因素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有两方面:一是关羽这一历史人物个性品质中所包含的合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内容,二是唐宋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环境的时代风尚与要求。
(一)历史人物关羽“忠义仁勇信”的个性品格与风尚
从关羽这一历史人物本身的情形来看,尽管其在历史中不可能做到时时处处都体现出完美人格的形象,但在他身上的确体现出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倡导和追求的“忠义仁勇信”等品格特征。这一点虽然不少学者在研究中有所论及,却大都以唐宋以后文学艺术作品及民间传说中关羽的形象为依据,或虽依据魏晋时期史籍记载的相关内容却并未给予深入而全面的论述。实际上,关羽的这种个性品格早在魏晋时期较为理性客观的史书记载中就有诸多体现。
从“忠”“信”“义”角度看,在关羽与刘备、张飞三人关系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史载其“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1]939。建安五年(200),刘备被曹军击败而投袁绍,关羽被俘,曹操“礼之甚厚”而“拜为偏将军”,并派张辽试探关羽是否有为曹所用之心,关羽长叹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1]940之后,袁绍围攻曹军于白马,关羽受命为先锋,策马刺袁绍大将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为此,曹操对其重加赏赐并表封为汉寿亭侯。而当关羽得知刘备消息,即“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1]939。在这一系列事件和环节中,不仅充分表现出关羽对刘备的“忠”“义”,也表现出对曹操的“信”“义”。并且在关羽这里,“信”“义”之举总以“忠”为先为主,而不是撇开“忠”之大节而随意地讲“信”修“义”,故能在关键时刻弃曹归刘。其后,当孙吴袭荆州,公安、南郡、江陵、宜都等地相继归吴,关羽困于当阳、麦城时,虽只余随从十余骑,却仍坚持不降。这表现出关羽的大忠大义。由此不难理解时人议“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的关系时说,得关羽死讯,刘备若“不能为兴军报敌,于始终之分不足”[1]446。
从“仁”的角度来看,似乎在关羽身上表现得并不突出,但从史书记载中仍可见其风尚。《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在记述关羽出处时并无他语而只说其早年“亡命奔涿郡”,后世文学作品及民间传说中将其演绎成关羽在乡里为救助民人、惩治豪强而被追捕,不得已“亡命”他乡。这种推演并非没有道理。其一,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只有得罪于豪强势力或贪官污吏才会导致无法容身而亡命。反之,若鱼肉百姓之有权势之人往往在乡里称霸,一般是不需要“亡命”的。其二,史载关羽为人“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1]944。关羽虽然对上层人物“骄”,但是对下层人物还是体恤的。况且也并不是所有地位高的人他都轻视。刘备看重黄忠“勇毅冠三军”、屡立战功,欲用为后将军。诸葛亮担心远在外地不知就里的关羽听闻后会心中不悦,而刘备则言“吾自当解之”,之后黄忠果然得与关羽齐位[1]948。可见,关羽为人虽然有“刚而自矜”倾向,也不是不讲道理而一味盲目地骄矜。至于关羽的刚硬与骄矜后来造成部属麋芳、傅士仁心存不满,以致孙吴攻袭荆州时俩人投降孙权,这在关羽一边来看,与其说是关羽的“骄”造成的,倒不如说是关羽在“智”上的不足。因为每个现实的人不可避免有着各种个性偏向,有智谋者临大事必能以“大义”来克制个性偏向而不致任性而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甚至关羽身边的刘备、曹操皆属此类人物。这在当时现实人物关羽这里难以做到,否则关羽很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位蜀汉的将军了。总之,关羽个性偏“刚”并不意味着“仁”性的不足。
“武”“勇”是“忠”“义”之外关羽身上最为显著的品格。当年在白马之战中斩颜良于“万众之中”,袁绍“诸将莫能当者”,已充分显示出关羽威武之风。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率军北伐曹魏之襄阳,降获于禁,斩杀大将庞德,周边“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以致曹操“议迁许都以避其锐”[1]941,再次表现出关羽的勇武善战。史载张飞也“雄壮威猛”,也“亚于关羽”[1]944。连曹魏谋士也承认关羽为“万人之敌”[1]433“勇冠三军”[1]445。《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中还记载一事:“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適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1]941从这个事例中也足见关羽之神勇。
颇有意味的是,清代史学大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七中专门列有“关张之勇”一条,列举各种史书所载曹魏、孙吴以及后来的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众多文臣武将称赞和比附关、张之勇武的事例。可见,唐宋以前关羽在历史上声名最卓著的是他的勇武精神,而其“忠义仁信”品格虽于史书有迹可循,却并不为人们所看重。直到唐宋以后,这种品格与其勇武精神一起成为关公信仰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内因。而要明了何以有此历史性变化,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唐宋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风向与特征。
(二)学术研究对宋代“三教融通”下中国文化精神与特征的忽略
对于唐宋以后的“三教融通”与关公信仰兴起之关系,不少学者都有所论及,如胡小伟的《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论唐代的关羽崇拜》[2]和《三教圆融与关羽崇拜》[3]384-406,蔡东洲的《关羽崇拜与儒、释、道三教》[4],郑镛的《论关公信仰与儒释道的关系》[5],吴晓峰的《关公信仰与儒学的关系探究》[6],王运涛的《从民间信仰的“三教合流”看关羽形象演变》[7],等等。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就“三教”如何利用和推动关公信仰的发展与兴盛来论说,对于“三教”何以选择和利用关公信仰则未能解析。
胡小伟在《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论唐代的关羽崇拜》一文中,通过对唐人小说的深入剖析,揭示出唐代中晚期从朝廷表“忠臣”到民间标“义举”所体现的对“忠义”观的重塑与倡导,与关公信仰在此时开始兴起具有一致性。但因受由小说揭示唐代中后期忠义观的出现这一主题所限,文章并未对此时倡导“忠义”观与关羽崇拜之关系作具体讨论。在《三教圆融与关羽崇拜》中,胡小伟曾就“三教”将关羽崇信进一步推向兴盛的情形作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称:“关羽以‘托梦显灵’与佛教结缘,以‘降神靖妖’为道教祈禳,以‘忠义孝友’被儒家纲常推崇。其与三教之渊源,先后形成于唐宋时期,而以宋代为实际发端。而有宋一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圆融三教,创建新文化的关键时期,也使关羽崇拜从此融进中国主流思想文化的大题目中。”这段话在揭示关公崇信的兴起与发展方面极富洞见,但仍未能就宋代“三教”与关公崇拜“结缘”的关键环节进行深入论析,终使人只获得一种二者相关之朦胧认识而难晓其中之必然性关联。
蔡东洲在《关羽崇拜与儒、释、道三教》中着重分析了宋元明清时期儒、佛、道出于自身发展甚至是竞争之目的而对关羽崇信不断提升和推进的情形:“佛教在唐代的中国化步伐加快,以适合生存和发展环境,很容易附会出顺应中国文化氛围的东西来。关羽自三国而降一直以神勇见称于世……把这样一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历史名将同佛教联系在一起,既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具体表现,又是天台宗提高本系地位的实际需要。”“道教属于多神崇拜的宗教,其神系构成极为庞杂,而且随着道教的发展演变,神祇还在不断增多,宋元时代不少传说中人和历史名人被道教徒或奉教者拉入玄门,载入道教典籍。关羽就是其中的一个。”“此外,一些秘密宗教也同关羽攀亲结缘,其价值取向与道教相同,即伏魔镇妖。”“不管佛、道教徒怎样渲染关羽同本教的关系,但在儒士们看来,关羽只能是儒教圣人。”尽管在这些论述中,也似乎涉及“三教”皆有从“忠义”等个性品格角度对关公崇信的不断提升,但却始终未能就“三教融通”所昭示的中国文化演进发展到宋代的价值观念之共性特征,以及这种特征与关公信仰兴起与发展之紧密关系进行分析和讨论,从而使人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仅仅停留于“三教”对其大力推动作用上,却难以明了“三教”同时选择标榜和崇信关公的真正根源。
总之,现有涉及关公信仰与崇拜的众多研究成果,尽管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和层次上对其兴起与迅速发展的诸多因素都有涉及和论述,但却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历史人物关羽个性中“忠义仁勇信”等品质在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在唐宋以后这种文化精神已经成为包括“三教”在内的从上层统治者到民间大众公认的思想意识。这种研究状况,就会造成人们在认识关公信仰与崇拜在宋代以后迅速兴起与发展的根源时,难以深入而准确。
二、由两种决定因素的结合解读关公信仰与崇拜兴起与发展的历史逻辑
在唐宋以后,关公信仰迅速兴起与发展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关公个性中的道德品质与唐宋以来“三教融通”背景下中国文化精神与特征这两个因素的决定意义极为突出,这二者才是解开关公信仰现象奥秘之所在,解答了如下的疑问:一是何以关公信仰与崇拜兴起并迅速发展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后期即宋元明清时期,而不是在此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或是此后的历史时期?二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忠义仁勇信”等人格品质的人物非常多,甚至有些人物在某些品格方面还远胜于关羽,何以宋元明清时期以“三教”为代表的不同文化流派及社会各个阶层不约而同都选择关羽作为信仰的对象?
(一)“三教融通”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总体态势与特征
要从根本上把握关公信仰何以兴起并迅速发展于宋元明清时期,首先需要认清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与根本特征,即“三教融通”、中国文化核心理念的树立、文化在社会阶层的下移趋势与状况。
这里所说的儒、佛、道“三教”特别是儒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以“三教”泛指以此三大流派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主体部分。这三大流派早在汉魏时期已经形成。儒家文化的历史最为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其较为完备的思想文化体系。佛教至晚在东汉初已传入中国,并在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较迅速发展,以致到南北朝时期许多王朝都将佛教作为国教而置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道教兴起于东汉,也在魏晋时期得到显著发展并逐步形成诸多流派与支系。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大分裂与动荡纷乱,除儒家名教处于衰落之势外,佛、道两家的发展也基本上局限于其内部的自我丰富与充实,三家之间更多的是相互间的排拒、抨击而少有融通,彼此在思想理念上的差别性也更为显著。这种状况到隋唐时期有所改变。随着大一统王朝统治的建立,儒、佛、道三大家文化体系呈现出一种并存共处的局面,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也同样是儒、佛、道三者并重。这个时期,承续着南北朝以来宗教兴盛的格局,佛、道两家在社会各个阶层均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儒家名义上虽有尊崇地位甚至被纳入科举之“明经”科,实际上却远不及佛、道两家的受众多。正因如此,唐代中后期,韩愈、柳宗元等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吸收佛教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由此拉开“三教融通”的序幕。到北宋理学(道学)兴起,完成了立足于传统儒学立场又吸收融合佛、道文化而对传统儒学的新发展,并重建了儒学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韩愈曾对儒家人性道德之学的传承这样总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8]224到了北宋理学家这里,便自觉地承接上这个“道统”。程颐为程颢所作墓表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力功大矣。”[9]640这种儒家道统论后来便成为理学不易之论,由此也体现出宋代理学兴起正是在传承并发展先秦儒家思想基础上实现的。与此同时,佛、道两家在思想观念中也不断吸取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多因素而逐步呈现出在一些核心理念上与儒家的趋同性,特别是在倡导“忠义仁勇信”等道德伦理观念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佛教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本土化、世俗化的倾向,禅宗就被认为是深受儒学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式佛教。《六祖坛经》中有一段偈语:“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这段指示修行法门的偈语,就充分反映出佛教对儒家道德伦理观念的接受与认同。
“三教融合”的基本精神,体现在价值观念上,开始呈现出三家共同趋向于对包括“忠义仁勇信”等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和价值理念的认同。尽管这种文化精神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本已包含,但自汉代以来的儒家思想多偏重“外王”即所谓“王道”思想体系,而使先秦儒家有关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圣”思想隐而不彰。事实上,这种道德伦理思想在先秦也并不局限于儒家,而是包括儒家、道家和多数诸子流派在内的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共有的显著特征,由此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特色。因此,当唐宋以来在“三教融通”背景下各家对传统文化道德理念实现共同认可时,在儒家和道家并不十分困难,于儒家是远承孔孟思想而继以理论体系的哲学化发展,于道家则是适应时势需求的思想观念更新与发展。即使对于佛教而言,在中国化、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发展中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思想观念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已有相当程度的融通。可以说,在宋元明清时期“三教融通”背景下对包含“忠义仁勇信”在内的中国传统道德理念及人本精神的肯认,对于儒、佛、道三家而言,固然都有立足于其派别的生存、发展需要而采取的策略的缘故,但从根本上言,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流之后的重新汇通与发展。换言之,重新注重人文之德性精神并将道德理念置于文化形态的中心地位,正是唐宋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显著特征。宋明理学从前期程朱理学到后期陆王心学的发展进程,恰恰是这种态势和特征进一步演进的体现。
与注重人格修养的德性精神相并行,“三教融通”背景下中国文化在唐宋时期表现出的另一特征是文化主体由社会上层向中下层普通民众扩展的趋势日益显著。纵观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先秦时期的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平民和奴隶没有文化权。秦汉以后,文化主体的下移也仅止于社会中层,以及具有跨阶层性的“文人”群体。隋唐时期,才出现民间文化登上历史前台。特别是唐代后期至宋代,民间大众文化在文学艺术领域和宗教领域已十分兴盛,所谓传奇小说、变文、说话人的出现即其重要表现。这在前文提及的胡小伟的《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论唐代的关羽崇拜》中,就有所表现。至于明代,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平民文化。显然,在文化主体下移的进程中,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正是民间大众文化兴起的重要阶段。由此而来的是立足于人本立场上对普通个人成长的关注,而不是仅限于帝王将相、贵族官宦。佛教《大法鼓经》中有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六祖坛经》也说:“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到宋明理学这里,也同样承认这种大众立场。陆九渊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人。”[10]449这即是说,人格的成长,道德的修养并非仅仅是社会上层的专属,而是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全体民众皆可追求的境界。到阳明心学兴起后,就出现所谓“良知人人本有”和“见满街都是圣人”的景况。可见,宋代以后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对于普通民众地位的肯定,这与注重道德品性一同成为唐宋以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特征。
(二)关公信仰与崇拜在唐宋以后兴起与发展“时运”的文化机理
刘志军在《对于关公信仰的人类学分析》中引用清代学者刘献庭的一段话说:“予尝谓佛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11]同时,还列赵翼将关羽“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的现象归因于“鬼神之衰旺亦有数”,以此来引发其对关公信仰与崇拜“时运”问题的探究。虽然此文中也将关羽个性中“忠义”内涵与儒家精神紧密结合并指出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但却宽泛地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立言而并未与唐宋以后“三教融通”下中国文化发展特征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明晓唐宋以来“三教融通”背景下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与特征之后,就可以对此“时运”的奥秘获得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即从根本上解答前面提出何以在唐宋以后出现关公信仰迅速发展的问题:在中国文化史上,为什么在众多历史人物中,恰恰选择关羽作为神圣化的对象,且这一神圣化的过程不早不晚,恰恰出现在“三教融通”背景下的宋元明清时期?
就历史时代性的选择而言,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已有传统儒家学说的基础,有道教的流行与佛教的盛传,但那个时期社会动荡分裂,儒、佛、道文化分立,在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上各持己说、莫衷一是。无论是民间大众还是上层社会,都很难获得共认的安身立命之精神支撑。这个时期,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即使其个性中的“忠义”“神勇”仍然受到人们的肯定并屡见于史籍,也难于形成社会大众对其共同推崇。唐宋以来,在“三教融通”基础上公认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及“忠义仁勇信”理念,并且这种理念得以贯彻于社会各阶层的背景下,关羽这位历史人物的“忠义仁勇信”品格才获得大众普遍的肯定与接受,才能在“三教”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中获得共同的承认与推崇。
就历史人物的选择来说,关羽能够在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中被纳入信仰和崇拜的体系并不断提升到神圣境界,也的确有其特殊“时运”。从个性品格上讲,在关羽之前和之后,有无数的历史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忠义仁勇信”的品格,其中不少人在生前或死后较之于关羽的地位和声名都显赫得多,但这些人中只有少部分在历史上留下声名而大部分都被湮没。撇开其他时代的人物不论,仅以与关羽同时代的三国人物为例,如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于“忠义仁勇信”等人格品质上也皆有可圈可点之处。如刘备的宽仁、忠信皆在关羽之上,其为人“少语言,善下人”“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1]872。建安十二年(207),荆州牧刘表嗣子刘琮降曹,曹操率大军已至宛,刘备率荆州军民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而南奔。有人劝刘备临难之际应放弃百姓以减轻拖累,但刘备以“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而拒绝。正因刘备的宽仁信义,才能“情感三军”,招揽人物,“终济大业”[1]877。再说曹操,史称其:“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1]55除智谋过人,其在信义仁勇上也有可述之处。如建安元年(196)刘备势弱归附曹操时,曹操待之厚,“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1]874,屡屡为之上表请封。建安五年,曹操俘获关羽后,对关羽礼遇备至。当关羽亡归刘备时,其下属欲追之,曹操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裴松之为此评论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1]940这些作为虽难称大仁,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义”。至于智如诸葛亮、法正,勇如黄忠、马超以及曹魏、孙吴各自的谋臣义士则更多。同这些人相比较,或许关羽在智谋、仁义、信勇等某个具体方面未必皆超人一等,但能同时将“忠义仁勇信”等多种品格属性集于一身者,的确少有匹敌者。另外,关羽出身社会基层,后来地位虽高也是以战功升迁为一名武将。曹操、刘备等终属帝王之类,诸葛亮也高居丞相之位,他们都不能像关羽作为一个平常人那样更容易受到唐宋以后各个社会阶层,特别是广大的中下层大众的重视和推崇,这也恰是顺应唐宋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平民化方向的一种历史取向。
总之,就关羽个人而言,一方面是其“忠义仁勇信”的品格较为集中,另一方面是其平民阶层的身份,由此在唐宋以前“三教”各自独立、竞争而未形成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的形势下,在没有整合出整个社会统一的人本精神根基条件下,关羽的形象始终未能超出一个历史人物的范畴。而在此后则完全不同,当人们以道德品性作为人本精神支撑并以此来寻求历史资源以为当代人的精神文化滋养时,关羽就是最恰当、最符合时代需要的榜样。由此,关羽信仰与崇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后期的发展兴盛就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种中国文化演进逻辑的必然产物,是一种中国文化核心观念演进的必然结果。
三、探究关公信仰与崇拜兴起与发展历史逻辑的意义与启示
人对一切问题的探究,对一切知识的获得从来都不是没有现实目的和意义的。关羽信仰与崇拜自唐宋以后兴起并迅速发展,不仅兴盛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后期,直到今天这种信仰与崇拜仍在继续发展。延续近千年而不衰的历史足以昭示其内在深厚的生命力。通过探索构成其内在生命力的根基,通过探索对关羽信仰和崇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后期迅速兴起与发展根源,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至少有如下的启示。
第一,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总是围绕现实人的发展和需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人本立场的一个立足点。关公信仰与崇拜的现象,在国外是不可能出现的,只有在中国文化的范围内才能够产生,这是与中国文化的人本精神、人文精神特质紧密相关的。换言之,这种文化特征正是人格神产生的重要文化根源。
第二,人的终极关怀永远是文化的核心,永远是文化随时代不断传承发展与进步的核心动力。任何时代的文化发展,要做到方向正确、前景光明,要做到根深叶茂,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文化精神的核心目标才能有所成就。从先秦的德性理念,到魏晋南北朝动荡中的流派分立与冲突,再到唐宋以后的融合汇通与发展,重新回归到人本精神,充分显示出文化发展的这一特点。这个特点启示我们,在今天现实社会建设中,要十分注重文化核心价值观、人本观念、德性观念的树立。只有认准这个立足点,才能把握文化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既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立场,也是其生命力的本源,同时也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与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薛正昌在《关羽与关公文化析论》中言:“关公文化的核心内涵并非神化,而是‘忠’和‘义’,它是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两个道德范畴,也是中国传统伦理中最普遍且最有约束力的两种行为规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活力的行为准则。这是关公文化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维系社会、家庭发展与稳定的文化纽带。”[12]在今天社会与文化建设中,这种道德文化的社会价值与功能具有同样的效能。
第四,关公信仰与崇拜的发展虽然是通过神化关羽的路径来实现的,但认识这一文化现象的价值与意义却不能简单地用倒推法将关公还原为历史人物关羽的方法来进行。这其中有一种文化理想的境界存在。神格化的关公已经不是具体的人格化的关羽,神格化的关公是一种超越人格、超越现实的理想镜像,是现实人们对人生不断上升性发展的终极追求,是一种人的境界修养的最终取向。因此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关公信仰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理念的导向,是一种“忠义”符号性的文化指向[13]。神格化的关公所彰显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人格力量。只有立足这样一种理念上,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关公信仰的实质和核心。也只有把关公信仰定位在这样的立场上,才能够把握好在当前形势下如何传承好、运用好关公信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