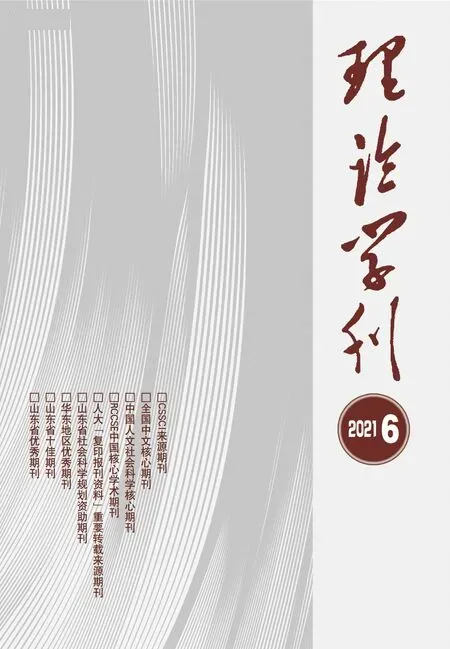文史融合:翦伯赞治学路径初探
2021-12-28黄文丽
黄文丽
(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20世纪早期是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期,史学科学化是现代史学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在继承传统史学优秀基因的基础上,整合以历史学的现代性特征,实现了现代理性和传统积淀的融合。现代史学对于历史科学性的强调,使得文史关系成为史学现代化发展中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在西方现代学科分类被引入传统学术观念之前,在传统史家的认知中文史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在治学上有着文史融合的传统。而在历史被赋予“科学”的属性之后,文学与历史作为两个独立学科被明确地分割开来,二者的关系需要被重新认识。史学现代性因素对这一时期史家的文史关系认识的影响,在视“史释”和“著史”为治史之正途的唯物史观派史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看文史关系,史家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历代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二是历史撰述中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的艺术性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无论是唯物史观派还是史料考证派,都重视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而唯物史观派在此之外还以历史与文学各自的学科属性为基础,对文史关系作全面的理论性建构,并在历史撰述中实现了对传统历史叙事的现代性转换。唯物史观派学人中不乏文史并擅的名家,比如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其中翦伯赞堪称在理论研究和历史撰述中体现文史关系现代性转换认识的典型代表,他将对于文史关系的认识充分运用于史学、文学研究及各类著述中,因而在治学路径上有着明显的文史融合的特征。
翦伯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在治学的道路上深受传统学术文史融合这一特征的影响,同时又在史学研究中把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哲学依据。此外,他还是一位极富文学天分的史学家,与同时期史家相比,翦伯赞对于文学的关注也较为突出,因此在他的著述中,有着史学与文学互动状态下丰富的关系内涵。他极为重视历代文艺作品的史料价值,并将史学思想运用于历史剧创作的研究,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解读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他的《中国史纲》第1和第2卷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经典之作,该书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在书写上有着“文史合一”的历史叙事风格;他在历史撰著之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歌,其中有着在今天看来极为宝贵的史料价值。翦伯赞文史融合的治学路径,典型地体现出新旧史学转型期中唯物史观派史家的文史关系认识对于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
一、翦伯赞对文学作品所含史料的现代开掘
传统史家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着丰富的史料,“文史互证”“文史互补”的治学方法一直被或潜或显地应用于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如《晋书》中大量采撷《世说新语》及其刘孝标注,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中说:“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将文史之间的关系上升至理论性总结。近代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是对历史资料的范畴作了概括性的论述:“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无不丛纳之于史”(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其中文学无疑也被归入历史资料的范畴,成为史学的一部分。
翦伯赞认同传统史学中的文学史料观,他在《史料与史学》一书尤其是其中的《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和《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两篇文章中,重点强调历代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史料价值,认为“自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之传奇小说,乃至现在的许多文艺作品,它们表现出中国文学自己发展之一系列的历史过程,也反映出历史上所不载的社会发展的内容,所以它们是文学,同时也是史料”(2)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297、324页。。较之传统史学,翦伯赞对文学作品中的史料价值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在关于如何以科学的方法搜集和分析运用史料的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一)文学作品中有着较之史部诸史更为真实、丰富的史料
翦伯赞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史料较之史部诸史更为真实。在他看来,史部诸史中主观意识的存在影响了所载史料的真实性,而文学作品中的主观意识因为没有保存史料这一功利性目的存在,在无意中保留了真实的史料,当然要比较真切。翦伯赞指出:“固然,在史部以外的群书中,其行文记事,也夹杂着主观的意识,特别是各种文艺作品,如诗词、诗赋、小说之类,甚至还具有比史部诸书更多的主观意识。但是在这一类书籍中所表现的主观意识之本身,就是客观现实之反映,因而它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3)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297、324页。。主观意识所反映出的更真实的史料,指的是文学作品作者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心理、情感以及反映于作品中的特定历史环境下社会群体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况,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在人们心灵中的倒影,而且“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作者对当时社会所涂绘的阴影,不过他们所涂绘的阴影,有浓有淡而已。所以我以为集部之书,当作史料看,它们正是各时代的社会缩写,正是各时代的人民呼声,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记录。而且其中的历史记录,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来的”(4)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297、324页。。也就是说,正史中没有记录下来的,在文学作品中却可以得到真实的保留和生动的再现,尤其是在高度忠实于历史真实的文学作品中成为史料被记录和保存下来。
古典历史剧《桃花扇》是一部征实求信的典范之作,作者孔尚任自谓写此书的目的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5)孔尚任:《桃花扇》,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页。。翦伯赞在《桃花扇底看南朝》一文中认为,这部戏以儿女私情为线索,将明清之际的史实都贯穿了起来,而且写成的是“一部有声有色的明代亡国痛史”,剧中南明政府统治下的各色人等“人人活现,个个传神”(6)翦伯赞:《桃花扇底看南朝》,《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页。,当时的历史情形“历历如在目前”,“而这在将来的清史中,对于这一段历史,也未必写得这样生动”(7)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324—325、326页。。翦伯赞借由剧文串讲历史,对南明福王政权灭亡之历史过程展开细致的梳理,透过剧文中对历史上的实人实物鲜活、细致、动态的描述,读者仿佛被带领着又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看到一幅幅历史的活像,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和激荡,洞察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因而谁能说《桃花扇》只是南明王朝的历史而不是那一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心史呢?这些同样是史料,而且有着比史书记载更为真实和丰富的史料价值。同样的,在《杜甫研究》中,翦伯赞通过对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作品的解读,让读者不仅看到了一部天宝前后活现的历史,而且深刻地感受到诗人所身处的时代环境,正如翦伯赞所评价的:“杜甫的诗可以说是唐代天宝前后的时代呼声。即因如此,所以他的诗歌便具有一种不冷的热力。一直到现在,尚能鞭辟读者的情绪,震荡读者的心弦,所谓千古之后,有余响也。”(8)翦伯赞:《杜甫研究》,《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0页。
文学作品中的史料之所以较之史部诸史更为丰富,除了包含作品中的主观意识所反映出的客观现实以外,还有着为史部诸史所不记载的对社会状况的刻画以及丰富的历史细节描写。比如翦伯赞认为,在《楚辞》中对战国末年楚国流行风俗的描写,是战国时的史书中所找不到的;在汉赋中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对于两汉都市、宫室以及许多琐碎的掌故之记录,是前后《汉书》中所找不出来的;在唐诗中诗人记述所亲历之事变和目睹之社会状况的诗歌,是新旧《唐书》上所不能找出来的;元曲中描写元朝统治者的高利贷、贪污腐化以及元朝统治下知识分子之陷于饥饿的情状,又都是《元史》上找不出来的;等等(9)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324—325、326页。。固然文学作品中存在虚构,小说中的人物事实大半都是假设,但是翦伯赞认为,在作者当时必定有这一类型的人物和事实,以《红楼梦》为例,“《红楼梦》写大观园里的秽史。不管有无大观园,而在清代的贵族中有这样豪奢、腐败、淫秽的家庭,则是事实”(10)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324—325、326页。。
(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文学作品,探索文学作品的社会史价值
翦伯赞既重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又强调史料要很好地应用起来,使之成为历史的说明。在他看来,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在《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一文中,他指出:“搜集史料只是替历史研究准备材料,并不是历史学的终极目的。大家都知道历史学的任务总不能就是编成一些史料汇抄,它应该是一种分析史料的科学。”(11)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翦伯赞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9页。
在他看来,史料学中的科学方法非常重要,不仅是史料的搜集与整理需要科学的方法——“没有方法,不但不能写成历史,即搜集史料也不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正确的方法,则虽有史料,也不会成为说明历史的资料,‘正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12)翦伯赞:《正在泛滥中之史学的反对倾向》,《翦伯赞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翦伯赞所说的“正确的方法”,指的是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运用于历史资料的研究之中。就中国历代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史料而言,他认为由于没有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没有被系统地发掘出来,而且也没有被很好地应用于历史的说明。在翦伯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红楼梦》的研究。
翦伯赞在《论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一文的开首就作出说明:“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是企图说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13)翦伯赞:《论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翦伯赞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576、632、577、633页。文中,翦伯赞从清代的官书、地方志、笔记杂录等各类资料中查找出200多条材料,还大量引用了《红楼梦》中与社会经济相关的历史资料,用于说明在18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经济中已经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进而得出《红楼梦》创作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的时代背景之下的结论。
对时代背景的说明是为了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这部作品的时代精神和思想内容。翦伯赞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人,包括作家在内,决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而孤立地生存,因而任何作品,包括《红楼梦》在内,必然有意或无意地要反映作家生活于其中的周围世界。”(14)翦伯赞:《论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翦伯赞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576、632、577、633页。所以他认为,作者曹雪芹当然“并不是企图写出一部18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史或社会史,但是他却有意无意地在大观园的周围安置了18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历史”,“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他的作品中反映了他的时代,反映了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济情况和阶级关系”(15)翦伯赞:《论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翦伯赞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576、632、577、633页。,而作家又必然要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之上,“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他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倾向”(16)翦伯赞:《论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翦伯赞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576、632、577、633页。,《红楼梦》的作者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表示了对所处时代的态度,即揭露了他所身处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在社会经济的变化中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没落,同时在新的历史因素的影响下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新的市民的要求。
不同于胡适认为这是一部“随手拈来,初无成意”的自然主义作品,翦伯赞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思想性和人民性的杰出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它的价值在于作者“以批判的态度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时代,完成了他的时代使命”。胡适因为信奉历史唯心主义而将《红楼梦》归结为一部家史,而翦伯赞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红楼梦》中史料的研究,使得其中超越正史的社会史价值得以发掘出来,即如他在文末所说:“没有一个和曹雪芹同时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像《红楼梦》一样用那样具体、生动的现实生活,那样深刻、细致而又大胆的批判态度和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了我们一部18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史。”(17)翦伯赞:《论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翦伯赞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576、632、577、633页。
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是体现“文史合一”的经典之作
翦伯赞“心目中的理想史学是深厚的朴学功力、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卓越的宏观叙事能力的高度统一”(18)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他的《中国史纲》第1和第2卷可以说完全符合这一理想史学的标准。这部中国现代史学中的经典著作在出版40多年后,仍被秦汉史专家林剑鸣评价为是“大陆出版的水平最高的”一部书(19)林剑鸣:《秦汉史》(述评),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其中极为人所称道的是“文史合一”的撰述方式。翦伯赞非常重视文学语言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体裁是历史学的形式,而言语则是历史学的本体。因为任何形式的历史学,都必须借文字来表现其内容”(20)翦伯赞:《论刘知己的历史学》,《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7页。。他在继承传统史家“良史莫不工文”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又推动了传统史学中历史叙事方式的现代性发展。
(一)历史叙事的散文化风格与整体史观的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翦伯赞在《中国史纲》第1和第2卷中采用了散文化的历史叙述方式及解说历史的叙述风格,将丰富的史料、深刻的论述通过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文学的艺术性对历史诗意的阐发,使得这部史学著作阅读起来像历史散文般优美,所以郭沫若评价说听作者“为我们朗读”《中国史纲》可以“疗治”自己的“略略伤风”之疾(21)《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侯外庐也赞赏道:“他的作品能做到寓科学性、党性于优美而流畅的诗一般的文字语言中。凡读过《中国史纲》的人,无不有感于他锤炼文字的功力”(22)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7—138页。。
散文化的叙述方式又与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相互融合,并相得益彰。在翦伯赞看来,“过去以至现在的中国史著述,都不是中国史,而是大汉族史”,而且对于中国史的理解缺乏全球视野和现代观念,“中国史之于世界史,正犹细胞之于人体,他是一个个体,但他决不能离开人体而自由的发展其生命。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顾到他与世界史之间的关联”(23)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11页。。以散文化的方式书写世界史整体背景下的中国史,使得翦伯赞通史撰述中的开放意识、全球意识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在诗意且富有激情的历史叙述中,历史的演进被生动描述成为流动的画卷,又如同史诗般恢弘、气势磅礴。如在介绍西汉中叶以前世界的形势时,翦伯赞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此之时,假若我们登帕米尔高原而西望,我们所看到的,是罗马的文化圈在扩大,是野蛮人的骑兵在驰逐,是希腊人在走下历史舞台。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黑海与里海之北的广大原野中,有不少的游牧种族,他们驱着可爱的畜群,在那里唱着原始的牧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有名的探险家张骞到了中亚细亚。”(24)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翦伯赞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历史的发展片段则成为书中随处可见的历史图景,可以说“从头至尾,或任取一节,无不是凸现而清晰的画面,直如真景呈之于前”(25)曹月堂:《博通的风范——读翦著〈秦汉史〉》,《读书》1984年第8期。。历史图景的展示,又常常是通过将统治阶层和劳苦大众作对照的方式呈现的,如翦伯赞在《中国史纲》第1卷中如此描述商代都市安阳的场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坐着四匹马车的奴隶贵族,招摇过市;可以看到零落的自由民,徘徊于街头巷尾;也可以看到额上打了火印的奴隶大众,成群地走进各种的手工业作坊。此外更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种族的行商坐贾,熙来攘往。总之,当时的安阳,可以说是商代奴隶所有者的天堂,同时,又是奴隶大众和零落的自由民之地狱。”(26)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翦伯赞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这种对照式的叙述方式在历史编撰中的运用,体现出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以及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动因时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将理论运用于剖析历史时,会因为教条主义的影响出现生硬和空泛的弊病,而这种散文化对照式的表述方式却巧妙地“把史料融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27)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翦伯赞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说明“不引经据典完全可以很好地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说明历史”(28)曹月堂:《博通的风范——读翦著〈秦汉史〉》,《读书》1984年第8期。。
(二)历史事件的小说化形式再现与历史人物的人性化还原
传统纪传体历史撰述是以人物为纲,并借助故事性的叙述结构还原历史。历史人物的个性,通过特定历史环境之中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而得以体现。翦伯赞在对这种传统历史叙事模式承继的同时,又有着现代性的转换。他在《中国史纲》中以现代小说的形式叙述历史,实现了传统历史人物传记在现代语式中的转换;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注重用普通的人性为历史人物着色,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用文学性描述来刻画历史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以凸显出“人”这一历史活动主体的历史作用。
《中国史纲》中小说化这一带有文学性品格的历史书写方式,并没有违背历史学的科学性特征。无论是历史人物内在世界的刻画还是历史场景的描述,包括其中想象的成分,无不以可靠的历史史料为基础,翦伯赞所做的只是以历史典籍为依据,借用现代性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文学性的艺术手法,使历史以更为完整的形态得以还原。
如《秦汉史》中写楚汉之争中的“霸王别姬”一幕:
夜已深沉了,在项羽的军幕中,点燃了巨大的蜡烛。四面皆有楚歌之声,于是这位三十岁左右少年英雄,开始结束他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
虞姬在侧,骏马在门,项羽在痛饮美酒。酒酣,项羽慷慨悲歌,虞姬和之。……项羽的眼泪滴下来了,卫士们都垂下头。
楚歌的声音更逼近了,蜡烛快熄灭了,骏马在长嘶,卫士们都拔出了雪亮的刀剑。大概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虞姬就与项王永别了。同时,项王也就跃上了他的骏马,带了八百名骑士,冲出了千军万马的重围。在项王军幕中留下来的,是酒,是泪,是血,是美人的幽灵,是英雄的歌声。(29)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翦伯赞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500页。
“霸王别姬”这一秦汉史上的经典片段源自《史记·项羽本纪》中的生动记载,千百年来在史书、文学作品以及各种艺术形式中被反复记述和诠释,翦伯赞的创新在于他以现代小说形式赋予了这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现代性色彩,从而更加贴近当代人对历史的感悟方式。在《中国史纲》中,翦伯赞擅长用小说化的形式重现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场景,而在小说化的外观下,是对历史学法度的严格遵守。这种以现代小说的形式叙述历史的方式,似与今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那些极富文学色彩的史学著作有着相通之处,而史景迁所说的“我写的不是‘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即编造出来的故事(fiction)。我只是‘将历史写得像小说’(writing history so that it reads like a novel),务求以最活泼生动的方式来写历史而已”(30)杨秀慧:《专访中国历史专家历史侦探史景迁》,《香港经济日报》2005年11月18日。,用于评价翦著中对历史事件的小说化描述,也是极为贴切的。
(三)历史哲理的文学性表述
史学著述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历史思想的表达,这既包括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和总结,也潜含着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史家的观点有通过论赞来表达的,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等;也有通过文学艺术手法来表现的,最典型的就是《史记》中“寓论断于序事”,“这一特点与其说是特殊的‘史法’,不如直接说这就是一种文学手法,是运用文学手法来写历史。因为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作家的思想、观点,作品的倾向性,不是诉诸于直接发议论和由作家直接出面作出裁夺,而是靠着对事物的生动而客观的描述体现出来,而且‘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31)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翦伯赞作为一个有着“深刻历史洞察力”的现代史家,在表达上升至理论层面的历史认识时,借鉴了《史记》这种以文学手法表达历史观点的方式,并在“寓论断于序事”之外,通过形象化的表述、思辨性的语言,达到对历史规律、历史哲理的更好的阐述。
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常通过类比的方式,对复杂的历史问题作形象化说明,使读者在心领神会的同时,又为其语言之形象、精炼且幽默化的风格所折服,而这既需要史家充分掌握文献材料、深刻洞悉历史问题,又需要具备文学性的思维以及高超的文字表述能力。比如在阐释汉代担负着儒学传播职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专制化的意识形态统治之间的关系时,翦伯赞用了这样一段漫画似的形象化表述:“汉代的统治者,把它(儒学)当作一种材料,筑成了一条文化思想的狭路。在狭路的起点,写着知识分子由此入口;在狭路的终点,堆积着大堆的禄米。为了获得禄米,必须通过这条唯一的狭路。因此,在当时,这条狭路中便挤满了利禄之徒。他们口里念着圣经贤传,心里想着高官厚禄。为了多领禄米,总得东扯西拉,说些‘子曰诗云’。这样一来,儒家学说的‘枝叶’遂日趋‘繁茂’,以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32)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翦伯赞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500页。这段对二者关系所作的简明、生动的描述,远胜于枯燥的理论性论述,在此基础上,读者自然而然地理解了汉代儒学之所以会变得愈益繁琐且僵化为“永恒不变的真理”的原因所在。
翦伯赞还经常用凝练且富有思辨性的语言道出历史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规律与历史哲理,比如在论述东汉末期的党锢之祸时,他认为士大夫的政治抗争只是要求政治的改良以挽救这个政权,但是外戚和宦官是“最反动的一群”,“外戚、宦官走进朝堂,士大夫就必然退回田里,这几乎也是中国史上的一个规律”(33)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翦伯赞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72—473、80—81页。;或者仅仅通过生动、简略的描画就能说明历史的哲理,比如在分析秦朝末年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时认为陈涉、吴广领导的农民“大叛乱”之爆发,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爆炸,而是自始皇兼并天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的归结,“军事的征发,经济的榨取,政治的收夺,以风行雷厉之势,齐头并进,把那患贫血病的社会之最后一滴血液,也抽出来了。匈奴打退了,南越征服了,长城建筑了,驰道开辟了,阿房宫也落成了,可是旧贵族的铁椎也伸出来了,农民的反叛标语,也发现了”(34)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翦伯赞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72—473、80—81页。。貌似简易平白的语言却极富史学智慧,于史实的排列中暗含着对历史发展中因果关联的说明,令读者在获得理性认识的同时也有了更为深刻的历史领悟。
三、翦伯赞史家情怀的艺术呈现
翦伯赞对文史关系的认识并不局限于史学领域,他还以史学家的身份深入到文学领域中,并留下了探索和实践的印记。翦伯赞的文学关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历史剧创作,他的历史剧评有着以文学为本位、以历史为着眼点来完善历史剧创作的倾向;二是以文学作品为载体记录他所身处的历史时代,并将他体现于史著中的灵动飞扬的文采在文学创作中更为充分地加以发挥。
(一)历史真实应是艺术真实的前提
文学领域中的文史合一主要体现于以历史为载体的文学作品中。历史文学作品对历史题材的运用涉及到如何将文学的艺术性与历史的科学性在作品中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因为历史文学作品在传播历史以及发挥历史的教化功能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历史文学中的历史真实是不容忽视的。具体到历史剧中历史真实的重要性,翦伯赞认为:“文学的感染力是很大的,特别是戏剧。一个戏剧家在历史剧中的虚构可以从人们的头脑中挤掉历史的真实。”(35)翦伯赞:《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翦伯赞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6页。
翦伯赞对历史剧有很深的研究,他的戏剧研究著述12篇,绝大多数都是和历史剧创作相关,田余庆曾评价他的历史剧评“兼有史家、作家、文艺评论家精湛的修养,篇篇都是佳品”(36)田余庆:《历史主义无罪》,北京大学历史系:《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20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关系的讨论,就是由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发其端的。翦伯赞对于历史剧创作中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历史真实应是艺术真实的前提,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遵循历史主义原则。
翦伯赞在写于1960年前后的几篇研究历史剧创作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中这样阐述道:“固然,写历史剧不像写历史教科书,每一件事都要力求准确,但既然是历史剧,在主要的问题上,或者说在总的历史形势、历史倾向上,应该符合于历史真实。昭君出塞是不是民族国家的屈辱,这个问题,攸关着戏剧家对待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态度,不能说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最好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他认为过去的诗人、戏剧家出于大民族主义情感和封建道德观念,把昭君出塞描述成民族国家的屈辱,把王昭君描述成一个悲剧人物,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应该让王昭君从天国回到人间,从道德领域回到历史领域,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37)翦伯赞:《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翦伯赞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4、843页。。而越剧《文成公主说了话》,在翦伯赞看来做到了基本上符合于历史真实而又没有受到历史真实的拘束,“作者按照自己的目的把历史的真实进行了艺术加工,使历史的真实上升为艺术的真实,以服务于这出戏的主题思想——民族友好团结”(38)翦伯赞:《文成公主说了话》,《翦伯赞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21页。。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他看来,历史剧是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本质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的,歪曲历史事实本质的艺术虚构则有违历史剧创作的基本原则。
除了历史事实,历史文学作品中能否用历史主义原则来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同样关系到是否会“从人们的头脑中挤掉历史的真实”。对史学家翦伯赞来说,“历史主义是他史学思想的核心与特色所在”(39)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这一史学思想同样被他运用到了历史剧的研究之中。翦伯赞写了不少关于历史人物翻案剧的评论文章,例如《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等,他认为过去历史剧中塑造的一些历史人物需要重新翻案,这是因为当时的剧作家在定义他们的历史形象时所秉持的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正统主义历史观,而非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为了宣传正统主义历史观,当时的剧作家甚至会歪曲历史,使人们不能获得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客观准确的认识。而现代的一些历史翻案剧如越剧《则天皇帝》,也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杰出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甚至对历史人物存在误解,如把武则天说成是一个妇女解放者,这是很不妥当的。翦伯赞从“历史学家的立场”(40)《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出发,结合史实纠正被歪曲的历史事实,运用历史主义原则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价值与意义,对历史剧中不利于“历史真实”还原甚至可能导致对历史本质产生误解的所谓艺术虚构予以修正,为历史剧创作中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真正统一提供历史学支援,从而体现出现代学术研究中学科之间融贯的特征。
(二)翦伯赞的文学创作
作为一位有着很高文学造诣的史学家,翦伯赞在历史撰著之外还有着文学创作的实践,可以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在诗、散文及多种文艺形式的研究和写作上都有精湛造诣的文学家”(41)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翦伯赞以散文、诗歌创作和时事评论的方式记录了他所处的时代。“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而且“当代人能直接观察、亲身感受、耳闻目染当代史本身,至少能部分地直观到历史的所谓‘本来面目’”(42)王学典:《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翦伯赞的文学创作正是他书写他所身处的当代史的一种方式,而且因为书写的是身处其中的历史,所以至少是部分地保留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方面,其中所记录的社会图景、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有着宝贵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因为作者身处所记录的历史之中,记录中所传递的历史氛围在今天读来仍是有历史温度的,可以让没有亲眼看到和听到那个时代的后人某种程度上获得重返历史现场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翦伯赞的文学创作是对自身所持文史关系认识的实践。
在翦伯赞的文学作品中有着为他所刻意追求的史料价值和历史观念,体现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在时代巨变中强烈的责任感。他的写人叙事散文不沉溺于个人的情感天地,而是以宏大的关怀和历史的视角去审视他生活其中的环境和当时的底层社会状况。如在《回忆歇马场》一文中,他全面而又生动地记录了抗战时期他所见闻的四川农村生活,歇马场完全可以看作是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尤其是文中对民生的热切关注,以及用细致的笔法对农民的生活状况和与之作对照的地主生活的描述,使得此文在今天读来仍给人以颇为强烈的历史感。他追忆冯玉祥、陶行知等故交的回忆性散文,重点关注的是这些历史人物所具备的非凡个人品格和历史人格,可以说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确立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有的位置。他的游记散文有着对“二战”时期欧洲历史影像的记录,被记录下的不仅仅是法西斯武装侵略之下的欧洲社会状况,还有当时欧洲所充斥的紧张、压抑、混乱的社会氛围。
翦伯赞还被誉为现代中国历史散文体裁的开创者(43)戴逸:《融学术、哲理、诗思于一身——纪念翦伯赞同志》,《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6期。,他的历史散文名篇《内蒙访古》在范式上称得上传统历史散文向现代历史散文转换的典范之作。在该文中,翦伯赞将古迹和史料相结合并作了大量的考证,使历史真实的严谨与历史本身的诗意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以历史之真为散文的诗意增加了深度;他将论从史出的史论精神体现于历史评述中,深刻的历史洞见既体现出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史识,也为这篇历史散文增加了智性的分量。历史的诗意和充满智慧的史论相结合,体现出中国传统历史散文情与智兼具的特征,这一特征与现代散文文学性品格融为一体,对于历史散文在创作中如何处理好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示范价值和效应。
翦伯赞的政论文史料价值也很高。统计可知,他发表的政论性文章多达70篇,时间跨度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新中国建立后的1960年。这些政论文章评论的内容紧跟时事政治的变迁,仅通过文章的标题就足以感知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对此,张传玺曾作出这样的评价:“文章的基本内容,都是根据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结合民族和民主革命的需要,从理论、国情出发,大声疾呼,宣传反帝反封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呐喊呼号。毫无疑问,这些文章在当时,都是投向敌人的锋利匕首;对今天来说,又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44)张传玺:《〈翦伯赞全集〉书目解题》,《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5期。
翦伯赞还写有大量的旧体诗。在这些旧体诗中,他多采用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的手法,生动地记录了历史的事实、细节以及当时的氛围和情思,因而同样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如他的《春节感怀》:“钩党风声夜半传,山村寂静正新年。难忘小市疏灯夜,急雪寒江独觅船。”这首诗追忆的是1940年因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在刚过完农历新年的一个大风雪之夜乘舟逃离湖南溆浦前往重庆时的情景,从诗中所描述的景况可以了解到当时很多的历史信息。翦伯赞不仅写诗,而且研究诗和诗人。他对杜甫的研究尤其深入。在《杜甫研究》一文中,翦伯赞提到自己曾一度对中国文学发生热烈的兴趣,当时最喜欢读杜诗,认为杜诗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现实主义,并评价杜甫的诗“完全是纪录他的时代,纪录他的身世,而且丝毫不走样地纪录出来”(45)翦伯赞:《杜甫研究》,《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2页。。可以说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对翦伯赞的旧体诗创作乃至文学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四、结语
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期,是史家们对文史关系的认识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唯物史观派史家因为现代学科分类下对历史学科学属性的强调,所以他们的文史关系认识体现出现代史学的理性色彩。他们对于文史关系的理论研究较之传统史家更具有思辨自觉,所作的通论性研究和归纳性总结亦有着明显的科学性、现代性特征,这一学术特点在翦伯赞对于传统文史关系认识的理论发展上体现得很明显。
翦伯赞关于文史关系的理论阐发主要是以文学作品中的史料价值为重点,有着较之传统史家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论认知和论述,而且由于新的研究路径的开辟,即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社会史价值的探索,遂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了对文学作品中所蕴藏的史料的发掘和分析引用。他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发掘和理论阐释上的贡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史观派特征,而他在历史剧研究中对历史真实的强调以及将历史主义运用于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价,无不体现了现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特征以及各学科在专精基础之上融贯的特点。
其他唯物史观派代表性史家也在不同方面阐述了对于文史关系新的理论认识。李大钊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人,在《史学要论》和《史学与哲学》中多次谈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他将学科属性作为讨论文史关系的立足点,认为文史之间既相通又有着严格的区分。范文澜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论述了优美的文学语言对于广泛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性。郭沫若以史学的科学性与文学的艺术性为基点来探讨文史关系,其对文史关系的论述多结合自己的历史剧创作来展开,既强调历史剧创作是以尊重史学的科学性为前提的对于历史的艺术化处理,同时又重视文学作品独立的艺术性。而当脱离了历史剧创作的范畴来谈论文史之间的关系时,郭沫若和李大钊一样,都认为史学研究需要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可见,唯物史观派史学家们是从各个方面建构两大学科之间的科学性关联,较之传统史家对文史关系的认识无疑更加全面和系统。
在历史论著的书写上,唯物史观派史家们体现出“文史合一”历史叙事风格的群体特征。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语言优美、叙述通俗、深得广大读者喜爱的史学名著。身为史学家和文学家的郭沫若,在他的历史论著中融史学家的科学态度和诗人的气质于一体,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等著作,既展现出文学家的才情,又能规避文学艺术性对史学理性特征的干扰。以上这些史学经典著作(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当然也应包括在内),都在叙写历史的过程中体现出文史之间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关系内涵。
整体看来,处于新旧史学转型节点上的唯物史观派史家们形成了传统学术观念与历史学现代性特征中和之下的对于文史关系的新认识,既强调史学的科学性是其本质属性,又认同历史研究、历史叙事与文学之间相互融合、互为支持的关系。由学术史上文史关系认识的变迁来看,他们的文史关系认识较之传统史家更为全面、系统和科学,较之现代史学中因对历史客观性追求的绝对化而出现的文史应该彻底分离的观点,以及后现代史学中因质疑历史学所能达到的客观性而提出的文史等同的观点,都更为客观、理性,因而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代表性史家翦伯赞关于文史关系的理论认识,尤其能体现出唯物史观派史家的文史关系认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化发展这一学术特点,由此衍生的文史融合的治学路径实现了对传统路径的现代性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