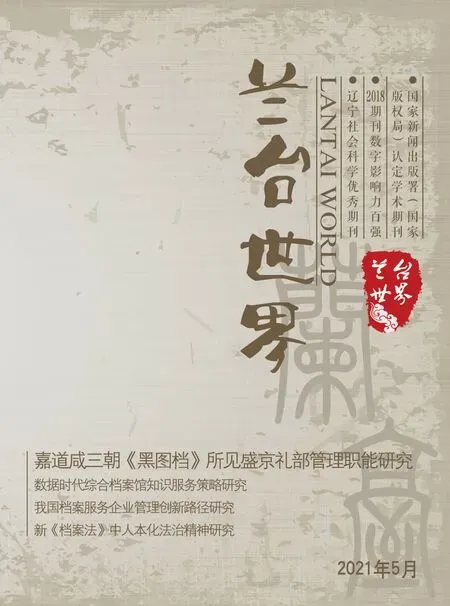出土简牍所见秦至汉初的县廷令史
2021-12-28李奇灿
李奇灿
秦汉时期,令史普遍设置于县廷,协助县长吏处理行政、经济、军事等方面事务。关于县廷令史的研究,学界已有诸多成果,但主要集中在令史的职能方面①。在令史的性质、设置和待遇问题上,探讨的文章较少,缺乏更详尽和深入的论述。
令史究竟是县廷的吏还是县令的吏,依然存在很大讨论空间。大多研究都认为,令史职能涉及基层行政的方方面面,但并没有系统性地进行研究。在令史的设置问题上,已有研究主要强调令史的升迁问题,忽视了对令史具体选任途径的研究。此前受材料所限,令史待遇问题的研究也较为缺乏。针对以上问题,有必要从令史的性质、职能、设置和待遇等方面对秦至汉初的县廷令史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县廷令史的性质
在县廷令史的性质这一问题上,学界主要有“县令的属吏”和“县廷的属吏”两种观点②。秦汉时期的基层机构大致可分为稗官与诸曹两大类,本文将从诸曹与令史的关系角度来探讨县廷令史的性质。
里耶秦简8-269中记载了县廷令史在曹中任职的事例:
资中令史阳里扣伐阅
十一年九月隃为史 □计 户计
为乡史九岁一日 年卅六(第二栏)
为田部史四岁三月十一日 可直司空曹
为令史二月(8-269)[1]125-126
从简文下端的“可直司空曹”来看,令史扣在考核合格后充任司空曹。但这只体现了令史能在司空曹任职,并不能看出令史扣是以何种身份进入司空曹。
在里耶秦简中,关于毛季的两条史料也值得关注:
私进迁陵主吏
毛季自发(8-272)[1]126
进书令史毛季从者(8-1529)[1]350
简8-272记载有人上书给迁陵主吏,既然是毛季亲自拆开了这封文书,那么毛季就应当是迁陵县的主吏。在秦至汉初,以组织名称指代主管者是惯例[2];某曹的主官也称为主某[3]。据此,简8-272中的迁陵主吏毛季应当是迁陵县的吏曹主管者。虽然在简8-1529中,毛季又以令史的身份出现,但还不能断言毛季同时有任令史和吏曹主管者的双重身份。
里耶秦简中的另外两条简可以提供新的思路:
司空曹计录 赎计 凡五计
船计 赀责计 史尚主
器计 徒计(8-480)
仓曹计录 器计 马计
禾稼计 钱计 羊计
贷计 徒计 田官计
畜计 畜官牛计 凡十计
史尚主(8-481)[1]164
这两条简是司空曹和仓曹的簿籍计录,均是由名尚的史主管。由于目前刊布的秦至汉初的简牍中尚未直接出现“掾史”或“曹史”,可知尚并非是曹内特设的史,也就是说,史可以以原本的身份充任诸曹,毛季也可能是以令史的身份充任吏曹的主管者。简文中有关“尚”的记载还有“尚视平”“史尚视平”“令史尚视平”。在秦至汉初,“视平”一般只能由官啬夫或令史参与,因此,“尚视平”“史尚视平”应是“令史尚视平”的简写。
如此,司空曹和仓曹中的“史尚”就是参与了视平的“令史尚”,令史与曹的关系也逐渐明朗:令史以原有身份充任曹的主管者,协助县廷的辅助部门正常运行。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多有“即令令史某诊”的记载,但并未言明主语。值得注意的是,爰书中多有“丞某告某乡主”“丞某讯丙”的记载,说明县丞是审理案件的负责人。那么,令令史诊的也极可能是县丞。
如果县廷令史只是县令的属吏,那么二者就是辟属关系,令史无需听从县令以外的差遣。但由上文可知,令史不仅可以充任曹的主管者,还听从县丞调遣、协助其处理案件,那么令史就不当是县令的属吏,而是县廷的属吏。
二、县廷令史的职能
随着近年来简牍文献出土与刊布,关于令史材料愈加丰富,可见令史具有处理文书行政、簿籍管理、县官买卖、出仓入仓、循行府庙、治狱和镇压盗贼等职能。
1.文书行政。文书的上传下达维系着秦帝国行政系统的运行,县廷令史作为基层吏员,不仅参与了文书的抄写、封印、传递等一系列工作,还有校雠律令的职能。里耶秦简8-1511中令史感同时承担了文书的抄写和传递工作;里耶秦简J1(16)6B面中的“令史犯行”也说明文书是由名“犯”的令史传递。
令史可以封印文书,但没有专属的印章,张家山汉简记载了这种情况: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箧若匣匮盛,缄闭,以令若丞、(331)
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封府户;节(即)有当治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湊)令若丞印,啬夫发,即襍治为。(332)[4]54
文书一旦封毁,就必须重新封印,并附上檄文注明情况。一般情况下,在县级中邮行的文书,封泥需要加盖县令或县丞的印章。“令史、吏主者完封奏(湊)令若丞印”说明了令史和吏主者也可以封印文书,但必须加盖县令或县丞的印章。目前所出土材料中并未发现令史的印章,可推知县廷令史并没有专属印章。
从以上材料来看,秦至汉初,令史的职能涵盖较为全面,包括文书的抄写、封印、传递,以及律令的校雠。然而,即便令史的工作几乎涵盖了文书行政的各个环节,却仍没有属于自己的印章,在文书封印时只能使用县令或县丞的印章,说明令史并不是县廷长吏,只是比一般的基层吏员地位稍高。
2.簿籍管理。令史参与了各类簿籍的保存和管理工作。从张家山汉简328、331、332上看,令史应与其他吏员一同检查、核对簿籍并将其封存。
在保存簿籍的基础上,里耶秦简8-873+8-874“令丞、令史主解说爵及薄(簿)已何解”[1]239-240体现了令史有解释簿籍的职能。
令史能够解释簿籍,是基于对簿籍的了解,而这种了解来源于另一项职能——上计。
此条简提到了每年令史上计簿籍的内容及参与的令史人数。正是因此,令史才能对县廷簿籍的内容如此了解。
3.监察县官的交易活动。县廷吏员在进行买卖时需要令史监察。岳麓秦简243明确了“令史监”的规定。岳麓秦简《田律》简111、112、113规定:吏员在县廷购买粮食后,钱应当封存在缿中,令史持三辨券中的一辨,起到了监督的作用。里耶秦简8-907+8-923+8-1422[5]246记载,县廷中的吏员建和般去卖祭祀后撤下的酒,令史监督了这场交易。
令史对县官买卖的监察是在特定情况下进行的。在简111、112、113中,归休吏员购买的是县廷的粮食;简8-907+8-923+8-1422中,建和般是在为县廷卖酒。两处买卖的都是官府财物,卖出的钱也应上交到官府。“令史监”一条出自《关市律》,是适用于关市内部的律令。因此,令史对县官买卖的监察职能是以买卖官府财物为前提的。
4.出、入仓。令史在县廷出、入仓时需要“视平”,扮演了监察者的角色。根据睡虎地秦简151:
空仓中有荐,荐下有稼一石以上,廷行事赀一甲,令史监者一盾。(151)[6]128
本应出尽的空仓中还余有一石以上的粮食,说明在入仓或出仓的过程中有失误,首先追责的是县廷办理这件事务的吏员,其次就是负责监督的令史,强调了令史监督的重要性。
《汉书》中有关于令史出仓的具体事例:
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赐物及当稟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7]113。
有司针对文帝元年诏上请,年满九十以上的老人由县长吏阅视,县丞或县尉发放衣食;八十到九十之间的老人的衣食由啬夫和县令史发放。这些财物都是从县仓中发出,是县廷令史出仓的具体事例。
5.循行廷、庙。县廷令史有循行廷府的职能:
毋敢以火入臧(藏)府、书府中。吏已收臧(藏),官啬夫及吏夜更行官。毋火,乃闭门户。令令史循其廷府。节(即)新为吏舍,毋依臧(藏)府、书府。(198)[6]64
此条简文规定令史需要巡查其衙署的廷府,明确了令史对县廷府库的监察职能。
不仅是廷府,令史还有“行庙”的职责,如里耶秦简中记载:
廿六年六月壬子,迁陵□、【丞】敦狐为令史更行庙诏:令史行
失期。行庙者必谨视中□各自署庙所质日。行先道旁曹始,以坐次相属。(8-138+8-174+8-522+8-523)[1]78
简文正面记载着“令史更行庙诏”,行庙即巡视庙,行庙的令史要认真地巡视庙并做好巡视记录,从距庙最近的令史开始,按坐次轮流巡视;背面是令史行庙的具体排次记录。令史循行廷府是为了检查府库的安全等,行庙的目的也类似,此外令史还需要负责庙的修缮:
如下邽庙者辄坏,更为庙便地洁清所,弗更而祠焉,皆弃市。各谨明告县道令丞及吏主(321)
一旦县廷的庙有损坏,应当选择合适的地方重新修筑,如果没有修整就直接进行祭祀,负责人要被弃市。明令每个县、道的令丞和吏主者主持修整工作,令丞和吏主者需每五日巡庙一次,令史每旬一次,县令或县丞每月一次。令史每旬都要巡庙,也是为了保证庙不受损坏并及时发现需要修整的地方。
6.治狱。睡虎地秦简的《封诊式》中,以“争牛”案、“告臣”案、“贼死”案、“出子”案为例,可见令史在治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县廷接到报案时,通常会派遣令史调查情况并做好记录。“争牛”案中,甲乙二人都坚持这头黑色母牛是自己的,于是让令史齿牛,通过牛的年龄判断牛的归属。“告臣”案中,甲因为奴隶丙骄横,想将他卖给县廷,令史按照规定检查丙的身体状况。“贼死”案中,某亭求盗发现了一具不明身份的男子的尸体,令史带人去验尸并询问案情。“出子”案中,孕妇甲因与丙斗殹而导致流产,令史将丙捉拿到县廷后,又与有过生产经验的隶妾检查流产的甲和胎儿的情状。
从以上案例来看,令史在办理案件时,除了勘察、询问,以及捉拿被明确指出有罪的人到县廷外,还有一个“诊”的过程,即勘验。“争牛”“告臣”案中,进行勘验的是令史;“贼死”案中,勘验者有令史和牢隶臣,并未指明验尸的人;“出子”案中,虽然根据爰书记录“令令史某、隶臣某诊甲所诣子”,但诊甲和胎儿的是有生产经验的隶妾。因此,令史会亲自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勘验工作,但在涉及专业的方面时,会让有经验的人进行勘验。换言之,令史在勘验工作中,起到的是总领、负责的作用。
7.镇压盗贼。在秦至汉初的基层行政组织中,除县尉、求盗、游徼负责镇压盗贼外,令史也有镇压盗贼的职能。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有相关记载:
刻(劾)下,与休(攸)守(134)
根据以上记载,县廷令史的职能十分复杂。《秦律十八种·置吏律》规定,官啬夫不在时,令史可以代掌其职。令史的职能几乎涵盖了县廷日常行政的各个方面。然而,令史身为县廷的属吏,如果职权甚大,显然与“斗食令史”的秩次不符。分析其职能与办公过程,明显可以发现,县廷令史常以诸曹主管者的身份出现,多与其他吏员一起协作完成工作。因此,县廷令史仅仅是县廷行政中比较重要且职能较广的属吏,虽然职能众多,但通常只是起到了参与和协同的作用,令史没有属于自己的印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三、县廷令史的选任
有关县廷令史的选任,《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7]1720-1721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也有类似记载:
史,殿者勿以为史。(476)[4]80-81
虽然两处记载在具体数字上有所差别,但大体过程一致:史学童要先通过识字的考核成为史;之后,要通过多种书体的考核,成绩最好者才能成为县廷令史。但如果只有这种选拔方式,就意味着令史的选择范围仅为通过了史学童考核的史,且同一批史中只有一位。这样严苛且少量的选拔,明显不能满足县廷对令史的需求。因此,县廷令史应当还有其他来源。
睡虎地秦简的《编年纪》中,墓主人喜的生平记录证明了他是从其他史职中选任为令史的:
今元年,喜傅。(82)
二年。(92)
三年,卷军。八月,喜揄史。(102)
【四年】,□军。十一月,喜□安陆□史。(112)③
五年。(122)
六年,四月,为安陆令史。(132)
七年,正月甲寅,鄢令史。(142)[6]6
喜在秦王政三年升为史职,秦王政四年任安陆乡史,秦王政六年任安陆令史,秦王政七年任鄢令史。如此一来,喜是由其他职位被调任为令史,与前文史学童任令史的途径不相同。因此,由史学童两度考核成为令史并非是选任令史的唯一途径,县廷令史也可以由其他职位调任。
喜并非是非史学童选任为县廷令史的个例。在里耶秦简的一份伐阅簿中,也可以看到扣被调任为令史的记载:
资中令史阳里扣伐阅
十一年九月隃为史 □计 户计
为乡史九岁一日 年卅六(第二栏)
为田部史四岁三月十一日 可直司空曹
为令史二月(8-269)[1]125-126
扣从十一年九月升为史职起,任乡史九年零一日,任田部史四年三个月零十一日,任令史两个月。扣从乡史到田部史再到令史,主要依据其“功”或“劳”,并非是由史学童考核而来。因此,从喜与扣的仕宦经历可以明显看出,除了史学童的途径外,令史确可通过其他职位调任。
许多吏员都曾在迁陵县任过令史和令佐,且这两个职位并未有明显的先后区别。因此,令佐与令史之间的调任在县廷内部应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令佐转任为令史,也是令史选任中比较常见的途径。
结合以上材料,县廷令史的选任有两种途径:从史学童中选拔或其他吏职调任。相比而言,从史学童开始进行考核并选任的令史虽然可能质量较高,但数量较少;调任应当是更为普遍的令史选任方式。
四、县廷令史的待遇
县廷令史的待遇问题,首先应考虑令史的俸禄。县廷令史俸禄微薄,东汉的仲长统在《损益篇》中就提到过吏禄问题:“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8]1656秦因为重军用,吏禄较少;汉承其业,也没有改善吏员的秩禄。直到汉宣帝的神爵三年才给吏员加过秩禄:“秋八月,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7]263宣帝在诏书中强调了小吏俸禄微薄,可见至少到宣帝时期,吏禄仍十分微薄。张家山汉简的《赐律》中有“斗食令史”,说明令史的秩次为斗食。《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一条记载了“斗食”的俸禄:“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7]274也就是说,县廷令史的秩禄不到百石。
既然基层吏员们的俸禄如此微薄,那么不管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还是为了稳定吏员使其能够继续在县廷中工作,吏员们都还需要其他收入。
官啬夫免,复为啬夫,而坐其故官以赀赏(偿)及有它责(债),贫窭毋(无)以赏(偿)者,稍减其秩、月食以赏(偿)之,弗得(82)
居;其免殹(也),令以律居之。(83)[6]39-40
此条简出自睡虎地秦简的《金布律》:如果曾经被免官的官啬夫又重新任啬夫,而无法偿还赀债,可用其秩禄和月食分期偿还。吏员的秩次是固定不能更改的,那么这里“稍减”的“秩”就不是秩次而是秩禄。
从“月食”的名称来看,便知其是按月发放。既然整理小组将“稍减”释为分期扣除,那么月食和秩禄就不应当是一整年积累下来扣除,而应当是按月扣除,月食和秩禄既然是按月扣除,那么也应按月发放。换言之,秦至汉初的县廷令史的秩禄是月薪而非年薪。
至于“月食”的具体意涵,高敏理解为“廪给制度”[9]216-219;安作璋认为是按月供应的口粮[10]。结合睡虎地秦简《司空律》中的一条:
官长及吏以公车牛稟其月食及公车乘马之稟,可殹(也)。(128)[6]50
官长和吏可以用公牛车去领自己的月食和官有驾车牛马的饲料,二者可以一起去官府领,说明性质类似,既然后者是官有驾车牛马的饲料,那么前者也应当是每月由官府供给的粮食。因此,应将“月食”理解为官府每月发放给吏员的口粮。
除了俸禄和月食,县廷令史还有“赏赐”作为收入,但赏赐是按照秩次高低排序的,令史作为斗食吏,得到的并不多;且赏赐也不常有,令史不可能将赏赐作为主要的收入。因此,令史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秩禄和月食。
令史也能享受到官府的一定优待。“吏归休”一条中,县官吏休假回家可以用县廷的乘马。“官长及吏以公车牛稟其月食及公车乘马之稟”一条中允许县官吏使用公车乘牛马领取自己的口粮,不必靠人力背回。
吏员也有休假。岳麓秦简中“吏归休”“己卯归休”“戊戌腾归休”,张家山汉简中“诸吏乘车以上及宦皇帝者归休若罢官而有传者”等记载,都说明秦至汉初的吏员有休假制度,那么县廷令史也不当例外。张家山汉简《置吏律》中详细规定了吏员的休假时间:
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岁予告六十日;它内官,卌日。吏官去家二千里以上者,二岁一归,予告八十日。(217)[4]38
县廷令史属于简文中的“吏”及“吏官”,按律令规定,每年有六十日的假期,如果离家较远,则两年一休,假期为八十日。
秦至汉初县廷令史的主要收入为按月发放的俸禄和月食,偶尔会得到一些赏赐。县廷令史的秩次为斗食,俸禄不高,每月仅有不到十六斛,十分微薄,属于令史的基础工资;月食是官府发放的口粮,类似补贴;赏赐最不稳定,且受秩次影响,所得不多。县廷令史可以有一些使用公家车马的优待,并且有休假制度。但总的来说,县廷令史在秦至汉初的待遇不算太好。
秦至汉初,令史普遍地设置于县级政府,在基层行政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余一些机构虽然也设有少量令史,但并未形成体系,令史群体仍以县廷令史为主。随着基层行政制度的日益发展与完善,各职位间的职能分工变得更加明确,秦时临时性的诸曹系统变得普遍、规范,曹内置掾也使得诸曹与令史相对独立;同时,由于令史是县廷的属吏而非县长吏的属吏,在职能分工越发明晰的过程中,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县廷令史逐渐减少。但因为令史在文书行政方面的能力,其他机构,尤其是中央公卿,仍需令史处理文书事务,令史也由此逐渐从县廷消退,更多地以秘书的身份出现在中央公卿的属吏队伍中。
注释
①刘晓满列出令史具有主典文书、主管籍账、参与司法审判工作、管理仓库、镇压盗贼和举劾官吏的职能;王斌帅认为令史有主典文书、监察和接受其他派遣的职能;刘向明则认为令史具有管理行政文书、司法文书、士兵名籍、人口户籍和档案库房的职能。具体论述参见刘晓满.秦汉令史考[J].南都学坛,2011(4):14-19;王斌帅.秦汉县廷令史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7;刘向明.从睡虎地秦简看县令史与文书档案管理[J].中国历史文物,2009(3):72-78.
②以严耕望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令、丞、尉各有属吏,县令史只是县令的属吏;以高恒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令史是县廷的属吏。
③喜在秦王政四年十一月应任职为安陆乡史,参见陈侃理.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喜”的官历[J].国学学刊,2015(4):4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