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陈氏家族的文学取向与近代文化变革
2021-12-27杨文钰
杨文钰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陈氏家族在晚清民国时期文化家族中颇具声望,凡论文化世家,陈氏多在其列。吴宓曾以“文化之贵族”称之,认为陈氏一门是“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1]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1560但相较于根深流长的吴越钱氏、吴门潘氏等世家,陈氏家族的崛起要晚得多。传统文化家族的鼎盛,往往需要持续的量与质的双重积淀,而陈氏的崛起,具有在不长时期中集中爆发的特点。时局的动荡变化为陈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遇,诗书传家、务实经世的家族精神也使陈氏一门得以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以文化家族之名为世人所重。
晚近时期文化家族众多,陈氏自有其独特性、典型性。其发家路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家族,其文学取向又有别于变革的主流。彼时的士人学者皆面临着文化转型及发展方向的抉择:民族的还是世界的?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改革的还是革命的?陈氏一门以其发展历程及文化成果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以民族为本位,才有与世界对话的底气;钝感保守中需有所坚持,才不会在激进的浪潮中迷失自我。陈氏家族的文学取向与近代文化变革方向既有牴牾,也有暗合之处。
一、作为晚清文化家族的典型性
清代文化家族的发展自咸丰朝始,呈现出两个异于以往的变化特征,一是清中后期面临内忧外患,传统文化家族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力量逐渐弱化,且文化特质逐渐式微,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对清中后期文化家族的发展造成较大阻碍;二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实用主义与重商主义在世变之下得到推重,市民阶层崛起,社会实力与日俱增,传统文化家族的部分话语权转移到了新兴商贾家族手上。在此背景下,江西义宁陈氏却以文化家族的身份崭露头角,成为晚清民国时期较负盛名的文化家族之一,这得益于时运与实力的双重加持。正是因为祖辈的积累、家学的传承与对机遇的敏锐把握,陈氏家族成为此时期具有独特典型意义的文化家族范本,既展现了文化家族在世变时期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为文化家族这一传统群体形式在大变革时代的发展与转型提供了新思路。
陈氏家族在晚清文化家族群体中的典型性,首要表现为向上发展过程中的厚积薄发与蹊径另辟。江西陈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望族,不同于既有前朝先祖积淀、子孙辈又在新朝锐意科举、三代皆是进士的京江张氏家族,也不同于通过科举实现阶级突破,由普通庶族上升为文化望族,绵延八代而为“科第人文之盛”代表的吴门潘氏。陈氏从陈公元(1711—1795)“以好义乐善闻”[2]黄文棨《大学生鲲池年伯先生墓志铭》,18,到陈宝箴(1831—1900)以“封疆大吏”名,仅有百余年时间。这百余年间,陈氏家族取得了不少成果:陈克绳(1760—1842)兄弟四人成为义宁地方士绅代表,“完成了从棚民到耕读之家的转变”[3]195;陈伟琳(1798—1854)曾创办梯云书院引领地方学风,后又组织义宁团练,义宁陈氏开始声名外扬。而陈宝箴于咸丰元年(1851)乡试中举,则意味着陈氏家族在文化上始有所成,毕竟此前陈家四代均名落孙山,未能得举。
陈氏家族的文化崛起似乎应当由陈宝箴中举而得以起步,只是他赴京两试均不第,家族到底未能经由科举而仕途大通。但在京期间,陈宝箴敏锐地把握住了良机,先是咸丰十年(1860)献计运粮初立声名,又在同治二年(1863)入曾国藩幕,同治三年(1864)入席宝田幕后屡立战功;同治九年(1870)得任湖南候补知府,由此开启了他的从宦生涯,后官河北、浙江、湖北等地。光绪二十一年(1895)经荣禄举荐,陈宝箴得任湖南巡抚,领导了颇有时誉的湖南新政,陈氏家族在近代政坛的地位亦随之日涨。由棚民到湘抚,陈氏祖孙四代通过实干,实现了一步一个脚印的阶级跃升。此时陈氏家族为世人所重的,是陈宝箴的政绩,而在文艺界的影响力的提升,则是由陈三立(1853—1937)及其子辈完成的,但这也得益于祖辈对家学与教育的重视。
经史诗书传家的文化坚守特性,亦是陈氏家族之所以特立于晚清众家族的原因之一。陈氏在竹塅的新居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落成,陈公元名之曰“凤竹堂”,以寄“盖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实,后之子孙,必有仁居义由昌大乎门闾者”[2]陈光祖《凤竹堂屋记》,19之期望,陈氏家族对人格理想的追求也由此定下基调。陈伟琳对子辈的教育问题十分重视,自陈宝箴乡举后,“益督以学”“日取经史疑义相诘难”[4]郭嵩焘《陈府君墓碑铭》,1856。陈宝箴的发迹虽由实干政绩而起,但对为学之道始终坚持不殆,强调子孙读书作诗须“志超流俗,诗不求佳,然志气高矣。又当俯仰古今,读书尚友,涵养性情”,“摆脱一切流俗之见,高著眼孔,拓开心胸”。[4]《书塾侄诗卷》,1841其子陈三立更是看重家学的教育作用,以为“天下之变既亟矣,人才窳下、风俗之流失,寖以益甚,察其所由,自一人一家子弟之失职始也。……世之君子,究知礼乐之原,其尚加意于此哉?余故取而论之,以明王政之所见端。若夫勤学之方,因材之等,达于世变,而无悖于古”[1]《菱溪精舍记》,781-782。
陈氏家族不仅看重后代的教育,对地方的教育事业更倾注了不少心力。陈伟琳认为“士失教久矣,自天下莫不然,独义宁也与哉!诚欲兴起人才,必自学始”[4]郭嵩焘《陈府君墓碑铭》,1855,因而倡建梯云书院,致力于义宁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陈宝箴就任河北道期间创建致用精舍,巡抚湖南时期创办时务学堂,亦为人才培养做出诸多努力。光绪二十九年(1903),陈三立大力支持柳诒徵等人创设思益小学,可谓承先辈之志。若无几代人对教育的看重,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陈氏一门在文艺领域,特别是在诗坛上的大放光彩。虽然陈氏的诗名自散原而大彰,但其先辈亦能诗。陈伟琳著有《北游草》,“诗尤长,而不乐为名,故世亦莫能知”[4]郭嵩焘《陈府君墓碑铭》,1856;陈宝箴存诗不多,虽不以诗名闻世,而所作“精粹有法”[5]《故湖南巡抚义宁陈公墓志铭》,524,郭嵩焘称其“诗笔亦极工雅”[6]71。
陈氏家族的崛起与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息息相关。维新运动是清代末期的重大社会事件之一,伴随着诗界革命的开展,清代诗歌因此增添了许多慷慨激昂的肝胆血性,诗史上亦留下了戊戌变法诗歌与诗界革命重要而辉煌的篇章。而维新运动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难以拯救深陷政治危机的国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陈氏家族的发展逐渐偏离政治、转向文化。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陈宝箴与子三立均因此被革职永不叙用,两年后陈宝箴逝世,陈三立备受打击,自此绝意于仕进。“文学家往往需要借由事件形成介入历史、推动历史的力量”[7],戊戌变法时期陈氏父子的经历,不仅体现出文学家是如何通过参与政治事件进而发挥自己的力量,更反映了事件,特别是重大的、典型的社会事件同样反作用于文学家身上,且影响可能更为幽微深远。陈氏家族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也自散原始,经由子辈发扬光大,最终以文化家族之姿特立于近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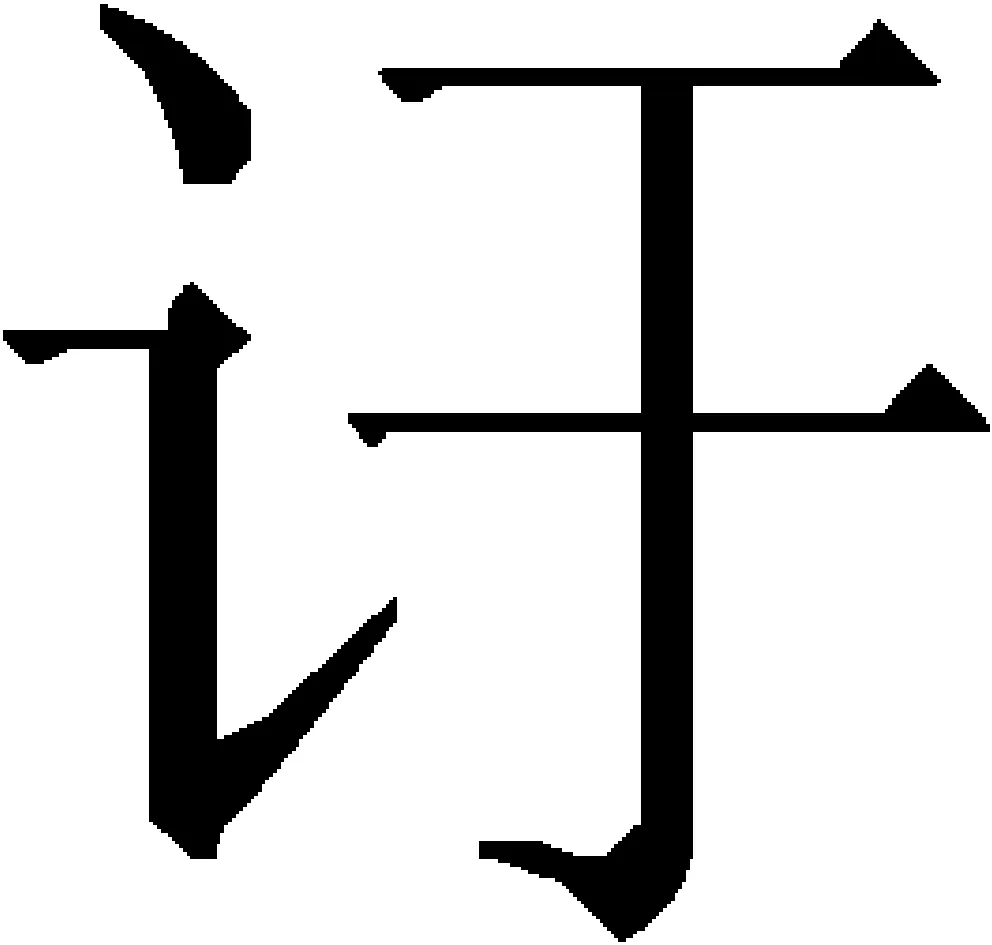
关于陈氏兄弟诗学成就的评价,陈衍曾言:“散原诸子多能文辞,余赠师曾诗,所谓‘诗是吾家事,因君父子吟’者也。”[11]《石遗室诗话》,285胡朝梁曾感慨:“陈家兄弟文章伯,佳句流传江海间”[13]《赠陈师曾时师曾自日本归》,34,可见陈氏一门诗艺之传续。钱仲联先生谓:“寒柳亦能诗,而功力不能与其兄衡恪、隆恪敌,亦非如其季方恪诗之风华绝代也。”[14]50陈声聪则言:“散原老人诸子,皆工诗,皆不为其父之诗”[10]177,“彦和(衡恪)之诗,亦不主一家,大体近涩,论功力,有过于师曾、寅恪,而聪明微不及师曾,才气微不及寅恪云。”[15]169以上所举诗论,评点各有所重,但总体上,陈氏兄弟的诗词创作,是受到近代诗坛广泛认可的。
从陈三立到陈氏兄弟,陈氏一门在近代文艺界的影响日渐扩大,从诗坛到画坛,再到学术领域,陈氏兄弟的文化地位逐步上升巩固,于20世纪前中期达一时之盛。值得注意的是,从陈宝箴发迹,到陈三立执诗坛牛耳,再到陈氏兄弟几人的光大,陈氏家族在晚清文化领域的影响是由单一而多元的,从政坛到诗坛,再到文艺界、学术界的多方位辐射,陈氏家族所取得成绩突出且实至名归。相较于如德清俞氏这般从俞樾、到俞陛云、再到俞平伯的单线性发展的文化家族,陈氏的家族继承发展呈现出由一到多的正金字塔形的分布;再如广东新会梁氏,与陈氏家族同期,亦是近代史上颇有影响力的家族,从梁启超、梁启勋、梁启雄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达、梁思宗、梁思礼等,涵盖的领域从政坛到学术、军工领域,梁氏诸人均取得辉煌成就。相较之下,陈氏家族则有着文化家族的“纯粹”,领域的相对固定和家族的持续影响,使陈氏家族在晚清乃至近代的众多家族中,既多了几分特异,又多了几分难得。
二、文化保守主义的钝感力
清末民初的中国处于风云激荡的变幻之中,文化思想领域不断涌现新主张、新提倡,新变是此时的主题。陈氏家族作为当时颇有名望的文化家族,却未一味迎合新变的潮流,总体呈现出有所不变、有所变的保守姿态,不变在于钝感,变则体现了钝感的力量。这种态度,与陈氏家族并非传统的簪缨世家出身有一定关系。他们对部分传统文化的维护,与对激烈革命的反对,实是源于文化观念,而非出于阶级利益。相对于激进派的热烈,陈氏家族展现了一种较为迟缓、相对淡和的钝感力。这种文化观念上的钝感,一方面表现为对激进革命的抵抗、退守;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防御性的精神力量,钝感力也发挥着相应的作用,钝而不冷,有感则鸣,众人秉持着家族一贯的文化主张,坚持在以传统为归的基础上实现进取。
陈氏家族在文化观念上的钝感力,首先表现为对传统纲常文化精神的扬弃。晚清时期,以科技为主的西方文明不断冲击着中国社会,功利主义应和变革的需要,成为大势;个性解放、文明重造是当时部分知识分子所欲实现的目标。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的陈氏家族,虽然积极参与维新事业,对激进革命却不大认同。他们认可个性解放,却对文明重造惕惕不已,认为个体精神须有所恃,因而选择钝化彼时革命的热烈尖新,在维护部分传统纲常伦理、认可以家族为单位的群体结构的能量的基础上,强调保国保种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陈三立就有“天下之变既亟矣,人才窳下、风俗之流失,寖以益甚,察其所由,自一人一家子弟之失职始也”[1]《菱溪精舍记》,781-782的感慨,虽然此时西方的文明思想学说还未在中国大范围传播,但陈三立已经察觉到人才的寥落、风俗的流失等问题的严重性,认为人才的培养、风俗的导引、政局的应变须从一人一家的基本单位开始,而后才能拯救社会大局。随着西方文明思想在国内的影响日益扩大,传统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以君父为根基的纲常伦理秩序备受抨击、摇摇欲坠,前半生致力于维新事业的陈三立对此却无积极响应,反而持论“宗法,吾国之所独也。世方以为病,欲一切扫荡之,以拯贫弱,跻富强。……夫治乱更迭,文质递邅,若循环然。由今之道,吾未见其可常也,不靡而从之,因民之所习,存什一于千百,剥极则复,又恶知夫文翁、信国、壮烈之治行节义,不重光于天壤也?吾将于宗法之不尽亡者卜之矣”[1]《萍乡文氏四修族谱序》,1139,又将宗法纲常进一步申论为“保种保国”[1]《光裕堂修义宁陈氏宗谱序》,1370,强调变世之下,有固守而不能失者、不容少变者,以纲常秩序为中心的立人之本、社会基础即在此列。陈三立所看重的,是家族、家庭对个体的导引与凝聚作用。
陈寅恪在此观念上紧随其父,将作为秩序与原则的纲常进一步延伸为理想精神,以为“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16]《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12,将纲常文化由行为准则进一步凝练为精神指导。在陈寅恪的论述中,纲常减弱了形而下的器之用,更多地体现出形而上的道之本。在他看来,纲常的崩裂,是文化精神的溃散,表现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16]《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12的殉道行为。纲常在陈氏父子相续之中,由器而道,他们持论社会经济制度可依时而变,而文化理想之道却不可弃,惟有如此,个体方可成为有道德、有理想、知行合一的人,人人如此,则家庭和谐;家家如此,则社会稳定富强。陈寅恪一方面强调个性解放,持论为人治学应当保持自由与独立,剔除了纲常伦理中禁锢个体发展的缺点;另一方面,他还认为“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17]《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261,斯文之传统或有朝重新受到重视,学者应基于传统,取外来之学说以固己本,而不能一味地全面否定传统。
由重家族进而重民族,是陈氏坚守传统文化的又一表现。从陈三立的保种保国论,到陈寅恪的民族精神论,“中国”“中华”的概念是扩展了的。在陈寅恪的论述中,中华民族以文化精神为纽带,是具备同一文化意志的共同体。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直言“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8]200。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也持论“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18]79。中国的历史发展,包括了不同种族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与融合、改造,所以陈寅恪认为“国可亡,而史不可灭”[17]《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362。只要历史传统还在,只要文化精神仍在赓续,民族便可绵延不灭,“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19]9-10他将种族主义进一步扩展为文化精神上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改变无疑丰富了“中华”的概念意义,在文化精神层面尽可能地聚合了民族的力量,超越了政教的局限,以文化精神为载体,统归具有共同文化历史及精神基础的群体,进而壮大力量。
重视民族文化传统,既可视为陈氏家族的钝感表现,又可用以证明陈氏作为有影响力的文化家族,在近代承担了应尽之责。陈氏家族虽对新变不热烈追捧,但在继承传统以适变的道路上,始终发挥钝感之力量,在近代历史道路上踽踽前行。陈宝箴抚湘时推行各项维新事业:董吏治、辟利原、变士习、开民智、勅军政、公官权,究其思想主张,不难见出其身居官位的保守,但他的保守中又常有摇摆。光绪二十四年(1898),朝廷中关于康有为的人品学术争执不断。陈宝箴于5月27日所呈折子中有论:“当康有为年少时,……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伤理而害道。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20]《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材摺》,779又言“康有为可用之才、敢言之气,已邀圣明洞鉴。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20]《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材摺》,780。言辞之间虽不赞同民权、平等,但仍表现出对人才的维护,钝而不愚。陈宝箴所主张的救国之策,主要落于实业,尤其看重经济人才的培养:“夫善战者,师敌之长以制之。今且不较彼己之长短,不论彼之所以得,而先明我之所以失。盖中国自康、乾以来,承平日久,士大夫不务为实学,徒以虚美相高,竞尚考据、词章之习,争新斗巧,以博虚誉。……今幸朝廷振兴学术,诏开经济特科,以期造就人材,共为济时之彦。诸君既有志于学,正宜及时自奋,与同志诸人共相讲习,切磋琢磨,捐弃故技,以求振国匡时、济世安人之要道”。[4]《南学会开讲第一期讲义》,1932而他抚湘时期的种种举措,也足以说明他虽不主张民权平等,亦不激进,但仍取得不俗的成绩。
陈三立的思想承自其父,亦偏保守,因此初与谭嗣同交好,后期却分道扬镳,谭嗣同冲破网罗的决心与陈三立的“纲纪匪狡狯”[1]《读侯官严复氏所译英儒穆勒约翰群己权界论偶题》,83本质上是互相牴牾的。陈三立不满盛倡灭古擅新的时风,但也不全盘否定西方文明,主张有所取舍以为我所用,其诗中亦不乏新思想的阐述,如“公宫化杳国风远,图物西来见典型。安得神州兴女学,文明世纪汝先声”[1]《视女婴入塾戏为二绝句》,8“主义侈帝国,人权拟天赋”[1]《次韵答黄小鲁观察见赠三首》,75“日手东西新译编,鸾姿虎气镜台前。家庭教育谈何善,顿喜萌芽到女权”[1]《题寄南昌二女士》其二,87等。
陈衡恪作为近代画坛的代表,面对文艺界兴起的反传统潮流与西方文艺思潮,亦清醒地从传统出发,对西方艺术美学理念进行本土化融合。他认为美术可以表现国民之特性,重申中国文人画具有独特的文艺价值,所谓“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21]147。对于过分追求功利的文艺观,他也持反对意见:“或又谓文人画过于深微奥妙,使世人不易领会,何不稍卑其格,斯于普及耶?此正如欲尽改中国之文辞以俯就白话,……欲求文人画之普及,先须于其思想品格之陶冶;世人之观念,引之使高,以求接近文人之趣味,则文人之画自能领会,自能享乐。不求其本而齐其末,则文人画终流于工匠之一途,而文人画之特质扫地矣。若以适俗应用而言,则别有工匠之画在,又何必以文人而降格越俎耶?”[21]147在他看来,绘画作为艺术,具有形而上的精神引领作用,不能一味地就低适俗。而西方的文艺思想亦可为我所用,其要点正在于促进中国绘画自身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画是进步的且发达甚早,不必妄自菲薄,“说到进步的原则,就是由单简进于复杂、由混合进于区分,不拘滞、善转变。……文化以及各种学术之发达都是由这个涂辙,经这种阶级,缓缓儿往前进,所以我说中国的画也是这样。”[21]《中国画是进步的》,149他论画看重思想的转换求新,认为历代画作珠玉在前,但仍有“历史风俗画这条道路大可发挥”[21]《中国画是进步的》,152,他的《北京风俗图》正是传统而不失进步的绘画观的绝佳体现,在近代画界颇受认可。
陈寅恪则在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史学领域,实现钝感的前进。他认为本国之历史“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17]《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363,历史不仅涵盖本国之过往,更存有指导未来的经验。不仅如此,他还敏锐地察觉到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存在很大空间,“异族之史,殊方之文”具有重要价值,而统归于中国历史之下,一方面重新强调了本国历史的价值与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扩大了本国历史的研究面。他认为外国的学术思想不是不可借用,但要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本位,对外来学说加以改造,方能重振本国的学术研究。
就整体而言,陈氏家族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站在保守主义的一方,相较于革命的种种激情热烈,他们表现出迟缓甚至带有些许冷淡钝感的反应态度,但迟钝并非沉默,冷淡也不是冷漠,他们在诗学、绘画、史学等多个领域均不吝于表达己见,并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落实于实际的创作与研究过程,在盛倡学西方、反传统的近代,承担了作为文化家族的应尽之责。
三、新旧对蹠中的文化转型
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失败迫使清朝统治阶级不得不睁眼看世界,从器物到政治、文化,均求变以自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知识分子不断寻求济世救国的良方,思想启蒙与文化改革是他们寻求变革的重点,在文学领域,他们率先将目光聚焦于诗学上。清末的诗学变革,尤以同光体派的形成壮大、诗界革命与南社的文学革命为重,共同构成了晚清诗歌史最浓墨重彩的一章,它们或希冀赓续风雅,或期望化旧为新,但都难以对冲激烈的革命潮流,某种程度上亦是20世纪中后期旧体诗词没落的先兆。
以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体派(1)①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中,陈氏家族中有陈三立、陈衡恪、陈方恪被列入同光体派中;钱仲联先生的《近代诗钞》中,陈氏中人有陈三立、陈衡恪、陈隆恪在同光体派之列,由此可见陈氏子辈与同光体亦关联密切。在宋诗运动的基础上,经由地域辐射不断壮大,成为晚清中国诗学上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派。他们提倡学古人诗而应能自有变化,所谓“不肖不成,太肖无以自成”[11]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四,200“应存己……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奥,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1]吴宗慈《陈三立传略》,1512,主张创新而自成面目、超脱古人藩篱,但创作观总体上没有超越传统诗学和诗教观的范畴。他们多为传统士人,学术主张及创作均植根于传统儒学文化,是以他们虽积极参加维新事业,但于文化改革上,大多坚守传统,有“余作前儒托命人”[1]《余过南昌留一日渡江来山中适闻胡御史亦至有征刊豫章丛书之议赋此寄怀》,453“国之所以为国,一如人之所以为人,必有其本然之性质,浅之为语言文字,深之为风俗道德,而后政教施焉”[22]492等论说。因此,在文化变革时期,同光体派诗人因其根基深厚且影响广泛,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同光体也逐渐变成一个文化符号,被视为是守旧的一方;随着“诗界革命”“南社文学革命”“文学改良运动(文学革命)”等运动的开展,由革理想到反传统,新旧两大文化学术阵营逐渐形成对蹠之势。
1899年梁启超首次提出“诗界革命”概念,并倡导“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23]《夏威夷游记》,1826。1909年高旭发表《南社启》曰:“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24]499-500明言要一洗旧弊,倡导新风。汪兆铭所作《南社丛选序》说得更明白:“革命文学之采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成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一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25]1无论是诗界革命还是南社文学革命,在创作上虽主张不一,但仍立足于传统,他们所要实现的,是在旧体诗中融汇新语句、阐发新意境、表达新理想。文学的新旧之争,此时尚未呈现出势不两立的局面,旧体诗的创作仍被寄寓“新理想”。
但传统文体的内部革新终究难辟新境,近代文学改革的深入,总归要突破传统文体的限制,于是文学革命应运而生,明确表示与传统割席,期望破旧立新,新旧对蹠几成势不两立之局面。1916年胡适提出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要求全面摆脱传统的限制,包括语言、形式、典故等,强调全方位的独创。随后,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明言:“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26]相较于诗界革命与南社文学革命,胡适、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无疑是更为彻底的、决绝的。此后,文学革命进一步深化为新文化运动,影响日益深远。
胡、陈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时间激起层浪,响应者众,反对者也不少。1917年柳亚子再次揭橥文学革命之目的,谓“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27]。成舍我随后发文支持:“譬之于国,中国,格调也,专制共和,理想也。谓中国须由专制改共和可也。谓中国须改为英国,或改为法国,则又乌乎可哉!此足与亚子之论互相发明也。”[28]梅光迪更是直言:“独所谓提倡‘新文化’者,犹以工于自饰,巧于语言奔走,颇为幼稚与流俗之人所趋从。”[29]
在文化界颇有名望的陈氏家族,虽未明确直接地参与争论,但亦或多或少表露意见。陈三立于1931年所作的《朱鄂生真斋诗存序》中直言:“自鄂生卒后,运移祚覆,大乱益炽,匪徒斫杀焚劫之祸绵岁纪而盈宙合,而邪说充塞,蹄迹纵横,莽莽非人世,其狂逞几欲举古先伦纪道德典籍文字尽摧灭而变易之。”[1]《朱鄂生真斋诗存序》,1078陈三立对彻底的反传统主张是极为不满且痛心的。而陈氏子辈与胡适、陈独秀等人年龄相仿,成长、教育背景不无相似之处,对新文化运动却无甚好感,在“新”“旧”问题上,也不似胡、陈二人那般激进。
陈衡恪为《蜗牛舍诗》所作序中写道:“吾师周印昆先生论吾父诗为有清诗人之殿,亦旧诗之殿。时世日新,后之诗人所以自为所以讽人对物者,必大异于昔所谓新与旧也。彦殊年才五十,前所蕴藏与老辈若,后所感写又将何若?此不可有所假借,又无所用其依违,盖诗教转捩之键也。彦殊今之所以存者,予知之矣。陈、夏两公亦知之矣,予将持此以读其后此之诗。”[13]205此序作于1923年,此时文学革命已开展数年,对诗歌创作的新旧问题的讨论早已众议喧腾、态度各异。当多数人还在为内容形式、思想精神之新旧进行辩论时,陈师曾所论似已脱离诗体的新旧皮相,主张回归创作本位,即无论新旧,随着时间推进、阅历增长与学习的深入,评价诗人的标准其实在于是否能写出真正具有自家面目、具备独特价值的好诗,这也是“前所蕴藏与老辈若,后所感写又将何若”一语背后的未尽之意,此观点与他“所以能视听言动触发者,乃人之精神所主司运用也。文人既有此精神,不过假外界之物质以运用之”[21]《文人画之价值》,143的绘画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均强调创作中主体的重要性。
陈寅恪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较其大兄更为明确,甚至有直接互舛处,所论也不仅仅针对诗体变革而发,根本在于文化与学术精神,“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不能一味“偏重实用积习未改”。对于“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的主张,陈寅恪是不以为然的,他认为“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30]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4具体到用典、对仗等传统写作手法,陈寅恪亦与胡适之提倡多有异议。胡适认为用典是无才的表现,“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湾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31]。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中谈道:“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32]234他认为古典可用,难在用好,要能“融会异同,混合古今”,这是对作者能力的要求。关于对仗,胡适认为束缚创作自由,陈寅恪则以为“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33]164。
当然,陈氏家族中也有创作白话文学者,陈登恪曾于1926年用笔名“陈春潮”发表《留西外史》长篇小说,文风深受外国小说影响。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中也不乏旧体诗人,可见在变革的过渡时期,无论团体还是个体,在文学理念上或许各有主张,在实际创作上却不是彻底的泾渭分明。此时期的文学变革,既有明面上的新旧对蹠,也有潜藏的、隐性的文化转型蕴含其中,或自觉、或不自觉,体现在部分同光体派诗人的实际创作中,只是在变革的大潮流中,潜在的转型往往来不及被重视。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及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新文化运动,是清末民初时期政治与文化领域上的几次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仅在近代史与文学史上产生强烈震荡,亦对以传统为归的诗人影响颇深。因此,他们作品中不仅有反映传统的家国忧患与功业未成的焦虑,还有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斯文不再的忧虑;又因他们的坚持与变革主流不甚契合,进而引发对个体抒写的思考,着重于独立与自由两方面。从家国到文化精神、再到文化个体,体现出此时期的诗歌创作潜在的转变,表现为从政治附庸到文学本位,从公众属性到个体书写的思考及抉择。这一转变,较为明显地体现在陈氏家族两代人的创作中。
陈三立早年诗集《诗录》四卷多行旅酬唱之作,即使抒发一己之慨,也多带有社交属性,如《武昌提刑官廨除夕》:“氍毹行酒列华筵,澹沲花枝鼓吹边。几倚宾僚送歌咏,坐看江汉接风烟。镫迷游屐鱼龙市,星冷高城雁鹜天。四十无闻垂老大,愁从明日说新年。”[34]62基于个人功业的焦虑多少夹杂着时势与同侪的压力。陈宝箴的逝世,使散原对“家国”已有幻灭之感,尽管后期所集《散原精舍诗》中亦不乏酬唱,但总体而言创作的内容已向个体及自我倾斜,着重表现于西山崝庐系列诗中。1901年,陈三立写下《崝庐述哀诗五首》。在崝庐,他“昏昏取旧途,惘惘穿荒径”,痛呼“呜呼父何之,儿罪等枭獍。终天作孤儿,鬼神下为证”,亦自悔“儿今迫祸变,苟活蒙愧耻”。[1]《崝庐述哀诗》,16-17而后二十余年间,崝庐述哀与西山见感成为陈三立的写作主题。在西山崝庐,他回归了“儿子”的身份,却再无父亲可依靠;每次回到此处,入眼皆是空荒绝巘、云雾缥缈、山木森森,是不可探寻的茫茫天地,倍感“从知人间世,不值一杯水”[1]《崝庐写触目》,310、“人生顷刻不自保”[1]《庐夜风雨雷电交至晨霁倚楼眺西山作》,113。但自然天工的西山、幽寂宁谧的崝庐,又是陈三立“网丝存吾庐,擎烛悬余喘”[1]《渡江入西山晚抵崝庐》,406的精神栖息地。虽然在西山崝庐有过不少团圆欢景,喜乐的背后却始终盘绕着关于死亡与未来的双重迷雾。在此处,陈三立既是丧父的孤儿,也是文化信仰崩塌的孤儿,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依靠均已不再。因而他笔下的西山是片面化的、个体化的。这种片面化、个体化的呈现,有主观选择因素,譬如写西山崝庐的诗大多与扫墓、雨夜有关;另一方面则是陈三立的潜意识外化,“孤儿”身份将他的创作导向悲哀,使他不自觉地将西山塑造成了一处适合精神隐遁的悽然之境,这是主观对客观环境的有意识塑造。
无论是写扫墓、楼坐,还是写散步,在自我记录外都有主观改造的抒写,陈三立笔下的西山崝庐充满了自我色彩。他以自我尺度塑造了诗中的“西山”形象,且不是一时兴起、偶然为之,而是在二十余年内不断重复、强化,这一系列诗因而成为其作品中的独立系统,表现出“人文主义”文学的特征。只是陈三立的创作并非有意识地突破传统诗教的规束,也不是彻底的自觉,所以西山系列诗并非彻底的“人文主义”现代化作品,而是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充满了个体无依的焦虑与自我疗慰。陈三立的一生,疑惑无措是多于洞见觉悟的,深受文化背景体系与时代环境的影响限制。因此,其诗虽有不自觉的自我书写,但没有超越时代与文化的局限,其创作的整体风貌仍是传统的,但西山崝庐系列诗确实是此时期旧体诗中难得的、闪烁着现代化“人”的光芒的作品。在陈氏家族中,充分自觉的个体书写体现在陈寅恪的作品中。
不同于陈三立在诗中不自觉地以个人尺度进行创作,陈寅恪始终带有史学家的旁观与冷静。他在激烈变革中成长、老去,无法避免时局变化对个体的影响,却又试图与现实保持距离;所以在学术研究上执着追求自由与独立,在诗中时常感慨自由与独立的难得,强调自我独立,充满个性主义,这是其作品中人文主义的最直接呈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强调的人文主义,意在突破封建传统对所有人的束缚,所以此时提倡的“人”,是群体性的。而在陈寅恪的文化世界里,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是落在个体身上的。但人永远无法真正独立于时代与社会之外,保持自由独立是艰难的,因此,他在诗中反复感慨“不自由”(2)①如《阅报戏作二绝》“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戊寅蒙自七夕》“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
陈寅恪认为“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16]《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12。热烈澎湃的革命往往带有一丝不理性,个体也容易湮没于时代洪流中。旧有文化秩序的坍塌对社会全体造成影响,新的文化精神秩序的建立和塑造却只存在于小部分人之间。陈寅恪痛惜旧有文化秩序的消失,怀疑正在形成中的新的文化秩序,也认识到“大我”与“小我”在此时期不可避免的抵触,进而强调独立与自由,以自己文化观念上的“旧”对接当时层出不穷的“新”,以诗笔之冷对接时局变化之热。他多次在诗中使用“食蛤”之典,其情绪不是愤慨指责,而是冷冷讽刺,可见他在政治上,是抽离旁观多于热情参与的。他在诗中常以“惜花人”“看花人”身份自居,而看花、惜花又常与残春相联系,怀旧贯穿于日常生活,表现为对时间流逝的无措与对当下及未来的惘然,如《吴氏海棠二首》其二所写:
无风无雨送残春,一角园林独怆神。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闻道通明同换劫,绿章谁省泪沾襟。[16]22
时危世变与春残花落之慨是传统常见题材,陈寅恪将这两种变化置于同一语境下,并不断重复强调。两年后的春暮,他又写道:“无端来此送残春,一角湖楼独怆神。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16]《残春》,23对世运之劫与落花之命的探讨,固有评点时事之义,更多的是对春必残、花必落所代表的永远的循环变化,与“去年人”的不变身份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思考。春残花落看似无常,其实是不变的循环,去年人的“不变”在时间流逝中,其实是变化不再的,通过重复探讨花与人的对立,隐括个体想要突破现实的冲动。陈寅恪一生所经历的时局,处于不断的变化调整中,他却始终执着于“看花人”“去年人”的身份,对不断变化的现在始终保持抵抗,这是其诗中自由独立的个体主义的展现。
事件,激荡和改变了诗史。“研究事件如何构造诗歌的历史是立足于文学艺术的思维活动,是基于事件所包含的冲突性及其断裂、介入、融会的能量,蕴涵着对诗史改变、演化的动力源,具有诗史构造力。故建构事件诗史不在于发现作为诗人书写背景的历史动态,而在于发现具体事件中的诗人位置、精神状态和创作实践,在‘事件’与‘诗’的契合点中阐述某种关系。”[7]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新旧对蹠的文化转型时期,部分传统诗人面临着双重压力,在夹缝中试图寻找自我表达的途径,有焦虑,更有坚持,某种程度上亦反映出这一类诗人的坚韧品格。文化变革时期传统诗人的心绪转变,可用陈方恪《风日始晴美偕友吾薄饮市楼赋此眎之》诗句概括:“古今患难生,虽云同一轨。惟兹大祸源,开辟绝坟史。玉烛不能调,璇玑讵可拟。浡潏隳天纲,隄防在人纪。惨黩无穷期,遘迕正伏倚。吾侪猥小民,微命寄蝼蚁。掉转风轮中,何能虑终始。但愿保岁朝,得以亲耒耜。”[35]28从家国忧患到文化焦虑,从功业未竟的无奈到蝼蚁微命的自我展现,方恪与寅恪均不惮于在作品中表现个体的微小与无力。事实上他们在各自的人生中是顽强的、尽责的,譬如陈方恪于1942年后便参与了地下抗日的秘密工作,被严刑拷打也不曾开口泄密。在现实生活中,陈氏诸君皆是有风骨的、脚踏实地的,他们的诗作中不仅有传统的群体性的家国忧患、风雅焦虑,更有对独立自由、个体表达的正面输出。
四、结语
近代历史进程呼吁破旧立新,频繁发生的政治与文化事件为近代历史与文化史增色添彩。陈氏家族则以钝感保守之姿持旧求新,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陈宝箴完成了陈氏在政坛上的首次亮相,陈三立则在文学界实现了家族的艺文转型,陈氏兄弟五人则实现了由艺文而文化的转变,他们证明了个人本位主义并不囿于家族这一形态,家族亦会为个体追求自由独立提供物质与精神支持。一门风雅,当之无愧,陈氏诸人皆创作出较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保留了群体性的关于变革的激烈的时代记忆、关于家国的伤痛,也保留了个体的呐喊与彷徨。以陈氏家族为例,可见近代变革时期,社会事件、地域、学术、社会身份等多重因素对家族发展的影响,陈氏作为坚守风雅的典型样本,仍有等待进一步挖掘的文化价值。
家族制度由于其宗法性质,在近代被视为洪水猛兽,是亟需被批判、被推翻的存在。陈独秀曾言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36],个体与家族在此论中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家族制度也绝非全无益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家族形态会形成一股较为稳定的力量,而家族文化也在代代相续中发挥其培育人才、凝聚精神的作用。“欲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必当注意研究中国之家庭”[37]《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199,家庭、家族往往是社会的缩影。从陈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中不难见出“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实”这一文化理想的实践,既有家风延续的必然性,又侧面反映出在动荡的近代,坚守传统精神文化是艰难的。陈氏家族因文化而得其名,又因品格而成其实。文化二字不仅在于文学或艺术创作之成就,更在于“以化成天下”的影响与引导作用。无论是陈氏家人,还是喻兆藩、俞明震等姻亲,均展现了文化家族的正面导向意义。对于文化变革的方向,他们也用坚持给出了答案:“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17]《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246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士不仅仅是身份,更是品格与精神的彰显。尽管他们大多被视为是保守的同光体诗人、保守的文化遗民,但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上,对家国未来有忧虑、有努力,对个体发展有呼吁、有坚持。陈三立是晚清诗歌史中的一座高峰,而衡恪、寅恪兄弟几人则是近代不可多得的文化人才,面对潮激波荡的变革运动,他们秉持着自身的文化理想,坚守着一方中华文明精粹的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