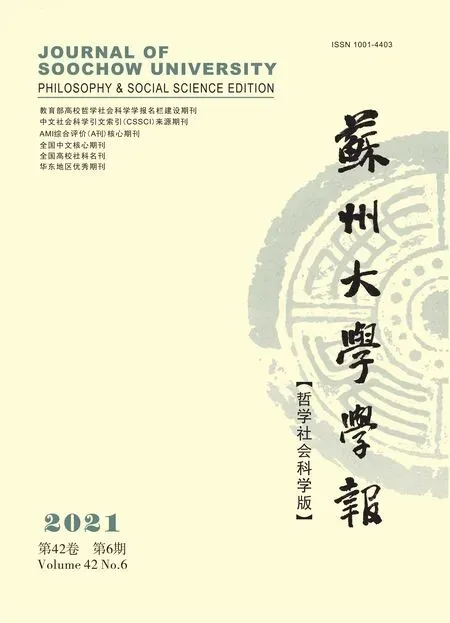论江声对历史命题“微旨”的阐发
2021-12-27钱宗武
秦 力 钱宗武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清代乾嘉时期,古文经学大盛,经学研究整体呈现出小学化特征,文字训诂、历史典章考证成为经学研究的主要工作。相比之下,对经典微旨的研究和阐发则鲜有学者问津。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是乾嘉时期明确以微旨阐发作为主要任务之一的经典诠释著作,凭借此书,江声得与王鸣盛、段玉裁、孙星衍并列为当时《尚书》研究四大家。这四大家中,王鸣盛《尚书后案》侧重《尚书》辨伪、《尚书》古文家说辑佚研究与《尚书》郑注研究,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与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侧重《尚书》今古文异文与《尚书》今古文异说的辑佚及研究,而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在博采旧注、解字析义、考证史实的基础上,尤重经典微旨阐发,在当时显示出较为独特的学术旨趣。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微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具体文史著作中微旨的考证以及对晚清学者微旨阐发的研究,对于微旨的类型、特征等本体研究尚待深入,对于江声微旨阐发的研究尚付阙如,对于清学学术大视野中的乾嘉古文学者的“微旨”阐发亦少涉及。本文且作椎轮为大辂之始,试就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对历史命题“微旨”的阐发及相关问题,论述如下。
一、“微旨”的类型、特征及江声“微旨”研究溯源
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微旨”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意义上,“微旨”泛指一切精深微妙的意旨或隐而未露的意愿,而在狭义意义上则专指《春秋》微言大义。《春秋·桓公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谷梁传》杨世勋疏引东晋江熙曰:
案宣四年“公及齐侯平莒及郯”,传曰:“平者,成也。”然则成亦平也。公与齐、陈、郑欲平宋乱,而取其赂鼎,不能平乱,故书“成宋乱”,取郜大鼎纳于大庙,微旨见矣。
而后释之云:
(江熙)以成为平,直书取郜大鼎,纳于大庙,足以示讥,是微旨见矣。[1]2373
据《左传》,鲁桓公二年春,宋太宰华督父攻打司马孔父嘉,且夺其妻。宋殇公怒,华督父因为恐惧遂弑杀宋殇公。鲁桓公与齐、陈、郑三国国君会于稷,本意当是平定宋国这场叛乱(“以成宋乱”),可鲁、齐、陈、郑四国却因为收受华督父的贿赂,反立华督父为宋相。其中,华督父将郜国大鼎作为贿赂送给鲁国。鲁桓公于夏四月将郜国大鼎从宋国取回鲁国,并于戊申日放入太庙,《左传》评此举“非礼也”[1]1740-1741。
《谷梁传》解“公及齐侯平莒及郯”经文谓“平者,成也”,江熙据此指出“平”与“成”字义相同。按:“平”“成”在文献中确可互训,《尔雅·释诂》:“平,成也。”《诗经·小雅·节南山》“谁秉国成”毛传:“成,平也。”但江熙随即又指出,在《春秋》经文语用系统中,一般平定叛乱只用“平”字,不用“成”字。此处《春秋》经文却用“成”而不用“平”,系辞例之变;再结合下文,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可知《春秋》此经之所以不云“平宋乱”,而变其例云“成宋乱”,实借此寄托微旨,隐晦表明桓公实不能平乱,且有违礼之举。
由上例可知,《春秋》“微旨”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主要依靠文句中个别字词展现;(二)往往违反《春秋》经文通常的字词使用习惯(辞例之变);(三)往往采用委婉表达方式,使得话语呈现出双层意义,既有表层意义,也有深层意义;(四)表层意义一般是文献故训中的常见义;深层意义与表层意义不同,需要结合经文语境方能显示;(五)通常涉及伦理价值判断。
自唐代以降,“微旨”一直是《春秋》学研究热点,出现了以“微旨”命名的《春秋》学著作,如唐代陆淳《春秋集传微旨》、清代雍乾间刘绍攽《春秋笔削微旨》等。而乾嘉学派吴派创始者惠栋,一家四代人(惠有声、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皆研治《春秋》。惠栋之父惠士奇著有《〈春秋〉说》,其中亦有对《春秋》微旨的探讨。
《春秋·僖公五年》:
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不盟。
《襄公七年》:
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郑伯髠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陈侯逃归。
《春秋》这两段经文所记述的都是诸侯会盟之事,且郑伯、陈侯皆逃归。既然皆“逃归”,则二人必然皆“不盟”。但是《春秋》载“郑伯逃归”后,特书“不盟”二字,而陈侯逃归,则未书“不盟”。对此,惠士奇分析说:
郑伯、陈侯皆逃归也,曷为郑伯独书“不盟”?郑伯独书“不盟”者,以后之乞盟而书。前之不盟者何心?后之乞盟者又何心?《易》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既会而不盟,不盟而复乞,郑伯之志乱矣。故《春秋》薄责陈侯而厚责郑伯。曷为薄责陈侯?陈邻于楚,楚之属国久已背晋而向楚,且陈之叛楚,由子辛。楚杀子辛而立子囊,遂改行而疾讨陈。陈有朝夕之急,能无往乎?则鄬会之逃,陈侯其何诛焉?《春秋》事同而文异者,必有微旨在其中。学者不可以不察。[2]882-883
惠士奇指出:“《春秋》事同而文异者,必有微旨在其中。”意谓如果《春秋》对相同性质事件的记载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则其中定有微旨。就此例而言,陈侯、郑伯皆会而未盟,中道逃归,之所以郑伯书“不盟”,而陈侯未书“不盟”,是因为郑伯后来复又乞盟。按:《春秋·僖公八年》:“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郑伯乞盟。”据《左传》,僖公五年,郑文公与会之时,周惠王遣使命郑国追随楚、晋二国。当时齐国国君是齐桓公,国力强盛,不臣服于齐国的唯有晋、楚二国。郑文公一方面“喜于王命”,另一方面害怕得罪齐国,故最终逃归不盟。虽大夫孔叔劝谏,谓“国君不可以轻,轻则失亲。失亲患必至,病而乞盟,所丧多矣”,但郑文公一意孤行。次年夏,诸侯即为郑文公“逃首止之盟”而伐郑。至僖公八年,郑文公慑于齐国声威,主动向齐国乞盟[1]1795-1799。经文于僖公五年书“不盟”,正是照应僖公八年之“乞盟”,以讽刺郑文公无原则的骑墙态度。相比之下,陈侯于会盟时逃归,实属客观情势急迫,不得已而为之。起初陈国归服楚国,楚国令尹子辛贪得无厌,欺压小国,导致陈国背叛楚国。后来楚国杀子辛,另立子囊为令尹,并派军队包围郑国。在这种危急时局下,陈侯首先选择向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诸国求救,无奈时局迅速恶化,为了存国,陈侯不得不返回陈国,臣服于楚。[1]1930-1939因此,《春秋》没有对陈侯进行严厉贬斥。此外,除明言“微旨”外,惠士奇有时亦称“《春秋》之微辞”[2]884,意义与“微旨”相同。
当然,学术史上,对“微旨”的探讨也并不局限于《春秋》学,非但在经学、史学著作中常见,甚至如道教、佛教论著乃至中医论著中,亦皆可见。道教、佛教以及医书中的“微旨”意义大都已泛化,不再关涉伦理价值判断;但是经学、史学著作中对“微旨”的阐发,则与《春秋》“微旨”关系紧密。惠士奇之父、惠栋之祖惠周惕著《〈诗〉说》,其书解《诗经·卫风·硕人》云:
《诗》美王姬则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美庄姜则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美韩侯则曰:“汾王之孙,蹶父之子。”(1)①今按:《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毛诗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据此,本句当作:“美韩侯之妻则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永嘉陈氏曰:“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亲也。”余谓诗人之意不止此,盖有重婚姻、别姓氏之义焉。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卫宣公为子娶于齐而自为,则婚姻乱矣。聃叔娶于郑,晋献娶于贾,鲁昭娶于吴,则姓氏不辨矣。惟为明著其所自来,曰此某氏之男、某氏之女,则显然有卑不得配尊、贱不得配贵、同姓不得通婚姻之义。此诗人之微旨,《春秋》之笔法也。故太史公作《外戚传》,惟窦太后曰“良家子”,余则曰“生微”,曰“故倡”,曰“母臧儿”,其亦诗人之意也夫。[3]
惠周惕总结《诗经》辞例,推断《诗经》之所以在歌颂王侯之妃时介绍其父祖,隐含之义则是凸显“重婚姻”“别姓氏”的义法,表明婚姻合乎礼制。惠周惕将之概括为“诗人之微旨,《春秋》之笔法”,可见他实将《诗》之微旨与《春秋》微言大义相类比。由此至少可以说明,在惠周惕的认知中,“微旨”确与《春秋》“微言大义”同义。不仅如此,惠周惕是在《诗经》研究中将《诗》之“微旨”与“《春秋》笔法”相联系,可见“微旨”作为历史命题,正渊源于《春秋》学,而其应用范围亦当是由《春秋》学延展到其他经史著作的研究中。惠周惕于文末联系《史记·外戚传》对皇妃出身的介绍,亦当是直接基于《史记》与《春秋》之间的联系。表面看,其谓太史公“亦诗人之意也夫”,似是将《史记》与《诗经》直接联系,但一方面,根据此处文势,“故太史公曰”等语系紧承“《春秋》之笔法也”六字,当是直接由此六字引发联想。另一方面,从文献性质看,《春秋》与《史记》虽然一为经书,一为史书,但其实都属史家之体。《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大事编年,实属史书范畴。《诗经》与《春秋》虽同为经书,但其实前者属于诗体,是文学性著作。因此,惠周惕虽称太史公“亦诗人之意也夫”,其实是以《春秋》作为中介桥梁,只是因为他的这部著作是《诗经》研究著作,为凸显《诗经》价值,才称史公“亦诗人之意”,而未称“亦《春秋》之微旨”。总之,作为历史命题,“微旨”实源自《春秋》学。另外,上述分析还说明,直到清代前期,“微旨”依然是经典诠释的重要研究课题。特别是作为吴派宗师惠栋学术渊源的惠周惕、惠士奇父子,他们已尝试将考据学方法与“微旨”研究相结合,并能将“微旨”阐发扩展至《春秋》以外的经典诠释中。
然而,至乾嘉时期,随着注重文字训诂和历史事实的考据学风的兴盛,对微旨的研究依然不可避免地遭到学界的批判乃至反对。比如与乾嘉吴派颇有渊源的钱大昕(2)②今按:多数学者认为钱大昕属于吴派,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参见王记录:《钱大昕是吴派吗?——兼谈乾嘉学术派别问题》,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不过,钱大昕是嘉定人,且与王鸣盛等吴派学者学术交流紧密,又是王鸣盛妹夫,称其与吴派学术颇有渊源当无问题。认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4]350吴派学者王鸣盛也谓:“《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5]474-475由钱、王两家论述可知,当时对“微旨”研究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传统学术的“微旨”阐发具有较大随意性,学者多主观发挥,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大多逐渐放弃对“微旨”的研究。而与王鸣盛年龄相近且同为吴派学者的江声,却能绍继惠周惕、惠士奇等清代前期学者,摒弃传统学术“微旨”阐释的随意性,发扬乾嘉考据学的严谨性,将传统学术的精髓与乾嘉考据学融为一体,在吴派学术乃至乾嘉汉学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二、经、注微旨推阐路径:“异”中识微,考据立旨
江声是乾嘉时期吴派著名学者,师从吴派宗师惠栋,其声名最显赫者在所著《尚书集注音疏》一书。江声在《尚书集注音疏》中十分重视对微旨的阐发。这从其对《尚书集注音疏》书名的解释中就能看出:

江声对“注”的定义因袭自孔颖达。孔颖达谓:“注者,著也。言为之解说,使其义著明也。”[1]269江声指出,集注,即“亼(集)合先儒之解并己之意”,目的在于“箸(著)明经义”;而疏的目的则在于阐发经与注中蕴含的微旨。
(一)根据字面义与文献记载的矛盾推阐微旨
例如《洛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江声注云:
疏云:
《洛诰》此句经文系周公追述当年代成王摄政之事,“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其字面义为“王若弗敢逮及文王、武王所受天命”[6]549,即周成王仿佛不敢继承周文王、周武王所接受的天命,亦即不敢践天子之位。按:蔡沉《书集传》云:“成王幼冲退托,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7]98可知蔡沉已将“成王幼冲退托”与“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相联系。江声“不能”之说,实源自蔡沉,但与蔡沉相比,他明确阐释了“不敢”二字背后之微旨。江声据《礼记·文王世子》,指出成王当时年纪尚幼,尚不具备践位亲政的能力,因此,成王当时没有践位,实是客观条件使然,而非成王主观态度上“不敢”。可如此一来,《洛诰》经文即与《礼记·文王世子》所载相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江声推阐“不敢”二字微旨,指出周公作为臣子,理当为王者讳,径称王“不能”做某事需要慎之又慎,一般情况下不可称王“不能”。因此,周公遂变其辞,将客观上的“不能”表述为成王主观意志上的“不敢”,使成王不践王位看上去仿佛出于主动选择。经过江声阐释,则“不敢”的深层含义其实是“不能”,周公将“不能”表述为“不敢”,既显示了成王的谦冲圣明,同时也强化了自身为王者讳、谨遵君臣之义的贤臣形象。
(二)根据异文推阐微旨
例如《微子》:“我用沈酉句于酒,用乱败氒(厥)惪(德)于下。”江声注“我”字云:
我,我纣也。
疏云:

此句是微子对父师、少师所说。经文此句上句为“我祖厎遂陈于上”,江声据马融注及孔传指出“我祖”指成汤。此句“于下”与上句“于上”对言,“我”亦与上句“我祖”对言,故知此处“我”当指与先王成汤相对的当世之王,亦即纣王。但江声不满足于上下文语境推理,指出《史记》录《微子》此句径作“纣沉湎于酒”,知西汉时太史公即解“我”为“纣王”,从而增强结论可信性。但是,《微子》篇中微子数称“我”,绝大多数都是指微子自身,此处微子指称纣王,为何不径称“我王”或“我君”,而单言“我”?与《微子》同属《尚书·商书》的《盘庚》篇即载盘庚臣民抱怨之言:“我王来,即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1]168即以“我王”与“先王”对称。对此问题,江声解释说,微子愤懑于纣王之所作所为,本欲直言“我君”,但“为王者讳”的观念最终阻止其直斥君王之恶,故而在说出“我”字后隐去了“君”字(或“王”字)。江声通过异文材料,判断出此句“我”实指纣王,而非说话者微子自称,进而对“我”字微旨进行阐发,表现了微子在“忧国忧民”与“为王者讳”之间的矛盾与挣扎。微子最终只称“我”,未称“我王”,大有别于普通臣民百姓,更凸显出微子谨遵君臣之义的忠臣形象,进而反映出传统儒家“尊尊”“贤贤”的理念主张。
(三)根据词义色彩演变推阐微旨
《大诰》篇首“王若曰”,江声引郑康成曰:“王,周公也。周公凥(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而后疏之云:

关于《大诰》“王若曰”之“王”是指成王还是周公,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大诰》“王若曰”系周公代宣成王之命。江声首先引据《礼记·明堂位》的相关记载,表明周公摄政时确已称王,至少是名义上的假王。接着又根据《尚书·周书·多方》及《多士》篇辞例,指出倘若《大诰》“王若曰”系周公代宣王命,则当明确区分周公与成王的身份,或如《多方》篇云“周公曰‘王若曰’”之例,或如《多士》篇先以叙述性文字交代此篇系周公诰辞,于诰词中再言“王若曰”,然《大诰》开篇径言“王若曰”,之前并无“周公曰”或其它说明性文字,加之《大诰》所记又是周公摄政时事,故“王若曰”之“王”正当指周公。但郑玄注在明确“王”指周公后,又进一步解释说“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对于郑玄此解,江声尤其重视“权”字,指出“权”与“正”是相对概念,亦即权变之义。按:《说文解字》释“权”字义:“一曰反常。”与其他吴派学者一样,江声对《说文》极其推崇,然此处却未引《说文》为证,而是引《春秋公羊传》“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以为“权”字说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羊传》释义与《说文》同中有别。其同者,《说文》云“反常”,《公羊传》云“反于经”;而不同者,《公羊传》云“然后有善”,强调“权”的伦理道德属性,即行权动机当出于善,若出于恶,则不能称为“权”。此处江声引《公羊传》为证,不仅解释“权”的理性义,更主要的是为了说明“权”字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本具有褒义色彩,非如后世所谓“权术”“权诈”“权佞”等带有贬义色彩,避免读者误解郑注,乃至将周公与后世玩弄权术的权臣等量齐观。基于上述,江声进一步对周公行权称王的动机加以解释:根据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礼制规范,只有王才有权力处置国家重大事件,因此周公平时虽然为谨遵君臣之分而不称王,但当需要处置国家重大事件时,则惟有称王才合乎礼法。周公正常情况下不以王自居,而“命大事则权称王”,皆是符合礼义之举,证明了周公行权的合伦理性。
传统学术微旨阐发,多重事理发明而轻史实考据。江声微旨阐发则将二者有机结合,互为犄角。另外,传统学术“微旨”阐发大多根据“辞例之变”,而江声则能够根据字面义与文献记载的矛盾、异文材料以及词义色彩演变推阐微旨,大大拓宽了微旨推阐路径。当然,若从更宏观的视角考察,无论“辞例之变”、异文材料、词义色彩演变还是字面义与文献记载的矛盾,本质上皆属于“异”的范畴,都是通过不同证据之间的彼此矛盾出发探究微旨所在,这体现出江声对传统“微旨”阐发路径的继承。
三、微旨推阐之体式:自注自疏,注简疏详,纲举目张
自注自疏是《尚书集注音疏》体式方面的重要特色。传统的注疏体著作,注和疏一般不出于同一人之手,通常是后人为前人之注作疏。江声此书之所以采用自注自疏之体,并非因为其不屑于古注;相反,江声与吴派其他主要学者一样,都表现出强烈的嗜古之风。然而,《尚书》流传过程中,许多旧注散逸,仅存只言片语,语意未尽,有待补充;还有的古注释义犹未精善,需要另立新说,重新解释。可既然如此,江声为何一定要采用注疏之体,而不采用说经体或其他体式?一方面,江声之注,虽然部分系自注,但亦有不少采用汉儒旧注,故采用注疏体,以示尊古。而另一方面,注文与疏文其实代表了两种学术风格:注文通常简质,往往只有结论和少量关键论据,而鲜有论证。疏文则论据详实,论证环环相扣,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即使初学者读之,亦能信服。传统学术对“微旨”的阐发,近于注文,一般言简意赅,论据较少,而论证更简;而乾嘉考据学风,更近疏文,强调证据,追求论据、论证的完备性。例如,《皋陶谟》:“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江声自注“其”字曰:
其者,不决之词。知人安民,实非舜所难,而言“帝其难之”者,盖圣心冲虚,禹推舜心,当未敢以为易,若《论语》曰“尧舜其犹病诸”。
而自疏云:

此例江声于“自注”中仅仅表明结论,并未提供论据,更未展示推理、分析过程,从表面看近似凿空敷衍之论。但随后江声即在“自疏”中对“自注”所言逐句考证。他首先分析“其”的字面义,指出“其”是“不决之词”;随即又指出,根据《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舜去四凶,举十六族事(3)①《左传·文公十八年》称:“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以及《礼记·表记》载虞帝“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可知“知人”“安民”对舜而言并非难事,这一点毋庸置疑。既然如此,则《尚书·皋陶谟》“惟帝其难之”之语并非事实,难道《尚书》记载有误?在经学时代,《尚书》作为经学经典,权威性不容置疑。为了化解这一矛盾,江声提出,帝禹推求帝舜至心,认为帝舜内心长久保持冲虚欿然、不自满止的心理状态,因此才用“其”字,通过疑问、推测语气含蓄、委婉地进行表达。经过他的阐释,非但“知人安民”对于实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的重要性仍然可见;而且还深入阐释了言外之意,通过“其”字诠释帝舜和说话者帝禹的谦冲、至圣形象。
为进一步证实此说,江声于疏文中详考群经,指出《论语·雍也》《宪问》皆言“尧舜其犹病诸”,无论句式还是语意,均与《尚书·皋陶谟》此言相近。尤其是《宪问》篇,上下文语境亦与此经上下文相似。按:《尚书·皋陶谟》云:
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1]138
《论语·宪问》云: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2514
《皋陶谟》载皋陶向禹谏言,倘若果真推行德政,就能决策英明,群臣同心,具体方法,首先是“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意谓要保持自身谨慎的态度,坚持不懈提高自身修养,使九族之人敦厚顺从,贤明之士勉力辅佐。由近及远,要从这些开始做起。随后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知人”和“安民”,对此,禹表示,若要做到此二者,即使舜帝恐怕也难免感到为难。而《论语·宪问》篇,孔子递进式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三个修身的目标,其中“修己以敬”与《皋陶谟》“慎厥身,修思永”相仿;“修己以安人”与“惇叙九族,庶明励翼”相仿,“修己以安百姓”则与“在知人,在安民”相仿,而孔子“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之语亦与大禹“惟帝其难之”语意相仿。通过文献语例乃至文献语境的类比分析,江声证明“其”表示谦虚、委婉,并非孤证,从而增强了结论的可信性。江声在自注中仅呈现观点结论,而在疏文中则步步为营地对微旨加以考证、推阐,使“后学”认识到看似凿空之论的注文背后实有大量文献考据支撑。
又如《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江声注云:
有夏,谓禹也。有室,卿大夫之家。竞,强也。多贤人,故曰“大竞”。《诗》云:“无竞维人。”言古之人有道者,惟有夏之为天子矣。其巨室多贤,其君招呼其贤俊以谅天功,以尊事上帝。
疏云:
赵岐注《孟子·离娄》篇云:“巨室,大家也。谓贤卿大夫之家。人所则效者。”此“有室”,犹《孟子》所云“巨室”,故云“有室,卿大夫之家”。……“竞,强”,《释言》文。引《诗》者,《大疋·抑》及《周颂·烈文》皆有是言。毛公《烈文》传云:“竞,强。”郑君笺《大疋》云:“竞,强也。人君为政,无强于得贤人。”笺《周颂》云:“无强乎维得贤人也。”得贤人,则国家强矣。兹引之以证“大竞”为多贤人。[6]591
此条江声“自注”亦简质,仅提供结论、译文以及一条旁证,并未加以论证,具体、详细的论证则见“自疏”。按:“竞,强”之训见《尔雅·释言》。乃有室大竞,《尚书孔传》释“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径训“大竞”为“大强”;《尚书正义》则谓“乃有群臣卿大夫皆是贤人,室家大强”[1]230。不过孔疏没有解释“皆是贤人”与“室家大强”之间的关系,颇似增字解经。非但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卿大夫室家大强”一度是值得帝王、国君高度警惕的现象。东周时期,诸侯强大而王室衰微;三家分晋,亦是由于晋国内部卿大夫势力的日渐强大,正如《礼记·郊特牲》所谓:“天子微,诸侯僭;大夫强,诸侯胁。”[1]1448与之相应,“强”也派生出一系列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诸如“强狠”“强权”“强横”“强黠”等等。如此,则孔传、孔疏对“有室大竞”的解释,难免令“后学”疑窦丛生。
为了消除这种怀疑,江声对“竞”字的微旨加以推阐。他首先征引《尔雅·释言》及《诗经》毛传,表明“竞”的字面义确实当训为强;但其随后即引《孟子·离娄》赵注以及《诗经·抑》《烈文》郑笺,将“强”与“贤”联系起来。按:《孟子·离娄》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赵岐注《孟子》时,先释“巨室”为“大家”,而后进一步解释为“贤卿大夫之家”,特意补充、强调“贤”字。而孔疏进一步指出,卿大夫上可以辅弼天子,下可以垂示万民,因此是宣扬德教的重要枢纽。[1]2719江声通过征引《孟子》赵注以及《诗经》郑笺,表明华夏传统观念中,任用贤人治理国家是政治稳定、国家强盛的核心根本。卿大夫倘若能够贤明,则其强非但不至威胁君权,反而能够光大王政。尤其是《立政》此语乃是针对夏禹而言,而禹作为一代圣王,其卿大夫定能为贤而不僭越犯上。此条江声通过对“竞”字“微旨”的阐发,表明卿大夫之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意义,从而为“后学”破惑。由此亦可见,江声对“微旨”的诠释,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由传统观念造就并笼罩于经文文本之上的文化语境的解读。“后学”可能对于这种文化语境比较陌生,故易产生质疑;江声于疏文中对这种文化语境进行细致阐释,从而使读者了解到“大竞”与“多贤”之间的文化关联,从而在正确理解《尚书》经义的同时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由以上二例可知,江声借自注自疏之体,搭建起勾连传统学术与乾嘉考据学之间的桥梁,尤其是于自疏中采用乾嘉考据学研究方法,引领后学认识到传统学术“微旨”阐释中的合理性,进而对“微旨”研究产生认同。可为参照的是,江声平生极其推崇《说文解字》,著述、书札乃至账目、药方,皆用篆书,以致遭人非笑,但他全然不顾,我行我素,甚至对不识篆书者申斥詈骂。[8]112江声崇《说文》,严守至此,与其对古注简质风格的坚守如出一辙。只不过,面对不识微旨的后学,江声并未像对待不识篆书者那样申斥詈骂,而是不厌其烦地通过考证加以引导,因为他担心后学丧失对传统学术“微旨”阐释的认同。江声拳拳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四、术语和行文的“微旨”阐释:斟文酌字,尊贤尚德
《尚书集注音疏》中,江声对微旨的阐发,除体现在采用自注自疏体对《尚书》经、注微旨加以阐释,还体现在学术术语的推敲和行文的斟酌。这些“微旨”与《尚书》经文文本关联不大,但与《尚书》以及其他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则息息相关,更可见江声对微旨阐发之执着与自觉。如江声于“《尚书集注音疏音疏》卷一”标题下称“江声学”,并解释说:
非敢云籑述也,学焉而已,故曰学。仿何劭公注《公羊》偁何休学也。[6]348
按:陆德明《经典释文》谓:“学者,言为此经之学,即注述之意。”[1]2196陆德明的释义系表层义,在这层意义上,称“学”、称“注”区别不大,二者所指相同,都是指对经文的注解。但何休此处称“学”其实是谦辞,意在表明所注之观点内容实传承自师长,而不敢擅其功。《公羊传》徐彦疏引《博物志》云:“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学’。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谦辞受学于师,乃宣此义不出于己’。”[1]2195据此,则“学”系谦辞,何休借“学”字表明己之注说实出自其师。而反观江声,似亦有此意。其述《音疏》之著作缘起,谓:

又其于《尚书集注音疏》书前所附《募刊尚书小引》一文云:
可见惠栋的《尚书》辨伪研究直接促成了《尚书集注音疏》的写作,而江声因袭惠栋之说实不在少。可知江声称“学”而不称“注”或“撰述”,或系为凸显“尊师”之言外意。历史上,尊师重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价值观念,江声称“学”字,而其自身之敦厚学品亦跃然纸上。当然,本文无意于从事道德褒贬,但江声所谓“微旨”确与道德褒贬关系密切。
又如,江声于卷末《尚书集注音疏述》题下自疏云:
述即叙也。不名叙者,《正义》谓郑康成《书赞》避孔子百篇之叙名而曰赞,然则郑君且不敢偁叙,声安敢偁叙邪?故曰述。述者,述《尚书》兴废之由,并自述集注之大意。[6]684
称“述”称“叙”,所指亦无差别,但江声指出,之所以称“述”而不称“叙”,是因为孔子有百篇《书序》,郑康成为前代鸿儒,尚且为避之而将己之叙改称“赞”,而自己作为后儒,称“述”实蕴含“尊往圣前贤”的言外之意。
江声对郑玄十分推重,《尚书集注音疏》中,江声于注中引郑玄语皆称“郑康成”,不称“郑玄”;而引他儒则皆称名,如马融等。对此,江声解释说:
马融偁名者,于先圣之经书先儒名,正也。然则康成何以不名?《春秋》之谊,名不若字,康成学行兼优,圣人之流亚也。尊异之,故字之。若《春秋》书邾娄仪父是也。[6]348-349
江声明确指出自己称郑玄为郑康成是仿“《春秋》之谊”,之所以称郑康成,是因郑玄“学行兼优”,属“圣人之流亚”。江声还引《后汉书》郑玄、马融本传,指出马融在晚年屈服于权臣梁冀,“颇为正直所羞”;而郑玄虽曾师事马融,但在党锢之祸中遭禁锢时“隐修经业,杜门不出”,之后面对权臣何进的礼遇,又“不受朝服,以幅巾见,一宿逃去”。[6]347-348所以,江声对于马、郑之学行实有所褒贬,为了表达对郑玄的格外推崇,因而行文中称郑玄之字而不称其名(“尊异之,故字之”)。江声明言此举是仿“《春秋》书邾娄仪父”例。按:《春秋·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蔑。”此据《公羊传》本。《左传》及《谷梁传》本经文“邾娄仪父”作“邾仪父”。据《左传》,邾仪父即邾子克。而《公羊传》解云:“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1]2197-2198结合何休《公羊传》注,可知按照常例,称诸侯当称其爵,如称齐侯、秦伯、楚子之类。此处按例当称“邾子”或“邾娄子”,但《春秋》经文并未称其爵位,而是称其字,是为表示对邾国国君的褒扬。之所以褒扬邾君,是因为当时鲁惠公去世,庶出长子息(亦即鲁隐公)代行鲁国国政,意欲与邻国修好以安百姓,而邾国能够在对隐公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作出决策,最先响应鲁隐公盟约,故《春秋》褒扬其德。由此可知,江声称“郑康成”,不称“郑玄”,主要是基于对郑玄道德品行的褒举。
这样的例子在《尚书集注音疏》中还有很多。江声既在《尚书》诠释中注重对经文微旨的阐发,也在著述行文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微旨观念。他既是经典微旨的诠释者,也是经典微旨的忠实传承者和践行者。对于江声而言,宣扬“微旨”已然内化为生命自觉。
五、结论:江声“微旨”阐发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江声对“微旨”的阐发,揭示了经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完善了微旨历史命题的阐释系统,推动了清学中期向晚期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江声以前人对《春秋》微旨的阐发为基础,在四个方面拓展了“微旨”阐释的内涵和外延。
(一)完善“微旨”的判断标准
江声之前的学者一般多注意到“辞例之变”是判断“微旨”的标准。例如南宋学者章如愚谓:“圣人之文,苟异于常,则必有旨。常文者,史册之旧文也。异于常者,笔削之微旨也。”[9]180又如上文所引惠士奇云:“《春秋》事同而文异者,必有微旨在其中。”江声判断“微旨”的标准,则不拘“辞例之变”,而将字面义与文献记载的矛盾、异文材料以及词义色彩演变等也作为判断“微旨”存在的重要线索。
(二)拓展“微旨”的推阐畛域
《春秋》微旨多反映于《春秋》经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性文字,属于“史家之笔”。而《尚书》主言,因此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所论之微旨不仅仅见于叙述性文字,更多则见于《尚书》中所记载的人物话语。如上文所举《洛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以及《立政》“乃有室大竞”之语皆出自周公之语,属于典型的“圣人之言”。江声将“微旨”从“史家之笔”扩展到“圣人之言”,其中一以贯之的则是“微旨”的伦理价值属性,反映了江声对义理问题的深刻关切。在学术史研究中,乾嘉学术向来被认为以小学见长,而对义理学关注相对较少。而江声的“微旨”研究,说明乾嘉学派对义理问题仍然十分重视,只是乾嘉学派对义理的讨论多穿插于文献、文字考证之中,不同于宋儒对义理的直接阐发。
(三)确立“微旨”的诠释理念
江声能够充分利用汉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微旨进行考证,有别于西汉今文学派。西汉今文学派注重阐释微言大义,但往往不重视历史事实、典章制度的考证,且所言又多由经文肆意引申,难免支离破碎、凿空臆说之弊,“解有微恉,而证据不详,后学莫信”。江声担忧乾嘉后学专注考据,忽视传统“微旨”的诠释方式,通过小学考证的方法,为“微旨”提供文献、史实等实证支撑,同时运用汉学方法辅助“微旨”阐发,表明“微旨”研究对于考据学亦有相辅相成之效。其实,乾嘉学派对小学的孜孜以求,根本目的仍在于由训诂以通义理。微旨常寓于经文字词,遂成连接训诂与义理的纽带。与江声同为乾嘉《尚书》学研究大家的学者段玉裁,在其经文考证性著作《古文尚书撰异》中也颇涉“微旨”的研究。如其解《尧典》篇“厘降二女于妫汭”,谓“古文每字必有法,古凡言妻者必为其正妻,凡言女者不必为其正妻”,“凡言‘妻之’,一人而已。虽有娣姪之媵从,必统于所尊也。凡言‘女之’,则不分尊卑,故曰‘二女’”,并结合对《诗经》《礼记》《左传》等经典的详细考证,指出《尚书》经文书“女”字而不书“妻”,是因为当时情况特殊,嫁娶没有完礼。在此基础上,段玉裁批评《孔传》“女,妻也”之解,因为孔传“女,妻也”之训仅仅解释字面义,而未凸显经文微旨。[10]28-29值得注意的是,段玉裁曾长期居于苏州,与江声相友善,其《古文尚书撰异》中有若干处与江声商榷之处,可知其阅读过《尚书集注音疏音疏》,且江声于《尚书集注音疏》所载《募刊尚书小引》中指出段玉裁曾为其刻《尚书集注音疏》捐资[6]346,然则段玉裁对《尚书》微旨的探讨,或也受到江声启发。
(四)创新“微旨”的推阐体式
隋唐以降,经解多用注疏体式。《尚书集注音疏》采用注疏体,不仅以示尊古,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为使乾嘉“后学”能够对“微旨”产生认同。江声之注,虽然部分系自注,但多数仍是袭用汉儒旧注。注文通常简质,往往只有结论和少量关键论据,而鲜有论证。疏文则论据详实,论证环环相扣,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即使初学者读之,亦能信服。传统学术对“微旨”的阐发,近于注文,一般言简意赅,论据较少,而论证更简;而乾嘉考据学风,更近疏文,强调证据,追求论据、论证的完备性。江声或是借自注自疏之体间接表示,传统学术对“微旨”的阐发一般并非无稽,只是古时学风简质,或者有些证据在饱学经师眼中属于不言自明的常识,不必赘言。通过以疏解注,江声引领后学认识到传统学术“微旨”阐释中的合理性,进而对“微旨”研究产生认同。
江声对“微旨”的阐释,兼综汉学和宋学,强调经解的价值导向,实际上就是提倡通经致用,对嘉、道以后的清学学者均有较大影响,诸如,常州学派的庄述祖、刘逢禄,桐城派的吴汝纶,湖湘学派的魏源、王先谦、王闿运。刘德州曾评述常州学派治《书》:“常州诸子治《尚书》,以阐发‘微言大义’为主,通过议论《尚书》中史事、诸经互相发明、解说圣人笔法、旁参宋学,对《尚书》经文作全新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公羊学的影子,同时也受到宋学的影响。”[8]136-138常州今文学派以《春秋公羊传》“微言大义”为根基,而在具体治究过程中重视考证,对乾嘉考据学方法多有吸收。系统研究江声对“微旨”的阐释,是考察乾嘉吴、皖古文学派与常州今文学派以及晚清今文经学之间关系的枢纽,也是史学研究和清学研究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