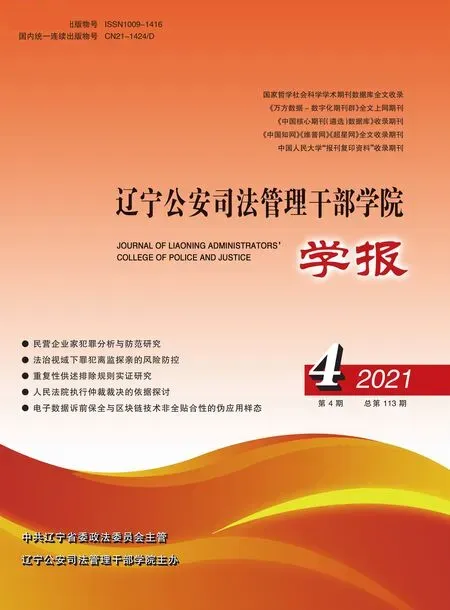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理论辨析与实践探索
2021-12-27张小荷
张小荷
(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检察院,辽宁 朝阳 122000)
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理论与实践辨析
检察建议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检察机关的传统工作手段,检察建议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五十年代。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同年底,最高检下发《关于各地人民检察院试行一般监督制度的情况和意见》,明确指出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纠正和防止违法的形式之一,并创设检察建议书、抗诉书等法律文书,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手段自此发端。
随着检察职能的调整和职权行使方式的创新,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检察建议的身影在诉讼活动中日渐活跃,被广泛应用于随案预防之中,并被纳入中央有关综合治理的文件以及高检院出台的各类工作规则、意见、办法、规定之中。201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正式写入检察建议制度,从立法层面确认了检察建议实践探索成果。通过法律法规体系的逐步完善,检察建议工作制度得以进一步明确。2019年2月26日,最高检印发了《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以下简称《工作规定》),将五类检察建议纳入一个总体框架,打开了认知检察建议的新视野,标志着检察建议体系化的确立。
(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性质及其法律制度保障的缺失
根据《工作规定》第5条所确定的分类,检察建议分为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检察建议、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以及其他检察建议。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在《工作规定》中作为一个独立的分类被首次提出,表明其实践价值得以重新定位。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主要是对检察工作中发现的社会管理问题、防控风险,行政惩戒、违法犯罪等现象,提出的加强治理、改进工作的建议。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的本质是一种法律监督方式,是基于检察机关的十大业务的开展而延伸出的法律监督职能。
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是非程序规范的法律监督方式。《工作规定》中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检察建议、公益诉讼检察建议都能启动法律监督后果的诉讼程序,分别由民事、刑事诉讼法及高检院民事、刑事诉讼规则所赋权,而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则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赋权。虽然《工作规定》第19条明确了被建议单位的回复义务,但仍没有改变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的预防性质和柔性特点,其监督职能的提起、监督刚性和监督程序、监督效果都缺乏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展示了“中国之治”的宏大愿景,增强了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为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作为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应当切实发挥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纠错、整改、预防和引领作用。
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初衷,就是为了通过履行检察职责过程中对个案和类案分析发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漏洞和不足,提出整改、完善的工作建议。一是通过制发个案检察建议,保障个体权利,矫正具体的违法行为,修复制度漏洞。二是通过对类案的分析,制发类案检察建议,透过个案问题从制度层面反思和修复漏洞,更加系统、更为深入地解决社会治理问题。三是提出立法建议。我国是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法律的制定遵循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按照这一路径,如果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提出的建议比较成熟,则可以通过各级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经过法定程序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这是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更高价值所在。
最高检《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出台后,L省各级检察机关紧贴“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协调发展形势,积极构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机制,制定细化工作规范,优化制发工作流程、创新送达方式,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取得新的发展和成效。
经统计,L省C市两级检察机关于2019年1月至2020年10月共制发社会管理检察建议138份,均为书面送达;收到回复136分,回复率为100%,采纳率98%。其中向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制发的检察建议29份,占总数的21%;向行政机关制发36份,占总数的26%,其他依次为:学校、企业以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等等、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在上述检察建议中,最多的两种情形分别是预防违法犯罪、改进监督管理,各自占总数的46%和51%;规范行政执法、司法行为类的占35%;化解矛盾纠纷类的占23%。针对多起在当地有重要有影响的案件制发检察建议,从助力社会治理角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统计数据显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在检察机关“四大诉讼”即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公益诉讼中都有分布,十大检察业务中都有制发,在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中发挥了愈加重要的作用,有效助力了创新社会治理工作。
1.助力公正规范执法
C市C地区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发现,C监狱未能严格落实“5+1+1”制度,周六周日加班劳动情况较为普遍,且劳动报酬发放低于规定标准;监狱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配备不足,存在医疗保障不力的问题,为此向监管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建议监狱强化医疗保障,严格落实假期休息制度,保障服刑人员合法权利。
2.助力营商环境建设
L省检察机关积极发挥检察建议作用,促进企业提升公司治理水平。S市Y区检察院通过对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批准逮捕的案件数据分析发现WP(沈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诈骗、盗窃案件较为集中,分析发现该公司在商品退换货、商品防损、物流流通等环节存在较为严重的监管漏洞,于2019年7月25日向WP东北运营中心公开送达检察建议。该公司收到检察建议后,通过自查以书面复函方式提出整改方案,杜绝类似案件再次发生。S市D区检察院在办理某商业贿赂案盗窃案后,向S市知名企业H公司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公司加强内部管理,规范公司员工行为,助力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3.助力违法犯罪预防
发挥检察建议预防作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C市L区查办的未成年人有偿陪侍及招用未成年服务人员的案件中,经查明,位于L区Z大街的Z歌厅存在未成年人有偿陪侍及非法拘禁情形,歌厅老板侯某等人组织歌厅服务生共10人以盈利为目的,招揽17名未成年少女进行营利性有偿陪侍,并且非法拘禁限制其人身自由,侵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C市L区检察院于2019年11月22日向C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在以后工作中加强对辖区内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保障娱乐场所的健康发展,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有效预防违法犯罪发生。
三、完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的路径
增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功效,达到“刚性”的标准和效果,提升服务和保障国家治理效能的水平,需要在立法层面进一步确认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权力来源及属性,在实践中重视检察建议质量、狠抓落实,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机制,更好地发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预防、规范、引领作用。
(一)从理论层面确立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
自上世纪50年代末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被废弃后,理论与实务界对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讳莫如深。学界通常将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等诉讼活动合法性的监督职能称之为诉讼监督,而一般监督则是指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是否遵守法律的监督职权。在实际运行中,一般监督权与诉权、法律监督权有着显著区别,体现在提起违宪或违法审查权、检察建议权、行政执法监督权等等。从依法治国方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看,检察机关更需要把一般监督权理论作为强化法律监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理论支撑,通过赋予检察机关有限的一般监督权,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为基本履职方式确立重构检察建议权。
(二)从立法层面确认其监督地位、保障其效力
检察权有着鲜明的法律依据、严格的权力边界。诉讼类、监督类检察建议所依托的是三大诉讼法,而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并没有法律赋权。立法欠缺导致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的法律位阶不高,执行力不足,权威性和法律效力难以得到保障。对此,应当通过专门立法,确立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的性质、地位,设置司法实践中被建议单位不予回应以及回复不整改的救济程序,保障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法律效果的强制性。
按照工作要求,检察建议达到刚性,一方面需要规范制发、送达、督促落实,提高检察建议质量;另一方面需要以立法形式给予其法律保障。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应当成为以立法形式授权于检察机关的一种国家权力,具备国家权力的一般特征,并明确其权力边界,保障其法律效力。
首先,从制发主体看,检察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次,从权力来源看,检察建议依据检察权而提出,具有权力要素;最后,应设置相应救济程序,保障检察建议的实施。为此,应当通过加强立法推动政府规章制度建设,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以立法确立检察建议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重新确立检察机关有限的一般监督权,可以从立法上通过三大诉讼法或设置单独的检察建议法来确认实际已经运行的检察建议权等一般监督权,进一步丰富、规范检察建议权的内涵和外延,保障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对宪法、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予以全面有效的监督,助力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
(三)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
检察建议工作机制不健全、不规范,必然影响检察建议工作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确保检察建议工作的制度保障,检察机关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1.更新工作理念
充分认识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权的重要方式、也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把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置于依法治国方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谋划推进。加强类案检察建议的制发,努力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社会效果;强化实践应用,聚焦扫黑除恶,公益诉讼、三大攻坚战,经济领域逃废银行债务等重点领域,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和类案,制发具有普遍和典型意义的高质量检察建议,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在深度应用中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监督的精准度,把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大局工作以检察建议的方式落到实处。
2.扩大检察建议制发案源
实践中,检察人员只能在司法办案中发现制发检察建议的线索,导致制发动力不足。对此,应当通过控告申诉、自行调查、社会反映等渠道广辟案源;取得显著社会效果的检察建议,由检察机关根据检察官法的相关规定对建议制发人员予以表彰。
3.加强检察机关间的沟通协调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在“四大检察”不同业务下制发检察建议的规律和特点进行深入调研总结,使“四大检察”十大业务、五类检察建议在各层级、各地区检察院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均衡发展,以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及社会效果。
4.强化合作共赢理念
与相关部门构建良性互动积极的工作关系,探索检察建议法权新领域、拓展理论新外延。善于应用法律智慧做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工作,提升检察建议的回复率、采纳率。
5.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从实践层面规范制发内容、程序,统一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制作的文本格式,规范检察建议送达模式;建立统一运行的检察建议管理平台,提高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的信息化规范化水平;加强对检察建议工作的领导,对于重大检察建议严格把关、保证质量、落实效果,由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或专职委员现场宣告送达,适合公开的检察建议要及时向社会公开,符合问责条件的要及时启动问责程序,促进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的接受和采纳,发挥检察建议在社会治理中的规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