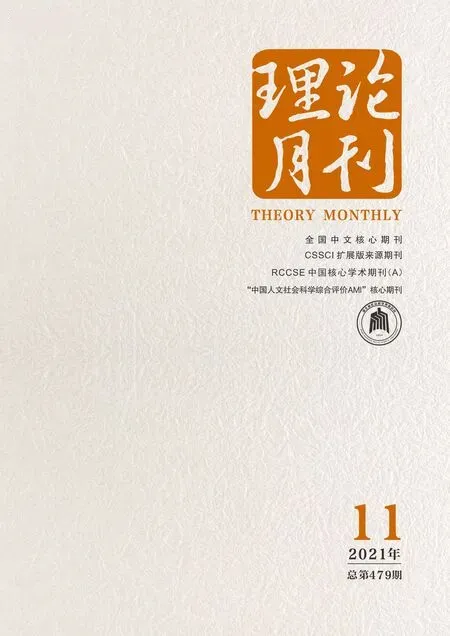诗意的社会学:欧文·戈夫曼的修辞
2021-12-27王晴锋
王晴锋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100083)
欧文·戈夫曼是二战后西方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在社会科学领域一直保持着极高的被引用率。戈夫曼毕生致力于研究寻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他的观察细致敏锐,语言充满讽喻,且一针见血。很多学者交口称赞戈夫曼对生活的敏感度、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犀利的思维洞察力以及丰富的学术想象力。与许多理论家不同,戈夫曼的著作读起来并不枯燥、晦涩,而是富有生活的质感,而且读者容易产生代入感。在资料来源方面,戈夫曼广泛利用不同类型的资料解释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譬如小说、自传、回忆录等,他自成一体的文风糅合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行为学家、小说家以及新闻记者的叙事风格。在其30余年的学术生涯里,从英格兰北部的设特兰岛研究到后期关于谈话形式的一般性分析,戈夫曼写得酣畅淋漓,毫无隔靴搔痒之感。
本文主要探讨戈夫曼的修辞,并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学的艺术形式。古典修辞学主要关注言说,它与注重抽象逻辑的论辩明显不同;而现代修辞学主要关注书写,包括叙述、阐释和分析等[1](p54)。戈夫曼使用的修辞方式包括反讽、混杂、隐喻等,这种修辞既增强了分析的说服力,也使戈夫曼的社会学富有诗意。本文所说的“诗学”采用保罗·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的定义,即主要用来剖析关于阅读或书写的惯例性做法,这些惯例构成了文本的肌理,它们不仅使文本变得真实可信,而且也促进了美学特征[2](p63)。社会学的诗学与小说、诗歌、戏剧等密切相关,同时亦对社会学理论提出了审美关照。广义而言,这种诗学的含义接近于符号学,它是一种用于比较符号系统以及从它们那里推演出来的知识类型的理论或方法;狭义而言,诗学特指有关语言艺术的符号学,它表明社会学亦是一门艺术[3](p8-9)。
一、戈夫曼社会学的特质
戈夫曼机智诙谐,充满幽默感,他的著作读起来令人会意一笑、心领神会。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学家,戈夫曼同时拥有小说家对事物独特的敏感性和观察能力。因此,他的社会学既有科学的陈述,亦不乏文学的描述。戈夫曼能够捕捉到日常生活中那些细微琐碎、被人视而不见或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互动细节,并通过概念提炼、术语创造等方式使之陌生化,进而重新审视其特殊性。大体而言,戈夫曼的社会学具有如下五个特质,这也是他在学术界内外拥有大量拥趸的原因。
第一,跨界的学者。戈夫曼绕开了很多人自我设置的专业陷阱,而是驾轻就熟,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路径。对很多学院派而言,戈夫曼是离经叛道者。他不拘泥于任何社会学理论传统,而是自如地跨越不同的学科界限,因而很难按照传统的流派进行归类。戈夫曼是人类学家,学生时代受过良好的人类学训练,其博士论文是在英国北部的设特兰岛上进行为期一年的标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他是研究人际互动和越轨的社会学家;他崇尚行为学家的研究方式,并通过谈话的框架分析介入语言学研究,同时他的研究不乏社会心理学色彩。由此,戈夫曼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固有藩篱,在社会学领域内外获得了广泛影响。
第二,源于日常生活的研究主题。戈夫曼研究的主题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他从选题到论证都源自每个人身边时刻发生着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戈夫曼探讨的是人们在生活中都会遭遇的经历,如面对面互动、社会污名以及精神疾病带来的困扰等。因此,每个人都带着好奇心阅读戈夫曼的著作,以期得到答案。尽管是探讨日常生活之平凡琐事,但戈夫曼却避免平淡无奇和陈词滥调。他对错综复杂的经验世界洞若观火,对生活世界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同时也不乏新意和洞见。戈夫曼关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洞见极易引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同时也能引导读者重新认识日常生活中的互动秩序是如何运作的。总之,戈夫曼厌恶空谈理论,重视经验研究,他善于提炼、抽象和概化经验材料,同时以概念为媒介重新整合经验生活。
第三,写作语言通俗易懂,笔调辛辣,且不失调侃。戈夫曼的著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没有高深玄奥的理论体系或晦涩难解的专业语言。他从学术层面探讨面对面互动系统,比人们在日常谈话中使用的语言稍具抽象性。戈夫曼对词汇具有很强的驾驭能力,极为善于创造新的概念,如“礼节性忽视”“自发性卷入”等,它们使读者兴致盎然。他在《污名》里也创造了大量新术语,如“身份挂钩”(identity pegs)、“传记性他人”(biographical others)等。在戈夫曼看来,社会学的假设应产生一些概念,它们“能够重新排列我们对社会活动的观点”[4](pxvi)。这套术语体系对于戈夫曼描述微观互动世界、勾勒互动秩序颇为重要,它使原本不可言说之物变得可以言说,甚至登堂入室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这是戈夫曼对社会学的学术贡献。戈夫曼通过重构或创造概念表明,社会生活并非完全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并促使人们关注原本被忽略的事物。在当代社会学与人类学著作里,戈夫曼的写作风格和语言特征较为少见,他采用的修辞包括反讽、双关、隐喻等,这种写作风格与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契合的。譬如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戈夫曼的措辞在冷酷中带着一丝嘲讽,很多时候他以超然的旁观者的立场进行论述,也只有这种“不涉入”才能保持超脱的姿态。
第四,广泛利用资料来源,尤其是各类二手材料。戈夫曼在报纸、杂志、小说、传记以及日常生活中充分地选择适合其论点的资料,而不是一味地恪守“科学的严谨”而放弃资料的丰足性。戈夫曼的写作资料相当广泛,除了学术性文本之外,他还偏爱使用一些在传统社会科学家看来是非正统的资料,尤其是小说、自传、新闻报道、礼仪手册,甚至学生的论文等。戈夫曼还对商业广告图片进行内容分析,开创了视觉社会学之先河。戈夫曼自称他采用的是一些“极具个人色彩的社会心理学材料”,倘若说这些资料显得微不足道,那是因为社会生活本身就如此琐碎。戈夫曼亦采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如参与式观察和定性资料分析等。如前所述,他的博士论文即是在对一个传统社区进行长期民族志观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也就是说,戈夫曼没有过于放纵他散文式叙述风格,他仍将自己视为科学共同体的一部分,只是以相对客观的姿态呈现自身。此外,“散论”“札记”等文体形式也使他在资料处理手法方面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无独有偶,人类学家格尔茨也偏爱采用“散论”的形式,它是用于展现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与技巧的重要工具[5](p30)。
第五,深切的人文关怀。戈夫曼的社会学生动展现了人类情感的微观世界,尤其是现代生活中个人遭遇的苦恼、惊惧与荒诞,并积极介入批判现代主义的非人性和非道德性。就此而言,戈夫曼可被称为“学术界的卡夫卡”。他同情精神病人、污名携带者、女性等弱势群体面临的困境,在这方面他的道德立场很明确。也就是说,戈夫曼的民族志描述是负载着情感的。除了这些特定的群体之外,戈夫曼对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进行了不偏不倚、不带感情色彩的观察。譬如在《收容所》里,戈夫曼大多数时候是以不掺杂个人情感的语言进行描述,读者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他竭力克制的情感和道德评判,这种冷静、客观的论述笔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正是通过以科学的语言对不同的机构特征进行非评判性的比较,戈夫曼最终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控机构”概念。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戈夫曼避免传统的价值判断,不是谴责或辩护,而是专注于客观的描述。这种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增加了社会批判的可信度和力度,《收容所》的读者都会对精神病院里非人性化的实践产生深刻的印象,但戈夫曼批判的不是任何具体个体,而是这种机构形式和制度设置本身。
瑞卡·埃德蒙森(Ricca Edmondson)曾指出,社会学的书写或阅读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彼此依赖的互动过程,它涉及读者既有的观念与行为,因而作者需要从某种可辨识的视角或框架来审视某个社会学主题。就戈夫曼而言,他具体是这样做的:先寻找某个话题,预料在该话题中至少能与某些读者达成共识;然后通过详细阐述该话题与更具争议性个案之间的相似性或类比,从而引导读者扩大这种共识[6](p149)。人们阅读戈夫曼的著作犹如阅读自身,而且他们一旦被改变观点,就会自动完成戈夫曼的“省略推理式解释”[6](p148)。也即读者自动调用相关的经验、认知与意识,完成戈夫曼设置的“完形填空”。这种文本阅读体验调动了读者的主体性,文本形成的阅读效应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协同完成的,并且因人而异。因此,对不同的读者而言,戈夫曼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放性和可读性。倘若读者认同戈夫曼的观点,那么他也会为自己在阅读过程中体验到的认知能力达到的新高度感到欣喜不已。总之,社会学的沟通不是根据方法论规则的一系列离散型交换活动,而是一种对话性的协商过程,作者与读者之间“交互影响与适应”[6](p150)。为了增加读者的参与感,还可在文本建构过程中采用各类符号、表征、类比、常规惯例及假设,而不是正式结构化的模型,这些都可谓社会学的修辞技术。这种阅读体验对读者是一种思维训练过程,它使读者对社会生活中细微的或习以为常的问题变得更加警觉,进而摧毁那些未经思索或不加批判的“道德沉浸”。
总之,戈夫曼对生活世界有着很强的领悟与洞察能力,对互动行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描述。戈夫曼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经验,他阐明了此前未被关注的社会行为,创造了一套新的术语体系描述和分析微妙的互动关系,从而使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事物变得“刮目相看”。就文风与修辞而言,戈夫曼的著作具有卡夫卡式散文风格[7](p292),同时亦具有齐美尔式文风。从整体上而言,戈夫曼“或许吸收了齐美尔、库利、涂尔干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等人的思想,但他通过在熟悉中寻找陌生,很大程度上开垦了一片新的领域”[8](p291)。戈夫曼犹如《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天真地道出了人世间的真相,“他的罪(与救赎)是敢于不断地、大声地说出那些令人烦恼的事实”[9](p21)。也正因如此,戈夫曼是“现代社会学领域中真正能激发灵感的少数思想家之一……戈夫曼之后的社会学从此不再一样”[10](p129)。
二、反讽与混杂式文风
自从1937年以来,帕森斯晦涩、沉闷的抽象著作似乎成为社会学写作的标杆,到了20世纪50年代,戈夫曼以独特的文风打破了这一潜规则,他的语言平实流畅、通俗易懂,没有矫揉造作、故弄玄虚,而是辅以大量生动的事例,尤其是没有如米尔斯所批判的帕森斯式宏大叙事。与同一时期其他社会学作品相比,戈夫曼的著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如《污名》一书的最后,它甚至没有被西方学者奉为圭臬的索引与参考文献。戈夫曼的文风具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反讽。反讽是从对立面看待事物,对于作为“道德科学”的社会学而言,反讽能够增进读者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更好地认识事物的存在及其属性[3](p172)。另一个特征是混杂,戈夫曼的混杂式文体主要受文学评论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影响,后者论述了修辞的社会性,赞同日常生活是戏剧的观念[11](p64)。戈夫曼与弗洛伊德的书写风格在“意合”(parataxis)层次极为相似,即通过重复、并置、对照以及基于这些方法的详细阐释来论证观点[2](p63)。这种文风也与方法论特质存在密切关联。戈夫曼采用移情式内省的观察法,因而他常被赞誉“富有洞见的、敏锐的观察者”“睿智诙谐的写作手法”“才华横溢、富有挑战性”等。
“对于不自觉地以自己及周遭的人所习用的终极语汇来描述重要事物的人而言,常识就是他们的标语。”[12](p106)而常识的反面就是反讽。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戈夫曼的重要批判性武器是反讽,他充满嘲讽的口吻是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强烈批评。戈夫曼与米尔斯、里斯曼等人处于同一个时代,《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几乎与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同时出版。戈夫曼著作中的隽语、并置、断裂式修辞以及他对社会污名、精神疾病、生理缺陷的持久关注等,这种风格被班尼特·伯格(Bennett Berger)称为“歌德式”或“卡夫卡式”[13](p35)。戈夫曼的反讽具有一种敏感化效应,不仅使人们关注社会生活中原先被忽略的角落,同时使他能够对日常现实中感知到的“自然序列”进行重新组合[6](p155)。反讽还是一种强有力的论证手段,并且带有道德评判意味。戈夫曼赋予涂尔干与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以社会心理学的色彩,从而将社会生活的多义与反讽置于核心位置[14](p458)。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戈夫曼称表演者是“道德贩卖者”;在《收容所》里,他运用诙谐作为文体,包括讥讽、反语和挖苦等形式[15](p90)。戈夫曼嘲讽精神病学犹如一门“修补生意”[16](p321),而精神病学家则是“修理匠”,笨拙不堪地“修补”病人的生活,试图纠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精神病人的亲属和社会控制的执行者才是精神病院的“真正的客户”。
戈夫曼的文风还具有混杂特征,尤其在阐释论证过程中大量使用文学素材,从而巧妙结合厚重的社会学论述与轻盈的文学描述。具体而言,这种独特的文风体现在将来自田野研究的经验资料与文学中的片段描述糅杂在一起。例如,《污名》的开篇是一封名为《绝望》的信,这封信的内容事实上来自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的著名小说《寂寞芳心小姐》(Miss Lonelyhearts)。在《行动之所在》一文里,戈夫曼大段引用海明威的小说《危险的夏天》中斗牛的场景。在《框架分析》《性别广告》中,戈夫曼也表现得如同一流的文学与艺术评论家[17](p110)。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夫曼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文学品质,但文学性的书写方式不仅仅表现为语言文字的修饰与润色。在文学社会学领域,波纳德提出“文学即社会表现”;朗松则将文学视为社会的补充物,“它表达在任何别的地方都难以实现的东西,如人们的遗憾之情、梦想、追求等”[18](p94)。除了文学素材之外,戈夫曼用以阐述经验活动的资料还包括剪报、漫画、小说、电影等。如在《框架分析》里,除了学术著作,戈夫曼亦采用各种体裁的资料,如舞台表演(如木偶表演)、艺术/影视/音乐/文学桥段(小说)及其批评、笑话/字谜等文字游戏、新闻报道、时事热点、流行歌曲、纸牌游戏、体育竞赛(如拳击比赛)、精神分析案例及论述、戏剧(情景剧)、情景对话、脱口秀、电台/电视节目以及各种真实或想象的现实情境设置(精神病院、赌场等),并采取大量脚注的形式对文中内容添注说明。戈夫曼一贯的论述模式兼顾剧场性的、文学的、虚拟的讨论和现实的生活,即充分结合“理想类型”与“真实类型”、微观互动与宏观结构。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序言里,戈夫曼交代了他使用的资料类型:“本研究中使用的阐述材料是混杂的:有些来自严谨的研究,关于可靠的记录下来的规律性作了有限制的概化;有些来自不同肤色的人们写下的非正式的回忆录;许多材料都处于这两者之间。此外,频繁使用的还有一项我自己对设特兰岛社区的研究。”[19](pxi)戈夫曼认为这些例证和阐释符合内在一致的框架,“这种框架将读者已经具有的经验片段组织起来,并且为研究者提供了在关于制度性社会生活的个案研究中值得检验的原则”[19](pxii)。戈夫曼还具有很强的类型化思维能力,他关注社会类型分析,这种分析方法聚焦于模式概化,因而可以从不同社会背景中寻找异质性的论据。戈夫曼采用的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资料搜集方式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非系统性或不严谨的研究方法[20](p139)。戈夫曼的作品:
以它自己独特的方式创造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形式。他无意试图在笔下重现社会现实。……戈夫曼的社会学类似虚构(fiction),但它是带有强烈文学色彩的视觉化虚构……他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是,除了类似小说的途径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书写它。[21](pxxxvii)
格尔茨也发现了戈夫曼书写形式的混杂风格,正是这种文本书写方式,使格尔茨察觉到当时社会科学的语言风格出现混杂趋势,他称之为“模糊的类型”,并认为这引导并体现了当时社会科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思想转型[22](p20)。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上,由于过于强调文本本身曾一度出现“表征危机”,对民族志写作中的表征危机的元反思表明“人类学关注的重心已从对它与异文化之间的关系,开始转向对我们文化中的表征传统和元表征的元传统的一般性关注”[23](p304)。而戈夫曼素来没有沉浸于文本分析,在他那里,经验并非理论的献祭或脚注,文本与现实均是活生生的社会存在。戈夫曼混杂、交互使用拟剧、博弈和仪式等隐喻,如关于“礼节性忽视”的论述既有拟剧隐喻又有仪式隐喻,关于面子功夫的论述则结合了仪式和博弈,而策略互动也包含拟剧和博弈。即使他对方法论的使用也是策略性的、混杂的,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强调其中某一种的重要性[24](p17)。譬如,戈夫曼研究互动仪式时混合采用三种启发式工具,它们分别是概念、修辞和分类[13](p12)。戈夫曼通过文本内的排序、定位从而给予想象以秩序性,表明社会学的世界无法与文本彻底割裂开来。
三、隐喻及其功能
作为社会观察者,戈夫曼具有独特的敏感性,哈维尔·特雷维尼奥(Javier Treviño)将这种对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的关注称为“戈夫曼式触觉”[13](p34)。戈夫曼采用的修辞手法包括隐喻、讽刺和否定等,其中隐喻不仅是社会学发现的手段与工具,它本身甚至成为象征性的实在。概念、活动和语言都是以隐喻的方式建构的。隐喻不仅是语言文字的特征(诗意的想象和修辞多样性的一种策略),也是思想和行为的特点(思想与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以隐喻为基础),其本质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25](p3)。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认为,隐喻是一种从已知过渡到未知的认知途径,它将两种互不相干的经验领域(尤其是陌生和复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阐释性的、图像般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意象的方法[26](p14)。维克多·特纳在《象征之林》(The Forest of Symbols)一书中亦认为,隐喻将熟知的和陌生的事物特点合并在一起,或将熟悉的特点进行异化的合并,从而有助于激发思想和产生全新的视角[27](p44-46)。
(一)戈夫曼社会学里的隐喻
隐喻具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作为一种阐释策略,使某个层次或参照框架的术语用于其他不同的层次或框架;作为建构模型的关键,此类隐喻又分为两种:类比与反讽;作为根隐喻,它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根本性的形象[3](p78)。戈夫曼主要采用拟剧、博弈、仪式和框架等隐喻,用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生活中的面对面互动现象,其中拟剧是戈夫曼社会学里最重要的隐喻。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将拟剧、游戏等称为“根隐喻”[3](p78),社会学的阐释图式正建立在这些根隐喻的基础之上。曼宁认为,拟剧、博弈与仪式等隐喻在戈夫曼的研究中呈螺旋式相互交织的状态,这正是戈夫曼方法论的特色:
在方法论上,这意味着以一种“螺旋性的”策略探讨各种不同隐喻和视角的优劣。在螺旋的某个折返点他接近于某个视角,(然而)到了下个折返点可能是其最严厉的批评者。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隐喻在社会学研究中所处的窘迫地位,但却不失为一种务实之道。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戈夫曼通常将拟剧隐喻当作通向另一种分析的有趣的踏脚石:中途的小憩处,而非终点。[24](p55)
戈夫曼的隐喻类似于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创新行为》(1967)中提出的“异类联想”(bisociation)。在他那里,隐喻是作为概念模型出现的,隐喻并非阐释的附属物、例证或工具,相反,它就是阐释和现实本身。戈夫曼式社会学以隐喻为内容的独特文本性或书写策略不能与它的研究方法孤立开来。戈夫曼采用三种方法探索面对面互动,即拓展的隐喻式描述、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和民族志(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24](p141),其中拓展式隐喻主要是将生活视为戏剧和博弈。如前所述,隐喻与其他研究方法或修辞策略之间不是分离的,有时可以结合使用。隐喻是戈夫曼用来阐释面对面微观互动系统的策略之一,他对隐喻、概念等思维工具持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后来的学术生涯里,戈夫曼逐渐用正式的定义和分类取代隐喻,这种转向明显地体现在《框架分析》里。
(二)隐喻的功能
戈夫曼描述的世界通常就是他自身栖居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隐喻的引入是为了减少复杂性,它能够在分离的现象之间产生认知的跳跃式连接。因此,隐喻既可以将那些不熟悉的事物和现象变得熟悉化和简单化,也可以将那些熟悉的事物陌生化。菲利普·曼宁(Philip Manning)认为,社会学研究中采用隐喻具有重要的功能,它能使社会世界陌生化,从而质疑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隐喻还能创造关于生活世界的“语义映射”,这种认知观念体系能不断衍生出新的关联性阐释[28](p78)。戈夫曼将各种隐喻运用于解释不同的社会现象,在它们之间形成联系,从而赋予它们某种观念秩序,使我们得以窥见互动秩序的结构、过程及其产物。
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提出关于隐喻的三个观点:首先,隐喻均有蕴涵,隐喻通过其蕴涵来凸显我们经验的某些方面并使之连贯;其次,特定的隐喻是凸显和准确连贯组织经验的这些方面的重要方法;最后,隐喻是自我应验的预言,它可以创造社会现实[25](p142)。他们认为隐喻是生活中创造新意义和新现实的机制,是对追求绝对真理的颠覆者,从而对前苏格拉底时代至今一直统治西方文化的客观主义神话提出挑战。在戈夫曼那里,隐喻为揭示社会生活和互动行为提供了新的洞见,它是一种参照工具,与被解释的现象之间存在显著不同,这表现在戈夫曼说的拟剧视角的“脚手架”功能。也即,剧场术语及其隐喻仅是一种智识上为搭建其他事物的权宜性手段。关于拟剧的隐喻本身并无新意,但戈夫曼通过它将分散、琐碎的常识条分缕析,并重组成一致的、逻辑性的分析框架,从而将对日常生活中熟悉事物的观察置于复杂的分类图式。戈夫曼通常将拟剧与博弈的隐喻结合在一起讨论,因此对互动秩序的分析也简化为信息管理与仪式,这种二元性贯穿于戈夫曼社会学,从他早期的博士论文《孤岛社区的沟通行为》中策略性和圆滑得体的行动之对比到后期《谈话形式》中系统制约和仪式制约的对比[10](p100)。在格雷戈里·史密斯(Gregory Smith)看来,戈夫曼关于信息控制与仪式之二元性的一贯立场使他得以调和互动行为中的理性和情感要素以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古典二律背反[10](p11)。
四、诗意的社会学:学科范式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3](p9)。若要化解这场危机,需引入一场新的范式革命。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修辞性转向”,其核心主张认为现实与真理是通过表征与阐释实践形成的[29](p188)。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也发现表述方面广泛存在的危机:
他们承认他们所称的“基本概念”,如社会结构或原始性,已经被侵蚀了。这种表述危机影响了大部分社会科学,通过将科学本身也看作是有待诠释的文本代码,向过去40年中具有影响力的实证主义思想体系发起挑战。[3](p288)
在这种背景下,旧的表述体系逐渐土崩瓦解,并且在民族志文本写作中激发了大量的人类学实验。社会科学新的发展方向是不断融合人类经验中的诗歌与想象力,将它们从“被驱逐的地方重新推导前台中央”[31](p77)。戈夫曼通过独特的书写方式向读者们转述和传达他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他的文本书写实践预示着社会科学领域即将来临的一种修辞转向。格尔茨敏锐地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知识界发生的微妙变化,社会科学家“从规则—实例的解释观已经转向个案—阐释,他们较少去寻找诸如地球(引力)与钟摆之间的联系之类的东西,而是更多地探寻菊与刀之间那样的联系。另一种现象是关于人性的类比在社会学的认知中开始扮演某种角色,而这种来自不同行业和技术的类比在物理学的认知中由来已久”[22](p19)。对于那些摒弃还原论立场的社会科学而言,这种类比更多地来自“文化表演的发明”,遵循着这种路径,“杠杆在物理学中的作用,在社会学中则由象棋给予承诺”。社会科学向人文学科寻求解释性的类比以及它取自人文学科的想象、方法、理论和风格等,正体现出作品体裁的多样化以及“阐释性转向”,“社会越来越少地呈现为一种复杂精妙的机器或拟有机体,而更多地表征为一场严肃的博弈、一种路边的戏剧,或者一种行为的文本”[22](p22-23)。相应地,社会科学的书写出现一种“混合体裁”。对此,格尔茨以生动形象的笔触如此写道:
哲学研究看起来像是文学批评,科学探讨像是纯文学片段,巴洛克式的幻想故事表现得像是不动声色的经验观察,历史的构成变成了各种等式、表格或法庭证词,纪实档案读起来像是真实的忏悔,寓言摆出民族志的姿态,理论性的论著叙述得如同游记,意识形态的论证犹如史料编纂,认知论研究弄得像是政治小册子,方法论的争论打扮得好似个人回忆录……我们只差等待诗歌中的量子理论或者代数中的传记。[22](p20)
在这种混合、模糊的书写体裁下,很难给作者贴上适合的标签或对作品进行归类。格尔茨强调,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另一种文化地图的重绘,而是一种“绘图原则的改变”,进而重塑社会思想的进程,它是以混合类型的叙述和阐释去适应与还原流动的、多元的、去中心化的、零乱的现实世界。格尔茨认为,将社会行为视为某种形式的游戏/博弈的思想主要源自维特根斯坦关于生活形式作为语言游戏的思想、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关于文化的游戏论观点以及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些不同的思想导致社会科学的阐释具有强烈秩序感的同时,又对这种秩序的任意性有着同等强烈的感受。在格尔茨看来,尽管戈夫曼也使用舞台语言,但这只是互动游戏的一种独特形式,因此他的所有作品基本上都是关于博弈的类比,而不是真正拟剧性的,在全控机构中不断上演的则是一场场争夺自我的“仪式博弈”。
除了游戏/博弈、拟剧和文本之外,社会科学领域中人文主义的类比方式还包括奥斯汀和塞尔(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如哈贝马斯的“沟通能力”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之类的话语分析,深受卡西尔(Cassirer)、朗格尔(Langer)、冈布里奇(Gombrich)和古德曼(Goodman)等人的认知美学影响的表征主义取向,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高等符码学(cryptology)等,它们对传统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核心假定构成了严重挑战,如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的严格分离,即“残酷的事实观”;试图创造一套正式的分析词汇以净化所有主体性的指涉,即“完美的语言观”;宣称价值中立和全知全能的观点,即“上帝的真相观”,当阐释被视为行动与其意义而不是行为与其确定因素之间的联系问题时,这些假定无一能够成立[22](p33-34)。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物理过程的类比转向符号形式的隐喻,这一转变引发了对社会科学的方法及其目的的根本性争论,传统社会科学普遍约定的目标是探寻集体生活的动力机制,并改变它们使之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如今,这一社会科学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这种潜在的范式转变在戈夫曼学术生涯的巅峰时期——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正处于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正因如此,才有如此多的学者对戈夫曼的方法论持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在如今看来(至少通过格尔茨的立场看来),戈夫曼是社会科学的这种范式转变过程的重要推动者。
五、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戈夫曼社会学的文类体裁与语言修辞,混杂与散论式文体使戈夫曼得以摆脱传统社会科学写作的束缚,自由地采用不同的修辞手法,从而大大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与齐美尔一样,戈夫曼也研究社会交往的形式,尤其是探讨自我呈现的非言语形式。戈夫曼的文风亦与齐美尔颇为相似,他对日常行为采取反讽和隐喻式描述,并认为不同类型的资料来源都可以用来阐明日常生活的经验结构。戈夫曼自视为经验研究者,采用学术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表述形式。在阐释面对面的社会互动时,戈夫曼还运用不同学科的观点,诸如博弈论、行为学以及身势学等。在当代实验民族志不再遵循实在论传统的背景下,戈夫曼的修辞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混杂的文类体裁和修辞风格也使戈夫曼的社会学充满含糊性,难以避免地遭受各种非议、误解和抨击。就本文的写作主旨而言,相关批评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相较于同类社会科学作品,戈夫曼的作品在语言上不够精确。对于像社会学这样一门强调实证的学科而言,隐喻缺乏实证性,这可能使社会学沦为文学[24](p16)。第二,戈夫曼的修辞特征之一是创造大量“本土性术语”用于分析社会现实。这些术语的优点在于能使分析者把握其内在的符号联系,但缺点是它产生一种“内向的文本”,导致非专业人士无法使用,或者“容易读,却难以领悟”[32](p180-181),在不经意间错过他的要旨。第三,希瑟·洛夫(Heather Love)认为,戈夫曼关于日常互动的仪式和身势的描述“充满细节,但不丰满或温润”[33](p387),他既忽略社会结构,亦无视个体心理学。在深度阐释学里,戈夫曼仅提供了“有关表象、运行与互动的描述”[33](p375),这种描述“接近但不深入”,即属于浅描范畴。类似地,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戈夫曼对互动的论述给人以一种平板化或同质性的感觉,他的分析性实例往往彼此雷同,这种分析路径是循环迂回地兜圈子,而不是层层递进,因而缺乏垂直的维度[34](p273)。在吉登斯看来,戈夫曼的著作缺少“累积性的特质”[34](p251)。究其原因之一,是他的许多著作由论文集构成,其散论式写作风格也容易让人产生这种印象。
戈夫曼社会学的修辞与文体相关,文体与特定的研究方法相关,而研究方法与他对共同在场式互动在社会学研究中所处地位的判断相关,即独特的修辞与文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戈夫曼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研究态度。斯坦福·莱曼(Stanford Lyman)曾认为,戈夫曼细致敏锐的观察和描述是无法概括的,它像诗一样无法完美地进行转译[35](p362)。而汤姆·伯恩斯(Tom Burns)认为,拟剧隐喻为戈夫曼提供了一整套现成的术语来分析个体与自我,但最好将它视为一种“启发式手法”,而不是概念框架或理论[36](p358)。对于安东尼·吉登斯、希瑟·洛夫等人的批评,菲利普·曼宁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戈夫曼的定义、分类、范例、例外、缺陷及重新定义等,这一系列过程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思维状态,他称之为“戈夫曼的螺旋”[37](p230)。这表明戈夫曼文本中的修辞具有层次性。